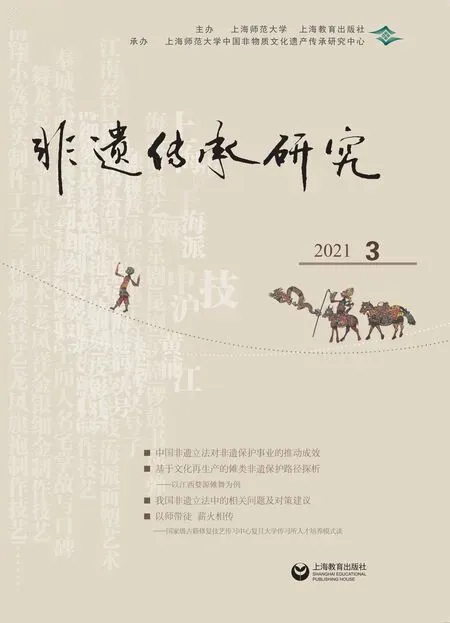神话非遗资源向城市文化品牌的创造性转化
——以武汉市大禹神话园为例
邓清源
神话传承至今,它除了带给人们对历史、对自然、对人类自身的思考,还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地自我调整。回顾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外出现了很多神话资源转化的探索。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塑造城市的文化品牌是城市保持地域文化,凸显自身特色的重要手段,而神话非遗资源是塑造城市文化品牌的重要来源。武汉市建立大禹神话园的目标是成为武汉的“城市文化符号”,但开园时几十万人参观的热潮过去之后,今天的大禹神话园已经渐渐不为人所知。
一、传承现状:活跃于研究,渐隐于生活
我国大禹神话的研究是伴随着神话研究的兴起而逐渐发展起来的。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思想影响,各阶层仁人志士不断引进外国文学作品。其中,“神话”这一概念被引入文学和历史两大领域,学者们借助“神话”这一途径来探索讨论民族、文学和历史的起源。大禹作为上古洪水神话的重要主人公之一,成为神话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在学术界研究逐渐深入的同时,大禹神话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承与传播却逐渐弱化,许多民众只知大禹其名而不知大禹神话本身。
1.大禹神话研究滥觞百年
中国古代文献中是没有“神话”这个名词的,梁启超在他于日本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历史与人种之关系》里,第一次使用了“神话”这个词。1922年,梁启超在《太古及三代载记》中提出,古籍记载中华民族的上古史上发生的大洪水有三次,分别是“女娲氏积芦灰以止淫水是也”“共工氏触不周山是也”“鲧禹所治也”,[1]这是大禹神话首次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从梁启超开始,后来学者也开始关注洪水神话及大禹神话研究。
当时,许多论著和学者都借鉴神话学的观点,从不同角度论及大禹神话,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顾颉刚在1923年提出他的古史构建“层累说”时,以大禹问题为案例对其做了通盘的研究。他认为大禹是由上帝派下来的“神”,而不是“人”,这一观点一扫将大禹看作夏朝的开国圣王的传统认识。1937年,顾颉刚和童书业合写《鲧禹的传说》,除对上述观点又作了更透彻的论证外,还提出禹的神职是“山川主神”,是“社神”,也是古籍中提到的“后土”和“句龙”等。[2]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中提出“禹当得是夏民族传说中的神人”的见解。[3]
大禹神话在神话学滥觞之初就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无论是史学、文学,抑或是人类学的研究,都能在大禹神话中找到自己需要的研究对象。一方面,当时的社会希望通过对上古神话的研究来探寻具有现代性的价值意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大禹神话本身内涵丰富、外延广阔。大禹神话的研究伴随着中国神话学的发轫不断发展,早期研究学者多关注于论证大禹是神还是人,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认为大禹是“神话历史化”的结果,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从其他学科视角来研究大禹神话。
冯承钧的《中国古代神话之研究》(1929)认为,中国的洪水和西方《圣经》中的洪水性质不一样,他以古籍中记载的大禹为例,证明中国的洪水神话包含了治水的意义。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采用历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以地下材料《秦公敦》和《齐侯钟》,参证先秦古籍,考证出大禹实有其人,大禹治水也实有其事。到目前为止,仍有学者在试图证实大禹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徐旭生在《洪水解》中通过梳理古籍弄清楚“大禹治水”的全过程、主要方法,其中也包括鲧治水失败的原因。程蔷的《鲧禹治水神话的产生和演变》讨论了鲧禹治水神话的本来面目,大胆提出鲧禹神话在被《山海经》记录的时候就已经被流传者改编了。
大禹神话的研究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神话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21世纪以来逐渐形成了全国各地研讨、海峡两岸互动的研究态势。对比学术研究领域百花齐放的热闹景象,大禹神话在民间的传承传播却呈现式微趋势。
2.民间口头传承不断弱化
大禹神话传说的保存大体上以三种方式为主。一是保存在文献典籍之中,例如《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禹杀相柳”,《墨子·兼爱中》记载“禹治水”,《太平广记》中《戎幕闲谈·李汤》记载“禹伏无支祁”,《集仙录·云华夫人》记载“瑶姬助禹”,《滇南杂志》记载“禹制铁柱”,《巫山县志》记载“禹斩龙”等。二是以实物的方式保存,例如河南洛阳的禹王池,池中所立巨石相传为大禹开凿龙门时所用的工具,岳麓山巅的禹王碑则记述了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三是保存在民间的口头上,即民众口口相传的大禹神话以及传说,活在民众的记忆里。
我国大禹神话的传承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变化过程。20世纪初期,学人受国外民间故事书籍影响,意识到民间文学材料的搜集整理尤其重要,大禹神话的搜集和记录逐渐起步。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民间文艺三大集成的搜集整理工作,这一普查性的工作较充分地挖掘和保存了大禹神话的全貌。现如今,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记载了大禹神话的故事集,还有许多以大禹神话为基础改编、创作的文学作品,以及以影像方式存在的纪录片、电影等。对大禹神话的传承而言,多样化的传播媒介扩大了大禹神话的传播范围,与此同时,科技的进步也使得神话、传说赖以流传发展的口承文化环境发生巨大变革。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也潜移默化地“剥夺”了口头传承的机会。
2016年“大禹治水传说”入选湖北省第五批省级非遗名录,2021年“禹的传说(大禹治水传说)”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扩展名录),但大禹传说的口头传承仍逐渐弱化。年逾古稀的程涛平是武汉大禹治水传说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以社区、居住地附近的中小学为阵地,主动讲解大禹治水传说;黄国华、张引娣等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则是立足工作单位,向全国各地来晴川阁访问大禹治水遗址、遗迹的游客宣传和介绍武汉地区大禹治水传说。然而相较于以往人们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当下这种宣讲、介绍的方式使得民众处于一个被动接受的地位,最终很难形成讲述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
在神话的接受过程中,神话内容的再造承载着后人对神话的理解与阐释,人们在保留大禹神话基本要素的基础上,结合武汉本地的地域文化特点,再造出诸多大禹治水传说,这是历史与民众共同创造的作品。但这些传说正在逐渐变成观赏的“标本”、历史的记忆,它们不再拥有活态存在的文化环境,亟需各方力量伸以援手。
二、转危为机:政府主导建成神话雕塑园
2004年武汉市计划在长江、汉水与京珠高速公路围成的包括老汉阳地区在内的扇形地带建设武汉新区,面积达368平方千米。而汉阳江滩的第一阶段工程就在晴川阁至长江大桥之间400米的滩地上进行。当时负责新区建设的副指挥长程涛平在把握建设汉阳江滩要有厚实的文化根基的原则上,确定了在汉阳江滩用雕塑形式表现大禹治水的历程,与晴川阁祭拜的大禹相呼应。当时设计建设大禹神话园是一举多得的:首先,大禹神话精神符合武汉城市的文化传统;其次,神话园雕塑满足了武汉城市和市民不同层面的多重文化需求;最后,神话园的建成为大禹神话的传承提供了新的机遇。
1.城市文化的传统
任何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其文化传统,都要在文化的历史积淀和传承转化中塑造城市性格。武汉处于九省通衢的地理中心位置和荆楚文化的核心区域,武汉的城市文化以荆楚文化为底色。武汉作为大禹治水的得胜之地,继承了大禹治水救民的遗志。几千年来,武汉因水而兴,也曾因水而衰,但面对洪灾的侵袭,面对民族的危亡,武汉人民从不退缩。在诸多古老民族的洪水神话中,洪水是不可抵御的大天灾,人民只能找各种各样的方法避祸。但是在华夏民族的大禹神话中,洪水却被大禹治得“地平天成”,武汉城市文化内核与大禹治水精神一样,是不屈不挠、不胜不休的。
在武汉的城市发展史上,一直回响着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声音,从“披荆斩棘,以启山林”到“盘龙建城,汉镇崛起”,从勇于革命、救亡图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重镇,都展现了武汉独特的城市性格。大量的历史典籍记载着大禹治水时期洪水泛滥、民不聊生,面对滔滔洪水、民无定所的情形,大禹站出来,成为敢为人先的治水英雄。治水过程漫长且艰辛,但大禹为天下百姓操劳,这种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品质与武汉的城市性格不谋而合。
在武汉地区的大禹传说中,大禹引导汉水与长江交汇于武汉,赋予了武汉得天独厚的水运交通条件。在治水过程中,他善于借助各方力量,借助圭对河流、土地进行全面考察,认真总结前人治水的经验教训,集众人之所长,达到治水退洪的目的。大禹精神早在夏商周时期就以其事功和品德成为思想家推崇的对象、执政者效法的对象和人民大众歌颂的对象。到了当代社会,大禹精神与武汉城市文化的特质呈现遥相呼应的态势,武汉人民对大禹治水神话的认同和接受是受普遍的文化传统取向的影响而形成的。
2.文化发展的需求
在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代生活中,人们的自我实现追求也不断多样化,由此产生的文化精神需求也不断增多。而对于一座城市的发展而言,独特的地域文化是加强民众凝聚力和加深认同感的重要基础。
一个城市的文化包括文化生产、文化消费和文化创新,对民众而言,最重要的是有可利用和享受的文化设施与文化资源,能够满足市民对文化、艺术参与的需求,通过市民的文化理念和精神认同,在日常行为中形成生活氛围,提升生活品质。大禹神话园建立之初,武汉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并且全市开始积极规划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这对于武汉城市文化的建设以及市民对文化滋养的需求都是持续利好的。新时代的武汉人民在文化消费上有着更高的追求,不仅需要更丰富多样的文化消费方式,还需要不断跟进的文化基础设施。文化基础设施是文化消费得以实现的载体和平台,大量的文化设施为城市繁荣创建了有利条件,也为市民文化消费提供了基础。大禹神话园坐落于龟山东麓长江江滩,与附近的晴川阁、龟山公园等旅游景点形成集文化旅游与健身休闲为一体的旅游片区,可以为市民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享受。
从武汉城市的兴起、发展历程来看,武汉曾数次成为时代的经济中心。抛开过去的辉煌、沉浮,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发展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浪潮涌来,文化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武汉大禹神话园作为武汉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能够与其他传统文化构成武汉城市的文化品格,建立全市普遍信守的文化理念,实现对区域文化精神的集体认同,促进对内凝聚力的形成、对外吸引力的提升。
3.神话传承的机遇
神话产生于远古时代,而传延至今,在不同阶段的社会生活中以不同的形态发挥着多样化的作用。尽管神话是遥远历史中的文物,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神话无处不在。在神话研究还停留在依赖古代文献记录或结合考古学资料时,神话资源已经在当下大众文化中得以创造性转化,如文学、电影、网络游戏、雕塑绘画、遗产旅游等领域,人们已经开始从古老的神话资源中找寻价值,重构意义。神话的回归源于人类对现代文明的反抗,但对大禹神话园而言,它的建立是大禹神话在当代新的传承机遇。
大禹神话园建立之初,恰逢“五一黄金周”,一周内有30余万游客入园参观。15年过去了,虽然大禹神话园游览热不复以前,但仍有许多游客慕名前往。某旅游点评网站上对大禹神话园的评价,几乎都是惊呼大禹神话园文化底蕴十足,大禹神话园在点评网站上的评分普遍达到四颗星及以上(满分五颗星)。由此可见,虽然大禹神话园如今不复刚开放时的热闹场景,但其背后的神话精神仍然能够打动前去游览的民众。借助网络媒介,更多的人通过游客的点评知道了大禹神话园的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大禹神话的传承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大禹神话园是由武汉市政府主导建设起来的,其设计理念、雕塑艺术至今仍极具教育价值。令人扼腕的是,当初建立大禹神话园的目的是成为武汉“城市文化符号”,如今却没有实现预期的文化影响力。面对新时代新的发展机遇,大禹神话园如何蜕变成为武汉的城市文化品牌,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三、发展路径:神话资源与城市文化整合创新
神话资源创造性转化的最基本准则就是挖掘并发扬最核心的文化内涵,并与当代文化相结合。只有挖掘出神话资源中“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内容,才能推动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民众提供精神指引,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对武汉市大禹神话园而言,只有形成具有影响力、号召力的文化品牌,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才能够使广大民众更多地了解与传承大禹神话,而不是任其消亡。
1.借助现代传媒技术,形成神话传承传播生态
武汉大禹神话资源作为一种长期依赖民众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形式,其在当代社会的现实遭遇与其他民间文学类似,面临着口头传承环境的消失和文化传播方式的更迭。虽然社会的发展是不可逆的,神话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这是神话本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但是民众可以通过被动引导和主动选择的方式,形成新时代的传承传播生态。
在现代传媒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生活方式和生活乐趣也随之改变。信息传递极其迅速的社会大环境,理论上来说更加有利于文化内容的传播。“文化生态指的是人类与文化的相互关联及其存在状态,包括人的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如同自然界中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一样,是密不可分的,也是相互依存和影响的,体现出一种生态性特点。”[4]当人们与这种文化发生交集、产生关联之后,自然会成为这种文化生态中的一员,进而形成新的文化生态。
从大禹神话园建立至今,在知乎、博客、微博、大众点评、抖音等各类网络平台上,许多网友纷纷分享大禹神话园的游览经历、摄影作品、视频作品以及感悟体验等,游客们的反馈积极主动,他们的分享在网络上发散式传播,产生了涟漪式的影响,促使更多的人走进大禹神话园去感受大禹神话的魅力。2020年8月25日是农历七月初七,武汉市水务局在大禹神话园内举办了武汉市第二届江滩七夕文化节。这次文旅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前往参与,并且设置了类似与“九尾狐说亲”雕塑合影领取小礼品等环节,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大禹神话多方面的了解。这种引导民众参与的活动产生了较强的传播效应,在未来若是能够继续优化活动内容,丰富活动体验,那么大禹神话园将会成为江城人民每年最浪漫的期待。利用传媒手段,在网络上形成“日日有推荐,年年有期待”的传播效果,将讨论大禹神话、参观大禹神话园、参与大禹七夕节形成常态化的文化活动,那么线上线下的互动分享会逐渐形成大禹神话传承的文化生态。
2.优化文化空间体验感,增强文化认同凝聚力
大禹神话园通过园区内步道的线路,串联起14组大禹神话雕塑,在短短400米的公园里构建出一个史诗般壮丽绚烂的神话世界,当空间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时,场所帮助唤醒故事,故事使场所产生意义。但是应当注意,并不是所有游客都拥有大禹神话的知识背景,那么在文字简介有限的情况下,提升游客的空间体验感,就能增强游客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就目前的群雕来说,游客大多处于一种景仰、旁观的状态,一旦不理解或看不明白,可能就会直接跳过,最终无法形成对大禹神话的全景式了解。为进一步优化参观者的空间体验感,一方面,雕塑可以在适当的位置留出空间给参观者,例如在“躲避洪水”这一雕塑里,人类、鸟兽纷纷逃到高山上避开洪水,虽然雕塑里各个人物都刻画得很生动,但若能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到雕塑中,成为“躲避洪水”的一员,也许就更能体会到大禹治水对天下百姓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可以采取一定的高科技手段,如VR、全息投影等方式,让雕塑中固定的人物“动”起来。多样化的互动方式能让参观者拥有更强烈的认同感和同理心。
与此同时,武汉大禹治水传说内容将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与山川大地相融合,呈现出极强的地域性特点。如功臣“龟”“蛇”二将最后化作武汉的龟山与蛇山;“禹青扔纱帽堵洪水”,纱帽化作武汉的纱帽山;“大禹贮粮米粮山”,其中用于囤粮的山被称为米粮山,沿用至今;“忽必烈正名禹功矶”,讲述元世祖忽必烈南巡时来到武昌蛇山,命令将长江对岸龟山突入江中的一块石矶复名为禹功矶,并命在矶上建禹庙,“以寄禹功之思”;“总督寻宝镇水怪”,讲述清代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寻宝时与被大禹镇在水底的水怪之间发生的斗争。但是群雕中没有足够地体现大禹神话与武汉之间的联系,并且媒体报道中也没有凸显大禹神话与城市武汉之间的联系。[5]对武汉市民而言,更能引起共鸣的是大禹与武汉这座城市之间发生的故事。
3.完善文博旅游产业链,形成文博旅游集聚效应
截至2020年底,武汉市拥有博物馆121家,其中文化和旅游部门直属博物馆30家,国有行业(高校)博物馆45家,非国有博物馆46家,比2015年末增加38家,每万人拥有博物馆数居全国城市前列。[6]武汉市的博物馆数量众多,截至2020年底,年均参观人数突破1000万人次,这些参观人群也会是文博旅游的重要参与者。文博与旅游融合发展,是一个以文博带动旅游发展、以旅游促进文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互惠共赢的过程,推动文博与旅游融合发展,对促进文博行业与旅游产业协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武汉大禹治水传说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它的传承与大禹文化博物馆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大禹文化博物馆日常的开放活动基本上只集中在博物馆内,并没有延伸到大禹神话园,即使大禹神话园与大禹文化博物馆有门廊连通,仅一墙之隔,大禹神话园也常常是游览中被忽略的。囿于园区和博物馆分属不同单位管理,目前达不到园区和博物馆的互动联通。与此同时,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与武汉有重要关系的龟山、蛇山景区旅游,同大禹神话园也是处于不相干的状态。大禹神话园的地理位置很容易成为汉阳江滩边旅游被忽略或被放弃的一环,但若是能够将大禹神话园与大禹博物馆乃至周边的长江大桥、龟山景区联动起来,形成“旅游+文博”“休闲+娱乐”一体的“大禹神话体验之旅”,那么这种具有文化底蕴,与休闲娱乐相结合的文博旅游方式,会带给人们更丰富的文化体验,对于形成武汉城市文化品牌将大有裨益。
四、结语
我们讨论神话非遗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实际上是在讨论神话非遗资源传承与发展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当我们把神话非遗资源视为城市文化品牌之源,就会找到神话非遗资源传承与发展的新路径。神话以新的形式走向民间,成为民众触手可及并且紧密联系生活的方式时,神话非遗资源的传承才能成为有效的传承。城市文化品牌最终要落实到实践中,承担城市文化发展的使命。因此,神话非遗资源向城市文化品牌的创造性转化,既要与市民社会相适应,又要注重文化精品的打造;既要注重文化环境的浸润影响,也要注重传承人的带动作用。在转化过程中,更不可忽视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