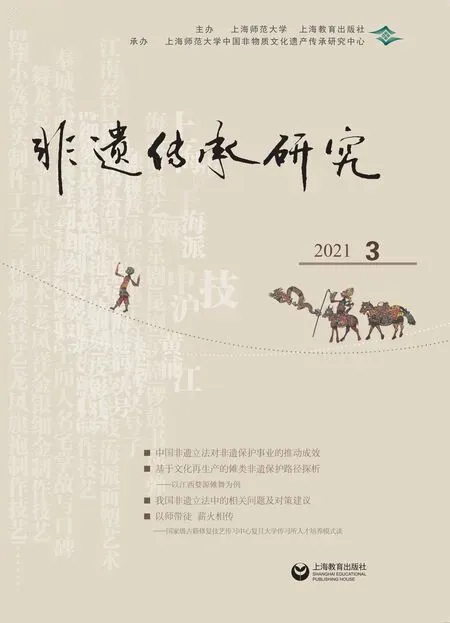作为民间戏曲传承方式的“村班”
——以鲁西南刁庄村花鼓戏村班为个案
王生晨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走向没落的趋势明显,且已产生了很多后果,具体到戏曲行业,很多地方戏剧目甚至剧种的消失就是其重要表现。虽然近年来在非遗保护的推动下,民间戏曲呈现出活跃的状态,但很多学者仍怀忧患意识,认为这只是一种表象,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其走向没落的现实。[1]在原因分析与建言献策方面,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指向同一点,即“挣不来钱”是最大的问题。将生存诉求置于文化需要之前的选择无可厚非,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保护和复兴传统戏曲是最正当也是最可能的路径。针对这一点,学界早有涉及,傅谨在其台州戏班的调查研究中指出,民间戏班最重要的特点是营业性、流动性和职业化,只有让民间戏班回归到自然生长的环境当中,还原其本身的商业属性,才能真正地让它生存下去。他甚至提出,政府越不干涉,越有利于它的自然发展。[2]更有学者认为,政府部门应该引导而不是主导,不能切断观众“喂养”戏曲的自然“生物链”,只有一方人养一方戏,民间戏曲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3]这是近年来除非遗保护理念外最为主流的观点。仔细思考会发现,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将戏曲展演当成一种经济行为来看待,略带“经济决定论”的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戏曲展演本身是一种文化行为,人们从戏曲中得到的是情感与精神的满足,真的不存在商业演出团体之外的戏曲演出组织吗?在戏曲演出市场不景气的今天,民间戏曲就必然走向消亡吗?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山东省郓城县刁庄村花鼓戏村班的一段历史,现将其呈现出来,以期为当下民间戏曲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个案。
一、窝班、混搭班与村班:民间戏曲班社的不同组织形式
在娱乐方式匮乏、生活节奏单一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戏曲展演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在丰富乡民精神生活,调节乡民生活节奏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民间戏班作为民间戏曲及艺人的存在方式,对研究戏曲在民间的生存与传承情况,了解乡民的娱乐方式与生活状态,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根据民间戏曲展演场域与艺人组织方式的不同,民间戏曲班社一般可以分为窝班、混搭班与村班。
窝班和混搭班是最常见的两种商业戏班组织,虽然在商业性的总体诉求指引下,它们都以商业演出为主要业务,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但具体而言,二者在人员构成、传习方式、内部关系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在人员构成上,窝班是指由师父和徒弟组成,一般以师父掌班领导、徒弟效力支持的形式构成,组织相对稳固,管理较为严格,演出风格和水平因为师出同门而大体统一。混搭班是指以非师徒关系的朋友、兄弟、夫妻等个人关系为纽带的组织,是跨村落甚至是跨区域的,人员构成时常调整,具有轻松活泼、灵活随机的特点。因为人员来自不同的地域或师承,演出风格和水平存在差异,不甚统一。
在传习方式上,窝班以师父带徒弟的方式进行,一边教一边学一边演,从小角色到大角色,从词少到词多,在学中演,在演中学,俗称“随班起”,是民间戏曲传习的主要方式。混搭班一般是由学成出师、可以独立搭班的成熟演员组成,不存在固定的传习关系,即便存在年轻演员向前辈艺人学艺的情况(称为“偷师”或者“跑腿”),也只有师徒之实,无师徒之名,演员们相对独立并相互尊重,和传统师徒制的组织关系有很大不同。总体来说,窝班是一种教学与演出并重的组织,而混搭班主要以演出为诉求,教学传习只是商业演出的副产品。
在内部关系上,窝班中的师徒关系更为亲近,更符合“师徒如父子”的传统说法,徒弟对师父甚至有生养死葬的责任。师父对徒弟更具责任心,态度也更严厉。另外,窝班的师父有给徒弟“撑腰”和“掐腿”的义务与权力。“撑腰”是指当徒弟遇到困难或者被同行欺负时,师父有出面保护或者帮忙平息事端的责任,这对师父有一定的道德约束性,如果师父管不了或者不想管,师徒的情分可能就此瓦解。相反,假如徒弟得罪师父,师父可以断绝师徒关系并让同行晓知,足以让徒弟难以在圈内生存甚至失业,这种情况被称为“掐腿”。不管是“撑腰”还是“掐腿”,都显示了窝班中师父对徒弟的强大影响力与把控力。而混搭班的演员之间更多是一种平等互惠的合作关系,约束力不强。
所谓“村班”,在笔者看来,起码有两个方面含义。“村”是指民间戏曲的传承、传播及展演都是以村落为依托;“班”是指具有展演目的和能力的戏曲演出组织,如果只传播知识而不演出,顶多算是一个教学组织,不在本文所谓“村班”的范畴之内。从这个角度上说,村班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很多以村落为依托的民间文化事象都具有这种性质,如张士闪关注的山东昌邑西小章村的“竹马”表演和朱振华关注的鲁中三德范村春节“扮玩”活动等,都在此列。其实,在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民间文艺多数是从村落内部兴起并留存的,是村民们在农闲或者节庆时进行自娱自乐的方式,它本身就是村民生活的一部分。[4]只是随着演出活动的进行和演出水平的提高,一些组织被超越村落范围的乡民认识和肯定,开始走出村落进行表演。只有当人们将文艺展演当作谋生手段时,商业性质的演出团体才开始出现,也正是这种在乡间不断流动的商业演出组织的出现,使民间文艺展演成为只有越来越专业的少数人才能掌握的技能。[5]平心而论,这种转变促进了民间文艺作为行业的存在,也有助于展演团队专业水平的提高,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民间文艺与民众生活的鱼水关系,整体上不利于民间文艺的长远发展。
和窝班、混搭班相比,村班不以商业演出为基本诉求,具有更为自主的公益性质。鲁西南刁庄村的花鼓戏村班有着固定的班底,它既不搭别人的班,也不让村外的人进入自己的班子。另外,刁庄的村班还具有明显的代际传承脉络,从第一代到第四代,每一代都有明确的代表人物、活动时段以及重要事件。黄旭涛将这种组织称为“窝儿班”,本文认为其缺乏窝班最重要的特征——固定的师徒关系,故虽然具有一定的窝班性质,依然不能称为窝班,而属于“村班”的范畴。[6]总之,刁庄花鼓戏村班以本村村民为构成主体,以村落为传承场域,从自发形成到被村落接纳成为“官方”组织,再到脱离村落走商业演出道路以致没落解散,其形成、发展及转变过程都以村落为依托,最终形成了村落传统与村落标志性文化。[7]
二、一村四代:刁庄村花鼓戏村班的历史进程
郓城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其西北部、北部和东部被黄河和大运河交叉环绕,南倚中原腹地,处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带,历史上人口稠密,交通便利,商业贸易较为发达。不同行政区划的交界有利于各种文化风潮的交流互通,加之受大运河的影响,使之接触外来思潮的机会增多。[8]郓城民间艺术历史悠久,人才济济,许多优秀艺术在此得到继承和发展,郓城花鼓戏则是花鼓传入山东郓城,与当地民间文化相结合的产物。[9]潘渡镇刁庄村位于郓城县城北10千米处,是一个普通的鲁西南乡村。刁庄村花鼓戏村班自1930年代由戏曲爱好者成立开始,到后来作为村落的宣传组织为村落所用,再到后来走向商业演出的尝试,最后在经济大潮来临之后消解于无形,完整呈现了以村落为基础的戏曲演出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迷到高潮再到没落的全过程。
1.村班草创期:花鼓戏爱好者的自发组织
刁庄村花鼓戏村班目前可以确定的第一代艺人以刁怀志和刁怀美为代表。刁怀志出生于1905年,因为酷爱戏曲而跟逃荒来村的流浪艺人学艺。据村内老艺人回忆,他脑子聪明,学东西快,经常是别人学“单边子戏”(只会唱某一个角色),他学全场戏。而且他后半生独自生活,给他学戏、唱戏、教戏创造了有利条件。刁怀志是教授学生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老艺人,后来几代花鼓戏艺人基本都是他教出来的,可以称得上是刁庄村班的奠基者和创始人。刁怀美的父亲是当时郓城县保安团长的结拜兄弟,在村落中长期掌握话语权,对待戏曲的态度保守且权威,正如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中描写的中国人对待戏曲的矛盾心理一样,他自己喜欢听戏,但又坚决反对儿子唱戏。[10]刁怀美在台上演出时,得知父亲要来,便带着头面和妆容直接从台上逃跑的事时有发生,成了村民们长时间茶余饭后的谈资。就在这种激烈的观念碰撞中,由戏曲爱好者自发组成的刁庄村花鼓戏村班逐渐建成并初具规模。
2.村班发展期:演出水平的提高与演出范围的拓展
刁庄村花鼓戏村班的第二代艺人出生于1915年左右,演出时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至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代表人物有刁怀广和刁秀海等人。刁怀广出生于1916年,攻旦角,最擅长的剧目是《秦雪梅吊孝》,在四里八乡颇具名气。刁秀海和刁怀广年龄相仿,曾经长期担任班主,尤其是“改弦”之后,他作为教戏师父和第一代艺人刁怀志一起培养了不少后辈艺人。以刁怀广和刁秀海为代表的第二代艺人们在第一代艺人的基础之上,不断拓宽演出范围,逐渐提高演出水平,为它被村落收纳而成为村落宣传与村际交流的“官方”组织做好了准备。
3.村班成熟期:作为宣传方式与村际交流的“官方”组织
进入集体化时期后,为了丰富集体生活,文艺活动成了受重视的话题,加上宣传工作的需要,很多村落成立了自己的宣传队,既有的花鼓戏村班便承担起刁庄村宣传队的职能。村落组织对宣传队的支持除了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物质保障外,还将学戏演戏当作“集体劳动”,可以得到和参加农业劳动一样的工分。排除掉多数人不爱唱、不能唱、不会唱等因素,刁庄村花鼓戏村班每一代大约有七八人,可以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演出组织。
集体化时期主要是第三代艺人从业后期和第四代艺人的从业期。第三代的代表有刁望存、刁秀奎、李明晨等,出生于1930年左右,主要演出时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十多年间。第四代艺人的代表有刁秀运、刁秀豪、刁望林、刁怀三等,出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演出时段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在集体化初期,刁庄村花鼓戏村班主要作为农闲节日期间村落公共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在村落内部表演,而随着演出的日渐成熟,周边村落慢慢知道了它的存在,于是刁庄花鼓戏村班开始走出村落,受邀去外村演出,作为乡里的一种互助行为,也作为村际交流的一种方式。[11]据老艺人刁秀豪回忆:“那时候都抢箱,来得晚了就抢不上了,有一年春节前戏箱就被一个村派人扛走了。”刁庄村花鼓戏村班在宣传上级思想、丰富村落生活、加强村际交流、促进村民集体意识与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和之前第一代、第二代老艺人的自发组织相比,集体化时期的第三代、第四代艺人演出得到了集体的认同,虽然没有为家庭带来收益,但是也从耽误干活的“玩儿”变成了可以挣工分的劳动,从业余爱好变成了群体认同的“事业”,代表国家权力的村委的参与和支持对村落艺术团体的传承和发展有决定性影响,也深刻影响了民众的思想观念。[12]加之戏曲演唱需要先天条件,一时间,唱戏成了“能人”的职业,这大大增强了艺人们的信心,也鼓励了他们的后续投入,使刁庄村花鼓戏村班迎来了发展的高潮期。
4.高潮与没落:商业大潮来临后的兴与衰
刁庄村花鼓戏村班发展的高潮期是从集体化时期后半段开始的,因为郓城花鼓戏的唱腔和戏词不符合特殊年代的要求,所以刁庄村花鼓戏村班的艺人全部改唱两根弦,即上文所称“改弦”。由于两根弦的演出场面比花鼓戏大,需要的人员比较多,所以这个时期的戏班班底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另外,两根弦演出需要有正式的装扮,音乐伴奏也更为复杂,所以刁庄村花鼓戏村班在这个时期加大了对戏箱的投入。据老艺人们回忆,当时一次性购买戏箱就花费了一千多元,这对40多年前的中国农村而言,近乎天文数字。既然投入这么多,艺人们的演出激情也空前高涨,准备干出一番事业,所以即便后来村里不给他们计算工分,艺人们还是坚持外出演出,在他们的努力下,刁庄村花鼓戏村班取得了很高的知名度,演出邀约逐渐增多。此时的村班兼具公私双重性质,一方面仍作为村落组织进行宣传演出,另一方面以个人身份外出演出,其性质与形式和今天民间戏班开展副业的商业经营方式十分相似。在这种情境下,村落组织不再提供相应的支持与补给。
随着集体化时期的结束,刁庄村花鼓戏村班的突然解散,这让笔者十分好奇,但是老艺人刁秀运的解释十分平淡:“分地①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的施行。之后,大家都开始忙着种自己的地,慢慢就解散了。”解散后,刁庄村花鼓戏村班再也没有重新组织起来,刁秀运老人除了偶尔去文化部门参加汇演之外,也不再参加其他演出,至今已经40多年。在回忆和讲述的过程中,可以体会到老人对青年岁月的怀念以及对花鼓戏的钟爱之情。几年前,在菏泽市文化馆同志的帮助下,刁秀运成为郓城花鼓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但对花鼓戏的传承事业,老人一直耿耿于怀:“咱自己的孩子都不学,怎么让别人学呢?现在挣不来钱就不行,当年我们就是为了挣口饭吃,现在光管饭谁还唱?挣得少了都不唱。我也只能自己撑着了,如果没有我了,花鼓戏也就完了。”
三、村班:民间戏曲的一种传承方式
通过对刁庄村花鼓戏村班历史进程的梳理,可以看出村班不同于窝班、混搭班的显著特性。
第一,村班的形成不是以商业演出为目的,而是由村落的业余爱好者自发组织起来的。在相当长时间内,作为自娱自乐的兴趣组织,它的传承、展演都在村落内部,与民众生活融合在一起,是民间戏曲最为传统的生存方式。
第二,村班的代际传承脉络清晰,每一代艺人的活动时段、代表人物、演唱风格、主要事迹等都十分明确,这对其他组织形式来说基本不可能,而在村落内部,确实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第三,戏班组织从以兴趣为导向的自发组织,到被村落收纳为“官方”组织而承担宣传任务,再到集体化时期之后商业演出的探索,直至最后消解于无形,刁庄村花鼓戏村班的发展过程之完整是其他戏班组织所不具有的。这个发展过程说明,民间戏曲演出组织是在艺人情感、国家政策法规、乡村生活环境和经济基础等多方面复合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维系的,它可以作为反观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视角,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启示。
第四,从整体上看,刁庄村花鼓戏村班的专业性相对较低。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刁庄村花鼓戏村班所能演出的剧目较少。据老艺人刁秀豪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村班可以熟练演出的剧目只有五六出,所以他们在同一个地方最多演出三四天(非特殊情况下,在同一个地方一般不能重复演出相同剧目,所以五六个剧目最多演三四天)。与他们同时期的一些能力较强的老艺人能记住100部左右的剧目,保存到今天的郓城花鼓戏剧目也有30多部。只能演五六个剧目,不管是对当年还是现在的戏班来说,都不能说是一个专业的演出团体。其次,演出范围较小,不与别的戏班合作。刁庄村花鼓戏村班多数是作为村落宣传与村际交流方式在周边村落进行演出,前文所讲第二代艺人对演出范围的拓展以及后来商业演出的探索是十分少见的,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走入演出市场接受磨炼和打造,演出的专业性略显欠缺。最后,刁庄村花鼓戏村班在集体化以后迅速解体,一方面说明他们难以适应新的演出市场,另一方面也说明班内人员对戏曲演出的兴趣和热情不高。
第五,刁庄村花鼓戏村班的演出活动几乎没有带来经济收入,即便是最高潮的演出时期,所得利益也仅够购买戏箱,并没有给艺人的家庭带来收益,“顾嘴”的思想与传统,或许是导致戏班在经济大潮来临之后迅速解体的直接因素。
作为一个专业性不高的民间戏曲演出组织,刁庄村花鼓戏村班的如上特性正是其能够在没有经济收益的情况下存活半个世纪之久的深层逻辑。它的传承与展演在熟人环境的村落中公开进行,村民入班也是自发行为,它的存在已经内化成民众生活的一部分,而非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动机,自发性与非商业性是其存活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是在经济大潮来临之后迅速解体的根本原因。今天,在戏曲演出市场持续低迷,商业演出团队也难以为继的局势下,一味强调以市场为导向的实践探索一直没有突破,民间戏曲的专业演出组织也在经济社会的整体环境下日渐式微,逐渐走向消亡。或许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从作为非商业组织的刁庄村花鼓戏村班中获得一些生存的启示。
四、结语
新时期的文化语境较40年前已经有了深刻变化,和20世纪80年代经济大潮刚刚来临时大家趋之若鹜的心态有所不同的是,经过40年的发展,人们开始对一味强调经济利益的论调进行反思。在文化领域,人们对消费文化存在审美疲劳的心理,对碎片式的快餐文化开始有所反省和戒备,借助非遗保护与乡村文化振兴的东风,很多村落开始思索并梳理自己的文化传统。
在强调传统文化和个性文化认同的语境下,以村落为依托的民间戏曲班社或许还有生存的契机,尝试营造民间戏曲生存的传统文化氛围,不再强调其作为谋生手段的商业导向,以村班作为组织方式,让民间戏曲贴近民众生活,回归村落传统,激活村落社会,结合新时期民众对民间文化的整体诉求,在村民观念转变、村落行政倡导和专业团体有益引导的多重作用下,激发民众自下而上的文化自觉,走出民间戏曲保护传承的一条新的可能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