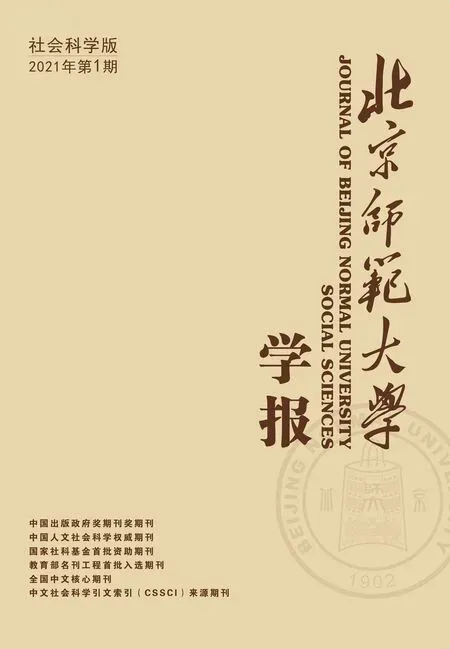五四时期“文白”论争中的中间派
王泽龙,周文杰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诗歌研究中心,武汉 430070)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在新文学阵营提倡白话,并提出用白话取代文言的时候,保守主义势力与新文学阵营展开了关于文言和白话的论争。但论争双方并不是全部持二元对立的观点。这一场论争中,部分认同新文学基本立场的成员,他们属于论争中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一类群体,本文把他们称为论争中的“中间派”。
五四时期文言与白话的论争是“五四”文学革命新旧思想交锋的聚焦点,是“五四”文学运动最重要的内容。提到这场论争,人们一般皆把文言和白话处于对立的位置,事实并非如此。以往的研究中较少涉及“文白”论争过程中有关中间派人物的基本立场与差异性观点。“文白”论争中的不同声音共同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变革潮流,为我们提供了深入认识“五四”文化变革与文学现代转型时期具有丰富性、复杂性的历史语境与思想资源。
一、渐进派的“文白”观
渐进派是“五四”文言白话论争中的中间派的一类,他们对待文言和白话的态度处于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他们是新文学的同路人,认同白话的价值,但认为专用白话而废除文言是不可取的,白话应该吸收文言的精华。他们对白话的态度经历了从怀疑到认可,再到主动尝试白话创作的逐渐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是在与胡适等人的讨论中以及他们自己的白话文实践中完成的。代表人物有朱经农、任叔永等,他们是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的好友,在胡适留美期间就已经开始参与了中国文学改革问题的讨论。
(一)渐进派态度转变的过程
渐进派的代表人物任叔永、朱经农等与胡适都是好友。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曾与他们进行过关于文学革新的讨论和争辩,这些交流可以说是《文学改良刍议》的酝酿过程,为胡适的文学革命观点奠定了重要基础。对任、朱等人来说,正是一次次的讨论让他们对白话的态度从最初的反对或轻视转变为后来的认同与接受。他们讨论、争辩的主要过程在胡适的日记里留下了明显的变化轨迹。
1917年6月,胡适即将回国之前写有白话诗送给在美国的好友们,其中一句是“前年任与梅,联盟成劲敌。与我论文学,经岁犹未歇。”(1)《胡适日记》,沈卫威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4、31、32、33、34-35、54、56、44页。可见,任叔永、梅觐庄与胡适的文学变革主张是持相反态度的。这一场论争要追溯到1915年。1915年9月胡适做了一首诗送给将去哈佛大学的梅觐庄,这首诗没有遵循律诗平仄和用韵的严格要求,在诗中还用了11个外国字,并且胡适第一次提出了“文学革命”这个词,他把这种诗当作是文学革新的一种尝试(2)《胡适日记》,沈卫威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4、31、32、33、34-35、54、56、44页。。任叔永把胡适诗中11个外国字连起来做成游戏诗一首送给他,诗的最后两句是“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胡适认为任叔永在挖苦他的“文学革命”的想法,在1915年9月19日的日记中记载道:“右叔永戏赠诗。知我乎?罪我乎?”(3)《胡适日记》,沈卫威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4、31、32、33、34-35、54、56、44页。
我们虽不能仅凭此判断当时的任叔永是反对文学革命的,但至少可以看出他对胡适主张白话诗是不以为然的。胡适用任叔永游戏诗的韵脚又做了一首诗答复,其中提到“要须作诗如作文”(4)《胡适日记》,沈卫威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4、31、32、33、34-35、54、56、44页。。
“作诗如作文”这一越轨性的大胆主张引起了激烈的争辩。梅觐庄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诗和文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诗界革命要从诗歌自身入手,仅仅把“文字之文”移用诗歌之中是不行的。任叔永对梅觐庄的主张也表示赞成。他认为“无论诗文,皆当有质”,“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5)《胡适日记》,沈卫威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4、31、32、33、34-35、54、56、44页。。胡适此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以白话入诗,但是“作诗如作文”这个观念本身至少已经蕴含了要以俗字俗语作诗,而且包含了要突破传统韵文格律的界限,主张诗文合一的倾向。而此时任叔永认为诗歌的好坏并不在于文字的形式,他对于“不避文的文字”入诗是持反对态度的。
胡适决心作白话诗是在1916年7月,起于任叔永所作《泛湖》一诗。他在日记中记载:任叔永与梅觐庄、陈衡哲等人在一起划船游湖时,快上岸时船翻了,又恰遇大雨,打湿了衣裳,任叔永作了一首《泛湖即事》诗寄给胡适,而胡适对该诗提出了部分意见,任叔永和胡适就该诗进行了几番讨论。梅觐庄看到胡适的反馈后也加入了讨论,并对其中文字的死活观、以俗语白话入文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文学革命不是简单用俗语白话即可,在他看来,文学不应该通俗化,即使是借用白话的内容也需要经过美术家的“锻炼”(6)《胡适日记》,沈卫威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4、31、32、33、34-35、54、56、44页。。而胡适认为不应该等美术家把白话锻炼好之后再用,而应主动用白话实践,便做了一首白话长诗《答梅觐庄》,其中也有少年人的游戏之意,然而这首诗又挑起了一场与梅、任二人的论争。任叔永认为胡适此次作的白话诗是完全失败的,虽然是用白话所写,但并不能被称为诗,在他看来诗歌不仅要用韵,更要讲究音调之和谐,“审美之辞句”(7)《胡适日记》,沈卫威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4、31、32、33、34-35、54、56、44页。。他赞同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的观点,但认为文学改革的重点不在于用文言和白话的区别。他承认白话有白话的用处,可以用白话写小说,写演讲稿,但白话不能用来作诗。如果白话都可用来作诗,那“京腔高调”全都是诗了。
虽然任叔永依旧不赞同用白话写诗,但是他已经认同了白话的价值,开始尝试使用白话文。胡适曾在日记中写道,1916年6月在绮色佳的时候与任叔永、杨杏佛、唐钺三人谈论文学改良的方法,其中一条提到文言适用范围没有白话广,在演说、讲学等方面无法使用,而白话是集读、听、歌、讲于一体的言语。这一番讨论也收到了反馈,任叔永表明自己“将以白话作科学社会年会演说稿”(8)《胡适日记》,沈卫威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4、31、32、33、34-35、54、56、44页。。胡适把任叔永称作留学界的第一古文家,而现在第一古文家也开始尝试使用白话,他对任叔永的这种尝试感到非常惊喜,肯定了任叔永对白话态度的转变。
随着与胡适的不断交流,同时看到了越来越多关于文学革新的讨论以及白话诗实践的成绩,任叔永对白话诗的态度也逐渐有了改变。他在1918年已经承认了白话也可以作好诗。任叔永1918年致信给胡适表明他反对胡适所主张“文言只能做死文字”这一观点时,举出了许多优秀的律诗,证明文言可以作好诗。他因此得出了结论“可见用白话可做好诗,文话又何尝不可做好诗呢?”(9)任鸿隽:《致胡适》,《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尽管任叔永在这里是客观分析文言的优势,但可以看出,他已经认可了以白话入诗、白话可作好诗的观点。
朱经农和任叔永一样,对待白话的态度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尤其是他对白话诗的看法。胡适曾在日记中记载过朱经农给他写信的部分内容。朱经农给胡适的来信中说到:“弟意白话诗无甚可取”(10)《胡适日记》,第65、65、45、68页。,明确表明了白话诗没有什么值得认可的地方。他认为胡适所作的《孔丘诗》是古雅之作,并不是白话诗,古诗本就不事雕琢,甚至说读完朋友所作“不为功名不要钱”之句觉得十分好笑(11)《胡适日记》,第65、65、45、68页。。到1918年的时候,他已经不反对用白话作诗,并且也认可胡适所作的白话诗:“总之足下的‘白话诗’是很好的,念起来有音,有韵,也有神味,也有新意思,我决不敢妄加反对。”(12)朱经农:《致胡适》,《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渐进派的同人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深受传统文化的习染,对文言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认同,但是他们又接受了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洗礼,因此能以一种更加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对待白话文。在经历了白话文与文言文论争,看到了白话文创造实绩与社会影响之后,渐进派逐渐接纳了白话文。
(二)渐进派对文言和白话关系的认识
渐进派认同文学革命的立场与方向,但是对于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主张并不完全赞同,主要是不认同完全废除文言的观点。
朱经农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现在讲文字革命的可以分为四种,其中“第一种是‘改良文言’,并不‘废止文言’;第二种‘废止文言’,而改良白话”,他把这两种归于“文言存废问题”(13)朱经农:《致胡适》,《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他认为不管是专用文言而排斥白话,还是专用白话而废除文言都是不可取的。对文言和白话应该采取“兼收而不偏废”的态度。他反对文言是“死文字”,白话是“活文字”这一观点,并以《红楼梦》、《水浒》、《春秋传》、《史记》等中国文学史实绩说明了文言也有千古流传的经典,不应全部抹杀。他还以《新青年》为例,指明其中所载陈独秀、钱玄同的大作也是文言和白话夹杂使用,并非完全放弃文言。因此,在文学实践中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用文言还是白话。他不反对用白话作文,但是,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吸收文言的精华,摒弃白话的糟粕,建设“文学的国语”。
任叔永在1918年给胡适的信中表明了对文学革命的支持,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支持白话文,但也和朱经农一样举出了文学史上很多优秀的文言文学作品,以此为例来反对胡适的文字死活观。他反对废除文言,认为文学改良的根本不在于文言或白话,“并非与白话作仇敌,也非与文言作忠臣”(14)任鸿隽:《致胡适》,《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他认为白话与文言都只是工具而已,改良中国文学只要用驾驭文字的能力,“白话不白话,倒是不关紧要的”(15)任鸿隽:《致胡适》,《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创造新文学作品以实现改良文字的目的,这与胡适“文学的国语”观点不谋而合。此外,他认为应当把翻译西方文学作为第一步,以此作为新文学创作的积累。
任叔永、朱经农都曾留学美国,当时与他们一起留学的还有胡适、梅光迪、杨杏佛等人,他们1916年前后关于白话文、白话诗的讨论,对胡适后来提倡白话,进行白话诗创作有重要影响。与任、朱二人一样,杨杏佛也是白话的支持者,并且主动进行白话诗创作。1916年杨杏佛曾寄给胡适一首他为《科学》杂志向赵元任催稿所作的白话诗《寄胡明复》(16)《胡适日记》,第65、65、45、68页。。此后他也作了白话诗送任叔永,虽然被胡适调侃:“老杨寄一诗,自称‘白话诗’/请问朱与杨,什么叫白话?/货色不地道,招牌莫乱挂。”(17)《胡适日记》,第65、65、45、68页。但是可以看出在胡适的影响下,杨杏佛成为白话文的积极实践者。杨杏佛并不支持用政府的势力强行推行用白话代替文言,他认为提倡白话自然可以,但“言论思想,尚不可箝制,不可统一,何况言论思想的工具”(18)陈保平:《新民春秋·新民报·新民晚报八十年》,上海: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他认为古文和旧诗保存到现在自有其存在的理由。
渐进派在文言和白话的关系辩论中,赞同提倡白话文是文学革新的重要手段,肯定白话的价值;既承认文言文有日益僵化等缺点,也肯定文言的价值,在实践中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语言和文体方式。
(三)渐进派的“文白”诗歌观
白话入诗是白话文运动最重要的使命,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古代文学中,文言占据统治地位,而诗歌又是中国文学的主流。诗歌被认为是雅言的文学,俗语白话不被认作文学正宗,这也是白话入诗引起诸多争议的重要原因。胡适说过:“我的以白话文为活文学这一理论,便是已经在小说、故事、元曲、民歌等领域里,得到实际证明的假设。剩下的只是我的诗界朋友们所设想的韵文了。这剩下的一部分,也正是我那时建议要用一段实际实验来加以证明或反证的。”(19)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8页。的确,与白话作文相比,人们对以白话作诗普遍持怀疑态度。渐进派也是经历了从怀疑到逐渐接受的过程,并且对白话诗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朱经农在1918年给胡适的信中表明了他对胡适白话诗的认可,认为胡适的白话诗兼具音韵和神味,而且有新意思,“我绝不敢妄加反对”,但是他也强调诗与文的区别,认为写白话诗应该“立几条规则”(20)朱经农:《致胡适》,《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他看到当时很多人所作的白话诗难以入眼,认为白话诗创作要遵循规律,他所说的规律也就是韵律、平仄、对仗等要求。可以看出,朱经农对白话诗创作现状并不满意,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否定白话诗的价值。
任鸿隽也认为白话可以作好诗,但他也指明文言同样可以作好诗,作好诗的关键在于是否有“诗心”,并不在于所用的文体。他认为即使不谈胡适所举的杜甫的《兵车行》、《石壕吏》,以及陶渊明、白居易的诗是否全是白话诗,就算把这些算作白话诗,那我们也不能否认杜甫还有像《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很多律诗,这些诗也是好诗。可见,文言也可作好诗。
其次,在诗体问题上,任叔永认为应该借鉴旧体旧调。作新诗,不仅要注意诗意,也要注意诗调,同时兼顾二者难免会顾此失彼,因此任叔永说不如直接用旧体旧调,“便可把全副精神用在诗意一方面,岂不如创造一方面更有希望呢?”(21)朱经农:《致胡适》,《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他把中国古代诗歌诗体的变迁作为建议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古诗从《诗经》的四言诗到汉魏的五言诗再到唐人的七言,这种变迁大概是因为人们说话从简短急促到迟缓的发展。从七言发展到宋元的词曲,长短句夹杂,解决了诗句过长或过短的问题。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诗歌的音调平仄也越发讲究,需要遵循的规律也越多,这在他看来是可厌的,但是也是作白话诗的人必须遵循的。因为现在流传下来的诗体正是“自然”的代表,是几千年来无数人的实践总结出来的,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因此,任叔永认为用经过实践检验的旧体旧调,然后全神贯注地研究诗意才是创作新诗最好的途径。
胡适对他们的看法进行了一一反驳。胡适分析,他们认为目前大部分白话诗写的不好,是因为他们看的不够多,看的不习惯,以旧观点看新诗,如果多读些白话诗自然能发现其中妙处。胡适也提出白话诗应遵循“诗体的解放”特点,但是目前处于尝试的阶段,不应遵守任何既定规则。任叔永提出用旧调以便把精神全用来作新诗意,胡适指出,应不拘泥于诗调,有什么用什么更方便(胡适始终回避了任叔永提出的文言也有好诗这一点)(22)胡适:《答任叔永》,《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胡适始终坚持白话入诗的立场与方向,与渐进派论争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四)渐进派与保守派的异同
保守派在这里主要是指国粹派、学衡派和甲寅派,他们在文言和白话的论争中始终坚定地维护文言。在这里之所以把渐进派和保守派进行比较,是因为在对待文言的态度上他们有共同之处。尽管目的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反对废除文言,承认文言的价值和意义。此外,即使是保守派,他们也不是绝对地否定白话,认为白话一文不值。学衡派代表人物梅光迪、易骏等人都有过肯定白话文价值的言论,甲寅派章士钊也曾说过“白话文在相当范围以内,自有其存在价值。”(23)章士钊:《答适之》,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第2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219页。
渐进派与保守派最大的区别,首先就在于他们的立场及总体态度不同。渐进派总体上是站在白话一边,认为文学改良要靠白话来完成,但是在白话的建设过程中应该积极吸收文言的精华。但是保守派的立场是坚定地维护文言的正统地位。虽然他们也认为中国文学应该改良,但他们主张文言本位,主张改良文言,祛除文言中僵化的部分,吸收白话中有意义、有价值的部分,尤其是白话实用的部分,使文言能够更容易被理解,增强文言的生命力,使之顺应时代发展需要。梅光迪在美国时就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四大纲领,其主要原则便是对文言进行改良,使其能够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前两点“摈去通用陈言腐语”、“复用古字以增加字数”(24)《胡适日记》,第69页。,都显示了他的文言立场。虽然他也提到了白话的价值,即第四点“选择白话中之有来源有意义有美术之价值者之一部分加入文学”(25)《胡适日记》,第69页。,但他明确表明第二点最重要,第四点效果最轻。一直到梅光迪回国后,和吴宓、胡先骕等人创立了学衡派,与当时有广泛影响力的白话派胡适等人抗衡,他的保守主义思想始终没有改变。
其次,从阵营来看,保守派因有共同的理论主张,形成了鲜明的文学派别。学衡派和甲寅派都创办了自己的期刊《学衡》和《甲寅》,而且都有领军人物,如梅光迪、吴宓、易峻、章士钊等,他们在各自的杂志上发表了理论主张和文学作品。而渐进派并不能算一个文学流派,不是因为有共同的宗旨特地聚集在一起。他们多是胡适的朋友,在交流过程中对白话和文言表达出相似的观点。他们的观点主要在胡适的日记和《新青年》上有所收录与刊载。
再次,在“五四”前后文言文和白话文论争的过程中,渐进派是白话本位,认可胡适文学改良的观点,只是对其中部分主张不赞同,所以他们更多的是直接和胡适讨论,态度也较温和。保守派因为坚定的文言文立场,所以他们的论争对象是白话文倡导者,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他们的态度也更显激进与偏颇。
二、改良派的“文白”观
改良派在“文白”论争中认同用白话取代文言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们也主张客观对待文言,认为只要精神上是白话的,吸收文言的优点为白话所用是建设白话的重要途径。改良派代表人物有朱我农、常乃惪、吴康、杨喆等人。他们是一群关心民族危亡以及文学发展的进步知识分子,当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之后,他们深受影响,深刻认识到文学改良的必要性,并与新文学主将积极讨论文学革命的方法,但是在具体的改良主张和方法上与新文学的主将有所出入。他们的主张多发表在《新青年》以及北大、清华的校园期刊《新潮》和《清华周刊》上。
(一)改良派对文言和白话的态度
改良派认同白话的立场。当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等新文学主将们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的文章之后,一群知识分子纷纷就此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与他们开始热烈的讨论。改良派首先积极认同《新青年》文学革新的立场,他们也认可白话的价值,支持白话文学的倡导与建设。
胡适等人从进化论角度考察了欧洲语言和文学发展的历史,得出了言文一致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这一重要结论,认为言文一致是“五四”文学革命关于文学语言的核心问题。改良派看到了白话文符合时代发展趋势,以白话作为文学改良的方法必将行之有效。朱我农就明确表示:“先生等主张暂时将文言改为白话:为改良文字的入手办法,此一着我极赞成。”(26)朱我农:《革新文学及改良文字》,《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9月15日。北京大学学生吴康作为改良派的代表,他坚定支持白话文学正宗地位,认为这是时代发展的需求,“按今日时势之要求,白话文学的确立,是用不着怀疑了”(27)吴康:《我的白话文学研究》,《新潮》,第2卷第3号,1920年4月1日。。杨喆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白话文问题之商榷》一文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由文言降为白话乃自然之趋势”(28)杨喆:《白话文问题之商榷》,《清华周刊》,1920年第186期。,他认同如今白话取代文言这一趋势。
他们认为,我国语言和文字差距过大不仅不利于文字和教育的普及,而且阻碍了文学的发展,用白话作文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黄觉僧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古文的四点弊端,其中第三点就是“不能使言文渐趋一致,沟通民间彼此之情意”(29)胡适:《答黄觉僧〈折衷的文学革新论〉》,《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15日。。常乃惪认为白话文可以帮助普及教育,解决言文不一致带来的弊端:“且白话作文,亦可免吾国文言异致之弊,于通俗教育大有关系,较之乞灵罗马字母者,似亦稍胜也”(30)陈独秀、常乃惪:《答常乃惪(古文与孔教)》,《独秀文存通信》,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张厚载在谈及文学改良益处时,也提到使用白话诗是实现文言一致的重要途径,“新文学干净明白,使人易于了解;且杂以普通习用之名词,尤为雅俗所共晓”(31)张厚载:《新文学及中国旧戏》,《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5月16日。。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更加关注文字的实用性,此外,认为文字本身的发展趋势就是由繁而简,这些都成为改良派支持白话文的原因。吴康认为人们要敢于舍弃文言,“我们现在对于白话文学和古文学的态度和对于日常用器具的态度应该没有分别:便于我们生活底用他,不便于我们生活底不用他。”(32)吴康:《我的白话文学研究》,《新潮》,第2卷第3号,1920年4月1日。在他看来,如今用文言作文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既如此,我们便要大胆放弃旧习惯,用白话代之。他用火柴取代火石子成为日常打火工具打比方,虽然开始的时候人们会不习惯,但是这是不可遏制的。杨喆也表明“文字必由艰深而降为简易”(33)杨喆:《白话文问题之商榷》,《清华周刊》,1920年第186期。,这是文字发展的趋势,白话比文言简单易学,因此不必遏制白话的发展。
改良派对待文言的态度如何?改良派虽然认同文学改良的观点,站在白话的立场,但是他们并不主张完全废除文言,或者立即废除文言。在他们看来,白话取代文言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应该以白话为基础,借鉴文言的优点,以此来建设白话文学。吴康看到了当时白话文学的内容还不太完善,很多地方需要增补修正,因此他认为可以运用文言入白话,前提是明确作文章的态度:“当我们作文的时候,兴之所到,要借用文言的地方也不妨借来一用。但要知道那我们借来用在白话文中的文言,精神上已经变为白话,失掉他文言的本质了。”(34)吴康:《我的白话文学研究》,《新潮》,第2卷第3号,1920年4月1日。可见,吴康并不反对文言,他所说的保持态度上和精神上是白话的,其实就是站在白话文的立场上借鉴文言。杨喆也客观认识到当时用文言的人依旧不少,文言也有存在的价值,不能完全否定,所以他提出“白话文言二者实未能偏废,要在用之适当”,用文言还是用白话关键要看是否得当,二者都有各自的适用场合。他还进行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应该用白话的时候却用文言,就像穿礼服戴礼帽上厕所,难免令人发笑;应该用文言而用白话,就像觥筹交错的宴会上有一人披蓑戴笠一样,难免遭人白眼。由此观之,无论使用文言还是白话都要注意场合,最重要的是得当。他得出结论,平常所用文字“不如以不过深亦不过俗之文字为标准,即所谓普通文字者是”(35)杨喆:《白话文问题之商榷》,《清华周刊》,1920年第186期。。在对文学革命讨论的过程中,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有很多。梁朝威主张应该客观对待白话和文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故以为文体可以文言,可以白话。非白话不足以明白则白话可也。非文言不足以动人,则文言可也。两者各有短长,兼取其长,而去其短斯可也”(36)梁朝威:《改良中文刍议》,《清华周刊》,1920年第186期。,文言和白话各有优劣,要博采众长,去粗取精。
此外,他们也提出白话取代文言应该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正如张厚载所言:“改革过于偏激,反失社会之信仰,所谓‘欲速则不达’,亦即此意。”(37)张厚载:《新文学及中国旧戏》,《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5月16日。张寿朋也认为文学虽然要改良,但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诸君又何必大惊小怪的树起一块‘文字革命’的招牌来呢?”(38)张寿朋:《文字改良与孔教》,《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在他看来主张越是激进,人们反对声越强,因此不必闹“文字革命”,说“改良文字”即可。他把我国国民比作惊风小儿,惊风小儿越受恐吓越不愿服药,在我国文字改革也是如此。方孝岳也提出“急进反缓,不如姑缓其行”(39)方孝岳:《我之改良文学观》,《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他认同白话文学将来是中国文学之正宗,对文学进行改良也必须按此趋势从作白话文开始,但是不能矫枉过正,一时之间各种文字都使用白话,颠覆传统与人们的习惯会遭到强烈反对。
(二)改良派的白话建设观
主张白话与教育的相互作用。“五四”前后改良派提倡白话的原因之一就是白话易学,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关于白话对教育的影响,很多人都有过表述。吴稚晖在给张效敏的答书中提到:“兄弟的主张,也是渴望有白话文字通行,在现在的教育上生出极大的作用。”(40)吴稚晖:《吴稚晖答张效敏(文学上之疑问三则)》,《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黄觉僧在分析文言的弊端时也提到了文言不适用于教育,不适于说明科学,不适于传播新思想,白话则刚好相反。
学校教育是人们接受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学校教育中使用白话也是推广白话的重要途径,因此学校教育改革十分重要。当白话得到部分国人的认可之后,如何进行改革来推广白话,从理论向实践层面转换是当务之急。正如盛兆熊所说,他十分赞成胡适所倡的白话文字,但强调想法产生之后就要付诸实践,因此专门给胡适写信谈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问题。盛兆熊把目光聚焦于学校教育改革。他提出改革要从高等学校开始,当大学招考要求用白话的时候,那么中等学校以及小学为了顺利升学自然会随之改变,主动重视白话(41)吴稚晖:《吴稚晖答张效敏(文学上之疑问三则)》,《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不过,盛兆熊也看到了大学改革的难度,因此写信给《新青年》希望今后注重研究改革的方法。
胡适与盛兆熊的看法不同。胡适认为从高等学校开始改革困难重重,如果非要从学校教育考虑,那应该从小学做起,用国语编撰教科书,三年级以上才能学习古文,另外要重选教科书材料。但当时白话材料有限,所以改革的当务之急还是要提倡白话文学,创造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当国民都认可新文学的时候,白话改革才会没有阻碍。关于大学国文改革,清华大学梁朝威面对清华学生中文水平差的情况,从教材、教授、文体、作文等方面提出了改良的办法,其中也提到了文言和白话的问题,认为这两种文体在大学皆可存在。此外,他还提出教材要分为实用和文学两类,学生可自由选择(42)梁朝威:《改良中文刍议》,《清华周刊》,1920年第186期。。不过,胡适的看法则不同,他不反对学者研究旧文学,认为古文在大学中可被设置为“专科”,但是古文不能作为文学正宗。
改良派提出美术文与应用文之分。白话取代文言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当新文学主将们提出白话的文学正宗地位时,改良派的很多人想到了文学界限问题。他们认为要先确定“文学”这个概念具体所指,在此基础上都强调了要区别对待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或者美术之文和应用之文。方孝岳提出“以文学概各种学术,实为大谬”,他认为文学当以美观为主,改良文学要从划定文学界限说起,他给文学下的定义是:“凡单表感想之著作,不关他种学术者,谓之文学”,其内容主要包括“诗文戏曲小说及文学批评等是也”(43)方孝岳:《我之改良文学观》,《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应用之文以表达清楚为目的不在美文的范围内。黄觉僧也把文学分为应用文和美术文两种,又把美术文分为通俗的美术文和旧美术文,通俗的美术文更侧重实用功能,作教育普及用,可以用白话;而研究旧美术文的都是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文言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障碍,因此在旧美术文领域不需要废除文言。
常乃惪强调了美术之文的重要性。他考查上古文字,指出最早“文”就是专指美术之文,从韩愈提倡古文之后,后世又倡文以载道,美术之文被摧残。在他看来,文学改革要注意文体的不同,美术之文虽然实用性不强,但是对于铸就高尚的理想,引起人们对美感的兴趣必不可少。他最早把非美术之文命名为“史”,认为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判断文史的界限,在此基础上从两方面进行改革,改革史学使其更具实用价值;改良文学使其“成为一种完全之美术”(44)陈独秀、常乃惪:《答常乃惪(古文与孔教)》,《独秀文存通信》,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他认为文言和白话有不同的适用范围,白话表现力不如文言,表达境界不如文言优美,因此美术之文应专用文言,而实用之文专用白话。但是,他并不否认将来白话文更加成熟之后也能达到文言表情达意的功能。陈独秀在给常乃惪的答书中对把说理记事之文称为“史”提出质疑,常乃惪也表示接受并认可陈独秀所提的“应用之文”,但他依旧强调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的区别,美术之文必不可少,可以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
沈兼士也说“应用之文,必须用俗语。文学之文亦可用俗语,固为吾人之所公认。惟其为文之性质不同,故其用字之范围广狭,亦宜因之而有区别。”(45)沈兼士:《新文学与新字典》,《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25日。由此观之,在对应用文应该使用白话这一点上,改良派的意见基本一致,都表示赞同。而对文学之文,他们中有人认为可以使用白话,有人则认为白话不适用于文学之文。在他们看来,文学之文必须是美文,也就是很多人所说的美术之文,白话虽然具有实用性,但是白话暂时不具备文言的表现力,缺乏美感,所以不适合于美术之文。
改良派反对废除用典和对仗。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了“不用典”、“不讲对仗”的主张;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针对骈体文的盛行,提出了经典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要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这些主张的提出与文言的日渐僵化息息相关。正是文言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这么多问题,用白话取代文言才更显迫切。这些文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文学的载体“文言”一起被打上了落后的标签,成为新文学主将们批判的对象。
改良派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反对“不用典”、“废除骈体文”这类主张。常乃惪对胡适指出文言的缺点并提出文学改良表示认同,但是他不赞同因为改革而废除骈体,禁用古典的做法。他认为我国的骈文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文字(46)陈独秀、常乃惪:《答常乃惪(古文与孔教)》,《独秀文存通信》,第14、14、54、16页。,不能随意抛弃。六朝文学的弊端不能归咎于骈体之过,而是方法不对。他形象地比喻,这就好像给木偶穿华丽的衣服,既不能说是华衣连累木偶,也不能说是木偶连累华衣。假如用作古文的方法来驾驭骈文,那骈文自然不会有问题。至于用典,他认为废除用典是矫枉过正,诗文中的用典就像服装上珍贵的装饰品一样,偶尔使用可以使文章文辞优美、更为生动,“但不可如贫儿暴富,着珍珠衣过市已耳。”(47)陈独秀、常乃惪:《答常乃惪(古文与孔教)》,《独秀文存通信》,第14、14、54、16页。用典要适量,用好典故可以帮助文章更加简洁凝练。李濂镗对用典和对仗的看法和常乃惪十分类似:他认为用典和对仗与文学家的关系,正如毒物与医生,脂粉与妇人的关系。庸医用毒物只能杀人,但良医用毒物能发挥其神奇的功效;无盐女用脂粉可能会更丑,但西施用脂粉只会更加貌美如花(48)李濂镗:《致胡先生》,《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因此,在他看来用典和对仗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只要用典适当、对仗自然,一样可以创造好的文学,不能一味把文学陈腐空泛的原因归咎为用典和对仗,文学家自身的创作能力十分关键。陈丹崖认为,“无高尚优美隽永妍妙之文字,决不能载深远周密之思想。”他也对用典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惟绝对地不用古典,则为过甚。”(49)陈独秀、陈丹崖:《答陈丹崖(新文学)》,《独秀文存通信》,第27页。
改良派中也有赞成不用典故的人。张厚载就认为用典最容易阻碍思想的发展,他还举袁枚话为证:“袁随园亦谓:‘用典如陈设古玩,各有攸宜,然明窗净几,亦有以绝无一物为佳者,孔子所谓‘绘事后素’也。”(50)张厚载:《新文学及中国旧戏》,《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5月16日。不用典故,用好白描,也能够写出最美的文字。曾毅也说:“中国之文,尤坏于滥用典故”(51)陈独秀、常乃惪:《答常乃惪(古文与孔教)》,《独秀文存通信》,第14、14、54、16页。。仔细辨别他们的主张会发现,他们反对的不是用典,而是“滥用典故”,这与大多数改良派的观点是一致的。用典本身没有错误,不仅可以使文章简练,还可以使表情达意更为准确,只是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很多文人为了追求文章的华丽深奥,不了解典故的来龙去脉,致使典故失其原意,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加重了文章的陈腐晦涩,使文章因困于典故而“束缚性情,牵强失真”,即胡适所说的“用典之拙者”。在改良派与新文学主将们的来回讨论中关于用典的态度也更为明晰,陈独秀也承认不必禁止使用典故,不反对偶尔用典,只是反对“胡君所云,乃为世之有意用典者发愤而道耳”(52)陈独秀、常乃惪:《答常乃惪(古文与孔教)》,《独秀文存通信》,第14、14、54、16页。。
(三)改良派与渐进派的比较
改良派与渐进派都是文白论争中处于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中间派,他们对文言和白话的态度没有那么绝对化。改良派与渐进派的共同之处是他们对白话的态度有向“五四”文学主流靠拢的趋势。总体上,他们都站在白话本位立场,认同白话的独特功能,肯定白话的价值,认为白话取代文言是可行的,但是他们都属于温和的改革派,对文言的态度较为中和,主张站在白话的立场上吸收文言的优点。从历史主流的角度看,中间派的主张存在某些问题,但是他们的主张对白话文建设与发展有重要意义。
渐进派是最早与胡适探讨文学改良问题的,所以最初他们对白话的态度比较保守。在经历了不断地探讨与文学尝试之后,他们对白话的态度从最初的迟疑到支持白话在应用文领域使用,再到最后的认可白话可以作诗,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但始终保持着较为谨慎、冷静的态度。
改良派处于激进派和渐进派之间。他们从一开始就支持白话文,认可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做法,但是在对待文言的态度上,他们没有激进派那么绝对偏激。在他们看来,没有必要立马彻底废除文言文,文言文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方面还是优于白话的,在全面建设白话文学的初期尤其应该吸收文言文的长处,以文言的优势补白话之不足。造成这个区别的原因主要与文学革命的进程有关。渐进派成员与胡适交往密切,是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的朋友,在胡适文学改良观酝酿初期,他们就已经开始与胡适讨论中国文学的出路问题,可以说正是在与渐进派的讨论中,胡适逐渐明确他的白话文学观。当胡适和陈独秀正式在《新青年》提出用白话取代文言的时候,白话观已经有了明确的内容,“文白”之争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所以改良派对文学革命主张有更多的认可,只是就其中的部分观点与新文学主将展开修正性讨论,并没有渐进派的变化过程。
三、“五四”“文白”论争中,中间派与激进派的历史评价
五四时期文言和白话之争不仅是语言文字的重要论争,也与文学变革、新旧文化、中西文化之争密不可分。中间派站在白话的立场上认同文学革命,他们与激进派积极探讨白话借鉴文言的可能性与方案,从整体上与激进派实现了互动互补,与保守派形成不同阵营,与激进派结成建设性力量,有力推进了白话取代文言的胜利。
(一)“文白”论争中,中间派与激进派的思想异同
在“文白”论争中,中间派着眼于语言或文学自身的发展,通常针对激进派的各种具体的主张进行辩驳。他们首先反对的就是胡适所说的文学死活观,认为文学死活的标准不取决于语言的差别,而在于文学的内容情感是否有生命力。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他们自然不同意完全废除文言的激进观点,在与激进派的讨论过程中,经常以文学史的实绩证明文言不是死文字,文言也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朱经农就曾致信胡适表示不赞同他的文学死活观,他认为《红楼梦》和《水浒传》是活文学,文言所作的《史记》也并非是死文学。梁朝威也明确表示不赞同文言是死文字的观点,“诗莪蓼篇,王褒诵之,未尝不痛哭流涕。其感人之深,一至于此!孰谓古籍尽死文学耶?”(53)梁朝威:《改良中文刍议》,《清华周刊》,1920年第186期。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产生了数不胜数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就是对“文言为死文学”最好的反驳。
激进派与中间派不同,他们从现代性思想启蒙角度来看待文言和白话,认为白话取代文言不仅仅是文字改革与文学改良问题。传统文学无法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变革社会的思想武器,文言成为启蒙运动的拦路虎。激进派总体上的反文言立场,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现代化变革进程中的一种策略性选择。显而易见,激进派与中间派的论争聚焦点并不完全一致,二者在论争时经常产生错位。论争焦点的错位经常使论争双方产生偏颇。
总体上说,以新文学主将为代表的激进派在“文白”论争的态度和立场总体上虽然是激进的,但实际上激进派内部也有相对温和之人,认识到在白话取代文言获得书面语正宗地位的过程中,也可以吸收文言的优点。傅斯年就认为文言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虽然僵化,但是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值得借鉴;白话现在虽然被提倡,但是文字积淀不足,因此在进行白话创作中应该吸收文言的优点为白话所用。这也正符合他对白话的定义:“以白话为本,而取文词所特有者,补苴罅漏,以成统一之器,乃吾所谓用白话也。”(54)傅斯年:《文言合一草议》,《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刘半农根据平日翻译和创作经验也发现,很多时候同一个意思,用文言一句话即可解决,而用白话好几句都说不清楚,文言比白话更准确方便,但是,很多情况则刚好相反,用文言总觉得“呆板无趣”,而白话则十分自然,“神情流露”。因此,虽然他对“白话为文学之正宗”深信不疑,但也提出了“文言和白话可处于对等的地位”(55)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这一说法。蔡元培作为北大的校长,致力于使北大成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之阵地,所以即使他支持新文化运动,支持白话文,并与林纾进行了论战,他也能谨慎冷静地对待文言文,让文言仍保留一席之地。
(二)“文白”论争中,中间派与激进派论争的意义
郑振铎曾说“当时有一班类乎附和的人们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不少的言论,却往往是趋于凡庸的折衷论”,“这些折衷派的言论,实最足以阻碍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56)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56页。他列举了方宗岳、余元濬两人的言论为例,但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他指涉的对象的普遍性。本文没有延续郑振铎“折衷派”的命名方式,而是采用了“中间派”这一称谓,因在郑的语境下,“折衷”已带有贬义色彩。中间派从整体上与激进派形成互动互补,形成一股建设性力量,有力推进了白话取代文言的胜利。
首先,中间派对文学革命积极做出回应,扩大了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影响力。“五四”初期文学革命召唤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新青年》在“五四”初期发布的关于文学革命的探讨的文章,大部分都由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学阵营内部同人执笔。中间派积极介入“五四”初期的这场寂寞的讨论与争辩,营造了一种较为宽松的论争环境,并引起了更多人对白话文的关注,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开展,扩大了白话的影响力。
其次,中间派关于文言和白话的讨论,对于白话文的建设有重要意义,完善了对现代白话文建设的整体构想。激进派也吸收了中间派的建议,并对文学革命相关问题不断修正、说明,减少了白话文建设的失误。正如胡适在回忆他倡导文学革命活动时所说:“我的决心实验白话诗,一半是朋友们一年多讨论的结果,一半也是我受的实验主义的哲学的影响。”(57)胡适:《逼上梁山》,《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渐进派在胡适白话观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建设作用,在与他们的讨论过程中,胡适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白话主张。改良派十分重视白话文实践,他们主张的文言和白话自古以来就是相互融合促进的观点,也启发了激进派。比如,胡适“不用典”的提出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常乃惪与陈独秀的通信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在与常乃惪的两次通信中,陈独秀对“不用典”作了具体的解释,从“行文偶尔用典,本不必遮禁。胡君所云,乃为世之有意用典者发愤而道耳。”(58)陈独秀、常乃惪:《答常乃惪(古文与孔教)》,《独秀文存通信》,第16、26页。到“行文本不必禁止用典,惟彼古典主义,乃为典所用,非用典也,是以薄之耳”(59)陈独秀、常乃惪:《答常乃惪(古文与孔教)》,《独秀文存通信》,第16、26页。。这种解释显得更为客观,双方在用典问题上形成了较一致的看法。文学革命初期,白话书面语尚未成熟,中间派对文言的重视为实现白话文建设、文言合一提供了一种途径,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再次,中间派的文学革新与文学改良的观点与态度,构成了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思想文化多元化的重要内容。不少人把白话和文言的论争看成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对峙,忽视了从历史语境考察这场论争。对中间派与激进派论争的研究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五四时期关于文言和白话论争思想主张的复杂性。这一场论争并不是只有非此即彼的观点,还有像渐进派、改良派这样的存在,他们共同构成了“五四”多元文化的丰富形态。
(三)“文白”论争中,中间派与激进派论争的问题与反思
在与激进派论争的过程中,中间派也存在需要反思的问题。从他们自身的观点看,在新旧对立冲突十分激烈的时候,他们虽然整体上属于新文学阵营,但是,正如郑振铎把他们称为“凡庸的折衷论”,中间派虽然认同激进派用白话取代文言的主张,但没能从思想文化变革的宏观历史视野上理解这种主张的意义,而是更多的从语言或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白话,忽略了白话所承载的现代性思想文化启蒙的任务,这就导致了他们在论争中总是拘泥于文言作为一种语言和文体本身存在的优势,与激进派的思想难以一致。
中间派忽视了激进派“文白”论争态度的“激进”,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学革命运动斗争策略的选择。胡适曾说:“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60)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姜义华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0页。可见,胡适极力推崇白话,急于确立白话的正宗地位,坚定地反对文言,都是为了文学革新顺利进行清扫障碍,不破不立,只有采取彻底反对文言的姿态,并“猛着一鞭”,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警醒。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的性情是喜调和的,“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61)鲁迅:《无声的中国·三闲集》,《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中间派并没有完全觉察出这种良苦用心。
文言在中国有数千年的传统,白话取代文言不可避免会面临强大阻碍。文言的落后不仅表现在实用性不足,更体现在文言所承载的传统文学以及传统文化无法适应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需要。中间派对文言保持客观谨慎的态度,吸取文言优点为白话所用的确有助于白话文建设,但是如果过多突出取长补短,博采众长,将文言白话总体上处于同等地位的观点得以盛行,将延缓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过程,丧失这场文学现代变革的历史机遇。事实证明,“文白”论争中白话文地位的确立所代表的“五四”文学革命的主潮,推动了中国文学与思想文化走出历史困境,开创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变革与文学变革的新时代,这是我们在回望这一场“文白”之争的复杂性中,应该看到的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