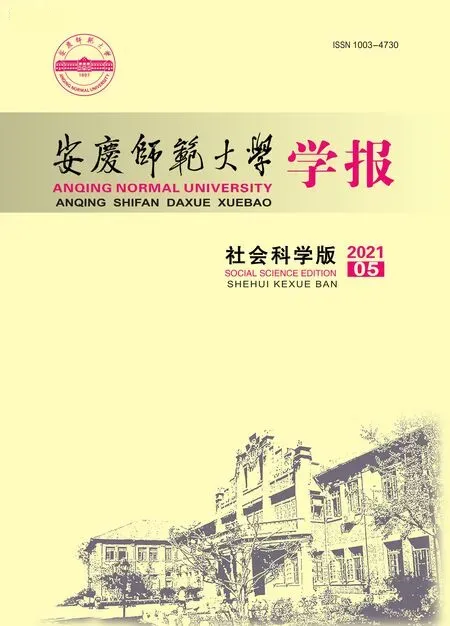空间旅行与双重视角:张恨水的故乡书写
王 谦
(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安徽安庆246011)
在张恨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诸如《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经典小说,也有像《两都赋》《山窗小品》这样风格清新的系列散文。这些作品或以城市为写作背景,或以城市为描写对象,特别是张恨水足迹所至且生活多年的北京、南京、重庆、成都等城市,都得到了多维的呈现。可以说,这些作为“他乡”的城市在张恨水的作品中占有主导的地位,相比之下,张恨水的故乡写作则不太引人注意。一般以为,与现代文学史上擅长乡土书写的作家如鲁迅、沈从文相比,以城市书写闻名的张恨水似乎忽略了对现代中国乡土社会的描绘,因此有学者认为,“张恨水在小说中不写乡愁、乡情、乡趣、乡怨,而执著于都市生活”[1]。实则不然,在张恨水数千万字的作品中,有《天河配》《似水流年》《现代青年》《天明寨》《秘密谷》等长篇小说以故乡作为背景,还有大量的散文回忆了故乡生活与乡土社会。
张恨水的故乡书写与乡土写作之所以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可能是因其前期城市书写的影响太大,人们过于看重他作为都市记者的身份属性与通俗文学写作的文学史地位,而后期爱国主义又成为张恨水写作的另一重要主题,遮蔽了张恨水故乡书写的真实性与时代价值,故乡书写与乡愁意识再次被忽略,但正因其被忽视而更具讨论的价值。张恨水的故乡书写在其城市书写之外提供了另一条理解现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思路,提供了另一个观察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视角。因此,回到事物本身,回到张恨水的作品及其生命体验本身,重新审视张恨水笔下的故乡,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一、空间旅行与发现故乡
张恨水祖籍安徽潜山,生于江西景德镇,在江西度过童年时光,九岁时举家移居南昌,并接受学校教育,在南昌生活多年,因此他把南昌称作“第二故乡”[2]。被张恨水称为“第二故乡”的还有北京与重庆两座城市。北京是张恨水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从1919 年(24 岁)离开故乡到北京开始,先是住在家乡的会馆中,随后租房住,继而又买房居住,家眷也都接到了北京,至1936 年举家迁往南京,在北京共生活了十七个年头,此后,张恨水便称北京是他的第二故乡。抗战开始后,张恨水于1938年由南京经安庆、武汉辗转来到重庆,至1946年重回北京,住在重庆的南温泉,彼时生活条件艰苦,屋漏不足挡雨,张恨水遂将自己的住处命名为“待漏斋”,如此艰难坚持生活了六年多,“久客之地,成了第二故乡”[3]。
张恨水长至十岁才回到祖籍潜山,至十二岁又随父亲到江西,直到十七岁时他的父亲去世才迁回潜山居住,次年即离开潜山至上海、苏州等地谋生,此后虽陆续回到潜山短住,但与他在北京、重庆、南昌等地的生活时间相比,潜山在张恨水的生涯中时间长度是最短的,他自己也说:“予少随祖父宦游,鲜返故里,壮又以糊口奔南北,仅十载一省庐墓。故家居胜地,而予反少闻知。”[4]因此,张恨水在谈到自己的籍贯时亦颇感为难,“其初,我也有点不愿称潜山籍,而况我在江西出世,一直活到十岁,至少是半个江西老表。”[5]尽管张恨水在安徽生活的时间不长,但他自己所承认的“第一故乡”,只有安徽潜山,他的回忆散文如《故乡的小年》《故乡的四月》等,写的都是安徽潜山。这可能是因为,潜山是张恨水的祖籍,张家的宗族亲人都生活在潜山,传统社会的宗族关系起到了维系人心的作用,强化了张恨水对原籍的身份认同感,且潜山的乡下有张家祖上留下的祖屋,不似在江西时追随父亲宦海漂泊,无固定居所,空间与场所是心理认同与情感记忆的最好载体。
故乡,本质上是一个心理空间,故乡所承载的是生活记忆、情感归属与身份认同,但故乡终究会指涉具体的物理空间、地域,心理空间与物理空间的融合共同构建了精神上的故乡。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恨水的故乡书写指涉了三个不同的物理空间,即皖江地域、安庆城与潜山乡村。
皖江地域是一个宏观的地理概念,“皖”即皖山,是安庆潜山县境内天柱山的别称,皖江连用,则泛指安徽境内长江流域的安庆、池州、铜陵、芜湖等区域,今人在讨论皖江文化对张恨水创作的影响时均以此立论[6]。皖江地域的地理风貌、历史文化与人文精神具有内在的相似性,特别是青年时期的张恨水,在安庆与芜湖都有过生活、工作的经历,成为后来张恨水书写故乡的一种重要记忆,反映清末太平军运动的长篇小说《天明寨》即以皖江地域的潜山、桐城、太湖、宿松等地区为背景,小说《似水流年》对怀宁县及皖河流域的乡村风貌做了形象的刻画,抗战期间写的《野人寨好比小宜昌》《岳西》等杂文,都是以皖江地域为背景的。
然而,这种以地域为背景的故乡书写往往是印象式的,缺乏感性的情感体悟与生活体验,皖江地域与皖江文化对张恨水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张恨水作品中的表现并不典型,情感的缺席与心理认同的模糊削弱了皖江地域的故乡色彩。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张恨水笔下的皖江地域似乎不及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特点鲜明,失于空泛。
安庆城是张恨水故乡书写的另一物理空间。在近代,安庆一度是安徽的省城,是安徽省境内长江流域上游的第一个城市,素有“长江万里此咽喉”之称,是重要的军事重镇,在近代中国也曾引领过近代化、工业化的潮流,是近代安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安徽西南部的交通节点。因此,安庆的地缘优势决定了它是皖江地域与外部世界连接的必经之地。
如果说皖江地域与皖江文化孕育了张恨水的创作基因,那么安庆则是张恨水走上创作道路的一个物理空间起点。安庆是张恨水去往外部世界的首站城市,沿江而下,可至芜湖、南京、上海,溯江而上,能至汉口、重庆,因此,在张恨水往返于故乡与外界的路线图中,安庆都是无法绕过的地点。但安庆在张恨水的生涯中只是一个旅行中的过渡点、中转站,尽管张恨水在安庆也为他的原配妻子郑文淑购置了房产,但除了往返于潜山与外界之间的短暂停留,张恨水在安庆并无太多的生活经历,安庆对于张恨水来说更多的是一个空间概念,没有丰富、真切的生活体验。因此,早期张恨水对安庆的书写多是城市局部意象的描绘,如写安庆城郊长江边的大观亭:“这里原没有什么花木园林之胜,只是土台上,一座四面轩敞的高阁。不过在这里凭着栏杆远望扬子江波浪滚滚,恰在面前一曲;向东西两头看去,白色的长江,和圆罩似的天空,上下相接;水的头,就是天的脚;远远的飘着两三风帆,和一缕缕轮船上冒出来的黑烟,却都看不见船在哪里;只是吹着浪头,翻了雪白的花,一个一个,由近推远,以至于不见。”[7]79-80颇能见出江边城市的特点。对安庆玉虹门的描写,则将对历史的感慨融入了城市之中:“这玉虹门有安庆一道子墙,当年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军队,两下对峙的时候,在山头上新建筑的。出了这门,高高低低,全是乱山岗子。山岗上并无多少树木,偶然有一两株落尽了叶子刺槐,或者是白杨,便更显着荒落,不过山上枯黄的冬草,和那杂乱的石头,也别是一种景象。这里又不断的有那十余丈的山沟,乃是当年军营外的干濠。西偏的太阳,照着这古战场的山头,在心绪悲哀的人看着,简直不是人境”[7]401。总之,张恨水对于安庆的体验更侧重于城市本身的历史文化,是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来观察、体验安庆的,因此,那些象征着安庆历史、政治、军事的城市空间符号更易引起张恨水的注意,建国后张恨水又写了《安庆新貌》《迎江寺塔》《菱湖公园》等散文,仍是以一个游客的心理来书写、记忆安庆。由于缺乏丰富的生活体验,张恨水笔下的安庆没有空间的整体性,也不能深入表现安庆城的日常生活,显示不出安庆城的特征性与地方性,这种概念式的描写远不及他对北京、南京的书写细致、深刻,缺乏对城市的情感体验与价值评判。总之,张恨水对安庆这种印象式的描绘还是难以见出故乡的情感归属,安庆对于张恨水而言只是籍贯的象征,而不是精神的故乡。
张恨水的精神故乡及其故乡书写集中体现在以潜山为代表的乡土社会的记忆与书写里。
潜山以其境内的天柱山著称,张恨水写于1933 年的长篇小说《秘密谷》就是以天柱山为背景,张恨水曾有感于天柱山在中国的名气不大,还曾专门撰文宣传:“潜山县是以山得名,可是这名县的潜山,比庐山伟大,比庐山雄奇,比庐山壮美,反而湮没不彰了。在南宋以前,这山似乎走过一时运,石崖上有着东晋到宋许多名人题名,是老大的证据。南宋亡了,这山也就深沉了,未知何故。前年金大生物系,光顾到这无人睬理的潜山主峰天柱山来,测量出它拔海四千余尺(零头似乎是七百),带了许多稀有的标本去,这山才略微出点头。去冬在故乡,我曾深叹此山之不幸。只恨人微言轻,不能发扬光大它罢了。”[8]天柱山所在的潜山及乡村社会是张恨水真正的心灵故乡。
在北京时,张恨水称自己是籍贯潜山的京剧名家程长庚的“程大老板同乡”,而同为京剧名家的杨小楼,“予一向认为系怀宁石牌人,恒少注意其家珍。今既知为同乡,他日回故里,或可访得其祖父一二逸事也”[9]。在张恨水所用的众多笔名中,诸如“潜山人”“我亦潜山人”一类亦证明他对潜山的故乡认同。
张恨水的宗族自元代迁至潜山[10],随后在潜山境内繁衍,兴建祠堂,因此,在张恨水的故乡叙述中,在他一生复杂的空间旅行中,只有潜山的乡村才能获得他的心理认同,位于大别山余麓的那个山村与乡土社会才是张恨水真正的精神故乡。
二、双重视角下的乡土社会
与沈从文用一种近乎理想的笔调来描绘现代湘西的农村不同,张恨水则力图呈现皖省乡村的真实面貌。张恨水对乡村的观察并不仅是一个“乡下人”的视角,还站在一个经历了现代都市文明的“城市人”的立场重新体验乡村,即站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立场上来回忆乡村。基于这种观察视角的双重性,张恨水的乡村记忆呈现出内在的矛盾性,传统乡村的田园生活与“城市人”眼中乡村的落后之间的巨大张力,构成了张恨水对故乡的复杂记忆。
张恨水的祖居位于潜山北部的一个山村,交通闭塞,这个位于大别山区的乡村在近代中国仍处于未开化的“前现代”社会,经历过现代都市文明的张恨水对故土乡村的贫困、落后、封闭用一种近乎写实的笔调进行了再现,这种再现不同于沈从文笔下室外桃源般的湘西,不同于萧红笔下的充满了苦难的东北,也不同于鲁迅批判地书写故乡绍兴。
一方面,张恨水以本乡人的立场书写乡土社会的生活体验,感受农耕社会的自然与纯朴。张恨水笔下的乡村更接近于原始的农耕文明,对于他生活并不长久的乡村,张恨水丝毫不吝啬描写乡村自然风光的笔墨,他用极为真实的笔调描写故乡的旷野、麦田、油菜花等田园景色,用故乡的方言模仿鸟儿的叫声,“‘割麦栽禾,蚕豆成棵。’那年年必来的布谷鸟,这又开始工作了。乡下的农人们,似乎也因为有了这种声音,工作得很起劲,男子们在田时割了麦,一挑一挑的大麦,成捆的顺着田埂,向麦场上挑去。田沟里的水,在绿色的短草里叮叮的淙淙的响着,随着田埂的缺口,向割了麦的空田里流去,真个是割了麦又预备栽禾了。”[11]122如此写实的田园风光描写,正是张恨水在故乡生活的真实观察与体验,也表明了他对乡村的真情实感。但这种对皖西南乡村田园的牧歌式赞美并未掩盖张恨水对乡村社会的细致观察,故乡前现代社会的闭塞、落后导致的贫穷,在张恨水的小说中如镜像般保留了下来,如写乡村居住条件的简陋:“这里有一间房,四周都是黄土墙。有个钉了木棍子不能开动的死窗户,正对着夹道开了,只透些空气,并无别用。屋顶有两块玻璃瓦,由那里放进一些亮光来。虽是白天,屋子里也是黑沉沉的,而且最不堪入目的,便是那靠黄土墙的所在,高的矮的,围了许多篾席子,里面屯着稻谷。”[11]204-205又如,对于故乡日常饮食的描绘,张恨水似乎也保留了新闻记者般的写实眼光,小说《天河配》中的王玉和家是当地的大户,接待北京而来弟媳的第一顿饭:“那张矮桌上,有一个大瓦盘子,装了北瓜,一只粗瓷蓝花碗,装了一大碗苋菜,又是一只旧瓦碗,装了一大碗臭咸菜,四方堆着四大碗黄米饭”[11]205。《似水流年》中的黄惜时家“虽是一乡的巨族,可是自家吃饭的人很少,只有五个人,除了黄守义夫妇和惜时,此外还有个寡嫂冯氏,一个六岁的小侄子小中秋儿。三代坐了四方,桌上一碗煮豆腐,一碗盐菜,一碗炒老茄子,都放在桌子中心。另外一碗红辣椒煎干鱼,一碟煎鸡蛋,都放在惜时面前”[12]5。此外,乡村的生活细节,诸如烧茅草煮饭、用石磨磨面、用碓臼舂米等,张恨水都真实的加以还原,类似于民俗学家的社会纪实调查。在小说《秘密谷》中,张恨水借助几位南京的城市青年,以一种猎奇、探险的视角呈现天柱山一带的前现代社会生活。张恨水以其切身的乡村生活体验,用一种冷静的笔调复述着故乡社会的日常生活,既没有虚伪的同情,也没有表现出欣赏式的歌颂,而是像一个理性的社会学家一样,用近乎田野调查的方式还原故乡生活的真实面貌。
此外,小说《天河配》中回忆潜山乡间过年时祭祖的习俗,颇有民俗学的价值。不管是记忆故乡生活的散文[13],还是关于故乡的写实小说,都力图还原故乡生活的原貌,这种真切的故乡记忆与朴素的叙述,呈现了一个未经现代性侵蚀的乡村社会,是乡土社会的现代挽歌。
另一方面,张恨水又借助外来的“城市人”的眼光来“发现”乡村生活的封闭,毫无留情地展示农耕社会的落后与弊端。
如果说张恨水对现代都市贫困空间的书写是从社会学家的视角着手,是为了揭示现代城市社会的症结,对大众读者进行“抚慰”和“警戒”[14],那么他对故乡乡土社会生活的贫困书写则更多的是为了突出其故乡的风土民情,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与情感寄托,故乡社会的贫困生活在张恨水的记忆里不是无法忍受的艰难岁月,而是乡土中国的本真面貌,凝聚的是他在经历了现代都市生活后的情感返归。
张恨水对前现代故乡社会的记忆,并不像沈从文对湘西的深情歌颂,把乡土田园当成是理想的乌托邦,而是以其真实的生活体验来冷静地剖析乡村田园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人情。数年的潜山乡居生活让张恨水亲眼目睹了乡土底层农民生活的艰辛,他以现实主义的笔触真实地还原了乡间农夫艰辛的劳作生活。例如写农夫们车水灌溉的劳作场景:“车水工作,须半夜起,日入而止。农人立转动之车轮上,凡十余小时。家近者,可归餐。否则有妇人或童子,以竹篮送饭至树荫,呼而食之。食饭外,唯农人藉抽旱烟,得小歇。附近或无树荫,即从水滨烈日中,于腰间拔旱烟袋出,将田岸上所置燃火之蒿草绳,就烟斗吸之。偶视同伴,尚作一二闺闼谑语,以自解嘲。盖除此外,亦无以调剂苦闷与枯燥也。”[15]又以同情的口吻描写故乡农民在种植水稻过程中除草时的辛苦:“耙草者,戴草帽,赤背。然背不能经烈日之针灸,则以蓝布披肩上,藉稍抗热。下着蓝布裤,卷之齐腿缝。与都市女郎露肉,其形式一,而苦乐殊焉。农人赤足立水中,泥浆可齐膝。然实不得谓之泥浆,经久晒,水如热汤,酿浊气扑人胸腹。水中有蚂蟥,随腿蠕蠕而上,吸人血暴流,更有巨蚊马蝇藏水草中,随时可袭击人肉体。耙草者一面耙草,一面须防敌人。身上不仅谓之出汗,直是巨瓮漏水,其披在身上之蓝布,不时可取下拧汗如注溜也。”[16]在现代作家群体中,将乡村田园生活描绘为人类幸福家园的不在少数,他们大多常站在“城里人”的立场用一种猎奇的眼光来看待乡村社会,像张恨水这样站在农民的立场来体验真实乡村生活的并不多见。在沦陷时期,张恨水居住在重庆的外郊,曾用细腻的文字详细地回忆了故乡农村收获小麦与插秧的农忙事,打麦子、唱山歌、看水牛、“吃插田饭”等前现代的乡间生活在张恨水的记忆里是一种难得的“农家乐”。但张恨水也像唐代诗人白居易那样,对这种田间生活的“乐”是理性认识的:“不过,由我想,农夫们是不怎么乐的。太阳那样晒人,我看他们工作,自己却缩在树阴里呢。田里的泥浆水,中午有点像温泉,插秧的人,太阳晒着背,泥浆气又蒸着鼻孔,汗珠子把披的那块蓝布透湿得像浸了盐水。皮肤晒得像红油抹了,水点落在上面会滑下来,但泥浆却斑斑点点,贴满了胳膊和两腿。于是我了解他们为什么唱山歌,为什么中午的山歌,唱得最酣了。”[17]他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来观察乡村生活贫苦、艰辛的真实面目,“是知风雅事,实不及于农村。古来田园诗人,每夸农村乐趣,固知谎也”[18]。
张恨水笔下的田园生活不是浪漫主义的故乡乌托邦,而是一个现实的乡土社会。张恨水的乡愁并不是一味的赞颂乡村的田园生活,而是在回忆故乡生活的日常琐事中融入了真切的现实关怀。张恨水的城市书写呈现出鲜明的田园气息,或许就来自他乡下人的生活经历与对“乡愁”的心理补偿。
在批判乡土社会的落后与农民性格的缺陷上,张恨水虽不及鲁迅深刻、典型,但张恨水笔下的乡土社会更加形象、立体,这些作品对乡土社会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张恨水本人的生活体验,是一种蕴含着复杂情感的批判;在呈现潜山乡村的地域、人文特征上,张恨水又不像沈从文对湘西的热烈赞美,张恨水对潜山乡村带有“乡下人”的乡土眷恋,对田园生活的肯定,对乡土社会的同情、体谅,但对乡村社会的实质又有着清醒的理性认识。因此,张恨水的乡愁在理性的社会批判之外又带着对故乡生活记忆的温情,是一种矛盾的心理。
三、城乡二元与现代人的乡愁书写
在张恨水的70 余年的人生旅程当中,只有青年时期在潜山乡村生活过几年光景,对于乡土社会的空间体验算不上丰富,却对故乡留下了深厚的生活记忆,形成了真挚的心理认同,书写了都市游子的乡愁;在张恨水数千万字的作品中,直接书写故乡的文字虽不及书写城市厚重,但其呈现的故乡形象与乡愁在现代文学史上亦能独树一帜,既展现了皖省乡土社会的独特空间形态与地域特征,深入皖省的乡村生活,呈现了前现代乡村的真实面貌,又对乡土社会进行了理性反思,在往返于城乡的空间旅行、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时代背景中重现了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境遇。
短暂的潜山乡居生活使张恨水对故乡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即便张恨水在成为“城里人”、接受现代都市文明之后,还念念不忘故乡的老屋、池塘、冬青树等,“门外即草塘一所,环堤种古柏垂杨之属,更其右有旷场冬青一树,高入云霄,数里外即望之,年期既届,在满日阳春之下,与群儿戏冬青树下,以急线爆竹,掷水中燃放,终日不倦。今十年未归,闻堤树多坏,冬青亦倒却,弥增感慨也。”[19]十多年后,张恨水仍用了纯净的笔触回忆在故乡旧居中读书的闲适生活,老屋、草塘、小院、古桂、鸡鸣、麦田、野雉等乡村社会的空间意象,构成了他浓厚的乡愁,“恒觉诗情画意,荡漾不止。”[20]
乡愁是离乡游子的共通情感,乡愁书写体现了作家心中的故乡心理空间与身份认同。数年的皖省乡居生活是张恨水排遣不去的故乡之忆,通过对故土乡村的描绘与记忆,呈现出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里“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特殊乡愁意识。
有学者认为,现代作家的故乡书写呈现出肯定型认同与反思型认同两种乡愁形态,前者以沈从文、废名为代表,后者以鲁迅、师陀为典型[21]。张恨水的乡愁显得与众不同。张恨水笔下的乡愁游走在这两种故乡认同之间,显示出其乡愁书写的双重性。一方面,潜山的乡村社会与田园生活寄托了游子张恨水的故乡记忆,承载了他生命成长历程中的特殊情感与对故乡的肯定认同;另一方面,张恨水又能站在现代性的视角上冷静地回忆、反思乡村社会的弊端,在往返于城乡之后反思传统的乡土社会。
乡村与城市是近代社会转型的两极,背井离乡进入城市是全球性的社会运动。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谈及19 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乡村写作时指出,乡村的真实生活被新兴的城市文明与文学书写所遮蔽了[22]。与欧洲等国家自发性的现代化相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则更加曲折、复杂,乡土写作亦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景象。一方面,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与伦理秩序经过数千年的实践,顽强地证实了其存在合法性与适用性,直到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乡土社会中仍起着主导作用,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详细地分析了中国乡村中的熟人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外来的现代性以一种“后发”的姿态由城市向乡村渗透,大量的人口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生活空间的迁徙、转移形成了近代中国人的群体乡愁。特别是乡村中的青年群体,他们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乡村来到城市,往返于城乡之间的空间旅行使他们体会到了现代性对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挑战,重构了他们的故乡意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萧红都曾描写过故乡社会,但其故乡书写缺乏现代空间旅行经验的视角,鲁迅、师陀则深刻地揭示了乡村青年在进城、返乡后对故乡的反思与批判,就这点而言,张恨水的故乡书写更近于鲁迅与师陀对乡村社会的批判,乡村生活的真实体验使张恨水对故乡社会的认识与文学呈现更加现实、理性,更接近乡土社会的本原面貌。
张恨水笔下的故乡并不仅仅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乡下人”的书写与记忆,还以一个经历了现代都市空间体验的“现代人”来观察故乡,多年的报人生涯让张恨水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无论是上海、南京、北京、杭州、沈阳、重庆、成都等大型城市,还是他特意而为的西北之行,都使他能在丰富的空间旅行之后用一种更为全面的城乡二元视野来反观自己的故乡。在体验了现代都市文明以后,张恨水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故乡“离省城有七八十里,隔绝了一切城市上的物质文明”[11]123。这种空间距离形成了心理认同的差异,凸显了传统乡土社会文明与现代都市文明的紧张关系。小说《天河配》里的青年王玉和在北京求学、供职,回到故乡吃乡下的饭菜已“有些吃不惯”[11]125,玉和从北京带回故乡的媳妇桂英(在京是当红的京剧演员)认为“理想中的家乡,一定是和住西山旅馆那样舒服。不料到了家乡,竟是这样的不堪”[11]207。《似水流年》中的青年黄惜时看到家中仍以油灯照明,“立刻想到住在城市里,电灯是如何地光亮,而今在家里,却是过这样三百年前的生活”[12]4,甚至嫌弃自家厨房“不卫生”,嫌乡下人吃冷东西“不卫生”,总觉得“乡下物质不文明”[12]5,急着去北京求学,享受现代都市文明。
但张恨水又不是简单地赞颂都市文明、批判乡村的落后,而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空间差距中来评价乡村与城市的差异,“乡村人家,到处都露着古风,物质上的设备,往往是和城市上相隔几个世纪的。在城市里的人,总是羡慕乡村自然的风景,在乡村里的人,也总是羡慕市里物质文明”[12]3-4。
有学者认为,张恨水之所以“始终保持对‘安徽潜山人’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父亲亡故后再度回到过安徽潜山、经历过难忘的人生低谷有关”[23]。特别是张恨水成年后往返于城乡之间的空间旅行经历,使他能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体验、感知现代城市与故乡农村两种不同社会空间的差异,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经历了现代都市的空间体验与物质文明后重新全面地反观故乡,新闻记者的从业经历与对都市社会的深入探察也为他反观乡村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张恨水的记忆中,故乡并不完全是精神归宿的乐园,还是一个充满着偏见、功利的客观现实,他在青年时期到上海谋生未成,回到故乡,遭到了乡亲们的非议[24]。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张恨水写道:“辍学归里,闭户不敢出。因乡人认读书必作官或赚钱,不作官而耗财者,谓之曰败子。予向不与人作无谓之争,况在乡里,以是埋牖下,将家中所藏残篇,痛读一遍。”[25]在另一处回忆中张恨水则把这种切身之怨呈现得更为直接,“十九岁二十岁之间,我因家贫废学,退居安徽故乡。年少的人,总是醉心物质文明的,这时让我住在依山靠水的乡下,日与农夫为伍,我十分的牢骚,……二十一岁,我重别故乡,在外流浪。二十二岁我又忽然学理化,补习了一年数学。可是,我过于练习答案,成了吐血症,二次回故乡。当然,这个时候耗费了些家中的款子(其实虽不过二三百元,然而我家日形中落,已觉不堪了),乡下人对于我的批评,十分恶劣,同时,婚姻问题又迫得我无可躲避。乡党认为我是个不可教的青年,我伤心极了,终日坐在一间黄泥砖墙的书房里,只是看书作稿”[26]。张恨水家道的中落与事业的挫折,让他更清楚地看到了乡村社会的真实面目。这个乡土社会不是唯美的桃花源,而是一个充满了蒙昧、偏见的前现代社会。
张恨水以一个返乡的“城市人”的立场,将对故乡社会的体验、记忆与批判写进了小说里。《现代青年》中的农民周世良由于无法忍受乡下人的谣言与东家的算计,毅然卖掉了乡下的田地房产,被迫带着儿子周惜时离开了农村,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安庆城里谋生。《天河配》里乡下青年王玉和在北京带回一个唱京戏的女演员桂英,受到乡下人的非议,来自北京的桂英一看到乡下社会祭祖时的习俗,“还是执着前清那一派的老古套。这样的家庭,怎样安插我一个唱戏的女人”[11]234。最后他们二人不得不离开乡下到城市谋生,王玉和在临行前感叹道:“不是哥哥催我出去,也不是乡下人催我出去,只是这乡下传下来千百年的老风俗,逼着我不能不出门,到了现在,我知道旧礼教杀人这一句话,不是假的了。”[11]237
此外,张恨水还站在社会学家的立场深入反思乡村的社会结构,理性地看待乡村社会的人口结构与乡村治理方式,对于故乡的“族长式”基层乡村治理也有清醒的认识,指出了皖省乡村“支祠”中存在的“小族长”现象,“他们有一机构作为单位,就拿了这个作武器,上可以抗大族长、大户长,下可以统治一部分同族的忠实分子,对外也足以与外姓士绅周旋。至于不断的在公家白吃白喝,分调些公款,尤其余事了。……国人慎勿学皖中人士也”[27]。在回忆故乡、抒发乡愁的同时,又能理性地认识、批判故乡社会的弊端,为理解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是另一种“乡土中国”的叙述。
由乡村到城市,是现代中国转型的一个必经历程,张恨水本人及其笔下的乡村青年都经历了这一过程,张恨水的乡愁最终指向的是潜山乡村而不是安庆城,显然是他故意为了突出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往返于城乡之间的空间旅行以及在城市中的现代性体验是张恨水对故乡社会的批判重要参照点,因此,张恨水对封闭、传统的故乡社会的揭露与批判具有一定的启蒙意味。
然而,处于转型时期的乡村青年在经历过现代性的体验之后想再回到故乡已无可能,张恨水在青年时期的数次返乡都以不愉快地离开结束;《似水流年》中的王惜时在徒步旅行过大半个中国后失意地回到故乡,才发现乡村已经没有他生活的空间,最终不得不告别故乡外出流浪。张恨水以其记者的敏感,真实地记录了现代中国转型时期的乡土社会的真实境况,又以故乡之子的真挚书写了城乡空间旅行后的乡愁。
故乡,是一个人在空间旅行后形成的视角重影,是一个物理空间、心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相交融的符号。在现代中国,故乡所指涉的乡愁是乡土社会与现代都市文明的碰撞中形成的空间疏离感,是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有学者认为,张恨水的乡土写作能“如实反映乡村大环境中的农民个体和农民生活实况,甚至兼顾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心理的变迁,细致而入微,虽然并未触及灵魂本质,但也提出了城乡对峙等值得探讨的严肃问题”[28]。
对张恨水而言,书写故乡的意义不仅在于呈现了乡土社会的深层结构与排遣心中的乡愁,更在于在城乡之间旅行后所形成的观察故乡的双重视角,这种视角形象地再现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以及处于转型时期人的特殊境遇。讨论张恨水的故乡(乡土)书写,不仅为重新理解张恨水的创作提供了可能,也为重新理解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路径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