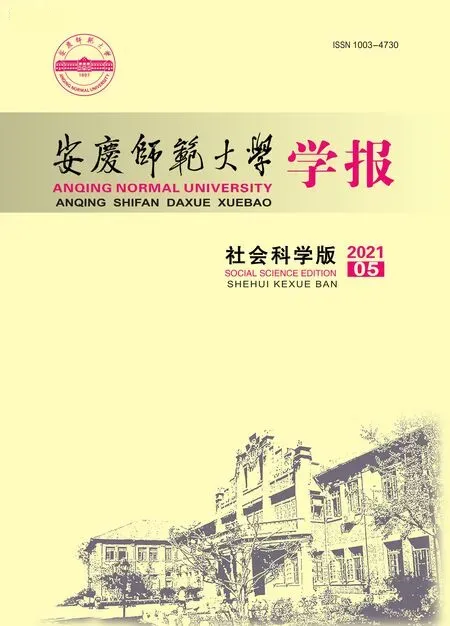帝国衰落侧面像:大英帝国运动会的兴起(1891—1930)
郭缅基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19世纪下半叶,随着各国工业化的推进,英帝国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增大,维系帝国的压力与日俱增。为加强帝国内部联系,将帝国凝聚成一股力量,帝国主义者进行过多种尝试。“帝国联邦”(Imperial Federation)的构想,是最为人所熟知的手段之一。但这一计划遭到各白人殖民地的反对,最终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这标志着以正式控制来维系帝国的想法已失去可能性。尽管如此,在帝国内部广泛存在的帝国情结并没有随着帝国政治联系的减弱而消失。即使进入20 世纪,帝国臣民对帝国的感情依然强烈而真诚,帝国主义者们愈发希望在政治之外寻找维系帝国的途径。
现代国际体育竞赛,为帝国主义情感提供了宣泄的途径。国际体育竞技具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其跨国特征下“国家”成为参与比赛的基本单位,其二是在国际竞争的基础上得以加强的身份认同功能。19 世纪末,英帝国主义者开始渴望通过体育竞赛来构建“想象的共同体”,一方面通过共同体来加强帝国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共同体来守卫帝国的稳定。1930 年,第一届大英帝国运动会的成功举办,正是这二者共同的结果。本文试图从宏观角度梳理19 世纪末到20 世纪30年代英帝国在面对国际体育竞赛时的态度与应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大英帝国运动会兴起的过程。
一、巩固帝国:大英帝国运动会的思想渊源
自19世纪末起,英帝国开始步入衰退期,但帝国范围内关于庞大帝国的想象仍然火热,对帝国的忠诚与渴望,支撑着英帝国主义者们企图通过“帝国”来塑造世界的理想。正如19 世纪末的英国首相阿奇博尔德·普里姆罗斯(Archibald Philip Primrose)所说:“既然这个世界可以按照我们的模式来改造,那么关注这个世界形成英国的面貌——而非他国的面貌,将是我们遗产的一部分。”[1]对于帝国主义者们来说,关于英帝国的想象仍有无限可能,而这种想象的可能性不仅为帝国主义者抒发自身的帝国热情和巩固非正式帝国提供了路径,也为大英帝国运动会的兴起提供了思想渊源。
在体育领域,通过运动会来展现身份认同并团结帝国,是帝国主义者狂热帝国情绪的一部分。帝国想象启发了帝国主义者们将运动会作为纪念帝国成就、巩固帝国联系的手段,其中,约翰·库伯(John A.Cooper)所发起的讨论最为典型。从1891年到1895年,库伯在《泰晤士报》(The Times)、《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以及《十九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等刊物上发表多篇旨在讨论团结大英帝国的文章,并在讨论过程中提出了举办“泛不列颠尼亚节”(Pan-Britannic Festival)的设想。在库伯的期望中,大英帝国乃至讲英语的民族将会引领世界的发展,“‘泛不列颠尼亚节’的作用在于为即将统治20世纪世界文明的英语民族提供联结的平台”[2]。而在库伯具体构想中,这场节庆将每隔四年举办一次,是帝国内部科学、人文以及体育的盛会,其将通过庆祝共同的经济与文化纽带来加强殖民地和母国之间的联系[3]。其中,一场汇集帝国内白人殖民地优秀运动员的运动会将成为节日庆典中最引人瞩目的项目。
这场关于帝国盛典的讨论在刊物上热烈开展,体育盛会的提议获得了广泛支持。讨论者将体育竞赛看作帝国内部交流、融合的重要途径,而帝国内部的竞赛也将是盛典中最能激发观众帝国情结的节目。在库伯的考虑中,这场运动会将囊括田径、摔跤以及板球等项目,其中板球是帝国内各殖民地与母国间交流最频繁的体育活动,也是最能体现帝国纽带的竞技运动[4]。可以说,“泛不列颠尼亚节”的重点就在于一场维系帝国团结的体育盛会。
作为一种巩固帝国的想象,库伯还有着更高层次的文化共同体追求。库伯关于体育竞赛的讨论乃是将古希腊奥林匹克式运动会作为模板。体育竞赛和身份认同的关系殊为紧密,早在公元前的古希腊社会,便有通过体育竞赛来加强共同信仰的尝试。“尽管在现实中必定存在消极的影响,但一般认为以‘奥林匹亚赛会’为代表的‘泛希腊赛会’,在加强古希腊民族认同和促进希腊人的内部团结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泛希腊主义’观念的形成,这是古希腊世界得以逐渐形成一个集体而区别于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5]库伯正是希望通过模仿,以“古希腊文明”为模板将帝国情结强化成一种基于文明认同的“单一民族”情感[2]。基于这种想象,库伯坚持“‘奥林匹克’计划必须囊括讲英语的‘种族’中的每一个部落”,并希望以同是“讲英语者”为由邀请美国运动会员参与运动会,其中美国将在泛大不列颠构想中充当“斯巴达”的角色,与此对应的还有英格兰的“雅典”角色[2]。库伯不以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来限定盛典的参与者,而是以一种共同的文化认同来赋予参会资格,在库伯的想象中,“它将使那些说着同样语言、继承着同样习俗的人保持亲情。”[6]
继而,库伯实际上提供了一种超越政治帝国的文化帝国主义理想,该构想以文化认同构建起一个以英国为核心的文明帝国,讲英语的种族将是该帝国的成员,该帝国对内包容开放,对外则封闭独立。这种包容性与排他性的矛盾构想,以“家庭”及“亲情”作为一种价值依托,展示了一个鼎盛帝国塑造世界的野心。由此,运动盛典将成为帝国热情传达的手段,而奥林匹克式的运动会则将强化“家庭”内部的身份认同,强化世界的不列颠尼亚特征。
然而,关于“泛不列颠尼亚节”的讨论最终落空,1894 年起,顾拜旦(Le 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所发起的关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讨论冷却了“泛大不列颠尼亚节”的热度,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运动会在顾拜旦的努力下被提上日程,世界性质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最终取代了英帝国性质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但举办大英帝国运动会的思想就此萌发,关于“泛大不列颠尼亚节”的讨论,其意义在于舆论及宣传上的影响。19 世纪末正值帝国主义竞争日益激烈的阶段,英国人认为体育在英国霸权的获得和巩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帝国主义者往往希望以体育为媒介,塑造英国统治阶级的能力、价值观和品格[7]。库伯的“泛大不列颠尼亚节”正是迎合了这一思想,突破了以板球、马球为代表的帝国内部体育交流模式,首次将帝国与综合性运动赛事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泛不列颠尼亚节”中关于帝国“家庭”的构想,这一构想将成为日后大英帝国运动会得以举办的思想基础。
二、守卫帝国:现实困境下奥运会与帝国的结合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所提倡的是一种世界主义,其初衷是增进国际间的体育交流,并将友谊、进步及和平等要素置于比赛的胜负之上。这种“重在参与”的主张十分契合英国传统中“为体育而体育”(Sport for Sports Sake)的“业余主义”(Amateurism)精神。但奥运会的举办受到政治的影响,奥运会在无形之中被各国赋予政治使命。20世纪初,随着世界局势紧张化,奥运会的竞争性加强。奥运会成了国家间相互竞争的非正式舞台,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奖牌数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衡量国家强弱的显性标准之一。
英帝国在国际体育竞赛上具备一定的优势,奥运会为帝国主义者们宣泄帝国情绪、表达帝国忠诚提供了空间。在早期奥运会中,英帝国各殖民地及其母国①母国(Home Nations)以联合王国的名义(最初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以及爱尔兰构成)出席奥运会,最初以“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为队名,后改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各有队伍,但在实际中的身份界限十分模糊,队伍成员的身份可以变动[8]。出生于伦敦的埃德温“泰迪”·弗莱克(Edwin“Teddy”Flack)在1896年的雅典奥运会上为澳大利亚夺得了800米和1500米两项比赛的金牌;英印混血的诺曼·普理查德(Norman Prichard)在1900年的巴黎奥运上为英国拿下两枚银牌;长期侨居加拿大的厄尼·韦伯(Ernie Webb)代表英国先后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和1912 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拿下3 枚银牌。宽泛的身份认定为帝国这个更大的共同体提供了想象空间,殖民地运动员所取得的成就被看成是帝国的荣耀。正如澳大利亚人理查德·库姆斯(Richard Coombes)所宣称,英国运动员可以在大多数项目上挑战美国,但“母国在短跑项目上尤其无力,在100码到880码的热门项目中大英帝国最需要帮助”,“澳大利亚将借由罗利(Stanley Rowley)的参赛来协助帝国,而加尔各答也将通过诺曼·普里查德(Norman Pritchard)来帮助帝国。”[9]
因此,在早期奥运赛场上,帝国与殖民地相互成就。其一,帝国是殖民地想象中扩大了的共同体,该庞然大物可以放大殖民地运动员所取得的成就,借此殖民地将获得帝国层面的自豪感。其二,殖民地也将奥运会看作检验殖民地发展成果的一大机会,奥运会的舞台就如同一个重要的现代化试验场[2]。殖民地通过提高自己在帝国中的作用来克服“中心-边缘”的窠臼,“落后的”殖民地对帝国的自豪感甚至比母国更为强烈。殖民地希望通过展示自己的发展成果来赢取世界的目光及母国的承认,同时展现自己独立的能力并借此提高自身在帝国中的地位。在此,殖民地与母国都渴望通过赢得国际体育比赛来展示帝国的霸权。
另一方面,奥运会对于英帝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尤其体现在英帝国的母国——英国在体育领域举步维艰的困境。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德国、美国快速崛起,英国则相对衰落。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狂热的煽动下,出现了英国种族正在走向堕落的悲观预感[8];在国际社会中,英帝国“日不落帝国”的地位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很快在国际比赛中占领一席之地。1896年举办的雅典奥运会中,美国获得了11块金牌,位居奖牌榜第一位,美国自此很少跌出奖牌榜前列。反观英国,由于体育传统中“业余主义”的影响过于强大,其系统化、专业化的训练并未及时建立起来。就如工业化一般,当真正进入国际体育领域,英国的体育“优势”很快就被“赶超”,这是因为其他国家也在逐渐积累经验,一旦这些国家在政府的直接援助下建立起自己的体育机构和风格,并摆脱了“业余观念”的束缚,那么英帝国长久以来地体育优势便荡然无存[7]。
英国对自身体育优势的丧失表现得后知后觉。直到1908年,伦敦获得奥运会举办权,英国对奥运的冷漠态度才开始转变[10]5。为了在奖牌榜上胜出,英国作为主办方偏袒本国运动员,比赛过程充满不公正判罚。其中,400米游泳项目和拔河项目中偏向英国的判罚直接导致美国选手的抗议和退赛。最终,英国如愿以偿获居奖牌榜榜首,共获得145块奖牌,而第二名的美国只有47块。然而,伦敦奥运会上的骄人成就并非真实的体育优势,“英国人对英美两国的运动实力对比感到不安。”[11]1912年的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英国人惨遭败绩,在奖牌榜屈居第三,落后于瑞典和美国。赛后,英国的失利被媒体解读为“一个国家的灾难故事”和“一个英国衰落的公共广告”[8]。英国业余田赛协会(The Amateur Field Events Association)的秘书韦伯斯特(F.A.M.Webster)甚至认为,英国已经衰落到“连欧洲小国都能打败的地步,而这些欧洲小国在过去几代人的时间里一直是我们体育休闲活动的学生”[10]121。
体育优势的丧失迫使英国向帝国寻求帮助,守护帝国成为一种需要。为了在1916年举办的柏林奥运会上赢回荣誉,帝国内部兴起了一场关于组建帝国代表队的辩论。早在1911年,理查德·库姆斯便提出建立帝国代表队的建议,他在悉尼《裁判报》(Referee)上发文声称:“这无疑是帝国典范——母国和她的孩子以及殖民地的力量一同汇聚在不列颠的海岸上以凝聚帝国之力,然后一同航行到斯德哥尔摩的战场,并在友好的竞争中挑战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8]库姆斯的提议得到不列颠奥委会(British Olympic Association)的关注,但最终因为资金短缺和时间紧急而不了了之。1912年奥运会上的败绩随即让这一计划重新浮出水面,要求培养专业运动员的呼声也愈益高涨。这一次,建立帝国代表队的想法得到了不列颠奥委会的正式讨论,并得到了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等公众人物的声援。
当讨论深入到实践层面时,帝国代表队的计划陷入停滞。其一,帝国代表队意味着殖民地代表队将被取代,并且必须成立一个由伦敦直接管辖帝国的统一组织,殖民地的自主性将受到损害。对此,加拿大业余体育联会(Amateur Athletic Union of Canada)主席詹姆斯·梅里克(James Merrick)不得不承认,在各殖民地中“国家身份(National identity)的认同是最强烈的,而将殖民地自己的运动员选送至帝国代表队的做法将难以维持这种认同”[8]。其二,必须考虑队伍人数问题。在奥运会的规则中,每个代表队对每一个项目可以派出12名队员。帝国代表队的计划虽然使运动员具有统一的身份,但同时也会限制代表帝国参与奥运会的人数。其三,不列颠奥委会并不具备在管理层面进行改革的决心。建立一个囊括母国以及殖民地的帝国组织并非易事,且奥委会并非政府组织,其改革缺少必要的资金。不列颠奥委会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向公众发起筹款,但结果惨淡。改革的资金问题直接宣告了帝国代表队计划的破产[8]。虽然1916年的柏林奥运会因为一战的爆发最终没有举行,但英国丧失国际赛事中优势地位的情况却已难以避免。
总之,20 世纪初的奥运赛事虽为英帝国展示自身实力提供了舞台,但同时也将英帝国拖入一个国际环境之中。英国在国际体育竞技上的虚弱,及其向自身帝国寻求援助的倾向,实际上反映了英帝国在面对国际体育竞争时的被动姿态。一种守卫帝国的需求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形成,帝国代表队的想法和“帝国联邦”的构想在思想上具有共同点,它们都是英帝国在面临外部压力时所采取的被动防守策略,其目的在于增进帝国内部的联系与团结,将非正式的帝国转变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以帝国的形态而非国家的形态来应对外部的挑战。帝国代表队计划的失败预示着英帝国在国际体育竞赛中难以凝聚力量。与此同时,国际比赛中的压力与日俱增,美国在国际体育竞赛中的优势地位逐渐稳固,相比之下英帝国的体育优势消失殆尽。奥运会所提倡的业余主义渐渐被专业性所压制,国际间的体育竞争日益激烈,这使得英帝国庞大的身躯愈加被动,但也为此后英帝国运动会的创办提供了现实需求。
三、回归“家庭”:大英帝国运动会的创立
20世纪20年代,英国面临着一个更加激烈的国际体坛。一方面,奥运会上竞赛的专业化趋势继续加强,奥运会的比赛规模和参赛规模也在持续扩大,而媒体和政治家的参与更加增强了奥运会的世界影响力。实际上,奥运会的兴起与发展在实际中迫使“不列颠世界”必须通过与其他国家竞争才得以维持其体育优势地位。英国作为一个重要的“体育国家”,由于奥运会而不得不接受外部势力进入其曾经主宰的世界[2]。自此,英帝国,尤其是英国在奥运会上的成败已经成为影响帝国正当性的一个因素:帝国必须在比赛中“维持统治”,否则帝国情结难以找到宣泄途径,而“被打败”则可能昭示帝国衰落甚至分裂的前景。
另一方面,美英之间的体育竞争日趋激烈,美国的职业体育优势威胁着英国传统的业余主义精神。美国利用自身体育优势确立了自己在国际体育竞赛中的强者地位,英国为了维护自身地位不得不接受“挑战者”的角色。在国际形式及国际力量对比的变换中,英国不得不接受转变,放弃19世纪以来经受他国挑战的姿态,主动去适应外部的体育竞技标准[12]。
国际比赛的职业化压力及帝国衰落的悲观预感是促成大英帝国运动会(The British Empire Games)的重要因素,奥运会的竞争性迫使帝国主义者另辟蹊径去寻找缓解压力之法。加拿大人波比·罗宾逊(Bobby Robinson)是大英帝国运动会的重要推动者。作为加拿大代表队在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的随队人员,罗宾逊在比赛期间感受到参赛者之间日渐增长的对抗性,认为现代奥运会所提倡的业余性已被遮盖。正是出于重提业余主义的目的及其对帝国的感情,罗宾逊开始着力去说服加拿大哈密尔顿(Hamilton)的市政官员,成功说服该城市为运动会提供场地及资金。同时,罗宾逊协助加拿大业余体育联合会组建了一个运动会的筹办委员会,其成员中既有成功的商人,也有卓越的运动员。这些社会公众人物积极发挥自己的影响,一方面既提高了运动会筹办过程中的热度,另一方面也作为游说团队,负责游说母国和各殖民地组织运动员到加拿大参加比赛。一则向公众筹集运动员旅行经费的公告道出了大英帝国运动会的举办动机:“如果大英帝国运动会能将母国与殖民地通过另一链条联结起来,如果它能在帝国范围内激励体育运动的发展,如果它能鼓励英帝国的青年男女形成真正的帝国精神——那么一切金钱和精力上的花费及可能遭遇的麻烦,都是值得的。”[13]最终,委员会成功地联结了帝国,甚至获得了英王乔治五世(George V)的赞助。1930 年8 月16 日,为期一周的大英帝国运动会最终在加拿大哈密尔顿举行,这场运动会为来自帝国内部11 个国家或地区①包括澳大利亚、百慕大群岛、英属圭亚那、加拿大、英格兰、北爱尔兰、纽芬兰、新西兰、苏格兰、南非以及威尔士。的四百多名运动员提供了展示舞台。
大英帝国运动会的思想渊源在于库伯的“泛大不列颠节”,但其呈现出一个收缩的取向,大英帝国运动会不再想塑造世界,而仅是团结帝国大家庭。虽然二者都强调维系帝国的联系,但库伯更多的是为了展示帝国的鼎盛与霸权,后者则是为了维持帝国的团结,是一种霸权的内向型展现。也正因如此,大英帝国运动会愈加突出帝国团结的“家庭”氛围。罗宾逊对此就曾表示,他“相信他在帝国运动会上提倡的家庭氛围将为比赛提供一个更为放宽松环境”[9]。大英帝国运动会的使命宣言指出:“它将被按照奥运会的模式进行设计,无论是在总体的结构上还是在对业余选手的定义上。但与奥运会不同的是,它将摆脱国际体育场馆所带来的过度刺激和过度竞争。比赛应该更强调快乐,而不在于严格,它们将用新奇冒险的刺激性替代掉国际竞争的压力。”[14]10而第一届运动会确实在多个方面减少比赛的竞争性,例如,在比赛的组织上,主办方明确规定参赛运动员必须证明自己是业余运动员,同时规定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个项目上只能派出一名参赛选手,以避免某一国家或地区在某一项目上的垄断[15]。在奖品方面,组委会在奖牌之外为每一位在比赛中“表现优越”的选手颁布“友谊证书”,以此弱化奖牌的重要性[15]。
此外,在正式比赛中,这次运动会的也突出了友谊的色彩及和谐的氛围。在比赛过程中,新西兰短跑运动员艾伦·艾略特(Alan Elliott)在两次起跑失败后本应失去比赛资格,但当全场观众逐渐注意到他伤心的神色时,观众们发出了巨大的噪音,以致下一轮比赛难以进行,最终裁判们准许艾略特重新回到比赛中。种种情况都表明这一场运动会的目的不在于名次,而在于享受体育比赛,在于为运动员及观众提供一种归属感。因此,这次运动会也被媒体们形容为“家庭聚会”“伟大的家庭派对”[12]。罗宾逊在总结报告中表示:“这次运动会的成果巨大,证明了帝国家庭中的成员是可以在比赛中碰面的”,“任何有幸能够观看这场运动会的人都将知道,它的整个过程是完美、和谐的——而且此间还能一种我在奥运会中无法寻得的比赛精神”[14]19。另有报告称赞此次运动会:“在哈密尔顿,只有不列颠人(Britons)参与其中,其中满了友谊的温暖、真挚甚至是无私的精神,这肯定会在不列颠种族的年轻男女中结出硕果。”[16]
总的来说,1930 年的英帝国运动会并不仅仅只是一场运动会,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像一场庆典一样宣告帝国的团结与稳定。这场运动会也是英帝国在面对他国日益明显的体育优势时所举办国际比赛,其目的在于避开奥运会上国际竞争的压力,为帝国内部的运动员提供一个强调业余性的比赛平台。大英帝国运动会的正面所展现的是对帝国的新想象,但其侧面却是不可扭转的帝国衰落趋势,运动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它举办过程中所彰显的特点,体现的正是帝国的收缩与防守。在运动会盛大庆典的背后,英帝国主义已不再具有使“使世界形成英国的面貌”的预设目的,它转而收缩成以“维持帝国”为目标。
四、结 语
1926 年,英帝国议会起草了“贝尔福报告”(Balfour Report),确定自治领具有和英国完全平等的地位,而且拥有对内对外事务的全部权力;1931年,英国议会制定了《威斯敏斯特法》(The Statute of Westminster),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自治领和英国具有同等地位,并享有完全独立的立法权。这两份文件的颁布标志着英联邦正式形成。但是,英联邦并不意味着帝国的终结。正是在帝国影响力不断减弱、帝国概念加速崩塌的这个时间点,英帝国运动会的举办证明了“帝国”作为一种想象的生命力。1932年,鉴于哈密尔顿英帝国运动会的成功,一个英帝国运动会联合会(The British Empire Games Federation)得以成立[12],英帝国运动会正式成为常设赛事。自此,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库伯他心目中帝国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设想。
虽然运动会的成功预示着帝国内部“非正式控制”的强大生命力,但其历史也见证了帝国在影响力上的衰落。大英帝国运动会的举办,表面上是帝国纽带的加固,但实际上只是大英帝国衰落的一个侧面像。从库伯的“泛大不列颠节”到哈密尔顿第一届帝国运动会的举办,帝国运动会的取向从塑造世界收缩为维持“家庭”。帝国的衰落并与解体,正是大英帝国运动会得以举办的重要原因。1954年,英帝国运动会更名为英帝国与英联邦运动会(British Empire & Commonwealth Games);1966年,运动会更名为英联邦运动会(British Commonwealth Games);1982年,运动会更名为联邦运动会(Commonwealth Games),沿用至今。进入20世纪后期,“英联邦成员国的增加与凝聚力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英联邦日益成为争吵、力量虚弱的代名词,到最后沦落为一个体育盛会。”[17]可以说,英帝国运动会名称变更的历史是一部去殖民化的历史,也是一部英帝国解体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