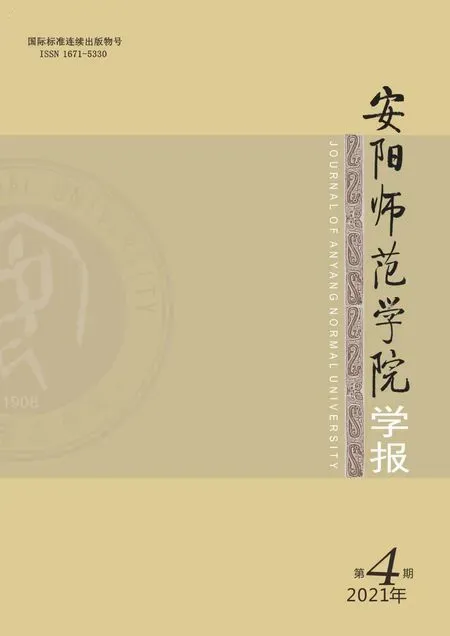师陀小说地域性探寻
——从《果园城记》的意象建构谈起
赵晓菲
(南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299)
毫无疑问,师陀所作《果园城记》并不刻意强调小城的所属地域,作品也并非特意对中原地方文化进行书写,甚至有意将果园城作为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正如师陀在后记中所言:“这小书的主人公是个我想象中的小城,……我从它的寿命中切取我顶熟悉的一段……凡我能了解的合乎它的材料,全放进去。这些材料不见得同是小城的出产,它们有乡下来的,也有都市来的,要之在乎它们是否跟一个小城的性格适合。”[1]但是,就文学创作而言,写作这一具有作家主体性特征的行为本身便包含潜在地域性因素的影响。
“在小说修辞的影响中,故乡文化始终是一种重要的因素,也许它本身只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凝聚了一地人们的智慧,所以,它也就成为生活在这一地域的作家的智慧主要来源,作家看待问题、思考问题难免会带上故乡文化的烙印,最终反映在他的小说创作上”[2],在此意义上,故乡之于文学创作如同“胎记”之于婴孩体肤。《果园城记》一定程度上显露出师陀故乡的中原传统文化特质和中原景观特征,也因此形成他创作风格的一部分。师陀对果园城意象的建构以故乡为参照并非有意,而是故乡中原文化环境、自然环境作用于他记忆、情感的结果,它们形成了作家在创作中的审美自觉。
一、地域·环境·意象
“中原”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在《辞源》[3]中,“中原”这一区域性的位置坐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其广义上的范围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狭义上是指“今河南一带”。根据地理层面的理解,中原作为一片特定区域,既存在着自然外观上的特征,也存在着因历史的特殊性导致的别于他地的文化形态和精神文化特征。“中原”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古往今来承载了中华文化重要一脉,生成独特的中原文化形态。
文学作品的地域性特征首先表现在作品对某地自然环境的刻画,例如北方边塞诗中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之粗犷,而南方风景则有“小桥流水人家”之淑柔;再如沈从文笔下山明水秀的湘西世界、萧红笔下冰天雪地的东北小城。其次,文学的地域性特征还体现在作品对某地人文环境的描述,如建筑、道路、雕塑等,都体现着标识性的文化内涵。“作家总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中,不能不感受到地域文化的气息。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渗入地域文化的因素,表现出地域性”[4]。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经典之一的《诗经》便是北方文学的代表,集中体现了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文学与地域景观、文化之间的精神与心理联系。
英国现代派诗人艾略特认为“一个著者的想象只有一部分是来自他的阅读。意象来自他从童年开始的整个感性生活”[5]。出生于河南杞县的现代作家师陀,在高中毕业前未曾离开过故土,这段幼年时期的生活与记忆参与构成了他对故乡——中原区域一角的初始影像。《果园城记》是师陀的代表作之一,可以说,这部作品通过对小城多个意象的建构,实现了他对一座中原小城印象式的虚构,也显示出师陀思想内潜在的地域意识。《果园城记》一面承载着其回望故土,对出生之地如婴孩恋母般的情感依赖,一面又携带着其对封建凋敝的以故园为参照的小城背后中原传统文化劣性的严肃批判。每一篇都凝聚着他对故乡河南既热爱又痛恨的复杂情感。无论是对“果园城”这座小城外形的想象还是对果园城百姓或善或邪故事的撰述,都打烙着师陀年幼时期的原乡印象与文化心理印记,这些都在小说意象群落的塑造中得以呈现。
二、小城意象的创建
文学作品中,意象不会独立于作者而孤立存在,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是作者储存于内心的富有人格化精神的抒情表意对象,它带有作家独特的创作特质,而地域性因素是构成作家创作特质的一部分。文学作品中的意象脱离了自身作为客观存在的单一性,成为包容作家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物,地域因素影响着作家对文学形象的塑造,因此意象也“不由自主”地蕴含着作家的地域性特征。英国作家大卫·赫伯特·劳伦斯提出文学创作中故乡之于自我表达的意义——每个人都有故乡,他们通过呈现故乡而进行自我表达,故乡各有不同,乡土精神对于每一个作家而言都是被内化的存在[6]。在与作家、作品结合之前,意象仅代表它自己——一项客观实在的物象本身。而没有以作家为精神主体的意象同样是无意义的存在。因此,作家对意象的选取便是其自我意图的表达,而在这一过程中,作者难以规避自身的原乡记忆和所携带的地域文化影响。作为师陀“精神返乡”之作的《果园城记》,植入了其对童年生活故地风物的记忆和地域文化的陶染,它们不仅是师陀进行自我表达的原动力,也是构成果园城意象集合的原素材。构成“果园城”意象集合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犬一猪,都蕴藉着中原故土对师陀记忆和文化的濡染。这些意象如情境背景般铺排在不同的故事情节里,为小说的叙述涂抹上一层浓郁的中原底色。
(一)建筑意象
“建筑的问题必须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因为建筑是在文化的土壤中培养出来的;同时,作为文化发展的进程,并成为文化之有形和具体的表现。”[7]如果一座城市的建筑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表现形式,那么地域文化作为城市文化的内容之一,也显示在这座城市的建筑群像中。在地理位置上,中原位于我国中部地区,位置相对闭塞,交通运输业尚不发达之时与外界沟通较少,形成相对封闭守旧的地理环境,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原人保守排外的文化心理。在文化上,中原是古都胜地,中国八大古都中的四都(开封、洛阳、安阳、郑州)都曾位居中原,因而中原文化包含着源远流长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内容,封建、森严的宗法与等级观念渗透在中原文化意识形态中。此外,宗教文化也是中原文化的组成部分,据历史记载,中原地区是佛教最早的传入地,佛教文化在中原地区影响广泛而深远。
果园城的建筑文化以中原文化为原型,它中原式小城的外在形象建立在这些建筑意象里,它封闭保守、枯槁凋敝、死气沉沉的内在性格也藏在这些建筑意象里:空洞少人的城门、复套幽深的宅第、蕴藉着痛苦与死亡意识的佛塔,构成“果园城”闭塞排外、等级森严又充斥着苦难与死亡的建筑意象集合。三个标志性的建筑意象象征着这座中原小城孤僻幽闭的文化性格、极权专制的尊卑思想以及生而苦痛的命运意识和以死为安的生命观。
1.城门意象:封闭保守的文化意识
瑞典学者喜龙仁在其著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这样形容城门对北京的意义:“城门可谓是一座城市的嘴巴,它们是这座容纳着五十万以上生命的城市得以呼吸和言语的通道。全城的命脉都集中在城门处,进出城市的所有生命、物品都必须经过这些狭窄的通道——不仅是人、车、畜,还有思想与欲望、希望与失望,以及婚丧仪礼所蕴含的生与死。在城门处,可以感受到全城的脉动,似乎整个城市的生命和意旨都在这些狭窄的通道中流淌——这种脉动赋予了这个极其复杂的有机体以生命和运动的节奏,而这个有机体的名字叫‘北京’。”[8]城门作为一座城市的交通枢纽是其经济和精神发展的动力源泉,它肩负着与外界沟通交流的重任,是一切新鲜的事物、思想、文化的入口,是实现城市与外界精神与物质交换、交流的中介,喜龙仁将城门比作一座城市的“嘴巴”,将城门看作一座城市能量的供给处,强调的是城门对物质、精神的输入意义。但是,果园城的城门却是一副萧条冷清的模样:“必须承认,这是个有许多规矩的单调而又沉闷的城市,令人绝望的城市。我走进深深的城门洞,即使把脚步尽可能放轻,它仍旧发出咚咚的响声。并没有人注意我。其实,我应该说,除开不远的人家门前坐着两个妇人,一面低头做针工,一面在谈着话的,另外我并没有看见谁,连一条走着的狗也没有看见。”[1]果园城的城门是孤僻而沉默的,这里没有车水马龙的门路,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没有人声鼎沸的闹市,甚至没有一条狗的出没,它“单调而沉闷”,不动声色地注视着城内的死气。它将一座城门沟通与输送的作用闲置起来,甚至生成与“沟通交流”完全对峙的另一个意义:封锁。果园城的城门将果园城与外界对立起来,使果园城形成一个被封锁起来的闭塞孤立空间。它排斥外来的新形式、新思想、新文化、新事物,也决不包容任何形式的进步与发展。《傲骨》中的年轻人接受了新教育,带着一腔热情希望为果园城注入新思想带入新变化,换来的却是全城人的打压和抵抗;《贺文龙的文稿》中抱有作家梦的贺文龙,被劳苦的工作、生活的负担拖累,它们磨灭了他的“希望、聪明、忍耐、意志”,甚至再看到自己当年创作的文稿,他的态度已然麻木,“在心里念着这些好像是一种讽刺”,这些当年满含抱负的文字变成了他“已经不能十分了解的文句”。果园城就是这样吞噬着一切新生的希望的种子,它只肯守着自己,享受停滞不前的现状,直到一代又一代果园城人在它悄无声息的脉动中老去、死去。
2.宅第意象:权力空间与尊卑意识
同样,作为封闭、保守、落后中原传统文化象征的建筑意象还有“果园城”的宅第——“鬼爷”的老宅和布政第,它们同时也是中原政治与制度文化中封建宗法、等级意识的体现、专制极权文化的象征。所谓宅第,指的是较大的居所,由房屋及院落两部分共同构成。旧时,能够拥有宅第的人群往往是仕宦家族。一座宅第体现着一个家族、一座城、一片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中原传统文化从哲学理念、政治制度、家庭伦理、审美标准以及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其布局、结构、形式和细部装饰……一系列大大小小、变化无穷的封闭空间,与屋宇等级化、院落的封闭性一起体现了宗法社会的礼制秩序,成为典型本土中国的象征”[9]。我国明朝实施“海禁”并修筑明长城,清朝闭关,拒绝与外界发生联系,长期的排外政策形成我国闭关自守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在建筑上体现为极强的封闭性和孤立性。中原宅第建筑跟随北京宅第建筑带有部分四合院特征,“中轴对称,左右平衡,对外封闭,对内向心,方方正正”[10],中原少水,因而宅第中较少以水为衬,“通常一个家族拥有一个大的院落,大院落由无数个小院落构成。根据尊卑长幼序列等级居住,有严格的伦理规范约束,院落布局非常严谨,具有封闭性,保守性,私密性,阶级分化强烈的特点”[11]。果园城“鬼爷”的老宅便是如此:首先是表示官级高大并安鸱尾的大门,大门洞里为雉门,雉门前为画屏,内为大堂院,左右两厢,中间是大厅,再进去,是一个完全相同的庭院,再往后还有三个院子,如此形成复套幽闭的空间领域。一系列阻挡视线的关卡将宅第外的空间与宅内隔绝起来,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门内,是一个暴戾阴鸷封建地主的极权场域,门外,是其伪善奸诈的“游戏”空间。一座宅第把一副罪恶的面孔遮掩起来,封锁着宅内一个封建专横的地主鲜为人知的残暴和凶狠。果园城另一座具有代表性的深宅大院是《三个小人物》中“久经尘封”的拥有一重一重房屋的布政第,它“高大阴森,没有人敢进去,也没有人想进去”。宅第是一个家族的法律,它体现着一定范围之内的政治文化和权力分布,它幽深森严,限制外界的窥视,拒斥除宅主外任何权势力量的进入,具有封闭排外的深刻寓意和权力分明的尊卑观念。
3.佛塔意象:痛苦意识与死亡符号
中国建筑中,塔常作为一地的地标式建筑,果园城的标志也同样如此。塔为佛教建筑,是佛教文化的象征实体。中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宗教文化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中原文化受宗教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影响深远,因而中原多塔。根据河南省宗教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李邦儒的研究,印度佛教最先传入河南,佛教文化最初在河南盛行并发展[12]。佛教文化是构成中原传统文化的一源。果园城以中原为坐标虚构而成,塔作为果园城的地标式建筑是佛教文化在师陀小说中的具体体现。塔的建筑形式来源于佛教传说:佛陀被弟子问及何以示忠心,佛陀不语,以方袍铺地,化缘钵倒扣于上,锡杖立于钵,形成佛塔最初的原型。塔为佛陀的涅地,蕴藉着印度人对灵魂深挚的关怀意识,因而以坟形为塔形[13]。佛教死亡观认为,世间众生存在即痛苦,一切生命不具有自主性,因而无常性是生命痛苦的根源。死亡则是对痛苦的逃逸,是终结痛苦的唯一途径。无论从佛教传说还是佛教文化所包含的痛苦死亡意识上来看,塔都有受难与死亡意项,因此塔可以理解为受难与死亡的象征符号。在《果园城记》中,关于佛塔的意象建构和传说寓意无不带有着佛教文化里的受苦受难喻旨和死亡意识,由此可见中原传统宗教文化对师陀的深刻影响。果园城的塔是无数可怜生灵痛苦和死亡的见证者,它降落在果园城是由于仙人一次醉酒后偶然的遗落,于是它看见果园城里被赌徒鞭打的妇女,被处死刑的无辜者,准备上吊的少女……塔的存在与果园城所有背负着痛苦和压迫的微弱生命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存在是为了见证他们的痛苦和死亡。在与塔有关的另一个寓意深厚的故事中,老员外的太太死了,三女儿的疯病也因闲眺时望到了塔,并被男巫解释为受困于塔里的狐仙,而最终换得安宁的方式是选择死亡,面对死亡时的三女儿在夜里不再疯傻,而是变得“很平静”。塔是见证老员外三女儿痛苦的开始,死则是对她痛苦的救赎。塔作为果园城的见证者,见证的不是果园城人民的幸福,而是“无数次只有使人民更加困苦的战争”“许多年轻人的死”还有“一代又一代故人的灵柩”——生来痛苦是果园城人无法逃逸的宿命,反抗命运的唯一有效方式是与生命告别,走向死亡,而塔在这里所行使的是见证与超度使命。
(二)自然意象
法国作家史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认为自然环境对作家风格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南、北方文学因自然环境的差异会形成不同风格[14]。南方大自然形象丰富,文学喜于将自然形象与人的情操相结合,北方因自然环境恶劣,人们缺少生活乐趣,文学则更善想象,有独立意识。在此意义上,自然环境不仅为文学形象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意象资源,也为作家提供了思维方式、创作内容、情感形式等创作要素,实际上,不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当它们作为艺术发现进入作家的审美视野之时,它们便已内化为作家创作的精神资源,经由作家的艺术构思,形成作家风格的一部分。文学作品中自然意象的书写不仅反映出作家自身的风格特色,还体现着文学的地域性——作为带有地域特色的风景的一部分。美国学者皮尔斯·刘易斯在《阅读风景的原则》一文中有言:“我们人类的风景是我们无意为之,却可触知可看见的自传,反映出我们的趣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渴望乃至我们的恐惧。”[15]通过建构中原地区的自然意象,师陀再现了故乡的特色风景——它们引导了小说的情感走向——在回望中热爱也在批判中痛恨。
1.河岸和草木意象
《果园城记》中不乏对中原特色风物的描绘,自然风貌丰富多元。果园城是师陀以位于中原地域的故乡为原型想象建构的中国小城,这里的景观没有诗情画意的小桥流水、蛙鸣蛇舞、山柔水秀,而是中原地区特有的苍黄色平野、堆积在路面上厚实的浮土以及偶尔漫走在路中间的一两只猪或者狗。间或在满是砖头与浮土间偶有的植物,也是近河处才野蛮生长的鸭跖草、蒺藜和蒿蓟。“中原”有自己的景貌,它地势平坦,微尘四浮,少雨多风。因而在师陀的果园城里,几乎不曾提及一个“雨”字。虽然师陀在“创建”这座“中亚细亚式”的小城时有意将它作为所有中国小城的代表,但很显然它与中国的众多小城相似甚至雷同的方面仅在于它们共同的“精神面貌”,如它的封建保守、凋敝落后等,或者说它与它们之间的相通之处仅在于神似,而非形似。在外观上,“果园城”有着自己的形态,在《塔》一篇中,师陀用近乎白描的手法概述了果园城的整体特征:果园城并没有什么名山,除去很费力地从山里运来的碑石,此外就连比较大点的石头都找不到,更不必说楼台湖沼之胜。它有的只是在褐色平原上点染几座小林,另外加上一两个破陀。可以看出,它的外貌以中原地貌为基础,尘土裹挟着路面,平野一望无际;家禽牲畜少见鸭鹅,多为牛骡鸡猪,更是没有鱼塘这类近江近海地区才有的景观,即便是在《阿嚏》中,老渔夫和小渔夫打鱼的水域也是中原黄河两岸地区多见的河湾。果园城是干燥与湿润并存的,它带有明显的中原地貌风格,风起而沙随,少雨却不少水,它的湿润来源于中原黄河水系。它是干瘪枯槁的,同时它又是丰润多姿的。师陀这样描述果园城的河岸风景:“你曾看见晨曦照着静寂的河上的景象吗?你曾看见夕阳照着古城野林的景象吗?你曾看见被照得嫣红的帆在慢慢移动着的景象吗?那些以船为家的人,他们沿河顺流而下,一天,一月……他们直航入大海。”[1]对于师陀而言,多姿的自然风光是之于故乡美好的所在。《果园城记》对这座中原小城风景的描绘占用了不少笔墨,可见故乡河南的自然地理风貌给师陀印象的深刻。这里有城坡上浓密的青草,羊羔会在细雨后的草地弄湿它们的腿,有从城外平原上升起的太阳、晨辉映着古塔、闪烁草间挂着秋毫的露珠、荒凉的河湾和招摇多姿的水草……一系列丰富多元的意象设置,呈现出中原地区绮丽多姿的风光景致和师陀对故乡中原地区的眷恋,更体现着师陀与中原故土深厚的精神和心理联系。
2.尘土与牲畜意象
虽然果园城美妙的中原景观时时出现在故事叙述中,但师陀最常提及的自然意象却是深厚的尘土和偶尔漫步路间的一只猪或一条狗。它们以类似暗示与象征意味的画面偶尔显现在小说的叙述情节中,与果园城的故事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仿佛没有果园城浮动的尘土和偶尔出没路间的猪狗,便没有这座小城生命的脉搏。相异于其他自然意象,小说对尘土与牲畜意象的描绘失去了鲜艳唯美的色彩和亮丽的形容,而是采用白描手法且仅用一两句话去塑造这两个单调的意象,并在不同故事中多次重复出现,显示出的是灰暗、无奈、压抑的情感氛围。如《果园城》一篇中描述城门之时,与空洞孤寂的城门相映的“满是尘土的大街”以及街岸上正在打鼾的决不叫唤的狗、吟哦着横过大路的猪,它们的出现作为孤立寂静城门的陪衬加剧了小说对果园城灰暗凋敝印象特征的塑造。再如,《鬼爷》中描写魁爷老宅所在的西门大街:魁爷住在西门里。一进果园城西门,我们的视线顺着宽广的,时时走过猪或狗的,浮土很深的,——永远很深的西门大街……以及魁爷赐死四姨太后,对果园城恢复往日平静日子的描绘:“猪照常安闲的横过街道,狗照常在路边晒暖,妇女们照常在门口闲谈……”[1]尘土与牲畜意象的出现,呈现出风波之后城内的压抑和死寂,果园城又恢复了往常的灰色。小说利用尘土和牲畜两个带有典型中原特色风貌的意象,勾勒出了果园城在封闭排外的地理、文化环境下压抑灰暗的精神轮廓。借助尘土和牲畜的灰色意象组合,师陀对故乡精神文化的劣性予以批判。
三、结语
《果园城记》以大量的笔墨塑造了果园城多个建筑和自然意象,折射出师陀创作中鲜明的地域风格特色。在众多意象的构建中,师陀对故乡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充分显现,通过对果园城意象的建构,作者一面在河岸草木这样来自中原特有的自然意象中建立作品的审美感受,追怀童年故乡,另一面也在城门、宅第、佛塔意象、尘土牲畜意象中开辟了审丑视角,形成与审美感受相对立的审丑空间,不动声色地将中原传统精神文化的劣性予以表现、予以批判。这些意象作为小说叙述的背景,不仅给作品打烙上鲜明的地域色彩,也成为形成师陀创作地域风格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