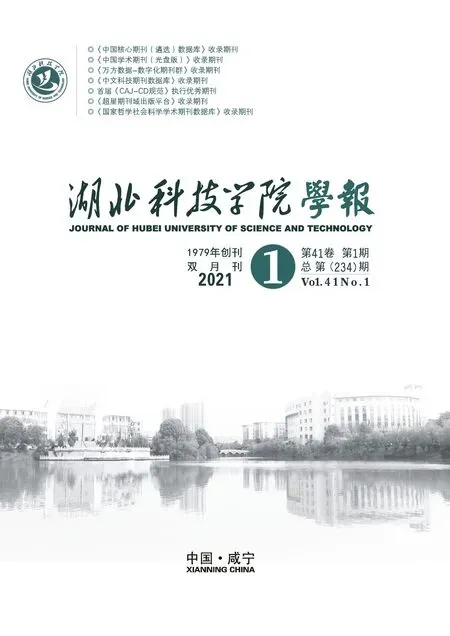论近代词人王允皙对姜夔词的接受
张 莹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0)
王允皙(1863—1903),字元辩,号又点,又号碧栖,祖籍长乐(今属福建),世居闽县亭头乡(今属福建连江)。清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应奉天将军依克唐阿之招为幕府,民国间任安徽婺源县知县,随后又入北洋政府交通部供职。[1](P1 602)著有《碧栖诗词》二卷。王允皙自少时便胸怀疏朗,好交游,与福州城内名士、学者过从甚密。允皙天资聪颖,极为喜好诗词,在诗词上下了苦功。友人何振岱曾提到,允皙近三十岁时就“诗境如登仙境,非人间之食烟火者所能道出一字”。[2](P105)其词最初学王沂孙(碧山),故自号“碧栖”,取栖心于碧山之意,一说取自唐人“问君何事栖碧山”之诗义。后又学张炎(玉田)、姜夔(白石),最终以姜夔词为归宿。
从题材来看,王允皙的词作中,恋情词、爱国词及咏物词占比较大,与姜夔类似;从词作的意境和词中的意象来看,允皙承继了姜夔词中的独特意象群,词境“绵渺新逸,如仙云袅空”[2](P105)。此外,允皙词也有意识地遵循着姜夔词所形成的范式——自度曲以及其经典化主题。姜夔词在清代浙西词派的推崇下,曾形成了一个接受高潮,浙西词人以“清空骚雅”为旗帜,大力模拟姜夔词写作,但效果却不太好。赵尊岳《填词丛话》卷三云:“词意极深挚而出以清疏之笔、苍劲之音者,白石当屈首指。原来笔苍不害情挚,而深入浅出,尤为词家之致义,唯运笔特难。千古词人,学白石多不可得,可以知之。”[1](P271)浙西词派诸人对“雅”的极致追求,使他们忽略了姜夔词中更重要的情感内涵。相比之下,王允皙对姜夔词的继承,兼顾了其词境的独特性与情感的真实性。从王允皙对姜夔词的接受情况,也可见出姜夔词对近代词人的深厚影响。
一、对题材的接受——恋情词与爱国词
词人作词,题材的选取十分重要。词的长短句特性使词适宜抒发一时之感,但这一时之感却并非情感,而是情绪。情绪是一时的,情感则与人的社会性需求有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深刻性。[3](P17)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允皙词在题材上与姜夔词的相似性,并不仅仅是王允皙的因袭,而是由于他们有着相似的情感体验。
(一)恋情词
有关合肥情人的恋情词在姜夔词中占比大约四分之一,包括《浣溪沙·著酒行行满袂风》《踏莎行》《长亭怨慢》《暗香》《疏影》等词作。这些恋情词中的情感源于一位女子,此女子是一位善弹琵琶的歌女,姜夔二十余岁时与她相识,二人都通晓音律,就此成为知音。但造化弄人,姜夔与女子最终分离。王允皙也曾有一段风流韵事,所遇是一位歌女,名唤雅仙。雅仙聪颖秀美,能琴善歌,也颇通诗词,允皙为之一见倾心,苦苦追求,终打动芳心。奈何歌女身份低微,两人在一起也历经许多磨难。[2](P107,108)允皙曾有一首五言律诗记其事:“已放杨枝岁,偏迎桃叶时。若非见颠倒,反谓得支离。四面纵君看,寸心不自移。尊前如再问,暂笑总强悲。”[2](P108)其中“杨枝”“桃叶”均指代所爱歌女雅仙,语意真挚淡远,诗中满是哀伤之感,可见允皙用情之深。姜夔与恋人最终分离,而允皙与恋人的结果看似圆满,却也免不了生离死别,允皙临终前,仍不忘挂念雅仙,以三千金遣之。二人相恋之人皆是歌女,恋爱之艰难自不必说。这也造就了两人的恋情词与其他恋情词的不同。自花间以来,恋情词就难以脱离“艳”的窠臼,北宋更甚。而姜夔的恋情词则脱离了这种传统的俗艳格调,这不仅在于姜夔用字用词的雅化,更在于其内心难以言明的深挚感情。[3](P21)且看其《浣溪沙》[4](P25):
著酒行行满袂风,草枯霜鹘落晴空。销魂都在夕阳中。恨入四弦人欲老,梦寻千驿意难通。当时何似莫匆匆。
词人喝了些酒,略带酒意在原野之上奔走,秋日寥廓,举目远望,枯黄的草木一眼难以看尽,草原之上,一只苍鹰正从高远的晴空中飞向原野。词人就在这一片苍茫的天地中,由景生情,在夕阳中感受到了冉冉的忧伤,人与宇宙已然融合在了一起。然而天地高旷,景色壮美,词人却在此间感到“销魂”,“销魂”二字便引出了下片——词人真正的作词意图。“恨入四弦人欲老,梦寻千驿意难通”一句,对面着笔,想象身在远方的恋人对自己的思念。“四弦”指琵琶,远方的女子弹着琵琶思念情郎,沉重的思念也好似要催人老,即使在梦中,魂魄飞过千驿也难以寻到郎君以诉衷情。“当时何似莫匆匆”,此句应是词人感慨,痛恨自己在离别时太过匆忙,而今相距甚远,再难一见。
再看王允皙《浣溪沙》[5](P1 604):
别梦凄清记未全,含啼人坐绿窗前。自家赚与自家怜。无力层楼休更上,夕阳如水水如烟。好春只在夕阳边。
允皙在词中采用了与姜夔类似的表现手法,将隐含在心中的情感借梦的形式予以表达。词人做了一个有关离别的梦,一朝梦醒,梦中何景已经记得不太清明,唯有凄凉之感萦绕心头。细想,居室窗前,仿佛有一女子,泫然欲泣,正是词人的爱侣。此处亦是对面着笔,而允皙更添妙思,字句皆是梦中所见,景虚而情实。下片转回词人视角,一梦过后,词人对爱人的相思之情更难以压抑,想要登高望远,却无力更上层楼。辛弃疾有词曰:“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词人苦于相思,自然不会同少年一样无忧无虑,即使登上高楼,所见也只是满含凄凉的夕阳之景。水色与天色渐渐混融,词人也好似在夕阳尽头看到了爱侣的故乡,“好春只在夕阳边”与姜夔“销魂都在夕阳中”同用“夕阳”意象,前者却略微地中和了夕阳的哀伤之感,虽然不知何时能够相见,可词人仍旧期待着重逢之日的到来。
两首《浣溪沙》相比较可看出,两位词人有相似的情感体验,使他们的艺境都透着凄清而又淡远的意味。允皙作为后人,其《浣溪沙》一词,上下片皆笔无虚设,情与景之层层递进,浑然一体,虽然沿用了姜夔的“夕阳”与“梦”的意象,却也有其创新之处。两首词的结尾句也略有不同,一放一收,允皙末句虽不及姜夔余味悠长,但收住了词中的凄凉之感。
(二)爱国词
王允皙与姜夔所面临的家国遭际也十分相似。姜夔一生主要活动于南宋中期,面对南宋朝廷苟安于江南的做法,姜夔同当时其他文人一样,内心愤恨不平。奈何仕途不顺,姜夔无法入朝为官,一生浪荡江湖,布衣终老。即便如此,姜夔仍在词中表达了他的家国之悲和对盛衰兴亡的感慨。如《扬州慢·淳熙丙申至日过扬州……》一词[4](P1):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姜夔在小序中说明了此词的写作时间,即“淳熙丙申至日”,词人路过扬州,看到扬州城在战火摧残下,“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悲从中来,感叹不已,自度此词以抒发黍离之悲。[4](P3)“淮左名都”便指“扬州”,词人见到今日扬州,不禁想起扬州城曾经是令人神往的名城,而在“胡马”的铁蹄践踏之下,只剩下“废池乔木”,词人此处将环境拟人化,借物寓情,实则表达自身对战争的痛恨之情。上片以扬州昔日之草木青青,与今日之黄昏迟迟作对比,下片则以昔日之繁华与今日之冷落作对比。同为南宋时人,若把姜夔与辛弃疾、陈亮等豪放词人进行对比,便可见出其爱国词的独特之处。他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呈现其爱国情感,不甚激荡,却含蓄而有余味。
王允皙的爱国词承继了这一点。允皙生于清末,当时战乱频频,国家危在旦夕,允皙也曾经历甲午海战和庚子事变,面对国家衰弱的境况,允皙悲愤难当,词中常有无力报国的感慨。与姜夔一样,允皙的爱国词很少纪事,而是通过今昔对比,抒发兴亡之叹与黍离之悲。词人将浓烈的爱国情怀在心中反复沉淀,在词中缓缓流出,因此少了一份激昂,多了几分凄凉。如《八声甘州》[5](P1 608):
又黄昏胡马一声嘶,斜阳在帘钩。占长河影里,低帆风外,何限危楼。远处伤心未极,吹角似高秋。一片销沉恨,先到沙鸥。 国破山河须在,愿津门逝水,无恙东流。更溯江入汉,为我送离忧。是从来、兴亡多处,莽武昌、双岸乱云浮。诗人老、倘题诗句,莫寄神州。
这首词作于庚子(1900)五月,正是八国联军攻华之时。当时,允皙旅居天津,与战争发生地距离很近,可说是亲身经历,感慨万千,便以此词寄予友人郑孝胥。[5](P1 608)夕阳西下,余晖透过幕帘洒入内室,面对夕阳之景,词人耳边仿佛响起侵略者兵马的嘶鸣声,看着这风光尚好的高楼水影,心中却浮起哀伤苍茫之感,只因那战争的号角由敌人吹起。允皙学姜夔的手法,在上片中以景抒情,又加之声音意象,声与景的结合,使词中的悲感更甚。“一片销沉恨,先到沙鸥”与姜夔“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有异曲同工之妙,并非是沙鸥先感到国家衰没之痛,而是词人自己。这首词为寄友人词,词人望着滚滚东逝的流水,希望它能永久安宁地流淌下去,直至入汉江,将自己的担忧寄至友人。末处又回转到自身己老而难以报国的现实。
同样的家国际遇使两位词人有了相似的作词感触。国破之恨,家国之忧皆以平淡的字句于词中流出,因此词境也颇为相似。两首词的独到之处都在于情景交融的笔法。赵尊岳《填词丛话》中云:“情景杂糅之作,所见者景,所动者情。以有所见,方有所思,以有所思,遂似更有所见,益生其感叹之致。故作此等语,以质实写景,以清空言情者,初乘。以清空写景,以质实言情者,中乘。并此清空质实之笔,低回感叹之情,寓之于字里行间,而不必一一明述者,上乘。若更超空言之,写景而不嫌其质实,言情而不涉于蹈虚者,斯为无上上乘。”[1](P245)这种笔法在允皙的其他爱国词中也有体现,如《水龙吟》中“地冷无花,城空多雁,斜阳千里”,寥寥几句,既呈现出了末世之景,又是字字血泪,使人为之伤感不已。
二、对意象的继承——“冷”与“梦”
(一)“冷”意象
宋代张炎推尊姜夔,《词源》中称其词“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自此,“清空骚雅”便成为了姜夔词的代表性评价。而其中“清空”之特点,与姜夔词中善用“冷”意象是密切相关的。姜夔词作八十多首,其中明确使用“冷”字的有十一首,更有许多带有清冷意味的意象遍布其词,如“清角”“暗雨”“春寒”等。姜夔将这些带有冷意的词语融入到自己对于环境及事物的独特感受中,就形成了其词凄清空寂的风格。[6]姜夔词中“冷”字的运用,通常与通感的手法相配合。如《忆王孙》中“冷红夜夜下塘秋,长与行云共一舟”,这首词为怀友人、伤漂泊之词,词人以“冷红”开头,既点名了季节,将枫叶称为“冷红”,便有了对秋日的“悲寂寥”之感,下句写自己与云同行、漂泊不定的生活,也与“冷”字相互映衬。再如恋情词《踏莎行·燕燕轻盈》,此词是姜夔为合肥情人所作,其中“离魂暗逐郎行远”一句,写深爱郎君的女子苦苦相思,甚至魂魄离体只为追随郎君,然而紧接便是“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深情至斯,女子却仍旧寻人未果,淮南千山在凄清的月光下,显得那样冷寂,魂魄就在这凄冷中独自归去,词人的情感在“冷”字下显得极为深刻。
王允皙明显继承了姜夔对于“冷”意象的偏爱。从数量上看,他的四十九首词中就有十处运用到了冷字[1](P1 602~1 611):
《满庭芳》:“何日归来散发,人间事、露冷风清。”
《水龙吟》:“地冷无花,城空多雁,斜阳千里。”
《迈陂塘》:“算略似飘零,寒炉醉卧,酒味变凄冷。”
《壶中天》:“樱笋韶光都过了,冷落衣篝香气。”
《木兰花慢》:“料试衣未妥,晕妆还懒,鬓冷倚蝉。”
《长亭怨慢》:“记风外、瘴花红冷。”
《琵琶仙》:“红渐冷,枫心未损,倩越娘、淡写裙侧。”
《疏影》:“画里危亭,山冷花迟,不见逋仙行迹。”
《西子妆》:“冷襟怀、洒北来冰雪,吴儿争辩。”
《念奴娇》:“白首心期,青山世业,梦冷承平后。”
从“冷”字表达的情感上来看,由于一生漂泊,情无归处,姜夔对于人生的孤独感和凄凉感体会颇深。因此他用“冷”字既可营造清疏的诗境,也可侧面表达自己的孤独失意。相比之下,王允皙辗转各处做官,常有漂泊之感。如《壶中天》写词人夏日寓居别处,怀念与恋人相处的春日,云:“樱笋韶光都过了,冷落衣篝香气。”[5](P1 605)春日已过,词人与恋人分离两地,伊人不在,自然“冷落”,词人实是借“冷落衣篝”表达自己内心之“冷”。类似的还有《满庭芳》:“何日归来散发,人间事、露冷风清。” 在不同的情境下,王允皙词中“冷”字的意义也略有不同。《水龙吟》下有序云:“甲午十月,辽沈边报日急,偶过琴南冷红斋闲话,感时忆旧,同赋。”[5](P1 604)词人收到甲午海战的消息,痛惜焦急之际,回想自己与友人林纾曾立志报国,感慨万分,于是词中有“地冷无花,城空多雁,斜阳千里”之语,这是词人想象中遭受侵略的景象,大地一片冷寂,不见草木之色。“城空多雁”有万民流散之意,“空”与“冷”虽意义不同,却相互映衬,使冷意更浓。
(二)“梦”意象
姜夔作词极为擅长追求混沌模糊之美。即使是恋情词,姜夔在表达心迹时也常常是虚实相生,借物寓情。他的词中总有一种朦胧的意境,并喜欢通过对梦的描写来造就这种意境。[6](P22)如《鬲溪梅令》中“木兰双桨梦中云”一句,叙词人与合肥情人别离相思之苦。词人另辟蹊径,全词本就是想象语,此处更是想象叠加想象,词人遨游在自己创造的梦境中,想象着与爱人共乘一舟,恍若在云间穿梭。又如《江梅引》:“几度小窗幽梦手同携。今夜梦中无觅处。漫徘徊,寒侵被,尚未知。”[4](P121)在此词中,词人“见梅枝,忽相思”,想到可以入梦见之,稍感安慰。谁知这一夜的梦中没有寻觅到爱人,只得独自徘徊,比《鬲溪梅令》更添一层悲情。
王允皙对姜夔独特的造境手法自然也有所继承,尤其是对“梦”意象的继承。“梦”字在允皙词中出现了二十次,频率很高。如《浣溪沙·海棠花下作》[5](P1 602):
叶底游人不自持,枝头啼鸟尚含痴。玉儿愁困有谁知。 浅醉未销残梦影,薄妆原是断肠姿。人生何处避相思。
词人于观赏海棠花时触及相思,想象远方的爱人也像自己一样饱受相思之苦。下片词人因相思而借酒消愁,睡梦中与爱人相逢,虽未实写梦境,却以“薄妆原是断肠姿”一句表现出梦境的美好与现实的残酷,得见佳人“薄妆”本是欣喜,一朝梦醒,佳人化为泡影,所以感觉是“断肠姿”。一句之中即由梦境转为现实,比姜夔《鬲溪梅令》末句“漫向孤山山下觅盈盈。翠禽啼一春”的转折更为隐晦,也独有其妙处。与姜夔不同的是,允皙仿佛十分热衷于记残梦,再如《浣溪沙》中“别梦凄清记未全。含啼人坐绿窗前”一句,同样强调梦境的残缺未全,能够忆起的也都是爱人身影。这应是允皙对姜夔记梦手法的发展。梦境本来虚幻,词人梦醒之后,那些梦中的场景情形都已经模糊,唯有爱人身影被词人牢牢记住。情之深挚,在此处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对范式的延续——自度曲及其经典化主题
姜夔精通音律,善用乐器,也能度曲。在他近百首词作中,有沿用前人词调的词作,也有自己独立创作的自度曲。姜夔自度曲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是存有工尺谱曲谱的自度曲,共十七首。其中多数无所依傍,为姜夔原创。如《扬州慢》《长亭怨慢》《暗香》《疏影》《惜红衣》《角招》《徵招》等;第二种是未留下曲谱的自度曲调,如《琵琶仙》《一萼红》《八归》等;第三种是在以往词调上改变某些因素而成的新调,如《平韵满江红》,姜夔将原本用仄韵且用入声韵的《满江红》改为平韵,以协声律。[7](P64)王允皙对姜夔自度曲的接受度非常高,沿用白石韵的词作也很多。陈兼与《读词枝语》中云“(允皙)长调多填琵琶仙、长亭怨慢、疏影诸调,知其服膺白石也”[2](P93)。允皙四十九首词中,直接使用姜夔自度曲的有九首,分别为《长亭怨慢》三首、《疏影》两首、《徵招》一首,未留曲谱的《平韵满江红》一首、《一萼红》一首、《琵琶仙》一首。
在姜夔以前,创作自度曲的词人也很多,如柳永、周邦彦等,各人自度曲也各有特点,柳永擅度慢词,周邦彦则精于协律。姜夔自度曲的特点在于:他在词格上提供了一个可接受的学习范式。在他的自度曲中,他进一步拓宽了词序的功能,使词作的题、序、及正文相互联结,构成整体,且秩序井然。因此,他的自度曲所提供的不仅是曲谱,而是包含了题、序、词、曲四部分。[7](P66)从宋代词序的发展史上来看,北宋词人张先用题序将日常生活引入词中,给词序增添了叙事性,后来苏轼等词人也用题序来交代创作缘起和背景,姜夔在沿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将词序与曲、题、正文紧密结合起来。如《惜红衣》序云:“吴兴号水晶宫,荷花盛丽。陈简斋云‘今年何以报君恩,一路荷花相送到青墩。’亦可见矣。丁未之夏,予游千岩,数往来红香中,自度此曲,以无射宫歌之。”[5](P38)此自度曲中的“红衣”即指荷花,词人在序中提到游赏之事,这是词的创作缘起。后引陈与义《虞美人》词句,这是叙述词的情思起源。前后数语铺写景致,既创造了正文的情致取向,也对正文中的虚写做了实景的补充。如序中写“荷花盛丽”,正文中又写“虹梁水陌,鱼浪吹香,红衣半狼藉”[4](P38),正应词调“惜红衣”怜惜美人迟暮之意。这种序、题、词相伴相生的构造,是姜夔的独创,《暗香》《疏影》《长亭怨慢》等其他自度曲中也运用了这种构造。
允皙在追和姜夔的自度曲时,也承继了这样的作法。如《疏影》[1](P1 608):
余以光绪丙申年归自塞外,信宿湖上,孤山梅侯已过,嫩叶青青。亭舟草际,光景奇丽。己亥冬日再至,独登巢居阁,老柳慌波,萧廖满目,俯仰不能无感。适迪臣太守以《孤山补梅图》属题,用石帚自制调写之。
涟漪数尺。浸翠微雁影,凉思堆积。画里危亭,山冷花迟,不见逋仙行迹。诗翁此意无人会,自斩遍,苍寒苔壁。问旧时、春在谁家,总有断云知得。 堪笑当年倦旅。卧枝看未足,关上吹笛。万里归来,身世悠然,换了西冷愁碧。湖鸥不管人情怨,但劝我、重摧吟笔。又怎知、明日经过。漠漠半蓬香泣。
王允皙《疏影》序中,写其两次赏孤山之景,都错过了梅开时节,见到《孤山补梅图》,心有戚戚,于是用《疏影》原韵作之,也是咏梅之作。这里允皙不仅继承了《疏影》咏梅的主旨,序的形式也沿用了姜夔词序的构造,情、事、景皆备,与词作其他部分构成整体,不可分割。上片从描绘图中景象转向抒发自我的孤独失意之感,下片把孤山意象与自我情感结合起来,具有多重指向。这也类似于姜夔《疏影》。两首词皆主旨不明,可能是怀念恋人、寄托国事、追念旧游多种情感的多重表达。允皙的另一首《疏影》,则有所突破,在咏花的基础上将咏梅置换为咏菊,亦有其味。允皙在使用姜夔自制调时,不仅延续了姜夔词“序-题-词”为一体的形式,还借重了其词作的先验情境,引起读者关联想象,再用自作词的独特性抒发自我的情感,文本就有了多层意蕴,引人入胜。
四、结语
王允皙作为近代词人,其词作以其艺术成熟度在近代词坛占有一定地位。王允皙受清代浙西词派影响较深,其词作经由学王沂孙、张炎词,最终归于姜夔词。王允皙对姜夔词的继承和接受体现在多方面。第一在于对题材的接受,王允皙的恋情词和爱国词在其词作中占比较大。第二在于对意象的继承,尤其是“冷”意象和“梦”意象,王允皙学姜夔,善于用意象制造清空、幽雅的词境。第三在于对姜夔自度曲的学习,王允皙喜用姜夔原创的曲调作词,借其主题和情境出之,也时有创新。王允皙对姜夔词的接受,抓住了姜夔词的精髓,即情感的真挚与语言的苍劲。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浙西词派的缺点。从王允皙的词学实践可以看出,近代词坛对姜夔词的接受已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