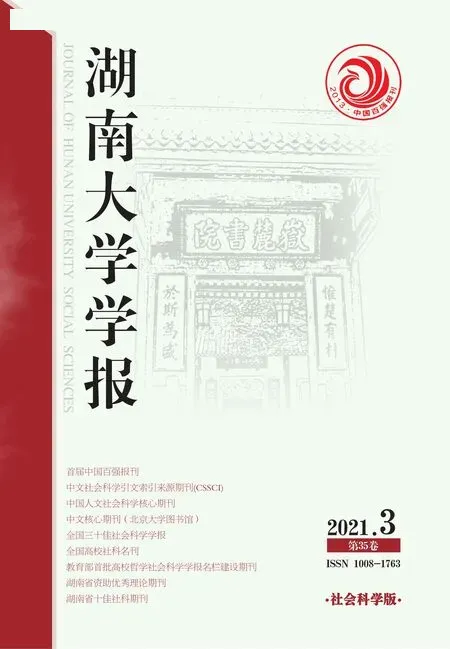关于“一分为三”与辩证法*
周 德 义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南 长沙 410008)
众所周知,只有名实相符、恰如其分的概念才能够涵盖与之相关的所有内涵和对应表达事物相关的所有规定性。因此,在本体论的研究中,我们说存在者不是存在而仅仅包容种种具体的存在物。存在与本体都是有层次的,合理合法的有之概念的存在可以终结认识历史中的所有存在物。
关于辩证法的认识正是如此这般的。在人类漫长的认识历史进程中,代表不同文化的哲学及其哲学家曾经对于辩证法皆有过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彼此拥有差异的理论阐释,大家总是意图从不同的理论概括中寻找到对于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准确而全面的描述。
一 辩证思维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
辩证法是西方哲学创造的名词。在古希腊哲学时期,“辩证法”一词较多见于柏拉图的著作中。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也是西方古典哲学辩证法大师。亚里士多德创立形式逻辑,黑格尔发现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
在中国哲学中,“辩证”的“辩”字,为会意字,从“言”,从二“辛”。“言”者,争辩也;“辛”者,可以理解为言词相向的对手,表示“辩论”“争辩”的意思。《墨子·经上》云:“辩,争彼也。辩胜,当也。”意思说,围绕一个问题进行争辩,是为了分清对错,也就是辩论求证的意思。
所谓辩证法,是指用全面、发展和变化的目光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也是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与规律的方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说过,辩证法的宇宙观就是用联系的、变化的、运动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去看世界。
辩证法是运用变化发展的理念研究事物存在、运动和变化发展的理论。而辩证思维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将对象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经过对事物内在矛盾运动、变化及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进行考究,从本质上系统地、完整地认识事物。
辩证法认为,宇宙世界是从无到有的,是统一的,也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即中国哲学称之为“道”不断地变化发展的。无论是中国的哲学家,还是欧美的哲学家,无不认为世界万物有着共同的起源,这个本原可以用高度抽象的“一”来表示。因为世界是一,所以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同一的。也就是说,事物具有无限可分的性质,或者说事物是“一分为多”的。
在研究事物系统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不难推导,本原作为一种原初的存在,必然具有一种特性,它可以进行自我复制,即自己制造自己、自己肯定自己、自己依据自己。唯有如此,它才能够成其为本原。而其他一切的东西,都是由它制造的,被它肯定的。也就是说,只有本体是作为其他东西的依据而存在的。或者说,只有本原是永恒的存在,其他的一切存在者都是由它化生出来的;只有本原是无限者,其他的一切都是有限者。譬如,《易经》所说的“易”“太极”,老子的“道”“无极”,孔子的“仁”,子思的“诚”,孟子的“心”……都是具有这样意义的本体存在。
如果运用现代哲学话语系统,我们可以从系统本原“A”出发,经过辩证“易”化过程,可以揭示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种种可能性。
首先,我们设定本原为“A”——它既相当于西方哲学所指的“上帝”(他们所说的上帝并不一定是宗教意义上的上帝,而是哲学意义上的上帝),也相当于老子哲学的“道”、“程朱理学”的“理”、“陆王心学”的“心”本体等,无非是一个绝对者意义上的存在,因为唯有在绝对者之内,一切存在者才能得以显现出来。
第一层次(或层级):本体“A”的内部必然地发展异化为“A”与“非A”即“B”。其中,“A”与“B”只是符号而已,其“A”中有“B”,“B”中有“A”。本原的“A”与下一层次的“A”“B”都只是符号而已,三者均具有共同的本质(可以用a表示),其中本原的“A”可以用aa表示;下一层级的“A”也可以用aa表示(说明本原具有自我复制的能力);“B”则可以用ab表示,从而形成第二层级或者新系统“AB”;
第二个层次(或层级)或者新的系统即是“AB”系统,其中的“A”内含有“a”,“AB”内含有“ab”,系统内部通过相互作用,产生出与“AB”相应的“C”,形成第三层级或者新的系统“ABC”;
第三层次(或层级)或者新的系统“ABC”。在“ABC”系统内部“AB”内含有“ab”,“ABC”内含有“abc”,系统内部通过相互作用产生出与“ABC”相应的“D”而形成第四层级或者新的系统“ABCD”;
第四个层次(或层级)或者新的系统“ABCD”。在“ABCD”系统内部“ABC”内含有“abc”,“ABCD”内含有“abcd”,系统内部通过相互作用产生出“ABCD”相应的“E”而形成第五层级或者新的系统“ABCDE”;
第五层次(或层级)或者新系统“ABCDE”,在“ABCDE”系统内部“ABCD”内含有“abcd”,“ABCDE”内含有“abcde”,系统内部经过相互作用产生出与“ABCDE”相应的“F”而形成第六层级或者新的系统“ABCDEF”;……
这里需要指出,在本体的整个发展变化的系统里,每个层次(或层级)内部的A、B、C、D、E、F……及其相互之间所表达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逻辑关系,因此称之为逻辑层次;而在A、AB、ABC、ABCD、ABCDE、ABCDEF……每个层级之间所表达的是事物发展的价值关系,所以称之为价值层次。正如我们所命名的“第一层次(或层级)”“第二层次(或层级)”“第三层次(或层级)”……无论是层次内部的变化,还是层次之间的变化,都是事物内部对立面之间的矛盾斗争和谐统一的结果,其中不仅有“形”而且有“势”。问题通常不能在同一层级得到解决。
作为理论构建,如果我们设定“心”为本体“A”,那么人心本善,有心地善良必然有心地非善(如歹毒);心善必然具有爱心;有爱则有非爱(如恨);爱恨情感产生憎恨和爱恋,相继又会产生美丑、真假的概念,词语之间因为相互关联而产生出概念的系统。
哲学的基础是概念。理论系统的基础是概念。由概念构成理论体系和大厦。由概念我们得到关于种和类的概念,进而又得到系统的概念。我们知道无论在系统横轴上的A、B、C、D、E、F……还是在系统纵轴上的A、AB、ABC、ABCD、ABCDE……任何两两、两三、三三两两……之间又会发生无穷的排列和组合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感觉认知事物,从感性得到知性,从知性得到理性;我们可以通过对于事物的认知,产生情感、情绪和情结,进而转化为自身的意识和意志,创造性地建设与改造我们的生活与社会……如此循环的演变乃是一个无限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可能世界的不断显现的过程。但是在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发展进程中间,万物都是源自于本原的存在。至于在现实的演变进展中,变化自然实际且复杂得多,因为在演变进程中的各种因素之间均可能发生反应,而各种反应之间又是纷繁复杂的。而我们在上面讨论中所列举的无非便捷、直观的形象和模式化的表示而已。
事物发展通常按照螺旋式上升的方式而不是按直线方式进行。对于某一物体的变化来说,既可能是飞跃式的,也可能是渐进式的,总之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的。此时此刻,它既是自己也不是自己,说他是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具有同一性质之物彼此之间互相依存,有着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是一种连续变化的过程,如同是一条河里的水,每一点滴既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是不同的。
恩格斯曾经这样描述过生命现象的矛盾性。他说:“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自然辩证法》)毛泽东说:“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一切过程中矛盾著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著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种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矛盾论》)
对于事物的任何系统来说,由于系统内部的一切组分和部分之间,以及它们与本体之间皆因为有着意味深长的联系和内含相同的“a”而具有同一性。也就是说,存在与非存在、善非善(如恶)、美非美(如丑)、真非真(如假),以及存在者与非存在者都是源自本原的在。
本体论认为,宇宙世界、万事万物都是来自一个具有开端意义的本体。大凡对立双方都肯定的东西与否定的东西是一回事。同样的道理,否定的东西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它的自身内包含着一个肯定的东西。那么,这个“肯定的”或者“否定的”东西将要肯定或者否定谁呢?它将要肯定或者否定的正是自身而已。
也就是说,“善”与“非善(如恶)”具有同一性。因为,我们所说的“非善(如恶)”的东西,其中自然地包含着“善”的成分,只不过这种“善”是在“善”“非善(如恶)”的演进之中,处于一个较为先前的阶段或者说是较为低级的程度而已。譬如,我们说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封建主义或者资本主义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时期,曾经是先进的革命的。也可以说,“非善(如恶)”必然是与“善”同时产生的,并且包含在“善”里面。在我们表现为“善”的时候有人会表现为“非善(如恶)”。这是不言而喻的。有人说,“善”是“非善(如恶)”创造出来的,也不为过。
也就是说,“自由”是由“不自由”创造出来的,正与负也是如此的。太极是阴阳对立的统一体。我们说我们朝气蓬勃、青春焕发,我们又说我们气息奄奄、日薄西山;我们说我们身体健壮,我们说我们年老体弱;等等。这些相反的性状属性原本就如同种子般早已经埋藏在我们的机体里,只是按照一定的秩序或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和在一定的环境里萌发而已。“善”与“非善(如恶)”也是一样的。“人性本善”,但是人性的恶也相依相伴地隐藏其中,所以这正是“一念之间”的善与非善(如恶),也是佛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道理。只有当理性,包括道德理性和科学理性,统管感性的认知与欲望时,自由才是人性的。
辩证法认为,事物正是因为其内在的矛盾性推动着自身的变化发展。所谓矛盾性也就是事物的对立统一。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一分为三”的。但是相比而言,“一分为三”更具有普遍性。否则事物也就不成其为事物。所谓“一”,即是指一个事物,“二”即是指事物内部对立的两个方面,“三”即是对立的两个方面“合二而一”(“此一”非“彼一”)成为一个具有新质的“一”,所以“此事物”亦非“彼事物”,事物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之中。此“中”即是“时中”,就是孔子所言的“过犹不及”“中庸之道”的“中”。
儒家“中庸”之道具有辩证法方法论的意义。其“中”含蓄“真”“善”“美”,是事物存在的本然状态。
从直线流动而言的“中”乃是两端之间的“中”,如是“A”“B”之间“A而B”之间的某一位点“ab”;
在平面坐标系中,“中”则是平面圆上的圆心,如第二层次“AB”系统里的“abc”;
在立体结构上,是曲线形成的球体的球心和螺旋上升、前进的螺旋体的中心,如第三层次“ABC” 系统里的“abcd”……
当我们审视直线运动时,我们必然看到直线的两端,也看到两端之间的中间区域;当运动围绕中心进行曲线运动时,我们得到圆心和周行的概念;当运动向着四面八方运行时,我们得到球和球心的概念;当运动因时因地向上螺旋前行时,我们得到螺旋上升的螺旋体中心。只有此时,我们才会感悟到庄子追求的“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庄子·齐物论》)的理想境界。方以智曾经在《东西均》中说:“万古所师之师惟有轮尊。轮尊无对而轮于对中。”所谓“轮尊”是其虚拟的最高尊者,是人格化的宇宙之道。庞朴注释:“轮尊超越一切对待之上,寓于一切对待之中。”所谓“轮”即是“均”。《东西均》开章说:“均者,造瓦之具,旋转者也。”[1]14-19
此所谓的“中”的位置乃是本然的状态,也是真理所在。因为“中”的位置是动态的,是时时刻刻都在变易之中的,所以要求“中”必然是“时中”。《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伊川说:“中者,当其可而已。”可见,“中”是与“时”(时间)、“空”(空间)、“缘”(条件)、“权”(权衡)、“变”(变易)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当其可”用现在的话语表示,就叫做“与时俱进”“实事求是”。
二 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演变
中国古代文化哲学具有深刻、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也是研究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哲学专著。因此,可以说《易经》是最早具有“辩证”和“辩证法”思想观念的著作;也可以说,易经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辩证法。
抽象性是哲学的基本属性。而“数”(包括数与数量)具有抽象性,故古今中外“数”被哲学家作为概括、阐述事物特征的手段与工具而被广泛使用。中国哲学自易、老始就偏好运用“数”“象”“形”及其三者的关系阐述形而上问题,以及表达世界物质的构成与衍变。形由象生,象由数设。其中,“数”是最高级别的抽象形式,如老子哲学的“一”“二”“三”、孔子哲学的“一以贯之”等。
既然事物具有无限可分的特性,那么事物的“分”“合”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分”可以包括“分裂”“分化”“分解”等,而“合”则包括“结合”“融合”“合作”等。事物的多元性、多样性正是世界多样化的基础和保证。事物“一分为多”是客观世界的实在性与人类思想的自由性、事物存在的无穷规定性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法思想形式,用形而上之数表示,主要有“一”“二”“三”“一分为二”“一而二”“二而一”“一分为三”“一而三”“三而一”“三极”“一分为多”等。这些我们都能够在《易经》《论语》《道德经》等经典著作中找到它们的形象及其演变的轨迹。
第一,孔子注《六经》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回溯孔子时代,礼乐崩坏。孔子惧怕世道衰微、人心堕落,进而“修”《春秋》,重在明礼(理)而言志(心),以明确规定做人做事的原则和规矩,整肃社会风纪;再是注《易经》作《易传》,赋予《易经》以形而上意义,奠定了儒家乃至中国文化形而上的基础;后来传人特别是(北宋)周敦颐主要根据《易》的形而上思想精神著《太极图说》,从而完善了儒家本体学说,构建了中国文化的宇宙观。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孔子略传》一章中评说:
“孔子晚年最喜《周易》,那时的《周易》不过是六十四条卦辞和三百八十四条爻辞。孔子把他的心得,做成了六十四条卦象传,三百八十四条爻象传,六十四条彖辞。后人又把他的杂说纂辑成书,便是《第辞传》、《文言》。……除了删《诗》、《书》,定《礼》、《乐》之外,孔子还作了一部《春秋》。孔子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的。他的《诗》、《书》、《礼》、《乐》都是他删定的,不是自己著作的。就是《易传》的诸传,也是根据原有的《周易》作的,就是《春秋》也是根据鲁国的史记作的。”[2]50-51
《易传》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又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其中,“易”含有变易、变化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变化之源的“易”就是“道”。如果从辩证法的角度讨论,“易”即是变化之道,《易经》可以翻译为论述变化之道的经典,也就是中国古代的辩证法。
“易有太极”,意思说宇宙变化都是从“道”从“太极”开始的;“是生两仪”讲由太极而“阴阳”;再是经过阴阳相互作用形成四种不同形象即“四象”,《易经》称之为“太阳”“太阴”“少阴”“少阳”;再是经过“四象”与阴阳相互作用形成代表八种不同物质的式样即“八卦”……《易》正是通过阐释“易”“道”“器”“太极”“阴阳”“六爻”“八卦”“六十四卦”等概念的辩证演变过程,从本体出发论证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或宇宙生成论。
朱熹在《周易本义》的序中写道:“‘《易》有大极,是生两仪’。大极即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
在《论〈易经〉的“一分为三”思想》一文中,我们经过深入探讨《易经》辩证思想的形成和变化,指出:
《易经》论证、揭示和阐述:道立于二,以阴阳为本;物成于三,以三极为用;三生万物,以变易为动的“一分为三”思想。
《易经》充分揭示了事物“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的辩证思想……儒家与道家无不是以“一分为三”的思想作为自家学说的理论基础。[3]
“阴”与“阳”两个方面是相互对立而存在的。通常说,阴阳相互作用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变化。阴阳的关系是:有阴则有阳,阴中有阳;有阳则有阴,阳中有阴;阴阳同一,二者对立统一地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在现实世界里,我们把“阳”的方面比喻为正能量,是刚健向上积极有为的推动力,而“阴”的方面相对而言则比喻为负能量,是阴柔的静止的牵扯事物发展的力量。一般说,“存在”与“非存在”、“存在者”与“非存在者”之间既是对应的关系;也是同一的关系。
第二,孔子以“中庸”为“三观”。中庸之道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基石,也是孔子终身倡导并始终厮守的为人处世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
《中庸》记载,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是对至(最)高的德行,可惜持之惟艰难。用现在话语说,所谓“中庸”就是规矩、礼义和法则,是做人做事做学问的一个适宜的“度”。这种“适度”,就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与此相悖的是“过分”与“不及”。《论语》记载: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由此可见,孔子认为“过”与“不及”都不符合中庸之道的处事原则。也就是说,孔子将事物“一分为三”为“过”、“不及”和“中庸”三个类型。即是“不及—中庸—过”。在这里,“过”“不及”是相对于“中庸”而言的,是先有“中庸”,而后有相对于“中庸”的“过”与“不及”。孔子还说了中庸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即是“执两用中”: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
在这里,孔子将中庸之道定义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简称“执两用中”。由于有“两”,故而有“中”,抓住两端,中间也就凸现出来了。这种形式是相对于“过犹不及”不同的另一种用中的方式。前者是先有中间的“中庸”,后有两端的“过”与“不及”;后者则是先有两端“过”与“不及”,再有中间的“中庸”。
第三,老子以“道”为本体的宇宙生成论。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物极必反”“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观点讲的都是关于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矛盾的对立面是向着对立方转变,是一个永远循环往复的过程。正如前述,事物内部“A”中有“B”,“B”中有“A”;“A”的内部必然地发展异化为“非A”即“B”。事物的发展是由A而B的过程。宇宙万物乃是阴阳化生的对立统一的和谐整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这是老子构建的以“道”为本体的宇宙生成论。首先,“道生一”,即指“道”是世界的本体,是“一”。“一”也是无极,是宇宙。无极内含太极。其次,“一生二”,是指由“一”化生为“二”,“二”即是阴阳。最后,“二生三”,是由“阴阳”相互作用化生出“三”。这个“三”即是具有新质的“一”,也是“合二而一”的“一”。
“一分为二”的“一”与“合二而一”的“一”在通常情况下不是一个相同的“一”,之所谓“此一”非“彼一”。合起来说,“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过程,也是事物“一分为三”地发生、发展的过程。
老子的“二”,学界也有的解释为“天地”;“三”也有的解释为“人”,即是天地人三才之道,如儒家《中庸》所说的,人可以与天地为参。“三生万物”即是人可以参天地之化育万物。故老子有云: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
在这里,老子指出“道”是“一”,天、地、人为“三”,并且阐述了“一”与“三”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一分为三”的另一种理论形态即是“一而三”“三而一”的结构。
第四,(西汉)扬雄用“一分为三”模式解释宇宙万物的形成。扬雄模仿《周易》的体裁,运用老子道学、阴阳家和五行思想知识,作《太玄》。其本体为“玄”,其体系为“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4]4-5
所谓“玄”意为玄妙之意,源出《老子》“玄之又玄”,相当老子哲学“道”的地位。对于《太玄》的写书动机与方法,扬雄云:
“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其所循也大,则其体也壮;其所循也小,则其体也瘠……故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也,其可损益欤?”
在这里,扬雄说明其著《太玄》的目的在于以“玄”为本体探讨探究宇宙发生、运行的规律。他说:
“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又云:“玄有一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此三生者,参分阳气,以为三重,极为九营。是为同本离生,天地之经也。旁通上下,万物并也。九营周流,始终贞也。”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对于扬雄及其《太玄》作了详细评介。他认为扬雄的《太玄》是“与哲学有关”的著作,称赞其“在当时纬书谶书盛行之际,而扬雄能持《老易》之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实可谓为有革命的意义也”。他解读“夫玄也者”说:
“此谓一玄之总原理,分而为三,名之为方,有一方二方三方,共三方。三方又各分而为三,名之为州,每方有一州二州三州,共为九州。每州又各分为三,名之为部,每州有一 部二部三部,共为二十七部。每部又各分而为三,名之为家,每部有一家二家三家,共为八十一家。此所谓‘方州部家,三位疏成’也,所谓‘以三起’也。”[5]47-49
也就是说,“玄”乃是本原,是开端,也是“一”;所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即是“一分为三”的一种说法。其相似于我们所说的“一分为三”中“一而三”“三而一”即“三极”的理论形态。
第五,(北宋)张载提出“一物两体”的辩证法思想。张载,世称横渠先生,“是北宋时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6]1。他提出“太虚即气”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一物两体”的辩证法思想,为王夫之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哲学中,“太虚”的概念是泛指虚无缥缈的宇宙空间。张载认为,“太虚”不是虚无缥缈的真空,而是充满着“气”体物质的空间。太虚与万物都是“气”体的不同的存在状态和运动形式。
气是万物的本体。太虚是气散而未聚的本然状态。气聚集的时候,万物有形;气散的时候,万物无形而归于太虚。气聚时有形,则称其明,气散时无形,则称其幽。“幽”和“明”都是事物存在的状态,不是虚无。
张载认为,作为世界本体的气是永恒的,是不会消灭的。他还以水的形态变化举例说明,当水为液态时即为液体水、当水为固态时则为冰。气在太虚中的聚、散如同冰在水中的凝结和溶解一样的道理。
在“以气为本”的自然观思想基础上,张载认为事物的变化发展的根据是内因而不是外因,是气的阴阳两体的矛盾对立推动事物的变化发展。他认为,气具有阴阳两体。两体又表现出形形色色的形式。但无论如何,有阴阳对立之两体,即有对立的统一。进而,他对“两”与“一”的关系做了比较详细深刻的辩证阐述。“两”即是“两端”,是指“阴阳”两个对立面。如果对立的两端发生交感作用,则复归于“一”,即统一为“一”。他认为,事物没有不是阴阳两体的。有矛盾即有对立,但是一切事物矛盾对立斗争终究必归于和解,他说:
“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张载的这些论述与黑格尔哲学“正反合”的思想、“矛盾终归消解”的思想很相似。所以说,心与物、天与人交相胜也。在《正蒙·参》中,张载进一步论说认为,天体的运动主要是由于其内在的动力,而不是来自外在的推动。他的“一物两体”,之所谓“不有两,则无一”、“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和“动非自外”的辩证法思想,在中国哲学史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第六,(北宋)邵雍以“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推衍宇宙万物的生成。北宋象数学家邵雍在《观物外篇·先天象数第二》中对于《易传》的“易有太极……”句诠释道:
“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上交于阴,阴下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天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故易六位而成章’也”。[7]321
邵雍理解《易》与我们前述的思想有比较大的差距。他研究《易传》解密《易经》,用所谓“加一倍法”诠释四象、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形成,并且以图、象解说之。冯友兰说:“康节之宇宙论,大概即此推衍,而又以图象明之。”[5]167
南宋思想家朱熹发展了邵雍的“一分为二”思想。他认为,不仅“一分为二”,而且“二”又能复归于“一”。朱熹说:
“阴阳虽是两个字,然却只是一气之消长,一进一退,一消一长,进处便是阳,退处便是阴;长处便是阳,消处便是阴,只是这一气之消长”(《语类》卷六九、七四、九八)。
这表明事物虽然存在着矛盾对立之“两”,但是这个“两”又是不可分割地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中,即两者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渗透,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通书·动静》)。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著《思问录》,对于事物发展的可分性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他不同意邵雍解《易》的方法,认为邵雍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系辞》)解释为“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并且以此作为宇宙生成的法则,是死板的、机械的,不足以概括世界变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王夫之认为,世界事物变化发展是复杂多样的、无穷无尽的,绝不可能像邵雍那种呆板的数字游戏所能解释的。他说:“见一阴一阳之云,遂判然分而为二,随而倍之,瓜分缕析,谓皆有成数之不易,将无执与。”(《思问录·内篇》)
“一分为二”学说自隋代学者杨上善提出“一分为二”的概念之后,邵雍、朱熹等都作了各自的阐述和发展。明末清初哲学家方以智在前人“一分为二”认识论的基础上,从自然界、人类社会乃至人类思维等方面作了充分的论证后概括说,“尽天地古今皆二”“凡天地间皆两端”“无非错综,无非反对”,从而肯定在事物内部存在着两个相互排斥的方面;又说“岂非天地间之至相反者,本同处于一原”,就是说,“分”是相对于“合”而言的,“分”必然要“合”,“一而二”必然导致“二而一”,正如“合无不分,分无不合”,从而进一步建构与完善了“一而二”“二而一”的哲学逻辑结构体系,使之进入“一分为三”辩证认识论水准。
第七,(明末清初)方以智的辩证法思想。方以智,庞朴称他是明末清初可以与王夫之“齐名”的“伟大哲学家”[1]3。笔者以为庞先生的评价一点也不为过。方以智确实称得上是中国古代辩证法的集大成者。
方以智撰有研究辩证法的专著《东西均》《一贯问答》等辩证论著。《东西均》可以简单地理解“东西”为事物或者事物“两端”,“均”则是“调和”“执两用中”的意思。《东西均》《一贯问答》是专门研究一与二、一与三、一分为四、一分为五……一与多的关系的辩证法著作。他说:
“大一分为天地,奇生偶而两中参,盖一不住一而二即一者也。圆∴之上统左右而交轮之,旋四无四,中五无五。”[1]62
他在《易余》中解释了“旋四无四”即是当一参乎两中,而两旋为四,犹二至旋二分,故有旋四之用,无四之体;“中五无五”即是有中五之用,无中五之体。也就是说,“一分为三”能够包含“一分为四”“一分为五”……他的意思是,两端之中亦有两端,惟中惟一;贯通两端,方得其一;两端用中,一以贯之。
方以智在《东西均》的“三征”篇中,对“一”与“二”、“一”与“三”和“一”与“多”的辩证关系作过详尽的分析研究。他认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又是“合二为一”的。而且他构建了一个颇具思想深度的“三即一,一即三”的“一分为三”模式。
“明天地而立一切法,贵使人随;暗天地而泯一切法,贵使人深;合明暗之天地而统一切法,贵使人贯。以此三因,通三知、三唯、三谓之符。核之曰交、曰轮、曰几,所以徵也。交以虚实;轮续前后;而通虚实前后曰贯,贯难状而言其几。暗随明泯,暗偶明奇,究竟统在泯、随中,泯在随中。三即一,一即三,非一非三,恒三恒一。”[1]64
在这里,方以智提出了三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概念,即“随”“泯”“统”,并探讨和建立了事物“三即一,一即三”的模式。这个模式可以用“随——统——泯”表示。“随”即是顺从常识,承认现象世界的一切存在,也就是承认对立之为对立;“泯”即是消解万有的现象性存在,不承认一切事物的差别,也就是不承认对立之为对立;“统”即是综合以上两种观点,把两者贯通起来,一以贯之。这三者是统一的。也就是说:“究竟统在随泯中,泯在随中,三即一,一即三。”
他认为,对立者如何化解为“一”是以对立双方的性质为转移的,不是绝对的。“贯”通与“权”“变”“几”有关,他列举了“化”“超”“融”“无”“统”等贯通的方法,进而举例孟子的“塞”字、子思的“至”字、《易经》的“太”字,以及“善”“恶”之中为“至善”等等,所以说,妙不可言便是“贯”“中”“一”“本然状态”。
在“一”与“二”、“一”与“三”研究的基础上,方以智进一步研究了“一”与“多”的辩证关系。他说:
“一是多中之一,多是一中之多;一外无多,多外无一,此乃真一贯者也。”[1]424,427“一多相即,便是两端用中;举一明三,便是统体相用。”(同上,第427页)
方以智将“一”与“多”对举,认为只有“一分为多”才是世界万物的客观实在。换句话说,在几种辩证思维的表现形式中,他认为只有“一分为多”才是最为根本的。这与朱熹“理一万殊”的辩证思想相恰。
第八,(明末清初)王夫之是中国古代唯物辩证法集大成者。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是中国古代唯物辩证法集大成者。张岱年在评价王夫之对于张载学说的传承和发展时说:
“张载开辟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哲学的一个新阶段。后来,经过王廷相,到王夫之而达到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哲学的高峰。……王夫之高度赞扬张氏的哲学,认为‘张子之说……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张子正蒙注序论),他全面地批判了程朱‘理在物先’的客观唯心论和陆王‘心外无物’的主观唯心论。”[6]17,18
王夫之明确指出,宇宙是由气体构成的物质实体。宇宙世界的物质基础是“气”或“阴阳二气”。“气”充满整个自然界,从浩浩的天空,到无限的大地,都为“气”所弥漫。这表明了世界的物质(气)统一性。而“气”的变化有“显”与“隐”、“聚”与“散”、“幽”与“明”、“往”与“来”、“屈”与“伸”等多种形式形态。他在批判佛教“生死”观时指出,气体的“聚散变化,而其本体不为之损益”的物质不灭的观念。宇宙万物既是统一于“气”,也是生生不灭于“气”。
王夫之哲学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关于事物的动与静问题,他指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于运动而言的。他认为:“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关于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的问题,王夫之认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周易外传》卷五);关于理与气问题,他认为“气者理之依也”(《问思录内篇》)。关于矛盾的对立统一问题,他认为对立双方具有对立而统一的关系,“两端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也”。他继承发展张载的辩证法思想,认为大千世界,万事万物无处不包含着阴阳对立和统一,并且处于和谐状态。
他看到了事物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而且认为“统一”比“对立”更为重要。“非有一,则无两。”“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他十分推崇张载“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等思想观念,反复强调“和”,认为矛盾对立面最终的结果是和谐,因为事物“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最后对立双方的和解对于矛盾双方都是有益的。
三 “一分为三”是辩证法全面而精准的表达形式
“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多”都是对于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描述,是属于辩证法范畴。但是,如果光讲事物是“一分为二”的,则主要是为了突显出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和斗争性,忽略或者淡化了事物之间的整体性、统一性与和谐性;只有讲事物是“一分为三”的,才是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整体性、统一性和和谐性。因此,如果单纯讲事物是“一分为二”的,不能够算是完全意义上的辩证法;只有既讲“一分为二”,又讲“合二为一”,才能称得上是完全意义上的辩证法。“一分为多”是事物的一种属性,也是事物存在的一般规律性,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凡事凡物都有一种本然的存在状态,也就是唯物主义者称之为“客观”的存在状态。本然状态才是事物至“真”至“善”至“美”的存在状态,也是我们认识的理想境界。
我们也曾经对“一”与“二”与“三”……与“多”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无论一事或者一物,首先是整体的存在者。没有整体,何来的局部;没有系统,何来的组织结构。没有“一”则没有“二”,更没有“多”。事物内部具有矛盾性即对立统一的特性,是建立在事物之所以成其为事物的基础之上的。
“存在”是“一”,是本;对立是“二”,是体;系统是“三”,是用。本统体用。凡事静态地观察,都是对立的“二”;凡事动态地分析,都是和谐的“三”。哲学意义的“一”“二”“三”“多”之间的关系是:
事物普遍是一分为三的。“一分为三”的“一”是“一个东西(事物)”,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无任何规定性的存在。这个“一”是事物存在、统一的“一”,是和谐整体或全面系统的“一”。由于事物内在的矛盾运动和分裂、分化、发展的必然性,以及内在自我否定性。一般来说,“一”必然地分解为“三”个方面。一个事物与三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三极等重的关系,相互依存的关系;三个方面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同时,事物亦是“一分为二”“一分为多”的。但“一分为三”与“一分为二”、“一分为多”是不相矛盾的,而且“一分为三”作为事物的本质揭示和最一般规律的把握,它能够涵盖或包含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四、一分为五……一分为多。因为“三”具有哲学意义上“类”的意义。一分为二是一分为三的特殊表现形式。一分为三是一分为多的一般表现形式。至于万物,是具体的、丰富的、生动的现实个体存在,是“三”中两两相异的物种。“一”与“三”与“多”的关系可以用“‘一’(事物)——‘三’(类)——‘多’(万物)”来表示。[8]37-38。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是从“家”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而它具有看重事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谐性的特点;其二,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宗教基础的文化,故而它具有不信“神”而重视“人”,看重人的生命、主动精神和人生意义的特点;其三,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中庸之道”为核心观念的文化,是一种“内圣外王”的文化,故而它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具有明显的特点。
西方文化,主要指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一种源起于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文化,其核心理念是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矛盾对立的观念和斗争的哲学。它以认识世界、把握规律、征服自然、快乐人生为旨趣,重在于向外征服,向自然界、异种文化挑战,企图成为世界的主宰。因此我们又称其为入世的哲学。而以古印度佛教为代表,其次还有中国道家的一些思想观念,它们的基本理念是回避、泯灭矛盾,不斗争,持否定人生意义和超然出世的人生态度,基本特征是抱有远离社会和苦修来世的出家人心态,以解脱此生、追求来世幸福为最高目标。这是一种出世的哲学。只有以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中国文化,以“中庸之道”作为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立人达人、推己及人。“中庸”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还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在世哲学。儒家辩证法的核心即是“中庸”,表现为“执两用中”“中和常行”和“随时持中”的思想方法。
庞朴先生曾经对中国古代几大家的辩证法思想进行研究。他在《“中庸”平议》一文中评议先秦各家辩证法之发展过程[9]75-100,大体上可以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来描述它们各家的特点,如果说“道家辩证法”是一种只讲转化、泯灭对立的学说,那么“法家辩证法”则是一种夸大对立、排斥同一的学说,只有“儒家辩证法”是既着眼对立,又强调统一和谐的辩证法。
“一分为三”既是辩证思维的全面而准确的简明表述,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对于世界哲学的重大贡献,是人类思想宝库最璀璨的明珠。随着“一分为三”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逐步地认识到“一分为三”具有如下几种理论形态:
第一,中庸式。中庸式或是“一生二,二生三”式,或是“一而二”“二而一”式,是指先有本体的统一的“一”方,然后才有对立的两个方面。所谓“中庸”,孔子定义其为“过犹不及”。中庸式是先有中庸,然后有“过”与“不及”。“不及—中庸—过分”构成事物的“一分为三”。
譬如,如果没有“道德”“法律”,也就没有违法乱纪。中庸式是辩证法的一种形式,其中“中庸”是已知的,“过分”与“不及”是相对于“中庸”而言的,所以说,中庸式是“一分为三”形式中之“一实两虚”的理论形态。也就是说,“中庸”是“实”的,“不及”与“过分”是“虚”的。但是一旦“实”的确定了,“虚”的也就相应地变成“实的”。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关于辩证法的认识,曾经有过一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及辩证法关系的激烈争辩。这场事关意识形态和浓烈政治色彩的争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建设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记忆。时至今日,我们可以形象地理解,在辩证法的视域里,“一分为二”之后连续地进行“合二为一”过程,即“一而二”“二而一”是“一分为三”的。如果静止地机械地理解,当我们如此说时就已经不再是同一层次的存在而是下降到次一层次的抽象,而变化成为一个具体事物存在运动的两个过程,前后相继人为地被割裂为两个环节。其实,“一分为三”的“三”是在不断地变化之中的,是动态的,也是实实在在的。
第二,天人合一式。“天人合一式”或者对立统一式,是指先有对立旳两个方面,然后方有统一的第三个方面。如,在“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中,唯有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天地的作用是自然而然的。天“化”生万物,地“育”成万物,而人的作用是“赞”天地之化育,也是参与到天地化育万物的系统工程中去。既然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则具有可选择性,正如庞朴所言:“唯有人的作用是变量,它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可正可反,可迟可速”,“就是作为第三者,参加到天地的化育功夫中去”[10]289。当然,既然是“赞”助,就不会帮倒忙,一般是指积极的正能量的。
对立统一规律,是先有“对立”的双方,再有统一的“中”方。“对立”的双方是“实”的,统一的“中”方是依“实”而在的“虚”,所以这种理论形态又称为“两实一虚”的形态。如上所说,一旦“实”的被确定了,“虚”的也就相应地变成“实的”。中国古代哲学所谓的“两一”,也有相似的意思。上面说的孔子界定“中庸”为“执两用中”。这个界定中的“两”与“中”也是“实”与“虚”的关系。
第三,三极式。“三极式”或者“一而三”“三而一”式。“一”是“函三为一”的“一”。“一”中含有平等、平行的三个方面,之所谓“三极平等,和而不同”。这种理论形态包括“三虚”与“三实”两类情形:前者如《道德经》有云:“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在这里,老子所说的“道”与“夷”“希”“微”,以及与“一”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就是这样的关系。后者如在现代治理体系中,“决策—执行—监督”三者之间的关系,前面所说的“道”与“天”“地”“人”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小时候玩的拳头、剪刀、布的游戏也是如此。至于“虚”与“实”无非称谓而已。哲学意义上的“虚”与“实”如同“肯定”与“否定”,二者是同一的,相对的,也是可以相对存在的。当今我国政府提倡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一个多民族各美其美、多种文化共存的和而不同的世界。
如果我们按照上述的研究思路,并将其拓展开来研究中国哲学诸子百家的哲学辩证法形成及其之间旳同一关系,以及再扩展开来,研究几千年来中国哲学辩证法形成及其之间旳同一关系,以至我们研究整个人类历史产生过的种种哲学辩证法形成及其之间旳同一关系,以及可能世界……等等,我们将会得到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具有同一性的哲学辩证法体系。历史中所有种种哲学辩证法形式及其之间旳同一关系都会在这个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辩证法正是以这样的形式(式样)——如同小孩手中不停转动着的万花筒——动态地展现给人们“一时一世界”“一花一世界”的惊喜,也正是在这样的辩证思维框架里,人们的认识活动不断地涌现出各种思想的光辉,照耀着人类前行的道路,如同这个道体流行的现实世界的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