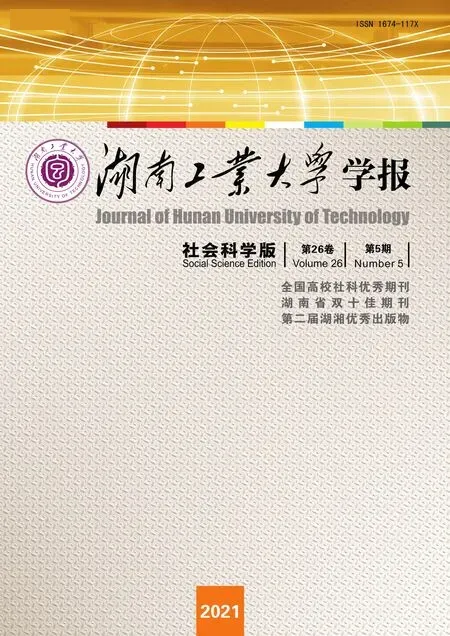“美美与共”的审美理想境界
——论屈原赋的生态美
吴广平,邓康丽
(1.湖南科技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基地,湖南 湘潭 411201;2.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生态美学推崇的美是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生态美,生态美的第一重体现便是“主体的参与性和主体与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1]。这里“参与性”和“依存关系”都在强调生态美并非一种单纯的美的形态,诸如艺术美、科技美、社会美等具有独立性质的美,而是一种关系之美。在生态审美的维度中,人与自然始终处于一种相关相依的联系状态,不能独立其中任何一方来完成审美过程,两者的审美联系不可分割。在这样的理念背景下,生态审美打破了人与自然主客对立的审美关系,践行一种“主体间性”的审美(或称“交互主体性”),即“同时承认并张扬自然主体和人主体,并特别强调这两类主体之间的联系的关联性原则”[2]128。在这种审美中,自然审美是其审美的第一要义和目的[2]213,自然审美是指“自然对象的审美属性与人的审美能力交互作用的结果,两者缺一不可”[3]。这表明在这样的审美中,审美活动中的各方是平等的、融合的,而非独立的。
生态审美的审美观与中国古典哲学智慧“天人合一”观天然相契。“天人合一”观正是一种同时强调“天”“人”以及“天人关系”的朴素哲学观,是一种宇宙人生通融合一的观念。屈原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天人合一”观的形成期,是时,几乎所有形而上的思想观念、文学艺术都是在“天人合一”观的范围中进行的阐述和表现。在屈原赋中,屈原对自然美的表现实质是将自然美与人格美、人情美耦合,创建出一种“美美与共”的审美理想境界,从而赋予自然美更深刻的意蕴。
一 物我合一,情景交融
在楚辞之前,《诗经》的无名诗人们就多运用“草木鸟兽”等自然物来比兴,其中感物缘情的表现手法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文人及大众的审美倾向,并迅速反映在当时的文艺创作中。诚如刘勰所言:“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4]65
《诗经》之比兴主要在自然感兴、言志抒情方面给后世文人留下宝贵的审美经验。自然感兴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感性的联系,形成“物我一体”的审美思维,因此超越了主客之隔,成为后世文人的审美智慧。言志抒情则将人的情感意识与审美意识融合,形成不可捉摸的审美直觉,给人一种朦胧飘渺的美感体验。屈原继承和发展了前代诗人的比兴手法,在感兴和抒情的基础上,赋予自然美更多的审美内涵,发展出具有象征性的自然意象。且看《离骚》下面一段: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5]2。
这里的江离、白芷、秋兰、木兰和宿莽是屈原赋中经常出现的香草意象。诗人以江离、白芷、秋兰为衣着服饰,早上去山里拔取木兰,傍晚去水洲采摘宿莽,这些看起来像另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样态。然而,诗人的笔锋却突然骤转,时间意识急入,江离、白芷、秋兰、木兰和宿莽与诗人被同时置于时间的维度中,都归原为一种时间性的存在。日月轮回,春秋代序,芳华一瞬,光景不待。在时间的意义上,一切生命仿佛稍纵即逝,一切生之努力都似乎徒劳,诗人对“年岁之不吾与”的恐惧和对“草木之零落”的感慨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此时的香草既指代香草本身,又代表着诗人自己,既是具有审美性的自然物,又象征着某种人格,与前面的“修能”形成呼应。在这一段话中,诗人并未描写江离、白芷、秋兰、木兰和宿莽的审美特征,而是将这些香草直接以一种独立的形式——审美意象,与诗中的“我”形成对照,又与诗中的“我”合为一体。诗人将自身对时间、人生的思考融入审美活动中,丰富了这些自然物的审美内涵。又比如: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5]8。
在这幅图景中,兰、蕙、留夷、揭车、杜衡和芳芷既保持着它们本来的自然风貌,又象征着不同的社稷人才。众芳争妍、欣欣向荣的风貌所对应的正是楚国人才济济、国家昌盛的情形,这又是一种二元合一的表现方式。
在屈原赋中,屈原对自然美的描写趋于一种意蕴丰富的象征表现,所塑造的审美意象具有独立自足的审美意蕴。与《诗经》对自然美的形象感悟不同,屈原笔下的香草是一种审美提炼后的象征意象——它们已然具备独立自足的审美意蕴,是不言自明的美的化身。从其本质看,它们是一种升华了的“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原是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作为一种视觉美感概念提出的。他在《艺术》中说道:“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6]文学、艺术就美感而言是相通的,视觉艺术中的“有意味的形式”是指通过线与色的搭配来表现的美感形式,而文学中的“有意味的形式”则是指文学家通过语言文字表现力对现实进行提炼升华所形成的美感形式,比如诗歌中的意象、意境。对此,李泽厚指出:“由写实到符号化,这正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也正是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原始形成过程。”[7]屈原赋中的自然意象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形式和内涵体现出物我合一的独特审美意蕴。比如《橘颂》篇写道: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5]133。
《橘颂》被称为“咏物之祖”,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咏物诗,诗中的“橘”与《诗经》中自然物只作烘托、起兴的审美形态相比要成熟很多,它不再是一种短暂的情感铺垫或者提示,而是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自然物。橘树是一种地区性物种,它只在南国才能长成橘树,是楚地特有的物产,《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8]屈原首先抓住橘树“深固难徙”的属性特征,感慨其“受命不迁”的自然本性。然后递进深入,细致地描写橘树的枝叶、花朵、刺棘、果实、色彩等特征,夸赞其美好繁盛的样态。从其描写的层次来看,屈原对“橘”进行了全方位的肯定和赞美——从内在的“壹志”到外在的“姱”,由内到外美善兼备,是天地间最美丽的树。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对橘树的审美观照与屈原对自我的认识和定位,即“内美修能”“内厚质正”“文质疏内”是非常一致的。很显然,屈原对橘树的观察和描写,渗透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因此,屈原在《橘颂》的后半部分写道: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5]134。
朱熹点评此段为“申前义以明己志”[9]。屈原在歌颂橘树的同时,也在歌颂他心中的理想人格,表达他自己的崇高志向。这种心理恰如H.加登纳所言,作家总倾向“先把自己铸入到一个强有力的、自信的个体身上去”[10]。橘树与诗人,在生命本质上都有着同样的质感厚度和纹路曲折,在生命境界上均是不改初心、独立于天地、繁茂而美丽,所以《橘颂》既是在颂橘,也是在颂人,前后对照,相互呼应,物我合一,异质同构,使“橘”这一自然意象的内涵充实而丰富,令人印象深刻。
从上述来看,屈原对自然美的呈现主要表现为自然审美意象的建构。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意象,是一个多义并存的美学概念,它是意与象、虚构与现实交融合一的产物,但其实这个美学概念还有更深层的内涵,它蕴含着精神个体与精神客体之间息息相通的一体性,诚如叶朗所言:“意象世界显现的是人与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世界万物与人的生存和命运是不可分离的。这是最本原的世界,是原初的经验世界。”[11]64他又说:“当意象世界在人的审美观照中涌现出来时,必然含有人的情感(情趣)。也就是说,意象世界必然是带有情感性质的世界。”[11]64由此可见,意象的本质是人的心灵与自然物的合一,是“情”与“景”的交融统一,是一种理想化的审美形式。屈原“以心灵体验生机,通过人与自然的协调相济进入了一种‘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境界”[12]。结合屈原赋来看,其中的自然意象往往是自然美与人格美的合一,呈现为物我合一的审美理想境界,不管是单独成篇的《橘颂》,还是分布在各篇诗赋中的香草意象,审美中都渗入了 “比德”的内涵。爱默生曾说,一个崇尚自然的人,会觉得“属于自然的美就是属于他自己心灵的美。自然的规律就是他自己心灵的规律。自然对于他就变成了他的资质和禀赋的计量器”[13]。屈原显然意识到了这两种美的互通性和相似性;他常常打破两者的界限和桎梏,使人与自然物既能相互转换,又可以融为一体,这种物我不分的审美形态在其笔下十分常见。
屈原将自己的生命意识投射于自然之中,又将自然内化于自己的人格精神中。在屈原赋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主人公形象,他或披叶戴花,或餐英饮露,或滋兰树蕙,或芷葺荷屋,或沐兰酿桂,或乘豹从狸,等等,过着一种亲近自然、融于自然的生活。香花香草的清白之体、芳馨之性、繁茂之态、坚韧之质,正对照着屈原自己的生命境界:“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离骚》)“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离骚》)“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沬。”(《离骚》)“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九章·涉江》)“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九章·橘颂》)“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九章·橘颂》)诗人与自然事物这种超现实的生命联系,也有如《离骚》中灵氛所言 “两美其必合”,自然美与人格美也因这种耦合而相得益彰。
除了塑造这些物我合一的自然意象,屈原还精于构造一种情景交融的自然意境。游国恩说,楚国“有九嶷衡岳的高山;有江汉沅湘的长流;有方九百里的云梦泽;有坼吴楚,浮乾坤的洞庭湖;森林鱼鳖,崖谷汀州,鹤唳猿啼,水流花放,无一非绝好的文学资料。”[14]59又说:“屈原便是善于利用地理来做文章的头一位。”[14]60结合屈原赋中的自然描写来看,诚如其言,屈原确实是将楚地大部分的名胜、名物都统摄于其笔下,构造出非同凡响的审美意境。比如《九歌·山鬼》: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采三秀兮於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5]61。
这些描写诗句虽不繁复,内容却凝练饱满,充分展现了江南之山的俊秀和清幽。那独立之高山、辽阔之浮云的豁然景致,和“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朦胧意境,无不在烘托此山的俊秀;山中幽篁遮天、猿狖啾鸣、风声飒飒、木叶萧萧,也无不在衬托山的清幽。在这俊秀和清幽的景象中,又飘荡着一股绵长不绝的怀思和哀怨,山之景象与人之情态浑融无间,构成飘渺幽弘的意境,恍若梦境。
屈原擅长以象征、通感、比喻、暗示等描写手法,在实象中造境,在境象中抒情,入景生情,融情于景,其笔下呈现出亦实亦幻的审美意境。比如《九章·涉江》:
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5]100-101。
屈原流放时途径溆浦,此时离首都郢都已相去甚远。冥冥深林、荒山野岭的陌生景象触发了诗人的情绪,而途中山高蔽日、山下多雨的天气和烟云雾霭的情景又给人造成一种不可遏制的压抑和孤独,寒冷和凄凉的境遇催化了诗人内心的伤感。从这一段文字所塑造的情境来看,它的空间逼仄狭窄,它的氛围幽暗诡异。诗人置身这样一处陌生之地,来路不可退,前途非大道,于是迷茫、孤独、彷徨、困惑、恐惧。加之失去家园带来的伤痛,旧痛添新愁,通通向诗人内心袭来,又都从诗人内心弥漫开去,因此其目之所及与心之所感融为一体。这种情景交融的意境恰如明代艺术家祝允明所说:“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15]在屈原赋中,这样的审美意境处处可见,比如: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5]50。(《九歌·湘夫人》)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5]115。(《九章·怀沙》)
惮涌湍之磕磕兮,听波声之汹汹。纷容容之无经兮,罔芒芒之无纪。轧洋洋之无从兮,驰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5]142。(《九章·悲回风》)
此外,屈原还善于用意象组合的方式来构建诗歌的意境,以实写虚,化虚为实,虚实相生,在审美法则的支配下,营造出一种绮丽灵妙的审美意境,如《九歌·湘夫人》: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罔薜荔兮为帷,薜蕙櫋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5]50。
这是一座水上搭建的“百草香屋”,是为湘水女神的降临而精心准备的“居室”。整座居室由香草搭建,荷叶为盖、溪荪为壁、紫贝做坛、桂木成栋、木兰做橑、辛夷为楣、白芷铺房、薜荔为帷,还有一些其他用作装饰和布置房屋的香花香草。从最终呈现的审美效果来看,如此繁花似锦、精妙绝伦的构建和布置,仿佛是将《诗经·蒹葭》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16]和海德格尔推崇的“诗意地栖居”以艺术的表现形式合二为一了。戴叔伦说:“诗家之境,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间。”[17]“百草香屋”不仅是一种美的形式,而且还具有深厚的思想意蕴。王逸对此注解道:“屈原生遭浊世,忧思困极,意欲随从鬼神,筑室水中,与湘夫人比邻而处。然犹积聚众芳,以为殿堂。修饰弥盛,行善弥高也。”[5]53溷浊而称恶的世界令屈原无所适从,奸佞小人的诽谤排挤更令他无法立足,因此,屈原在诗赋中为自己构建理想居所,以此屋的美丽和芳香来象征自己守节好修的“居世”态度和芬芳高洁的人格境界。从这种意义而言,“百草香屋”不仅是情景交融的表现,亦是自然美与人格美合一的体现。
老子云:“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18]“道”藏于“象”中,但非“象”,要把握“道”,必须打破“象”的局限,才能得其环中,因此屈原并不重视对物象的逼真刻画,而是在恍恍惚惚、朦朦胧胧中追求某种本原的状态,即物我合一、物我不分的状态。在其笔下,一切客观世界的障碍都不复存在,万物交合并生,诗人的知情意与自然的真善美相合,超然象外的审美体验油然而生。这是人与自然同契相通的结果,更是古代生态智慧“天人合一”观与诗人的审美理想完美融合的表现,既真实,又梦幻,耐人寻味,令人神往。
二 虚实相合,人神一体
从宇宙的角度来看,自然蕴藏着天地运作之规律、万物造化之形式,其生机之象、变化之态、和谐之美,互相交融,一气同流,创化出宇宙生态无尽之灵秀。即使到科技文明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人类文明也不能完全掌握自然规律,穷尽自然的神秘性,更无法创造出如自然形式这般精妙绝伦的形物,而只能师法自然或者从自然那里获取灵感来源。自然的神性内涵正是因为这种人类无法企及的创化高度被人类接受的。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人对自然的美感体验到达一定程度时,便会产生与宗教体验相似的敬畏感、崇高感,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对个体生命的有限存在和有限意义的超越,通过观照绝对无限的存在、‘最终极的美’‘最灿烂的美’(在宗教是神,在审美是永恒的和谐和完美,中国人谓之‘道’‘太和’),个体生命的意义与永恒存在的意义合为一体,从而达到一种绝对的升华”[11]135。故有学者认为,人对自然的美感体验除了具有超功利性和愉悦性等一般属性外,还具有神性特征,而要达到这种神性体验,只有当美感层次达到“万物一体”境界时才会产生[19]。这正是自然之神性美产生的渊源。
因为巫觋文化的影响,屈原的精神意识中保留着信仰自然的宗教意识。这种宗教意识对现实的超越性和对自然的超理性态度,使屈原能够凭借一种超然的直觉和想象,穿透自然之象,见到一种绝对的美和真。《九歌》是屈原赋中最具巫神色彩的作品,诗中的自然描写充满泛神的思想,因此也是最能体现自然之神性美的作品。这是一组基于民间创作基础上的祭祀诗歌,所祭之神以自然神为主,有日、云、山、川四种自然神(《东君》是祭祀日神,《云中君》是祭祀云神,《山鬼》是祭祀山神,《湘君》《湘夫人》《河伯》是祭祀川神)。自然种种不可思议的变化、力量和创造,在认知能力非常有限的古人看来,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神秘,一种让人顶礼膜拜的神力,一种让人叹为观止的“大美”。在这种情形下,人们的行动经验和想象代替认知行事,将自然的变化与人类行动经验类比,将对自然的敬畏和惊奇之感转化为对自然的神性体验,虚实相合,人神一体,那些耐人寻味的自然现象变成了某位神灵在显示神迹。基于这样一种原始宗教的心理氛围,诗人屈原摆脱了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思维的桎梏,打开神话世界的大门,以玄妙之思、化工之笔描写了一系列灵光飞扬的自然神以及它们的故事。
在《九歌》中,自然神的本质建构是人神一体,即人性与神性的合一;人性方面包括人的行为活动和情感活动,神性方面则主要指自然的美与力量带给人的超自然体验。屈原善于以神灵显隐变幻之行迹来解释和描绘自然现象,在自然之中别构一种虚实相合的灵奇之境,以此来表现自然万物的灵变创化之妙。其在《九歌》中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对自然本相之美进行细腻而灵动的描摹。比如《云中君》:“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5]44这是对“降神”前的想象,诗人以为云神即将降临,因而发出灵光。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可以知道,其实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即云受到阳光之朗照后变得明朗发光的情状。然而在古人眼里,它成了神明显现的征兆。无独有偶,海德格尔也曾用他细腻而生动的哲学语言对这种云貌进行过描写:“云盘桓于敞开的光华之中,而敞开的光华朗照着这种盘桓。云变得快乐而成为明朗者。”[20]云作为“明朗者”的状态正是云“烂昭昭”的状态,这两种描绘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自然现象以一种奇异的表象给人神性的、虚幻的美感,刺激人的思考和想象,人又将这种感受和体验融入对自然现象的观照中,从而获得一种更深层的美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神性的展现并未使自然神的形象脱离自然的本来面貌,而是在自然现象的基础上为其镀上一层奇异的灵光,使自然美在这种灵光的照耀下以某种形式涌现出来,是“如所存而显之,即以华奕照耀,动人无际矣”[21]式的美。
“謇将憺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5]44王逸对此注释道:“夫云兴而日月暗,云藏而日月明,故言齐光也。”[5]45此处描写的依然是云的变化貌。风起云涌,或聚或散;天光云影,或隐或露。云的动态变化在诗人笔下化作了神灵出没的表征,这不仅是一种诗意的想象,也是一种生命共感的体现。卡西尔说:“美感就是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性,而这种生命力只有靠我们自身中的一种相应的动态过程才可能把握。”[22]云的变化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生命的运动行为,诗人以自身的人性经验来对照云的变化踪迹,将其解释为云神的藏露动作,但由于这种自然现象不可测知,云的变化因此在诗人眼中焕发出可与日月齐光的神性之光。
诗人继续写道:“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5]44此句也是对云之变化貌的描写,阳光的投射与云的漂浮,相互影响,于浮光掠影中构成了这种忽“降”忽“举”的情状。诗人将此种情状想象为云神对“降神”的徘徊和纠结,也与人的活动十分拟合;“猋”一字的使用,既彰显某种灵动之意,又符合云变化丰富的特征,可谓神来之笔。
蒋骥评《云中君》为:“此篇皆貌云之辞。”[23]可谓一语中的。屈原以一种超现实的角度来呈现云之变化带来的神韵和美感,整篇《云中君》短短数十字,就将云的自然特征——舒卷自如,波诡云谲——描写得活灵活现、妙趣横生,给人一种奇异而灵动的美感。
第二,从自然事物的整体形象出发,抓住其主要特点,进行生动的描绘。比如在《湘君》《湘夫人》《河伯》中,湘君、湘夫人是“湘水之神”,河伯是“黄河之神”。
湘水在南方,有着江南水乡特有的那种柔美与恬静,因此是:
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5]46。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5]50。
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5]50。
远观,湖水澄明如镜;细察,江水汩汩流淌。清风扬波,水泛涟漪,湘水之神翩升于这烟波幽境之中,柔波似语,缱绻缠绵,动荡吐纳间,江南水乡之容态尽显无遗。黄河居北方,有着北国风光那种壮美式的滔滔莽莽:
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横波[5]60。
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纷兮将来下[5]60。
波滔滔兮来迎,鱼邻邻兮媵予[5]60。
河神所到之处,波涛滚滚,奔涌澎湃如神发力;流冰纷纷,冰道塞川如神垂迹。力的壮美与神的行迹相合,将大河非同凡响的壮阔气势展露无遗。
在这两相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屈原在描绘南北之水时,精准把握它们的性质特点,以不同的方式来展现南北水川的情状面貌。两种描写一柔缓一汹涌、一优美一壮美,对照异常鲜明,在突出展现南、北之川不同面貌的同时,又为其增添神性的成分,使得湘水之态、黄河之势显得愈发传神了。
第三,屈原还利用神话的内容和形式来展现自然的形象,比如《东君》。《东君》是一曲日神的颂歌,《东君》以太阳在天空中的“运行轨迹”为依据,融入神话成分,形象地描绘了太阳东升西落的情景:
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5]58。
这一段是写旭日东升的情状。在《山海经》中,日出的地点有很多,汤谷扶桑是其中的一个地点。书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24]《淮南子·天文》中也有记载:“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25]文中太阳神驭马骑龙的情形也是源于“日乘车,羲和御之”的神话典故。对此,《离骚》中也有“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的描述。当东方第一道晨曦刺破黑夜,漫漫长夜褪去,光明降临人间,大地显现,万物苏醒。这样的日出景象在古人眼中是一种非常壮观的天象。光明与黑暗的强烈对照直接刺激人的感官本能,在黑夜中沉睡的生命活力因为光明的到来而重新亢奋,仿佛昼夜之间经历了一场生死的轮回,由黑暗进入光明犹如由死亡进入重生。这样的神性体验使太阳在古人眼中充满神圣的光辉,太阳也因此被古人视作人间光明、希望、正义的化身。正如诗中写道:
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5]58。
天狼星位于东南方,是神话传说中有名的灾星,北斗七星则方位不定,因形状酷似古人舀酒的斗的形状而得名。诗人结合当时的天文知识,借用神话的想象,将太阳西落的情状生动地描绘成“射天狼”“援北斗”的情形,仿佛是太阳神为人们除暴安良后,用“北斗”痛饮了一勺桂花酒。至此,太阳神正义凛然、万丈豪情的英雄形象就赫然呈现在人们眼前了。
由于太阳与人们的生存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是自然之中最早受到人们信仰和祭拜的神灵,所以“日食”现象在古人看来是非常凶险的征兆。张树国认为《东君》就与古代“日食”现象的发生有关,《东君》的祭歌仪式实乃“日食禳救活动”[26]202-208。他进一步解释道:“日食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月球运行太阳和地球之间,成一直线,太阳为月所掩而造成,多发生在朔日。但在原初意义上,古人不可能认识到日食就是‘阴侵阳’、‘月掩日’之说,而宁可相信日食的原因是太阳神和猛兽搏斗造成的,这个猛兽便是天狼,所以伐鼓击钟以及下文的‘举长矢兮射天狼’便是这一心理支配下的巫术行为。”[26]206可见,是大自然的变化灵机赋予古人神性的感受体验,古人再将这种感受体验转化为对自然的认识,在这样的情形下,自然的形象就必然附上一层虚虚实实的神性光辉了。
第四,借用想象之臂来塑造自然神,以瑰丽谲怪的想象来展现自然神。比如《九歌》中的《山鬼》是一首祭祀山神的祭歌。在先秦时期,人们对鬼神并不做严格的区分,鬼神一体,鬼即神,都是古人祭祀的对象。易重廉就曾说过:“在古人的意识里,鬼神之分,的确是不严格的。……《九歌》中有《山鬼》,标明为鬼,人们却目之为神。……《九歌》本身,鬼神早已不分。”[27]孙作云曾作《九歌山鬼考》特意考证,认为屈原《山鬼》的祀主即巫山神女[28],郭沫若、陈子展、马茂元等楚辞学家也都赞成这一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屈原没有沿袭以往的山神形象进行创作,他在对巫山之神采的感性审美中,凭借自己的想象去发挥和创造。从最后呈现的《山鬼》来看,此时的“山鬼”与《山海经》中面目丑陋粗鄙的山神形象已完全不同,此处的“山鬼”形象宛如一位婀娜多姿的美丽少女。诗中写道: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5]61。
屈原笔下的山鬼——巫山神女以高山泉水为生活背景,衣以薜荔、石兰为装,飘带以杜衡、女萝为饰,含睇宜笑,窈窕作态,出行以豹狸为骑、香木为车,在石泉处饮水,在松柏下休憩,衣食起居皆自然,形象气质俨如自然的精灵。这一形象的塑造,幽峻中藏着娟秀,娟秀中又带着某种野性,无疑对应着江南之山清幽秀丽、怪石嶙峋的特征。诗人匠心独运地将巫山之生机神韵、灵秀精华集于“山鬼”一身,浓而不艳,质而不俚,富含灵气。
从审美的角度而言,自然神是自然理想的化身,其形象不仅反映自然本身面貌的美和精妙,而且也凝聚着古人对天地自然、世间万物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经验。从后者来说,自然神俨然是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浇铸,是自然美的化身。要塑造这样一种美的形象,就不仅要使其光辉璀璨,还要使其生动丰满、有血有肉。孟子言:“充实之谓美。”[29]如果只是塑造自然神的外在形象,而没有充实其内在,便不能使其形象树立起来,更无法建立楚人所看重的人神关系。为了充实这些自然神的内在,使其形象“美之可光”,屈原为这些自然神注入了许多人类情感的内容,这也成就了这些自然神的独特之处。在诗人的笔下,所祭之神虽都具有自然神力,却与一般威严肃穆的神明形象迥然不同;它们皆平易近人,富有人情味。诗人歌颂云神“云中君”的辉煌灿烂,但也同时表现出“云中君”的性格多变;诗人歌颂水神“湘君”“湘夫人”的安柔和静,但也同时将“湘君”“湘夫人”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隐含其间;诗人歌颂太阳神“东君”的光明伟大,但也同时展现了“东君”的勇武多情;诗人歌颂河神“河伯”的波澜壮阔,但也同时展现了“河伯”的友好和善;诗人歌颂山神“山鬼”的俊秀清幽,但也同时表现了“山鬼”的美丽多情。屈原以“情”深入自然之象,又以“情”凸显自然的创化,这些缱绻的怀思、为民除害的正义感、携手的情谊和孤独的哀怨,全然是人的情性、情绪和情感。这样,自然之中渗透着人情,而人情之中又漫溢着自然的气息,自然与人情在审美的境界中交响共鸣,恰如宗白华所言,诗人“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30]
从屈原笔下的这些自然神来看,自然的神性美表现为虚实相合、人神一体,屈原让自然性、神性和人性在一种理想形式中实现和谐的统一,在自然“美的形式”和“真的本质”中注入生命的活力,做到“酌奇而不失其贞”[4]48,从而塑造出如此有血有肉、生动丰满的自然神形象。
屈原赋的自然意象、自然意境、自然神形象体现了生态美学所推崇的人与自然是共生整体的关系,且富有古典浪漫主义的底蕴。这种别具一格的生态美呈现主要源于诗人将自己与自然置于一种广阔无限的联系中。具体而言,就是屈原在审视自然事物时,其审美活动是同时在两种维度中协调而成的:一种是现实维度,一种是想象维度。前者作为审美的客观基础,后者则是审美的灵魂和精髓,表现为一种包揽无垠时空、跨越物种界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两种审美维度不是相互对立,而是交叉同行。现实世界常常与想象世界混为一体,在屈原赋中就呈现为一种万象同一、“美美与共”的审美理想境界。其本质和核心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为我们当下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了古老智慧。
由自然形象到自然意象、自然意境、自然神,是从客观到主观的过程,因为自然作为相对客观的存在,人无法与自然实现交流,而把自然作为一种意识化、人格化的对象时,人与自然便拥有了共同的情志和语言,人就可与自然无障碍地交流,甚至其交流的丰富性超越了现实世界的其他交流,物我合一的自然意象、情景交融的自然意境、虚实相合人神一体的自然神形象的出现,都是这一丰富交流过程中所得到的自然形象。从生态美学视野来看这种独特的自然形象,它们正是古代生态智慧“天人合一”观的艺术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