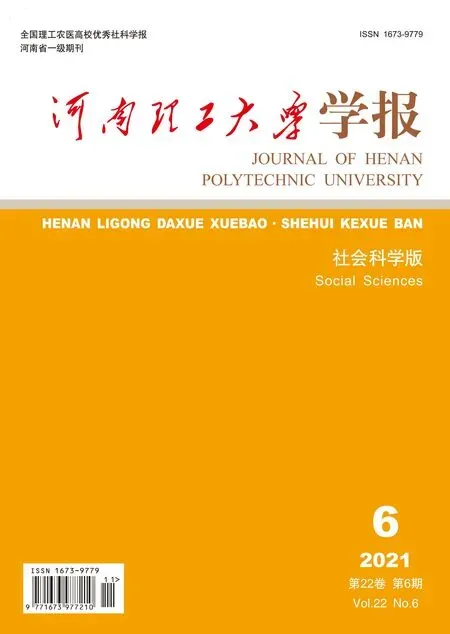论《金瓶梅》中的听觉叙事
陈 晨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 )
听觉是人类认识和感知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相比于其他民族,中国人对声音的接收,对听觉能力的使用更为频繁与敏锐。麦克卢汉甚至将中国人形容为“听觉人”[1]52,听觉这一感官形式之于中国人有着非常悠久的文化传统积淀与应用。因受视觉文化崛起这一人类发展历史上的大趋势影响,人类逐渐淡化甚至忽视对于听觉的关注,然而它作为人类掌握与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从来不曾消亡,小说的叙事方式必然会受到感官形式的影响,只是一直以来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了。自从人文学科的“听觉转向”[2]以来,听觉这一研究维度引起了国内外学者较为广泛的关注。在中国,傅修延等学者对听觉文化的研究有开拓之功,然而这一新的路径还未被深入应用到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研究之中,相关领域的研究尚需深化。听觉叙事是《金瓶梅》叙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中有大量涉及听觉的描写,值得做深入的考察。目前学界较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对《金瓶梅》作相关研究,然而这对于探讨《金瓶梅》的叙事方法与艺术成就,也是一个不可轻易绕过的问题。从这一角度进入文本深处,对作者的思想构思与艺术用心或可有更为清晰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谓的听觉叙事主要指在小说文本之中侧重于听觉这一感知形式,并具有特定意味或功能的相关描写。它不仅与视觉叙事一同参与到整个叙事网络的建构之中,更作为一种叙述动力推动了文本空间的演进,作为一种叙述手段参与了小说人物塑造。本文试图探寻《金瓶梅》中听觉与叙事之间的联系,并以此作为深化文本叙事分析的新途径与新方法。
一、听觉作为叙事的重要维度:与视觉叙事的互补与互建
听觉与视觉都是人类感知世界的的重要范式,感受世界的主要来源。虽然两者所倚重的人体器官不同,各有侧重的领域与对象,但在很多情况下,两种不同的感官形式协同互补,共同建构人的感性经验。加拿大学者梅尔巴·卡迪基恩曾经提出“耳朵可能比眼睛提供更具包容性的对世界的认识,但感知的却是同一个现实。具有不同感觉的优越性在于,它们可以互相帮助”[3]456。在叙事网络的建构中,听觉这一感官形式确实不应该被遮蔽与漠视。
人的身体构造决定了视觉感官更多地在日间发生作用,听觉的效用一般在夜间得到凸显。在夜间,视觉是弱效甚至失效的,听觉便自然成为了一种补充。由于一种感官的失效,导致另一种感官的放大,因此听觉就在夜间叙事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在夜间叙事中,听觉这一感官形式有时是在视觉失效时独自发挥作用,但更多情况下是与视觉叙事互为补充,共同拓展小说的叙事内容。在第十九回中,李瓶儿心心念念的愿望终于成真,百般曲折之后嫁入西门府,没想到等待她的却是羞人的冷遇,于是李瓶儿选择悬梁自尽,这一事件正好发生在夜间。刚娶进府中的小妾悬梁自尽,这是一件大事,而这一消息的传递主要依靠传达者的声音与接受者的听觉,接受者又成为新的传达者。两个丫鬟一觉醒来见灯光昏暗,发现李瓶儿上吊这一事件,这是视觉发挥作用。二人将这一消息传递给隔壁的春梅与金莲乃是通过声音传递。西门庆此时正在玉楼房中喝酒,“正说话间,忽听一片声打仪门。”[4]226这突然而响的打门声中隐含着春梅所带来的消息,昭示着李瓶儿自尽这一消息通过这种方式传入西门庆之耳,听觉效用在此时就已经发生。后来吴月娘与李娇儿也都听到这一消息来到李瓶儿房中。李瓶儿上吊这一事实的发现靠视觉来完成,而这一消息的传播却主要靠声音与听觉完成。
夜间密约幽会是《金瓶梅》中常见的情节,而在这一情节模式中,声音与听觉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十三回中李瓶儿与西门庆隔墙密约是此回的主要内容之一。她令丫头绣春向西门庆传达夜间约定:“晚夕娘如此这般,要和西门爹说话哩。”[4]176如此这般是哪般?这到后文中才有揭示,二更时分李瓶儿打发花子虚去院里吃酒,西门庆便推醉来到家中。“良久,只听的那边赶狗关门。少顷,只见丫头迎春黑影影里扒着墙推叫猫,看见西门庆坐在亭子上,递了话。”[4]177在这一段描述之中听觉这一感官占据主导地位,迎春在黑影中扒着墙,是有意使视觉的效用降低,避免金莲房中人看到,而推叫猫是因为在黑夜视觉效力减轻,必须使听觉系统发挥作用,于是以声音引起西门庆的注意,李瓶儿与西门庆的夜间幽会因此得以完成。在第八十二回中潘金莲与陈经济的月夜之约也穿插了一系列的声音信号,听觉在这一叙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潘金莲与陈经济之间本就属于不正当关系,故二人之约自然要避人耳目,又由于这一事件发生在夜间,所以声音无可避免地会得到某种程度的放大。当晚,西门大姐被吴月娘请去听宝卷,而西门大姐的不在场是潘陈二人偷期实现的必要条件,故西门大姐的其他场域之听是必要的。二人又要避免大姐随时可能回来,所以此时丫头元宵具有提示功能的叫门声就十分重要。既然是避人耳目的密约,双方的信号是偷期得以完成的前提。“原来经济约定摇木槿花树为号,就知他来了,妇人见花枝摇影,知是他来,便在院内咳嗽接应。”[4]1429花影为视觉信号,咳嗽为听觉信号,缺一则两人苟且之事难成。二人如此非只一日,又终被丫头秋菊听得,“夜间听见这边房里恰似有男子声音说话,更不知是哪个了”[4]1437。这又为日后二人奸情的被发现与被揭露埋下线索。潘陈二人偷期密约的整个过程中,声音信号点缀其间,听觉效用时常发生,二人行为的隐秘龌龊的意味也因此得以显现。
《金瓶梅》中充满了无所不在的偷听与偷看。田晓菲曾说《金瓶梅》乃是“一部充满偷窥乐趣的小说”[5]45。然而她只提到了关于视觉的维度,却忽略了听觉这一维度,与偷窥相对的窃听也时常在小说中出现。当然这两者在某些情境之中是不可完全割离开来的,区别只在于在具体的情节之中更侧重于听还是看。在第八回“烧夫灵和尚听淫声”一节中,更多的主要侧重于“窃听”这一层面,虽然此处的窃听行为是也以视觉作为补充的。“当时这众和尚见了武大这个老婆乔模乔样,都记在心里。”[4]112此时,潘金莲的容貌已经形成图像通过视觉作用呈现于众和尚的脑中并引发某些联想。然而,毕竟众僧的集体性欲想象却是主要通过“听”这一行为得以完成。于是,听觉发挥了视觉的替代性功能,和尚通过听觉的触发完成声音接受与图像形成的双重功效,加之一种集体性想象的加工,共同完成了一场盛大的意淫狂欢,讽刺意味毕现。烧夫灵之际,潘氏没有任何作为妻子的悲痛,作为凶手的愧疚,反而与西门庆沉沦欲海,表明潘金莲人性彻底泯灭并完全为欲望所操控。僧人本应六根皆净五蕴皆空,而在这里却全然没有佛门中人的半点影子,只有卑劣的窃听,暴露出他们肮脏龌龊的内心,佛性的庄严与清净被完全消解。而这两个层面讽刺意味的传达却皆与窃听这一行为有关。
在《金瓶梅》中,偷窥与窃听很多情况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小说文本之中“听觑”一词出现的频率很高,这一词语就包含视与听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暗中窥听行为本身。在第二十一回中,西门庆与吴月娘的和解便是因为一次偶然的听觑。“于是潜身立于仪门内粉壁前,悄悄试听觑。”[4]289首先西门庆通过视觉看到丫头小玉在穿廊下放桌,片刻之后看到“月娘整衣出房,向天井内满炉炷了香,望空深深礼拜”。这些画面都是通过西门庆之看呈现,是其视觉发挥作用。接着西门庆便听到了吴月娘至诚的祷告之词,心中不禁大为感动。这时西门庆才知道吴月娘是真心诚意地为这个家着想,二人遂重归于好。在这里视与听都是不可缺少的,缺少视觉画面的呈现,吴月娘的祷告之词就失去了出现的具体情境,缺少祷告声音的传达,西门庆便无从得知吴月娘的真实心意,二人的矛盾就无法消解。由此可见,很多时候视觉与听觉是交融在一起的,一旦某一项感官形式消失,就无法形成整体性的感觉经验。
二、两种特殊的听觉类型
听觉叙事在《金瓶梅》中有多种表现形态,不同听觉类型的运用会在叙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听觉类型根据不同的分类方式可分为常听、偶听、偷听、幻听等。限于篇幅,不能对其一一进行分析,故聚焦于幻听与偷听两种特殊的类型,但是听觉叙事的其他表现形态会贯穿于文章其他部分的阐释之中。
幻听是听觉表现形式之一,它是人在某种特定情景状态之下对于声音的反应。傅修延曾提及幻听这种听觉类型:“如果说幻听是感觉到了子虚乌有的声音,或是把一种声音听成另一种声音,那么这两种情况在正常人身上也时有发生。”[6]前者表现为无中生有,后者表现为主观性替置。三十八回中潘金莲的幻听就属于主观替置性的幻听:“猛听的房檐上铁马儿一片声响,只道西门庆来到,敲的门環儿响,连忙使春梅去瞧。他回到:‘娘错了,是外边风起落雪了!’”[4]563明明是风吹房檐下的金属片响,而潘金莲却以为是西门庆来家扣门环的声音。两个声音是有相似之处,但是却也有差别,作为听觉高手的潘金莲,如何却会听错。西门庆娶了李瓶儿,又包占了王六儿,身心皆被占据,已经很久未来金莲房中。潘金莲此时的幻听显出她对于西门庆的思念之切,争宠之切,以及对欲望疏解的强烈渴求。因此细微的动静都会使其向相关的方面联想,这时客观的声音已经成为人物主观化了的声音。
从精神医学的角度,“幻听是大脑听觉中枢对信号错误加工的结果;正常人的听觉将从内外部获取的声音信号正确地向听觉中枢传输,而幻听者由于听觉中枢出现变异,将声音信号歪曲或夸张,甚至按主观意图加以改造,因此这种情况可以看着是听觉变态或听觉的主观性臆造”[7]15。这表现为真实世界声音与心理世界声音的重叠交错或篡改替换,大脑无法对两者进行清晰明确的界定,这是精神错乱而导致的知觉感官失灵。当人的欲望无法达到满足却又强烈需要释放,而释放的过程受到阻碍的时候,就会造成精神上或心理上痛苦或者被压抑的状态,这种状态共同作用于人的肉体与心理,严重时会造成心理人格的分裂与骤变,形成某种精神疾病。幻听是精神或心理失衡的具体表现,但同时也是一种治疗方式。人类都有趋避痛苦的本能,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的欲望却通过幻听得到心理的补偿,减轻自我精神上所承担的痛苦,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心理自卫机制。潘金莲虽然没有达到患有精神疾病的严重程度,但其欲望之强烈,心理之阴暗,行为之偏激也暗示着她在心理上已经出现了某种病态的倾向,而这次幻听只是其变态心理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偷听这一听觉类型在《金瓶梅》中的表现形式更为多样,有主动的偷听,偶然间撞到的偷听,无意之听复变为有心之偷听等种种形式。偷听行为的实施者覆盖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西门庆的妻妾们、府中丫鬟小厮们、做法事的和尚们等等。关于偷听行为的叙写几乎贯穿整个故事脉络,是《金瓶梅》听觉网络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行为不仅影射出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心理、生活环境,更是作者丰富叙事的重要艺术手段。如果从更深层次去分析,他们为何会偷听,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目的与动机?这都是值得讨论的话题。
偷听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搜集获取信息,偷听频率最高的是西门庆的妾室以及府中的仆人们,这与其所处的地位与生存处境有关。作为西门府男主人的西门庆很少主动偷听,他位于西门府权力的顶端,无需通过这种方式维系自己的地位,更不需要通过偷听进行利益的算计。吴月娘也极少偷听,她是西门庆的正妻,这是其他妾室如何争宠都无法撼动的地位,并且偷听这一行为也与吴月娘的性格并不相符。李瓶儿深得西门庆的宠爱,同样不需要偷听。西门庆的其他妾室与仆人们如此热衷于偷听恰好说明了他们地位的低下以及生存处境的艰难。与此同时,这又与各自的性格相关,有强烈自尊或者柔软温和的人不会偷听,争强好胜或拜高踩低的人却很有可能会偷听。妾室之间勾心斗角只为争得西门庆施舍的一点恩宠,仆人内部的互相算计只为获得一点蝇头微利。他们只能靠偷听到的只言片语来判断眼睑三尺之内的所谓形势,做出自以为高明的决策,实施诡诈的计谋,却无法窥破自己身处泥沼徒劳的挣扎,何其可怜又何其可悲。相比之下,这一听觉类型在世情小说中尤为常见,也正说明世态人情的复杂以及人心的曲折幽微。
这当然也受人类居住模式的影响,“人类的群居模式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听觉空间的公共性质,在一个众声喧哗、隔墙有耳的集体社会中,任何人都难以避免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到,也无法阻挡别人的话语传入自己的耳中”[6]。西门府就仿佛这样的一个隔墙有耳而又众声喧哗的小型集体社会,所以窃听这一行为时常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与当时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也有关系,费孝通认为“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8]61,乡土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会对人际关系的交往产生影响,甚至形成约定俗成的伦理准则。在中国古代的熟人社会中,关系的远近基本上是以血缘与地缘决定的,在它们所辐射的熟人范围内,人们是互相了解和熟知的。甚至彼此之间了解的程度越深说明两人之间的关系更为亲近。如果有人过分强调所谓的隐私,刻意树立与他人的边界,是会被其他“熟人”排斥在外的。这就导致人们对于隐私的概念极为淡薄,个体之间也没有特别清晰的界限感。再加之人类本身好奇心的作用与发酵,偷听的行为就变得极为普遍。
《金瓶梅》描绘了一个欲望横流的世界,情欲是其中的重点表现对象,偷听则是故事中人物释放欲望的手段之一。无论是西门府中的女主人如潘金莲,还是丫鬟小厮如迎春、秋菊、平安、画童、琴童等,甚至本应是方外之人的和尚,都通过偷听他人的情事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欲望的替代性满足要以听觉系统为主要媒介之一,这是有心理学基础的:“从耳朵里传达进去的性的刺激是多而且有力,其多而且有力的程度要在我们平均想象之上。”[9]81从性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声音对于情欲的激发效果非常显著。日常压抑的欲望需要获得疏解的渠道,虽然他们所选择的渠道是以尊严的降格与丧失为代价的。除了情欲的释放之外,他们以偷听打发无聊的时光,正因内心无所依托、荒芜狼藉,所以不惜利用这种不光明的手段,寻求一点所谓的刺激,对于偷听情事的热衷也正映射出他们百无聊赖的精神状态。
三、词曲:一种重要的音景场域与听觉空间
音景形成的同时往往也意味着听觉空间的出现,如词曲或宣卷所营构的音景与听觉空间,但以往研究者对文本中所隐藏的这个空间大多是漠视的,声音所构成的场域空间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音景即声音所构成的景观,声音是听觉产生的本体之源,它可以界定空间属性,音景场域在另一层面也可称之为一种听觉空间。
词曲这一音景在整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音景形成之时也意味着听觉空间被营造出来。因为某种音景场域之内,一般是有听众存在的。当它作为一种音景出现时,发声者与听众往往都是故事中的人物,有时为独唱独听,有时是众人共听,这两种细分的听觉空间有不同的特点和功能。独唱独听式的词曲音景一般有利于某种氛围意境的生成以及对人物心理的深入挖掘;众人共听式的词曲音景更为复杂,它有时还夹杂着故事人物的对话交流,是多重音景的融合。这一音景场域与听觉空间的营构对于叙事内容与情节结构的设置都有重要的作用。
潘金莲比旁人更“晓得曲子里滋味”,她经常独奏琵琶吟唱小曲,很多情况下这个音景空间的听众也只有她一人。在小说第一回中,张大户将她嫁给武大,她内心的不甘与痛苦在这个音景场域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常无人处弹个《山坡羊》为证:想当初,因缘错……奈何?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甘美!”[4]12潘金莲聪明灵巧,武大却猥琐不堪,她本应配嫁好儿郎,却偏偏买金的遇不到卖金的。这种抑郁愤懑与凄凉不甘的复杂心绪无人可以表露,只能尽付词曲之中。与此类似的还有第八回西门庆刚娶孟玉楼,二人正如胶似漆,潘金莲久盼西门庆不至,夜间又弹唱了多个小曲。潘金莲为自己营造了一片听觉空间,她自我倾诉也自我倾听,无人怜爱便自我怜惜,她内心的独孤哀怨之情在自吟自听中又显露了几分。当她如愿嫁入西门府后,情感心理的挣扎并未减少,贪淫好色的西门庆并非良配,她陷入了更漫长的等待与更愁闷的煎熬之中。
第三十八回“潘金莲雪夜弄琵琶”一节,潘金莲再次久等西门庆未至,只能自己弹唱词曲遣闷,却只等来一场冬夜的簌簌飘雪。当她得知西门庆正与李瓶儿恩爱情浓之时,内心的孤独与悔恨,欲望无从浇解的焦虑与忧愁,再次在她所营造的音景场域内得到展现。哀怨之曲伴随着落雪与风声,更显凄凉落寞。但潘金莲不愧是听觉空间的建构师,这不同于以往的独唱独听,她又刻意拉入了两名听众,琵琶之音恰被处于李瓶儿房中的西门庆听知,引起了西门庆的注意。潘金莲此次弄琵琶定非无心之弄,聪明如潘金莲,怎会不知两处相邻甚近,此处之琵琶语,彼处必然闻之。她依靠琵琶成功引起了西门庆的注意,最终获得西门庆的一夜留宿权。潘金莲刻意营造了一个双方共闻的听觉空间,这是其工于心计处,但与此同时,她细腻敏感的心理,争强好胜的性格,炙热浓烈的欲望都通过这一空间表现出来。
俗语有云,无曲不成宴,这在《金瓶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词曲所形成的音景是大小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众人听曲更是西门府的家庭常态。无论是生日节日、喜丧嫁娶、朋友相聚、接待官员等都必有宴会,而词曲所营构的音景空间是宴会中不可缺少的亮色。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听众范围扩大,所以这一听觉空间所起到的作用功能显得更为复杂。这一音景空间很容易引起人物的情感波动或引发某种动机,从而直接影响到人物的心理叙事以及故事的情节走向。
第七十三回中,西门庆因思念李瓶儿点了一套《忆吹箫》,引起了潘金莲的不满,在席间与西门庆起了争执,可见潘金莲的心小量窄;生日宴会本是欢喜的氛围,西门庆偏偏点了一套离别之曲,念起了亡故之人,又可见西门庆贪婪淫逸之外重情的一面。宴会有时源于社交的需要,或许双方都有明确的社交目的与动机,但是在中国古代的人情社会中,双方情感之间的关系强弱直接影响到动机能否实现,词曲所营造的听觉空间有助于双方情感的联络。如果单谈目的动机,未免过于冰冷现实,词曲这一音景有一种柔化氛围的效果,使得双方的谈判得以顺利进行。如三十六回中西门庆意初欲结交蔡状元时,酒席刚开始时,就令苏州戏子及书童五人唱词唱曲。这一音景空间的制造有利于迅速拉近双方的距离,实现西门庆人情投资的目的。四十九回中,更是在西门庆刻意营造的词曲听觉空间中实现了双方的权钱交易。大多时候,听词曲只是西门府等富贵人家消遣娱乐的方式,可是小说前半部文本之中所形成的热闹喧哗的词曲音景,也正反衬出西门府没落之后的寂静苍凉。西门庆死后,妾室离心、伙计拐财、仆人欺主、昔日朋友更作鸟兽散,热闹的音景再难重现,也没有听众来重构往日的听觉空间,人情世事翻覆无常的哲理意味也在两重听觉空间的对比中得到了深化。
四、听觉叙事的基本功能
西门府中人物的家庭生活是《金瓶梅》的描写重点之一,其中人物的矛盾冲突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小说情节演进的动力构成,听觉叙事在其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此外,听觉叙事又与小说人物的塑造有密切关联,主要表现为人物内在心理的揭示与性格特征的呈现。
(一)情节推衍的动力构成
矛盾冲突是故事情节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小说中的很多矛盾恰是源于声音的传达以及听觉效果的生成。言语者的有意为之,听者的有心听之,往往引发某种冲突,矛盾冲突不仅成为情节演进的根本动力,也在小说叙事中构成一种特殊的张力效果。
各种大小不等的矛盾贯穿于西门府人物的日常生活之中。
潘金莲与孙雪娥、宋惠莲、李瓶儿、吴月娘等妻妾之间都存在重大的矛盾冲突,环环相扣的听觉作用使得叙述的动力不断得到加强,直接推进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以潘金莲与宋惠莲的冲突为例,二人矛盾的缘起乃是潘金莲在藏春坞月窗下的一场潜听。坞内言者无意,坞外听者有心。当潘金莲听知宋惠莲的脚比她小,并且还曾套着她的鞋子试脚,已十分不快,当她听之宋惠莲说她久惯老成,与西门庆是露水夫妻时,已记恨在心。此为听觉效用在此矛盾中的第一次凸显;孙雪娥将宋惠莲与西门庆私会之事告知来旺儿,来旺儿听记在心,此为听觉效用的第二次发挥。这直接导致来旺醉后毁谤西门庆与潘金莲,却被宿敌来兴儿听见,此时听觉再一次促使矛盾激化,来兴将此事告知潘金莲,潘金莲又将此言告知西门庆,来旺儿被陷害。然而宋惠莲的一番言语又让西门庆生出放过来旺之心,但是潘金莲却一再想致其于死地,故一直用言语挑唆西门庆,这导致了来旺被递解徐州,宋惠莲第一次轻生。这次轻生被解救,潘金莲仍不甘心,又在孙雪娥与宋惠莲之间搬弄口舌,最终导致了宋惠莲之死。在二人的这场矛盾之中,听觉作用贯穿始终,潘氏藏春坞下的窃听,雪娥将消息透露给来旺儿,来旺之言被人窃听,孟玉楼的无心之言,潘金莲的极力挑唆,这无不与听觉关联密切。作者通过听觉制造巧合的叙事形态,促使一个叙事空间向另一叙事空间不断演进。
潘金莲与李瓶儿是《金瓶梅》中极为重要的女性形象,二人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小说叙事的走向。潘李关系紧张的关键点仍是潘金莲的一次潜听,但是听觉在与二人相关的情节叙事中持续而剧烈地发挥作用,直至李瓶儿之死。在二十七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一节中潘金莲由于这次潜听,得知李瓶儿怀孕的消息,这加剧了她的妒意与恨意。这嫉恨之意随着官哥儿的诞生,西门庆宠爱对瓶儿宠爱的炽盛而愈加强烈,两人之间关系渐趋紧张,一直持续到李瓶儿生命的终结。李瓶儿之死是全书的重要节点,听觉效用的发生加速甚至直接触发了李瓶儿之死。“气”哪怕并非李瓶儿病痛的触发因素,也是加剧李瓶儿病症的重要原因所在。潘金莲见李瓶儿日益得宠,便时常与李瓶儿斗气。二人所居之处临近,如此便为声音的传达提供了便利。潘金莲常使用的计策就是打骂丫头秋菊,指桑骂槐,使声音传播到李瓶儿所居院落。但李瓶儿每一次都选择忍气吞声,这对于身体的损伤是极大的。尤其是潘金莲将官哥蓄意谋害之后,李瓶儿本就伤心过度,身体极为虚弱,而潘金莲小人得志,又明骂丫头,暗讽瓶儿。“李瓶儿这边屋里分明听见,不敢声言,背地里只是掉泪。着了这暗气暗恼,又加之烦恼忧戚,渐渐心神恍乱,梦魂颠倒,且每日茶饭都减少了。”[4]937如果说潘金莲对官哥儿的蓄意谋害是给李瓶儿的沉重一击,那么她多次将李瓶儿放置到她所营造的听觉空间中,则直接加速了李瓶儿的死亡。李瓶儿之死仿佛敲响了西门府的第一声丧钟,盛极终要转衰,到此《金瓶梅》故事情节的推衍已过大半。听觉效用的产生是小说重要的叙述动力,它促发了诸多关键节点之间的连接,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故事情节的设置与演进。
(二)人物塑造的重要手段
在《金瓶梅》中,听觉叙事与人物形象的塑造紧密相关,这主要表现为对人物内在心理的揭示与性格特征的呈现。听觉是人获取外部世界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如何利用听觉这一感官并通过这一感觉形式处理信息与人物本身的性格和心理有密切之联系。《金瓶梅》作者通过营造与利用特殊的听觉空间和听觉形式来展示人物的内在心理,并通过特殊的听觉表现样态与人物对言语声音的不同反应来凸显人物性格。小说中用于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是多样的,但听觉叙事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作者对潘金莲的心理描写是细致而深刻的,她本身就是一个心理情感复杂的人物形象。她本性就并非愚痴之人,又生得聪明伶俐,又加之音乐词曲的熏陶,心理情感自然丰富细腻。然而坎坷的身世境遇扭曲了她的性格,所以,敏感变为多疑,聪明变为算计。作者对潘金莲的心理刻画着墨颇多,并时常利用特殊的听觉形态或听觉空间揭示其隐秘幽微的心理。她雪夜之中的幻听也表明了她内心的空虚与落寞,情爱已经成为其人生的全部寄托。人生辽阔,终不能靠情爱填饱,她如同处在精神的荒漠之中,一次次地饮鸩止渴,却只是加速了自我的毁灭。
偷听是听觉叙事的一种表现样态,这一行为也多发生在潘金莲身上。这与其性格有关,她生性多疑,故总爱于背阴后听人言语。“性极多疑,专一听篱察壁,寻些头脑厮闹。”[4]137声音本应该是有界限的,潘金莲却通过频频越界的方式搜集声音,并且将扭曲后的声音再次传递给他人。她通过声音的搜集、传递来挑起事端、控制他人、实现自我目的。西门府的妻妾,主仆众多,却都无如潘金莲利用听觉之甚,这也显示出其争强好胜、性格多疑,阴险狡诈等种种性格的侧面。
小说人物的交流与对话有时可以形成独特的音景,它也是听觉叙事的组成部分。听觉系统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是声音信息传递的媒介物,有人听而不闻,有人闻而不应,这又与人物的心理机制与性格特征相关联,当听觉效用发生之时,对于言语的不同反应,也体现出人物的不同性格。潘金莲之所以是听觉高手不仅在于她会听,还在于她会利用别人之听达到自己的目的。李瓶儿听到潘金莲的言语挑衅并没有针锋相对地反击,反而忍气吞声,这自与其嫁入西门府后温柔包容的性格有关。吴月娘因处正妻之位,府中总有人向她有意无意的传递各种信息,而她的大多数反应是默不作声,这也正与她的性格特点相符。至少从表面上看,她是温和贤良的,所以不可能像潘金莲或者府中的仆人们一样到处搬弄口舌。“不言语”还往往暗示着隐藏在无声之下的复杂心理活动,有研究者认为吴月娘性格中有奸诈阴险的一面,或与此有关。作为《金瓶梅》中重要的女性之一,庞春梅的性格更为鲜明。在第十一回中,春梅只因被金莲凑巧骂了几句,便在厨房生气发狠,孙雪娥的一句无心之言,便使得她暴跳如雷,因此引出潘金莲与孙雪娥的一番是非。与之相呼应的还有七十五回“春梅毁骂申二姐”一节,春梅对于声音信息的反应如此强烈,这是与其独特的个性有关的,她的自尊心极强,内心极傲,将个人的自尊看得极重,但她心中又有不容人碰触的敏感区域,所以她对别人的话语极为在意,其听觉感知也就更为敏锐。由此可见,对听觉这一感知形式运用得是否充分以及对声音信息的处理方式,都会直接作用于小说人物本身的建构。
五、结 语
听觉叙事在《金瓶梅》中是值得关注的叙事现象,是窥探作者思维构思与艺术成就的重要窗口。作为一种叙事方式与叙事策略,听觉与视觉共同参与了小说叙事网络的建设。环环相扣的听觉叙事不仅产生了巨大的情节推动力,在呈现人物性格与深入剖析人物心理方面也起到巨大的作用。由此看来,听觉在小说文本之中发挥着多层次的功能与作用。从这一路径进入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对其中所含深层内蕴进行分析也有利于推进小说叙事中听觉复位,重新赋予听觉应有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