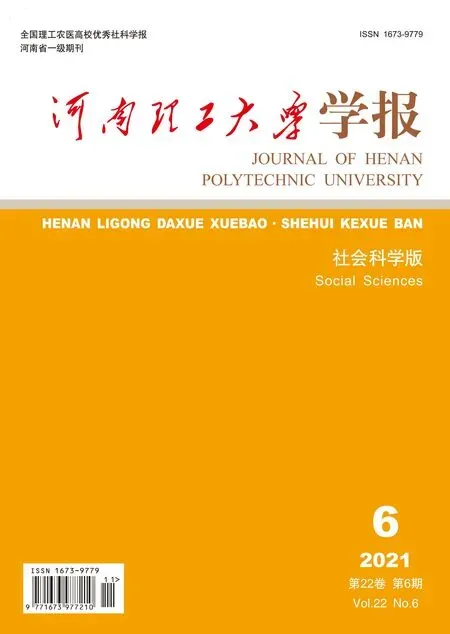明代乡会试贡院研究述评
郑 欣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明代乡会试贡院是科举考试的专用考场,故其成为保证明代科举制度长期稳定运行的基础设施和运行载体。学界涉及该论题的研究大致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但随后进展缓慢。在2007年,有学者指出对明代贡院制度的研究“迄今只是在个别论著中有零星的介绍,尚无一篇对其进行专门探讨的学术论文”[1],十几年过去了,该研究有何进展和不足?本文拟对此试作述评,以期为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参考。
一、明代乡会试贡院的修建历程
学界对明代乡会试贡院修建历程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属个案探讨,其中因顺天贡院系乡、会试两用贡院,应天贡院“为天下贡院首,其制度亦为四方所取法”[2],故学界对此二座贡院的探讨较其它贡院更为深入。相关成果梳理出的明代多地贡院发展脉络,是贡院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内容。
关于明代顺天贡院,张振华指出其于永乐十三年在元代礼部旧址上兴建[3]。河边指出该贡院在正统三年、十一年及万历二年进行过修建[4]55。龚笃清论述了万历二年顺天贡院因狭小而拓建的情况[5]363。张森指出此贡院在天顺七年发生火灾后也进行过修复性建设[6]。
针对应天贡院,龚笃清指出明初应天“原无贡院,每次开科,借京卫武学为之”,景泰五年才将罚没的罪臣旧邸改建为贡院[5]364。马丽萍认为这“奠定了江南贡院的基本格局”,并探讨了嘉靖十三年、万历二十九年的修建情况[7]。孟义昭对天顺间应天贡院的两通碑记进行了分析,得出应天贡院创立于“景泰五年至七年之间”的结论,并探讨了弘治四年、嘉靖十三年、隆庆元年以及万历六年、二十九年、四十三年等六次修建该贡院的情况[8]。
在明代十三布政司乡试贡院中,学界最先讨论的是云南贡院。早在1993年,朱惠荣、马荣柱就对云南贡院在明景泰的创建和弘治十二年的迁建做了较详细的叙述,并提到嘉靖、万历朝也各有过一次修建[9]。史红帅认为明代陕西贡院始建于景泰间,增修于嘉靖四年,嘉靖十九年的重修奠定了明清陕西贡院基本格局[10]。周会娟对明代广西贡院在洪武初年、天顺间的两度迁址和嘉靖四年的重修做了梳理[11]。张玉娟论述了明代河南贡院在宣德九年、天顺六年、弘治十年的修建情况[12]237;随后武明军补充了河南贡院在嘉靖四十三年和万历七年的两次修建情况[13]。王雅秀简述了明代山西贡院在正统十年的创建与万历元年的增修过程[14];李嘎、王雅秀则补充了隆庆四年山西贡院为防火将号舍由木制改为砖砌的情况[15]。李兵指出弘治七年、嘉靖九年贵州地方官两次请求设立贡院未果,直到嘉靖十六年朝廷才同意设贡院[16];王力进一步补充了弘治十二年贵州巡按张淳曾请求设贡院的内容,还探讨了贵州贡院在嘉靖间的创建和万历二十二年的修整情况[17]。
二、明代乡会试贡院的选址
最早关注明代贡院选址问题的研究者是史红帅,他认为明代陕西贡院改变了元代时位于城东南角的布局而建在西安城西门内北侧,其原因一是“与南北院门官署区较近……便利了主管官员考试时的监临”;二是此处“居民不稠,可扩大贡院基址”;三是“相对僻静,宜于做好考试时的保密、防范工作”[10]60。
随后刘海峰、李兵则首次从共性层面总结贡院选址特点,认为“明清时期贡院多坐落于京师和省城的城东或东南,以表东方文明之意”。此为学界对明代乡会试贡院共性研究的肇端,但因限于写作主旨和篇幅,未能进行更深入的探讨[18]320。
马丽萍总结了明清贡院选址的考量因素,除风水因素外,还提出两条新观点:一是根据地势、交通等因素变通,择便于供给和扩建之地;二是借用已有建筑以节约成本[19]。随后马丽萍在其硕士论文中将其观点进一步提炼为“占风水之吉地”“择交通之便利”“借城中之活水”“借旧时之公署”“与商市之结合”[7]。
在马丽萍之后还有一些个案研究对选址问题有所补充。王雅秀论及明代山西贡院“位于城东南隅地势相对较高之处,可减少夏季城内水患带来的损失”[14];武明军提出明清河南贡院数次迁址考量因素之一为“现实因素”,即选址需“地势高亢干燥”[13]。二文均指出了贡院选址过程中对防范水灾的考量。
三、明代乡会试贡院的建筑规制
贡院是科举制度的物化,其规模、形制均是对科举考试的“量身定制”,故探讨贡院建筑规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科举制度。学界目前主要探讨了建筑布局、单体建筑形制、建材等三方面问题,相关研究进展如下:
朱惠荣、马荣柱最先论述了明代云南贡院的建筑布局,指出贡院中心的大堂为至公堂,其后为监临、提调、监试、考试四房,其左右为弥封、誊录、对读、供给四所,至公堂前为明远楼,明远楼东西处为文场,贡院四角有用于瞭望的高楼。再往南为龙门、仪门,门外设牌坊。该研究基本将贡院外帘主要建筑及相对位置呈现了出来[9]。
随后史红帅对明代陕西贡院布局做了探讨,认为其可被划分为三个区域:“机要区”“试场区”和“考官休憩区”,这种对贡院分区的思路常为后来者所借鉴。相较于朱惠荣、马荣柱描述的云南贡院布局,史红帅考察出陕西贡院至公堂以北有二座东西相对的收掌试卷房和一座“为国荐贤堂”;注意到了分隔内外帘的“文衡门”;指出文衡门以北依次为“五星堂”“聚奎堂”“主考厅”,五经房分列主考厅左右;还提到五星堂前设有水池,用于防火且有开风气、广文风之意。作者自绘“明清时期西安城贡院内部平面布局图”,对之后的研究有重要的示范作用[10]。
刘海峰、李兵认为“明清各地贡院在建置上是整齐划一的,只是规模大小不同”,并将贡院结构分为三部分:一是“以明远楼为中心的贡院主体建筑”、二是至公堂、三是内帘部分。作者还注意到内帘的中央建筑“于顺天贡院称为聚奎堂,各省多称衡鉴堂或衡文堂、抡才堂”,并指出内帘中除聚奎堂外,“还有内收掌、内监试、内提调等部门以及刻字房和印刷房”[18]320。
之后的几位研究者进一步补充了贡院中其他建筑物的分布情况或对贡院分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河边提到明代顺天贡院会经堂后有“十八房”[4]。李兵认为明清贡院区域可分为“号舍与明远楼”“外帘部分”“内帘部分”[16]。龚笃清提出明代应天贡院中建有飞虹桥,至公堂旁有外帘官宿舍[5]365。张玉娟指出明代河南贡院文衡堂旁有寓居堂,内帘门与至公堂之间有监临等官讨论公务的场所——洗心堂,贡院“前二门之外有搜检官寓所”[12]。马丽萍将明清贡院划分为“候场区域”“试场区域”“外帘办公区域”“内帘办公区域”四部分,对贡院建筑的研究范围进行了延展,还指出了贡院候场区域有吏舍和外执事官厅,内外帘中有厨房、浴室等辅助用房[7]。王力将明代贵州贡院划分为“内帘区”与“外帘区”两部分[20]。郭培贵认为贡院可分为“考官出题、评卷所在场所”和“考生考舍”两部分[21]。张延昭以明远楼为分界,将“贡院前半部空间”分为了“考场区域”“考务区域”两部分,还认为明远楼对贡院建筑整体布局有重要影响,即“占据了至公堂前甬道的空白点,将甬道截为两段,减少了考生可能聚集生事的空间”“与位处前场四角的瞭楼相呼应,形成全景监视的效果”“形成对号舍的多重‘压制’,从而营造出对比鲜明的独特氛围”[22]。
学界对贡院单体建筑形制的研究中,着重探讨了号舍和明远楼,对其他建筑略有涉及。
刘海峰、李兵指出明清贡院“每排号舍编为一个字号,用《千字文》排列”,每一字号内的号舍“约有五六十间到百余间,均面向南排成一条长巷”,巷宽4尺,巷口有栅门,并配备号灯和水缸,每排号舍末尾有厕所,“每间号舍三面用墙围住,南面没有门”[18]321。刘海峰在其随后的著作中指出洪武十七年“贡院内考生所处的地方也还是称‘席舍’,而尚未称号舍。大概至迟到明成祖永乐十年(1412年)以后,具有明远楼和号舍的贡院形制已形成了”[23]289。龚笃清考证出了明末贡院号舍的具体尺寸;认为号舍屋顶盖瓦,为一面坡走水,每间以砖墙隔开;还探究了明末号舍的活动坐板式设计——“每间之三面,都是墙,离地约二尺,砌成上下砖缝两层承板,置阔之木板二块,长宽与房间相等,而可以抽动”[5]366。刘海峰则认为直到清雍正十年京师贡院才首先将砖土坐凳改为坐板,“估计随后各省贡院也逐渐跟进”[24]。张森估算明末顺天贡院有号舍6000余间[6]。王雅秀指出明代山西贡院有号舍4000余间[14]。王力提出“嘉靖十六年至万历二十二年间贵州贡院号舍的数量应在九百到一千三百之间为宜”[20]。郭培贵认为贡院“‘席舍’就是号舍,都是指称考场。席舍之‘席’,是用来说明建‘舍’的材料”,每考生“一舍”的“‘号舍’式考场结构”在洪武十七年时已形成[25]208。裴家亮指出,应天贡院创建后“号舍达到三千间”,嘉靖十三年达3700间,万历二十九年增筑300余间[26]。孟义昭指出应天贡院在万历七年时有5000余间号舍,四十三年,又新建200余间[8]。郭培贵指出应天贡院“万历时考舍达七千余间”[21]。
刘海峰、李兵认为明清贡院明远楼是“最高的一座建筑,规定为三层楼建筑,二、三层有柱无墙,或者四面都是窗户”[18]321。马丽萍提出明清贡院明远楼“一般是二或三层楼阁式建筑”,还进行了实例分析,指出如明代顺天、应天、陕西贡院明远楼“平面皆是正方形……二、三层直接开窗或通透式设计,没有外廊”,其中两京贡院“四面开拱券门……陕西贡院一、二层是正方形,三层转换成八边型”[7]。张延昭认为明远楼最早出现于景泰、天顺年间南方的一些乡试贡院中,后逐渐被其他乡会试贡院采用,综合了谯楼、鼓楼与望楼的功能与形制,并推断明远楼“并非明廷的制度规定,而是地方贡院设计建造者不断探索、借鉴的产物”[22]。
此外,对于至公堂等其它建筑形制,学界也有所涉及。朱惠荣、马荣柱指出明清云南贡院至公堂“坐北朝南,面阁五间,建筑面积517平方米”[9]。马丽萍认为明清贡院至公堂“多为五开间或七开间,也有九间者,屋顶以悬山形式居多”[7]。周春芳、王军指出,明清陕西贡院至公堂为“卷棚五间”[27]。龚笃清认为“明代贡院围墙外墙高1丈5尺,内墙高1丈”[5]366。马丽萍认为明清贡院外帘办公区域的“办公用房和辅助用房多为硬山顶”,聚奎堂“通常为5开间或7开间”[7]。
学界对贡院建材的探讨绝大多数针对号舍,仅偶尔论及其它建筑。
刘海峰认为明初贡院号舍多为木制墙板,随后因易发火灾,便改为砖墙[24]。张森指出顺天贡院万历二年才“将木板房舍改为砖瓦结构”[6]。张玉娟发现弘治十年河南贡院号舍材料由“席子”改为“木板”[12]。田建荣指出,嘉靖四年陕西贡院“将数百间号舍席棚改为木构”[28]。王力指出万历二十二年贵州贡院号舍由木制改为砖石材料[20]。郭培贵认为“明初号舍一般是用苇席搭盖的,明中后期才先后改为‘板建’或砖瓦结构”[25]208。武明军发现明代河南贡院在天顺六年时“受卷等所及士子号舍,皆以席为之”,直到弘治十一年才将号舍“以板易之”,到了嘉靖四十三年重修,“将弘治时期的板易为砖”[13]。孟义昭指出,应天贡院在隆庆元年将号舍材料由芦苇改为砖瓦,万历二十九年将明远楼用砖改建[8]。李嘎、王雅秀指出明代山西贡院在正统十年初创时号舍“以木板为之”,隆庆四年为防火而改为砖砌[15]。郭培贵认为顺天贡院在“天顺八年前由芦席搭建而成,之后改为‘板舍’,嘉靖后逐渐改为砖瓦建筑”[21]。可见,贡院建材虽总体向更坚固的状态演变,但同时期各省贡院之间、贡院内各建筑之间的建材也有显著差异,目前尚未见到对这些差异及其成因作系统分析的成果。
四、明代乡会试贡院的经费
学界近十年来开始出现涉及明代乡会试贡院经费的成果,主要着眼于两京贡院,对其他省份贡院经费的探讨较少。
张森讨论了明代顺天贡院因具有“全国性质”而产生的修建经费分摊问题,认为一般情况下其修建经费由国家与北直隶地方财政共同分担,并举了《明会典》中的规定及万历二年贡院修建的例子进行论证[6]。刘明鑫的《明代乡会试贡院修建与维护经费来源考述》是目前仅有的一篇专门研究明代乡会试贡院的论文,该文认为,明代乡会试贡院修建与维护经费来源有“官方拨款”“赋役派编”“分摊”和“社会捐助”等四个途径,其中“官方拨款、赋役派编与分摊是基础,处于主体地位;社会捐助作补充,处于辅助地位”[29]。裴家亮对明代应天贡院在景泰五年、嘉靖十三年、隆庆初、万历五年、万历二十九年五次修建的贡院经费来源作了逐一分析,发现“两次是乡试供应费用节省而来,两次以官员捐俸为主,一次是利用南京本地商税本色和猪的抽税机制变革来筹集”,因此认为应天贡院的修建“并无完备的经费筹措机制……经费也皆由主导贡院修建的官员自行筹措”[26]。刘明鑫在其博士论文中列举了作者所见的明代顺天、应天、湖广、福建、贵州等五地贡院历次修建、维护所耗费用数额及来源,并由此得出了“明代京师乡会试贡院的修建费用最多,其次是各省乡试贡院”的结论[30]。
五、明代乡会试贡院的文化
目前对明代乡会试贡院文化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涉及多个角度,既有对小说、诗歌、楹联等贡院文学内容的关注,也有对贡院民间信仰的研究,为今后的深入探讨提供了思路。
刘海峰、李兵较早对明代乡会试贡院文学予以关注,在其著作中使用了不少与明代贡院有关的文学类材料,如天顺七年会试贡院火灾后,民间出现的“回禄如何也忌才,春风散作礼闱灾”诗句以及《儒林外史》中对老童生周进参观贡院时撞号板情景的描写等,这些文献让我们得以从新的角度观察贡院[18]323、330。李兵关注到了明代贡院的楹联,认为文人“用楹联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贡院的认识”,这些楹联中有些描写了贡院建筑的功能,有些可起到激励考生积极应考或警示考生、防止作弊的作用[16]。龚笃清考察了明末贡院祀奉考神之事,认为“考神”可能是张飞,还介绍了祀奉的方位与陈设[5]366。张亚群认为“贡院内建筑物的布局设置、命名及匾额、对联,集中反映了科举文化的意蕴”,并用两京贡院中的楹联等相关文化产物进行论证[31]。王力举出嘉靖间贵州贡院掌卷所的“魁星石”之例论证其“贡院中的建筑常被赋予象征意义”观点[20]。白金杰利用了明清小说中描写明代贡院鬼神之事的材料,探讨了贡院中的民间信仰问题[32]。
六、结 论
经过近三十年的积累,明代乡会试贡院研究取得了较明显的进步,学界对贡院修建历程、选址、建筑规制问题有了一定的关注,也对其经费、文化等问题有所涉及,为进一步加深和扩大该领域的研究发挥着积极作用。不过,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其一,学界对该研究的重视仍不足。从研究数量来看,目前对该论题的专门研究仅有一篇论文,涉及该论题的相关成果也仅有几部全面研究科举的著作与20余篇论文。从已有成果的写作主旨来看,目前唯一的专门研究仅关注了经费问题;其他成果则基本以某宏观论题之下的从属研究形式呈现,直接探讨明代乡会试贡院的篇幅十分有限,难以展开深入研究。这种研究匮乏的状况与该论题的重要程度仍是不匹配的。
其二,研究不够全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已有的个案研究未能实现对明代15座乡会试贡院的“全覆盖”,对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山东、四川等七省贡院几乎未予关注;二是研究视角的缺失,如学界探讨贡院经费问题时很少关注两京之外的贡院,论述建筑形制和建材的成果则大多着眼于号舍,还有很多重要论题如明代乡会试贡院建设中地方士人的社会参与、贡院的多元化用途、贡院建设工程的监管及工期等未得到深入探讨,甚至无人问津。
其三,相关探讨多停留在表层。目前学界对该论题的大多数研究仅停留在较表浅的“器物”层面,如对贡院修建历程、建筑规制等进行梳理,而未能将其与科举制度紧密结合、探究有关贡院的历史现象背后的深层动力,更鲜见综合利用历史学、建筑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方法对贡院相关问题作出的深入分析。同时,目前的个案研究往往难以将研究对象放入全国贡院发展的整体历史进程中探讨,而已有的共性研究因又缺乏对各地贡院个案深入分析后的全面考察,结果多是浅尝辄止。
其四,“贡院记”未被充分挖掘和利用。贡院研究中最关键的史料当属“贡院记”,但其在方志、文集等文献中分布很零散,全面占有这类史料相对困难,且同一篇“贡院记”在不同种类、版本文献内的承袭过程中极易出现信息丢失、扭曲的情况,然目前为止,这类史料仍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由此造成的问题颇为常见,如某文认为正德十五年顺天贡院明远楼被烧毁,次年由御史汪嗣等主持修复并扩建贡院道路,但通过爬梳史料可知此事实际发生在福建贡院,主持者也并非“汪嗣”,而是“汪珊”,因此次修建对应的贡院记(即林俊为福建贡院所作《文场修建记》)[33]未被仔细审读而导致了“张冠李戴”的结果;又如多篇论文在探讨万历二十九年应天贡院修建情况时所用史料均是转引自《南京夫子庙志略》一书的“(明)李机《应天府修改贡院碑记》”,此据石碑抄录,因原碑文字漫漶,故用大量“□”代替,且识错处较多,然此文也收于《李文节集》[34]中,其作者实为“李廷机”,这一版本清晰易识却未被学界注意,实属可惜。
在明朝覆亡三百七十余年后的今天,明人所建乡会试贡院绝大多数遗址已不存,但我们的先人寓于其中的智慧仍是一笔珍贵的财富。中国台湾地区宋史专家梁庚尧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提出贡院是“科举文化的具体象征之一”[35];“科举学”概念的提出者刘海峰也认为贡院是“是科举制度的有形体现,也是科场的具体表现”[23]286,可见学界对贡院的历史价值已有高度认同。明代乡会试贡院严格按照科举考试规制建设,其演变同步映射着明代科举制度的发展进程;乡会试贡院的建设离不开官民的合作,从中可窥见明代科举与社会的互动状态。所以,深入、细致、全面地研究明代乡会试贡院,既可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明代科举制度,也为我们考察明代国家、科举与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新的线索。可以预见,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贡院这一几乎与科举制度相始终的文化遗产会为新时代的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