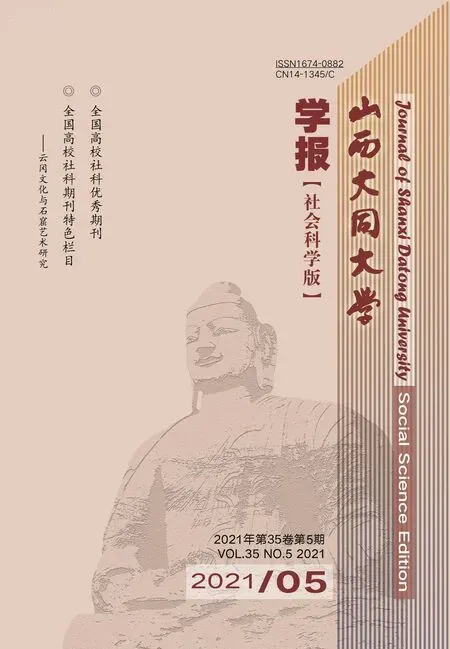论宋代中央诸司厅壁记中的官员心态和史料价值
宋 凯,胡传志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康有为认为在中国两千年官制历史之中,宋代官制最为完善:“宋之官制凡有五善:一曰中央集权;二曰分司详细;三曰差易官;四曰供奉归总;五曰州郡地小。”[1](册7,P252)虽然宋承唐制,但是宋代统治阶级更加注重加强中央皇权,对社会整体发展全面控制,尤其是对商品经济的掌控。中央集权在宋代得到加强,形成“强干弱枝”的官僚体系,因此中央诸司的权力和职责都较前代更为集中,与全国的发展紧密相联系。中央诸司所作的厅壁记,反映了统治阶级集团中掌握核心权力的一批官员独有的的行文风格、为官心态,同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里对中央诸司的界定与地方相对,主要包括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和监察机构。
关于厅壁记的定义,前人多有论断,今融合众人观点加以提炼,宋代厅壁记的定义应为篆刻或题写于官员办公官廨建筑之上,内容围绕着官廨、官员以及由此二者引发的思考而进一步展开议论的记体散文。目前学者普遍认为厅壁记兴盛于唐代,厅壁记创作确实在唐代出现了一个小高潮,但是相比较于宋代440篇的创作量,不足其四分之一。但学者们较为关注唐代厅壁记,对宋代厅壁记关注不足且研究的侧重点在于概述,对其中的文学和史学价值均挖掘不足。厅壁记在唐代成熟和定型已成公论,但宋代厅壁记没有原封不动的接纳,而是与时代风貌相结合,打破厅壁记作为记体文的文体限制,融入散文文法而独具一家特色。
一、立意的独特性——职位自豪感
官场众人无一不希望位高权重,或是为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2](册1,P1)或是想借此追求荣华富贵,但宦海浮沉,即使如欧阳修、苏轼这般的文坛领袖也是仕途崎岖。经历重重磨勘而擢升高位的中央诸司官员,其厅壁记中包含着强烈的职位自豪感,这是低层基础官员厅壁记中几乎不具备的特点。以韩元吉《吏部尚书厅记》和《建安县丞厅题名记》两篇厅壁记为例,对比分析前述现象。
韩元吉是宋代桐木韩氏家族第六代孙,字无咎,以词闻名,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誉。方回曾给予韩元吉极高的评价:“当是时,巨儒文士甚盛称无咎与茶山。”[3](P829)其最初以门荫进入仕途,后几经磨勘官至吏部尚书,于乾道九年(1173年)刚任职时创作了《吏部尚书厅记》,据记载吏部尚书“南宋为从二品”[4](册6,P3231)。韩元吉擢升高官,意气风发地写下此篇厅记,此时他并未料到不到一年时间就被弹劾。
文中开篇“天下之官总于吏部”[5](册216,P225)所言不虚,吏部为六部之首,“其上者尚书独主之”。[5](册216,P225)吏部尚书仅设置一人,为六官之长,先表明职位之重,其后紧接着介绍权责之大:“惟吏部由魏晋而降者,分职甚重,得以甄叙人物,进退群吏。”[5](册216,P225)接连用了“独”和“惟”,其自矜自喜之情不言而喻。接着在文章中第二次强调职位之重:“虽其职稍异于古,其重则犹古也。”[5](册216,P225)既强调职位的源远流长,又以古比今,凸显吏部尚书一职的历史厚重感。其后在文章结尾再次呼应职位之重:“今兹职以治官者也,以其治官者治己,推而至于治天下,亦是道焉。”[5](册216,P225)治理天下是皇帝和宰相的职责,韩元吉此言有继续擢升的期盼在里面。文中不惜笔墨,再三强调吏部尚书的职责之重,可见其对于职位的重视和自豪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相同语义的多次表达本为散文创作之忌讳,但如周振甫先生所言:“在写作中,作者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有时是故意重复的。”[6](P152)韩元吉采用变化的表述,前后呼应但不累赘,其写作技法之匠心独运据此可见一斑。
韩元吉早年曾担任县令,应其部下莆阳林智可之请,写下《建安县丞厅题名记》,此文之中的感情与任职吏部尚书之时的自豪感截然不同。虽然全文大段篇幅都在介绍县丞,但与夸耀吏部尚书权责职位之重要不同,此文重点强调县丞之难。韩元吉以建安县丞为例,将县丞的共同难处概括为两点:其一,职责之繁琐。如“至县,则事无大细,悉关丞”,[5](册216,P209)一县之事,县丞都要去辅佐办理。其二,复杂的长贰关系。如“然长或能,率其权不以予丞,丞或才,复擅其权不以事长。苟异是,则必退避畏缩,而举听于丞;远嫌绝疑,漫不助其长”。[5](册216,P209)县令与县丞之间的矛盾早在韩愈的《蓝田县丞厅壁记》中就已经披露,县丞在侵权与渎职之间难以两全。吏部尚书位高权重,更加干系国家治理,远比县丞难以担任,但是有关吏部尚书的厅壁记中反而没有论述职责艰难的内容,有的只是反复强调职位之重要。再如同样是为辅佐之官,韩元吉对于县丞的态度是“屈为丞”,[5](册216,P209)可见其认为县丞一职不能让人充分发挥才干,其后所述“盖不卑其官如此”[5](册216,P209)表面是夸赞林智可作为县丞能不以其职位为卑是件难得的事情,但也因此透露出当时对于职位低下的官职有偏见的现象。再反观《吏部尚书厅壁记》,韩元吉在乾道九年(1173年)八月一日担任吏部尚书之前数月,任职前任吏部尚书的辅佐之官,“元吉幸为之贰也”,[5](册216,P225)一个“幸”字与“屈”字形成鲜明的对比,究其原因,虽都为辅佐之官,但职位高低相差悬殊,心态自然也不同。通过韩元吉在担任不同职位时所作的厅壁记,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其中包含的感情之不同:职位低下时,郁郁不得志,感到不能物尽其用,是为屈才;位高权重时则意气风发,充满着强烈的职位自豪感。
通观中央诸司厅壁记,自豪感的表达往往自足于职位之上,而较少从个人的角度表达,这是因为中央诸司接近皇权,相较于郡县类厅壁记,其严肃性特点尤为明显,个人情感的表达会使文章带有私人化色彩,降低文章的庄重感。郡县类官员远离皇权,且多有不平之鸣,严肃性相对较弱,私人化色彩浓厚。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记文作者对于“职位自豪感”的表述多样化:
其一,通过职位未来提升空间来体现。如丁伯桂《官诰院续题名记》中所载:“在昔名公,率多发轫于此。不但伉台衡,持从橐,登要路,垂足为荣。”[5](册304,P187)官诰院又称为官告院,隶属于吏部,丁伯桂以名公“多发轫于此”[5](册304,P187)来表明官诰院的重要地位。对于渴望晋升的官员来说,其官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再如张宦《馆阁续题名记》所载:“异日谋谟庙堂,安社稷于谈笑,垂功名于竹帛者,不无其人。”[5](册154,P283)
其二,强调职位选拔人才之慎重。如周必大所作《兵部郎官题名记》中“而郎非历监司郡守不可得”[5](册231,P223)。任希夷所作《司马厅壁记》中“以京朝宰邑有治理效者为之”[5](册283,P375)。这些都表明只有那些有资历有绩效的特定官员才能被选拔上这些职位,以此来凸显“国家重六院之选,圣上尤切留意”(谢諤《诸军题名记》)。[5](册220,P28)
其三,通过与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来表现。如张叔振《登闻检院题名记》中记载:“虽职事清简,比他院无剧务,然九重明目达听所系,民之休憩,军国之利病所由达。”[5](册272,P277)虽然职务比其他官职简单,但是因为对统治者和人民有重要作用,如齐庆胄《刑部长贰厅题名记》中所言:“一或不得其平则为民患。”[5](册258,P426)因此其职责具有关键性作用,不容小觑。再如周必大《唐政事堂记》中所载:“以正朱紫之乱,使人主尊荣,中外称美。”[5](册231,P276)同样是通过表达对于统治者的重要作用来凸显职位的重要。
其四,以职责繁多来凸显。如黄钧在《太常寺厅壁记》中叙述道:“礼以命伯夷,乐以命夔,礼乐之用参天地、和神人,非一官所能备也。今顾以奉常一官主之。”[5](册223,P361)前代数官之职责今汇集于一官,权责广则职位自然重。
其五,以古衬今。如周必大在《兵部长贰题名记》称:“其职视唐尤简,况于成周乎。”[5](册231,P223)看前代唐时的相同官职之职责尤嫌简单,反衬出现如今的官职之繁重。韩元吉也在《吏部尚书厅记》中表明:“虽其职稍异于古,其重则尤古也。”[5](册216,P225)儒家钦羡于古时的治理制度,以古比今,自然是看重如今的官职。
记文作者往往力求避免直接的表达,以免使文意失于浅显,同时也是为了在官场中保持自矜的良好形象,此外婉转曲折的多样化表达也显示出记文作者行文构思的创新和特色。
二、官方思想影响下的创作——颂圣与逞学
马茂军先生认为“循默简静在当时(宋代)几乎是一种社会心理”。[7](P54)宋代文职官员确如马茂军先生所言,大多懦弱避祸、萧规曹随。越接近皇权越是谨小慎微,循默简静的性格在上层官员中尤其明显。又诚如刘勰《体性》中所言:“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8](P145)作家的循默心理会影响到文章的风格,尤其是厅壁记这类公开性的文体,既要避开敏感性的话题,又要体现才学。相较于其他类厅壁记,中央诸司厅壁记受官方思想影响最为深刻。
在官方思想影响下,最重要的创作表现是在文中颂圣。由于接近王权,受官方中央集权思想的影响,在厅壁记中对统治者的歌颂也就约定俗成。颂圣文化历史悠久,在典、谟、训、诰、誓、命等文体中较为常见,因多与宗祠庙堂相联系,文人对此并无太大非议。但是宋代有着注重文人品格的大环境,颂圣放在其他文体之中,多被视为阿谀之词,历来评价不高,苏颂就曾在《审刑院题名石柱记》中指出宋代“文吏巧诋”[5](册61,P371)之弊,如才华横溢的丁谓被后人视为大奸之人,其颂圣作品多被视为奉承之词。厅壁记这种文体的特殊性在于其属于官方文体,但又具有其他文体的自由性,因此颂圣在厅壁记中有其合理性,既可以借此博得统治者的好感,又不会流于阿谀之列。综合中央诸司厅壁记的内容来考察,颂圣在其中主要有两类表达方式:
一类是直接对皇帝本人的颂赞,如高文虎《工部郎官题名记》开篇即赞颂:“高宗受命中兴,驻跸钱塘,咸复承平之旧,广延才俊,辑图治功。历孝庙、上皇至于今上,盖六七年矣,维持冯藉,又当传之无穷。”[5](册242,P64)宋高宗赵构执政前期迫于压力,起用主战派官员,后期则重用主和派,并处死爱国名将岳飞,总体功绩弊大于利,但是记文作者只是着眼于其进步的一面,有明显的粉饰太平之嫌;另外,此文作于庆元四年(1198),正是宋宁宗赵扩发动“庆元党禁”打击理学,禁止朱熹等人参加科举之时,对科举及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文中却一片盛世景象,对统治者的弊端毫无提及。高文虎此类颂赞之词大而空,忽视统治阶级昏暗腐朽的一面,完全是一种程式化、理想化的表达。
另一类倾向是对于盛世的歌颂,如周直方在《太学云阶斋壁记》中所载:“时惟中兴,大辂鸣銮,圣皇涖止,乃倦持志,贲如濡如。丰芑之仁,涵育数世,弼从魁杰,声光烨然。噫,盛矣夫!”[5](册306,P157)通过华贵的物象如“大辂”“声光”等营造出盛大华美的氛围以突显“邦家之光”。[5](册306,P157)但是空洞无文,颇有台阁体文风的弊病。在上述两种情况之外,还有部分记文作者本着自矜的心理将颂圣意图融化在字里行间,如刘克庄《登闻检院续题名记》:
嘉定以来,当路讳言,箝结成风,天子患之……于是英断赫然,更化改元,举相去凶,下诏求言。……封事辐辏,语或激讦,上亦不以为忤,亲洒宸翰,申命近臣差择而施行焉。[5](册330,P235)
此文大约作于端平年间(1234—1236),正是宋理宗赵昀励精图治之时,史称“端平更化”。文中表明朝廷日益腐朽,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但在这一片衰世景象中“天子患之”,能够清楚认识到问题所在,并且主动“下诏求言”,即使谏言“激讦”,依旧虚心听取。刘克庄选取天子听谏一事,展示了朝廷上下君臣一片和谐的景象,传达出君主宵衣旰食、改革积弊,实乃求治之秋的信息。对于天子的赞颂之情和对盛世的期盼之情融化在字句之中。这与前面的空洞浮靡的颂赞之词截然不同。
考察中央诸司厅壁记中记文作者颂圣心态,全部都是主动为之。这种整齐划一的现象有其特殊的原因:其一,循旧例。前面已经论述过宋代文人善于继承前代成果的特点,此不赘述。其二,仕途的需要。宋代儒学大盛,诚如周直方《太学云阶斋壁记》中所言:“宋受天命,五纬躔奎,人文化成,国以儒寿。”[5](册306,P157)儒学和科举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在为文人带来优越性的同时也造成了宋代的冗官冗臣现象,为了能够在众多官员中得到卓拔,通过颂圣以取悦统治者无疑是一条捷径。如在元丰年间,周邦彦献《卞都赋》歌颂新法,因此被擢为太学正。其三,宫廷文化的影响。宋代皇帝大多沉迷物质享受,宫廷宴饮、宗室集会之上应制颂圣之作必不可少,统治者的需要以及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都会成为在厅壁记中颂圣的诱因。其四,儒家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儒家思想体系从本质上来说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虽有一定的民本思想,也是在忠君的前提之下,对皇权的尊崇是儒家不变的宗旨之一。在此影响下,颂赞统治者可以理解为儒家学子的一种“使命”,尤其是在盛世或者君主兢兢业业救世之时,对于功绩的歌颂更是义不容辞。上面论述的《登闻检院续题名记》就是刘克庄有感于“端平更化”而发自内心的对统治者的褒赞。其五,专治皇权下的必然产物。马茂军先生指出“赵宋王朝在剥夺将帅兵权同时,对文人进行了羁縻政策。伴随着思想强化、道德强化、文人除了歌功颂德外,几近循默”。[7](P62)此观点适用于北宋前中期以及主和派占据优势的时期,宋代虽然给予了文人优待,但是思想控制却非常严格,虽然会有卓荦的文人奋起反抗,打破这思想控制下的循默,但是大多数的文人碌碌无为,甘心做王权专治的忠诚追随者。以上的种种原因促使了厅壁记中颂圣文化的繁荣,但也因此使得文章空洞靡丽。其六,政党斗争中的妥协。傅璇琮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中指出“在蔡京实施党禁和秦桧履行和议时期,文坛几乎为歌功颂德的谄诗谀文所覆盖”。[9](P244)在残酷的党争中,即使写下《贺新郎·寄李伯季丞相》来谴责秦桧的张元干也在后期创作了阿谀之词。厅壁记的记文作者均处于官场之中,自然会受到影响。
官方思想影响下的另一个创作倾向是通过叙述官职历史流变以逞学。厅壁记作为公开性的文体,记文作者借此既可以显示博学的才识,又可以展示政治观点。但中央诸司官员在官方思想的桎梏下创作范围有限,因此为了能够充实文章内容和显示创作水平往往倾向于“逞学”,并将其与官职流变相结合,少则一两句,多则可超过半篇章节,内容涉及到官职设置时间、官职前身、官职职责、官禄、历朝历代的选拔等多方面的内容。单就中央诸司厅壁记来看,提及到官职流变的篇章占半数以上,由此可见记文作者对其的重视,试看几例: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司马光《谏院题名记》)[5](册56,P231)
昔周之盛时,封同姓五十三国,而公族之居王朝者尚重,始置宗正以纠正之,所谓“彤伯为宗”是也。(葛胜仲《宗正寺少卿壁记》)[5](册143,P36)
汉九卿,将作大匠沿袭秦官,亦少皞氏以五雉为五工正,以利器用。唐虞共工,《周官》考工之职也。历代虽因革不一,大率典司皆营缮土木之事。隋开皇中,始定以寺为监。唐天宝中,始定以长贰为监少、丞。自汉置主簿,自晋置员之多寡亦不同焉。本朝盖因唐制。(孙祖寿《将作监厅壁记》)[5](册207,P205)
这种“逞学”行为不仅是个人的选择,也同样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马茂军先生认为“宋人尚博是尚文时代风气发展的必然结果”。[7](P145)例如同样是对于宗正寺起源的考察,据《汉书》记载:“宗正为古官,始于秦汉。”[10](P730)据《隋书》记载:“宗正寺之设,始于北齐。”[11](P755)厅壁记中的有关宗正寺的记载比史书更为生动详细:
首先,葛胜仲将宗正寺的起源与宗法制联系在一起,形象地解释了其最初设置的原因是为了打压“公族”在朝中的势力,维护宗亲分封制度;同时又通过宗正一职选拔官员方式从“率用同姓”[5](册143,P36)到“杂以同姓、异性充选”[5](册143,P36)的变化,揭示了宗法制从周到宋的变迁,其叙述更加骨肉丰满,颇具文采。
其次,弥补了相关记载只叙“源头”不叙“流变”的不足。《汉书》和《隋书》都只是点明官职的起源,但是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官职体系,对于其在不同朝代的流变考查不足。所谓后人修前史,宋代中央诸司厅壁记不仅对于前代的官职流变做了总结归纳,而且将宋代相对应的官职体系明确叙述在内,如葛胜仲《宗正寺少卿壁记》花费大量的笔墨对于宋代宗正寺的情况做了细致的描述:“景祐中,始韶推择属近望高者二人判大宗正事,至纂修玉牒属籍,则用他官兼领。神宗皇帝董正治官,肇置九寺,深惟庆系之重……诏即广亲诸第建六学,凡三舍,校试升迁法悉视应泮,而以寺长贰总之,宗正选益重矣。”[5](册143,P36)内容详细到任职人员和年号,这些都给后代修史提供了一定的可信度较高的史料依据。
最后,增加了文章说服力。《汉书》《隋书》虽然是可信度较高的史书,但是因为古时朝代更替频繁,书籍屡遭禁毁,在书籍重修的过程中就容易导致记载有误,单就上文所提到的宗正寺的起源,二书对此的记载就不尽相同,且没有给出相应的依据,说服力不足。部分中央诸司厅壁记则相对改善了此弊端,对于一些起源及流变不甚明确的官职尽可能地给出合理的解释,除上述例子之外,如吴博古的《审计院厅壁记》:“审计非古官也,而原于古。古者凡官府皆有要会,而财用稍食之会尤详。”[5](册271,P13)吴博古虽不知审计院具体起于何时,但是给出了猜测的依据。
综上所述,中央诸司厅壁记在官方思想的影响下,在继承前代厅壁记写作模式的基础上蕴含着创新。此外厅壁记本身的特殊性与时代环境的综合影响,使得颂圣文化在其中得到一席之地。
三、无意之史——细节的还原
厅壁记作为记体文学的分支,记文作者在创作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留下一些史料记载,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诸司厅壁记中的史料相对零散,乃是记文作者无意为史,但因为其中的史料少见于正史记载,因此相对可贵。郡县官员则有意为史,中央诸司厅壁记所记载的内容较之其他类别厅壁记更有可信度,相较于其他类别厅壁记的记文作者,其地位显赫,因此作品更容易传播和保存。宋代厅壁记虽然逐渐散文化而有相当的文学性,但是也同样具有史家实录的性质。苏辙在《京西北路转运使题名记》中表明记文作者的目的之一是传之后代,使“后世将有考焉”,[5](册96,P174)因此“敢以史笔之法书其可知者”[12](P499)。
最有意义的史料价值是对于个别官职当值生活及环境的展示,如洪迈绍兴三十年(1160)所作《礼部郎官厅壁记》,这篇厅壁记文风简朴,似家常话娓娓道来:
天明省门开,繇大丞相以下毕入听治。吾同舍郎南典选,北理财,文书鳞午,吏四绕不少置,独仪曹之廷可设翳罔。予方理蠹简,呻呫毕,作书生事业。倦则偃一榻上,迟食时矍起,摩睡眼以出,卒食,舒舒而行,伺丞相上马已即去,至无毫毛可用以为勤,以白长官者。[5](册222,P69)
与史书记载内容不同,洪迈此篇厅壁记补充了礼部员外郎的官职职务及当值日常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在名称上,礼部员外郎又可称礼部郎官。礼部员外郎流传较广的简称和别名有三个,一是“员外郎”,此称呼也是“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员外郎通称”[13](P216)。二是“瑞锦窠”,[14](P256)此称呼因礼部员外郎职掌描绘祥瑞图的特征而得名。《春明退潮录》载:“(王元之)谓(礼部)员外郎为瑞锦窠。”[15](P13)三是“知名表郎、名郎”,因吏部郎中和员外郎撰写贺、谢等表,且表后有此二官的署名,故此得名。曾巩《西园席上》曰:“省阁名郎国羽仪,瀛洲仙客众蓍龟。”[16](P92)据《洪文敏公年谱》所载,洪迈作此篇厅壁记时,任职礼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再据文中所言:“予访老吏,质太史,越数月而后彼颇得其梗概。”[5](册222,P69)当为任职期间所作,由此可知,礼部员外郎也可称为礼部郎官,龚延明先生的《宋代官制辞典》即少收录此种别称。其次是补充了礼部员外郎的工作生活。由文中记载可知,礼部员外郎天明随丞相入朝听治,其后“南典选,北理财,文书鳞午”[5](册222,P69)。处理批阅相关文书一直到中午,文书的内容包括典选和理财,此处“典选”应该为略写,由礼部职掌范围可推知全部应为官吏选举及赋税财政等方面的相关礼仪。据黄畴若《礼部郎官厅记》所记载的内容可知,礼部官员大多数时间“比他曹为闲暇”[5](册290,P251)。洪迈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工作闲暇时的生活,“理蠹简,呻呫毕,作书生事业”,[5](册222,P69)空闲之时整理生虫的书简,也因此可见礼部藏有大量的典籍。“呻毕”一词出自《礼记·学记》:“今之教者,呻其占毕。”[17](P123)后以“呻毕”为诵读书籍之意。“呻呫毕”应为“呫呻毕”的倒装形式,可意为小声的读书,古人读书好大声朗诵,此处碍于礼部环境,故只能放低声音似耳语一般读书。工作疲倦之时还可以“偃一榻上”[5](册222,P69)休息,榻当为礼部公共设置,可见其工作环境较为人性化,但偃榻休息是否有固定时间则不可考。此外,从“迟食时矍起”[5](册222,P69)可以看出礼部官员享有工作餐且有固定用餐时间。洪迈此番论述在史书的基础上还原了礼部员外郎真实的工作生活,比一板一眼的史书记载更加血肉饱满。最后在基础设施上,独礼部可设置翳罔。此处细节不见于《宋史·职官三》。“翳”为遮蔽之意,“罔”通假“网”,翳罔可以意为遮挡阳光的纱帐。至于为何设置则无明确记载,据文中“吏四绕不少置”[5](册222,P69)可进而猜测礼部或人员众多,部分职员或需要于庭院办公,因此需要纱帐遮阳。
官吏的选拔都有一定的流程规则,看似公开公正、有条不紊的背后,实则暗藏各种隐性条件,如家世、样貌等,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案例,如黄巢貌丑惊吓到唐僖宗,因此被剥夺武状元身份,其后发动的黄巢起义,开启了唐王朝灭亡的序幕。这些隐性条件并不会被记载在官方史书之中,只能从一些个人文学作品中窥见一二,中央诸司厅壁记就是这类文学作品之一。
一些特殊的官职选拔对于形体有一定的要求。黄畴昔在《礼部郎官厅记》记载:“至于事笔研于其间者,亦必廉悍俊拔,如柳宗元、刘禹锡辈乃称。”[5](册290,P251)古人重视礼仪,职掌礼仪之人实则代表国家形象,礼部在元丰新制后职掌“参领礼乐、祭祀、朝会、宴享、学校、贡举之事。”[18](P216)因而此职位有外貌要求合情合理。文中提到的“廉悍俊拔”[5](册290,P251)意为俊俏精悍、卓异出众之意,韩愈曾在《柳子厚墓志铭》中称赞柳宗元“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19](P332)可见礼部郎官对于官员外貌有明确的要求,非外貌俊朗出众之人不能胜任。
再如部分官职升迁需要特定的任职经历。如周必大《兵部郎官题名记》中表明兵部郎官“非历监司郡守不可得”。[5](册231,P224)再如汪之疆《司法题名记》中指出司法部门要求“非已试吏者,不得处其职”。[5](册319,P188)以上资料都不见于正史记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完善宋代官吏选拔细节。且有些官职专为荫官大开方便之门。徐清叟在《六部架阁续题名记》中指出:“公卿大夫子弟之俊秀者,朝家就有擢用,必储以是职。”[5](册325,P286)六部架阁实际上成为世家子弟晋升的一个过渡阶段。
此外还有一些官职磨勘年限不固定。文武官员按照磨勘惯例,在职均有固定年限,但是据谢諤《诸军题名记》所载:“而其满其未满,视监察御史与寺监薄有缺多加采择,盖尝有因之即持节者。”[5](册220,P28)由此可见,诸军粮料官员的磨勘年限视具体情况而有所调整。
综上所述,中央诸司厅壁记以其自身的优势,可以“以文补史”与“文史互证”,对于部分记载不详的宋代官制给予完善,其中的史料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