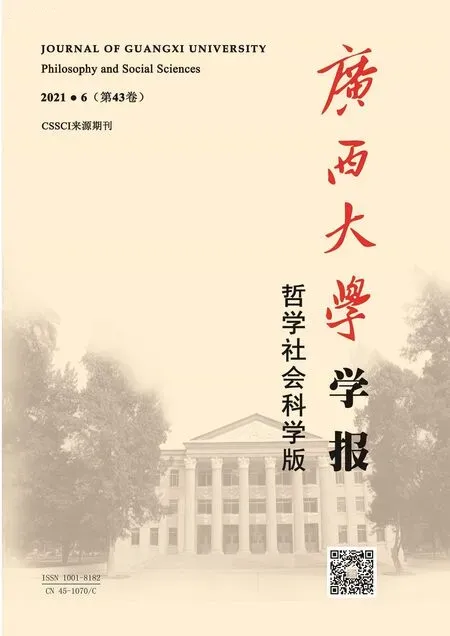意象说的哲学根源及其思想实情
——兼论叶朗的意象本体说
蔡祥元
叶朗在朱光潜、宗白华有关意象说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美学的基本问题即美是什么,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特征进行了一个总结性的概括,提出了“美在意象”的美学观,也即美的本体是意象。“在中国传统美学看来,意象是美的本体,意象也是艺术的本体。”[1]55意象本体说在引起美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的同时,也引发不少的批评。何光顺从本体概念入手,认为以意象为本体,会暗中引入西方古典美学的实体论与主客二分思想,从而与其意象本体论所主张的主客非实体性、非主客二分相矛盾[2]。何光顺这个批评看来误解了“本体”概念,简单将它等同于实体。
下面我们首先追溯意象说的哲学背景,表明意象基本内涵在于情景交融,它将哲学领域的易象、道象转化为情意之象,并以此成为审美活动的基础性概念;然后考察叶朗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意象本体说,并围绕情感意向性、生活世界和体验三个基本概念来拓展我们对情景交融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结合上述概念的现象学背景,重新审视叶朗相关“拓展”是否合理,看如何从现象学视角出发推进意象美学的当代建构。
一、意象说的哲学背景
“意象”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象思维在美学领域的体现,因此《老子》《庄子》《易传》等文本中有关象的论述构成意象说的思想来源。道不同于一般的物,它没有形,所以是形而上者。那我们如何知道这种形而上的东西的存在呢?老子认为道虽然无形,但可以以“象”的方式呈现出来。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老子》第十四章)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第二十一章)
大象无形。(《老子》第四十一章)
根据老子的论述,象处于有形无形之间。所以它不单是形象层面的东西。一般意义上的“物象”或者现代汉语中的“形象”,跟我们这里讨论的“象”有区别。物象、形象归属于物,而“象”不同,它归属于道,是道之象。正因为如此,它无法通过我们的感官来把握。庄子在《天地篇》中对老子的观点有一个生动描述: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庄子·天地篇》)
“玄珠”指道。庄子这里通过寓言的方式表明,道这种东西,不能用理智(“知”)来把握,也不能通过感官(“离朱”)来获得,还不能通过语言思辨(“吃诟知”)来获得,而只能通过“象罔”来获取。这里的“象罔”与老子那里的“象”意思基本一致。“罔”有“无”“忘”“迷惘”等义,考虑到它跟“网”也有关系,它还可能有虚构的意思,庄子补充上“罔”字,可以避免我们把“象”对象化、有形化,更加凸显象处于有无之间、有形无形之间的那个维度。
象则非无,罔则非有,不皦不昧,玄珠之所以得也。(吕惠卿:《庄子义》)
象罔者若有形若无形,故眸而得之。即形求之不得,去形求之亦不得也。(《庄子集释》)
宗白华在此基础上,从艺术形相对“象罔”作了进一步诠释,他认为“象”是境相义,“罔”是虚幻义,“象罔”合在一起体现了艺术形相的基本特征,是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一种“虚幻的镜相”。他又认为这种艺术形相是宇宙人生真际的“象征”。
非无非有,不皦不昧,这正是艺术形相的象征作用。“象”是境相,“罔”是虚幻,艺术家创造虚幻的境相以象征宇宙人生的真际。真理闪耀于艺术形相里,玄珠的皪于象罔里。[3]81
他对“象”“罔”的解读没有问题,跟艺术经验的结合也富有创见。但是,从“象征”的角度来解说象跟道或者艺术形象跟人生真际的关系,泛泛地说也可以,但严格追究一下,并不是很合适,会造成我们对象的存在方式的误解。象征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往往通过某种在场者来“代替”不在场者。当然,这种代替不同于单纯的符号,而是象征物跟被象征的对象存在某种直接的关联,从而以某种方式让被象征之物获得了某种在场。比如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因为十字架跟基督教有某种直接的关联。
象征不仅指示某物,而且由于它替代某物,也表现了某物。但所谓替代(Vertreten)就是指,让某个不在场者成为现时存在的。所以象征就是通过再现某物而替代某物的,这就是说,它是某物直接地成为现时存在的。[4]
象征这种让被象征物在场的方式,不同于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象”跟“道”的关系。“象”不是“道”的代现物或代表,它本身依然是一种“呈现”,“见乃谓之象”(《易经·系辞上》)。换言之,象乃是道的某种直接呈现,只不过它呈现的方式不同于有形之物。
对于象跟道的关系,《易传》有进一步的展开。《易经》是中国古代象思维的思想根源与集中体现,它就是通过象的方式来呈现天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经· 系辞》)《易传》对于古人为什么要通过象的方式来表现天道有一个解释,它构成了意象说的直接来源。“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下》)正如叶朗所总结指出的,这里通过区分“象”和“言”,并把“象”和“意”联系起来,以此表明“象”能够比“言”更能达意,这就为“意”和“象”这两个概念的融合提供了可能。“因此‘立象以尽意’的命题,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把形象和概念区分开来,把形象和思想、情感联系起来。”[5]72如果把这里的“圣人之意”替换为“诗人之意”,那么,如此所提供出来的“象”就是意象了。
王弼的“得意忘象”说接续并深化了《易传》的言象意之辨,进一步促成了意与象的融合: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所以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出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是故,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乃非真象也;言生于象而存焉,则所存乃非真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周易略例·明象》)
王弼诠释“立象以尽意”的时候引入了“忘”这个概念。前面有关“象出意”“言明象”的说法只是对言象意关系的具体化,“忘”不同,它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为言象意之辨从认识论问题转向审美领域提供了思想契机。“得意忘象”,从字面看,是要表明“意”相对于“象”的优先性,似乎要分离开意和象。但是,“忘象”不意味着不需要或者舍弃象,相反,它表达的恰是融入、沉浸到象之中的意思。因此,确切说来,它也是一种把握象的方式,只不过不是以“存象”的方式,也即不把“象”作为对象来把握。通过“忘象”这种把握象的方式,我们就能够透过象体会到“象之意”。王弼说以“存象”的方式(只看到象而看不到象所由生的“意”)把握到的象不是“真象”,由此我们可以说,以“忘象”的方式把握到的才是“真象”。由于在“忘象”的过程中“意”会显露出来,并且,“意”也不能脱离“象”而独存,在这个意义上,“真象”就是“意之象”或“意象”。由此可见,王弼的“得意忘象”说其实已经暗中实现了意与象的融合。不过,他这里的“意”还是本体论层面的“圣人之意”,因此,它所隐含着的“意之象”还不直接就是审美领域的“意象”。
“得意忘象”隐含的审美维度在宗柄的“澄怀味象”说这里得到了彰显。宗柄在《画山水序》中将老庄易玄中的道论、象论引入直接审美领域:
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画山水序》)
宗炳这里的“味象”把“忘象”的审美维度直接说出来了。由于此处的“象”不是卦象,而是山水之象以及相应的山水画之象,因而它的“意”也就是画家之意。“味”跟“忘”也有直接关联,因为“澄怀”的思路跟老子的“涤除”“玄览”、庄子的“心斋”“坐忘”思路一脉相承,也就是说“味象”本身也需要一个“忘”的环节。但是,它也不完全等同于“忘象”,而突出对“象”的一种正面感受,就是去体味、品味象。对“象”的体味、品味就是审美活动了。叶朗特别指出这里的“味”不是味觉的味,而是一种精神享受的味[5]208。我倒觉得没有必要做这种划分。“味象”是以味觉的感受方式为思想原型的,并且通过“味”的方式表明,这种审美的发生还有一种身体性的愉悦感呈现出来,这恰是审美活动不同于理智认知的区别。对美的“品味”活动,既不同于单纯的感觉活动,也还不是对它们的一种精神价值的把握,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身体性感受。
宗柄的“澄怀味象”将《老子》《庄子》《易传》中的观道之法用于观美,可以说完成了从道学、玄学向美学领域的直接拓展。到刘勰这里,“意”和“象”这两个概念开始融合,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范畴“意象”正式出场。
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文心雕龙·神思》)
这里的“意象”不同于一般哲学本体论层面的易象,而是引导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艺术形象。
二、意象的基本内涵:情景交融
作为艺术形象的“意象”,跟形而上学层面的易象、道象区别在哪里呢?对意象的内涵本身,刘勰又进一步规定:“神用象通,情变所孕。”(《文心雕龙·神思》)它表明,不同于易象,“意象”融入了作者情感、情意的形象。因此,情跟景(一般意义上的物象)的交融也就构成了美学领域对意象基本内涵的一个导引。在美学历史上讨论情景关系的文论很多,这里不具体展开,主要以谢榛和王夫之为代表,看情景交融如何构成了意象的基本内涵。
谢榛明确指出,情与景是诗歌创作的两个基本立足点:
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四溟诗话》卷三)
诗乃模写情景之具。(《四溟诗话》卷四)
他认为,在诗歌创作中要做到情与景的融合,也即是“情景适会”(《四溟诗话》卷二)。“情景适会”就是情景交融。他又从反面指出,如果情与景分离开来的话,就不成其为诗了,“孤不自成,两不相背”。这就进一步表明,在诗歌中情与景是相互依存的。
王夫之更为具体地描述此种依存关系。他说,情与景看起来是两个东西,其实是不可以分离的。如果分离开来,情就没有兴发人的力量,景就不成其为景。在诗歌中,情与景相互生成,相互蕴涵,一起构成诗歌的诗意要素之源:
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姜斋诗话》卷二)
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唐诗评选》卷四岑参《首春渭西郊行呈蓝田张二主簿》)
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虚景,景中含情。(《古诗评选》卷五谢灵运《登上戍石鼓山诗》)
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截分二橛,则情不足兴,而景非其景。(《薑斋诗话》卷二)
情景一合,自得妙语。撑开说景者,必无景也。(《明诗评选》卷五沈明臣《渡峡江》)
王国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人间词话》)可以看作对王夫之所论情景关系的总括。王夫之没有直接把情景交融之后的诗意形象称之为意象,但是,他在评价谢诗的时候,承袭了刘勰的意象观:
言情则于往来动止缥缈有无之中,得灵蠁而执之有象,取景则于击目经心丝分缕合之际,貌固有而言之不欺。而且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神理流于两间,天地供其一目,大无外而细无垠,落笔之先,匠意之始,有不可知者存焉。(《古诗评选》卷五谢灵运《登上戍鼓山诗》)
王夫之指出,谢灵运的诗歌实现了情景交融,“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两者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有象”“有貌”的艺术形象,所以“言之不欺”。对这种“艺术形象”的先行领会,构成了诗人诗歌创作的根源。“落笔之先,匠意之始”这句话来自刘勰的“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文心雕龙·神思》)。因此,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来,但也已经暗中表明,情景交融之后形成的艺术形象就是意象。
近现代美学家朱光潜和宗白华,受西方美学观念的影响,明确提炼出“意象”观,把它们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并对它的内涵从现代美学的角度进行了一些界说。他们都表明,意象就是审美活动的根源。
不仅如此,他们也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意象的内涵作了进一步分析。朱光潜将它与“感觉形象”和“表象”作了区分。表象是相对客观的,意象不同,它是情与景相互交融的产物。
诗的境界是情景的契合。宇宙中事事物物常在变动生展中,无绝对相同的情趣,亦无绝对相同的景象。情景相生,所以诗的境界是由创造来的,生生不息的。[6]
这两个方面,宗白华也从不同角度有所论及:
在一个艺术表现里情与景的交融互渗,因而发掘出最深的情,一层比一层更深的情,同时也透入了最深的景,一层比一层更晶莹的景;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为景,因而涌现了一个独特的宇宙,崭新的意象,为人类增加了丰富的想象,替世界开辟了新境,正如恽南田所说“皆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3]72
因此,意象的基本内涵就是情景交融。问题是,这种情景交融是如何发生的?谢榛、王夫之都强调并突出在诗歌中情与景是不可分离的,是相互生成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日常经验层面,情乃是人的主观感受,景则是一种客观存在物,它们到底是如何相互生成、合二为一的?他们对此虽有论及,但都未展开。朱光潜和宗白华虽然对情景相互交融作了不少描述,并且将它们直接与意象关联起来,但对于它的发生过程及其可能性的问题,同样没有展开专题讨论。
三、叶朗对意象的现象学阐发及问题
叶朗的意象本体说有两个贡献。第一个贡献是参照西方美学的问题意识,更为鲜明地表述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特征,提出了“美在意象”,以此表明意象乃是审美活动的对象,构成了审美体验的“本体”。它凸显了意象之为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特征,与西方美学观比如跟柏拉图的理念论美学观形成鲜明对比。在这方面,正如他本人所指出的,朱光潜和宗白华已经有了基本的考察与分析①叶朗:“朱光潜、宗白华吸取了中国传统美学关于‘意象’的思想。在朱光潜、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中,审美对象(‘美’)是‘意象’,是审美活动中‘情’‘景’相生的产物,是一个创造。”《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5页。。比如,朱光潜事实上也已经提出了意象是美之“本体”的说法:
“表象”是物的模样的直接反映,而“物的形象”(艺术意义的)则是根据“表象”来加工的结果。……物本身的模样是自然形态的东西。物的形象是“美”这一属性的本体,是艺术形态的东西。[7]71
在这个意义上,叶朗的意象本体说只是顺承了朱光潜、宗白华的意象观,这一提法本身并没有太大创见。他在意象问题上相比于他们而言更多的贡献在于引入现象学思想资源,进一步阐发了意象内涵,并以此对情景交融何以可能的问题做了更为具体的分析。这是他的意象本体说的另一个贡献,在我看来,也是更重要的贡献。
叶朗对于“意象是什么”也即对意象的内涵作了四方面总结。我们下面结合他自己的总结来考察其意象说的基本特点及其可能的思想新意。
第一方面说的就是意象不是物理实在,也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意趣盎然的感性世界。这里的“感性”不是西方哲学语境中与知性对立的感觉经验,而是一种情景交融的经验。这方面的论述,与朱光潜、宗白华的相关论述相比,并无多少新意。
叶朗总结的意象内涵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从审美意象的构成角度出发来阐释情景交融的思想实情。意象是在审美活动中构成的,它不是任何既成的、实体化的存在。
审美意象不是一个既成的、实体化的存在(无论是外在于人的实体化的存在,还是纯粹主观的在“心”中的实体化的存在),而是在审美活动的过程中生出的。柳宗元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彰”就是生成。审美意象只能存在于审美活动之中。[1]59
如果说意象就在于情景交融,而意象又是在审美活动中构成的,这也就表明,要理解情景如何交融,就需要进一步追问审美活动是如何产生的。情景交融暗示了意象何以产生的根源,正面回答情景交融何以可能,将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意象到底是什么。在这方面,叶朗借助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构成理论。在胡塞尔那里,人类的意识在接触到感性材料之后会内在地去“统握”或“激活”这些材料,从而使得杂多的感性材料归属于一个对象,获得一种对象性意识,如此获得的对象性意识就是意向对象(或意向相关项)。胡塞尔通过这种方式说明我们是如何感知到一个对象的。正是意识的这种意向性作用,使得我们在接触事物的时候不会停留在感觉材料层面,而是把它把握为一个对象[8]424。
叶朗将胡塞尔所论述的感知对象构成方式应用到审美对象的构成中来,表明在审美活动中也有意向性,并以此表明,审美意象是人的审美意向性激活感觉材料的结果。
这就是审美体验的意向性,审美对象(意象世界)的产生离不开人的意识活动的意向性行为,离不开意向性构成的生发机制:人的意识不断激活各种感觉材料和情感要素,从而构成(显现)一个充满意蕴的审美意象。[1]72
但是,这里叶朗只是做了一个类比推理,暗示了应该存在一种审美或情感意向性的东西作为意象的保证,并且对意象的产生做了一个含糊的描述。如果审美意象乃是情感意向性所激活的,那么这种审美意象跟感知对象有何区别?叶朗没有注意到,这里其实涉及两层意向激活。首先是感知意向的激活,使我们能够知觉到对象的存在;然后是情感意向的加入,使得感知的对象在我们面前呈现为美的对象也即意象。因此,这需要进一步区分不同层面的意向活动,并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这方面的内容超出了叶朗的考量范围。
事实上,胡塞尔本人对“情感意向性”有过分析。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他将意识行为分成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两大类。按胡塞尔的思路,客体化行为是奠基性的,非客体化行为需要奠基于客体化行为。也就是说,一种喜欢或好感的体验总是对某个东西的喜欢或好感[8]429。换言之,我们对某物的好感奠基于被表象的某物之中。审美体验作为一种非客体化行为,自然也需要以客体化行为提供的对象为基础。“例如对于愿望,对于美感来说便是如此。基层的客体化行为往往是一个复合体,它将这两种行为包容于一身。”[8]553这样一来,审美活动的“本体”依然是客体,而美只是我们对它的感受。按胡塞尔的思路,也就不存在什么情景交融的“意象”,我们对景的“好感”(“情”)并不事实上归属于“景”:
美的感受或美的感觉并不“从属于”作为物理实在、作为物理原因的风景,而是在与此有关的行为意识中从属于作为这样或那样显现着的、也可能是这样或那样被判断的、或令人回想起这个或那个东西等等之类的风景;它作为这样一种风景而“要求”、而“唤起”这一类感受[8]430。
意象能否成为美的本体,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并回应我们的审美活动是否能够构成新的对象性。这个问题在胡塞尔已有的思想框架中很难直接回答,他给出一些暗示、给予了重新诠释的可能性。他指出,当我们喜欢某物时,这种喜欢的快感一方面被立义为对被表象之物的感受,另一方面这种感受又被把握为客观之物自身的特性,也即有好感的东西自身看起来好像被附上了一层“美好的微光”,现在看来,如此被染色的对象才是我们好感的对象[8]432。这种被情绪染色的表象可以对应于中国哲学语境中的“意象”。但是,在胡塞尔这里,“意象”奠基于表象,要证成“意象”自身的本体性地位,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对感受行为的分析①关于胡塞尔有关情感意向性的分析及其与我们这里讨论的感通成象的区别,笔者将另撰文讨论,这里不再赘述。。这方面的工作到舍勒那里才得以展开。
叶朗所谓情感意向的分析,借用了胡塞尔的思路,提供了一个重新考虑情景交融如何可能的新视角,但他并未对情感意向性做专题分析,从而对于情景交融如何可能也就不能给予进一步的展开。
第三个方面是从“生活世界”的角度去诠释意象作为本体的思想内涵。如果审美世界像它通常看起来的那样依赖于物理世界,那么,意象的本体义就有落空的嫌疑,因为客观自在的物理世界才是真正的本体,美的世界不过是对此客观物理世界的一种主观“美化”,并不具有本体义。为了进一步落实意象本体的思想内涵,叶朗参考现象学的思想视角表明,意象世界就是原本“生活世界”,它才是真实的世界。这构成其意象本体说的真正立足点。
意象世界显现一个真实的世界,即人与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这就是王夫之说的“如所存而显之”“显现真实”(显现存在的本来面貌)。[1]59
“生活世界”这个概念同样源自现象学,胡塞尔、海德格尔都有过阐发。生活世界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解释。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叶朗借鉴他们的思路,在中国哲学语境中对它进行了“重构”。他总结出“生活世界”具有如下四个基本特征:其一,生活世界不是抽象的概念世界,而是具体的、原初的经验世界;其二,这个具体的世界是人与万物共在的世界;其三,它自身充满价值和意义;其四,它就是最本原的世界,是真理的原初展现[1]75-76。这几个特征,在叶朗看来,可以用于诠释中国美学中的“真”(“自然”)这个概念。在中国哲学和美学中,“真”就是“自然”,是万物本来的存在得到如其所是的展示①比如,宋代画论家董逌就把书画的“生意”与“真”、与“自然”关联起来。这里的“真”或“自然”不是客观真实或单纯的自然界,而是充满生意、充满意趣的天地万物的一种本然状态。“世之评画者曰:‘妙于生意,能不失真,如此矣,是为能尽其技。’尝问如何是当处生意?曰:‘殆为自然。’其问自然,则曰:‘不能异真者,斯得之矣。’且观天地生物,特一气运化尔,其功用秘移,与物有宜,莫知为之者,固能成于自然。”《广川画跋》卷三《书徐熙画牡丹图》——转引自《美学原理》第74页。。在此基础上,叶朗还进一步分析这种本然状态为什么会充满生意、充满意趣。他借助《易经》的形而上学体系表明,生意、生趣的根源在于天地具有“生生”的大德。由于人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也因此,人和天地万物的本然状态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种和谐统一的“和乐”态②叶朗:“按照《易传》的命题,天地万物是生生不息的过程,是不断创造、不断生成的过程。天地万物与人类的生存和命运紧密相联,而从这里产生了世界的意味和情趣。这就是‘乐’的境界。”《美学原理》,第74页。。在叶朗看来,这就是现象学家眼中的“生活世界”。它们的基本特征都是人与万物共为一体,这是最原本的“真”,也是最真的“自然”[1]78。这就回过头来说明,“生活世界”不仅是真实的,也是美的,它本身充满生意、生趣。由此,他将中国美学的基本理念与海德格尔的美学观关联起来,表明美乃存在的原初显示,是真理的“自行发生”,这就是真正的、本源的“生活世界”:
我们也应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海德格尔的有名的论断:“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美属于真理的自行发生。”[1]77③引文中的海德格尔的文本分别出自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载《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76、302页。
按这个思路,艺术作品照亮的乃是我们本然的生活世界,是主客未分的、万物合一的“生活世界”。叶朗由此拓展了传统意象观的思想内涵,提供了理解意象观的新视角。借助“生活世界”,意象本体说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那种主客二分框架下的客观世界并非真正的本体,真正的本体是主客未分的生活世界,也就是意象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美之本体就是世界的本体本身。
此思路虽然佐证了意象的本体性地位,但是它依然没有正面回答情景交融如何可能的问题。在叶朗的上下文中,“生活世界”就是主客未分、万物一体的世界,而万物一体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基本设定。这就相当于,对于为什么情景能够交融的问题,它的回答是原本的生活世界就是情景交融的。
为什么情景不能分离?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意象世界显现的是人与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在这个生活世界中,世界万物与人的生存和命运是不可分离的。这是最本原的世界,是原初的经验世界。因此当意象世界在人的审美观照中涌现出来时,必然含有人的情感(情趣)。也就是说,意象世界必然是带有情感性质的世界。[1]62-63
因此,“生活世界”观虽然提供了理解意象的新视角,但还是没有正面回应情景如何交融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叶朗的意象本体观描述了审美活动发生以后的“思想实情”,因此,对于情景交融何以可能的问题,需要考察的是审美活动的发生过程。
这就涉及其意象说的第四个方面。他借助张世英的相关论述表明,美感是体验,而不是认识。张世英在他的《哲学导论》里注意到审美活动跟认识活动有一个关键不同。认识活动潜在地以主客二分为前提,也即客体相对于主体的外在性,如此才有认识的必要和需要。审美活动不同,它不在意对方“是什么”,也不需要知道对方“是什么”,在审美意识中,我和对方交融一体,不分彼此。这里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客关系。一种就是基于认识模型的主客关系,这是一种主客二分关系,具有一种“主体–客体”结构。另一种主客交融的关系,在这里主客是贯通一气的。叶朗由此指出,以往对审美活动的考察暗中依靠了认识论的模式,很自然地把它纳入“主体–客体”的结构中来,这种做法根本上违背了审美活动的基本特点。审美活动不需要知道外物“是什么”,不需要把握它的本质和规律,而是通过体验来获得对“生活世界”的整体性把握,这种把握也就是对人与世界交融的体验。
对于什么是体验,叶朗同样借鉴了现象学的思路对它作了展开。他在伽达默尔相关文本的基础上总结指出,体验有如下几层含义:首先是经历性,也即它跟“生命”“生存”“生活”密切关联,在德语中“体验”(Erlebnis)是“经历”(Erleben)的再造,后者又是“生命”“生存”或“生活”(leben)的名词化形态;其次是直接性,也即,它是由生命主体自身经历而来的,是自身经历的产物;最后是整体性,也即,在体验中,体验与被体验物聚集成一个统一的“意义整体”[1]89-90。然后,叶朗借王夫之有关“现量”的说法来刻画中国古典美学领域对审美对象的基本特征,以此表明,意象是当下生成的“现量”,它展示了世界原本真实的那个面向:
“现量”,“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1]90
以下是叶朗对审美体验的基本特征的概括性总结:
审美体验是与生命、与人生紧密相联的直接的经验,它是瞬间的直觉,在瞬间的直觉中创造一个意象世界(一个充满意蕴的完整的感性世界),从而显现(照亮)一个本然的生活世界。
所以我们说,美感不是认识,而是体验。[1]98
叶朗这里用“瞬间的直觉”来说明意象世界的创构,这相比于情感意向性乃至生活世界,对于情景交融的思想实情有了进一步阐发。但是,这种“瞬间的直觉”的说法还是过于简略,不足以展开描述情景交融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且对审美体验的独特性阐释得也不够。叶朗虽然借助伽达默尔的论述表明体验具有经历的直接性,但他没有注意到两者的区别。这种亲身经历提供的只是体验的“线索”“素材”,体验还需要以此为基础进行一种新的构造①伽达默尔认为:“对‘体验’一词的构造是以两个方面意义为根据的:一方面是直接性,这种直接性先于所有解释、处理或传达而存在,并且只是为解释提供线索、为创作提供素材;另一方面是由直接性中获得的收获,即直接性留存下来的结果。”《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叶朗也注意到了体验(审美直觉)不同于单纯的知觉,还需要在知觉活动的基础上有一个“想象”,他还借助胡塞尔的现象学表明审美体验中涉及的是一种原生性想象,而不是再生性想象。他援引了张世英所举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原生性想象。这个例子说的是当我们看到骰子时,会自然想到赌博、进而想到倾家荡产、想到社会风气,以及想到制造骰子的材料象牙、由此想到大象,等等。但是,这里一连串的“想”主要是心理层面的联想,而不是那种被动综合的原生性想象。这个区别对于进一步说明什么是审美体验、什么是审美直觉,至关重要。如果意象是通过再生性想象(也即通常的心理联想活动)获得的,那么,意象就不是“现量”了,不是那种当下直接体验的对象。
由此可见,叶朗引入现象学视域中的意向性、生活世界和体验三个维度来展示意象本体的思想内涵,确实丰富了中国古典美学观的思想内涵,对于我们理解情景交融如何可能的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视野。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对相关问题的阐发还不够透彻,还可以借着现象学的思想洞见与方法,对它再做进一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