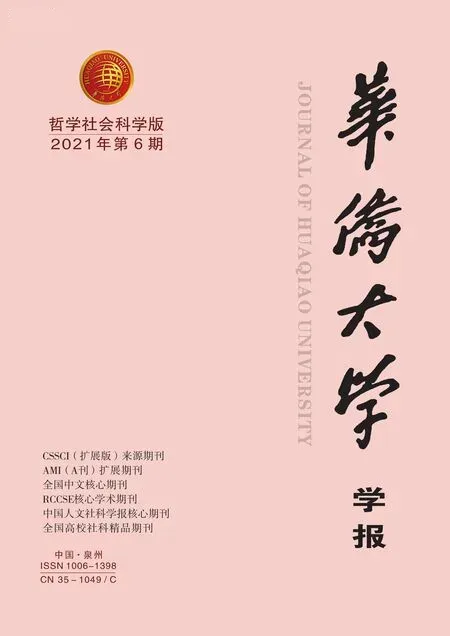自恨现象研究
——以犹太人和黑人为中心的考察
○李俊宇
在人类社会中,自恨(self-hate)这种现象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地,恐难以追溯,但可以明确的是,自恨缘于交往。它是一种心理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存在于个别人或整个群体中。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以及全球化的扩展,族群的主动或被动的迁徙、流散进一步扩大,它们之间的混合、交往日益频繁,文化碰撞加剧,自恨现象随之突显。最深刻的自恨源于弱势族群内化了强势群体对他们的偏见,从而憎恨自己,其极端化的表现形式是自恨者因自恨而心理扭曲,乃至罹患精神疾病。究竟哪个族群最先产生自恨,恐怕已无从知晓。目前国内外学者关注较多的是犹太人与黑人的自恨。相较而言,国内学界更熟悉后者,而对前者尚感陌生。其实,在启蒙运动之后的中欧地区,当犹太人从隔都中解放出来,与外界广泛接触之后,他们中就出现普遍的自恨,于19世纪末为烈。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犹太人中也出现了大量的自恨现象。西奥多·莱辛(Theodor Lessing)最早关注并集中论述了犹太人的自恨。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犹太人的自恨现象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分析,而且还提出解决自恨问题的方案。桑德尔·吉尔曼(Sander L. Gilman)详细梳理了历史上犹太人的自恨。而保罗·雷特(Paul Reitter)认为要慎重运用自恨概念及其理论。黑人的自恨问题在二战后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深入研究黑人的自恨问题,在其代表作《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中指出黑人由于内化了白人的种族偏见,产生了深度自恨,严重者患上精神疾病。法农还提出如何解决黑人的自恨问题的独到见解。随着自恨现象出现的是自恨话语的表达。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是揭示、批判自恨现象最常见的文本形式。在18、19世纪的中欧地区,表达自恨话语的文学作品屡见不鲜,如雅各布·瓦塞尔曼(Jakob Wassermann)的系列小说。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犹太文学中,也出现了许多自恨小说,以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较为典型。美国非裔作家也敏锐地发现黑人的自恨现象,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她的《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中对黑人的自恨现象以及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刻的揭示。总体而言,对自恨的叙述与研究跨越了文学、社会心理学、人类文化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由于自恨现象历史久远,而且涉及众多族群,难以一一细述,故此,本文以自恨现象比较突出和典型的犹太人和黑人作为个案来展开论述,并侧重于研究程度较深、造成心理扭曲和神经症的自恨。
一 何为自恨
顾名思义,自恨就是对自己的憎恨。据美国心理学家戈登·阿尔伯特(Gordon W. Allport)的解释,“恨是由一种强烈情感与责难的观念构成。恨者的这种情感、心理结构难以改变。恨的本质是一种外向惩罚,意味着憎恨者确信错在对方。”(1)Gordon W. Allport.The Nature of Prejudice,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1954, p.363.笔者认为,对于个体或群体而言,“恨”是一种情感与观念的混合体,它有其主体,即“恨”的发出者;它也有其客体,即“恨”的对象。当“恨”的对象是外在客体时,针对的是他人;但如果“恨”的对象是自身,即自恨。自恨的字面意义可以根据其近义词与反义词来理解,它的近义词有:自我轻视、自我厌恶、自我否定、自我怀疑、自暴自弃、自我毁灭、自卑、自贱,等等;而自恨的反义词则有:自尊、自信、自强、自我满足,等等。
国内学者吴泽霖早在1927年留学美国时就注意到了犹太人和黑人的自恨现象,不过那时美国心理学界还未广泛使用“自恨”这个术语,而更多的是用“自卑”来指称它。吴泽霖在《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中说:“很多被压迫者接受了压迫者的观点,拒绝认同于他们所属的群体,学院里很多犹太运动员不愿被列入犹太队长属下。”“很多黑白混血儿低估自己个人和种族的价值,肤色被认为是前进的障碍,对价值、美和成就的理想都模仿白人,至少在外表上。”(2)吴泽霖:《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237页。
学界公认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西奥多·莱辛在他1930年出版的德语著作《犹太人的自恨》(德文为Jüdische Selbsthaß,英文为Jewish Self-Hate)一书中创造了Jüdische Selbsthaß一词,至少是他首次将“犹太人的”(Jüdische)与“自恨”(Selbsthaß)连在一起作为一个词语使用。当然Selbsthaß早在Jüdische Selbsthaß之前已经被德语世界所使用。值得注意的是,“犹太人反犹”(Jewish Anitsemitism)出现在“犹太人自恨”之前。有的学者将二者并置使用,如吉尔曼认为“‘犹太人自恨’可以与‘犹太人反犹’互换使用”(3)Sander L. Gilman.Jewish Self-Hatre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保罗·雷特则认为“犹太人的自我憎恨与反犹主义之间有显著区别。犹太人的自我憎恨是更耸人听闻的,它的内涵是自我背叛,甚至是精神错乱。”(4)Paul Reitte.On the Origin of Jewish Self-Hatr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27.莱辛在《犹太人的自恨》中集中论述了“犹太人的自恨”这个话题。其实在莱辛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些表达犹太人自恨的作品。莱辛将犹太人的自恨看作一种精神疾病,他针对18、19世纪中欧犹太社会中的自恨现象这样认为,“犹太人多年的流散生活,以及对德国性的奴性忠诚产生了‘自恨’这种心理疾病。”(5)Susan A. Glenn.The Vogue of Jewish Self-Hatred in Post-World War Ⅱ America, Jewish Social Studies: History, Culture, Society, 2006(3), pp. 95-163.美国犹太重建派领导人莫迪凯·凯普兰(Mordecai M. Kaplan)也将在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犹太人中广泛出现的自恨现象看作一种精神疾病,他说“自恨这种疾病在美国犹太人中也是非常普遍的。”(6)Mordecai M Kaplan.Judaism as a Civilization, Skokie: Varda Books, 2001, p.4.
在“犹太人自恨”这一问题上,作为社会心理学家的库尔特·勒温坚持“自恨”不是一种犹太人固有的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而是一种社会现象。他在1941年发表的《犹太人中的自恨》一文中,运用社会学心理学上的演绎分析法对自恨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犹太人自恨既是一种群体现象,也是一种个别现象。”(7)Kurt Lewin.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8, p.186.即自恨既可以存在于整个群体,也可以只存在于个体之中。勒温还总结了犹太人自恨的对象,他认为,一个犹太人憎恨的对象可能是犹太人群体,或群体中的某一部分,自己的家庭/家人,甚至是自己,可能是犹太人机构、犹太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也可能是犹太人的语言、犹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理想。勒温还认为犹太人的自恨会呈现为无数的形式,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自己和自己的同伴的自恨表达往往是更为微妙的。”(8)Kurt Lewin.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8, p.189.勒温发现自恨这种现象常出现在弱势群体中,除了犹太人,“在美国人中自恨最为常见也最为极端的例子是黑人的自恨。”(9)Kurt Lewin.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8, p.189.
至20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社会心理学的迅速发展,学界普遍开始关注发生在不同族群中的自恨现象。戈登·阿尔伯特主要基于对犹太人与黑人两大群体的考察,于1954年在《偏见的本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一书给出了一个后来为中国学界广为引用的定义:“自恨这个术语通常用来指个人对自己所属群体所拥有的令人鄙视的特征感到羞耻,不管这些特征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出于想象的;它也用于指个人对所属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憎恶感,因为这些成员‘拥有’同样令人憎恶的特征。”(10)Gordon W Allport.The Nature of Prejudice,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1954, p.148.阿尔伯特试图从普遍意义上来定义自恨,而且他将自恨分为两类:个人对自己群体特征的自恨与对该群体某些成员的自恨。值得注意的是,阿尔伯特虽然提及但没有明确区分对一个群体的特征的自恨与对群体的自恨,他更没能指出从前者到后者之间必有一个过渡。在实际情形中,如果一个人只是对自身群体特征的自恨,那么他可能只会侧重抨击这些特征,当然偶尔会连带抨击群体,而他自己则会想方设法剔除自身的这些遭人鄙视的特征;如果是对整个群体的自恨,那么他常会居高临下地以整个群体作为抨击对象,而且在行动上会疏远该群体,在心理上则将该群体设置为他者。在历史上,犹太人“自我憎恨”与犹太人“憎恨犹太人”是有区别的,后者近乎“犹太人反犹”。
阿尔伯特这个宽泛的定义并没有真正指出自恨的实质。社会文化史家吉尔曼于1986年发表了《犹太人的自恨》这本专著,他借用了阿尔伯特书中的一些社会心理学概念,对历史上犹太人的自恨话语进行了详尽的梳理与深入的分析,他主要是从产生机制来析出自恨这个概念的内涵,“自恨并非某个特定犹太群体天生具有的特点,而是这样的群体内化了某种比较性差异。在一个社会当中,当边缘群体也有可能被接受时,他们将负面形象构建为一种虚构的自我,从而导致了‘自恨’”或‘拒斥自我’。”(11)Sander L. Gilman.Jewish Self-Hatre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08.换言之,即在一个社会中,当某个处在边缘位置的群体,认为如果放弃自我、接受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对他们的偏见,进而改变自己就能被接受时,他们就会产生自恨。 吉尔曼主要是从语言文化学视角来分析历史上犹太人的自恨现象,该书的副标题“反犹与犹太人的暗语言”(Anti-Semitism and the Hidden Language of the Jews)也表明了他的研究角度。
从西奥多·莱辛到吉尔曼,自恨已经从一个概念发展成一套相对完备的理论。而“自恨”概念及其理论的出现、演变与心理学、社会学、语言文化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但自恨概念、自恨理论的使用会发生偏误。针对吉尔曼的《犹太人的自恨》一书,保罗·雷特于2009年发表了重要文章《犹太人自恨章鱼》,该文认为“自恨这个概念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重新定义”(12)Paul Reitter.The Jewish Self-Hatred Octopus, The German Quarterly, 2009, 82(3), pp. 356-372.,并认为吉尔曼是在用“后见之明”(backshadowing)来分析卡尔·克劳斯的自恨话语并将其看作“犹太自恨者”与“犹太反犹者”。雷特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警示批评家在使用“自恨”时要慎重,不能脱离历史语境去分析自恨话语,否则会导致“自恨”概念的滥用,进而易于将“自恨”批评上升为意识形态,如动辄将对自己民族、群体、国家的善意批评者扣上“自恨者”的帽子。不过,如果细读吉尔曼的《犹太人的自恨》一书,会发现吉尔曼并没有轻易将他列出的那些德国、美国犹太文化人士冠以“犹太自恨者”之名,他只是表明这些犹太文化人士表达过自恨话语而已,毕竟表达过自恨话语与本身是自恨者之间是有较大区别的。不过,雷特的警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最近几十年里,当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出现犹太人批评以色列的声音时,“犹太自我憎恨”“犹太人反犹”这种指责之声随即响起。著名的美国剧作家大卫·马梅(David Mamet)于2006年出版了一部名为《邪恶的儿子:反犹、自恨与犹太人》(The Wicked Son: Anti-Semitism, Self-Hatred, and the Jews)的论著,将那些批评以色列的犹太人士扣上“反犹”“自恨”的帽子,并对之进行揶揄、讽刺和严厉抨击。
由上观之,“自恨”概念源于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史家对自恨现象进行描述、分析的需要,并进而形成“自恨”理论。自恨现象比较引人注目的两个群体是犹太人和黑人。前者的自恨在18、19世纪的德国社会和二战前后的美国社会出现两次高潮,后者的自恨在二战前后的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尤为突出。
随着启蒙运动在欧洲的展开以及拿破仑战争对欧洲封建势力的打击,中欧犹太人得以从隔都中解放出来,继之在18、19世纪的德国犹太人中出现了自恨的高潮。他们一心想融入德国社会,鄙视自身的犹太身份以及犹太特征。德国犹太人自恨的特点是他们接受了反犹的德国人的偏见,并将这些偏见看作是犹太人的缺陷。他们常常像反犹分子一样猛烈攻击这些缺陷。德国犹太人憎恨的具体缺陷表现在犹太人的语言、身体、职业、宗教、行为方式以及内含上述因素的身份,等等。在语言上,他们主要憎恨意第绪语。在身体上,则是憎恨女性化的、畸形的身体。职业主要指的是犹太人的商业行为,尤其是借贷业。宗教方面当然指的是犹太教,尤其是其中的哈西德教,他们将它看作是一种迷信和宗教狂热。行为方式上则予以全面的否定。而且德国犹太人常常讨厌、鄙视那些东欧犹太人。
据吉尔曼《犹太人自恨》一书的描述,在德国、奥地利犹太人中出现了大量表达过自恨话语的人物,如西奥多·莱辛、弗兰兹·卡夫卡、海因里希·海涅、卡尔·克劳斯,等等。其中以莱辛最为典型。他对自己的自恨有一段经典的描述:“能否认一株植物与它生长于斯的土壤的关系吗?我难道不是我憎恨并欲之毁灭的人与物的产物吗?我难道不是被弄得残废不堪、自卑深重、缺乏教养、拙劣至极吗?……自从孩提时起我就在学校被灌输了爱国主义和宗教的偏见,而在家里没有什么可以与之抗衡的教养,于是我相信做一个犹太人就是一件邪恶的事情。”(13)Theodor Lessing.Einmal und nie wieder, Bertelsman: Gütersloh, 1969, pp.77-78.莱辛的自恨主要源于他个人原因以及德国社会对犹太人的歧视与排斥。首先,莱辛蔑视他父母以及“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欧洲犹太人专横的利己主义和极端的物质主义特征”(14)Lawrence Baron.Theodor Lessing’s Crusade for Quie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82, 17(1), pp. 165-178.; 其次,莱辛从小体弱多病;再次,他在学业上表现糟糕。莱辛为此感到非常沮丧。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希望融入德国社会时遭到了对方的排斥。莱辛于1906年去过一次东欧的波兰,亲眼目睹了东欧犹太人的生活状况,回来后撰写了一系列贬低、挖苦东欧犹太人的文章,他尤其猛烈抨击加利西亚的犹太人。莱辛后来转向社会主义和复国主义,但他仍然痛斥欧洲犹太人。“莱辛提倡复国主义作为备受自恨煎熬的已同化的犹太人的解毒剂。莱辛对欧洲犹太人形象的贬低反映了他用来使复国主义合法化的同样的意识形态标准。”(15)Lawrence Baron.Theodor Lessing’s Crusade for Quiet, pp. 165-178.由于他公开的民族主义以及对纳粹的激烈批评,于1933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遭纳粹分子暗杀。
19世纪欧洲另一个典型的犹太自恨者是奥地利哲学家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1880—1903),他深陷自恨情结中无以自拔,最后在23岁那年以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魏宁格在其代表作《性与性格》(Sex and Character)中明确表达了他对犹太民族的憎恨。在该著作中,魏宁格将犹太人与女人类比,而将德国所谓的“雅利安人”比作充满阳刚之气的男人。尤其在该著的第十三章《犹太主义》中,他用偏激的语言对犹太民族展开猛烈攻击。魏宁格除了断言犹太人缺乏男子汉气概,还认为他们缺乏真正的信仰、高贵的精神、形而上的思辨能力,等等。《犹太主义》这一章中满篇都是这种恶毒的自恨话语,比如,“犹太人身上的女性素质比雅利安人更多,乃至最具男人气质的犹太人身上的女性素质也多于最少男人气质的雅利安人。”(16)(奥)奥托·魏宁格: 《性与性格》,肖聿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第334页。“无论是正统还是非正统的现代犹太人,都既不关心上帝也不关心魔鬼,既不关心天堂也不关心地狱。”(17)(奥)奥托·魏宁格: 《性与性格》,第337页。魏宁格还攻击犹太教,他说,“犹太人的一神教与对上帝的真正信仰毫无关系,它不是一种有理性的宗教,而是一种老年妇女建立在恐惧上的信仰。”(18)(奥)奥托·魏宁格: 《性与性格》,第341页。
二战前后的美国犹太人,由于受到同化和融入美国社会的压力,也曾普遍遭受过自恨的折磨。他们的自恨包括对自己犹太同胞的自恨和对自身的自恨两个方面。在美国,那些先到的已经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德国犹太人常常鄙视、憎恨那些后到的东欧犹太人。从19世纪80年代至一战前,大约有两百万东欧犹太人移居美国,这些贫穷且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犹太人在美国饱受歧视。久而久之,他们也习得了自恨,并且将自恨传给了下一代,“那些在美国长大的东欧犹太人的孩子,像以前的德国犹太人一样,将他们的民族之根,尤其是他们的宗教,看作是他们备受羞辱和耻笑之源。”(19)Richard M. Alperin.Jewish Self-Hatred: The Internalization of Prejudice, Clin Soc Work J, 2016 (44), pp.221-230.
在黑人当中也曾普遍出现、至今依然存在较为严重的自恨现象。一些黑人由于内化了白人对他们的偏见,从而鄙视自己。他们将白色视为美的颜色,将黑色视作丑的颜色。一些黑人妇女力图抹去自身的黑人特征,她们大量使用漂白剂来使得自己的肤色变浅、变白,“一些牙买加人使用皮肤漂白霜让自己的皮肤变成棕色或浅黑色……自恨和低自尊是漂白皮肤现象的注解。”(20)Christopher A. D. Charles.Skin Bleaching.Self-Hate, and Black Identity in Jamaica,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2003,7(6), pp. 711-728.可笑而又令人心痛的是,在黑人中曾兴起过“反对卷发”运动,他们认为卷发是黑人低人一等的生理特征,所以想尽办法将卷曲的头发拉直。一些黑人模仿白人尤其盎格鲁-萨克森白人新教徒的说话方式。在黑白混血儿中,自恨表现得隐秘而深刻,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自恨。黑白混血儿骑跨在黑白边界的栏杆上,在心理与行为上倾向于跨过这个栏杆,倒向白人一边。他们不仅憎恨自己的黑色特征,而且憎恨那些肤色很深的黑人。弗兰兹·法农在他的《黑皮肤,白面具》中描述了深受种族主义偏见毒害的安地列斯岛上的混血黑人,他们具有深度的、难以祛除的自恨情结。
自恨在程度上差别很大。几乎在每个人身上都曾有过偶发性的、轻微的自恨情感,但严重的自恨会导致心理极度扭曲和神经症。从轻微的自恨发展到精神疾病,它不只是量上的积累,更是质上的突变。轻微的自恨带有偶发性,易产生、易消失,但严重的自恨则是持久而难以消退的,即出现“自恨情结”,会伴随一个人的一生,如莱辛的自恨。在历史上,犹太人的自恨一度达到了一种极端的程度,“个别犹太人敦促雅利安人消灭像害虫一样的犹太人,有的犹太人甚至实施自杀来祛除犹太性污点。”(21)Fred Skolnik.Encyclopaedia Judaica(2nd. edition). Jerusalem: Keter Publishing House, 2007, p.266.奥托·魏宁格被认为是一个深度的犹太自恨者,后来以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可见,严重的自恨会极大地损害自恨者的身心健康,极不利于族群的健康发展。欲消除自恨,则需先厘清自恨产生的原因。
二 自恨产生的原因
在全球化时代,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族群与族群进行交往时,由于强势文化的霸凌态势,弱势文化往往处在被挤压的地位。那些弱势文化的民族或族群在与强势文化的民族或族群交往时,如果没有坚持自身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往往会产生自卑乃至自恨感。这是在交往中相互比较的结果。比如,在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显示出强大的活力,并产生一种将各个少数族群裹挟进去的内吸力,在这样的一种态势下,一些原本携带着深厚、悠久历史传统文化的少数族裔,在强大的盎格鲁-萨克森新教文化的威压之下,会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文化传统已经“陈旧”“落后”, 从而变得自卑、自恨。只有经过60年代的种种文化运动的激荡,到了90年代,多元文化局面的形成,“族群中心主义”的倡导,这时候这些少数族裔的自卑情结才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在民族、族群的交往中,除了文化地位上的不对等造成持弱势文化的民族或族群的自卑、自恨之外,还有就是种族歧视、种族排斥和种族压迫。种族歧视是种族偏见的结果,种族排斥的原因相对比较复杂,在历史上乃至今天,种族排斥一方面有着种族歧视作为前提,另一方面又是由于那些歧视一方感受到来自被歧视一方的压力,包括经济上的竞争以及被歧视一方人口的迅速增长,威胁到他们的民族“主体地位”。种族压迫由种族歧视和种族排斥演变而成,种族压迫会导致被压迫者的仇恨,而这种仇恨反过来又加剧了压迫者的压迫力度,造成恶性循环,导致心理的扭曲和变态,在被压迫者身上的表征之一就是自卑与自恨,流散境遇中的少数族群更是受害匪浅,他们的自恨最为深刻、最为严重、也最为典型。
流散的英文是Diaspora,Diaspora源于希腊语Diaspeirein,意为“散开、散布、播种”之意。国内有人将Diaspora译为“飞散”“离散”。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萨战争史》中描述过伊琴纳岛人的流散。学界公认的流散是公元70年犹太人被罗马军队赶出圣城耶路撒冷,从此流散世界长达近两千年。除了犹太人,目前学界比较关注的流散全球的群体就是非裔族群。简言之,“流散”意味着某些族群被动或主动地离开原本居住的地区,散居在非本民族占统治地位的国度或地区之中。在民族/族群的交往之中,那些处在流散状态中的民族,如犹太人和黑人,出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必须融入主流群体所控制的社会或圈子中去。如果他们拒绝同化,就很可能永远处在边缘位置。
但少数族群的融入、同化不仅需要付出文化上、精神上的高昂的代价,而且他们在此过程注定会遭受到种种沮丧和痛苦。首先,他们欲融入的主流群体往往对他们持有深刻的种族偏见,表现为一种刻板印象(stereotype)。阿尔伯特认为,“种族偏见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僵硬的普遍化而产生的憎恶。它或许只是一种内心感受,或许会表达出来。它也许针对于整个群体,也许针对于一个个体,而这个个体只不过是所憎恨的群体中的一员而已。”(22)Gordon W Allport.The Nature of Prejudice,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1954, p.9.种族偏见主要是文化偏见,但还包括身体上的偏见,血缘、出身上的偏见,如一些德国人认为“雅利安人”血统上最纯净、最高贵。追根溯源,偏见产生于差异性,以及对差异性的不认同、不宽容(intolerance)。这种差异包括身体肤色、身体长相、语言、宗教信仰、行为方式,等等。对于黑人而言,基本上不存在宗教信仰上的问题,因为他们大多在殖民时期已经接受了殖民者的宗教,主要是基督教。黑人与白人的根本性差异在于肤色以及卷曲的头发,以及他们的行为习惯。犹太人与非犹太人根本性的差异在于宗教信仰,这是犹太人在历史上反复、多次遭受种族歧视、仇恨的主要原因之一。
流散中的少数族群在融入主流社会过程中往往内化了这些偏见,并改变了对自身的认知。内化偏见是一种下意识的融入行为,其潜在目的是减少融入中的摩擦与矛盾冲突,其内在本质则是“屈从”。接下来融入者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抹去这些差异。同时,为了确立自己“新的身份”,或与“旧的身份”拉开距离,他们必须将自身的“他者性”排除掉,或在自己的族群中树立一个“他者”,因而往往会鄙视自己或同类中的其他人。
法农从让—保罗·萨特对犹太人问题的论述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汲取了灵感,深刻地揭示了黑人自恨产生的根源和导致的精神问题。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认为,由于历史上的殖民压迫和奴役,黑人内化了白人对他们的偏见,更可怕的是,这些偏见还成了黑人们的集体无意识。法农除了从精神分析和社会现象两个方面,还从文化因素上来分析黑人自恨产生的原因。他说:“不知怎么地,后来我读了白人的书,逐渐地我接受了来自欧洲的偏见、神话和习俗。”(23)Frant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 By Charles Lam Markman,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p.148.法农还指出欧洲殖民文化不仅改变了黑人原有的生活,而且玷污了他们的心灵,“白人文明和欧洲文化迫使黑人背离了他们原来的生存轨迹,而且我要表明的是:通常所说的黑人的灵魂已经成为了白人的人工制品。”(24)Frantz Fanon.p.6.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主要是针对法国殖民者对安地列斯人的殖民奴化而言的,其实,英国殖民者对非洲黑人亦如此。查尔斯指出,“英国殖民者拔高了他们的价值观,将之凌驾于非洲人的价值观之上,黑人奴隶被洗脑了,从而憎恨自己。这些被奴役的非洲人后代在社会交往中内化了白人对他们的偏见。”(25)Christopher A. D. Charles.Skin Bleaching, Self-Hate, and Black Identity in Jamaica,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2003,7(6), pp. 711-728
在流散境遇中,少数族裔长期的、委曲求全的适应生活,往往导致自身的“异化”,即失去本真。流散生活与寄居生活必然有文化上、心理上的适应。适应意味着迁就、改变、放弃,意味着压抑自己的个性,抹去性格上的锋芒。而融入主流文化则意味着很可能放弃原来的信仰、抛弃原来的民族身份,久而久之会导致自卑。因此,长期的流散生活事实上形成了流散者身上的某些“缺点”,并成为他人眼中的“怪人”。比如“19世纪许多德国犹太人具备了以下性格:奴性、自我贬低、取悦他人、心理不健康、像流浪汉、通过打击同族中的其他犹太人来建立自我。”(26)(美)克劳斯·P. 费舍尔:《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佘江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185页。另外,犹太人长期的隔都生活更是扭曲了他们的性格,正如犹太复国主义者赫兹尔所认为,犹太人“已在犹太隔都区养成了一种性格,逆来顺受、唯唯诺诺。我们多数人都是如此”。(27)(奥)西奥多·赫兹尔:《犹太国》,肖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06页。当然,犹太人的这种奴性性格的形成又是跟他们长期遭受反犹排犹分不开的。魏宁格十分偏激地批判犹太人,甚至将犹太人看成是德国社会这个身体上的“寄生虫”,他的描述中隐隐透露出当时犹太人的“异化” 事实。但我们知道,哪个民族、哪个族群身上没有缺点呢?而内化了偏见的、敏感的自恨者常常会放大这些所谓的“缺点”,并从攻击这些缺点上升为攻击并反对具有这些缺点的整个族群。
历史上黑人亦如此。比如在美洲的种植园经济中,黑人不仅遭受白人种植园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失去了自由与独立,而且由于长期为奴,年深日久,养成一种奴性。在美国19世纪60年代的南方黑人奴隶解放运动中,出现奇怪的一幕:部分黑人不愿离开他们原来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依附性的农奴生活,对奴隶主产生了深深的依赖感,加上对解放后的前途感到迷茫。黑人的这种可悲的状况,正像一头长久关在牢笼里的狮子,一旦牢门打开,狮子反倒不情愿离开笼子,有的走出笼门后又返回里面。
少数族裔为达到融入之目的,不仅内化了偏见,而且按照偏见设法去改变自己,即抹去横亘在融入之路上的差异。如18、19世纪的德国犹太人,纷纷改宗、积极学习和使用德语,力图进入德国主流社会。黑人亦如是,如上文所言,20世纪中后期许多黑人漂白肤色、拉直头发、学习纯正的英语或法语。这些犹太人和黑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对融入抱有极大的幻想,但事实证明,他们这种抹平差异的做法常常是一厢情愿。他们欲进入的群体并不因为他们那些“讨好的”做法而发自内心地接受他们。这有几方面原因。首先,主流群体的种族偏见根深蒂固;其次,这些主流群体恰恰需要的就是这种差异,来彰显他们的心理优势,或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心理上,主流群体将这些欲融入的群体看作可用作反复确定自身的他者,正如西方需要将东方看作一个他者一样。如吉尔曼所言,“当一个人接近参照群体所设定的标准时,这个参照群体的认可就会随之远去。”(28)Sander L. Gilman.Jewish Self-Hatre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在19世纪的德国社会,大多数犹太人似乎已经融入了德国,但事实上,那些反犹分子将犹太人的“进入”“渗入”看作是一种对他们孜孜以求的所谓的纯净的德国精神,德国身体的“玷污”,并进而在20世纪初对犹太人进行大肆排斥与迫害。
当犹太人、黑人遭遇到这种“欲进入而不得”的尴尬境地时,他们中许多人并不是退回到自身的传统、文化中去,而是执着的,“不知反省”地去改变自己,希望最终能够被对方所接纳。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改变、进入、拒绝、改变、自恨”不断循环的怪圈。很自然地,于此境地中的欲融入者倍感苦恼,这是一种“欲进入而不得”的痛苦,即“自恨者”的痛苦。
概略地说,自恨产生的第一个条件是犹太人/黑人希望能够融入非犹太人/白人圈子并被对方所接纳。第二个条件是遭到来自非犹太人/白人群体的种族歧视,即反犹/反黑。在这两个前提条件之下衍生了第三个条件,即犹太人/黑人接受并内化了对方看待他们的观点。这三个条件互为依存,必不可少。试想,如果犹太人/黑人不希望融入对方社会圈子,而是一直生活在自我封闭的圈子里,他们怎么能产生自恨的感觉?如果犹太人/黑人不是受到对方的排斥、仇恨,而是被对方悦纳,那么他们怎么会产生自恨呢?如果犹太人/黑人没有内化对方对他们的偏见,而是坚持认为自己的文化、身份特征没有问题,那么他们也不会产生自恨。拿黑人为例,如果白人都不讨厌黑人的身体特征与行为习惯,不认为黑色是消极的、邪恶的,不认为黑人是暴力的、色情的,那么黑人怎会产生自恨?正是因为白人将黑人的一些特征看作缺陷,看作消极的,而黑人又希望被白人所接纳,所以才导致内心产生自恨。
基于自恨产生的原因,一些哲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教育家提出了解决自恨的方案。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只有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才能彻底解决他们的自恨问题,如莱辛认为自恨“这种精神病理学上的疾病只有通过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人家园才能治愈。”(29)Susan A. Glenn.The Vogue of Jewish Self-Hatred in Post-World War Ⅱ America, Jewish Social Studies: History, Culture, Society, 2006(3), pp. 95-163.勒温指出,在对儿童与成人的教育上,首先要力求抵制自卑与恐惧两种情感。他认为,通过对犹太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教育可以有效地解决自恨问题。他也指出了民族认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认为“这种教育方式不是强迫青少年去宗教学校或周日学校学习,而是应该让他们在一点一滴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上产生民族认同感。”(30)Kurt Lewin.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8, p.194.更为重要的是,勒温从社会和历史层面上指出实现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真正平等才是解决犹太人自恨的根本途径,健康的自我批评才会取代自我憎恨。勒温认为,应该用长远和宽广的眼光来审视犹太人的过去与未来,并将解决少数民族的问题与所有人类命运的问题连接起来。
与勒温类似,法农也认为自卑是自恨的直接原因,因此,要消除黑人的自恨,首要的是如何解决黑人的自卑问题,从而建立起黑人的自尊。法农还提出,还得从社会结构入手来解决黑人的自恨,他说:“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我不仅应该帮助我的病人意识到自己的无意识,抛弃试图变白的幻想,而且要致力于改变社会结构。”(31)Frantz Fanon.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 By Charles Lam Markman,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p.74.勒温、法农尽管是从自身的民族立场上,以对自己民族的思考来提出解决各自民族的自恨的解决方案,但他们的这些策略对解决其他民族或处于流散状态中的族群的自恨都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 自恨文学
自恨文学指的是作家通过创作表达了自己的自恨,或在作品中批判了人物(通常是主人公)的自恨,或二者兼而有之的文学作品。而在吉尔曼看来,自恨文学是作家表达了自恨话语/修辞(rhetoric)的文学作品。自恨文学中最多的类型(genre)是小说,也有戏剧作品。在文学创作中,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并非同一,作者往往能够通过制造一定的距离来审视、驾驭主人公,加上自恨本身具有一定的内省、反观自身的性质,因此,如果缺乏审美判断和伦理判断的丰富知识和经验,读者往往难以分辨清楚自恨文学中到底是作者的自恨,还是主人公的自恨。本文以犹太自恨文学与黑人自恨文学为例,来探讨自恨文学的特点以及自恨文学的创作意义,尤其是对读者的作用。
犹太自恨文学到底起源于何时?其实,在《希伯来圣经》中就可以发现犹太人自恨的端倪,其中的“耶利米哀歌”就是自恨文学的一个经典原型。在启蒙运动中后期的欧洲,伴随着犹太人自恨高潮的出现,涌现了大量自恨文学作品。如德国犹太文学中的雅各布·瓦塞尔曼,创作了《齐尔恩多镇的犹太人》《年轻人雷纳特·芬奇的故事》《小鹅人》等系列作品,描述了犹太人的痛苦,“他们的痛苦也是瓦塞尔曼的痛苦,这些痛苦来自作为局外人的角色。他们真诚地寻求融合,但被恶意地拒绝了……他痛苦地争取被人所接受并仇恨自己。”(32)(美)克劳斯·P. 费舍尔:《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佘江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180页。又如在东欧犹太文学中有一些反映东欧犹太人因悲惨处境而自怨自艾的作品,如肖洛姆·阿莱汉姆的短篇小说《脑伯赤克:希伯来的讽喻》,(33)(俄)肖洛姆·阿莱汉姆等:《犹太小说集》,鲁彦译,开明书店,1927年, 第2页。作者将犹太人比喻为一条备受欺凌的狗,作品带有非常明显的自恨色彩。据吉尔曼的观点,索尔·贝娄也创作了带有自恨色彩的小说。
美国犹太文学中最经典的自恨小说是菲利普·罗斯的《波特诺伊的怨诉》。该作品发表于1969年,恰是美国社会急剧变化、动荡不安的时期,年轻一代的美国人掀起了反主流文化的狂潮,黑人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更是急剧高涨。该小说采用了当时流行于美国文学界的精神分析学叙事模式,小说主人公兼叙事者亚历山大·波特诺伊罹患了神经症,正在接受斯皮尔瓦格医生的治疗。波特诺伊在诊所里向医生回顾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包括幼年、青少年时期的家庭生活,以及他的性经历。在波特诺伊的近乎自白性的叙述中,他表达了对犹太传统的厌恶、憎恨。后来波特诺伊去了以色列,遇到希伯来女子劳米,在那里他发现自己的自恨是美国流散文化的结果。在小说中,以色列女子劳米(Naomi)直言斥责主人公波特诺伊说:“你只不过是一个自恨的犹太人!”(34)Philip Roth.Portnoy’s Complai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p. 122.该作品发表后,遭到了来自犹太社会的猛烈抨击。波特诺伊的神经症是自恨的表征,而波特诺伊的自恨原因主要是内化了反犹的偏见,加上在流散境遇中,波特诺伊极其希望融入美国主流社会。通过该作品,罗斯不仅描写犹太人的自恨现象,而且揭示了自恨背后的深刻原因。
二战后,美国非裔文学蓬勃发展,一些著名的非裔作家,如拉尔夫·埃里森、詹姆斯·鲍德温、托尼·莫里森、爱丽丝·沃克等等,创作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小说作品,来反映黑人在流散状态中所遭遇到的欢乐与痛苦(当然更多的是痛苦),他们在强势的美国主流文化中的慌乱、无依的感觉,以及他们的自恨情结。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美国非裔自恨小说。小说描写了女主人公凯佩拉一家在美国的悲惨遭遇,凯佩拉和她的母亲都是自恨的牺牲品,除此之外,作者还揭示了黑白混血儿隐秘而深刻的自恨情结。正如国内学者所言,“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揭露了这种自我憎恨心理给美国黑人所带来的危害,那就是放弃自我价值只能使他们的人格发生扭曲和变异。”(35)胡俊:《〈最蓝的眼睛〉中非裔美国人的自我憎恨》,《山东外语教学》2006年第1期,第95—99页。
如上文所论及,自恨几乎在所有人身上都发生过,包括作家在内。而自恨这种情感能够刺激作家的创作,点燃作家灵感之火花。敏锐的作家尤其注意捕捉这种普通而细腻的情感,通过适度的夸张来挖掘这种情感深处的奥秘,揭示造成自恨的原因,并指明了解决自恨的路径。自恨文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能够通过描写人的语言、活动,直达人的内心世界,揭秘人的内在心理纽结。罗斯是一位男性作家,他笔下的主人公也是一个犹太男青年,而莫里森是一位女作家,她笔下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女性。作家和主人公在性别上的对应,有利于作家感同身受地刻画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自恨文学的另一特点在于作家表达了一种文化上的批判立场。莫里森通过《最蓝的眼睛》中凯佩拉的悲剧表明,“少数民族团体和边缘团体的身份认可不是建立在抛弃自己的独特性上,而是建立在维护并发展自己的独特性。”(36)胡俊:《〈最蓝的眼睛〉中非裔美国人的自我憎恨》,第95—99页。
结 语
自恨现象由来已久,程度轻微的自恨几乎存在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以及任何人身上。当一个人、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产生之后,自恨的体验就随之产生了。尽管如此,但人类长久以来忽视了自恨这种现象。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人类自我意识的增强,表达自恨的话语也逐渐增多,而自恨概念出现在自恨文学之后,是莱辛第一次明确提出“犹太人自恨”。随着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自恨概念才变得越来越清晰。而对自恨现象、自恨原因以及如何消除自恨的学术探讨也成为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人类文化学的重要议题。自恨产生的原因在于文化上的强弱、种族歧视与排斥乃至压迫、流散族群的客观存在,只要上述因素还继续存在,自恨就不可能完全消除,而且它在一定时候还可能会再次盛行。对于一个民族或族群而言,要彻底消除自恨,首要的是祛除自卑与恐惧,建立民族文化自信。自恨不只是单个个体、单个民族或族群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需要建立种族之间、民族之间、族群之间、国家之间的平等、包容、互信,因此,自恨的消除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本文对自恨概念的论述进行了梳理,并力图揭示自恨产生的原因,但本文对自恨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至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而自恨文学的研究在国内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主要以犹太人和黑人作为研究的案例,其实海外华人中也或多或少存在自恨现象,且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因此,期待有更多学者能够关注自恨的话题,并展开对自恨文学的研究。
-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以法官独立为轴心的协作型统一法律适用之路
- 法益路径下合同诈骗罪中“合同”范围
——与涉合同的诈骗罪之区分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