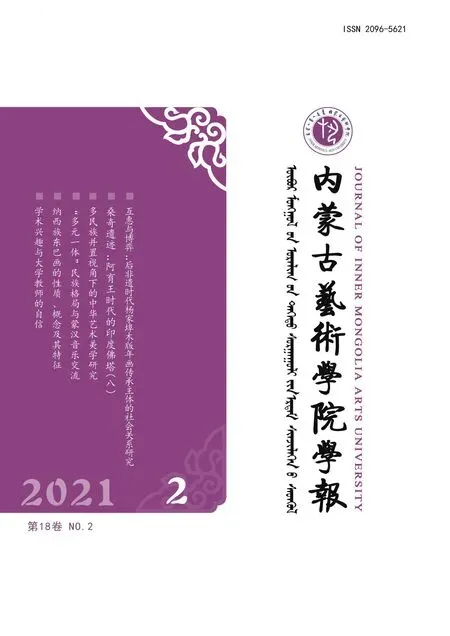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的优势研究
王芳雷 朱志宇
(1.内蒙古艺术学院新媒体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2.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动漫”一词,属中国特有。一般而言,是对动画与漫画的统称。宋磊在其著作《当动漫与旅游牵手》一书中将动漫界定为:“通过构建世界观和故事,推出想象的形象符号体系,再通过符号的反复呈现和不断传播,使其形成价值和品牌,最后通过营销体系使其价值不断变现和放大”的文化产品。其构成要素中,“根基是世界观和故事、核心是形象符号体系、成长路径是反复呈现和不断传播”[1](8)将动漫界定为文化产品,固然是商业社会的客观反应。但不论怎么说,动漫都是一种潜移默化中深度参与到我们现实生活之中结结实实的文化类型、文化形态和文化存在。世界动漫大国和我国动漫发展的漫长历程和实践经历都清晰的指明:创作独具本国特色的动漫艺术作品,走“民族化”发展之路是各国动漫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这种“民族化”体现在对本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合理性运用,并在其中提取出足够代表本民族特有的、生动的、形象化的符号体系。同时,通过当代的诸多媒介环境反复呈现,积极将本民族对宇宙、对人类生存空间、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客观事物的态度和观念与外界进行互动与交流,实现传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最终使传统文化形成价值品牌,在潜移默化中达到相互沟通与和谐发展之目的。
作为内蒙古的一名动漫工作者,我们有责任与全国同行一道,积极整理和挖掘本地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并与动漫创作进行互动与融合。这一过程是当代传媒语境中中国动漫人探索“符合本民族发展需求、彰显本民族文化特质的动漫文化品性与动漫产业发展道路,以及借助于动漫文化的传播、动漫产业的发展来促进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2](126)的必然选择。蒙古族非遗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代生活在我国北方草原的人们在漫长历史发展、民族融合和游牧文化中逐渐形成的独具草原特色和地域特点的文化形态与文化内容。饱含草原人们对自然草原、对人与社会、对历史与时空的“感觉、心性、历史记忆、无意识的文化认同……”[3](6)等文化的文法。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民族根基和重要的精神资源,是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在动力”[4](38)之一。该非遗涵盖大量的民间文学,传统音乐、舞蹈、美术、技艺、民俗等项目,几乎包含了草原生活的全部内容。这些内容在动漫创作中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体现在非遗在动漫作品故事构建、形象符号体系的形成与艺术特色的彰显、动漫作品价值观传递、动漫与非遗延伸产品的无限延展与变现等诸多方面都大有裨益。同时,对该非遗动漫化的优势进行分析梳理,有利于我们在动漫艺术创作中坚定文化自信,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的特殊价值,创作出独具中国特色和内蒙古地域特点的动漫艺术精品。
一、蒙古族非遗与动漫作品故事构建与价值观传递
《文心雕龙》中言:“夫才由天资,学甚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以翻移。”[5](334)故事构建置于动漫创作,就是这一“初化之功”的具体写照。它是动漫创作的重中之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关乎一件动漫作品最终的成败。认真分析世界动漫大国及其优秀动漫作品的成功之处,我们都会惊人的发现其故事构建的独到之处与价值观传递的微妙精深。中国动漫发展至今,传统文学始终作为其创作主题的母库,在动漫作品故事建构和价值观传递中发挥独特优势。诚如朱剑教授所说:中国动漫在“传达民族文化和思想,展示自己文化身份时,首选题材必然是本民族的文学艺术。”[6](248)
蒙古族非遗作为“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大量的民间文学、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等众多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内涵深刻的中华经典文学艺术形式和文化“原型”,是我们进行故事构建这一动漫创作“初化之功”的巨大题材源泉和剧本资源。具体如:《嘎达梅林》这一叙事长诗,讲述了嘎达梅林为了草原和人民的土地,不惜与封建王公、军阀集团和日本侵略者坚决斗争,最终战死沙场的悲壮故事,是蒙古族非遗民间文学项目中英雄史诗题材的重要代表之一;《巴拉根仓的故事》则是通过若干个极富幽默感和戏剧性的小故事生动体现巴拉根仓这个民间机智人物与封建的蒙古王公之间斗智斗勇的传奇人生。它充分反应了广大人民塑造的这一“主人公”的睿智和勇气,是该非遗民间文学中幽默讽刺题材的优秀代表,也是中国人追求真理、弘扬社会正气的生动体现;除民间文学外,该非遗的其他项目内容也能够延伸出独具特色的故事内容。像“科尔沁叙事民歌”这一传统音乐类非遗就极具“叙事性”。其中的每一首民歌都包含一个生动感人的精彩故事,也是动漫创作不可多得的故事来源。这其中,《奈曼大王之歌》是“从昭乌达盟奈曼旗第一位王爷关克巴特尔到最后一位王爷苏德那木道尔吉的三百年历史的概括。”[7](8-12)歌词中既有“对平民百姓有恩德”王爷的传扬、也有对“欺压人民的恶霸王爷”的揭露、还有对“保卫祖国的伟大王爷”的歌颂。该类民歌真诚质朴,其中提到的每一个故事、事件和节点都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和积极整理蕴含其中的生动故事。除了以上这些歌颂祖先和英雄的内容,该民歌中诸多爱情题材更是因当事人对忠贞爱情的歌颂、对封建婚姻的控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代表性的曲目《韩秀英》《格吉德姑娘》《北京喇嘛》等作品及其故事内容,充满了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对普通生活的热爱、对公序良俗的坚守和对人性的普遍关照。动漫艺术创作中对这类题材进行深入挖掘,有利于弥补当前中国动漫爱情类题材的缺失和不足,丰富动漫作品的题材选择和创作空间。该民歌中《波如来》《弟弟不要哭》等幼儿类题材,也都是以真人真事进行创作改编并传唱至今的。这些民歌及其蕴含其中的故事内容真情歌颂儿女亲情,积极褒扬同胞之爱,也能够为动漫创作故事构建和价值观传递提供优秀的题材资源和创意宝库;另外,我们还看到,围绕马头琴、呼麦、安代舞等非遗项目还有诸多或凄美、或神奇、或梦幻的精彩故事,亦是我们动漫创作不容错过的优质故事资源。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马头琴的传说”。该传说讲述了牧童苏和与自己的白马在成长过程中发生的可歌可泣和真挚感人的动人故事。故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诗意描绘、对人与马关系的细腻刻画、对人与人关系的客观呈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生态智慧的生动反应,也是中国人对善与恶、美与丑、因与果等生活与生命哲理的基本看法。传说结尾,白马“以梦相托”,苏和将白马之鬃毛、皮骨幻化为琴的过程,更是中国传统艺术创作中“性无善无恶,情有之。因情成梦,因梦成戏”这一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经典运用。
类似的民间文学内容和精彩的故事题材在蒙古族非遗中可谓举不胜举。纵观该非遗中的故事题材,我们看到:这些故事多以人物为中心,讲述他们的英雄故事、机敏心智、治世之功和生活轶事,歌颂他们敢为人先、不怕牺牲、甘于奉献、坚韧不拔、珍视生活的伟大斗争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同时,还积极揭露人性善恶、倡导健康向上的爱情观念、积极传递中华智慧和价值观念,饱含积极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和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从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讲述和表达着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深切认同,具有浓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此,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将这些优秀的故事资源转化为优秀的动漫作品,创作出了《海力布》《马头琴的故事》《勇士》等极具中华民族精神和地域特色的经典动画作品,引导人们诚实守信、维护公平、坚持真理,成为一代人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许勇等老一辈艺术家,以“嘎达梅林”这一传统文学为蓝本,用连环画的方式为我们生动还原了嘎达梅林这一英雄形象。成为那个时代人们认识非遗、歌颂英雄、倡导和平的最佳方式之一;另外,很多国外的动漫艺术工作者也积极从这些中国传统文学和非遗内容中寻找创作素材和创作灵感,创作出了享誉世界的优秀动漫艺术作品供人们欣赏。如:日本的绘本画家以“马头琴的传说”为蓝本,创作出了图文并茂的绘本作品《马头琴的故事》供孩子们阅读。成为人们认识草原,了解中国和中华文化的一面窗子。
以上分析进一步说明:蒙古族非遗中,传统文学、经典传说和优秀故事在动漫创作题材选择、故事建构与价值观传递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当代动漫艺术工作者应该积极继承老一辈艺术家的光荣传统,在创作中深刻挖掘该非遗中积极的故事内容和生动的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并合理的置于动漫故事构建和剧本改编。依托这些故事创作的动漫故事,必将大大突破当前中国动漫题材选择的局限,从“以儿童题材为主拓展到英雄史诗题材、爱情题材、幽默讽刺题材等不同的类型”。[8](181)进而,丰富并提高当前中国动漫的题材选择和内容构建。它是中华传统文化有序传承和当代发展的生存哲学和“生生”之道,更是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中华传统智慧和价值观念以动漫的方式向世界传递的一种特殊方式。
二、蒙古族非遗“符号”与动漫作品风格确立
一部优秀的动漫作品,不仅要有内涵深刻的故事内容,还要有鲜活的角色、独特的场景、精彩的动作、别样的背景音乐与之相生相伴,它们一起构筑了动漫作品独特的“视听”效果。当今世界,这种独特的视听符号充斥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使“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9](33)作为组成人类经验交织之网不同丝线的蒙古族非遗,在民间文学之外也当然的涵盖传统的音乐、美术、舞蹈、戏剧、曲艺、体育、游艺、杂技、医药、服饰以及相关民俗活动等诸多文化表达的内容和大量的符号体系。这些符号体系的各个构成部分作为构成动漫这一综合视听艺术创作的重要内容,并及时的推出想象的形象符号体系的优势亦是显而易见和值得期许的。
前文提到,动漫艺术故事构建之外,给人以强大“视听”体验的还有炫酷的画面和悠扬的“音乐”(在漫画中则表现为效果字或角色对话设计等)旋律。这种将非遗内容置于动漫艺术创作,则体现在帮助动漫作品实现故事构建的同时,它还能为动漫角色、场景、动作、音乐与声音设计提供强大的符号体系支持和艺术特色支撑。纵观中国动漫创作,动画电影《勇士》、漫画《射雕英雄传》、绘本《巴图和小马》等动漫作品就是将这些非遗“原型”运用于动漫作品创作,从而“陌生化”的呈现和推出想象符号体系的生动实践。
《勇士》以蒙古族搏克这一非遗项目为切入点,围绕“第一勇士”的争夺,构建了一个关于爱恨、复仇和成长的精彩故事。基于此,创作人员以搏克运动的服饰和配饰为依托,推出了故事所需的一系列想象的形象符号体系。这些符号体系包含动画角色、场景、道具,甚至影片音乐等诸多动漫创作环节和具体内容,成为电影想象符号体系和艺术特色形成的关键。现实中搏克运动的摔跤服——颈套五彩将嘎、上身着牛皮或帆布“召格徳”(紧身短袖背心)、下身穿宽松套裤、脚蹬蒙古靴等服饰搭配为影片中的苏和、霍都、巴特尔、小王爷和部分配角服饰设计提供了强大的造型设计支持。同时,创作人员以蒙古族服饰等非遗项目为依托,为这些动画角色设计了动漫化的常服。这些非遗“原型”或符号为动画角色的设计提供了强大的设计资源和具体参考,进一步使动画角色更具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为动画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彰显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因故事围绕搏克这一非遗项目展开,影片场景便在不自然中去推出想象的、“陌生化”的北方草原场景。这些或一望无际、或生机盎然、或广袤无垠的草原场景与动画角色相互映照,成为“吸引观众、感染观众、触动观众的电影视觉语言的一部分”。[10](3)
影片中,人与景的配合达到了“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11](1)的创作境界;与此同时,我们在影片中还看到,伴随铿锵的歌声,搏克手跳鹰步舞入场,裁判发令后双方拱手致意,比赛开始。搏克运动中甩、绊、拉、扑等技术动作和“膝盖以上任何部位着地即为失败”的胜负规则为影片多个不同镜头提供了动作设计和情节设置参考,成为动画角色进行“陌生化”表演和展示的重要依据;影片插曲创作和相关配乐设计中,呼麦和马头琴演奏等蒙古族非遗项目内容伴着动画角色在辽阔草原上演绎的一幕幕精彩故事和感人瞬间更是与动画视觉语言一起诠释了蒙古族搏克这一传统体育类非遗项目的巨大魅力,为影片的成功和艺术特色的彰显贡献颇丰。
整个影片中,蒙古族非遗能够综合运用自身项目内容为动画创作想象符号体系的生成提供故事、角色、动作、音乐、背景等方面全方位的参照与支持是显而易见的。非遗为动漫提供支撑的过程,似唐人写诗,并“不是简单地把玩一角小景、个人的小情小调”而是“重新发现、塑造甚至发明这个世界”。[12]也似中国画一般“在想象中,缔造出一种空旷而幽深、静谧而伟大的宇宙世界,并将我们的视线、精神,从有限引向无限。”[13](33)
著名漫画家李志清先生绘制的《射雕英雄传》,让我们看到蒙古族非遗漫画化的优势所在。与动画一样,这一优势体现在蒙古族服饰和相关习俗为漫画角色创作、情节推进和作品艺术特色彰显提供了巨大的“原型”支持和素材参考。作品中,彼时的蒙古族服饰和日常用具为“想象”中的漫画角色郭靖、华筝等角色服饰、发饰、配饰设计提供了巨大的资料支持。同时,郭靖驯服烈马的一大段情节和画面展示,是非遗技艺为漫画设计提供参考的生动展现。它让我们感受到了“陌生化”的视觉冲击和强烈的心灵震颤。这些画面与大量的效果字和对话旁白相互配合,将郭靖的驯马动作和烈马的桀骜不驯刻画的淋漓尽致。此时,“图画与文字的配合天衣无缝……就好像具有了魔法一般,可以对读者产生神奇的吸引力。”[14](17)这一吸引力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蒙古族非遗中的那达慕、勒勒车制作、搏克等诸多技艺、竞技和体育类非遗内容能够为动漫创作提供精彩的视觉效果,从而为进一步塑造角色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提供精彩的“原型”支撑。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内绘本也在故事讲述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将目光聚集于非遗的再现与传承。在诸多绘本中,保冬妮文、于洪燕绘制的作品《巴图和小马》以儿童的视角,通过巴图与小枣红马之间的互动,讲述了一个关于守信、重义的故事。作品以其精彩的故事、辽阔的草原景色、别样的服饰和情景道具设计,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在大人与孩子诵读和聆听的呼应中,完美演绎了一个极具中华传统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生动故事。这一案例亦让我们发现了非遗为绘本创作提供故事题材和符号体系的最大可能性。
综上所述,蒙古族非遗以其精彩的故事、强大的视听体系和“符号”系统为动漫艺术创作的诸多方面提供强大的资源选择和利用空间的优势是不容置疑的。它将这些作为人类经验的符号形式与动漫艺术融合互动,“在想象中共鸣,给人一种形式的真理……;在视、听、触等感觉现象的理解中给人以秩序……。”[15](799)这一秩序的形成,客观上必将促成中国动漫形象符号体系的形成与艺术特色的彰显,从而在“视听”层面进一步促成动漫作品艺术风格的确立。值得动漫创作者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积极践行和主动实践的。
三、非遗动漫及其价值意义
“无论是语言、文字、图片、影像,还是声调、表情、动作等,都表现为一定的物质讯号”[16](4)非遗的动漫化,就是将非遗中的这些“物质讯号”运用于动漫创作的各个环节和全过程之中。它创作出一个非遗与动漫相结合的“非遗动漫”的“和合体”。这一“和合体”以非遗“原型”构建动漫的世界观和故事内容,进而推出与其相关的“陌生化”的、想象的形象符号体系。这一动漫化的故事内容和形象符号体系以当代传媒语境为依托,以动漫作品为载体,通过互联网以电视、电脑、手机终端等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它把“技术、哲学和传播方面纳入更大的网络框架之内”,[17](29)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反复呈现和不断传播。其现实意义和实际价值重点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蒙古族非遗项目众多、内容丰富,不仅涵盖丰富的故事题材,也能够为动漫创作提供鲜明的角色形象、细腻的动作参考、严谨的道具设计参照,还能提供与这些角色、动作、道具相符的场景和背景音乐资源。在动漫创作中对其深入挖掘,有利于改变国内动漫创作在题材上以儿童为主,其它题材相对较少的现状。同时,也能够为国内动漫艺术作品风格确立和艺术特色的彰显提供可行的现实路径。
其二,非遗的动漫化过程,使非遗内容参与动漫作品题材选择和价值观传递,非遗“符号”体系参与动漫作品风格确立和艺术特色的突出和彰显。它将非遗这一“道”与“技”融入动漫艺术之中,“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18](160)这一过程是传统文化“当代化”传承和中国动漫艺术“民族化”发展的生动实践。
其三,“非遗动漫”作为以非遗为依托推出的想象符号体系,所“表达的意思是超越国境、超越代沟的。”[19](129)此时,动漫作品以生动的视听语言和强大的符号系统充当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并将非遗以动漫的形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它客观上促使动漫受众在潜移默化中认识和了解了非遗内容,也使不同的动漫受众接受了非遗动漫作品,不经意间实现了非遗内容和动漫作品的跨文化传播。这一传播过程使“认识的因素在艺术里面,就像水里放了盐,喝水知道咸味,但你看不见盐,也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但不一定很明确。”[20]它将非遗和动漫凝聚成为一个永久的现在——非遗动漫这个“和合体”,虽“毫不真实,却永不消逝。”这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的独特路径和传播谋略是其他传播形式和传承方式所无法比拟的。
其四,“艺术作品一旦通过传媒介质的制作和传递,便成为一种面向受众的文化传媒产品。”[21](51)非遗动漫这个文化传媒产品,在传播层面的优势必将使受众深刻认识和了解动漫作品中的服饰、配饰、道具及其相关物件,这些物件在动漫作品中形成的吸引力,也会使人们不自觉的产生拥有这些物件的潜在冲动。这种冲动一旦与动漫延伸产品相遇,便形成了非遗的物质实体与动漫的微妙邂逅。所谓:“身实学之,身实习之”、“重之以体验,使可见之施行,”[22](43)这一相遇是动漫与非遗的双赢和共存,哺育与反哺的过程。
艺术“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伟大手段,是求生的伟大诱因,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23](385)蒙古族非遗与动漫艺术的结合与互动便是“生活”进一步走进“艺术”这一手段、诱因、兴奋剂的生动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