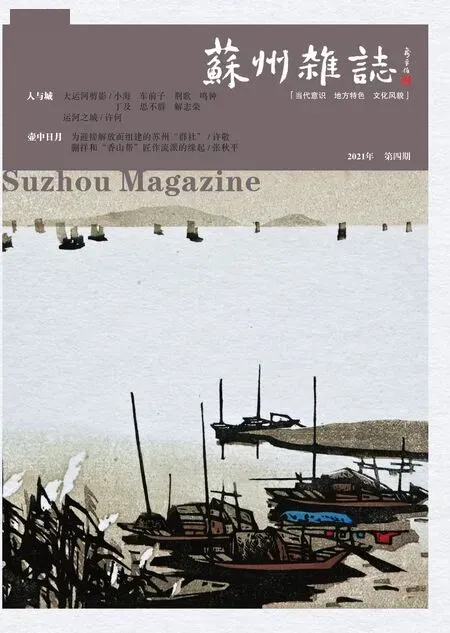吃馄饨
汪放
在太仓,年初五除了放鞭炮,家家户户都要包馄饨,也叫包兜财馄饨。为何有此风俗?正像我只知道:馄饨,在闽粤叫云吞,在巴蜀叫龙抄手。在苏北有些地方不知何故将其称为饺子。
我只知道,从我记事起,吃馄饨,是件改善伙食的大事。后来,无数事例告诉我:吃馄饨,是我们太仓非常重要的风俗和礼仪。说礼仪,它一如走红毯、献鲜花、放烟火。说风俗,它囊括了、浓缩了、饱含了几乎所有的亲情和友情。吃馄饨,以朴素的面貌婉约承载展示着世世代代黎民百姓的智慧、才情和祈愿。它比琴棋书画更亲民,比山珍海味更金贵。
结论似乎偏颇。
孔乙己先生的茴香豆有四种写法,包馄饨我知道的有三种,但我只会一种。我的包法是:加馅,双手先将皮子朝里对折,再朝外折,然后圈起来,用力将两角捏黏住,便完成了。我太太是先在皮子边上沾水,然后黏合。这样的包法好是好,确保下好的馄饨包住馅的汤汁,但速度慢半拍,我觉得费事,从未效仿。包馄饨,外婆总数落我反撬,她说包馄饨要包兜财馄饨,包好之后,要像元宝。哪能可以拿财气往外翻格。其实她的方法与我的大同小异,只是对折时有往外向里先后之分。小馄饨,也叫绉纱馄饨,一手擦一星馅,一手团握皮子,秒杀完成,但我从未试过。
反撬大概是我的习惯,乃至于本性。比如夹菜,我也是筷子反撬。这也常被我外婆、母亲数落。我反思,我的反撬,或是潜意识里的逆反,抑或是好奇心作怪。你们把馄饨视为兜财,我看是穷怕了,慕富。自发现了我有这种潜能,我就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这一反撬,打量周边的世界。
包馄饨,我们这里最常见的是包野菜馅馄饨,还有是小白菜馄饨和毛豆子馄饨。小白菜含水足,纤维长,很难挤控干,包出来的馄饨扁塌塌的,容易黏,既不好看,又不好吃。毛豆子馄饨,鲜是比小白菜鲜,剁起来滑来滑去,如果剁得不细,索落索落,吃口不好,食材又明显受季节影响。我们通常说包馄饨,指的就是野菜馄饨。约定俗成,特指荠菜馄饨,不必说明是何种野菜。母亲说要我们去挑野菜,又是特指的麻里头野菜,它与其他品种的荠菜大有不同,像乡下大姑娘,零星长于田埂场角,为人兽鸡鸭踩踏,它紧贴地面,叶小而色褐。挑拣麻里头自然不便,然其茎叶韧,出菜率高,有嚼头,比其他野菜香好多倍,尤其是根。至于长在大蒜田里的野菜,壮大肥实;长在油菜地、蚕豆地里的,碧绿生青,好看不中用,与种植的相差无几。
包馄饨,不能漏了君王。君王便是肉,猪肉。小时候,众多邻里乡亲一年到头,除了春节,是很少能吃到肉的,红烧肉更是奢望。平时吃馄饨是件很不寻常的事,因馄饨里面有肉。记得我家倘若包馄饨,总要分送左邻右舍一碗。母亲的小姐妹湘伯家包馄饨,总要提前两三天相约我们一家老小去帮忙。
湘伯剁肉糜很快,但和馄饨馅很慢。我很小就知道肉、菜、皮子的比例基本就是1比2比3,湘伯,一般的熟人叫她湘弟阿伯,似乎永远吃不准。她总是不断地添肉加肉,每次都要反复仔细观察肉菜的比例,嘴里总是喃喃自语:蛮肉,蛮肉。最后,总是让我母亲来定夺。湘伯的鼻子比狗鼻子还灵,她只要一嗅,就可精准明确馅的咸淡。肉是君,盐是臣。想当年,这君确实金贵,但臣子却是寥寥,除了一宰相:盐。还有两大臣,猪油和大蒜叶。不像现在我和馄饨馅,还要放鸡蛋、糖、醋、鸡精、生抽、蚝油、麻油、菜油、胡椒粉、孜然粉,杂合乱缠,各种调料有啥放啥,味道丰富,且有层次。写到这里,忽又觉得,当年的馄饨,汤清纯,味纯粹。
纯粹难免寡淡。1979年底,我在苏州读大学。那时江苏师范学院提供伙食,每月发的菜票是9元9毛。每天的伙食基本不变:早上两只白馒头,中午和晚上一块大肉,加一碗菜汤。肉很大,足有二两重。天天如此这般,未免寡淡。于是乎,周日,约上老袁或其他一两个家境稍好的同学,午后先步行去乐桥的古旧书店淘书,再去北局看场电影。电影结束,又去观前街新华书店。出书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几乎同时,喊一声:去!看官,我们这是去哪?告诉你,绿杨馄饨店。
绿杨馄饨店地处观前街东端南侧,两开间门面。现在挂的是中华老字号,有分店。除了馄饨,还有小笼、生煎等其他点心,以馄饨为主营。我们只要馄饨。绿杨馄饨不很特别,精彩处是汤。汤是鸡汤,外加鸡丝和蛋皮。寒冬腊月,天色已昏,饥肠辘辘,吃上10个馄饨,嘶啦嘶啦,仰天将最后一滴汤喝光,这个美啊,一辈子难忘。
我还有过一次一辈子都难忘的看吃馄饨。
父母在“五七干校”,大哥插队农村,二哥在沙溪读书,外婆老了,小妹还没上学,打水的任务自然落到我身上,那时我已经读四五年级。我家用水可提井水,井在院子的那头,需要穿过丛丛杂草,除了花脚蚊子,冷不防会爬出癞团、百脚。癞团我不怕,可以刮浆卖钱,百脚我也不怕,但是据说有人看到院子里有好几条绿幽幽的。前厅药店的老金说,绿百脚比地扁蛇还毒,因此,外婆要我到河里拎水。我家上水桥不远,只需穿过半条弄堂,再经过湘伯家的一个小天井和一个小凉棚就到了。
湘伯做家务几乎经年在凉棚,比如拣菜、纳鞋。她和她先生老叶一样好抽烟。他俩抽的都是水烟。抽水烟要折烟媒子,她就在凉棚里的小方桌上先折后卷,这活我很小就会。折一沓烟媒,老叶就奖励我一个香烟壳。他在供销社的烟杂店上班,曾给过我一个老刀牌香烟壳,那是解放前的东西,不知他哪儿来的。湘伯的凉棚,除了那张小方桌,还有好几张高矮不同的竹椅子,是为我外婆等备着的。
那是个夏日的午后,我又去拎水。知了在树上聒噪。我却听到湘伯在说,隔壁的隔壁阿毛家明天吃馄饨。有人问,阿是明华上门?答道,是。明华是我大哥同学明玉的姐姐,辫子长到腰眼里,是个民办老师,教幼儿园。明玉姓周,周老师多次对我说,我小时候她经常抱抱我。我想这肯定是真的。
不年不节,阿毛家怎么想到吃馄饨了呢?第二天早上,我套知了回家特地弯到阿毛家。阿毛家的宅基地不大,门前场上架着芦席,晒着几条新被头。还有一根竹头,一头搁在檐下的竹节上,一头搁在场当中的竹竿上,晾晒着两条被面子。一条是红底绿叶的牡丹花,一条是真丝的暗花被面。我就是从被面子下穿过,到西面河滩边上的。阿毛家的河滩边种有好几棵楝树,不高不矮,我的长竹竿刚好都够得着,但知了不是很兴,何况他家还有一只大黄狗。
我只是套了一歇歇。果然,明玉,还有明华和她爷娘、兄弟一众人等,推着自行车,提着些花里花绿的来了。阿毛的娘迎了迎,就进了屋。阿毛的爷发了一圈香烟,引着明玉爷娘、明华众人也进了屋,明玉与她的兄弟站在门口。过了一会,阿毛娘出来,递给明玉把蒲扇,说是要去包馄饨了,明玉也就跟了进去。
被面子轻轻飘动,几只鸡在刨地,我扬起竹竿,赶得鸭子呱呱叫,飞到了河里。
没看到啥,也没听到啥,不死心。下午三四点钟,我摸螺蛳回家,又弯到阿毛家。正好看见阿毛的爷娘送明玉的爷娘出来,明玉、明华他们跟在后头。只见阿毛娘一面扯着明华的袖子一边说:今朝阿伯一早晒的被头,暖热洞洞格,倷覅走,帮阿伯钉被头。一面朝着明玉的爷娘讲,阿哥阿姊走好,来白相哦。明玉的爷娘嘴里说着:好,好。也来白相哦。就上车走了。明华在阿毛娘的拉扯下,半推半就进了屋。
我百思不得其解,大热天的晒什么被头?阿毛娘是有名的巧手,钉条被头还要客人帮忙?几天之后,我上水桥,听那几个阿伯老太讲,明华到阿毛家吃过馄饨了,定在初三办事体。
腊月年底,明玉来喊,要我们去帮忙装喜糖。闲话中,我才知晓,那日名为吃馄饨,其实是办订婚宴,是我们太仓当地的风俗,也叫走通。当日最主要的事项是双方家长商定结婚日子,称为作日脚。吃过了馄饨,通常当夜女囡会留下过夜,从此之后,两个小青年就可以光明正大同居了。吃馄饨,是我们太仓一地约定俗成的婚姻仪式。
馄饨已从当年的大餐演变成了今日的小吃。但在我的家乡太仓,至今保留着大年初五、正月半、八月半这三日各家各户吃馄饨的风俗,还保留着将订婚称作吃馄饨的习俗。回想起这关于馄饨的种种,不禁觉得这简简单单小小的一碗馄饨,竟包蕴着一个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