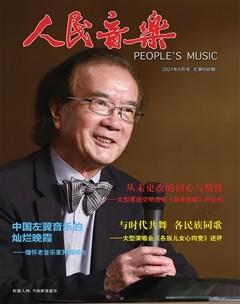论学术层次
20年12月8日,笔者应邀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的纪念民族音乐学会首届会议召开四十周年的系列学术讲座中作《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论超越在中国音体系研究中的引领意义和探索功效》讲演,反响强烈,说明这个话题切中要害。这次讲演的意义就在于针对目前音乐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重新论述学术研究的层次概念,即从形而下的研究层次上升到形而上的研究层次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浅入深分析抽象的“形而中”层次。如果我们把从“形而下”研究到“形而上”研究比作“到达彼岸”的话,那么,“形而中”的研究就是过河的船或桥,其不可忽视和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形而下”和“形而上”是中西共有的两个古老的哲学概念。在西方由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提出,即physics 和 Metaphysics。前者一般译为“物理学”,常常被当作理科概念。其实,它讲的是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是物理学家,在当时条件下,他一定是在物理学研究到达“极限”却仍不能说明宇宙奥秘的窘境下才领悟到必须由超越物理推衍“极限”的思辨去揭示某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真理。meta就是“高于”或“超出”的意思。亚里士多德是既能做“形而下”研究又能做“形而上”研究的哲人,两者在他身上是统一的。在中国,这对概念最早见之于孔子(前551—前479)编修过但成书年代不详的《易经·系辞》谓:“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后人对“器”有不同解释,但大体上与西方的认知是一致的。中国自古提倡“得道成器”,就是对“天人合一”说真正内涵的诠释——精下学之术,辨中学之义,求上学之理的天道践行。儒家奉行的“中庸之道”,如果摈弃其“不偏不易”的遁世哲学含义,从积极的意义上看,也可以说是一条通向学术人生巅峰的正道。“不偏”就是不走极端化、派性化的斜路;“不易”就是不投机,不跟风,不抄近道。这样理解就扬弃了中庸思想中“折中”“平庸”的遁世哲学含义,而取其目标恒定(“道前定则不穷”)、博学贯通(“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至诚尽性与天地参(“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①的进取哲学精华,实事求是地从问题出发,逐步深入学问肌理直至核心至理的践行。愚以为,这就是一切学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和基本能力;有这种素养和能力才能把学问做深做精。
凡音乐都以音响为媒介。它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听到,有结构形式,说明它是物质化的,通过声源的振动和声波的传送达到人耳和整个听觉系统,包括听觉心理的认知系统。所以,从根本上说,一切音乐学研究都必然含有从“形而下”到“形而中”再到“形而上”的层次化过程。其中,“形而中”层次扼守着某项研究通向成功的通道,在这个层次踯躅不前或铩羽而归就成功无望。
做任何层次的研究都必须既心有大道又手握利器。要避免学术中空,就要重提“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音乐形态研究而言,“事”指研究对象,即音乐本体及與音乐本体形态发展相联系的社会与人。“欲善其事”则必须首先做好表层的调查、搜证、归纳和描述,经过在内层步步深入肌理的分析和辨析达到对核心层次要义的理论抽象和晶化表述。“器”指科学化的方法论。“利器”,也称“大器”,不是钝器、沙器,更不是银样镴枪头的耍器。但任何利器都要人去掌握,是为“术”,对研究者来说,就是辨析能力和表达水平。“必”字和“先”字强调了“利其器”的不可或缺性和先决性。然而,大器的磨砺不是一日之功。整天赶潮流貌似在“学”,其实无“术”,到了写学位论文大限才临时抱佛脚,就只能去从词语上“摞叶子”装点门面了。
层次化研究的观念,据笔者从事的音乐形式分析和音乐形态分析的经验,可以把构成音乐本体结构的音调和节律两个主要方面各分为四个层次。图示如下:
这四个层次都是从音调和节律的具象或表象由浅入深的抽象步骤,具有可操作性。从音调到音列是对音高外形的初步抽象,最容易。大家所熟知的[0,2,4][0,2,5][0,3,5](即do-re-mi,re-mi-sol, mi-sol-la)“三音列”的五声音调归纳描述法,就属于这个层次。调式研究属于“形而中”的第二层次。我们的传统乐学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基本上是在这个层次打转,把调式辨别、分类和命名看成乐学研究的全部,因此出现了八十年辩不清“花音苦音”的实质,六十年结束不了“闰变”之争,四十年弄不清“同均三宫”对耶错耶的踯躅现象。赵宋光先生在1978年中央院作曲系和声课上所讲授的“两翼五度相生”和声功能体系和“180调音系网”达到了音乐形态研究的“调域”层次,使我辈眼睛一亮。笔者就是在那时继承了赵先生的理念开始对中国和东方音体系进行了几十年独立研究的,终于在2013年动手写《西北民歌新论》系列论文时突然意识到调性研究才是音乐形态研究的最高层次。没有调性研究的提纲挈领,调式研究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走入瓶颈。后来,在《什么是调性》(《音乐研究》2017年第4期)一文中把有关论述集中起来,对调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提出了新定义,并提出“调性即人性”的命题。
关于节律,我们目前基本上是在音型层次,由杨儒怀先生1978年在讲义中提出的节奏均分、点分、顺分、逆分为代表。从音乐形态研究的角度看,这种形式上的分析还远远不够。例如,“乐节”是个曲式划分概念,而“韵步”则是音乐律动概念。作为艺术化的语言,任何有语义的音乐形态都必然塑造出与人的脉动与呼吸相呼应的韵步才能打动人心,被人感知。例如,笔者年轻时听到一首《摇儿歌》,如果单用节奏节拍手段描述,无非是“徐缓的四四拍,四小节,两乐句”。然而,如果用层次化的韵步法分析,所见结果大不相同:
图2清晰地显示,在这首可以反复咏唱直至小儿睡熟的旋律中,至少隐含了四个波涌层次。②以下是笔者的辨析大要:
第一层最单纯,就是母亲或奶奶摇动婴儿的身体律动。图示中标示的“→←”是怀抱小儿的左右运动,呈无穷动式,向右为下拍,向左为上拍,不可逆反。如果只是拍打,也可用“↓↑”图标记谱。请注意:音乐形态分析与音乐形式分析的不同点之一就是观察和记谱必须包括对歌者体态运动和其他有意义的环境因素的记录,并且把这个层次纳入分析的范畴。
第二层是摇动婴儿时的哼唱,节拍与身体律动完全吻合,但节奏不同,就是与身体律动完全吻合的节奏只出现在第2和第4小节的前两拍四分音符(一动一音),之前是二分音符(两动一音),之后是两后休止(有动无音)。这是历代巢湖妇女的伟大音乐艺术创造!两动一音产生推动感,一动一音产生坠落感,有动无音产生期待感。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语义鲜明的韵步。从美学和心理学意义上讲,第二层与第一层的复式错合产生迷离效应。这就是为什么这首歌可以催眠的缘故。
第三层是韵步节律分析。从这一层开始是深入肌理向形而上层次突进的关键。这里,我们看到第一韵节和第二韵节的节律相仿,都是在第5拍上坠落,形成5∶3正黄金分割的起伏格局。这首先超越了“2+2”的乐节思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第2和第4小节的两拍无声运动中,歌者的呼吸是不同的。在第2小节的坠落之后,歌者是不会把气用尽的,只是屏息和细细地吸进一些气。所以,这个波浪不是乐句,而是推向后浪的一个涌动环节。有意思的是,到第4小节的第二拍,歌者是把气息耗尽了的,然后深吸一口气。她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两个韵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呼吸循环,前为吸,后为呼,如海浪之滚动,后浪高过前浪。与这种大节律的循环配合,音调以商音为中轴上下两个对称的三音组([0,2,5][0,-2,-5]或re-mi-sol,re-do-la)勾画出一正一反的、经得起无限反复的旋律进行。这不得不令我们这些矢志发现民族音乐奥秘的学者们再一次折腰敬礼!从美学和心理学意义上讲,这一层与前两层仍旧是复式运动,但主要是产生推动效应,使这四小节的短歌可以十遍百遍地滚唱不断。
第四层是乐句节律。笔者的新发现有二。第一,这是一个“一口气”大乐句,在第4小节并未完全终止,而是滚动式延展,所以不宜称为“乐段”。“一口气”原则是判断音乐基本结构的准绳。正常情况下中速四拍(心跳四下)为吸、四拍为呼。运动之后心跳加快就会呼吸急促;受到巨大惊愕或悲伤过度就会屏息,喘不上气来;在极端情况下,人的心理屏息忍受度可以达到或超过一分钟。这就是利盖蒂《大气》征服听众的原因。③笔者分析,这部8分钟的作品是由5个超长大乐句构成的,尽管没有旋律,却十分吸引人,奥秘就在于它迫使听众在8分钟内心理上只“喘”了五口气。第二,一个更重要的发现是乐句层次的结构仍是由黄金分割控制的,但不是从第1小节开始,而是从第2小节下拍的第一黄金分割点开始,第二黄金分割点为整个大乐句的黄金分割点,前后比例亦为5∶3。这样,第一韵节的节律功能就出现了双重性:在韵节层次,它本身是一个韵步(即一个起落);但在乐句的层次,它是一个“起”(“上涨”),而第二韵节是“落”。值得深入讨论的是,韵节层次的起落是小涌,乐句层次的起落是大涌,两者有错落、有重合,也是复式运动,只不过大涌的运动处于深层,不容易直观觉察,但绝不是不存在、不可感知或不起作用的。这种隐性或显性的复合层次的存在是音乐的共同规律,并不因为织体为单旋律就是“线性思维”。音乐之美,说到底就在于韵律美,而韵律美来自复合层次波涌的运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节律研究在所有的四个层面上都直接联系到人的生理属性中与情感趋向相关的部分。可以说,有什么情感就有什么韵律,韵律就是人性在音乐中的体现。
根据以上辨析,我们有充分理由说:第一层和第二层是“波”。波是韵律的表层,或称近景,是音乐形象感知的基本层面。在这首《摇儿歌》中,具体表现为人声哼唱对人体律动的艺术化。第三层和第四层是“涌”。涌是韵律的中层(中景)和深层(远景),也是可以感知的,但不是具体形象,而是总体的情感荡漾;没有涌动支撑,波动就失去感人的力量。这就是对一件音乐样品的复合韵律形态所作的“形—意—神”层次化综合分析。显而易见,这种分析能把凭感知得到的东西看清楚,从形到意,从意到神,大彻大悟,每一步却都不是臆想,而是以实证为基础的辩证。这就是朱载堉引用朱熹的话“盖下学中,上达之理皆具矣”④的道理。有了这个坚实的本体研究基础,通向形式分析、美学分析、心理学分析、文化地理学分析等等交叉学科的研究只在一步之遥。
这首歌是我少年时在北京表弟家偶然听他奶奶——一位从巢湖进京看孙子的老人——哼唱的,当时也没记谱,只是心里不断揣摩,赞叹不已。笔者在《西北民歌新论》开篇分析的《二十里铺夯歌》是1966年在陕北高原徒步行走时,在延安南郊看见对面崖畔上开凿新窑洞的汉子们唱着歌打夯用心所记,也是反复哼唱,赞叹不已,1983年讲曲式与作品分析课把它写进讲义里。笔者相信,这两首同为16拍一句体的短歌最终会被世人认识到是中国民间音乐艺术的双璧。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独具慧眼的辨识能力和言必有据的实证能力。如果有,就可以破石见玉,然后打磨任何珍品都不成问题。如果没有,就不可避免陷入“中空”的陷阱。
勿容赘述,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零星开始,40至60年代奠基,80年代后蓬勃发展的各种形式、各种学派的音乐形态研究是卓有成效的,已经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信息和素材。例如,我们在八九十年代陆续出版的各种音乐集成就是世所罕见的壮举。但是,我们在“形而中”层次研究手段的薄弱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只要这种现象还普遍存在,我们的音乐形态研究就会一直在“形而下”和“形而中”的下层打转,长久在“此岸”徘徊。解决方法只有一条:架桥造船,或者说,填补“中空”。如何做?笔者将在续篇《论超越意识》和《论达标意识》中奉献自己的拙见,与大家讨论。
① 以上括號内三段原文均引自《尚书·中庸》。
② 关于这首歌的音高、音阶、调式和调性,详见周勤如《〈巢湖摇儿歌〉调性
调式辨析——中国南方音乐形态个案研究之一》,《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77—86页。
③ 周勤如《利盖蒂〈大气〉结构与调性声景分析——兼论适应21世纪音乐
分析的若干新概念》,《黄钟》2017年第4期,第23—44页。
④ [明]朱载堉《律吕精义外篇卷之一·古今乐律杂说并附录》 ,冯文慈点注本,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第838页。
周勤如 《音乐中国》(英文)主编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