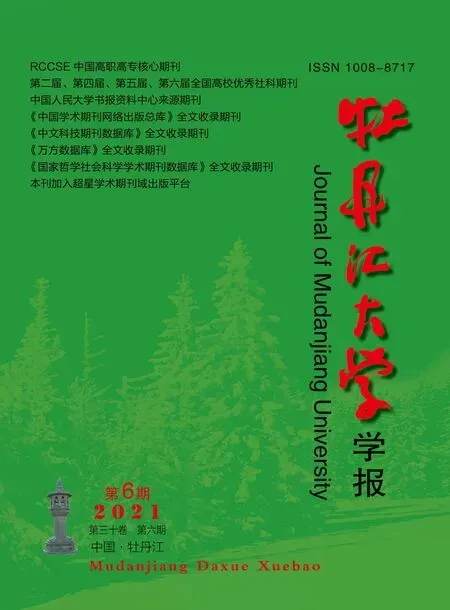现代都市的革命性与反革命性
——列斐伏尔《都市革命》思想探析
陈 芬 周 偎 牛俊伟
(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都市革命》是列斐伏尔于20世纪70年代完成并发表的一部哲学著作。此时资本主义世界动荡不安,城市革命甚嚣尘上,而1968年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更是让作为风暴中心城市巴黎的居民列斐伏尔感触颇深。他认为,随着时代迈过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阶段而发展到都市社会——一个彻底城市化、都市化的社会,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城市革命性的论断变得不那么切合实际了,由此他不满意甚至反对法国共产党照搬苏联的传统思想,试图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阐释。在《都市革命》一书中,列斐伏尔用瑰丽多彩的表述方式阐述了资本主义城市的现状,并试图论证都市革命可能性,由此阐发了自己对城市权利斗争的思考。“虽然全文充斥着人道主义的关怀和乌托邦的幻想,但瑕不掩瑜,对于城市建设如何更好地体现人的城市权利的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1]
一、城市何以具备革命性
城市的革命性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涵盖了以下三个部分的内容:革命的对象是谁、革命的力量依靠谁及在何处开展革命。虽然三部分的内容考察的对象不同,但殊途同归,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城市在其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城市革命性的相关论述,对我们理解城市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帮助。
(一)阶级对立简单化明确革命的对象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2]只有首先明确敌人是谁,革命的对象是谁,革命才能顺利开展。然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笼盖在层层迷雾中,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而不同的阶级中又存在特殊的阶层。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让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无法看清世界的真相,他们不明白导致自己生活悲惨、人生不幸的根源所在;他们被宗教利用欺骗,成为宗教攥取财富的“羊毛”。即使偶有农民起义,那也只是对压迫在身上最表层、最无关紧要的一种抗争,既不治标也不治本。列宁曾就俄国农民面对沙皇的剥削和压迫时指出,“过去他们曾经天真地和盲目地信任慈父沙皇,祈求慈父沙皇‘本人’改善他们的不堪忍受的艰难处境,他们只是谴责欺骗沙皇的官吏胡作非为,使用暴力,横行霸道,抢劫掠夺。”[3]显然,处于农奴制社会中的俄国农民根本就无法辨识出自己受压迫的力量其根源所在,于是出现了魔幻而诡异的现实——农民被以沙皇为首的统治阶级剥削,而农民却“信任”着沙皇,这种“信任”在野蛮的、隔绝的村野生活中得以加深。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和大工业城市的发展,这种“信任”日益侵蚀并最终瓦解,因为资本主义“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4]403资产阶级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撕破了过去掩盖在人们头上、缠绕在人们身上的封建的、宗法的关系,它打碎了一切职业神圣的光环,它使社会逐渐分化,并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富裕的资产阶级与贫困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这种直接的、明了的、没有形形色色羁绊遮掩的对立关系在城市中呈现出来,被剥削者能清晰的知道是谁在压迫自己、剥削自己,而自己反抗和革命的根本目标是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直接的对立的关系会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日益加剧,最终整个社会只剩下两大对立的阶级,由此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一目了然。
(二)无产阶级的觉醒与联合为革命凝聚力量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乡村由于其经济属性占支配地位,统治着作为政治、军事、宗教中心的城市,此时人口更多的是分布在彼此隔绝的村落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此时的居民大多数处于一种“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也即是列宁认为的“不流动、沉睡、麻木、愚昧的状态。”[5]他们愚昧而落后,既无法认清压迫自己的敌人,也无从知道自身所具备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动力。由此,一方面他们难以形成革命的火种,无法对剥削者进行真正的反抗;另一方面,彼此隔绝孤立的状态使他们难以形成一股合力,进而对封建统治产生冲击。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巨大工业城市的建立,它不断消灭人口的分散状态,使城市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同时也让这些居民迎来城市文明的洗礼,进而告别了落后、愚昧的乡村文明,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4]403与此同时,“城市生活的发展,工业的高涨,文化的普及,——这一切也引起闭塞的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他们意识到人的尊严。”[6]进入城市的农民逐渐觉醒,他们意识到自己身而为人应该是有尊严的,不能听信宗教的劝诫任由他人剥削和压迫;他们明确了自己的身份——无产者,同时知道了压迫自身的对象——资本家;他们认清了自身的处境,他们一无所有,所以他们无所畏惧,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这种局面。大工业城市将现代的工人聚集在一起,而大工厂的生产训练他们同心协力、锻炼了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凝聚和强化了这股革命力量。
(三)城市天然具备革命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推翻自己的武器,更为关键的是它还创造出使用武器的人,即背井离乡的、被资本主义大工业城市所吸引的、在工厂中从事生产的现代工人。在封建社会中,他们是农民,是受压迫者;即使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他们身份发生了转变,成为现代工人,但依旧是被压迫的对象,“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4]401大工业城市要求集中,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选择,由此大量的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进入城市,他们试图在城市中寻找通往美好幸福生活的桥梁,然而现实的遭遇让他们不得不从美梦中醒来,他们抛弃幻想拥抱现实,通过与资本家开展斗争甚至进行起义夺回自己应有的权利。而城市则天然成为工人开展斗争的场所:城市的集中性从各个孤立隔绝的乡村中吸引大量的农民流入,他们或者进入工厂成为工人,或者成为城市的“过剩人口”,成为产业后备军,大量的工人和“过剩工人”生活在拥挤的城市之中,这为革命的开展提供了群众基础;农民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礼成为现代工人,以前笼罩在他们头顶的形形色色的迷雾逐渐消散,他们觉醒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这为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城市的工厂中,工人时时刻刻都受资本家剥削,在工厂的集体劳动中他们联合起来与资本家开展斗争,并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俨然成为革命的爆发的导火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认为,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大工业城市俨然是一个易燃的火药桶,这里汇集着革命的武器、革命的力量、革命的思想及引爆火药桶的导火索,天然就是工人进行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空间场所。
二、现代都市的反革命性
列斐伏尔立足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思想进行了发展,在《都市革命》一书中,他创造性的“设定了一个作为乌托邦的‘都市社会’”,“明确把‘都市社会’作为其都市理论的前提假设”[7],以此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度的解剖和深刻的批判。他指出,资产阶级通过一系列的手段遏制和打击城市工人的革命性,维护城市生活表面的安宁,进而保障他们自身的统治地位。
(一)分工导致无产阶级分化,瓦解了革命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资产阶级时代的来临和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过往历史时代随处可见的社会等级和层次划分日益简单化,即阶级对立简单化了。“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4]401同时在每一个阶级中又划分出不同的阶层,但是在资产阶级时代,社会日益分裂,最终形成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然而列斐伏尔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往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料的那般阶级对立简单明了、社会矛盾直接显著方向发展,那种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似乎又卷土重来束缚住人们,在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之上又重新漂浮着一层又一层的迷雾,而这都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所带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对分工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论述,通过分工,人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开始分离,同时也有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划分,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无产阶级中有知识、有技能的从事精神劳动和复杂劳动的人能赚取更多的工资,而只能从事简单物质劳动的人只能获得微博的薪资,于是乎,那部分拥有较高工资的无产者从无产阶级中脱离出来,成为所谓的“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资产阶级通过种种手段分化无产阶级,不仅如此,他们开始隐匿其后,不再直接的面对工人阶级:通过招收职业经理人打理公司、通过资本操纵选举管理国家,这种间接地对工人进行剥削和管制的手段是无形的,二者之间直接的对立关系重新潜入水中,变得难以察觉或不可见。工人被迫进行斗争却无法寻找到真正的敌人,因此即使工人有时能取得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
(二)都市生活消费化,弱化革命的信念
都市生活总是令人流连忘返的,因为都市的集中性,这里汇集了大量人口、堆积了大量物品、举行了庞大庆典,尤其是随着商品社会向消费社会过渡,城市中的普通居民往往沉溺于消费、享乐带来的快感而无法自拔。列斐伏尔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从资本主义城市的“街道”出发,指出“街道”完全脱离了其作为过渡和交通地方的职责,成为了“商店之间的橱窗和过道”,“商品世界在街道上展开”。[8]21人们不是在街道上相遇,而是在随波逐流;处于街道上的人是脆弱的、被异化的,因为“商品成为(挑逗的、诱人的)景观,同时把人们也变成了景观并循环往复。”[8]21通过一种都市空间的殖民化,在街道上布置绚丽多彩的图像和广告等物质外观迷乱人们的精神世界,使人们不自觉地掉入消费主义的陷阱,而信用体系的建立则加剧了消费主义的横行。前者依靠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使消费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后者则通过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使人拥有满足消费欲望的资本,双管齐下,人们在麻木不仁中堕入了无休止的消费狂欢当中。他们沉湎于肉体的欲望得到满足而产生的片刻快感,无暇思考人生的意义、人的价值和尊严;他们被虚幻的景观重重包围,看不清现实也无力看清现实,因为“当景观铺天盖地呈现时,人就失去了自主判断能力,人就忘记了过去,从而沉迷于现在的虚幻。”[9]人被驯化成没有自主意识的动物,只知道满足肉体的需求,沉迷在消费主义糖衣包裹的伪世界中,并且无意识的捍卫着这个世界,革命的理想信念在无止境的消费下已荡然无存。
(三)加强城市的规划管制,遏制革命的爆发
空间不是“静止的、背景性的、没有对活动有积极意义的空间,空间是积极的因素,可以用来作为一个社会中政治霸权的工具。”[10]对都市空间的规划展现了作为统治阶级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内在的蕴含了统治阶级的某种战略目的,换而言之,都市规划是具有严重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随着资本在空间中的不断渗透,空间日益殖民化,变成一个纯粹的权利场所,等级的划分在对空间的占有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列斐伏尔指出,工厂里的劳动分工和相应的社会等级在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建筑中展露无遗,“资方住独栋,高管住高层,工人则挤在公寓里。”[11]在城市规划中,无产阶级被边缘化和分化,他们被大量的驱逐和排挤到城市的边缘地带,居住在郊区;而城市的中心开始中产阶级化,人口减少。这种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是都市生活方式的阶级性造成的,首先表现为资本与房地产勾结,通过房地产投机疯狂的攥取剩余价值,而都市生活方式为这种行为进行掩盖;其二城市的街道、纪念碑式的建筑成为遏制无产阶级革命,宣扬统治阶级作为“征服者和当权者的荣光”的“物体系”象征。列斐伏尔对“街道之弊”和“纪念碑之弊”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它指出,“消费的新资本主义结构在街道中展现了它的力量,它不仅仅是(政治的)权力,或者是实施压迫的权力(公开的或隐蔽的)。”[8]22人们只有在权力的允许范围内才能对空间进行一种“漫画般的”“外观的”取用,如开展舞会或节日,进行街道游行;然而一旦触碰到权力的底线,对空间进行“真正的取用”,开展实际的示威游行,那么街道立马会被封锁和清空,示威活动当即被镇压下去,并要求人们选择沉默和遗忘。至于纪念碑,它们是充满象征意义的。极少数的纪念碑是宫殿和陵墓,它们是纪念死者和美人的;而少许的“伟大的纪念碑是跨功能的(教堂)甚至是跨文化的(陵墓)”[8]24;剩下的绝大多数的纪念碑,表面上是光辉的,但其实质只不过是一种世界观在地面上的投射,是彰显权威和具有镇压性的。
三、城市革命的可能性与城市权利斗争的必要性
城市在一开始便象征着自由、美好、幸福之地,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便是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的,他们不甘忍受封建主无情、残酷的剥削,从封建主统治的乡村地区逃亡到城市,由此完成从农奴到自由民的华丽转变。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城市更是展现出其迷人的一面,乡村中的农民幻想在城市中告别贫困与剥削、远离愚昧和无知,能够沐浴城市文明的洗礼,享受城市生活的美好。然而,涌入城市中的人们发现,城市的美好是虚假的,人们并没有在城市中寻找到“栖居”之处。“资本主义社会现有的城市权利外延狭窄,仅为少数政治和经济精英设定,他们根据自己的诉求不断改造城市,使城市沦为他们创造财富的工具。”[12]人们远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却又陷入到“城市生活的愚昧状态”当中,剥削、压迫依旧存在,贫困问题依旧缠着他们。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大工业城市起源于“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需要”[13],是资本增殖的结果。换而言之,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工业城市并非是人们所认为的美好的“乌托邦”,它是为资本服务的,其诞生之初便带着“原罪”。当无情的现实一次次的冲击人们的心灵、折磨人们的肉体,他们遍体鳞伤、伤痕累累,于是他们害怕了、退缩了,他们终于看破了城市的假象,于是他们想退回到乡村。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乡村的面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们甚至发现乡村的生活与城市的工厂生活相比更加恶劣,由此他们陷入到绝望的境地。
城市革命可能爆发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明确指出城市革命的必然性并致力于推动城市革命的开展,而与此相反,列斐伏尔并未对此表现出积极、肯定的态度,他似乎对革命的发生不抱多大希望,只是小心翼翼地制定了几条战略。然而关于这些战略他并没有做详细的阐述和说明,反而只是一笔带过;他满怀希望能实现人“栖居”的现代都市的到来,但他又无力寻找到通往都市社会的实践路径,只能依赖于“元哲学”进行理论的分析。“列斐伏尔以城市革命与城市权利的思想从总体性上排斥了阶级斗争”[14],在他看来,十月革命式的城市武装革命运动已经成为过去式,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革命后的巴黎被规划重建,有利于无产阶级进行巷战的狭窄路口和街道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横穿整个城市的直线大马路,城市管理者用“直线、笔直排列和几何视角统治的组织方法”[8]126打造城市结构、进行城市规划。于是,当面临类似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城市革命运动时,资产阶级的暴力军事机器可以顺利开进城市进行武力镇压,这往往是最后不得已所采取的手段,资产阶级更擅长、也更倾向于瓦解和磨灭人们的革命热情和欲望。“无论谁创造了空间,他们都创造了充斥于空间中的所造物。”[8]177在资本主义社会,空间被资本所殖民,资产阶级通过创造城市空间对生活于其中的人进行间接而隐晦的干预和规划,人们一旦进入城市,他们于何处生活、工作和休闲便已经被安排的明明白白,但他们不自知;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通过图像、广告等“物体系”来制造外观和象征,宣传符合其利益的价值观,进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教育。在资本主义城市中的人们,他们的肉体(物质世界)被操纵,他们的灵魂(精神世界)被蚕食,他们已经无力进行城市革命了。
由此,列斐伏尔认为,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和目标的城市革命成为过去式,“革命的目标应该是日常生活空间,而不是经济改革或政治革命,”“要进行日常生活革命,不断争取日常生活的自主权。”[15]而这种“自主权”主要表现为弱势群体获取在城市中居住和工作等基本权利,城市权利斗争俨然成为列斐伏尔关注的重点。人们必须对都市规划中技术理性对日常生活的控制说不,人们有理由也有能力为私人空间的解放和自由进行抗争,他号召人们通过“文化革命”的手段进行抗争,一方面是因为文化领域的革命更具有现实性,其他领域的革命都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争取城市权利、在城市规划中体现公平正义不能依赖于统治阶级的施舍和许诺,因为那并不能解决问题,人们只有通过组织更强大、更有力的“文化革命”才能从统治阶级手中获得应有的权利。
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理论虽充斥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和“乌托邦”式的幻想,但是其城市权利斗争思想对于今天中国推进城市化建设具有极大的启发性。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城市问题暴露出来:住房问题、教育问题、社会医疗保障问题等,这些城市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城市生活质量和水平。如何在城市规划中体现城市权利的公平及正义,解决人们迫切面临的居住和生活难题,是中国继续推动城市化建设的首要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