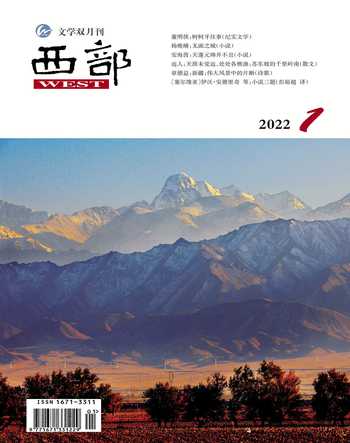祖母的老
徐春林
祖母躺在床上,谁都看不清她。
一天早晨,她突然说起村子里的树,讲起来来往往的人,说村子里只剩下一棵老树了,那棵树的寿命长,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
父亲站在床边:“娘,你在说什么呢?”“你走,我还死不了,赶紧去学校,别耽搁了孩子的课。”父亲一走,祖母又唠叨起来,滔滔不绝的,像是要把村子里的事一下讲完。
祖母说到大伯、二伯的时候,突然停住了。阳光从正门移到了侧门,屋子里慢慢地暗下来。墙边的矮凳上放着一个洋瓷碗,碗里装着半碗热气腾腾的鸡汤。她一口也没喝,以前是舍不得喝,把鸡汤都留给了老人和孩子,有得喝的时候,她一口都喝不下了。不过,她已经不在乎吃什么了,一双眼睛直愣愣地看着门口,像是要把刚才的话又说回来。
她在心里反反复复地说着村子里的事情,点滴她都记得。我们村子里人的生活,就这样如同一场梦,依旧实实在在地留在村子里。
门半掩着,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人来。门像是动了一下,一只老鼠从门底下的缝隙里溜了进来。气势十足地看着祖母,祖母想用脖子和头驱赶,脖子僵硬着,她就使劲,一直使劲,可无论她怎么努力,还是僵在原来的地方。
此刻她除了脑子清醒外,其他部位都等同于植物人。她还想继续说点什么,感觉一张口,声音就被风刮走了。除了她自己,谁都听不见。
以前在农村,是见不着这么大胆的老鼠的。祖母养了一只肥猫,猫守在房屋的某个角落,老鼠只要一露面,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会死在猫那锋锐的尖牙下。没有猫的地方,老鼠肆无忌惮地在屋子里跑。
自从祖母病倒后,照顾祖母的责任就全都落在了母亲身上。父亲是照顾不了祖母,祖母也没指望他,能说话的时候,就隔三岔五地给他打电话。说的也就是鸡毛蒜皮的话,这些话平常不知道重复过多少遍。
叔叔是不管祖母的,他和祖母闹了几十年。祖母说的话,他从来不听。和祖母吵闹的时候,他说他不是祖母的儿子,祖母也不是他的娘。祖母病倒后,他不仅不来照看,还背地里指责祖母偏心。祖母从不计较,说叔叔还是个孩子。祖母说这话时,叔叔已经四十好几了。
实际上,我也没有照顾过祖母一天,除了隔三岔五去看看她,帮她买点药外,好像她的走和停,都由风决定。她在想什么,也只有风知道。
每天母亲会去给祖母喂饭,来回要走一个小时的路。
母亲还有一堆的事情,她已经是一个有着十年糖尿病病史的患者,糖尿病并发症的时候会肚子疼痛,眼睛充血,严重时走路会眩晕,会忽然倒地。
她个人的困难,她从来不提起,依然很有耐心地照顾祖母,一到饭点就朝她那里跑。
说是喂饭,其实是喂米汤,几粒米沉在碗底,只有浑浊的米汤。开始时祖母还责怪母亲汤里米太少,说能吃的时候,就得让她吃饱。擦身子的时候,也是这里不如意,那里不如意,总说母亲擦重了,痛得咬牙切齿。祖母卧床快一年了,屎尿都拉在床上,屁股上到处长着褥疮。
母亲知道,像祖母这种病,不论如何服侍,祖母都不会如意,自己得耐烦。白天除了一日三餐,晚上还得给祖母送点鸡汤。哪怕是只喝一口,母亲还得再跑一回。就这样,无论是雨天,还是雪天,母亲都是准时到。
那天中午,祖母笑着对母亲说,你以后就不要再往我这里跑了,家里的事情不少,你身体也不好,跑了大半年也够了。母亲听了,眼睛就湿了:“娘,你这是哪里的话,是不是我服侍得不好?”祖母无力地摇着手。
这也是祖母最后的话。说完这些话,祖母就不能进食了。有时候会费好大的劲,勉强把嘴张开,有时候又不愿意张开,紧紧地闭着,就连气也不让出来。一年后,祖母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母亲去的次数更多了。
母亲离开后,屋子里也就祖母一个人。她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楼板,不让任何人来陪,也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她现在的样子。
她在心里和母亲做着对话,意思是“不用再喂了,让我早点走吧”。母亲不忍,用毛巾帮她把嘴角的米汤擦干,然后又用温水帮她擦洗身子,擦干净没几分钟满屋子里又是臭味。祖母彻底成了废人,一个轰动一时的民国美女,如今变得像只牲口,这是她自己最不想看到的。她想死,可动不了。她能说话的时候,对母親说过,她想死个痛快,不想半死不活的。没想到,偏偏是这个结果。母亲见她痛苦,不停地安慰她。母亲开口说话,她就流泪,后来母亲干脆就不说了。医生说,祖母这种情况,没那么快死的,少说也能活好几年。母亲不相信,说人不是铁打的,熬不了几个日子。
祖母想住套好点的房子,哪怕干净舒适点也好。可她再怎么想,也只能是想想,就像一个空荡的见不着头的理想,那个理想梦幻一般。
祖母这间房,窗户的玻璃已经很久没擦了,玻璃上有厚厚的油渍,黑黑的,挡住了窗外的光。母亲把窗户打开,让风吹进来。等里面的气味稍微淡点的时候,又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前些日子,母亲老远就听见祖母喊痛。祖母听见母亲的脚步声近了,嘴巴立马就停了下来。母亲推开门时,她仰着脖子,用微笑的表情看着母亲,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饿了吧?”祖母摇了摇头。“半天都没有喝一口水了。”母亲端起碗,用勺子在碗里舀了半勺汤,用嘴吹了吹,朝着干裂的嘴巴伸去。
刚刚碰到嘴唇,祖母就把眼神收了起来。她实在不愿意张开嘴,母亲用勺子朝嘴唇上压,祖母这才不情愿地张开嘴。还没喂两口,祖母就用舌头顶着勺子。“吃点吧!再来一口。”母亲像哄小孩一样哄着祖母。那时,祖母除了头部还有意识外,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没知觉了。实际上连头部也不能动了,但嘴还能哆嗦,舌头还在朝外顶。大概的意思,母亲也明白,“再不要朝我这跑了”。母亲放下碗,又帮她擦了擦嘴巴。纸巾在嘴角上擦来擦去,怎么也擦不干净。祖母可是个爱干净的人,她的性格有点倔,她在城里过的日子,总是挑三拣四的,租个房子总得找很多个地方,黑的不要,楼层高的不要,价钱贵的不要,离菜市场远的不要,房东不好说话的不要。找来找去总是找不着。母亲帮她找过几个地方,不要说光线好的,就连黑的也不愿意租给她。说她腿脚不便,撑着棍子走路时像划船一样,要是不小心摔倒了,死在谁家的屋子里,就连房子都租不出去了。祖母说,我是吃斋的。祖母说的吃斋是每逢初一、十五吃没有动物油的饭菜。实际上不算是完全吃斋。租房子的人可不理会这些,他们只想着把房子租个好价钱。
现在母亲真的后悔了,后悔没有帮她租个好点的房子。祖母刚到县城时,腿脚还算利索,还能到处走路。最早租住的地方在城南县三中后面,那是一栋茶科所的公家用房。离学校也就一步之遥。那时,城南还没有开发。那块地上只有茶科所那栋宿舍,附近还有一所老牌中学——修水县第三中学。她租住的那栋楼很破旧,比村里的房子稍微好点,村里的房子挂在悬崖峭壁上,泥巴筑的,杉皮盖的,下雨的时候满屋子漏水。这个房子是瓦盖的,虽然也有漏雨的地方,可比起村子里的房子要好得多。关键是这是砖瓦的房子,建的地块平整,不像村子里的房子建在山脚下,下大雨的时候还得爬起来观察。山体滑下来埋掉屋子是常有的事情。村子里有一户人家,半夜后山崩塌,他听见声响爬起来,刚走到地场,山体倾泻下来,将房子推倒,老母亲、妻子和两个半大的孩子全部被活埋。有了这场灾难,村民在选地基的时候,尽量选个宽敞的地方,可还是难以避免灾难。一场大雨过后,到处是山体崩塌。祖母觉得那屋子好、住得安心,关键的问题不是别的,还是离三中近,那是祖母在县城住得最称心如意的房子。我叔叔的女儿在三中上高中,叔叔很不争气,成天游手好闲,还经常和婶婶争吵打架。婶婶决定离开叔叔时,对三个孩子十分不舍,便来找母亲,意思是叔叔如愿意与她和好,她就算吃再多的苦都不走了。那时,叔叔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有脾气就往婶婶身上撒,时不时地拳打脚踢。一个女人,怎经得起他这般折磨。
一天中午,祖母把叔叔叫到家里。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祖母劝他,他不仅不听劝,像个孩子般把饭桌打翻了。一罐鸡汤洒得满地都是,祖母伤心了,那可是她杀了家里唯一的老母鸡炖的汤。
婶婶铁了心走了。走后半年,邻村来了个男人,找到我父亲说,他想和婶婶在一起,想和叔叔谈谈。“谈什么呢?”父亲问。
父亲找过叔叔,让他去把婶婶找回来,可是他晃着脑袋说,这个女人我不要了。他的性格谁都知道,决定了的事情,驴都拉不回来。其实,那时候叔叔还是个孩子,他是被祖母惯成这样的。婶婶不久便和那个男人走到了一起。
我听说当年叔叔不愿意和婶婶过还有一个原因,婶婶去广州打过工,叔叔觉察到婶婶和一个老男人有往来。这种往来,激发了叔叔的愤怒,几乎成了条件反射,使他失去理智地在婶婶身上不停地施暴。
也就是这个原因,叔叔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堂妹,后来与祖母一起生活。
几年后,我堂妹考到县三中,祖母决定到城里过生活。开始我父亲是反对的,她在农村生活了几十年,一辈子没去过县城,县城的生活可不是一个乡下人适应得了的。她要来谁拦得住?当时母亲有点受气。你这把岁数往城里跑,县城的车到处乱窜,出了事谁来过问?祖母可能真没想那么多,她只想着眼前这几年,说主要是让孩子有个照应。说到底就是烧菜、煮饭、洗衣服。她最早的计划也就是三年,等堂妹高中毕业后,她就搬回村里。可是后来,时局完全变了。我毕业后分到了县城的单位,我母亲也三天两头地往县城跑,送些米油盐之类的东西来。那时我的工资低,连房租和正常的生活都难以支撑。每次来,她总会去祖母那看看。母亲说,她活在城里气色比在村里还好。祖母喜欢过城里的生活,她喜欢去公园散步,喜欢去老年运动场看打门球,有时候遇上一场老年健身操,她也能站半个小时。那时她的类风湿关节炎已经相当严重,几根脚趾交叉在了一起。
祖母偶尔回趟村里,老远就在山背喊葵叔公、春英叔婆、青奇伯。其实这几个人年龄都和祖母不相上下,有大两岁的,也有小两岁的,祖母还是毕恭毕敬地按照辈分来,从不直呼其名。大伙见她回来了,表现得格外热情,像是好多年没见一样,其实最多也就隔了三四个月。大家搬来凳子,自觉地围坐着,她便开始滔滔不绝地对大家说城里的所见所闻。
其实一些东西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只是见着就描述,用途还不见得是她描述的那样。村里的人去过城里的少,她说什么大家都爱听,听着也开心,她就讲得津津有味的。她总觉得活在城里是件脸上有光的事情。祖母除了讲那些所见所闻,还会讲在城里怎么活的问题,不去城里生活是想不透的,城里人有十块钱当二十块钱的活法,当然也有二十当十块的活法。她讲她的房子,租金是六十块钱,面积是三十平方米,公共的卫生间,厨房就摆在门口,晚上把一些坛坛罐罐搬进来,早晨起床又搬出去。这点和村里不同,在村里东西摆在地场上都没人要,在城里放在外面的东西眨下眼睛就不见了。“城里的治安就那么差吗?”有村民瞪大眼睛问。“这不是治安的问题,一些人进城找不着工作,锅桶什么的都用得着,能省点钱。”“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这可是不道德的啊。”“这点就不如咱们村里的人,他们也是被生活所迫的,当然干这事的人是少数。”“在城里活不下去就回村里啊,总不能靠偷鸡摸狗为生吧!”
村里人最熟悉祖母的性子,当年日本人打进中国的时候,她的两个儿子也就是我的两个伯伯都参加了革命。我祖父是上门女婿,祖辈七代无子,要么是招郎上门,要么是带子传宗接代。到我祖母这一代,连生了两个男孩,而且长得眉清目秀。村里人都说,这下麦克有后了。麦克是我的祖先,他是從湖北南林桥迁到江西来的。可是,让村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祖父把两个孩子都送上了战场。一个在秋收起义时,被活捉砍了头颅;一个死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我大伯死后,二伯才去当兵的。这让村里人很是费解,死了一个,剩下的这个可是独苗了。大伯去当兵的时候,祖母算得上是深明大义,村里人敲锣打鼓一直送到镇上。二伯去的时候,村里人都拦在路口,可祖母铁了心肠,说孩子想通了,他要去就让他去吧!好男儿就该血洒疆场。这次是二伯的主意,祖母拦不住。二伯死在战场上好多年,祖母都不得音讯。太想念儿子的时候,就从夏家过继了我父亲到门下。她以为自己不会再生了,父亲十来岁的时候,叔叔便来到了人间。也许是祖母觉得亏欠大伯、二伯太多,对叔叔格外溺爱。这种爱,让叔叔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祖母在城里搬了几个地方,每次都神不知鬼不觉的。她搬家的时候,我们一点信息都得不到。搬了好些日子,她才会告诉我们换了个地方。搬房子实际上是很麻烦的事,她从不表露出半点的烦躁。
祖母在北门新桥旅社住了八年。堂妹高中毕业后就搬到了新桥旅社来住,这是我们村隔壁的一个被开除的校长盘下来的。祖父在村里教书的时候,校长和我家有过往来。祖母说,校长是个好人。我也相信校长是个好人,他是多生了一个小孩被副校长告下来的。不仅校长职位没了,连工作也没了。校长也知道不能超生,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避孕措施。那时农村违反计划生育是常有的事,怀上了就不想去打胎,毕竟是个生命。校长的孩子生下来后就送人了,他老婆躲在娘家待了大半年,按理说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可还是被传了出来。
校长找不着事干,就来县城将新桥旅社盘了下来,租了几间给在城里生活的同乡人。祖母在那里租住了八年,住在二楼,一个三十平方米的屋子,日子过得还算平稳,房租也一直没有涨。
校长后来患了脑出血,把旅社给退了。祖母的腿脚越来越不好使,再也爬不上二楼了,就重新租到靠近我住所的胡同楼下。房子里的灰尘很多,她又特别爱干净,买了些花油布垫着。她说靠着我住安心。可住在楼上的小孩每天晚上吵到半夜,她实在熬不住,住了半年又重新换了地方。这次搬得比较远,从城南搬到了城北。她很不高兴,说地方太破了,老鼠跑进跑出的。在村子里,见着老鼠在地上跑是常有的事。可那阵子她像是变了个人,一会儿说见着了老鼠,一会儿说窗台的风太大,一会儿说屋子里有臭味。总之事情特别多,经常给我打电话说这说那的,忽然又温柔地说,好久没有见着我了,让我有空去她那里坐坐。我至今记得那个声音,声音不停地在我的耳朵里跑来跑去。
那天傍晚,母亲给我打来电话,说祖母中风了,手不听使唤了。我去的时候,她坐在床沿上,一只手像是在荡秋千,不停地晃来晃去。我叫她把手停下来,她说手已经不听使唤了。我感觉她是在发泄情绪,手不停地晃着,是在向我们抗议,说她不想在这里住了。父亲的意思是就住在这里,进出方便,就是房子破了点,但无论如何都比村子里的好。她就像是个任性的孩子,无论如何都不愿意住。那时,我有点不太理解祖母。
其实,祖母是个顺风的人,一辈子不顺风的事不做。她刚嫁给祖父的时候,就住在屋头的牛棚里,也没有说过半句怨言。现在她整个人像是变了,变得让人不认识了。当然,我知道祖母嫌弃的不是房子,而是缺乏爱,住得远就和我们隔着距离。我也曾对她说,让她搬到我那里,住在一起,她说:“你的房子太高了,得背上楼去,还得背下来,整天见不着阳光,实在受不了。”她还想着每天到户外晒晒太阳,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
现在身体出现了问题,她更想和我们住得近点,她害怕她哪天走了,我们都不知道。我想这才是祖母不愿意住在这儿的原因,可是一个偌大的县城,的确找不着一个可以让祖母安心的地方。
父亲站在祖母的床前,还在做她的思想工作,可她把头扭向一边,说这屋子里半夜有怪异的声音,说墙上还写着字这屋里不能住人的。“写在哪儿呢?”父亲问。祖母指着墙壁说:“在那儿,你没有看见吗?”我觉得祖母可能精神出了问题,送她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情况还好,像是有中风的迹象。医生说,她那手不是不听使唤,如果她自己不愿意停下来,是停不下来的。
祖母似乎不想停下来,只要见着我们,手就一直疯狂地晃着,不见筋疲力尽的时候。她的脸上是那种虚弱的疲惫。
祖母终究还是中风了,这回倒下后就没能站起来,躺在床上,就连翻身都不可能。她还想着给我打电话,想让我帮她找个好点的房子。她连拿电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渐渐地,她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我去看她的时候,她的嘴巴歪着,嘴已经合不拢了,喝什么都会流出来。可她的舌头没有停,还在和我说着什么。我努力地听着,始终不明白她要表达的意思。她的手不停地抓着我,我感觉她真的有话要对我说,这回绝对不是说租房的事情。祖母嘴里不停地哆嗦着,哆嗦着。
我怎么也不敢相信,祖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记得我小的时候,祖母是特别爱打扮的,在我祖父面前她就是个淑女,几十岁的人了,可还是有模有样的。祖母比祖父小了十五岁,她总是以她优越的年龄差在祖父面前表现着她的体面。祖父是村子里唯一的书生。在祖母心中,祖父不仅是书生,还是她英俊、挺拔的男人。她在夸祖父的时候,声音特别大,生怕村里的人听不见。她对祖父也是苛刻的,说到了晚年祖父不能比她先走,要是先走了,她就会变成丑八怪去找他。我发现她特别依恋祖父,超出恋人本身的情感。一开始她还能喊出祖父的名字,每喊一声像是割着我们的心。我想让她静下来,可是不可能。
祖母的声音是慢慢消失的。一点一点,像是迷失在县城里。
说起来,我是有愧于祖母的。小的时候,有段时间祖父去山外教书,祖母一个人留在家里,每天晚上,她喊我去做伴。其实,我不是最听话的。我是图她晚上做的面条消夜,还有面条里的两块肥肉。另外,我晚上怕黑的,祖母整夜点着灯,生怕我醒来看不见光,半夜总是为我爬起来挑拨灯芯。
我上初二的时候,成绩在班上倒数几名。加之家庭特别的困难,父亲在几个孩子中做了考量,认为我是最没有希望的,决定让我回家放牛。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哭着鼻子找到祖母,把父亲的决定告诉了她。祖母从容地和我说着话,然后从箱底的油布包里掏出了八十块钱来,说这是她一生的全部积蓄,先借给我上学,等我毕业后再还给她。实际上,也就是祖母的这八十块钱,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一生。那时我觉得祖母是一个无比高大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祖母上过私塾,读過《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她懂得读书的意义。祖母是村子里唯一读过书的女人。父亲说,有一年县委书记去村里调研,祖母居然和他讲起了古人的道理。县委书记竖起拇指,夸赞祖母非常了不起。我听了也非常惊诧,不知道祖母是怎样上学的。追究缘由,还是曾祖父没有生男孩,把祖母带在家里,加之祖母好强所以才得以上学。祖母嫁给祖父不说是门当户对,至少可以说是郎才女貌。祖父是国立师范学校毕业的,在村子里也只有祖母配得上。
我祖父退休的时候,根据政策可以安排一个人顶替。父亲那时已经是一名木匠,会打木桶,一担木桶可以换回好几斤盐。叔叔刚刚初中毕业,祖父的意思是让叔叔顶替。祖母思来想去,决定把父亲喊回来商量。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祖父祖母为了他已经吃了不少的苦了,他本来就是个过继的孩子,应该把这个机会让给叔叔。就在祖父打算让叔叔去顶替时,祖母反悔了,说无论如何也要让“牛牙”去。“牛牙”是我父亲的小名。祖母怎么也不会知道,叔叔就躲在门后,此刻已经是一个泪人。亲生的还不如带来的,叔叔的心里有了一道不可愈合的伤疤。
说实话,我觉得自己是最对不起祖母的人。那天下午四点,我在办公室写稿,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祖母走了。我眼前一黑,仿佛整个世界塌了下来。我以为祖母没有这么快走的,她就偏偏走得这么匆忙,临行前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在她的床头桌子上,陪伴她的是母亲送的半碗鸡汤。母亲说,那天她有点事就离开了一会儿,说过会儿就会回来的。祖母看着她,眼里还流露出坚强的意志。母亲去之前,我还给她打过电话,让她对祖母说,我下班后就去看她。母亲说,她把我要去看她的消息也告诉了祖母。其实,只要再过一个小时我就下班了,就能和她见最后一面了。我见着她的时候,她已经安详地睡着了。她那顽固的性格、硬朗的脾气,就像是蒸发了一样,整个人变得面无表情。
我站在床前,还想听她嘀咕,可是再也不能了。任凭我怎么叫她,她都不再醒来。我跪在祖母面前,知道今生今世再无祖母了。
“不能闹动静,要是房东知道祖母在屋子里去世,必定会找我们麻烦,也会让她走得不安。”母亲一边流着眼泪一边交代我。我明白县城房东的规矩,租房前就已约法三章,如果住有老人,必须在老人咽气前就搬出屋子,否则是要赔钱的,赔钱是小,关键是还会闹事。祖母去世的消息,除了我和母亲,并没有告知其他人。
母亲说,得等到黄昏才能送祖母回村里。祖母先前留有遗书,要求走后将她安葬在青龙嘴。那是埋葬着我先人和大伯、二伯的地方。祖母还留了一张存折,里面有六万块钱,是留给叔叔交房款的。密码是叔叔的生日。祖母在最困难的时候,省吃俭用把这些钱留下来,用来弥补对叔叔的亏欠。
我点燃了一支蜡烛,放在祖母的床头柜上。我记得,她就是这样点着油灯照着我长大的。白色的光在她脸上晃来晃去,她就像个熟睡的孩子,一声不吭地睡在那里。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祖母的额头,额头冰冷得有些刺骨。
黄昏后,我抱起祖母,把她放在我的车后座,然后折了一个白色的灯笼罩住车里面的灯,把她送回了村子。一路上,我仿佛聽见她絮絮叨叨地说着往事,比如不要过于劳累,中午睡觉时一定不能晾着肚子……她的话一遍遍在我的耳畔重复着,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祖母的坚强其实也是脆弱的。她每张一次嘴,其实就在向生命发出挑战。她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做好了接受命运伤害的准备。
祖母真的走了。我知道祖母时刻思念着儿子,从她身上掉下的肉,她能不心疼吗?遵照遗嘱,祖母埋葬在大伯、二伯的坟墓旁。
在我们面前祖母始终没有提起过大伯、二伯。“娘,如果你想我的时候,你就抬头看看星星,星星离我最近。”这是二伯离开村子时对祖母说的话。
祖母走后,叔叔像是变了个人。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夜间就长大了。他跪在祖母的坟前,不停地磕着头,说着一些远远近近的话。
祖母走后的许多年,我一直没有动笔写有关她的文字。我一直在辨识祖母,我想客观地观察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祖母的死从表面上看与她的顽劣有关,实际上却不是。在她的骨子里,顽劣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想,即便没有那个租房的过程,可能也会有别的原因,她还是会在那个时间段离开我们。她似乎是在选择一种离开的方式,这种方式彻底毁灭了她在我们心中的形象,这种形象也会形成我们对她的偏见。我跟着祖母长大,怎能不知道她的良苦用心。
祖母老去后,我独自回过一趟湖北通山老家,在族谱上找到了我的名字。那不是我现在的名字。这个名字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祖父和祖母为我取的——鼎春。备注我是子明之子,子明是我父亲的名字。族长笑着说:“你是一人鼎两门的。”果不其然,后来我在夏氏族谱上,也就是我祖父的族谱上也找到了鼎春。我在祖母的族谱上姓徐,祖父的族谱上姓夏,名字都是鼎春。我查看了族谱记载的日期,是祖母去世前的两年,那时她还可以行走。族长说,这是祖父祖母在世时统一的意见。“那次回来,她住了三天,看着我们把庄稼收完才走。”族长说。
我记得,祖母每次回湖北通山老家,总会被随便的一件小事挽留一天。能留人的事多着呢。她离开的时候,老是回头望,总是恋恋不舍。老家在她的心里是一条长长的路,没有尽头。
这回,祖母真的走了。
栏目责编:李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