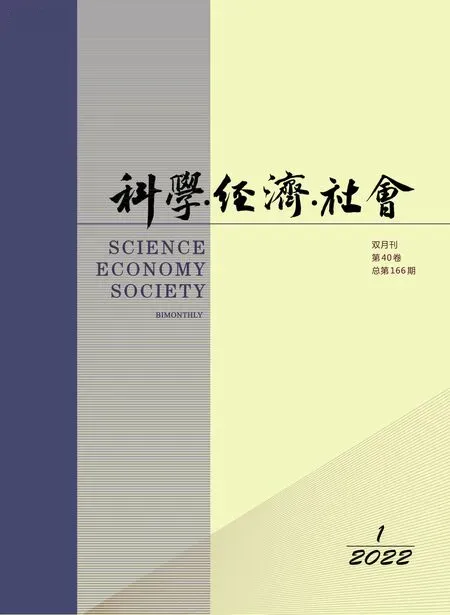“元宇宙热的冷思考”笔谈(上)
贾 韬 王国成 郭春宁
概念先行后的一地鸡毛:元宇宙会是例外?
贾 韬
收稿日期:2022-02-04
作者简介:贾韬,西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复杂系统、复杂网络研究。E-maill:tjia@swu.edu.cn
虚拟货币是不是一定要用区块链?虚拟货币在元宇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去建立一种生态,让货币生成,然后又消耗,来保证一个良好的循环,它并不一定需要区块链。
一、愿景需要技术细节支撑
2021年9月开学的时候,西南大学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全校的师生都要统一做一次集体核酸。做核酸计划是在操场,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空间,这时候就面对一个问题,做核酸的终端设备必须联网,大家做过核酸都知道,要么扫健康码,要么扫身份证,那怎么能够联网?传统的方式肯定是拉线,从某个接口拉根光纤,再转成网线,然后连到终端。那个时候我们就想,都21世纪了,是不是可以搞点先进的东西,5G不是挺好的吗?用5G联网,把设备全部连起来,这不就是5G可以落地一个应用吗?然后测试了一下,发现确实能用5G把所有的终端设备全部连起来,速度还不错。第二天,当老师学生们开始来测核酸的时候,我们却发现,网完全断了。为什么?因为当时来了几千个学生和老师,把我们基站一下给挤爆了。
我讲这个事情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在过去很多年里面,我们有很多这种愿景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们的技术细节和业务逻辑还根本不能支撑我们去达到这样的愿景。我们想用5G这种非常先进的技术,去把操场的终端设备连接起来,但实际上并发量太大时根本就连不起来,在应对这样一个技术场景的时候,我们是有细节上的缺失的。今天讨论元宇宙,我们的背景是什么?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概念是领先于或者说远远领先于我们实际的基础的。比如说,我们讲大数据讲了很多年了,那么数据孤岛能打通吗?政府工作报告年年都讲要打通数据孤岛,打了这么多年还是打不通,通过这次疫情防控我们就能很明显地看到,想要攻克数据孤岛,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最后大数据搞了半天是什么?数字大屏。我们做的几乎所有的大数据项目,最后都落脚到了数字大屏上面。还有物联网,我们经常万物互联,打造智慧城市,那物联网连到什么程度?其实也很少,最后落脚点还是数字大屏。还有数字孪生,这个概念提出来是非常厉害的,它意味着数字世界的改变可以同步映射到真实世界,真实世界的改变可以同步映射到数字世界。比如说我们想看一下如果把重庆市的一座桥切断,交通会发生什么状况,那么就不用真的去切断这座桥,在数字世界切断试一试就可以。愿景非常好,最后怎么样?几乎没有落地的,落地的还是数字大屏。还有高校里面经常讲的智慧校园、智慧教室,这些概念提了很多,前段时间有个老师专门来问我,现在这个智慧校园到底有多智慧,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讲确实谈不上智慧,现在我们还只是在做信息化,或者说多媒体教室。
二、技术突破何在?
个人认为,基于现有的技术水平,元宇宙就是一个概念炒作。我们现在有什么技术突破?虚拟现实技术已经炒了六七年,有很多落地的项目吗?很少,基本上就是在教育和培训、游戏行业有一部分,其他的都很少,几乎达不到以前我们所想象的程度。图像处理技术,低延迟能够打破吗?没有听说有新的技术突破。脑机接口,也没有听说过新的技术突破。所以说,当前没有任何技术突破可以让我们达到元宇宙。那么新的需求有没有?比如疫情期间,大家想要有更多的娱乐之类?好像在国内没有这样的需求,国内没有停工停产,大家日常的社交和以前是一样的,我看不出有任何新的需求会出来。新的主体功能有没有呢?比如我们讲元宇宙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会有新的主体功能出现吗?如果大家打游戏的话就知道了,不用往前几十年讲,就近几年,“我的世界”这样一些游戏理论上也能够完全实现元宇宙所勾勒出的一些功能。
没有技术突破,没有新的需求,主体功能方面也没有任何新的东西,所以说元宇宙就更像是一个概念炒作,而且它也符合概念炒作的一个基本特点:元宇宙就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比如说原来做虚拟现实的,现在我可以说我是做元宇宙的;原来做游戏的,现在我也可以说是做元宇宙的;原来是做静态的三维建模的,我也可以说是做元宇宙的,至于什么数字孪生、传感器都可以说是元宇宙。
三、关键的瓶颈
回到提纲里面讲的几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落脚的产业?其实元宇宙和虚拟现实、数字孪生这两个产业是最接近的,比如说Facebook,它提出元宇宙这个概念的时候,更大一部分原因是想卖它的虚拟现实眼镜。但实际上现在是没有什么炒作空间的。为什么?因为这两个行业在过去的六七年一直在发展,但是遇到了瓶颈,且瓶颈很大,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特别能够落地的、特别让人眼前一亮的、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的东西。接下来更和元宇宙相接近的应该是游戏产业,比如说Roblox,这个游戏公司在招股书里面直接提到了元宇宙。游戏产业实际上对应的是什么?是宅经济,宅男宅女经济,我天天在家里面,不用出去,就可以满足我的社交,就可以获得很多的快乐。但是,实际上这是要降低实体需求的。当然元宇宙的总体影响是有限的,我们面临的很多现状,并不是提出元宇宙以后才有的,而是一直都存在的。那么另外一个影响就是资本炒作,刚才刘老师也讲了,资本市场已经开始变冷,前天我看了一下,Roblox的股价从最高的134美元,跌到63美元,已经腰斩了,这说明资本炒作已经开始进入了所谓的割韭菜的环节当中。
四、区块链不必然是关键
这次的元宇宙热与以往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次很大的一个不同在于区块链,或者说币圈的人,他们开始非常热情地拥抱元宇宙了。他们提出一个观点,元宇宙需要区块链,互动艺术的NFT,也是区块链的一个应用。元宇宙离不开区块链,有两个主题,一个是虚拟货币,一个是虚拟资产。我们在一个新的世界里面,肯定要有交易,有交易就有货币,离开区块链为什么不行?因为会有货币的滥发,通货膨胀,会有缺乏监管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虚拟资产的管理,比如说打游戏的时候获得了一个装备,但是这个装备就有可能被别人复制,也可能被盗,它说白了就是服务器上的一个代码,我难以确权;它也是中心化存储,哪一天,这个原来的厂家没有了,我的这个资产也就没有了,而区块链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讲起来,会让人觉得,好像真的是需要区块链的,但我个人认为这个必要性还值得思考。首先第一点,虚拟货币是不是一定要用区块链?虚拟货币在元宇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去建立一种生态,让货币生成,然后又消耗,来保证一个良好的循环,它并不一定需要区块链。现在有一些所谓的元宇宙说是基于加密货币,但从本质来讲,只是说我在这个世界里面使用了加密货币,这和我在这个世界没有使用加密货币而使用人民币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并且,区块链的奖励机制如何与游戏相结合也很难,也就是说区块链和元宇宙是不是一个共生关系?我觉得现在是没有答案的。第二点是虚拟资产的问题,要知道区块链解决的仅仅是记账的问题,举个例子,现在有很多虚拟资产拍卖,比如我在某一个元宇宙里面去买房子,买地产,本质来讲,我买的只是记的账。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好比我在游戏里面有一个装备,比如一把剑,那记账就是有一把剑,有某些属性,但是这些属性如何发挥游戏中的使用价值呢,区块链管不了,只能记个账。这就反映出在元宇宙里面,区块链不能解决虚拟资产体现出自身使用价值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更核心的问题,本质上来讲,元宇宙一定是中心化的,我们很难去想象一个非中心化的元宇宙,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建元宇宙的话,我们要对它建模,要给出各种规则,那么这些规则都需要中心化才能实现。
五、技术的渐进才是常态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我们会经常去喜欢一些新的概念,每隔一年都会有新概念跳出来,但是事实上,科技渐进式的进步才是常态。可以想象一下,我是2000年的时候读的大学,那个时候,“纳米材料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生物技术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这种观点比起我们现在讨论元宇宙有过之而无不及,过了20年,有多大改变呢?渐进式的进步才是常态,颠覆性的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最后,我想用中纪委网站的一句话“我们不要低估五到十年的机会,也不要高估一到两年的演进变化”来结尾。我认为“不要低估五到十年的机会”可能都说得有点太乐观,在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都不一定能看到元宇宙真正落地。大家可以去搜索引擎上搜一下2012年也就是十年之前,我们当时认为十年之后的科技进展是什么,会大跌眼镜,在十年之前,我们所做的预测几乎没有能够实现的。
元宇宙是否是现在技术会聚的必然?我想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一定是Facebook要卖眼镜的时候才提出这个概念,然后一下子拨弄了大家的兴奋点?如果真的是技术会聚以后自然而然形成的,那么就会以一种非常多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也就是说在提出概念之前,可能就有某些东西已经在做了。举个例子,腾讯有个游戏叫“一起来捉妖”,是一个增强现实的游戏,再比如NFT的拍卖等都搞了很久,我个人感觉是没有达到会聚起来要爆发的程度。可以看到,大家好像蠢蠢欲动都想要去找一个燃点,其实这反映出来的是元宇宙本身动能的不足。我们过一年再来看就发现,我们今天讨论的东西、很多的热情可能就已经冷却下来了,没有什么太多可以真正实现或者说留下来的东西,这是我一个技术宅男的悲观的想法。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我们今天讨论元宇宙就跟讨论明天外星人要入侵地球我们该怎么去防御一样。
元宇宙与虚实交融的生产方式
王国成
作者简介:王国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计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博弈论及应用、行为/实验经济学、计算社会科学与智能决策、经济管理复杂性的跨学科交叉研究。E-mail:wanggc@aliyun.com
元宇宙最根本的问题是它能不能创造出来一个虚实融合的生产方式、认知方式、行为方式,使人类社会真正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不断体验和加深理解中的元宇宙
我们要在对元宇宙的不断体验和逐步加深中去理解元宇宙,要用元宇宙的观念来谈元宇宙,要用动态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元宇宙,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以及和自然界与科技进步的交互中来认知元宇宙,也就是说要与元宇宙的概念和具体发展同频共进。
(一)基本表现特征与延伸意义
元宇宙,一个玄妙神奇、色彩浓烈的热词,充满极度不确定性(高可塑性)的另类(虚实交融的)世界,有着极大诱惑和强大综合功能的事物形态和组织模态;已有的研究和文章从资本聚集、产业变革、技术整合、媒体传播等多个角度,出自不同目的来关注、描述、界定和构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从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阶段及哲学层面上看,其算不上新兴事物,可以说只是一种奇特(蕴含内在必然的)现象。表象上看好像是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和AI等先进技术的汇集、升级和集大成者,实质上则是在人性交汇点(根源是人及社会全面发展的需求)上的升华。如果我们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元宇宙是人类超越自我的一个新阶段,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真正元宇宙的本质和我们理解的它的含义该如何描述?资本聚集或技术整合等实际上都只是一个侧面,所以我认为它实际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红楼梦》里关于太虚幻境的论述是比较贴切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元宇宙实际上是个超然世界(Super-world),它的基本的特征就是高度智能,它不宜简单地概括为:新一代互联网、虚拟现实类VR+技术的高端产物、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升级版等,也不是什么区块链或者某些技术的单向进步,它实际上是人类认知变革和行为能力的跃升,所以不管叫它第二宇宙也好,人工社会也罢,它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智能的构体与现实世界交融共生的全新形态的世界(或者说是社会、宇宙),它是本体、实体、真实场景的高保真映射与数字虚拟体的融合,这也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元宇宙最核心的东西。
我们就从它涉及的物质与精神、同质与异质等基元问题来看,特别是经济学由理想化的理性个体、市场均衡收敛的过程,到现在复杂经济学的异象涌现等来谈。我这个年龄段对电子游戏的印象和了解不深,但我觉得像神笔马良、宝葫芦,还有刚才提到的《红楼梦》之中的太虚幻境以及《雪崩》里的科幻,实际上,元宇宙就是人类一贯的、从人类之初就有的神奇的想象和美好的愿望,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技术支撑下的一种实现形式。
(二)发展预期
从人类发展史来看,社会文明进步背后的原动力在于以想象力为驱动的人类的认知(行为)革命,当今人的异质性、社会复杂性加剧,新科技革命发力、科幻对人类深藏欲望的袒露和启迪,多维度力量叠加作用;而元宇宙在未来能否真正兴起和良好发展,起关键、决定性作用的是其能否为人类创造出新的生产(生活和认知)方式。渴望中的不“劳”而获,意念控制/造物,“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等拥有超然的本领和人与自然(人际)美好的关系并非不切实际的幻想;相应的还会有一系列概念更新和提法,数字化永生/死亡、生命永续、精神永存;梦幻世界、时空跨越、畅游太空,各色生成人等不同的未来人与人类共存,本体与摹体、当今与未来、物质与精神、意想与现实、抽象与具象、同质与异质、游戏与实验等虚与实的无缝对接、交互融合、激(发)创(新)共享,会呈现另一番现在还完全无法想象的图景。元宇宙目前还只能算是一种初级概念和社会现象,是一种探索尝试的信号和预兆,尚未形成特定的事物、学科和技术,对元宇宙的发展和能产生的作用,“短期不高估,长期不低估”,在未来可能的发展中要冷静理智地思考、谨慎乐观地行动,处理好迫切认知、基础探索、理论建设和应用研究的关系,以人为中心和重心,尽可能在人本轨道上映射摆放好“人—宇”关系及定位,让全人类中每一个体和社会都得以全面自在地发展。
二、元宇宙与物质财富的生产
元宇宙无疑是在改变和重塑人类及其与外界交互的行为方式与行动空间,在这样的超然世界中,会使我们更富有吗,会创新人类的生产方式吗?这就是虚实交融的生产方式。
真正决定元宇宙的未来发展不能仅靠技术进步,而是人类怎么样认可它、接受它并普遍应用。人类在技术发展中是相互激发的,它能够更好地激发人类的智创性,同时人类也能够更好地利用元宇宙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创造更多科幻中描绘的和虚拟的东西,包括艺术、文玩方面的产品。元宇宙最根本的问题是它能不能创造出来一个虚实融合的生产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使人类社会真正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可能会有的人说,经济学是比较俗套的,关心的只是柴米油盐,或者是GDP、CPI之类的话题,但是我们从生产方式来讲,这个元宇宙能让我们更富有吗?实际上在计算机辅助制造,包括ERP,甚至当今的企业数字化转型,都可以运用元宇宙技术来超越。但是真正的用元宇宙让我们的资源配置效率更高一些,让我们的成本更低一些(2019年网易在全国推广AR简易的头显眼镜,才合人民币300多元,可以替代美国的3 000多美元的同类产品),让我们的分配更合理,然后更能够去实现人类的美好生活需要。能否创造出并能迅速广泛适应的新的虚实交融的生产方式(资源配置、人际交互)和思维认知,互为支撑和实现条件,相互激发、相得益彰,成为元宇宙今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衡量标准。不仅是单项技术进步的应用延伸器官体能、更新资源形态和配置方式,而且是要跳出传统模式和框架,在智慧显化方面突破过去的不敢想不可能,在智能体、数字人、虚拟摹体,数据数字、灵感创意等非物质的精神层面因素的权重逐步增大,更有利于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经济整体的协调治理及预期调控。元宇宙创造了人类和虚拟世界交互的方式,完全可以使智慧场景和“幻想的”技术生产方案实现。所以它更多的应该是智慧和创造,或者说是预设引领和创设未来,所谓最好的预测未来就是设计未来。
另外,虚实交融的生产方式及相关问题,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因为它更有利于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使人们谋取物质财富的方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从原来的解放肢体,然后放大感官,最后到激发智慧创造,人类从未停止,所以元宇宙决定性的评价标准就是看它能不能实质性地创新生产方式。一方面是多渠道多方式实时获取真实场景中的活体信息,转换输入虚拟世界;另一方面是在虚拟世界中将各种可能发生的场景和条件下的时空放缩和物理量调控,如此交互对接、双向互反馈,现实世界—思维链网—虚拟世界融为一体,全过程、全息地对物质产品的需求意愿、产品设计、生产制造、分配交换、物流消费,信息、技术、制度和激励、智慧创造的综合利用机制,这些是元宇宙的应有之义和必有内容,将来也必然要以元宇宙或类元宇宙的方式来实现。
三、元宇宙与精神财富的生产
(一)元宇宙与知识生产
过去谈生产方式,主要谈的是物质财富的谋取方式,但实际上,元宇宙的更大作用表现在解放人的精神、激发人的创造力方面。所以元宇宙的观念和思维,包括对科学的理解、学科的设置以及对真理的冲击等,到那时就不一定是简单的“眼见为实”。真假混合,你分不清楚了,所以这个时候对科学真理怎么检验,实证分析中什么是实证等都会有一些迷惑。但是它的核心就是把逻辑推理升华到映射生成,这也是科学研究范式的一个华丽转换,人们用严谨的推理到想办法转变到用真实社会的映射,即generating-science生成式科学。特别是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和复杂的管理问题,研究的立场和角度、心理和伦理等,怎么融入知识获取的方式中。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人类文明和科技进步,以及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处结合起来?再来看人类社会的进化、科技的进步和元宇宙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就可以说从茫然到非常有信心了,最核心的就是人类的自我认知定位。所以从有我到无我、精神财富的创造,人类在原来的知识体系和知识获取方式中,主体性和易变性这些原来是没办法处理的。特别是人机交互、脑机对接和人机协同应对复杂性问题,要想真正知道人在临界状态、在奇点时的大脑思维、意识细胞、神经元怎么突变,以及到这个神经网络结构性功能等类问题,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类大脑与其他生物体类比肯定解释不清楚,而要把它当成木头或者当成物质的东西来研究,就更不对路了。裂脑实验中,被裂开脑以后的他不是真实的他;可要是不裂开,又不能观察到事实。所以怎么样通过元宇宙的技术,把人类大脑真实的东西,通过生物芯片、神经网络和类脑科学等大跨度的多学科交叉,同科技进步有机结合起来,人类对社会真实场景的一些感官,不同形态的信号转换、对接、传输、发送,不同的规则、逻辑和套路等问题要运用数字化从根本上解决,这是要从底层逻辑上解决规则转换问题。
多主体差异化目标设定,多场景交叠切换,多态数据形变统合,多科理论交互渗透,多模型思维建模,多模块算法分设组配,“无限”算力的支撑,多类终端云接网联,多领域应用检验等,认知方法论的升级变革,Metaverse在改变科学家的思维和研究方式,提供了全“真”实验室和具有超级强大功能的研究“平台”,成为科学家的新生产工具,催生科研新范式。真亦假,假亦真;规律的不规律,不规律的规律;思想实验、思维过程可视化展现,可任意精度和粒度上聚焦在任意的关注点上,能够综合、凝聚和提升现有各种研究方法和工具的优势。元宇宙有可能让我们逐步逼近真实,使探索真理的方式甚至真理的“标准”都可能会发生彻底的改变。
(二)元宇宙与精神财富创造
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有人宣告:我在元宇宙中证明了歌德巴赫猜想,攻克癌症和有效控制疫情大流行,破解DNA密码和意识的起源,测定质子寿命和暗物质成分,解释自然界超对称性为何破灭,成功演示薛定谔猫试验,深刻理解第一性原理的启示,充分展现大科学实验的成就,可控可视地提高人类思维的容量、速度、效率、逻辑性和精准度……当今人类面对的诸多世界级难题,或许在元宇宙中就不复存在,但还有可能会产生新的难度更高的元宇宙级问题。从观察感知、抽象假设、逻辑推演、实证检验,仿真模拟,现实中各种可能发生的场景,理论规律的验证:常规的与反常的,正反向因果相关、关联涌现,与真实异质性主体的各类关键行为特征交叉叠合,全都可摄入元宇宙,于是,人在回路的沉浸式体悟使历史可以重演,时空可以伸缩,虚实可以叠加,创意可任意地逼真展现,不同类效果也可比较鉴别,以此化解虚实交融带来的困惑、疑虑和茫然,同时也有可能使人类会面对更大不确定(未知),产生新的疑难。
从数字化视角看,元宇宙或许是个很好的实现工具和平台,所以我们能不能从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看元宇宙的未来发展态势和趋向,特别要强调元宇宙与人类的发展一定是协同进化的。人类超越或者说主宰、分布式区块链等都是单边技术的想象,真正我们最应该做的和最能把握住的是人类自身,人性自我认知的深化,把人类的创造性发挥到极致,从有我变成无我,才能达到社会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更高的有序的加速自组织境界。所以,以元宇宙为契机更深入地研究人类自身就是元宇宙的核心价值和最大贡献。
四、结语
总之,元宇宙无论是翻新概念还是新生事物,不管是喜欢还是讨厌,它无疑是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演进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时代标志。虽然对路究竟有多长,难度有多大,以及未来发展可能的方向和路径等还难以清晰想象,但人类与自然界、A世界(Atom:原子/物理世界)与B世界(Byte:虚拟/数字世界),虚实都必定是要相互依存、互动共进的,即使能纯科技、纯逻辑地创设出本—摹合体的新的超人或超然的X体,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人类主体。
人类与自然界交互是元宇宙的底色和主体内容,同时,元宇宙是人类活动空间和现实世界中心的组分和外化形式,不可用当今的思维模式、标准和方法去评价预见,要用以实为本、虚实融合的元宇宙观念,用动态演化的观点去理解、建构和发展,充分发挥、发掘和激发人类的智创性,在实践中畅想,在畅想中创造;一时难以抓准的本质和认清的东西可以留给未来,让后人去验证、去推进。到那时人可能既是人也不是人、生物体与思想精神既合又分、行为活动和生产方式等完全虚实融合,如此的元宇宙才有望为人类探索生存发展极大地丰富想象力、加深穿透力、增强解释力、拓展预见力。
元宇宙的动态结构、影像机制与数字迷思
郭春宁
作者简介:郭春宁,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人大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动画与新媒体艺术研究。Email:guochunning@ruc.edu.cn
一、反叛是元宇宙的基底
我对元宇宙关注可以回溯到2017至2018年间,当时我在荷兰访学,与位于内梅亨(Nijmegen)的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 Institute)神经语言学研究所的Asifa Majid教授(她还兼任荷兰拉德堡德大学Radboud University“意义、文化及认知”跨学科研究实验室的导师)及其团队合作。她们聚焦研究味觉记忆,因为我一直在做影像与视觉记忆的研究,Asifa教授非常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开启关于国际跨文化的记忆的研究,如今回想起来,这也是拓展视觉影像记忆之外的综合感知探索;我还发现荷兰国家科研基金的荷兰研究理事会(NOW)这样的一个分支机构,积极推动跨学科机构和个体之间的合作,那么不同领域的人们靠什么团结在一起呢?NOW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也就是一种好奇心,好奇心驱使我们在同一个命题下展开这样的跨界的合作。就如同今天我们不同领域的人们共同讨论和探索元宇宙,也需要一种对于未知领域的好奇心。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已经开启建立了这种对于元宇宙的一种新视听和基于神经感知的综合研究的跨学科的建构。
最近Facebook改名为Meta之后,也是在研发一系列新的动力触感装置,也就是认为元宇宙短期内听觉和视觉没有办法获得明显突破的情况下,要率先突破触觉感知。2021年11月Meta展示了一款触觉手套,这副手套能够帮助你在进入虚拟世界时,通过给手掌和手指施加细微的压力,模拟出虚拟物体的形状,让人们在虚拟世界中更好地感知触觉。还有Meta公司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与卡内基梅隆大学科学家一起造出了“Reskin”,就是一种厚度不到3毫米的可变性“皮肤”。这种皮肤利用磁场变化让人产生触觉。可以预见,在视觉、听觉、触觉之外,嗅觉和味觉的感知研发也会快速跟进。那么,元宇宙所开启的一定不是局限于视觉和听觉感知空间,所以我认为,元宇宙会激发对于局限于视觉方式的反叛,探索关注综合感知的动态结构和影像机制。
这种关于元宇宙的更深入和跨学科的合作,也体现在学者层面的反思,譬如《技术有病、我没有药》等专著和相关讨论,看到了一系列的技术伦理议题。我认为元宇宙它很重要的一个基底和机制就是反叛,而关于技术的反思和反叛让我们会联想到,技术作为一种可能的、新的智能生命其本身对于一种去中心化的、多元可能性的建构。
这里我想表达的是,把元宇宙视作一种新的数字神话和谱系。其实无论是1990年的《镜像世界》还是1992年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的《雪崩》,当时都是基于科幻作者对于现实的一种不满提出的一种反叛。比如《雪崩》中构建了所谓的元宇宙恰恰发声在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背景之下,美元急剧贬值,因此人们在交易中大多使用数字货币,通过各自的“化身”(Avatar)彼此交往,随意支配自己的收入。而小说的主人公恰恰是具有骇客精神,在元宇宙中行侠仗义之人。这种反叛性从科幻文本折射到现实世界的科技研发中,也就是说,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呈现出一种聚焦虚拟现实研发的趋势,而种种新视听的研发也在宣告,反叛以一种更注重开放结构和动态的影像机制展开了。
大家会看到一种可能,在元宇宙建构中,游戏不再是游戏,它成为一个大型的演唱会,玩家改变角色变成一个新的偶像崇拜者。我们看到在疫情期间,2 770多万的歌迷在“堡垒之夜”(Epic Games)中观看他们喜欢的歌手Travis Scott作为数字化的偶像“从天而降”(在游戏中歌手化身“巨人”,如同天外来客从大气层外“砸”进地面)。所以这也是一种新的神话的开端,对这种数字神话或数字迷思,即digital myth,当然应该开启反思。
二、数字身份系统和NFT
元宇宙是一个信息和身体的张力游戏,在元宇宙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系统,一个是数字身份系统,一个是以NFT(Non-fungible Token)为基础的一种非同质化代币的分布式记账系统。首先,“数字身份”超越了玩家的范畴,在未来也将超越我们已经比较熟悉的数字账号的层面,成为一种新的同步和拟真身份。这种新的虚拟身份,能够激发用户建构自身在元宇宙中的数字形象。以升级版的数字身份在元宇宙中结识新的伙伴,形成数字空间的社交关系网络。如今非常流行的各种类似“加密朋克”(CryptoPunks)、“猿猴俱乐部”(Ape Yacht Club)等像素风格头像的交易,就是体现出元宇宙初期,人们想为自己的数字身份进行包装。进而,这些头像不仅是一种包装,它们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货币,即虚拟身份头像和数字代币合体了。也就是说,每个“朋克”都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像素艺术图像,每个“朋克”都在区块链上拥有独特的数字身份。当一个个使用虚拟头像的以太钱包用户以玩家的身份入场交易时,他们竞购的对象也是虚拟头像,每个头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数字艺术作品本身,也是具有增值潜力的数字资产。这也是人们现在热衷购置这些头像的原因之一,他/她们希望以更具“游戏性”和“独特性”的方式参与到未来元宇宙中,因此“游戏化身份”也是现在NFT等加密艺术品台的互动基础。
基于这种新的身份系统和价值流通系统,艺术和设计的从业者想要去建构更有创造性的、绿色的、开源的、动态的影像生成机制。这种反叛的基底也应和了去中心化的背景,与后人类主义或者说后物种生成有关。因为后人类主义,召唤的是对西方长期工具理性而来的一种去中心化的思考,就是不要把人类作为至高无上的、世界的主宰。而这种对仅以人类为中心的主体性的驳斥,其实宣告了“人类特殊主义”的终结,也激发了新的创造性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一书非常具有代表,其实是回溯了在20世纪40年代,控制论形成的两个重要的推力,就是信息到底是抽象的,还是可以是具身的。而这就像当时的冷战阵营中最后的军备竞赛,反而促成了计算机高速发展一样。这两个理论的争论反而促成了人工智能形象在一系列无论是实验、还是科幻以及电影中的建构,我觉得这本书仍然值得重新去回眸和细读,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对人文主义消解的反思,而且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三个阶段,就是信息论如何去从这样的一种动态平衡到反身性再到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这种虚拟性的推动。
无论是梅西会议所形成的信息化和具身化的两个阵营的争锋,还是最后提出的脑机接口,都在像《堡垒之夜》这样的游戏变成的演唱会中的开放性挪移建构中实现了。在这次“元宇宙热的冷思考”之前,我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永谋老师、王小伟老师一开始就是从NFT的冷思考切入,和《中国美术》杂志合作策划主题组稿。因为我是艺术专业的,所以我们有这种可能进行理论上的探索,我把元宇宙和NFT进行结合,去进行新媒体艺术家的访谈。总之我认为它(元宇宙)是一种新的加密的梦境和数字迷思。
我们现在正在做从漫画到动画再到NFT的这种元宇宙项目孵化。为什么把元宇宙视作一种数字神话/迷思?从二战以来记忆学的兴起和对神话学的反思是共进的,而这种共进已经在召唤现在我们讨论的这种元宇宙。无论是巴特的《神话修辞术》对于数字神话一种方法论的贡献,还是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提出的在大数据时代要警惕这种新的贫富差距的拉锯和新的贫穷阶层的生成,甚至造出新的边缘人群。欧洲近年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奥托洛娃(Peppino Ortoleva)提出了数字技术作为一种神话主体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虚拟现实确实不仅是从产业的层面,更重要的是一种从视觉机制的层面成为了一个和元宇宙非常关联的内容。
从中世纪开始“virtual”这个词已经从神学层面出发,提出与确实/真实相反、但仍可以深入本质的一种探索。Virtue非常重要的比照的对象就是戏剧(theatre)。所以,半个多世纪间,virtual reality这个词从法文到英文,从科幻文本、软体运行一直到最后进入产业。但是从装置层面来讲,其实无论从19世纪到20世纪,我们都能看到个体、实验室开始研发,最重要的就是从1984年开始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介入以及1992年日本世嘉作为游戏公司对虚拟现实的开发。Facebook用20亿美金购买Oculus(眼睛)虚拟设备公司,而Oculus实际上2012年开始在kickstarter上的众筹产品,也就是它早期采取内容/设备共建,是在每一个玩家、每一个具有数字身份的人都能够出一把力的状态下去完成的。而通过众筹行为获得的项目成功也表明了很多技术—艺术研发是基于公众性的参与而实现的。
NFT也是显示出这种公众易于参与的特性,我认为由此它成为尤其对于创作数字影像非常重要的新平台。比如,以往在NFT这种分布式记账出现之前,数字影像(digital image)的艺术作品主要是通过动画节和美术馆去展映流通,在现代美术管理主要遵循的还是一种录像艺术收藏和拍卖形式。而录像艺术遵循的是版画的形式,它以特定的版本限定来进行这种确权。NFT使得我们通过这种分布式记账,使得作品看起来是一个可以被复制粘贴,但每一个收购者都有一个唯一的可追踪的编号。虽然是一个复制性的数字影像,它有了一种新的流通和共享方式。在2021年3月纽约佳士得首次以NFT加密艺术的形式拍卖的《每一天:前5 000天》(Everydays:the First 5000 Days)的创作者Beeple(本名:Michael Winkelmann)其实从2007年5月1日就开始每天创作一幅作品,这幅拍出近7 000万美金价格的《每一天:前5 000天》正是他13年半来不间断创作而积累完成的一个图片合集。
但是,在NFT机制产生之前,Beeple却只能在网络上一张张单独售出自己的作品,没有办法去保证他自身和购买使用人的转卖权利。而因为NFT艺术交易基于智能合约进行,作品每交易一次,艺术家都能自动获得一定的收益。并且区块链透明公开的特点,使得每笔交易的详细情况都可被追踪查阅。在区块链去中心化的技术支撑下,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市场门槛将被大幅降低。无论是艺术家还是购买者,都可以随时通过NFT艺术交易平台便捷地进行交易。NFT所提供的这种新的、甚至打通二级市场的方式,就是不受币种的限制,甚至可以用这个币去买游戏中的道具,由此形成新的货币流通。当然这是一个探索的阶段,我们国内还没有真正开放,很多国内的NFT形式还是各自为政的,只有抖音是在国外市场联通了的NFT,所以我觉得未来怎么去融通,这也是一个议题。但是对数字媒介创作的艺术家来讲,我觉得它无疑是一种新的展示、流通、收藏的一个机制。
有一些类型的NFT作品是取决于玩家或者是参与者的互动。譬如说取决于多少人参与在线的这个作品,或者如果是个动态影像作品,参与者可以如何参与到叙事结构里,或者一部分形象的改装中。这取决于创作者他愿不愿意把这个作品作为一种开放式的结构,交给他未来可能的收藏者或者是参与者。当然也有人选择一个封闭性的作品,只是用NFT作为一种流通的机制。所以我觉得它是多元的,而这种互动的结构也不是NFT独有的,但是它可能现在成为新的、更具流行趋势的形态。互动艺术此前就在美术馆展开过各种实验,但是不太可能有像刚才看到的那种两千多万的玩家在线或者是参与者在线的情况出现。所以若需要一个更广泛的、跨国界的人参与的话,我觉得需要NFT提供的开放平台。
三、中国的Z世代和中国的元宇宙艺术表达
在这种虚拟现实到元宇宙的过程开发中,我们中国的Z世代的年轻人,他们也在贡献从梦到神话的作品创作。无论是获得威尼斯电影节VR奖项的平塔工作室的《拾梦老人》,还有以神农为主题的《烈山氏》,都用虚拟现实的方式去述说中国的现实梦境和神话,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因为它代表了新一代的故事欲、神话情节和记忆书写。西方的一些主流媒体,他们在进行虚拟现实尝试的时候,首先都把焦点对准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边缘人群,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英国卫报的虚拟现实首秀就是关注囚室监狱的犯人,而且是独囚者。用户戴上VR目镜就如同置身于一个6×9英尺的监狱中,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中体验到好像被关了十几小时,一天这样在监狱中的这种悬浮感、幻觉、幻听等。元宇宙可能会为我们开启更多元的关注边缘人群的视角,我觉得这个是值得重视的趋势。
现有的二次元或者是元宇宙的头像看起来像素风格很低,我觉得恰恰是因为在一个去中心化的机制中,它不能达到即时渲染的效果。但是这种低科技(low tech)的像素风会开启一种后物种繁殖,比如说加密猫看起来视觉效果是扁平化的,却非常受到Z世代的人的追捧。在很多的游戏中你可能养一只宠物,如果这个公司解体了,你的猫也不存在了,但这个加密猫只要你拥有它,它就一直存在。而大家知道这个里面升值最大的基点就是一个猫的形象要通过基因配对而特立独行。比如零代猫就是加密猫链条上价值最高的一环。同时我觉得在艺术界来讲元宇宙也不只是炒作,比如说很多人在关注Beeple的作品近7 000万美金的天价,但我认为,实际上他是在总结5 000天的每一天创作,才产生可以伸展于NFT空间乃至未来元宇宙中的这幅像素画布。也就是说,这部拍出天价的NFT艺术作品是一个巨大的现实同步项目,艺术家将创作的一幅幅日常记录上传至网络,5 000天中每一天的作品最终成为这幅巨大画布的一格像素。可以看到,Beeple的这种成功非常精彩地诠释了“日常及宇宙”的概念,每一天既是艺术的勾勒,也是数字化的存储,更是艺术建构时空的范例。
中国艺术家蔡国强老师也一直在通过虚拟现实,无论是《梦游紫禁城》,还是NFT《瞬间的永恒——101个火药画的引爆》,都展示出传统的艺术进入到元宇宙的可能性,从而摒除元宇宙只是一个“成功学”的炒作。另外很重要的就是元宇宙它有可能带给我们超出年轻男性视角的、更有平权性别的可能性的空间。
元宇宙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从人工智能到大数据到云计算到虚拟现实还是区块链,学界和产业界都在探讨怎么使元宇宙进行可持续地、绿色开发。也就是,必须在全球关注的减少碳排放的语境中建构一种“清洁NFT”。对于此问题,目前已有一些积极的应对方案,譬如将画廊数字化、要求对加密货币提供工作量证明与持有量证明、加强对艺术品合作化及非商品化的支持等。而这个也是我们关注和致力于探索的。比如,我们在关注如何以开放数据的艺术化设计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和更新。其实图书馆本身在近20年已经在做很多新的开放数据,比如说和上海图书馆、文澜人工智能系统合作,我们研究:中文的人工智能系统——文澜怎么去“看”数据?这就涉及扩展“神经网络”的视听图景。同时,人工智能系统“看到”一些风景过程中也是需要视觉和听觉的同步;同时要跨越小数据到大数据的过程,而现在其实可能更需要在基于大数据的元宇宙的世界中进行一种个人的计量。这种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回到了20世纪80年的一个low tech的风格,我觉得它有助于去反思我们在40年的一个数字化(digitalization)发展过程中,具体到底经历了什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经历一个所谓的“第一视角”的一个游牧主体在具身化、数字化的过程,同时,需要去进行关联,需要继续进行连接,这过程同时也带动了更多关于科技伦理的探讨。
我想展示我们正在做的一个作品《科学城:父亲的炸弹》图像绘本,我觉得这个作品某种意义上见证了NFT到元宇宙过程中影响动态影像创作机制的一个过程。这个作品2019年在柏林电影节首先是作为一个图像绘本进行孵化的,我们把一个竖屏的漫画拓展成了一个横屏的后物种的创造,大家会看到这个背景的数字网格实际上是3D Max的数字建模网格,这给了我们提示,究竟是我们在创造这些数字物种,还是这些所谓被我们创造出来的后物种,在通过某种类元宇宙的数字网格反向地凝视我们。而且这个故事其实正好基于兰州的一个真实的化学实验中的爆炸事件。或许我们有机会从社会学、人类学,从计算机学,从哲学、艺术共同作为一种知识共同体,来重审元宇宙这样的数字神话和记忆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