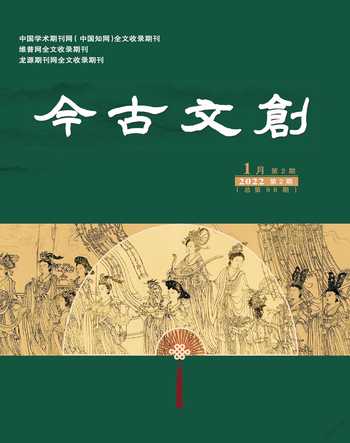《致身录》中的空间叙述
裘书莹
【摘要】 空间叙述是《致身录》重要的叙述方式。小说通过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塑造,形成了独特的空间叙述方式。地理空间的分离与联系不只建构起故事的框架,还对人物的塑造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两种不同的社会空间——朝堂空间、流亡空间,以其独特的文化环境和伦理环境,产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使得小说更具真实性。与此同时,精神空间的叙述中展示出创作者本身的精神倾向,从而使得整体呈现出立体性、可感性。
【关键词】 《致身录》;空间叙述;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2-0004-03
关于《致身录》的真实性问题,自明末以来不乏考证,史仲彬是否从往,此作是否为后人之伪托,本文不做讨论。本文立足于小说视角,对《致身录》的创作中的空间叙述进行大致探讨。空间是一种地理、社会、精神的多维存在。空间不只是故事发生的场所,更是叙述的组成部分,参与到小说的叙述之中。在《致身录》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类型的空间,空间变化推动叙述发展,不仅对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产生了重要影响,还流露出了创作者的精神倾向。本文主要通过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三个部分来谈谈《致身录》中的空间叙述。
一、地理空间的变换
《致身录》是明代创作的有关建文帝的一部小说。在小说中,并不是以某个地点为单一的地理空间,对其进行刻画与描写,而是通过各个地理空间的变换,实现文本的叙述。
《致身录》中地理空间的变换,是随着人物的行迹展开的,主要是两个人物,一是建文帝,一是史仲彬,《致身录》通过这两个人物的经历,来实现小说中地理空间的不断变换。在小说的开始,就刻画了建文帝在南京即位这一事件,接着去衡山受朝贺,之后叙述建文帝在南京的变革举措,燕王起兵攻入南京,建文帝带领部分官员流亡于江浙、云南、重庆、平阳、湖广等各省,在《致身录》中,以建文帝为主的空间变换大致是“南京——衡山——南京——吴江(史仲彬家)——襄阳(廖平家)——吴江(史仲彬家)——两浙之行——重庆(寺大竹善庆里)——云南(白龙庵)——云南(平阳庵)——湖广”。《致身录》中的空间变换,除了建文帝的行迹,还有史仲彬从亡建文帝的路线,这条路线大致为“南京——衡山——南京——山东——南京——吴江(史仲彬家)——襄阳(廖平家)——吴江(史仲彬家)——两浙——吴江——连州——重庆(寺大竹善庆里)——白龙庵——吴江——南康——襄阳——连州——云南(白龙庵)——鹤庆——云南(平阳庵)——吴江——湖广”。在小说中,建文帝自南京逃亡后辗转于各处,但主要是流亡在西南、两浙这些南京以西、以南之处。小说通过建文帝和史仲彬在各个分离的地点之间的往来展开叙述,建构起小说的主要框架。
除了省份地点这些相对较为阔大的地理空间的变换,在《致身录》中,还有小地点之间的变换,这些小地点的变换也使得故事更加饱满与立体。在燕兵攻入皇城后,建文帝出逃皇宫的路线的描绘就格外具有真实感。自鬼门出发,从水关顺着流经宫苑的河道出逃,在神乐观的西房会面,这些具体地点的出现使得故事的发生更加顺理成章,更具有真实性。
从地理距离上来讲,各个地点之间的关系是分离的。在这些地点之间的距离,是相对较为远的,在这些地点之间往来往往需要好几个月,甚至是几年。如史仲彬癸未正月二十日自吴江出发,于三月初三到达襄阳,吴江与襄阳之间的往来用了40多日;史仲彬于八月十三日从吴江的家中出发,九月二十五日到达湖广界的旅店;书中还提道:“正月中,遣僮往海州,请何洲同到云南,三月终才到 ①”,这一来一往也用了两个多月。地理空间之间较为遥远的距离使得跋涉艰难,在地点之间往来需要充足的时间与精力,这也就描绘出了建文帝流亡之艰难。书中在描述白龙庵这一地理空间时提道:“上下山阪逶迤曲折,越行十八九里而庵在焉 ②”。白龙庵位于白龙山深处,若按正常人每小时五公里的步行速度,到达白龙庵至少需要三个多小时不间断的步行,地点间在地理上有着较为遥远的距离,这也就反映出建文帝流亡生活之艰难。
在《致身录》中,地理空间之间不仅仅是分离的,各个地理空间之间还存在着联系。一是地理空间的变换构成了建文帝流亡和史仲彬从亡建文帝的路线,使得故事的情节得以顺利展开,二是通过比较两条线路的地理空间变换,可以发现史仲彬从亡与建文帝在流亡过程中有多次相见,分别是在吴江的史仲彬家、襄阳的廖平家、云南的白龙庵、平阳庵。在这些地理空间中的建文帝与群臣交往情景的刻画,使得建文帝等主人公的形象更加饱满。
总之,《致身录》中的地理空间的变换,在于建文帝流亡和史仲彬从亡建文帝时地点的变换,这些空间之间既有分离,也存在着联系。地理空间之间的分离,主要体现在距离上;而空间之间的联系,则主要体现在建文帝与史仲彬的活动之中。这些地理空间之间的变换使得情节的展开更加顺利的同时,也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饱满,让故事更加具有立体感、真实感。
二、社会空间的刻画
史仲彬在《致身录》中叙述地理空间的同时,也刻画了社会空间。在小说中,史仲彬通过对社会空间的文化环境和伦理环境的描绘来揭示空间所孕育的社会文化内涵,从而推动情节的发展和丰富人物的形象。在《致身录》中,社会空间主要是朝堂空间和流亡空间。《致身录》通过这两个空间的刻画,使得小说更加具有立体感、真实性。
朝堂空间主要是指书中提到的南京为主的建文帝统治时期的空間,主要是洪武三十一年戊寅五月辛卯建文帝即位到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建文帝逃出皇宫,在这一社会空间之中,主要是描绘了建文帝的改革和任命官员治理国家的情景,君臣之间的交往以讨论政治为主。朝堂的社会空间整体呈现出建文帝的开明和群臣的敢于谏言。在建文帝即位后,便征召山林才得士、更定官制、减免赋税,面对昌隆的“让位守藩”建议,群臣愕然和史仲彬气愤时,建文帝却说:“人臣之义,当以仲彬为正。昌隆素有敢言之气,请勿为罪。③”书中史仲彬之口说道:“幸逢皇上明圣,每从宽事,敢竭愚忠,伏听采择。④”面对燕王的入侵,军中都说是建文帝失之太仁,这些事件的刻画不难看出建文帝的善于纳谏、处事仁德。这朝堂这一社会空间之中,臣子也呈现出智、勇的独特品质,战争的失败,只是因为燕王用兵的变化莫测,将军仍是谋略第一、士兵仍是力战至死。当燕兵渡江后建文帝与群臣商议对策时,建文帝愕然无措、群臣恸哭、群臣众议哗然不决,茹常、王韦、方孝孺提议不同逃亡地点,表现出群臣的各种谋略,群臣讨论谋略时,只有当建文帝首肯时,群臣才决定策略。在生死的危难关头,建文帝虽然慌乱,但仍然听取群臣建议,群臣虽意见不同,但都认可建文帝的决策,在朝堂这一社会空间中,展现出以君为上的伦理关系,决策以建文帝为主,臣子听从皇帝的决定,呈现出仁德的建文帝形象。
相比于朝堂这一社会空间,流亡空间在《致身录》中对于生活场面有更加详细的描写与刻画。在笔者看来,书中的流亡空间主要有两个阶段,一是建文帝等人刚刚从皇城出逃至史家的阶段,二是建文帝流亡于西南这一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面对追捕的逃离,整体呈现出紧张的氛围。流亡于西南这一空间呈现出流亡生活的颠簸、艰苦,但艰苦之中,亦有和谐的君臣交往之乐。在这一空间之中,随着流亡进程的展开,不断出现不同地点之间的变化。在流亡这一社会空间之中,有详有略的流亡空间刻画使得故事更具有可感性。书中主要突出的是建文帝短暂居住的地点,分别是重庆的寺庙,云南的白龙庵、平阳庵,在这里,不难发现建文帝所居住的地点均位于西南一带且为庵和庙。当史仲彬等人去白龙庵寻找建文帝时,书中对于这一空间是这样描述却是月色皎然、山中,关于“平阳庵”,书中是这样描绘的:“前后深林密树不下数里⑤”。至此,可以发现,建文帝流亡空间中的环境大致为清贫、宁静、隐蔽。不同于朝堂之中的君臣交往,在流亡这一空间之中,整体上更具生活气息,更出现相互理解与包容。当皇帝出逃时,二十二人誓死追随,当群臣在白龙庵见面时,先是恸哭,再是听说有佳肴的大喜,之后日子里,群臣畅游山中、履请履留,最后分别,建文帝痛哭失声的不舍,“恸哭——大喜——畅游——痛苦”的转变把相见的喜悦、分别的不舍表达得淋漓尽致。平阳庵之中群臣悼念已故的建庵者、共同饮酒消融愁气场景的刻画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在开始流亡时,群臣誓死追随建文帝,在长久的流亡生活中,群臣仍挂念着皇帝的安危、多次冒险寻找皇帝;皇帝放下身段、不拘礼教、与群臣以师弟称呼,在流亡这一空间之中,淡化了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强化了在流亡生活中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的洪武三十一年戊寅五月辛卯确是历史上建文帝登基时间,建文四年六月也确是朱棣攻入皇城之日。《明史·恭闵帝本纪》记载“(建文)帝不知所终”,在时间上,书中建文帝登基与流亡与历史具有一致性;在人物上,书中提到的方孝孺、杨应能等人确为建文帝亲信,《致身录》中时间与人物的一致性使得故事中社会空间的刻画更加具有真实性。
总之,在笔者看来,在《致身录》中,社会空间主要是朝堂空间与流亡空间,朝堂空间主要特点是严明、庄正,呈现出明显的君臣关系,流亡空间主要是清冷、悲痛,君臣关系更加平等、密切,“君臣”关系向“师生”关系转变。社会空间的刻画把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社会生活更加连贯地叙述出来,体现了建文帝的处境,展示了建文帝这一形象由高高在上的皇帝变为普通人的变化过程与原因。小说通过社会空间的塑造,把不同社会空间赋予不同的社会寓意。通过空间的变换,营造不同的社会氛围,反映出君臣的成长与选择,形成了空间化、多样化的效果使得故事更加呈现出整体性、真实性。
三、精神空间的展露
在《致身录》中,除了地理空间、社会空间,还可以感受到精神空间。精神空间是人在精神上的一种反应。小说中的精神空间,主要是指叙述中流露出来的“互恤取代对立、颠沛取代杀戮、回归取代死亡 ⑥”的精神倾向。
焦竑 《致身录序》提道:“往岁戊辰,予同二三友人薄游茅山。会淫雨连旬,兀坐一室,老道以所藏杂文供翻阅,竟日无可意者,最后得史翰林《致身录》。⑦”也就是说,《致身录》出现于万历末年。刘琼云在《帝王还魂——明代建文帝流亡叙事的衍异》一文中提道:“《致身录》的出现和万历年间为建文冤案平反的声浪及实际作为有关。⑧”值得注意的是,万历年间之所以会选择为建文忠诚平反,是因为政治上对忠臣的需要与推崇,万历年间为建文帝平反的风气促使朝臣文士致身于建文朝史工作,在文学作品中,也流露出了这一倾向。《致身录》的刻画中,就有意识地强化了绵长坚韧的君臣情谊。君臣共同流亡、饮酒、恸哭等场景的刻画使得君臣间的情谊表现得格外明显。《致身录》中的君臣关系,很少带有矛盾冲突、意见不一的对立倾向,在危难面前,君臣之间仍为相互体恤,如建文帝出逃时,对群臣是否跟随都表达出了理解。君上体恤臣下、臣下为君上尽忠的塑造流露出创作者精神空间之中对于仁君忠臣的理想君臣关系的政治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万历帝为建文忠臣平反了冤案,但是由于其自身本为明成祖之后,万历帝始终未能同意别立“少帝纪”,只是同意“以建文事迹附太祖高皇帝之末,而存其年号⑨”。在《致身录》中,采用了“颠沛取代杀戮”这一叙述模式,对于燕兵军队,书中以客观的方式进行叙述,对其行为的刻画也不带有情感色彩。在燕兵攻入皇城时,书中并不刻画军队的行径,对杀戮场面也不展开叙述,取而代之的是对君臣流亡场景的刻画,在这之后,也不展开叙述明成祖追捕建文帝等人的情景,而是以不斷地流亡、流亡生活的刻画来取而代之。在《致身录》中,在肯定建文帝政治改革的同时,也并不否认明成祖起兵的行为,以颠沛的流亡生活的刻画代替了血腥的杀戮场面。
历史上关于建文帝的结局,说法不一,《太宗实录》提到明成祖在火中发现了建文帝尸体;《明史·郑和传》记载其逃往海外……各式的说法导致了叙述潜在的复杂性,对于建文帝的结局,《致身录》一书中以回归取代了《太宗实录》中葬身大火的死亡。在《致身录》末尾,建文帝经历多年流亡生涯后心态发生转变,“吾心放下矣⑩”表明建文帝已经获得了独特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感悟,对于皇位的归属已经释然,完成了回归,书中关于建文帝这一结局的塑造流露出创作者对于建文帝的理解、同情等独特的精神倾向。《致身录》对建文帝行迹的描写中,社会现象与个人情感的交杂,回归这一结局的选择展现出创作者精神空间中对于建文帝的一种理想结局。
在笔者看来,《致身录》所呈现出来的创作者精神空间中这些倾向有一定的一致性,那就是对于现实的无法截断,精神空间的展露中仍体现着理想君臣关系的心理活动主线,这是文人在政治、社会、历史等多个方面影响下形成的精神倾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致身录》中,空间叙述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空间的变化、刻画以及空间的展露都对人物的行为与故事的情节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在刻画时,也流露出创作者的精神空间的倾向性。《致身录》通过叙述不同的空间,使得空间的真实感、立体感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不同空间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细致刻画,也使得各个空间更加特殊化与多样化。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⑩史仲彬:《致身录》,上海涵芬樓景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排印学海类编本,1920年,第21页,第22页,第6页,第7页,第26页,第28页。
⑥⑧刘琼云:《帝王还魂——明代建文帝流亡叙事的衍异》,《新史学》2012年第6期,第82页,第67页。
⑦赵士喆:《建文年谱》卷下,清初刻本,第250页。
⑨潘柽章:《国史考异》,清光绪间吴县潘氏刻功顺堂丛书本,第308页。
参考文献:
[1]顾颉刚.史仲彬故事[J].中国史研究,1984,(3).
[2]刘德州.明末清初关于建文朝历史的编纂及考证[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