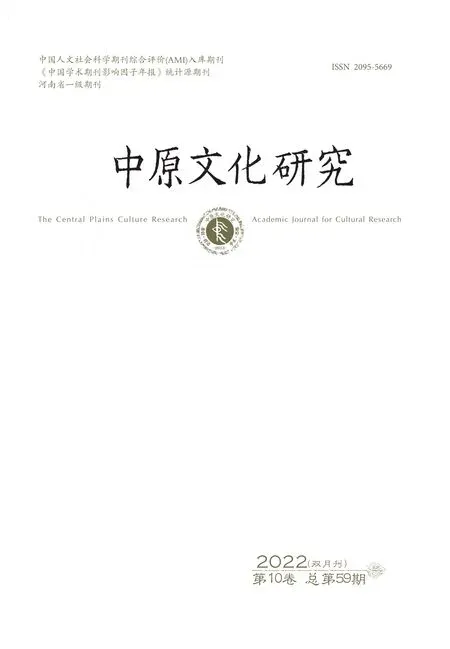论宋宁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诸葛忆兵
宋宁宗赵扩于绍熙五年(1194年)登基,嘉定十七年(1224年)去世,在位30年。宁宗朝权臣当政,结党营私,前有韩侂胄,后有史弥远。史论云:“侂胄用事,内蓄群奸,至指正人为邪,正学为伪,外挑强邻,流毒淮甸。……既而弥远擅权,幸帝耄荒,窃弄威福。”[1]781朝政糜烂,制度窳败,科举方面当然不能幸免。自南宋宁宗朝以后,宋代科举制度走向衰落。
一、禁绝道学
南宋后期科举制度之衰败,与党争关系重大。科举考试不再是相对公平公正地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方式,而成为朝臣排斥异己、打击政敌的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
禁绝道学,不始于宁宗朝,却以宁宗朝最为酷烈。
北宋程颐等倡导的理学,传播渐广,门徒众多,至南宋已成风气,时或称道学。科场时文立论,或尊奉王安石之说,或推崇程颐之说,渐成纷争之态势。高宗前期“最爱元祐”,当然倾向程颐学说。高宗朝宰相赵鼎,“深喜程颐之学,朝士翕然向之”[2]1418。又,“赵鼎作相,殿试策不问程文善否,但用程颐书多者为上科”[2]1591。程颐之说,一时成为科场风向标。
赵鼎罢相,左司谏陈公辅即上疏云:
朝廷之臣,……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是以趋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为大言。……狂言怪语,淫说鄙喻,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2]1807
高宗欲调和朝廷政策,所以一度同意陈公辅的主张。秦桧当政时期,无情打击政敌赵鼎等人,程颐学说亦受池鱼之殃。史官概述云:
自神宗朝程颢、程颐以道学倡于洛,四方师之,中兴盛于东南,科举之文稍用颐说。谏官陈公辅上疏诋颐学,乞加禁绝。秦桧入相,甚至指颐为“专门”。侍御史汪勃请戒饬攸司,凡专门曲说,必加黜落。中丞曹筠亦请选汰用程说者。并从之。[1]3629
秦桧去世,高宗再度回到调和的立场。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高宗言:“赵鼎主程颐,秦桧尚王安石,诚为偏曲。”[3]4305
孝宗朝,仍有意弥合党争。孝宗曾“泛论用人不可分别党与,须当尽公。又曰:‘朝廷所用,止论其人贤否如何,不可有党。’”[4]1783。然而,朝廷党争难以彻底消弭,科场王、程纷争依然。淳熙五年(1178年):
侍御史谢廓然言:“近来掌文衡者主王氏之说,则专尚穿凿;主程氏之说,则务为虚诞。夫虚诞之说行,则日入于险怪;穿凿之说兴,则日趋于破碎。今省闱引试,乞诏有司,公心考校。毋得徇私,专尚程、王之末习。”从之。[4]1822
谢廓然所言,可以见出朝廷党争之现实。不同党派人士主持科场,直接影响到科场文风,甚至有走极端的“穿凿”“虚诞”等现象。谢廓然建言的目的是纠偏,而非禁绝,依然能够体现出孝宗弥合党争的宗旨。
孝宗朝后期,朱熹等道学之士反对孝宗近幸弄权,卷入种种朝政内讧,道学再度成为攻击对象①。监察御史陈贾请禁道学,“由是道学之名,贻祸于世”[5],②。
综上所述,高宗、孝宗两朝虽有禁道学之说,但是或持续不久,或波及不广,尚未酿成党争大祸,对科场的影响也有限。
宁宗朝道学成为朝廷党争的分水岭。韩侂胄当政,大力排斥打击道学之士,酷烈程度超过以往,对科场影响十分重大。
宁宗即位,赵汝愚和韩侂胄皆有定策大功。赵汝愚信奉理学,时朝廷臣僚多理学之士。庆元元年(1195年)二月,赵汝愚罢相,在韩侂胄的主持下,全面禁绝理学之党争拉开大幕。“或又为言:‘名道学则何罪?当名曰伪学。’……学禁之祸自此始矣。”[4]2004庆元二年(1196年)正月,“刘德秀劾留正四大罪,首论其招伪学以危社稷。伪学之称自此始”[4]2008。
道学被定性为伪学,“党祸”演进为“学禁之祸”,直接祸及学校教育和科场考试。庆元二年科考是宁宗即位后的首次科举考试,“以吏部尚书叶翥知贡举,吏部侍郎倪思、右谏议大夫刘德秀同知贡举”[3]4242。三人秉承韩侂胄意图,通过科场考试肃清道学影响。例举二则材料:
省闱知举叶翥、倪思、刘德秀奏论文弊,上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并行除毁。”是科取士,稍涉义理,即见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4]2008-2009
宁宗庆元二年,韩侂胄袭秦桧余论,指道学为伪学,台臣附和之,上章论列。刘德秀在省闱,奏请毁除语录。既而,知贡举吏部尚书叶翥上言:“士狃于伪学,专习语录诡诞之说、《中庸》《大学》之书,以文其非。有叶适《进卷》、陈传良《待遇集》,士人传诵其文,每用辄效。请令太学及州军学,各以月试合格前三名程文,上御史台考察。太学以月,诸路以季。其有旧习不改,则坐学官、提学司之罪。”是举,语涉道学者,皆不预选。[1]3635
天下熙熙皆为利,“稍涉义理,即见黜落”,作用迅速,影响广泛。叶翥等甚至论及太学和州学的教育与考试。除了个别独立特行之士以外,多数考生要根据朝廷的风向标调整自己的学习内容和科场论文。“当时场屋媚时好者,至攻排程氏,斥其名于策云。”[6]细品叶翥等对道学的抨击,如读书破碎、语言诡诞、学问空疏、禅语欺人等,虽然也能道出追捧理学之士读书与写作的某些弊病,然而其根本目的是党同伐异,打击政敌,而不是为了端正学校和科场风气。这次科考之后,后来参加科举的士人,“前期取家状,必欲书‘委不是伪学’五字于后”[4]2017。如此无情排斥,不留余地,对科举影响之直接及巨大,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党争。
此外,他们要求严格遴选考官,剔除“伪学”之士。庆元四年(1198年)三月:
臣僚言:“比年以来,伪学相师,败乱风俗,所赖圣明力挽狂澜,一归于正。……科场主文之官,实司进退予夺之柄。倘或不知所择,使伪学之徒复得肆其险诐之说,则利禄所在,人谁不从?必至疑误学者。乞颁诏旨,将来科场,诸路运司须管精择议论正平、委非伪学之人,充诸州军考试官。仍开名衔,照应举格式,如涉伪学,甘置典宪,申尚书省、御史台照会。此去科场不远,乞下诸路漕臣,预先体访所属合差试官之人,究见是与不是伪学的实,庶几临期差拨,不至抵牾。”从之。[3]4602
此年各地举行发解试,臣僚上述奏疏因此而发。禁绝道学,从省试推进到发解试,从考生录取推进到考官遴选,法网越织越密。
“利禄所在,人谁不从?”利用科举排斥道学,在“官本位”体制中效果非常明显。“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4]2034众多学子纷纷与程颐、朱熹道学划清界线。
“稍涉义理,即见黜落”,大概仅仅是庆元二年科考之作为,或者有所夸张。庆元五年(1199年)科考已经有所松动。此年魏了翁第三名及第,“时方讳言道学,了翁策及之”[1]12965。韩侂胄等人的打击重点是朝廷官员中的道学之士,或者说是赵汝愚一党,科场禁令虽严,但仍有漏网者。魏了翁对此也有记载:
庆元五年,上始御集英殿,亲策进士。某与韩甲圣可、乐新子仁同舟而下,相与谋曰:“今事势已极,惟有忠正广大以作人才,安静和平以植基本。若相激不已,则天彝泯乱,人心愤郁,国亦随之。此而不言,是为有负。”或疑触忌干祸,而三人自矢靡他。奏入,有司第某为第一,寻置之第三,恩数仍视首选。甲、新皆乙科,授从事郎。[7]第311 册,128
魏了翁虽然不得状元及第,仍然是第三名高第。韩甲和乐新同时中第,此榜“稍涉义理”者并未一概黜落。
嘉泰年间,韩侂胄权位已经稳固,无需再利用“伪学”做文章,党禁有所松弛。“侂胄亦厌前事,欲稍示更改,以消释中外意。时亦有劝其开党禁以杜他日报复之祸者,侂胄以为然。”[4]2036嘉泰二年(1202年),“二月,弛学禁”[4]2039。此后,韩侂胄掌政期间之科考,就再也没有特别针对道学的言论或措施。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韩侂胄被诛杀,史官罗列其罪状,其一就是“以正学为伪学”[4]2065,为道学平反正名。随即,“雪赵汝愚之冤,……一时伪学党人朱熹、彭龟年、杨万里、吕祖俭虽已殁,或褒赠易名,或录用其后”[1]12417。宁宗朝围绕道学之诸多举措,至此大致告一段落。
二、盛行作弊
南宋后期科举制度之衰败,具体表现为科考环节中作弊盛行。所谓“据权势者以请嘱而必得,拥高资者以贿赂而经营,实学寒士,每怀愤郁”[3]4330。南宋后期科举制度,在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作弊手段冲击下,显得千疮百孔。
宋代科举考试是士人进入仕途的唯一正途。宋人甚至夸张地说:“不中进士举,无由得朝廷之官。”[7]第337 册,140士人万众一心,挤向科举考试之“独木桥”。而才力智商不及者、富贵多金者、有权有势之子弟,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群,总是期望通过一定的作弊手段,让自己更早更顺利地通过科举考试。只要有考试,就存在着作弊行为或作弊企图。换言之,宋代历朝科举考试都存在作弊现象。
然而,只有到了宁宗朝,科举考试作弊才达到盛行的程度,成为朝臣讨论科举制度时唯一的、持续的、反复的重大话题。这是宁宗朝之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宁宗朝臣僚奏疏所云“科举之弊,无甚于今日”[3]4320是如实叙述。笔者根据现存宋人科举文献资料,选取仁宗、徽宗、高宗、孝宗、宁宗五朝,对有记载的科举作弊事件和讨论的次数进行统计,说明宁宗朝作弊之盛行。之所以选取这五个时段,是因为这些帝王在位时间较长,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其间,徽宗、高宗、孝宗、宁宗四朝大致相连,可以看出宋代科举作弊之走势。具体统计如下:仁宗在位41年,有关记载共7 则;徽宗在位26年,有关记载共6 则;高宗在位36年,有关记载共15 则;孝宗在位27年,有关记载共15 则;宁宗在位30年,有关记载共53 则③。根据上述统计得知,南宋以来科举作弊现象在逐步增加,到宁宗朝则集中爆发。宁宗朝臣僚奏疏讨论科举作弊,往往是长篇大论,这也是以往所没有的。
首先是冒籍,主要是牒试冒籍。宋代牒试规定:“随侍见任守倅等官,在本贯二千里外,曰‘满里子弟’;试官内外有服亲及婚姻家,曰‘避亲’;馆于见任门下,曰‘门客’。是三等许牒试,否则不预。”[1]3628牒试虽有回避的作用,然解额较多,优待官员子弟之意非常明确。“官本位”体制下最大的作弊群体就是官员,宋代官员首先可以利用且风险最小的科举作弊手段就是牒试冒籍。孝宗朝曾多次整顿牒试,但是毫无效果,且愈演愈烈。
宁宗即位初,庆元元年八月:
臣僚言:“两浙州郡知、通避亲牒试,绍熙三年诸州所牒止五十人,今岁乃三百三十七人。夫以亲戚多寡宁不同,至于遽增六倍,则事理可见。乞付三省,令都司取两浙转运司两举人数,公共比照多寡,以今次所牒最多三数人职位、姓名将上取旨,或与罢黜,或与降官,或展磨勘,等第行遣。庶几稍肃官箴,稍严士则。”从之。[3]4526
仅以两浙路为例,相隔三年,牒试人数增加六倍有余,其间之冒滥,不言而喻。朝廷将其中的“所牒最多三数人”予以处理,以求杀一儆百之效果,本来就是放过多数作弊者的和稀泥行为,当然毫无作用。嘉泰二年三月:
御史台言:“庆元四年十月指挥,今后诸路运司牒试数多之人,令觉察闻奏。本台今据两浙运司开具今举诸州府知、通申到避亲赴试人数,比照数内牒试最多人,朝请郎、通判婺州汪德范牒一十四人,朝奉大夫、通判台州林谦牒一十三人。今照指挥,合行举觉。”诏:“汪德范、林谦各特降一官。”[3]4325
朝廷已经一再禁止,官员作弊仍然肆无忌惮,只能说明禁令未被落实,由此带来官员们的贪图侥幸。
终宁宗朝,牒试冒滥一直是臣僚们反复讨论的问题。举嘉泰二年之后的事例两则:
(嘉泰四年,1204年)右正言林行可言:“胄子之试,取人稍宽,岂非念其父兄莅官中都而优之欤?比年严期功之令,应牒颇艰,明注于榜帖之下,防闲亦密矣。既而复宽,厘务官所牒之员,待之甚厚。乃或非其本宗,矫揉冒滥,无复顾忌。果何取于胄子之名哉?……漕试之仍旧,正欲以优远方随侍子弟。今西北流寓,冒贯福建,类皆军中将校。书铺立价,仅出数千,便得一试,岂牒试之本意乎?”[3]4326-4327
(嘉定元年,1208年)刘宰《上钱丞相论罢漕试太学补试札子》:今之牒试,凡曰避亲,曰随侍,曰门客,鲜非伪冒者,而贩鬻者居其半。[7]第299 册,172
牒试成为官员贪赃敛财的途径之一,“书铺立价,仅出数千”“贩鬻者居其半”,这就能够解释为何一位官员牒十几位考生。封建专制体制下官场之腐败,通过科举牒试一端,就有非常充分的体现。
其次是挟书,又称怀挟。这就是偷偷携带各种文字进入考场,以便考试时抄袭,是最古老也是最普遍的考试作弊方式。宋代制度规定:“凡就试,唯词赋者许持《切韵》《玉篇》,其挟书为奸,及口相受授者,发觉即黜之。”[1]3605除上述韵书和字书外,不可以挟带其他文字进入考场。然而,挟书作弊永远禁而不绝,尤以宁宗朝以来为甚。摘取三则嘉定年间臣僚相关奏疏:
(嘉定元年,1208年)比年省闱取士,弊幸百端。最是挟书、代笔,尤为场屋之患。盖曩由宰相门客,怀挟败获,反将逻者施行。自后习以成风,绝无忌惮。又缘巡案例差局务小官,其曾应场屋者皆充对读,选择之余,方及巡案。势力既微,待遇又薄,全不加意。所差内侍,亦多官微位下,不能谁何。八厢目击其弊,类皆容隐。[3]4331
(嘉定三年,1210年)自侂胄窃权,内畏人言,纵弛试禁,邀誉士子。蝇头册子,山积案上,往来交加,无异阛阓。[3]4334
(嘉定九年,1216年)夫挟书有禁,旧制也。今郡至棘闱,日未及中,残编散帙,盈于阶戺。甚者,以经史纂辑成类,或赋、论全篇刊为小本,以便场屋。巧于传录者既以幸得,而真有问学者未免见遗。[3]4343
挟书作弊之严重,以至“习以成风,绝无忌惮”。考场所遗留的挟书,“蝇头册子,山积案上”“残编散帙,盈于阶戺”。这里提到的“蝇头册子”,是当时书商专门为科举考试作弊定制的小巧书册,以便挟书之用。北宋时类似定制,仅仅是个人手抄,“皆是小纸细书,抄节甚备。每写一本,笔工获钱三二十千”[8],规模有限。南宋则转为批量生产,规模惊人。南宋人云:“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率携以入棘闱,务以眩有司,谓之‘怀挟’,视为故常。”[9]嘉定十六年(1223年),国子博士杨璘亦言:“今书坊自经子史集事类,州县所试程文,专刊小板,名曰夹袋册,士子高价竞售,专为怀挟之具。”[3]4354宋代福建路建宁府,是当时图书刊印销售的一大中心,此地集中制作怀挟书籍,也是适应作弊盛行的市场需求。
最后是代笔,就是由他人替代答卷。其作弊方式大约有三种。
其一,考生与枪手同时入场,答卷完毕,互换试卷。嘉定六年(1213年),殿中侍御史石宗万言科场弊案:“封弥不谨,则有拆换家状之弊。”[3]4336嘉定十年(1217年),臣僚奏疏言及此类弊案,更为详尽,并提出对策:
日来多有冒名入场之人,颇骇人听。如甲系正名赴省,乙乃冒名入场。方州士子,纷揉错杂,书铺莫辨,安然入试,略无顾忌。十年之前,安得此弊?预榜之后,独有参验字踪真伪,非不严也。曾不知奸弊之生,出人意外。场屋制备卷,以防正卷之阙失。今乃预买备卷,冒名出试,则以场中之文,令正身誊上。及至中榜,计赂吏胥,抽换场中之卷,虽一二千缗,亦不惮费。吏辈为地,何计不遂!则比字踪之设,不足恃矣。备卷条印,通印卷首,以防拆换。此曹多是买下,或于帘前妄请,潜地袖与正身誊写。帘前纷陈之备卷,何所稽考?此弊之尤者,非怀挟、传义之比。乞下礼部,自今省试,只许监中印士人正卷。所有备卷,只许白卷纳入省场,令监试专差官监印,计数封起。引试之日,有请备卷,必逐名监给,抄上姓名、乡贯,以为后日稽考。私买、滥请之弊,仍令巡按等人巡缉。有正卷又请备卷,冒名入场人,必罚无恕,庶几伪冒可革。[3]4344
此种代笔作弊,有“冒名入场”“预买备卷”“帘前妄请”等花样繁多的手段,到了“略无顾忌”的地步。朝廷同意奏疏所提供的对策,只是一种被动应对的措施,即使贯彻实施,也只是预防“备卷”一项而已,无法根绝冒名代笔之弊。
嘉定元年(1208年),大理少卿费培言及考生与考场小吏趁“纳卷”之际串通作弊云:“吏辈肆奸,了无顾忌。欲拆换卷头,以甲为乙;誊写程文,以伪为真;受他人之嘱,毁坏有名试卷,亦可也。”[3]4332可见单一审核“备卷”不能根绝此类作弊。
其二,雇枪手冒名顶替,全程替考,即所谓“全身代名”[3]4353者。这应该是更加有势有钱者所为,省却了在场屋之内更换试卷等风险。嘉定元年,太常博士张声道较为详尽地揭示了此种作弊手段,云:
豪民上户,不务实学,专以抄写套类为业。广立名字,多纳试卷,将带笔吏,假儒衣冠,分俵书写,侥幸万一。至揭榜,或数卷两得,全中待补,则父子兄弟分认名目。及赴省试,则以多资换易试卷,或全身充代,窃取科第。[3]4331
“全身充代”,作弊者轻松中第。嘉定十二年(1219年),臣僚奏疏云“场屋弊极”,弊端之一就是“身不入场,榜出高中”[3]4346,指的就是这种代名考试。
其三,将考试题目外传,再将代答程文传入。方式大致也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考官锁院期间家书往来,挟带答案。嘉定六年正月:
臣僚言:“试院有平安历,不过以报平安。今则不然,其出也,所书项目,监门莫得而见;其入也,所传件数,监门莫得而稽。囊复封识,不知所藏何物。名为药裹,安知无简札往来?号为家书,安知无消耗漏泄?其弊有未易言者。嘉泰间,议臣亦尝推究关防矣,未闻许其发视而后通传。乞下所属,自今平安历早暮出入,监门官逐一点检,不许帕复缠裹,私自封缄。虽药贴家书,亦先开拆,方得收传。监试复视,则考试者无得容其私,就试者无以售其私。”从之。[3]4335
另一种是借助考场建筑空隙,传递答案。嘉定六年五月:
臣僚言:“贡院墙壁,本自低矮,年来颓圮。如西边一带,抵靠别试所晨华馆,而断垣及肩,践踏成路。传泄之弊,多由此出。最后正通大理寺前,居民搭盖浮屋于墙上,亦作弊处,莫可堤防。东畔墙虽稍高,却与封弥、誊录所相邻,而缝穴最多,关防须密。乞将贡院周围内外墙,并就旧基增筑高阔;里边掘成沟池,阔五六尺许,深浚亦如之。不惟得土筑墙,可省般运,而四傍潴水,亦可泄贡院卑湿。墙里加以池,则人不得而逾矣。仍约束居民,不得因墙起造浮屋,庶革传泄之弊。”[3]4336
代笔猖獗,其为害之烈,远超冒名和怀挟。冒名者,最终需要自身参加考试,只是钻漕试录取率更高的空子;怀挟者,还需自己有一定功底,以抄袭补不足;代笔则可以让完全不读书的纨绔子弟高中科名。开禧元年(1205年),臣僚云:“代笔之弊,最其甚者。显行贿赂,略无忌惮,或替名入试,或就院假手。故有身躐儒科,而不能动笔,污辱搢绅。”[3]4327又,嘉定十二年,右谏议大夫李楠言:“厥今之弊,曰传义,曰挟书,曰见烛,未若代笔,最失本意。盖科举以其业儒能文,而后设棘闱之防、门关之禁,监试有官,巡逻有人,堤防伺察,虑其有弊。今赂贿公行,代笔中选,十常二三。”[3]4346臣僚都一致认为科举作弊以代笔危害最甚。然而,“代笔中选”者高达“十常二三”,还是相当骇人听闻的,亦见宁宗朝科举糜烂之程度。
宁宗朝科举作弊手段多种多样,嘉定十六年,臣僚奏疏将其中最盛行的大致归纳为12种,云:
摭取其尤凡十二事陈之:曰门关,曰纳卷,曰内外通传,曰全身代名,曰换卷首纳白卷,曰吊卷,曰吏人陪《韵略》钱,曰帘内胥吏乞觅帘外胥吏,曰试宏博人怀挟、传义,曰诸色人之弊,曰帘外诸司官避亲,曰印卷子,谨条于后。[3]4353
宁宗朝科举弊案,举不胜举,科举制度大面积糜烂。
余 论
南宋后期科举之衰败,还表现在诸多其他方面,此处予以大概阐述。
其一,考官选差不当。考场的公平公正,既要依靠制度来规范,又要依赖考官来落实。宁宗朝臣僚对于考官的选差,曾发表过诸多言论。庆元元年:
臣僚言:“国家三岁大比,经义、诗赋分为两科,使各占其艺,以便多士,德之至渥也。惟差试官,有失立法之意。或全差治经而不差习诗赋者,或全差习诗赋而不差治经者,是以考校去取,间有枉被黜落,或滥中科名。今试期已迫,乞下礼部符诸路漕司,凡差试官,必经义、诗赋相半。虽远方小郡解额少处,亦不可使偏于一。收拾千人一律之腐语,识认同门共习之故文,怙势凭愚,故黜正论,连交合党,共取凶徒。甚者,秋闱敢举浮诞之说,发为策问,诳诱后学,遂使真贤实能见弃有司者太半。乞宣谕大臣,今后试官,须精加选择,委有文行,该通博洽可以服众,方严公正可以厉俗,始许以名闻。否则,科目前列,不在兹选。庶几学校科举自此少变,而朝廷收得人之实效矣。”从之。[3]4319
这则奏疏言考官选差之弊,涉及三个方面:考官或单治经或单习诗赋,不能公平公正录取考生;考官“识认同门”“连交合党,共取凶徒”;考官命题“举浮诞之说,发为策问”。前一点指出考官能力有所偏颇,造成录取不公;后两点则指出考官故意徇私,有违原则。其时禁绝道学,后两点显然针对道学之士而发。
此外,考官选差不当、各种作弊盛行、制度松弛败坏,还导致考官对待寻常试卷漫不经心。开禧元年,臣僚言:“比年以来,名为三场通考,往往考校之时,或倦披览之难遍,或局好恶之不同,经义、诗赋独取于一破题,舍是弗考。”[3]4327考官如此敷衍了事,考场不公便是常见现象。
考官以外,考场其他官吏选差,也有诸多弊病。如对读官“虽昏耄衰病,亦使备数”,誊录人“虽疾病癃老,不惯书写,俱不暇问”[3]4330,甚至“誊录者毁弃试卷”[3]4334。考场其他官吏,更有利用手中权力参与作弊者。开禧三年,臣僚奏云:“监门官……率小官下吏,寡少廉耻,将所给字号,为高资者得之,前途伺候,以行私嘱。”[3]4328这些官吏,或昏聩,或利用职权牟利,他们共同敲响了宋代科举制度的丧钟。
其二,经义合题荒唐。宋代试场各种考题和模范时文,以传抄、印刷等多种手段流行,考生反复记诵,应对考试。考官为了防止考生依赖记诵范文而中第,力求出题花样翻新。经义可供出题者终究有限,而诗赋考题相对难以重复,遂有合题一说。庆元四年:
臣僚言:“近者臣僚有请,自今试场出六经合题,深中场屋之弊。但本意正恐题目有限,士子得以准拟,返使实学不能见一日之长。臣谓若出合题,则合题亦自有限,士子仍旧准拟。乞下礼部,令遍牒诸路,自今出题,或尽出全题,或三篇中欲合一题,听从有司。庶几不致拘泥,不为举人所测。”从之。先是,礼部侍郎胡纮言:“国家三岁大比,以经义、诗赋笼天下之士,群试于有司者,必精通所习之业,可以中选。今之诗赋,虽未近古,然亦贯穿六艺,驰聘百家,有骈四俪六之巧。惟经义一科,全用套类,积日穷年,搜括殆尽,溢箧盈箱,无非本领。主司题目,鲜有出其揣拟之外。欲令有司,今岁秋试所出六经,各于本经内摘出两段文意相类、不致牵强者,合为一题,庶使举子有实学者得尽己见,足以收一日之长。而挟策仇伪者,或可退听矣。”从之。至是臣僚复有请焉。[3]4322
经义考试命题的窘境乃是“积日穷年,搜括殆尽,溢箧盈箱,无非本领”。“题目有限,士子得以准拟”,为了做到“不为举人所测”,于是要求从不同经书中摘取两段文字,拼凑到一起,成为新的考题,此即为合题。合题的要求虽然是“两段文意相类、不致牵强者”,实际操作中往往走样,合题演变为断章或牵强关题。嘉泰元年(1201年)臣僚奏云:
命题之际,或于上下磔裂,号为断章;他处牵合,号为关题。断章固无意义,而关题之显然浑成者,多已经用,往往搜索新奇,或意不相属,文不相类,渐成乖僻。士子虽欲据经为文,势有不可,是有司驱之穿凿。[3]4325
嘉定四年(1211年),国子祭酒兼权刑部侍郎刘爚奏云:“近年经学不明,命题断章,学者以巧于迁就为工,不以推本经意为正。……今后命题,不许断章,长短不拘。”[3]4334经礼部审核,颁为诏旨。然科场合题断章,已成为许多考官的偏好。嘉定十五年(1222年),秘书郎何淡奏:“为主司者,但见循习之文多,可命之题少,于是强裂句读,出其所不拟,专务断章,试其所难通。”[3]4350国子博士钟震等聚议时亦云:“场屋命题,多是牵合字面求对,更不考究经旨。”[3]4350可见合题断章之弊,至宁宗朝末年依然流行。
其三,童子科冒滥。宋代科举设有童子科,专门考试,选拔聪颖早慧、天资过人的儿童。“神童:十岁以下能背诵,挑试一经或两小经,则可以应补州县小学生。若能通五经以上,则可以州官荐入于朝廷,而必送中书省复试,中则可免解。”[10]一时之间,父母趋之若鹜。宁宗朝童子科之冒滥,屡见于臣僚奏疏。嘉定五年(1212年),臣僚奏云:
童子一科,近年应举者源源不绝,此皆明作人“小子有造”之效,然有恩数太滥之弊。照得童子能背念九经者免一解,兼讲说书免两解。今之所讲说者,不过父兄以讲义与之诵念,实未尝通晓义理。以背念九经方免一解,背念一经讲义亦免一解,是以讲说免者不其太侥幸乎![3]4466
嘉定十四年(1221年),臣僚再奏云:
迩来应是科者,或年至十二三,甚而十四五,俱冒称十岁以下。方居髫龀,而已示之以诳,异时见诸事业,欲其著诚去伪亦难矣。矧自己卯讫辛巳,仅逾二载,而取中者已四十有六。冒滥若此,顾足以为贵乎?[3]4467
朝廷因这道奏疏,诏云:“自今后童子举,每岁以三人为额。”[3]4467这项诏令,未见推行之文献记载。反而,宋末因礼部侍郎李伯玉言:“人材贵乎善养,不贵速成,请罢童子科,息奔竞,以保幼稚良心。”[1]896咸淳三年(1267年),罢童子科试。此时,离南宋灭亡仅十多年时间了。
宁宗朝科举制度之糜烂,渗透到所有环节,不胜枚举。再举两个特殊案例以见之。
宋代科举殿试通常都在三月,廷对唱名或三月或四月,大致在这个时间段内。偶因特殊原因改期,如南渡前期有因为战争及朝廷流亡而延后考试者。宁宗朝后期殿试虽然都在三月,廷对唱名却经常性延后。嘉泰二年始,此后多数廷对唱名都延至五月,嘉定十三年(1220年)再延至六月。究其原因,非常简单,类省试考生没有如期来到临安,为等待这些考生,廷对唱名只得延期。再追究这些考生迟到的原因,就令人啼笑皆非了。嘉定十五年,臣僚奏云:
臣采之舆论,以蜀士迟迟而来,盖自有说。在法,凡赴廷对,许量带税物随行,以助旅费。向也一舟五六人共之,行计易办。后来人各一舟,货物未足,卒难起离,遂成濡滞。夫不汲汲于功名,而孳孳于财利,则是未入仕已丧所守矣。[3]4388
为了解决部分家境窘迫的类省试考生赴京考试或廷对唱名的费用问题,朝廷允许考生携带免税货物,以长途贩运获取利润。宁宗朝后期,这项政策在实施中变味,相当多的考生追求利益最大化,尽量携带更多的货物,赴考兼贩运,未入仕途,先求财利。由此造成大量考生迟到,朝廷只得一再延期廷对唱名。同年,臣僚奏疏又云:
向者,士子必四五人共为一舟,舟楫易办。数举以来,或一二人为一舟,舟人浸成稽缓。水陆万里,风波险阻,涉历州县,关津滞留,势必至夏,始达行都。数蒙睿旨,展期以俟其集。盛夏炎赫,皇上临轩,汗透御服,臣子殊不遑安。嘉定七年、十三年,臣僚屡次申明,而玩弛既久,终未能革。[3]4387
据此奏疏,这个问题早就已经引起关注,却“玩弛既久,终未能革”,一直拖延到宁宗朝末年。考官和考生在考试过程中,皆“孳孳于财利”,对制度有极强的破坏作用。
另一特殊案例是开禧元年殿试毛自知状元及第,至嘉定元年降至五甲末:
诏:“毛宪落职放罢,毛自知降第五甲,追还第一名恩例。”既而,以臣僚言:“……往岁陛下亲策多士,毛自知唱名第一。公论籍籍,皆谓自知本名自得,冒其弟之解,叨预奏名。其父宪时为都司,与苏师旦素厚,经营传出策题。前期策成全篇,宪之笔居多。差为编排,文字可认,优批分数,遂膺首选。自知无以报师旦私己之恩,亲造其门,拜而谢之。都人至为歌词讥诮,喧传众口。师旦复与为地,除宪察官,而怀不平者始不敢言矣。方乙丑之春,边陲清晏,两淮、荆襄、全蜀之民熙熙如也。自知献策,以为:‘天亡此胡,决在此一二年。今不乘其机以定中原,窃恐必有豪杰之士仗大义,据关中,以令天下者。’又虑议不坚决,复于终篇言庙堂之势未尊,台谏之权未重,意欲钳天下之口而决用兵之策。不知自知何所见而然耶?自知趋媚时好,以取世资,谋身则善矣,如社稷生灵何!”[3]4384
这一弊案涉及冒籍、泄题、代笔、暗记、迎合权臣等关节,成为宋代科举史上的荒唐笑柄。高宗朝虽亦有秦桧之孙秦埙等科举不公、事后被处理的事件,然状元被处置,两宋唯此一例。
宁宗朝科举制度之衰败是南宋政权衰落的重要一环,朝廷后继乏人,南宋政权的日趋衰落,不言而喻。辛弃疾《摸鱼儿》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正是对南宋后期国势形象而确切的描述。实际上,南宋自高宗、孝宗二帝之后,颓势便无可挽回。以朝政角度而论,太祖以来建立的帝王之下集体领导制和台谏监督制被破坏无遗,皇帝昏庸,权奸当道,贿赂公行。大权独揽的相臣,又以党争的借口排斥和打击政治异己,从而对当时的文化和教育事业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影响,科举制度当然也不可幸免。以外事战争角度而论,元人兴起,大兵压境,疆土日蹙,直至亡国,宋代科举制度也随之衰落而走向终结。
注释
①参看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5-98 页。②道学党争,参看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8-120 页。③统计数据来源于诸葛忆兵编著:《宋代科举资料长编·北宋卷》上册,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257-595 页;《宋代科举资料长编·北宋卷》下册,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966-1137页;《宋代科举资料长编·南宋卷》上册,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307 页;《宋代科举资料长编·南宋卷》上册,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311-615 页;《宋代科举资料长编·南宋卷》下册,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671-911 页。按:帝王在位年数采用四舍五入统计法。又,数则资料记载同一事件,合计为一次。
——嘉定竹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