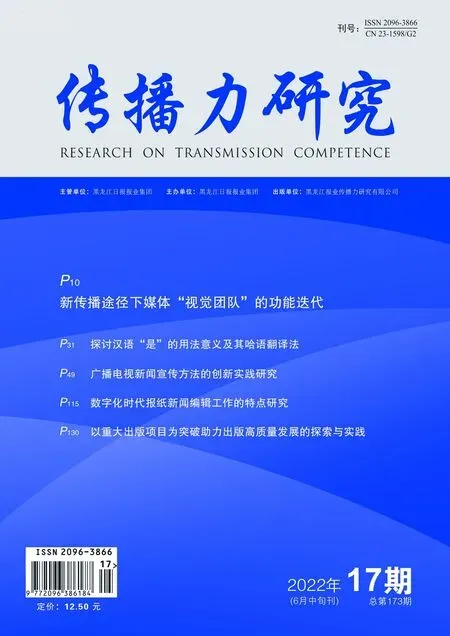身份认同的找寻与建构:从霍米·巴巴的文化位置观看《绿皮书》
◎薛 柯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7)
电影《绿皮书》根据真人真事改编。1962年,非裔钢琴家唐·谢利博士准备从纽约出发,向南开展全国范围的巡回音乐会。在种族隔离制度尚未终结的年代,唐·谢利雇了意裔托尼·维勒欧嘉作为司机兼私人助理在旅程中保护他的安全。一路上,两人互相了解、扶持,共同度过了许多难关,建立了跨越种族和阶级的友情,并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建构。20世纪,美国的殖民统治给非洲裔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到如今,横亘在美国社会中的种族鸿沟依旧没有弥合。白人至上的社会秩序下,黑人在信贷、教育、执法等众多社会领域仍然遭受着歧视和暴力。电影《绿皮书》帮助人们了解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社会风貌,思考被殖民主体和殖民主体的身份认同问题,也使人们重新反思当下的种族问题。
霍米·巴巴的文化位置观是对其文化翻译理论结果的进一步阐发。巴巴认为,模拟作为一种文化翻译的手段,为殖民主体和被殖民主体的身份带来混杂性,由此产生认同上的矛盾状态。但同时,文化翻译的过程中会打开一片“罅隙性空间”,通过占据这片混杂性的、居间的空间,可以实现文化意义的再现。
一、研究方法
(一)对象
本文将以电影《绿皮书》中两位主人公唐·谢利博士和以托尼·维勒欧嘉的为代表的白人群体人物的身份认同意识和行为作为研究对象。
(二)方法
本文将采用文本分析法,观察总结电影主人公作为被殖民主体和殖民主体的自我身份的找寻与认同行为,借助霍米·巴巴的文化位置观理论分析其身份认同的转变,探究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建构。
二、研究结果
(一)被殖民主体的身份矛盾
1.主动的模拟
霍米·巴巴指出,有两种文化翻译。一种是指作为殖民者同化手段的文化翻译,另一种是后殖民批评家所提倡的作为文化存活策略的文化翻译。模拟时常被当作殖民主体进行强势文化翻译的手段,成为一种殖民控制形式。殖民主体要求被殖民主体采纳霸权即殖民主体的文明,譬如,价值观、宗教、风俗等,摒弃自己的文明与信仰。他们建立起压制性行政管理及教育制度,通过让被殖民文化拷贝或“重复”殖民者的文化来覆盖殖民地的异域文化,实现思想、社会风俗上的高度统一,完成教化的使命,以便更好地征服新空间,巩固统治。
电影《绿皮书》中的主人公之一,杰出的非裔黑人钢琴演奏家唐·谢利可以被视作一个被殖民主体在殖民主体文明的教化下,认可殖民主体文化,并主动进行模拟的例子。他从小接受古典音乐教育,获得了三个博士学位;艺术造诣深厚,多次受邀到美国白宫进行钢琴演奏;生活优渥,生活起居一应有白人管家照料;谈吐不凡,深谙上流社会的社交礼仪与文化……他对美国精英阶层的文化始终呈现积极模拟的态度,在教育背景、经济及社会地位上俨然跻身上层社会,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中远离了底层黑人社区,在精神生活上远离了黑人族裔文化。不论是在心理上还是行为上,他都贯彻着白人的思考方式与行为准则,通过模拟塑造了自我的精英形象。
2.缺失的认同
虽然唐·谢利在艺术上有着极高的造诣,但他黑色的皮肤注定不会被白人群体完全接受,在现实生活中屡遭种族歧视。在罗利,他只被允许用树林里的厕所;在路易维尔,他在酒吧喝酒时被三个白人男子挟持并羞辱;在日落镇,他因日落后内不允许出现黑人而被针对;受邀在伯明翰演出,他不被允许坐进餐厅吃饭……白人群体对他的态度与他对殖民主体的文化模拟程度的高低并无关系,只因为他有着黑人的基因,生存空间与自由就不得不面对巨大的挤压。
没能在白人社区中立足,唐·谢利在黑人同胞中同样面对着不被认可的境地。西装革履、出行有白人管家跟随左右的他与作为被雇佣者、地位低下廉价黑人劳动力之间有着巨大的身份割裂,当与他们无声地对视时,贫苦的黑人们的目光复杂又不解。他时常因没有人陪伴而感到孤独,独自一人在阳台喝威士忌,看着楼下玩闹的黑人同胞。但当其他黑人向他发出一起玩的邀请,他又无法说服自己降低身份加入他们的行列,故遭到了鄙夷和谩骂。他无法融入底层黑人的群体,不认可他们的生存方式与文明,黑人们亦没有将他视为同胞。
由此可见,唐·谢利通过模拟习得的个人文化中带有的明显混杂性,让他处于白人与黑人社区的中间地带,不仅缺乏殖民主体文化的认同,也缺乏被殖民主体文化的认同。
被殖民主体对殖民主体的模仿不可能完全成功。被殖民主体的原始身份和文化残留决定了模拟殖民主体文化的人塑造出的个人形象是介于与原体的相似和不似之间的“他体”,既带有“被殖民”的痕迹,又与难以摆脱本土的特征,甚至出现从模拟走向“戏弄”的趋势。这种文化的混杂性导致了唐·谢利面对身份问题时的巨大矛盾,他没有收获身份认同,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在当唐·谢利与托尼争执时,他绝望地大喊:“我独自受苦,因为我不被同胞接受,因为我不像他们。如果我不够黑,不够白,不够男人,那么告诉我,我到底是谁?”振聋发聩的呐喊让他积累数十年的矛盾、屈辱、崩溃一瞬间爆发,充分表达出他无法活得自我认同和位置的痛苦与迷茫。
(二)殖民主体的身份混淆
1.纠结的模拟策略
霍米·巴巴在文化位置观中将“殖民话语的矛盾性”表述为:“既然殖民者的模拟策略总是要求属民与殖民者保持足够的差异,以便继续有臣民可以压迫,那么它就永远也不会完全成功。”殖民主体一方面打着文明教化的旗号,试图用自己的文化规训被殖民主体;另一方面又害怕他们被改造成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这就证明他们秉持的种族差异和劣等性概念是错误的,也证明他们的殖民话术是虚伪的。同时,又因为模拟的运作发生在情感和意识形态领域内,故而它与严苛暴政和赤裸裸的镇压杀戮有所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殖民地人民加以利用,害怕被殖民主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此,巴巴指出“殖民权力和知识是最难以把握也是最有效的策略之一。”
有了上述考虑,殖民主体的模拟策略往往是纠结的。殖民话语一方面鼓励并引导被殖民主体通过模拟殖民主体进行自我改进并逐渐接近他们的“优雅文明”,但另一方面殖民者则用种族差异和劣等性概念对这种改进与接近进行否定和抵制。如同电影中,虽然唐·谢利已经通过主动地完成了对殖民主体文化的高度模拟,但是白人群体仍然拒接给予他平等的地位和待遇。只因白人不愿意接受一个黑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就与他们平起平坐,通过种族歧视的方式暗示唐·谢利:你依旧来自劣等的民族。
2.两面增势的矛盾状态
然而,以唐·谢利为代表的精英黑人的出现还是给白人群体带来了恐慌和惊异。尽管许多邀请唐·谢利进行演出的白人对他黑人的身份有所顾忌,但都不得不承认他的艺术造诣是普通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出身于市井、混迹在夜总会打工的托尼在为唐·谢利工作前十分排斥黑人,将来家中工作的黑人工人用过的水杯扔进了垃圾桶。但在接受唐·谢利的采访时,他就对这位黑人拥有的资产与教养感到诧异。虽然拒绝了对方提出的雇佣要求,但与之交流的态度已经不同于对待普通黑人。在旅行中,唐·谢利数次纠正托尼的不文明行为,制止他偷窃的行径,并指导他用优雅的词句与妻子通信……经过长久的陪伴与扶持,托尼完全接纳了唐·谢利,并多次出手援助、支持他。
这种转变证实了巴巴的文化位置观中极具创新性的一点:被殖民主体对殖民主体不一定总是减势的,而是“两面增势的”,这种矛盾状态的结果是被殖民主体对殖民主体同时具有吸引力和排拒力。由于殖民主体的文明并不是尽善尽美的,殖民者在生活实践中也经常会产生误差与偏失。如作为白人的托尼粗鲁、自大、爱使用暴力。同时,被殖民主体在接受文化翻译时展现出了强大的学习天赋和主动性,这使得他们的不完全处于劣势地位,如德才兼备的唐·谢利。这种矛盾状态打断了殖民统治泾渭分明的权威,打乱了人们通常认为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简单关系。于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优越与自卑、纯正与掺杂、模仿与戏弄的矛盾状态中,经常形成一种既排斥又吸引的依存关系。
巴巴的文化位置观还指出,当部分殖民主体看到俨然成为自己影子般投射的被殖民主体之后,在道德的层面上会形成一种罪恶感与优越感交互混杂的模糊状态,从而改变自己对他们的看法与态度。在看到老板被旅旁酒吧里的白人欺侮时,托尼感到不公和愤怒,立刻站出来用暴力制止了他们的行为,将唐·谢利解救出来,并叮嘱他以后不论去哪里都要带上自己。由此可见,面对具有进步性的、高度模拟的被殖民主体,殖民主体会对被殖民主体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态度也会随之发生转变。
(三)双重身份的建构
上文提到,殖民主体与被殖民主体都处于不同程度和形式的矛盾状态中。因此,在强制性的文化翻译过程中,殖民主体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权威,被殖民主体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受害者。通过双方不断的文化商讨和交流,总会产生某种对抗和抵制的可能性。
因此,巴巴在文化位置观中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巴巴认为,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会打开一片“罅隙性空间”,通过占据这片混杂性的、居间的空间,可以实现文化意义的再现。这里所说的罅隙的、混杂的和居间的空间其实就是“第三空间”。这是个人或群体的自我地位得以阐述的策略性跨文化空间,是在不同的状态之间存在的一个持续不断的运动过程和交流过程。这种认同绝不是简单的从单一的某种认同到另一种认同的运动,而是不断的接触往来、争斗和挪用的过程,也就是后殖民论者常说的文化商讨过程。
面对二者的身份建构问题中,巴巴推崇一种“双重身份”的策略。双重身份并不是某人真的有着两个不同的身份,而重在指出:身份的协商具有重复性,有时候需要连续地重复、不断地修订和重新定位。在影片的最后,唐·谢利就完成了自我的找寻和双重身份的建构。通过一路南下巡演,他受到的种族歧视愈发严重。而伯明翰,作为演出嘉宾的他却只能在杂物间休息,也不被允许进入餐厅用餐。从前面对此种境遇,他都选择默默接受。但经过了雨夜与托尼关于身份认同的争执与交流,这一次他选择主动向餐厅经理表达自己需要进入餐厅用餐的合理需求,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在引发冲突并被不断拒绝后,他果断选择不再为他们提供演出。这一晚,他第一次尝试走进底层黑人的聚集地橘鸟酒吧。在这里,向来只演奏斯坦威钢琴的他在酒吧老板和托尼的鼓励下在酒吧的简陋钢琴上弹奏了古典音乐,而不是唱片公司要求的流行音乐。他高超的演奏技术立刻获得了在场黑人的欢呼,许多黑人拿着乐器上台与他一同合奏。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合奏的曲目正是唐·谢利和托尼出发伊始时托尼播放的黑人音乐,彼时唐·谢利还对它一无所知。影片的最后,他达成了与自己的和解,在保持原本的涵养、素质不变的前提下,逐渐接受黑人底层文明,主动融入到黑人社群文化中。通过与殖民主体的文化和被殖民主体文化的多次协商,唐·谢利在文化实践中建构了自我的双重身份。而一开始极度排斥黑人的托尼,也因唐·谢利的相处而不再对黑人种族怀有歧视与敌意,甚至多次主动维护唐·谢利,并欢迎他来自己的家中一起过圣诞节。作为殖民主体的一员,他也经历了矛盾状态,但却在文化协商中转变了偏见,对自我和唐·谢利的身份都有了全新的认知。
三、结语
不论是过去殖民地的受奴役者和被压迫者,还是现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难民、少数族,都面对着被挤压的生活空间和缺失的身份认同问题。他们“既是此又是彼”,或者既非此又非彼,身陷于文化翻译的动荡过程之中。他们居住于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于矛盾和冲突的传统中尝试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正是这种生发性的文化转换,为这些“移民”赢得了宝贵的后殖民视角,将他们置于一种“阈限性”空间,开辟出一片批判性思考的新天地。《绿皮书》带来的,不仅是人民对被殖民主体的思考,更是对殖民主体文化翻译过程与身份建构的反思。自我身份的找寻和建构在后殖民背景下固然困难,但后殖民文化认同的边缘视角需要被看到,需要被阐发,这也许是这部电影带给人们的重要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