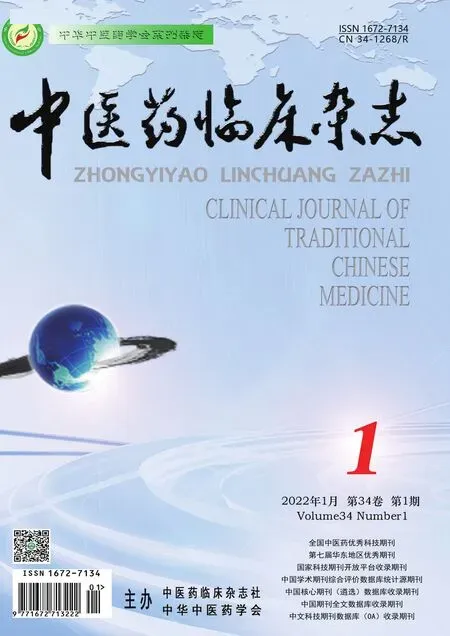青龙摆尾针法治疗中风后肩手综合征疗效观察*
李慧惠,王颖 ,计海生,刘秀秀,韩为
1 安徽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 安徽合肥 230038
2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合肥 230061
中风后肩手综合征(Shoulder-hand syndrome after stroke,SHSAS)通常认为是脑卒中后1~3个月内最好发的并发症之一,早在中风后的第三天,迟至6个月后均有本病的相关报道[1],发生率为12.5%~70.0%[2],其主要的临床特点为患侧上肢骨关节疼痛伴运动受阻,同侧腕、指及手背肿胀引起局部皮肤变红潮热,日久失治可致局部肌肉萎缩及肢体挛缩畸形,最后发展为永久性功能障碍[3],给患者的身体和心理带来极大的伤害。目前中医针灸治疗脑卒中后遗症的优势已得到广泛的认可,且传统针灸理论也随着时代在不断完善与发展,笔者将改良版的“青龙摆尾”针法应用于本病的治疗,并与常规针刺手法做对比,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效,并为中风肩手综合征的诊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
从2019年11月至2020年12月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一科收治的病人中选取符合标准的观察对象共计60例。根据入选顺序按照1:1的比例使用电脑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配,每组各30例。治疗组与对照组分别采取青龙摆尾针刺手法和常规的平补平泻手法。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病情的分布情况经卡方检验和t检验,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1。
表1 2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表1 2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注:组间比较,P>0.05。
组别 例数 性别/例 年龄/岁 病程/d 病情(例)男 女 脑梗死 脑出血对照组 30 19 11 57.48±8.62 48.23±5.32 18 12治疗组 30 16 14 57.60±7.75 48.47±6.08 17 13
2 诊断标准
2.1 中医诊断 中风的诊断标准依据中国中医药管理局脑病协作组《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分标准》[4]。中医证型参照《中医内科病证诊断疗效标准》[5]气虚血瘀证。主症为面色发白,气短乏力,局部肿胀疼痛;次症为功能受限,见瘀血斑;舌质暗或有瘀斑,苔白或有齿痕,脉弦或细涩。
2.2 西医诊断和分期 脑卒中的诊断标准依据第四次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6],所有参与本研究的病例均结合CT或MRI检查结果确诊为脑梗塞或脑出血。肩手综合征的诊断标准《脑卒中的康复评定与治疗》[7]中关于本病的诊断标准:①多发生在脑血管疾病的1 ~3个月内;②患手浮肿疼痛,颜色呈粉红色或暗紫色伴有皮温升高等血管舒缩功能改变,肩关节疼痛,并使关节运动受阻;③局部没有外伤、感染及周围血管病的证据。分期标准[8]:Ⅰ期:一侧上肢骨关节疼痛,运动范围很快明显受限,同侧腕、指及手背肿胀可引起局部皮肤变红潮热;手及手指弯曲时疼痛剧烈难以忍受,手指呈现强迫伸直位;Ⅱ期:突然表现为进行性加重的软组织肿胀,肌肉萎缩并逐渐发展为关节僵硬,关节活动日益受限;Ⅲ期:最为严重,手指屈曲挛缩,活动能力永久丧失,形成固定的有特征性的畸形手,皮肤蜡样营养不良性改观。
3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3.1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中风和肩手综合征的诊断标准;②符合肩手综合征Ⅰ期的诊断标准;③年龄35~75岁,病程在6个月以内者;④生命体征平稳,无言语功能障碍,神志清醒,治疗合作者;⑤受试者理解并自愿参加本次研究。
3.2 排除标准 ①不合符以上诊断和纳入标准者;②原发病为非脑血管疾病;③妊娠及患有严重心脏病、精神类疾病或有严重出血倾向者;④无法耐受针刺,不能正常交流者。
4 治疗方法
基础治疗:2组受试者均采用脑卒中的一般治疗方案予以抗凝抗动脉硬化、改善脑供血及脑代谢、营养神经对症处理并防控三高等基础疾病,降低并发症对本病的影响。
4.1 治疗组(青龙摆尾针法) 取穴:肩髃、肩髎、肩贞、臂臑、曲池、合谷、手三里。针具:选用规格0.30mm×40mm的(天协牌,GB2024-94,苏州天协针灸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次性使用无菌针灸针。操作:嘱受试者平卧或坐位,对针具和针刺部位进行消毒,一穴一棉球。进针后施行青龙摆尾手针刺手法,确保针感循经扩散,手法施行完毕后留针40min。周一至周六每天治疗1次,周日休息,6d为1个疗程,合计4个疗程。
青龙摆尾针法:调整患者呼吸,随咳下针。当医者针下有沉紧、涩滞感,患者亦有酸麻重胀的自觉反应时,将针退到穴位浅层(天部)。按倒针身,使之与皮肤呈30°~50°,肩三针及臂臑穴处针尖指向肩关节,手三里、曲池针尖指向肘关节,合谷穴处针尖指向腕关节。右手拇食二指捏住针柄,不进退、不提插,向左右慢慢摆动,摆动幅度在45°以内,往返摆针似行舟之摇橹。再分层进针:进针时按天三(腧穴浅层3次)、人九(腧穴中层9次)、地六(腧穴深层6次),退针时按地九(腧穴深层9次)、人三(腧穴中层3次)、天六(腧穴浅层6次)行针。每层行针3遍,共54次。
4.2 对照组(常规针刺组) 采用与治疗组相同的穴位、针具、进针方向及角度、深度。针刺当患者产生酸麻重胀的自觉反应时,手法行均匀的提插、捻转,捻转的角度在90°~180°,提插的幅度尽量要小,捻转与提插同时进行,即平补平泻。手法操作时间同治疗组,操作完毕留针40min。周一至周六每天治疗1次,周日休息,6d为1个疗程,合计4个疗程。
5 观察指标
5.1 疗效评定标准 参照肩手综合征评定标准[9]:基本治愈:临床症状消失,活动不受限;显效:腕手红肿基本消失,患侧肩手关节痛感显著减轻,关节主动及被动运动范围明显扩大;有效;患肢红肿胀痛略微缓解,上肢骨关节运动受限稍改善;无效:症状无改善。
5.2 评价指标 ①采用改良Fugl -Meyer量表(FMA)评估两组治疗前后患侧上肢骨关节运动状况,分值0~66分,评分越高,表示上肢骨节活动范围越正常[10];②采用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AS)评估两组治疗前后痛感强弱,分值0 ~ 10分,评分越低,痛感越轻[11]。③采用Barthel指数表评价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总分100分,评分越高,对生活的依赖程度越低[12]。
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内比较用配对t检验,组间比较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等级资料用卡方检验,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 2组中风后SHS患者运动评分(FMA)、疼痛评分(VAS)比较
见表2。
表2 2组患者FMA、VAS评分比较()

表2 2组患者FMA、VAS评分比较()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组别 例数 FMA评分VAS评分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对照组 30 37.65±7.83 45.13±8.01★ 7.09±1.35 4.57±0.94★治疗组 30 38.63±6.86 49.70±6.60★△ 7.12±1.74 2.93±0.79★△t-0.515 -2.416 -0.076 7.306 P 0.608 0.019 0.940 0.000
2 2组中风后SHS患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评分比较
见表3。
表3 2组患者治疗前后ADL评分比较()

表3 2组患者治疗前后ADL评分比较()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t P对照组 30 46.63±5.63 59.17±7.10◇ 8.440 0.000治疗组 30 47.53±5.85 67.57±9.23◇◆ 10.6320.000 t-0.604 -3.952 P 0.548 0.000
3 2组中风后SHS患者疗效比较
见表4。

表4 2组患者治疗前后疗效比较
讨 论
中风后肩手综合征(SHSAS)是脑卒中后跌倒、精神错乱的第三大并发症,如不及时干预则可发展为肌肉萎缩,前臂挛缩畸形,进而致残[13]。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相关研究[14]包括: ①交感神经刺激学说,认为急性脑血管意外刺激交感神经,引发血管痉挛;②“肩-手泵”受损学说,认为因肌无力而导致手泵机能障碍,引起上肢血液回流障碍;③继发性损伤、腕关节过度屈曲、内分泌功能失调等多种因素。目前西医对本病的治疗包括物理康复、手术治疗 、药物(关节腔激素注射、非甾体抗炎药物、抗抑郁及抗焦虑药物等)。但康复率不高,且手术容易导致粘连等问题。单纯的抗炎药物虽可缓解症状,但治疗周期长,患者还易产生耐药。长期应用激素可能会引起库欣综合征、骨质疏松、严重者诱发癫痫或精神病。而对于精神类药物,患者易产生依赖,突然撤药还会引起反跳现象及严重的戒断综合征。
本病根据其表现,古代医家将其归于“臂厥”“痹证”“偏枯”的领域,并指出SHSAS的主要发病机制为中风后久卧伤气,气血不足无以滋养筋脉,气虚无力行血,血运不畅遂而瘀结于腠理经络。出现“失养”与“不通”而致疼痛。瘀血日久化水,水气趁虚而入溢于肌表,滞于下而腕指肿胀。根本原因在于“虚”和“瘀”病久入络,即气血亏虚为本,气滞血瘀为标,经脉“不通”与“不荣”兼见。血气不充,经气不利则肝脾肾无以为养,可见筋弛肉缩骨痿。故病位在经筋,累及肝脾肾三脏。手三阳经均与此相关:首先中风后肢体萎躄不用,多因气血亏虚,治疗首选多气多血之阳明经,又因阳性主动,取之可激发阳气,补气活血,濡养筋脉以达扶助正气止痹痛之功;三焦气至则脉络通水道利,取其穴可加快水液代谢以达消肿之效。“小肠手太阳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出肩解,绕肩胛,交肩上”,说明经络与肩、手部功能活动密切相关,为针灸取穴提供了理论依据。临床以痰热瘀滞、痰瘀阻络、气虚血瘀、风寒阻络四型最为多见[15]。根据其病机治宜理气活血舒筋,补虚泻实,处方选取患侧手三阳经穴肩髃、肩髎、肩贞、臂臑、曲池、合谷、手三里。其中肩三针可疏通肩臂部气血,舒筋活络;臂臑、曲池、手三里均属阳明经,有益气活血,濡养肘部筋肉之功;合谷利水行气消肿。现代研究表明针刺肩三针及臂臑穴实际是对三角肌束的刺激,并通过反射中枢改善上肢动脉壁弹性及末端血供,减少促炎因子释放,达到中枢性镇痛的效果[16]。针刺手三里可通过松解拘急的结缔组织以活血消肿,其提高痛阈的机制与类吗啡性神经递质的释放有关[17]。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实验证明了曲池穴具有治疗半身不遂和慢性疼痛等病症的中枢功能机制[18]。针刺合谷穴可诱发瘫痪侧肌梭兴奋,通过脊髓传导通路实现对低位中枢调控,进而促进偏瘫侧手功能恢复[19]。
青龙摆尾针法首载于徐凤的《金针赋》:“一曰青龙摆尾,如扶船舵,不进不退,一左一右,慢慢拨动……”因其左右摇摆针柄以带动针尖游于病所似青龙摇晃巨尾而得名,为“飞经走气”四法中第一法。笔者是在徐凤的基础上,参考焦杨[20]的青龙摆尾法,其创新之处在于将三才分层、九六之数、捻转摆动等手法结合一体,是一种覆盖面广、强度高的刺激方法,使气的交流传导之力达到最佳。郭鑫等[21]提出:得气并非治疗的目的,气至才是针刺治病的真谛。针刺后得气仅是针刺治疗的第一步,第二步则需要施行手法运气到邪气之所居处,使“气至病所”。通过青龙摆尾法可引导经气可慢慢地沿经络循行流至患病之处,一方面刺激沿经之气血使经络得到滋养以达补虚之功,另一方面气可推动血液运行来冲破经络、关节中的壅滞以化瘀。有着扶正祛邪、标本同治的功效,对于正虚不足、血络瘀滞所导致中风后肩手综合征的有着针对性疗效。三才、九六之法融汇其中更使调气之力剧增,引邪由表而出。看似摆动针柄,实则力在针尖,意在使气速至病所,通关过节,从而疏通局部气血。血气一行,经脉则通,通则诸痛自愈;血利则水行故诸肿自消。而常规的平补平泻针刺手法常常不能达到“通关过节”的功效,而青龙摆尾针法起效之关键恰是其“气至病所”、“通关过节”的作用以至“荣”和“通”,具有温通经络、补气活血的作用。不仅可以治标散瘀(气滞血瘀),而且还可以固本补虚(气血亏虚),正恰中病机。正如“苍龙摆尾气交流,血气奋飞遍体周,任君疼痛诸般疾,一插须臾万病休”。相关实验[22-23]表明当针在皮下结缔组织作扫散摇摆的大范围运动时,会使局部三维构型发生改变并释放生物电通过换能传导至病变处形成反压电效应,局部离子通道发生改变,进而激活免疫机制迅速缓解病痛。还有一些学者[24]从针刺可以促使血清降钙素基因相关肽的表达量增加,通过增强血管、体液回流及汗腺分泌的角度来解释针刺能够缓解SHSAS患肢水肿的机理。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后,SHSAS证候均得到有效改善,而青龙摆尾针刺组在治疗后总有效率、FMA、ADL评分显著升高,VAS疼痛评分显著降低,与对照组比较,各项指标具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性(P<0.05),说明其治疗效果要优于对照组。综上所述,对于SHSAS的治疗上,青龙摆尾针法疗效显著,其缓解疼痛更为明显,且在改善关节活动度及降低日常生活依赖度上颇具成效,值得进一步发展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