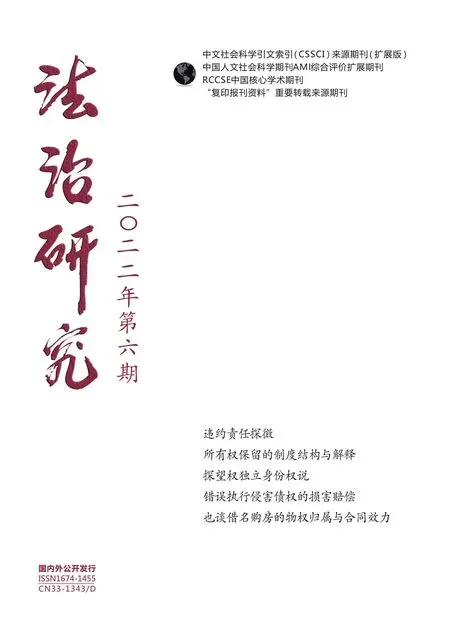离婚当事人约定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研究
雷春红
一、问题的提出
典型案例:刘某(男)与张某婚后育有一子小刘,刘某单位分房时,作为同单位职工的刘某夫妇与单位签订了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合同。2009 年6 月28 日,产权证尚未办妥,刘某与张某登记离婚。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张某的50%房产份额赠与小刘(时年7 周岁),归小刘所有。2009 年7 月,刘某单位通知申领产权证,根据该市购房政策,小刘是未成年人,不能登记在其名下,且须购房合同当事人共同申领。2009 年8 月26日,刘某与张某复婚,领取了不动产产权证,证书载明二人共同共有。然而,刘某与张某的关系日益恶化长期分居,双方先后起诉于法院诉求离婚。2020 年,第三次诉讼离婚时,双方都同意离婚,但就房产(市价约1000 万元人民币)的分割产生分歧。刘某认为,张某于2009 年6 月28 日登记离婚时已将其房产份额赠与儿子小刘,故无权分割房产。张某则提交了一份2020 年10 月其与小刘(18 周岁)达成的书面协议,写明小刘将50%的房产份额赠与张某,主张有权分得50%的房产份额。
本案中,如果没有小刘与张某的赠与协议,张某是否无权分割房产?2009 年8 月26 日,刘某与张某复婚后领取不动产权证,记载为二人共同共有,张某撤销赠与的行为是否无效?就算张某撤销赠与的原因是城市购房政策所致,她应在小刘18 周岁时兑现承诺,配合办理过户登记。但是在2020 年10 月小刘成年时,父母离婚,小刘认为2009 年8 月,张某“撤销”赠与没有侵犯自己的权利,反而与张某达成赠与协议,确保张某取得50%的产权份额。法院最终判决,刘某与张某离婚,二人共有(不写明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诉争房产,对半分割,刘某取得房屋产权,补偿张某500 万元。二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关于离婚当事人约定“赠与子女财产”问题,法学界已有较多探讨,但未形成一致意见;法院对该类争议的判决理由各异。这个案件的案情特殊,但并非绝无仅有。受某些城市房屋限购政策的影响,部分离婚当事人的房产纠纷已无法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得到合理解释和完满处理,本案说明了离婚当事人约定“赠与子女财产”情形的复杂性。简称《民法典》颁布后,有必要就现行相关法律规定做进一步研讨,以求法理的建构和制度的统一。
当事人离婚时,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子女的,主要有下列两种情形:一是登记离婚时,双方的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父母一方或双方将财产赠与子女;二是在法院诉讼离婚时,经法院调解制作的离婚调解书中写明父母一方或双方将财产赠与子女。
当事人约定“赠与子女财产”条款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下列三类:第一,赠与人能否撤销赠与?包括一方撤销赠与和双方共同撤销赠与两种情形;第二,受赠子女是否有权请求父母履行义务,交付财产或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第三,父母离婚时赠与子女财产的约定旨在逃避债务的,债权人能否撤销?第四,赠与子女的不动产尚未过户,债权人就该不动产申请强制执行的,子女是否有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排除强制执行?为解决上述问题,首先需确定离婚当事人约定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的性质。
二、“赠与子女财产”条款定性的各种观点与评析
(一)定性为赠与的观点与评析
定性为赠与的观点,又可分为两种:一般赠与且可撤销;特殊赠与且不可撤销。
1.定性为一般赠与、可撤销。早期司法审判的观点认为,此类条款属于“一般赠与”,在没有办理产权过户登记前,赠与人享有撤销权。①参见张翊雯:《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撤销问题探析》,载《人民法院报》2008 年10 月28 日,第 6 版。准许离婚当事人任意撤销赠与有失法律的公正、公平,已为目前裁判实践所摒弃。
2.定性为特殊赠与、不可撤销。此观点认为,离婚当事人约定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属于“特殊赠与”,赠与人不能随意撤销,至于不能撤销的理由观点各异,分别评析如下:
(1)定性为具有一定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不准确。有观点认为,离婚协议中的赠与行为与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及其他附随义务紧密相连,具有一定的道德义务性质,赠与人任意行使撤销权将有可能导致子女利益发生不道德的减损。根据《合同法》第186 条②《民法典》第660 条第2 款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请求交付。”的规定,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享有任意撤销权,故离婚当事人不能撤销赠与。③参见宋宗宇、何贞斌、李霄敏:《离婚协议中赠与撤销权的限制及其裁判路径》,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 年第2 期。司法实践中,较多民事判决书的理由持此观点,如(2017)川2021 民初1811 号民事判决书④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2017)川2021 民初1811 号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92992171c1e546bf8172a7b500f9e09d,2017 年7 月19 日,2021 年11 月21 日访问。、(2018)川17 民终1524 号民事判决书⑤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7 民终1524 号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f175d198417b4eda82f3aa1e011c1d7a,2019 年3 月28 日,2021 年11 月21 日访问。、(2019)川01 民终6431 号民事判决书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 民终6431 号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c48bd8db4c7d40dda0fcaa7d01646170,2019 年7 月5 日,2021 年11 月21 日访问。等。
道德义务是法定义务以外的,主要受伦理道德、民俗人情、社会舆论等约束的义务,不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史尚宽先生认为:“所谓道德上义务,不应狭义的解释,迫于人类连带责任感之给与,亦应解释在内。所谓报酬的(谢礼的)赠与或相互的赠与,于礼俗认为必要之范围内,应解释为道德上义务之履行。”⑦史尚宽:《债法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123 页。父母是否赠与子女财产取决于其本人的意愿,同时也受父母经济能力、财产多寡等因素的影响,但这绝不属于社会民众普遍认可的道义或民俗,更不能苛以其“义务”,否则将助长“啃老”的不良风气,无故地增加父母的负担,反而成为“不道义”之举。
(2)认定为一种目的性赠与的立论依据不充分。有观点主张,男女双方基于离婚事由将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给子女的行为,可认定是一种有目的的赠与行为。在双方婚姻关系事实上因离婚协议得以解除且离婚协议的其他内容均已履行的情况下,应认为赠与财产的目的已经实现,故该赠与条款依法不能随意撤销。⑧参见李静:《离婚协议中的赠与能否撤销》,载《人民司法》2010 年第 22 期。司法实践中,此观点为部分法院采纳写入判决理由中,如(2018)渝04 民终129 号民事判决书⑨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4 民终129 号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3126b6a5006a4d1699cea89a009d538d,2018 年3 月5 日,访问日期:2021 年11 月23 日。、(2011)浙绍民终字第343 号民事判决书⑩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绍民终字第343 号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629f4140c1364c0cb49f7a727fdb780d,2014 年11 月5 日,访问日期:2021 年11 月23 日。、(2018)晋0105 民初3226 号民事判决书⑪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8)晋0105 民初3226 号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60d622df06874409aad2a976010e5810,2018 年10 月19 日,访问日期:2021 年11 月23 日。等。
笔者认为,目的性赠与的立论依据不充分,离婚当事人将财产赠与子女的动机和目的复杂多样,并非只是为了避免过多的争端以迅速达成离婚协议为目的,也有为了子女利益的考虑,包括确保财产不至于在父母一方组建新家庭后被他人取得、弥补离婚给子女带来的感情创伤、满足子女经济上的需求、对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提供经济帮助等等。双方当事人已经就离婚达成一致,赠与子女财产只是妥善处理共同财产的一种方案。而且,离婚是主法律行为,子女的抚养、共同财产的分割、债务的清偿等是离婚引起的法律后果,所以,将赠与子女财产认定为为了实现离婚目的,是颠倒了离婚的因果关系,逻辑上不成立。
(3)视为一种附协议离婚条件的赠与行为存在逻辑问题。有观点认为,当事人在民政部门登记离婚时,双方将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给子女的行为,可视为一种附协议离婚条件的赠与行为,在双方婚姻关系已解除的前提下,基于诚信原则,也不能允许任意撤销赠与。⑫参见吴晓芳:《〈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适用中的疑难问题探析》,载《法律适用》2014 年第1 期。此定性与目的性赠与有相同之处,都是为了能顺利、迅速地办理离婚登记,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子女,以相互妥协。登记离婚后,离婚协议生效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任意撤销。但是,如前所述,离婚是主法律行为,财产分割与处理是离婚的法律后果;而且离婚父母向子女赠与财产的目的、动机不只是为了快速实现离婚,也有为子女利益的考虑。因此,定性为附协议离婚条件的赠与行为同样存在颠倒离婚因果关系的逻辑矛盾。
(4)类推适用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规定,不严谨。有观点认为,对于未移转登记的股权和其他财产,因离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已在离婚登记时获准予以登记,可视作对其中对子女的财产赠与经过公证不得任意撤销。⑬参见姚玉玲:《离婚协议中涉他行为的性质及法律适用》,载《知识经济》2013 年第 6 期。笔者认为,如此类推适用不严谨,存在定性错误。赠与合同的公证是证明赠与人与受赠人就赠与达成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的方案》有关规定,改制的公证处是执行国家公证职能、自主开展业务、独立承担责任、按市场规律和自律机制运行的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法人。《公证法》第6 条规定:“公证机构是依法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公证行为的性质,法学界的观点不一,但根据上述规定,不能得出公证行为是公法行为的结论。而民政部门颁发离婚证,是对离婚当事人就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等离婚协议书内容的行政确认,是行政行为。离婚案件中出具民事调解书是法院经过调解,使离婚当事人就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达成一致,由法院确认其具有终局法律效力和强制执行力,是司法行为。此二者均对离婚当事人具有很强的法律拘束力,没有必要采“举轻以明重”的民法解释方法,类推适用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能任意撤销的法律规定,这反而降低了离婚协议书、离婚调解书的法律效力,造成定性错误。如有法官提出,经法院确认的房产赠与,其效力等同于或高于经过公证的房产赠与合同,原则上是不能予以撤销的。⑭同前注⑫。
然而,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虽然离婚协议经过公权力机关的备案,这或许可以用来说明离婚协议中的财产约定与公证文书一样具有法律上的执行力,却与赠与人能否撤销赠与没有直接关系。⑮参见陆青:《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研究》,载《法学研究》2018 年第1 期。笔者认为此意见也不恰当,正因为离婚协议书、离婚调解书经过公权力机关的确认和备案,具有公示公信力和强制执行力,所以不能由当事人任意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70 条规定:“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后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因此,类推适用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得任意撤销的规定,不妥之处在于定性的错误,而不是与赠与人能否撤销赠与无关。
(二)定性为解除婚姻关系的条件存在偏差
司法审判中,有法院将双方当事人协议离婚时处分财产的行为认定为是否解除婚姻关系的条件。⑯参见肖峰、田源主编:《婚姻家庭纠纷裁判思路与裁判规则》,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233 页。与此类似的条件结构法律规范可见《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69 条第1 款的规定:“当事人达成的以协议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调解离婚为条件的财产以及债务处理协议,如果双方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以及债务处理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和第一千零八十九条的规定判决。”
附条件法律行为中的“条件”,是指决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产生和消灭的未来的不确定的事实。在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中,条件具有限制法律行为效力的作用,但条件必须具备的要求之一是不确定的事实。⑰参见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民法学》(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225 页。《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69 条第1 款中“协议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属于将来不确定是否发生的事实,表明双方当事人是否要走到离婚这一步或能否合意离婚尚不确定,符合“条件”的要求。但离婚父母“赠与子女财产”的条款不符合条件必须是不确定的要求,因为登记离婚或法院调解离婚后,“赠与子女财产”条款即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应当履行,这是确定发生的事实。《民法典》第158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根据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离婚因其身份法律行为的性质而不能附加任何条件,将“赠与子女财产”条款定性为解除婚姻关系的条件,违反了婚姻自由原则。故此定性不免存在偏差,以偏盖全。
(三)定性为向第三人给付合同/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过于牵强
有观点认为,离婚协议约定夫妻一方或双方财产归属子女,应视为夫妻一方或双方允诺向第三人给付,属于向第三人给付的合同或者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⑱参见常淑静、赵军蒙:《离婚协议中房产赠与条款的性质及效力》,载《山东审判》2011 年第 4 期。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是指订约当事人并非为了自己设定权利,而是为第三人的利益订立合同,合同将对第三人发生效力。⑲同前注⑰,第572 页。对此,《民法典》第522 条予以规定。将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条款定性为“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解决了当事人不能任意撤销赠与的难题,但是笔者不赞同此观点,理由如下:
1.赠与子女财产是离婚当事人处分自己的财产份额,不是对债权人或第三人履行给付义务
根据《民法典》第229 条的规定,因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发生效力。法院的离婚调解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夫妻关系解除,共同财产分割。所以,“赠与子女财产”的约定是当事人将自己的财产份额赠与子女,是对自己离婚后分割所得财产份额的处分。而依据《民法典》第522 条关于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规定并不能准确解释,因为赠与不是离婚当事人一方向对方承诺负有向第三人(子女)履行给付财产份额的债务,而是离婚当事人处分自己的财产份额。
2.离婚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对价关系
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债权人支付价款,债务人按照约定向第三人提供相当价值的货物或服务,双方形成对价关系。但是,离婚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对价关系,尤其婚姻关系解除后相互间不再负有法定的扶养、照顾等义务。有观点认为,离婚当事人间具有补偿关系,这属于债权债务关系,即一方将向另一方支付的财产归并款或应归另一方所有的财产直接向第三人(子女)给付,折抵另一方应向第三人(子女)支付的抚养费或其他债务。⑳参见龚明辉、赵文清:《离婚协议中第三人利益条款法律效力研究》,载《法律适用》2009 年第 4 期。然而,给付财产与支付抚养费的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基于约定产生的财产法上的义务;后者是身份法上的法定义务,给付抚养费的数额无法用财产的价值折抵。更何况诸多离婚当事人约定将财产赠与子女的同时,还约定给付抚养费的方式、抚养费数额等,这与赠与子女财产的价值大小无关。此外,离婚当事人赠与子女的财产难以现实地转换为每月、每日因抚养所需的经济供给,尤其是不动产赠与,因为不少城市购房政策限定:十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能办理过户登记。因此,离婚当事人赠与第三人(子女)财产以折抵其向第三人(子女)支付抚养费或其他债务的观点不成立。
3.无法解决获利第三人(子女)是否有权向债务人(父母)主张履行债务的难题
根据《民法典》第522 条第2 款的规定,只有在“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债务”的情形下,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第三人才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要求其实际履行。保险、信托等法律制度的宗旨是为第三人设定对债务人的受益请求权,即使债权人与债务人没有约定,法律也推定债务人向第三人作出允诺,第三人取得对债务人的请求权。但是,登记离婚、法院调解离婚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情形,也不能如同保险、信托等适用法律推定。通常,离婚当事人只写明“财产赠与子女”,并不写“子女可以直接请求父母向其交付财产或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离婚后,父母一方不履行赠与义务,作为获利第三人的子女只能依赖父母另一方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履行赠与承诺。如果父母另一方死亡,权利主张成为不可能。此情况属于向第三人给付合同中之“经由指令而为给付”合同,子女无请求权21参见许莉:《离婚协议效力探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 年第1 期。,如此显然削弱了离婚协议书、离婚调解书的法律效力。
(四)定性为身份法上的“离婚财产清算协议”欠缺说服力
清算是指法人终止前,应当对其财产进行清理,对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结的行为。之所以要求法人及时清算,主要是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并使法人能够及时终止,退出市场。22同前注⑰,第114 页。《民法典》第70 条第1 款、第73 条和第107 条对法人、非法人组织清算作了规定。可见,清算一词有其特定的涵义和适用范围,它是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终止前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清算程序是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退出市场的必经程序。
有观点认为,如果把夫妻关系理解为一种身份法意义上的继续性合同,可以借鉴合同解除后果(清算关系说)的理念,把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处理部分(包括给予子女财产)界定为“离婚财产清算协议”的范畴,并纳入到婚姻关系解除后的清算关系中予以综合考量,以此来解释所谓的离婚协议的整体性。23同前注⑮。借用财产法上的“清算”一词界定离婚协议的财产处理内容,并在其上加“身份法上的”限定词,是否妥当值得商榷。此观点亦表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合同解除,婚姻关系解除(离婚)下的清算关系显然更为复杂,……除了夫妻共同财产、债务的分割,还应把子女抚养、探视、对配偶一方的经济补偿、经济帮助甚至过错损害赔偿上的种种安排都纳入离婚清算关系的范畴作整体考量。24同前注⑮。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清算”一词是财产法上的特定概念,现实生活中,人们使用“清算”一词时亦有算清相互间的财产、债务,从此互不相欠、“一了百了”的意味,将其用在身份法上未免过于“冰冷”,离婚当事人间成为冷酷无情的“算计”。离婚后的子女抚养、探视、对配偶的经济补偿、经济帮助甚至损害赔偿的种种安排都是“有温度的”,是基于父母子女间无法割舍的亲情、前配偶间的感情纠葛(无论爱恨情仇)作出的安排。借鉴合同解除后果(清算关系说)的理念,在身份法上使用“清算”一词不妥当。即使在继承法上,被继承人去世后,各继承人继承、分割遗产,内容可能包括被继承人生前债务的清偿、去世后公司企业的经营等复杂的财产关系,亲情、感情纠葛的意味较弱,也不宜使用“清算”一词。因为“离婚的法律后果”“被继承人去世产生继承法律后果”已足以概括,在身份法上借用“清算”一词是财产法制度对婚姻家庭领域的过度扩张,并不能真正起到弥补现行婚姻家庭财产法律制度不足的作用。
关于为何将“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纳入此种复杂的清算关系中予以考量,此观点提出,离婚当事人约定“赠与子女财产”条款虽名为“赠与”,实则缺乏真正的赠与意思,更应理解为是父母(或其一方)从保障子女未来生活需要的角度出发,对抚养义务所作出的具体履行方式的安排。25同前注⑮。该论断并不准确。无论离婚当事人将财产赠与子女出于何种考虑、动机有多么复杂,都不能改变父母将财产无偿给与子女、归子女所有的目的和性质。许多协议离婚或法院调解离婚的案件案情相对简单,仅是一处房产赠与子女,没有其他财产分割、债务清偿、经济补偿等;对子女的抚养也达成一致,这又如何能定性为一揽子“清算”方案呢?而且,清算程序是法人、非法人组织终止前必经的法定程序,但离婚并不要求当事人必须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对方经济补偿。综上,笔者认为,定性为身份法上的“离婚财产清算协议”理由不充分,欠缺说服力。
(五)区分不同情况不同处理随意性过大
定性为身份法上的“离婚财产清算协议”观点认为,因涉及多方利益之平衡,在具体法律适用规则上,须综合考察三重维度:在夫妻关系维度,属于离婚财产清算协议;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上,属于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在与债权人关系上,债权人能否对“赠与子女财产”条款行使撤销权,应区分不同情形考虑。26同前注⑮。有法官认为,在登记离婚情况下,“赠与子女财产”条款可视为一种附协议离婚条件的赠与行为,不得任意撤销;在法院调解离婚情况下,生效的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强制效力,双方当事人必须履行,无权撤销。27同前注⑫。
区分不同情况不同处理,具有考虑全面、灵活性强的优点,但是,就法律关系或者行为定性而言,不够严谨,随意性过大,无益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同案异判”的难题,损害立法与司法统一。
三、定性为“特殊赠与”之证成
离婚当事人约定“赠与子女财产”条款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再次从微观层面提示了我国婚姻家庭财产法规则的“窘况”,诸多制度上的“空白”“缺漏”已无法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就本文的论题而言,上述各种观点固然具有其合理性,但都存在某些值得质疑和推敲之处,其共同的症结是,在现行婚姻家庭制度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推定适用合同法的规则。由于身份法与合同法的性质和情况迥异,“将就”地推定、解释必定出现各种各样的“纰漏”。笔者主张,离婚当事人约定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属于特殊赠与,虽具有赠与的性质,但不能适用《民法典》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理由如下:
(一)赠与是离婚当事人对各自财产份额的处分
离婚意味着夫妻财产共同共有的基础丧失,夫妻任何一方都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一般情况下是平均分配。离婚当事人约定一方应得的50%财产份额赠与子女,是对自己财产份额的处分;双方约定将共同财产全部赠与子女,则是对各自享有份额的处分,虽然是共同财产整体赠与,但不影响当事人分别处分自己财产份额的性质。这是定性为赠与的基础依据。
(二)定性首先应以《民法典·总则编》的相关规定为依据
《民法典》设独立的婚姻家庭编,实现了婚姻家庭法在民法典形式意义上的“回归”。因婚姻家庭法的特殊性决定其在民法典中的相对独立性,但婚姻家庭法的特殊性只是相对于财产法而言,并非相对于民法而言。28参见雷春红:《婚姻家庭法的地位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 年版,第223 页。离婚协议是解除配偶身份关系的协议,包含身份法与财产法两部分内容。坦言,债法对家庭法在立法和司法层面的影响都与日俱增,但将家庭法整体融入债法是否妥当,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29参见刘征峰:《论民法教义体系与家庭法的对立与融合:现代家庭法的谱系生成》,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夏吟兰教授所作序第 1-2 页。因此,在《民法典》“总—分”结构体系下,当婚姻家庭编没有规定时,首先应适用的是总则编的相关规定,而不是财产法具体制度。即使考虑参照适用财产法的具体制度,也要考究制度间是否契合、适用结果是否违反民法和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如果不契合或违反则排除适用,进而考虑增设和完善婚姻家庭财产法律制度的特定性规定。
基于上文,各种参照适用合同制度的观点都论证了“赠与子女财产”条款不得任意撤销,否则有违诚信原则,助长当事人离婚后再恶意占有财产,损害子女利益,但在法律原理和制度契合方面却存在欠缺。笔者主张,以民法总则的相关理论和制度为依据,将离婚当事人关于“赠与子女财产”的约定定性为特殊赠与。
(三)以《民法典·总则编》相关规定为依据定性的具体阐析
1.离婚父母关于“赠与子女财产”的约定就是代理子女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
有观点认为,赠与是双方法律行为,子女没有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故赠与合同不成立,子女无权请求履行赠与义务。30参见陈敏、杨惠玲:《离婚协议中房产归属条款相关法律问题探析》,载《法律适用》2014 年第7 期。对此,需分两种情况:
其一,子女是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包括未成年人和不能辨认或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一般情况下,父母是其法定代理人,父母合意离婚时将财产赠与子女,即是代理子女作出同意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如果作为子女法定代理人的父母拒绝接受赠与,又怎么会作出“赠与子女财产”的约定?这是不言自明的逻辑常理,无需法律推定。在特殊情形下,父母一方或双方不是子女的法定代理人,则由子女的监护人作出接受或拒绝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根据《民法典》第35 条的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如果拒绝接受没有负担的赠与,则可认定为损害被监护人(子女)的利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严重者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其二,子女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父母离婚时,子女已成年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则由子女自行作出是否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在开篇的典型案例中,即使认定张某撤销赠与无效,但小刘成年时与张某达成赠与协议,表明小刘放弃接受赠与,张某有权分割诉争房产。
2.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可采明示或者默示形式作出
《民法典》第140 条第1 款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行为人通过口头或书面的方式作出意思表示的,是明示形式;行为人没有明确表示,但可以根据法律规定推知的,是默示形式。由于父母子女是最亲近的人,是否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大多不采书面形式。而且,此约定属于家庭内部事务,具有很强的私密性,除了书面形式之外,口头表达接受赠与的明示形式与接受赠与的默示形式在证据规则的适用上,无实质区别。子女请求父母履行赠与财产的承诺,足以表明其有接受赠与的意思,至于是否曾经表示过,不应对子女苛加严格的证明责任。实际上,口头表示接受赠与,如谢谢、嗯、好等,或者默示方式,如点头等客观上已无法证明,但不能因此推定成年子女或子女的监护人拒绝接受父母给予的没有任何负担的财产赠与。
3.采意思表示的解释方法可“迎刃而解”
离婚当事人约定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是离婚协议书或离婚调解书的一部分,是诸多学者论证该条款不得任意撤销的主要理由之一。例如,有观点认为,离婚协议中的房产赠与条款与整个离婚协议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行使任意撤销权。31同前注⑫。有观点认为:“不能脱离离婚协议的‘ 整体’来看待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这个‘部分’,离婚协议作为一个整体,其标的具有不可分性,这是《民法总则》第 142 条第1 款32《民法典》第142 条第1 款:“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意思表示体系解释方法和‘行为的性质和目的’解释方法在身份关系协议领域的具体运用。”33王雷:《论身份关系协议对民法典合同编的参照适用》,载《法学家》2020 年第1 期。笔者赞同此观点。
意思表示的体系解释,又称整体解释,需要将各种意思表示的信息综合考虑,从整体出发准确地理解意思表示条款的真实含义。《民法典》第142 条规定要求结合相关条款进行解释,可以认为确立了整体解释原则。34同前注⑰,第203 页。离婚当事人赠与子女财产的约定与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债务清偿、离婚救济等内容构成一个整体,这是形成共识的,但缺少从民法总则规定的高度阐释,进而陷入适用合同法规则的“误区”。司法审判中,2015 年12 月4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用公开促公正,建设核心价值”主题教育活动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其中“于某某诉高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概括的典型意义是:“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夫妻共同共有的房产赠与未成年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是否有权予以撤销。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将共同财产赠与未成年子女的约定与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共同债务清偿、离婚损害赔偿等内容互为前提、互为结果,构成了一个整体,是‘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如果允许一方反悔,那么男女双方离婚协议的‘整体性’将被破坏。在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且不可逆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当事人对于财产部分反悔将助长先离婚再恶意占有财产之有违诚实信用的行为,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因此,在离婚后一方欲根据《合同法》第186 条第1 款之规定单方撤销赠与时亦应取得双方合意,在未征得作为共同共有人的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单方撤销赠与。”35“最高人民法院12 月4 日公布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官网,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6211.html,2015 年12 月4 日,2021 年11 月26 日访问。该案对统一离婚当事人不能单方撤销赠与的司法裁判起了典型示范作用,其理由就是离婚协议的内容是一个整体,“赠与子女财产”条款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能割裂出来予以撤销。但不足之处是,仅限于不能单方撤销的情形,“在未征得作为共同共有人的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单方撤销赠与”的措辞表明,如果双方当事人在离婚后共同撤销则是准许的。这就没有考虑到受赠人子女的利益保护,即使双方合意撤销,也存在先离婚再恶意占有财产的情况。而且,离婚导致夫妻共同共有的基础丧失,财产由男女双方按份共有,双方合意撤销赠与,也是对各自享有的财产份额的处分,仍采“共同共有人的另一方”的提法不准确。
所谓目的解释,是指在对意思表示进行解释时,应当根据当事人从事该民事行为所追求的目的,对有争议的意思表示进行解释。《民法典》第142 条要求从行为的性质和目的进行解释,这实际上也确立了目的解释规则。36同前注⑰,第203 页。定性为目的性特殊赠与的观点,可以说是运用此方法作出的解释。然而,实际生活中,离婚当事人约定财产赠与子女的目的、原因复杂多样,单一地将目的确定为解除婚姻关系不够全面。一方面,因离婚协议书或离婚调解书生效,离婚目的达到,当事人不能任意撤销;另一方面,当事人须为了实现除离婚以外的其他目的,主要是为了子女的利益,而履行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约定,不得任意撤销。
4.赠与人因特定事由可依据《民法典·总则编》的规定撤销或变更赠与条款
依据《民法典·总则编》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一方基于重大误解、受欺诈、胁迫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或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就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实践中,一方当事人以子女并非自己亲生为由请求法院撤销“赠与子女财产”条款,而另一方明知的,可认定为受欺诈,其有权撤销赠与。如果双方当事人做此约定时都不知道子女并非亲生,则可能构成重大误解,无过错方有权撤销赠与。
当事人离婚后经济状况显著恶化,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如果要求父母在履行法定抚养义务之外仍履行赠与财产义务,有失公平,也不尽人情。但这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规定的可撤销事由,司法实践中,法官可根据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减轻或免除赠与财产的给付义务。
还有的当事人以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为由,主张撤销赠与。由于“赠与子女财产”条款属于生效离婚协议书或离婚调解书的一部分,除非双方当事人约定了附加赡养条件的赠与,否则不能以此为由撤销赠与。父母可另行起诉子女,要求其履行赡养义务。
(四)符合社会民众的传统观念和朴素情感
夫妻二人曾经共同打拼积累的财产,在离婚后被对方分走一半,部分人心有不甘,尤其一方父母在购房时也有出资的,对方带走的财产中包含了该方父母投入的半辈子积蓄。出于离婚将导致财产利益损失过大的顾虑,许多夫妻选择“隐忍”。但是,孩子是共同的,无论如何,血脉亲情无法割舍,所以,离婚时将财产赠与子女是合理的解决方案之一。这符合中国“家产不外流”的传统观念,是普通民众舐犊情深、含辛茹苦朴素情感的表达。其他的让步,例如偿还债务、支付抚养费等方面的妥协,都离不开子女利益的考虑。因此,将离婚时当事人约定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定性为“赠与”,名实相符。正因这一缘故,此赠与具有特殊性,不同于一般财产赠与合同,不宜适用《民法典》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
综上,依据《民法典·总则编》的相关规定,从符合中国传统观念角度,得以论证“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的赠与性质。由于是父母协议离婚时的约定,具有特殊性,既是离婚当事人相互间的承诺,也是对子女赠与财产的承诺,是一项负担行为。登记离婚、法院调解离婚是公法行为,离婚协议书、离婚调解书一经生效即具有法律拘束力,父母一方或双方均不得任意撤销赠与,受赠子女因此取得请求父母履行赠与义务的权利。
四、子女行使履行赠与义务的请求权受时效的限制
离婚当事人关于“赠与子女财产”的约定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子女向父母主张履行赠与义务的请求权是债权请求权,受诉讼时效的限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受执行期间规定的限制。
(一)依据离婚协议书请求履行赠与义务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离婚协议书写明交付财产或办理过户登记时间的,从约定的时间届满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未写明的,受赠子女可以随时主张履行,但应当给予赠与人必要的准备时间。受某些城市购房政策的限制,年满18 周岁的成年人才能办理不动产产权登记的,受赠子女可以在年满18 周岁后随时主张履行,但应当给予赠与人必要的准备时间。
(二)依据离婚调解书、生效判决书请求履行赠与义务,受申请执行期间规定的限制
法院制作的离婚调解书,一经送达即生效,具有强制执行力。但是,当事人不能依据离婚协议书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因履行离婚协议书发生争议的,须先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协议书中写明,父或母一方将财产赠与子女(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并不实际履行的,另一方有权代理子女起诉。父母共同赠与子女(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双方都没有实际履行的,任何一方都有权代理子女起诉要求对方履行。父母双方都没有起诉的,并不是协商一致有权撤销赠与,而是代理子女放弃权利主张。如果父或母一方去世的,不履行赠与义务的另一方作为监护人实际上侵害了子女的财产利益,根据《民法典》第34条第3 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或组织,有权代理该子女向法院起诉。成年子女向父母主张履行赠与义务未果,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赠与人履行赠与义务的,该判决具有强制执行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8 条第2 项规定,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据此,受赠子女作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民事诉讼法》第239 条第1 款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据此,子女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父或母一方需及时代理其申请强制执行;成年子女则自行申请强制执行。父或母自己也可以作为申请人,在法定的执行期间二年内申请强制执行,否则子女接受赠与的权利不再得到法律的保护。
五、受赠子女与外部债权人的权利冲突与平衡
此处的“外部债权人”,是指离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债权人,“外部”是相对于离婚父母与子女之间家庭“内部”赠与关系而言。受赠子女与外部债权人的权利冲突与平衡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外部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与限制
根据《民法典》第538 条的规定,债务人以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债务人具有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离婚当事人“赠与子女财产”的约定是否具有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较难认定,若一方欠下巨额债务,为了逃避债务,离婚时承诺将财产赠与子女,而另一方并不知情,这不宜认定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为此,可从客观方面,根据债务的形成时间与离婚时间的先后顺序判断。
1.债务形成时间早于离婚时间的。债务形成后,债务人在离婚时承诺将财产赠与子女,其逃避债务的目的明显,即使财产已经交付或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债权人亦有权撤销赠与。由于这将减损子女的财产利益,故有观点认为,当“赠与”涉及子女抚养义务履行的约定时,不宜撤销。如果父母给付子女的财产价值超出必要的法定抚养费支出限度的,可允许撤销。37同前注⑮。笔者认为,如果债务人离婚时与配偶双方约定,将赠与子女财产充抵为支付抚养费,属于债务人的具有人身性质的法定义务,债权人就不得撤销。但是,现实中,明确约定充抵抚养费的情形极少见,赠与财产的价值大多远远高于法定抚养费数额,且二者的性质与实现方式均不同,无法计算折抵。将债务人是否支付抚养费以及抚养费数额多少作为撤销权行使的限制,既无必要,也徒增审判实务的复杂性。即使债务人不离婚,将财产赠与子女,影响了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债权人亦可行使撤销权,不必考虑其中是否包含债务人支付抚养费的内容。为了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在执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43 条和第244 条的规定,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即可。
2.债务形成时间晚于离婚时间的。债务形成于离婚之后,当事人离婚时赠与子女财产的约定不能认定为有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离婚后产生的债务属于个人债务,由债务人的个人财产偿还。债务人将离婚分割所得的个人财产按约定赠与子女,已完成交付或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的,债权人无权撤销。但未交付或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债权人能否主张撤销?笔者赞同不能撤销的观点,即合同关系成立在前履行在后的,不得将该履行行为作为诈害行为而主张撤销。38参见崔建远:《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49 页。基于生效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债务人对已赠与子女的财产不再享有自由处分权,包括不能用于清偿其在离婚后欠下的个人债务。即使履行赠与义务使得债务人名下的财产明显减少,债权人亦不能撤销,因为债务人在债务形成之前已对该项财产作了法律上的处分,交付财产或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履行行为不应认定具有恶意逃债的目的。
(二)受赠子女在特定情况下有权对抗外部债权人申请的强制执行
“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生效后,尚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前,外部债权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赠与人(债务人)名下的不动产,受赠子女是否有权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排除强制执行?对此,也可以区分债务与离婚时间先后判断。
1.债务形成时间早于离婚时间的。如前所述,债务人离婚时将财产赠与子女,减少了自己的责任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明显,故受赠子女无权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
2.债务形成时间晚于离婚时间的。此情形下,债务人赠与子女财产并无明显的逃避债务的恶意,受赠子女有权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但是,受赠人履行赠与义务的债权请求权与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请求权,何者优先实现?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12 条的规定,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 条、第29 条规定了房产买受人的债权可排除强制执行。受赠子女请求父母履行交付财产或办理过户登记的请求权性质与之相同,可谓交付型债权请求权或取得型债权请求权。最高院执行法官提出:“从实际权利人的角度考量,如果其(约定所有权人)已经实际占有使用房屋,且房屋产权登记正在办理变更或者对于未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没有过错,则其距离完整的法律意义的所有权人仅仅有一步之遥,其享有的权利的性质为物权期待权,对其应当优先于普通金钱债权人予以保护。”39王毓莹:《离婚协议关于房屋产权的约定能否对抗申请执行人》,载《人民法院报》2017 年11 月22 日,第7 版。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关某、王某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088 号中认为,夫妻离婚时约定归一方的房产,特定情况下可对抗另一方债权人对房产的执行。该案的特定情况可归纳为:(1)邵某欠王某的债务发生在邵某与关某离婚后,可判断二人《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房产归关某所有,并无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2)《离婚协议书》还约定,房产在双方的子女邵某某18 周岁后归邵某某所有,因邵某某未满18 周岁且出国留学,故未办理过户登记,邵某和关某对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没有过错。(3)该房屋由邵某负责出租,租金用于邵某某的生活学习使用,符合家庭伦理及善良风俗。
据此,笔者认为,受赠子女有权排除外部债权人申请的强制执行,但需符合以下要件:申请执行的债权是在赠与人离婚后形成的无担保的普通金钱债权或无偿取得的债权;受赠子女或其法定代理人对没有及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没有过错;受赠子女已经合法占有、使用或收益诉争财产。当然,“在约定所有权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要件审查中,应注意松紧适度,维持各方利益平衡。”40叶名怡:《离婚房产权属约定对强制执行的排除力》,载《法学》2020 年第4 期。
(三)离婚当事人转让房产情形下,受赠子女与外部债权人(受让人)的利益平衡
离婚当事人不履行约定的赠与条款,将名下的房产转卖或赠与他人,可视为撤销赠与。如前所述,离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不能任意撤销赠与,但是,双方共同将名下的房产出售或赠与他人,意味着任何一方都不会代理子女(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向另一方主张权利,视为放弃赠与财产,该房产由受让人或其他受赠人取得。离婚当事人不能以曾约定有“赠与子女财产”条款为由,拒绝配合办理过户登记,否则需对受让人承担违约责任。
受赠子女是成年人的,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撤销房屋转让合同或房屋赠与合同。如果受让人不知情,支付了合理对价,并且办理了过户登记的,基于物权登记的公示公信力和从保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由受让人取得房屋所有权,受赠子女只能请求父母赔偿损失。
六、结语
离婚当事人约定将财产赠与子女是基于配偶身份关系解除产生的财产流转关系,涉及身份法与财产法的内容。由此产生的问题相对复杂,相关法理分析与法律适用存在较大难度。笔者主张,应首先在婚姻家庭制度框架内研究离婚当事人约定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的性质;在现行婚姻家庭制度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应适用《民法典·总则编》的相关规定,而不应直接类推适用财产法具体制度,否则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不符合逻辑、过于牵强等问题。通过上文的分析,适用《民法典·总则编》的相关规定得以证明“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的性质是特殊赠与,不得任意撤销。而且,此定性符合我国民众的传统观念与朴素情感。
在定性为“特殊赠与”的基础上,受赠子女对父母享有履行赠与义务的债权请求权,该请求权受诉讼时效和申请执行期间规定的限制。当受赠子女的权利与外部债权人的债权发生冲突时,因其属于普通的财产关系,适用财产法规则处理。考究离婚当事人约定将财产赠与子女是否具有恶意逃债的目的,如果具有,则债权人有权撤销赠与,受赠子女无权对抗外部债权人申请的强制执行。在赠与财产变更登记前,父母将财产转让他人的情形下,基于物权法公示公信原则和维护交易安全的考虑,应侧重于保护善意受让人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