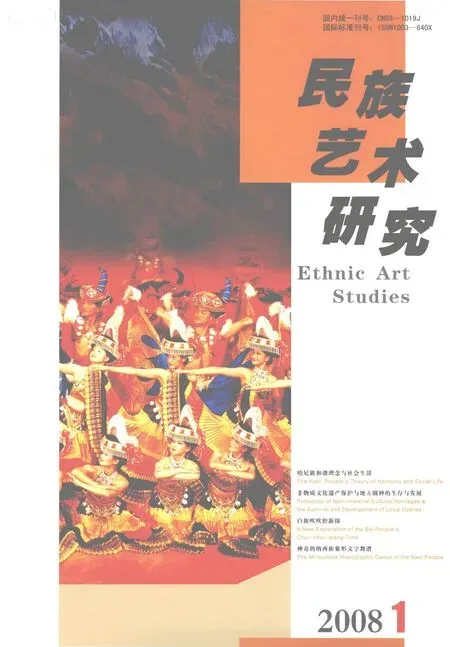关于中国民族艺术学学科定位的思考
邓佑玲
一、建构中国民族艺术学学科的历史坐标
人类已经步入全球化时代,因“空间压缩”形成的“地球村效应”决定了坚守“地方性思维”已经不可能,考虑和解决任何问题都不能偏执于一隅,须拥有国际化视野和全球性思维。与此同时,站位中国,考虑和解决任何问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问题,需破除“门户思维”。中国已经步入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央,21世纪将成为“中国世纪”“中国文化世纪”,须把解决好自身问题和对世界有所作为结合起来,争取对人类有所贡献。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全球化和“中国崛起”推动的本土化,这是我们思考问题和建构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历史坐标,也是重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基本参照。
往回看,随着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欧洲资本主义开启了全球殖民扩张的历史。既往全球化的历史也是世界各民族走向世界的历史。在欧洲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过程中,西方殖民者发现了世界上不同于欧洲的人群、语言、文化。对这些族群的语言、历史、艺术的文化研究形成了博物馆学、民族学、人类学、普通语言学、艺术学等学科。客观地说,民族学等学科是在欧洲殖民扩张过程中产生的。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人类学者的学术研究、学科成果服务于为其提供资助的殖民政府和国家政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殖民扩张过程中产生的民族学(人类学)是带有“血腥味”的学问。一些人类学家在他们的田野报告中对殖民者的所作所为大多讳而不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人类学者的学术取向,其语言研究、民俗研究、文化研究等学科成果服务于殖民者探险、扩张、猎奇、贸易、施政等殖民统治的需要。但是,往前看,全球化的进程不可能停止脚步,未来各民族参与世界历史书写的底层逻辑将会伴随单边主义的衰微和多边主义的兴盛而发生改变,未来的总趋势是和平、合作与共赢。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这正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重大历史使命。
当下中国正行进在复兴之路上,“中国崛起”之势不可阻挡。如何服务“中国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就需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建立本土意识和根性意识,在全球化框架下,更加重视中国本土文化,既关注世界优秀民族文化的中国化,又关切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进而在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发出“中国声音”。为此,不仅要应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挑起的贸易摩擦与价值观对抗,应对欧洲中心论、欧洲优越性丧失带来的焦虑心理,以及西方固有的殖民思维、美国单级霸权思想冲击,同时,在发展硬实力的基础上,中国还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和潜力,在提升科学和技术的能力之外,更加重视提升文化的软实力。即在物质领域之外,更加重视精神文化价值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肩负建构社会伦理、人文精神价值的重大使命和责任。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民族学、艺术学、民族艺术学等学科的建设来说,其承担着中华文化传统、社会伦理、精神价值建构的职能,而且还肩负着向世界传达不同于西方殖民扩张的发展模式,即“中国和平崛起”的新理念。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中国的相关人文社会科学需要阐释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走向世界的问题,这也是民族艺术学学科建设需回应的社会命题。
中国自古以来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价值理念、行为准则,在“仁爱”之心下追求有差等的爱,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近代以来虽然受到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工具主义、物质至上主义暗流涌动,但总体来看,中国文化的核心传统是坚守仁爱之心、推己及人的中庸之道,而且这已活化在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之中。因此,中国当下的发展与国际贸易,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基础建设,货畅其流,都秉持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理想,这是传统中国文化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所欲施于人”“仁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也是与西方传统价值观以及在这一价值观影响下的殖民扩张具有根本不同的中国之道。欧洲资本主义在殖民主义扩张过程中,充满了文化掠夺、种族屠杀,催生了人类学、植物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除了推动经济社会的繁荣与发展,我们必将给世界带来东方的人文精神、人文学科,给人类的知识谱系贡献中国智慧。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说,中国的发展并不可怕,因为中国人只会生产电视机,他们产生不了学说。这当然是“西方中心论”一贯的表现。但是,撒切尔夫人的傲慢偏见提醒当代中国学人,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推动的本土化这两个世界大趋势下,我们应当思考中国民族学,包括中国民族艺术学学科建设的方向和可能。
二、中国民族艺术学的学科价值取向
中国民族艺术学学科不是“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必须是上要站位高远、下要服务于民众的伟大艺术实践。这就需要树立“中国立场、世界眼光、人类情怀”的学科价值取向。
一是要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崛起。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民族复兴不止于经济增长。2021年,脱贫攻坚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圆满实现,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在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社会发展新的矛盾。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方面,艺术学科肩负着文化复兴的重要使命,民族艺术学科的作用不可或缺。例如,如何实现民族音乐、民族舞蹈等的功能与价值,并为全体中国人在解决温饱问题基础上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作出更多努力,这当然是未来中国民族文化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是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用以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如民族地区的艺术共享现象,即各民族不分你我,在共同的舞蹈、歌唱中获得情感共鸣、实现情感和文化认同,实现社区、社会的和谐。在此中间,舞蹈、音乐等艺术中的族际共享现象也许正是我们发掘人类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抓手。以此为载体,进一步归纳、凝练、总结、提升体现中国学术范式的民族艺术理论体系。
三是在中国和平崛起(非殖民化扩张)的理念下,如何以“美美与共”的各民族艺术形象,塑造“美美与共”的中国国家形象,以直入人心的民族艺术共同体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预言,“中国威胁论”将会始终伴随,但打破“中国威胁论”的根本需要更多有文化阐释力的理论。对于民族艺术学科来说,就是要拿出更多的中国民族艺术硬作品、硬代表人物、硬理论体系和硬话语体系,以至风靡全球,这是我们最大的短板之一,也是今后民族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努力方向。中华民族艺术走向世界,这是我们的目标,在这一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实现世界各民族艺术之间的交流与分享、互通与共融,这是民族艺术学前行的路径。但问题在于,走出去容易,关键在于我们拿什么给别人,这是民族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硬课题。
三、民族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几个具体问题
(一)关于民族艺术概念的界定
民族艺术的定义是在文化比较中确立的。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别,一般与特殊之分。广义的民族艺术,可以指向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艺术。中国民族艺术的概念是狭义和特殊意义上的,即指中华民族艺术(中国艺术),既包含中国各民族的艺术,特指为“我的”“我们的”“我国的”艺术,也指具有中国民族性、民族风格的艺术。以文化的“他者”做参照,在国内大多数语境下,民族艺术概念既指向了各少数民族的艺术,也指向具有民族风格、体现民族精神的艺术。笔者强调中国民族艺术的概念,其核心定义是指各民族艺术的“中国性”或“中华民族性”。具体到各少数民族艺术来说,是指一个集合概念。在各民族自己的文化生活中,并没有艺术、舞蹈、音乐这样的集合概念,只有具体的酒歌、古歌、飞歌、情歌、“花儿与少年”和跳舞等具体的活动。因此,当我们使用少数民族艺术这一概念时,虽然指的是各民族艺术的集合体,但关键是指其“中国性”或“中华民族性”。
(二)关于民族艺术的本质属性
民族艺术原本不是为了博物馆、展览馆收藏展览、神龛陈列所用,而是用来生活的艺术,是日常的活动。艺术的活动本身即生活的一部分,如藏族人民在修建房屋夯筑地基时的“打阿嘎”活动,既是建房夯筑地基的生产活动,也是一种歌舞艺术活动。民族生活中日用的艺术,如刺绣、制陶、编织、染织、修造、歌唱、跳舞等当然可以超越生活,展示各民族杰出的才能,标识其族群身份,表达对天地、山川、祖先的崇拜敬畏与感恩之情等等。这说明民族艺术的本质是生活的。因此,民族艺术学主要是研究族群生活、仪式、节日、经验中的艺术。进一步来说,就是要对族群的艺术审美经验进行理论化的人,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意识到族群艺术的创造者和欣赏者,与我们的家人和邻居的共同之处。族群的艺术本质上是生活的艺术,民族艺术与日常生活不是分离的,是有本质的内在黏合性的。因此,民族的生活、经验的在场及其意义,当是民族艺术学研究的重点。民族的生活实践与情感经验是民族艺术本体研究的重点。每一种文化都有着自身的个性,民族的文化个性在艺术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如蒙古族人、傣族人、藏族人、侗族人、苗族人,其生活实践、情感经验、艺术的表达方式都是独特的、真实的那一个。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态度、实践、记忆与情感经验的外化与体现。
(三)关于民族艺术学的研究对象
主要是研究各民族艺术“中国性”或“中华民族性”的形成、结构、特征和机制及其规律。具体到少数民族艺术层面,中国民族艺术学既要研究各少数民族艺术的具体事象,更重要的是要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研究其对艺术的“中国性”或“中华民族性”的构建逻辑、表达逻辑、价值取向、艺术征象、审美逻辑(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模式)。关于民族艺术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内部研究:即研究各族群的艺术生产者(主体)、艺术生产方式、艺术活动(过程)、艺术作品(结果)、艺术体验、艺术经验、艺术心理、艺术情感、艺术类型、艺术风格、艺术价值、艺术精神。
二是外部研究:即研究族群艺术与其所处地域、自然、环境、政治、经济、社会、民俗、语言、哲学等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民俗活动中的艺术和民俗艺术、节日活动中的艺术和节日艺术是研究的重点。正如杜威所说:“不知道土壤、空气、湿度与种子的相互作用及其后果,我们也能欣赏花。但是如果不考虑这种相互作用,我们就不能理解花——而理论恰恰就是理解。理论所要关注的是发现艺术作品的产生及它们在知觉中被欣赏的性质。”①[美]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页。对于民族艺术的外部研究就是寻找民族艺术产生形成的外部环境。
采用外部研究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加强对民族艺术的地方性与异化研究。由于经济全球化,经济上的世界主义的增长,经济体系的原因,贸易与人口的流动性,正在削弱或摧毁民族艺术与这些艺术产品曾经作为地方性的表现。一些民族的艺术品在失去其本土地位之时,即成为仅仅是美的艺术的标本,而不是特别的地方性的文化符号与象征。过去在传统社群生活中有地位、有功能并有意义的东西,在世界主义的大潮当中,也从其起源地中被孤立出来。由于这个原因,它们也从民族的普通的生活经验中分离出来,成为他者猎奇的对象,“他者”文化视野中特别审美趣味的标志。脱离民族实际生活之外的额外需要,成为满足“他者”如收藏、收集、展览、展演、交换、拥有与展示的乐趣,被装饰成为审美的价值或误读出艺术审美的价值,但对于本土的民族艺术而言,则是其本土性、地方性、民俗性审美的异化,其结果并不利于人类审美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
(四)关于民族艺术的跨文化研究
如上所述,民族艺术本质上是生活的艺术。因此,对于民族艺术的跨文化研究,无疑有助于对中国乃至世界各民族生活的了解与理解。对于民族艺术的跨文化研究,就是说在跨文化视野下研究各民族艺术对于现代文明的独特经验和意义。族群艺术之间的交流、影响与接受效果研究,是跨文化民族艺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具有独特的现实价值。休谟曾做过以拜占庭和穆斯林艺术为一方,以希腊与文艺复兴艺术为另一方进行的比较研究,这就是典型的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他说,希腊和文艺复兴的艺术是有生命力的、自然主义的,而拜占庭和穆斯林艺术是几何性的。他进一步解释道,这种不同与技术能力的不同毫无关系。这种鸿沟是由根本的态度、欲望与目的之不同造成的。我们现在习惯于一种满足方式,而将我们自己对欲望与目的之态度当作是所有人的本性所固有的,从而将其当作所有艺术作品的尺度,当作构成了所有艺术作品应该符合和满足的要求。我们具有一种通过“自然”的形式与运动的愉快交流而植根于渴望增加所有体验到的生命力的欲望。拜占庭艺术,以及一些其他形式的东方艺术,来自一种没有对自然感到喜悦、没有对生命力追求的经验。他们“表示一种面对着外在自然的分离的情感。”这种态度与造就具有埃及金字塔和拜占庭镶嵌图画特征对象的态度完全不同。这种艺术与西方世界独特的艺术之间的差别不能解释为抽象的兴趣。它所显示的是人与自然的分离与不和谐。①[苏格兰]大卫·休谟:《思索》,载[美]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32页。但在杜威看来,休谟的这个观点几乎完全不适用于中国艺术。
休谟对于东方艺术的表述和误读,表明在全球化的今天对各民族的跨文化的感受、体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因为艺术表现了各地区的不同人群生活样式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深层的调适态度,一种潜在的一般人类的态度观念和理想,艺术是以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共鸣、同理心而能进入到遥远的异域文明经验中最深层的手段,是突破地方、民族经验局限性,扩充和深化我们自身的经验、情感、审美,理解自身人性和丰富人性的重要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在何种程度上使他者的艺术成为我们自身态度、经验、情感的一部分,就在什么程度上获得了对他者的理解,而不仅仅是通过关于他者的知识条件来理解它。当我们在熟知语言、历史、民俗文化情境之后,再沉浸于四川黑水藏族人的歌唱、广西环江毛南族人的肥套仪式、土家族的跳丧祭祀仪式中时,便能够欣赏黑水藏族人歌唱家乡山水时的歌唱方式,异于我们听觉经验和情感经验的发音部位以及声音的独特性变得不再异样,而成为人类歌唱的一种独特性存在。从肥套仪式中师公的唱词和身体表演行为中,可以感受和欣赏到毛南族人家达成心愿的虔敬之心与心愿达成的欢愉之情。在土家族跳丧仪式中感受、体验到土家族生者对于亡者的陪伴和通达的生死观。笔者2010年和2017年春节期间曾带领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的演员和中国民族民间舞专业的本科学生在美国西海岸以及中东欧国家演出,在没有专题讲解中国文化的背景下,美国、中东欧国家的观众给予演出热烈而长久的掌声。这表明艺术在获得跨文化理解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艺术直接让跨文化的受众进入感知、想象、共鸣、同情、共情之中。艺术深入人心是直接的、生动的、鲜活的、富有情感和审美性的。如果说汉语、藏语、彝语、苗语、英语、法语等言语差别造成文化交流理解的障碍的话,但当艺术来“说话”时,这种障碍就淹没消失了。当我们进入他者的艺术中时,我们也就走进他们的身心与精神深处。通过对民族艺术的跨文化研究,在感受、体验、欣赏之上,研究不同民族在心理、情感、审美、精神上的相通之处,挖掘民族艺术促进人心相通、情感共鸣的功能与价值,阐释在不同民族艺术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逻辑和通过民族艺术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价值,这是开展民族艺术跨文化研究的必要性。
(五)关于研究主体
从民族艺术的研究主体来看,有两个群体值得关注。一个研究主体是具有族群身份的研究者,一个研究主体是跨文化的研究者。这两个主体在开展民族艺术研究时具有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前者持内视角,后者持外视角。前者主要进行主位研究,后者则进行客位研究。具有族群身份的研究者大多因为习得本民族的语言、习俗、历史、传统,掌握熟人社会关系,具有一些天然的优势和便利条件,省去翻译的跨文化转译,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其文化真实。相反,跨文化的研究者,仅仅是由于语言的障碍,就会折损诸多保存在族群语言当中的文化信息,如一些民族在歌唱中以特有的押韵方式,表达美、丑、好、坏、帅、爽、喜、怒、哀、乐等和深层情感经验的不同。族群主体的研究者与跨文化的研究者在情感的感受方式与表达方式上是不同的。族群主体的研究与跨文化主体的研究各有利弊,都需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功夫,以避免认知、判断偏颇。与之相关的还有研究者所采用的语言工具问题,会涉及比较复杂的文化翻译和经验描述、文化阐释的准确性、生动性等问题。
(六)关于民族艺术学使用的概念
学科独立依赖一套独特的话语、范畴和概念。民族艺术学究竟有哪些独特的核心范畴和概念?是否沿袭传统中西方美学、艺术学中的概念和范畴——悲剧、喜剧、悲剧性、喜剧性、崇高、美、荒诞、阳刚、阴柔、形神、神韵、品、妙、格、意象、意境、对称、平衡、均衡、清晰、光滑、明亮、整齐、对比等概念?笔者的观点是,要从各民族的艺术生活中提取其文化中本有的概念和范畴,而不是套用汉语经典艺术理论和西方艺术理论。在许多少数民族的艺术中,在表达艺术、审美经验时以形象化的、诗意的、比喻的、意象化的方式居多——不用美或美丽的词语,而是用雪莲花、格桑花形容;或以月亮描述美丽的姑娘,以太阳形容青年小伙。在每个民族中都有一套独特的表达其生活、情感、审美经验和精神的语言范畴。在民族艺术研究中,有关时间、空间、方位、自然、生活、视听、身体、心灵、情感、美丑等观念的表达,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连续性、关联性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学术范畴和学术概念。
(七)关于民族艺术学的研究方法
除现有各种艺术研究方法之外,本文主要强调三点:一是倡导从族人的生活出发的研究,避免将民族艺术“悬隔”为一种博物馆、艺术展览、剧场中的艺术,孤立地进行研究。要从黑格尔、康德对学术分科和将艺术孤立化的做法中走出来,不再陷入单纯的对艺术定义的讨论,跳出艺术是人类的一种独特活动所产生的独特产品的认识局限,忽视艺术生产与日常生活、产品生产之间的联系。要摆脱精英性的艺术概念,回到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民众的生活出发研究,使民族艺术研究建立在现实的对象基础上。从族群的生活出发应成为民族艺术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当然,其艺术研究的材料应当从所有的族群生活中去寻找,其艺术的产品应当为所有的人所接受。二是倡导语境中的研究。不知道特定地域的土壤、空气、水、湿度与种子的相互作用及其后果,我们也能欣赏花,但是如果不考虑这种相互作用,我们就不能理解花。而理论恰恰就是理解。只有在语境中理解解读,才能发现和分析族群的日常生活经验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性要素?我们日常所欣赏的景色与情境是怎样发展成特别具有审美性的东西的?这些都是重要的方法论思路。三是始终要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基本参照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在民族艺术的“中国性”和“中华民族性”上做文章,弄清其底层逻辑、形成机制、特征和规律。
结 语
民族艺术学学科建设始于20世纪初,从孙中山、梁启超等文化先贤翻译引进“民族”“民族主义”“民族意识”等概念,到岑家梧、凌纯声、方国瑜、江应樑、钟敬文等较早开展图腾艺术、萨满仪式乐舞、东巴乐舞、民间文学的调查研究,伴随着西学东渐影响而不断演化并走向深入。一方面是部分学者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情境中,激发出了对民族、国家、文化、身体和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全面检视和深刻反思;另一方面是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现代学科民族学、人类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传入中国,中国学人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中,直接推动了对少数民族文身、跳舞、歌唱、衣饰、故事等艺术的重新发现和描述探究。近百年来西方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美学、艺术学的形式分析等为中国民族艺术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借鉴,但是,从中国的艺术学理论、民族艺术学的理论知识谱系建构来看,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和世界化的关注不足,对中华各民族文化缺乏自信,甚至发展到了学术底层逻辑的“去中国化”的危险境地。本文主旨并不是对中国民族艺术学的学术史展开研究,而是旨在讨论在21世纪的今天,当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十几亿中国人实现了从民族独立到民族解放,中华民族从危亡到站起来、富起来,并走向复兴与富强的新时代格局中,中国民族艺术学的学科定位、学科目标、学科价值以及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几个问题,以供学者们深耕民族艺术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