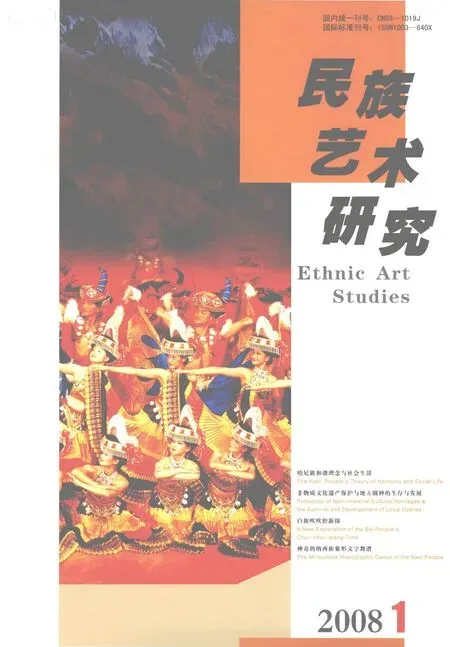共同体美学视域下的中国扶贫题材电影研究
龚金平
2020年11月23日,国务院扶贫办宣布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这标志着这场攻坚战取得了开创性的胜利,在此过程中,中国大地上不仅涌现了许多可亲可敬、可歌可泣的扶贫先进人物,中国电影人也创作了一批扶贫题材电影。在这些影片中,主人公一般都是共产党员,这既是真实的社会现实,也是影片政治意识形态表达的策略。身为共产党员,人物的任何奉献、牺牲、忍耐都变得合情合理、理所当然,这使影片在处理人物的行动逻辑时异常顺畅。但是,影片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如何使不是共产党员的观众对人物的选择也心有戚戚?这成了当前中国扶贫题材电影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为了使中国扶贫题材电影追求更为广泛的“普适性”,使影片不仅关注特定的社会现象、国家战略,也能在宽泛的意义上收获所有观众的代入感,我们需要将扶贫题材电影的艺术得失,放在共同体美学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更为深入和直观的揭示。
共同体美学由著名电影学者饶曙光于2018年末提出,其体现出实践性、继承性和集大成的重要品质。“共同体美学的基本思路是立足于‘我者思维’基础上的‘他者思维’,在文本层面倡导‘共同体叙事’,在产业层面坚持“共同利益观”,在电影的微观、宏观和相关方面都能产生良性互动。”①饶曙光:《观察与阐释:“共同体美学”的理念、路径与价值》,《艺术评论》2021年第3期,第27页。在共同体美学的视域下,我们对扶贫题材电影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就是看影片能否激发观众的他者思维,对人物的处境、选择产生认同心理。
一、缺乏共同体美学照拂的扶贫题材电影
扶贫题材电影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明显的政策宣传和社会公益特征,其主题主要是对扶贫政策、扶贫先进人物和扶贫成果的传播和赞美”。①何亮:《扶贫电影的叙事选择:情感力量的形成与主流市场的实践》,《电影艺术》2020年第6期,第52页。当然,影片的主题不应该是直白的自我展示或强行灌输,而应该让观众被情节感动,被人物打动,在一种情绪的浸染状态中自然而然地接受附着于情节和人物之上的道德、情感倾向,以及创作者对于世界、人生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共同体美学的理论视野非常重要,创作者要有对人类共通性情感的把握,准确捕捉观众心中的情感需求与道德渴望,并以一种艺术的方式完成对观众的心灵抚慰。遗憾的是,在扶贫题材电影中,能够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并不多,大多数影片一度满足于担任政策宣讲员的角色,以一种非常生硬刻意的方式完成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与主题表达。
(一)主人公的维度不清晰、性格形成没有由头,未能体现人物的真实性与立体性
主人公无疑是一部影片的主心骨,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来源。观众对主人公的熟悉、了解、喜欢、敬佩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观众对影片主题产生共情的前提。对于一个品格高尚,但不接地气、缺少生活质感的主人公,观众其实是敬而远之,甚至是感觉漠然的。
在一些市场反响比较一般的扶贫题材电影中,我们会发现,主人公看起来非常标准:相貌上一脸正气,举手投足间又有一种亲和力;对党的政策理解得非常透彻,执行到位;工作耐心细致,既有雷厉风行的一面,又有春风化雨的暖心之举;目标远大,意志坚定。对于这种人物,观众自然是钦佩的,但多少也会心存疑惑:主人公在工作过程中会不会有动摇、犹豫、退缩的时刻?主人公身上的这些正面价值究竟来自他的身份(共产党员、扶贫干部),还是源于个人层面的性格和心理因素?主人公除了是扶贫干部,以其他社会身份出现时体现出怎样的特点?对于这些问题,很多影片几乎没有涉及,而是从概念出发,按照理想中的扶贫干部面貌来打造正面形象,导致这些人物虽可敬,却不一定可亲可爱,甚至不可信。
影片《岭上花开》(2019年)中,袁紫丹来到崇家岭时,像是从天而降,观众对她一无所知。虽然,与村民见面时,她自我介绍毕业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但观众在影片中从未见过她展示相关专业背景。而且,她在对村里的具体情况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面对信用社的催债,轻率地承诺3年内还清50万元贷款的本金和利息。男朋友逼她离开这个村庄时,影片也未能为她的选择提供有足够说服力的东西。更令人诧异的是,袁紫丹与妹妹聊天时,毫无征兆地说,她要在崇家岭待一辈子。这种台词过于高调,像是为了突出扶贫干部的崇高而硬塞给人物的,却没有现实逻辑的支撑,更没有体现出对人物心理深入挖掘后的水到渠成。
本来,袁紫丹与崇家岭有血缘共同体的关系,因为非法集资的李建中和村主任都是袁紫丹的舅舅,但这层关系从未在情节中发挥任何作用,也没有对人物的选择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这说明,影片无心也无力营造一个共同体的场域,以便让观众进入深度共情的观影状态。
《一个不落》(2018年)中,扶贫干部李向东过于强大,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面对村民的不理解、吴副乡长的阻挠与报复,以及工作中遇到的难以想象的困难,他均能以身上的凛然正气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坦然面对。李向东作为一个完美的扶贫干部,确实让人敬佩。但是,观众回过神来就会意识到,这个人物毕竟过于模糊,观众不知他的家庭状况,不知他原来的工作单位和工作背景,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专长和性格脾性。
从电影编剧的角度来看,人物的塑造应该基于三个维度展开:生理、社会、心理。观众需要了解一个人的外在特点(年龄、性别、长相等)和社会身份(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社会阶层等),并由此揣摩人物的性格、脾性、潜意识等。有了这些信息做铺垫,一个人物才会显得真实,其性格特点才不会像无源之水,其行为动机才能得到观众的理解并认同。当部分扶贫题材电影忽略对人物背景的有效揭示时,就无法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只会以凭空想象确立人物的思想境界和政治水平,导致观众对人物的行为选择不明就里,对人物的思想境界心存疑惑。
(二)情节主次不分,核心冲突的处理没有章法、没有感染力
在一部影片中,观众总是对主人公如何解决核心冲突抱有最大的期待,这是影片的观影愉悦所在,更是承载主题的依托之物。对于扶贫题材电影来说,主人公如何带领村民打赢决胜扶贫攻坚战是情节的重中之重,任何对这个核心冲突的忽略与偏移,都有违创作的初衷。
《岭上花开》在情节安排上就缺乏“顶层设计”。直到影片52分钟(影片总共80分钟)时,袁紫丹才在路过一个农业生态园时受到启发,决心在崇家岭开发生态旅游。袁紫丹的报告很快得到了赵书记的同意和批准,赵书记还联系了一家企业。这家企业非常热心,为村里盖学校、平土地、建鱼塘,还支援了村里20万元。这种拖沓散漫的情节节奏、梦幻般的情节推进方式和童话般的核心冲突解决方式,实在让观众错愕。
《一恋之差》(2018年)中,林娟、林江、刘俊良3人想带领村民脱贫,他们写了一份开发生态旅游的报告。村委会主任将报告交给了第一书记,之后,林娟的创业就成功了。按照常理,影片的核心矛盾应是林娟如何创业,次要矛盾是林娟的爱情选择。除此之外,影片不应在其他支线上花费太多时间,不能让一些无关紧要的情节线索喧宾夺主或者令观众出戏。例如,谭木匠将林永贵藏在家里10年,照顾林永贵的饮食起居,却让林江、林娟兄妹承受了10年辛酸,让林永贵的妻子胡秀漂泊了10年,这种情节设置方式,有违人之常情,观众难以接受。当一部影片在现实逻辑和人物的情感逻辑方面出现了重大偏差和断裂时,情节的可信度就大打折扣,融注在情节中的思想内涵也就成了无根之木。
本来,《一恋之差》可以像《橙妹儿的时代》(2020年)那样,充分尊重当下观众的接受心理,用一种青春视角来讲述脱贫故事,“即以青年身份和个人理想来强化艺术表达的公众性,弱化了影片的政宣色彩,契合了观众的审美期待,谱写了一曲新时代农村建设的‘青春之歌’。”①饶曙光:《〈橙妹儿的时代〉:“山城”脱贫影像与共同体美学》,《中国电影报》2020年11月25日。但是,《一恋之差》的青春叙事非常失败、林娟是在城里工作岌岌可危、恋人也见异思迁的情况下,才想到回故乡的。这更像是把乡村当作避难所和疗养院,而非挥洒青春热情、实现梦想的舞台。
电影创作应该遵循基本的编剧规律,牢牢抓住情节主线,并让人物在情节主线的发展与结局中实现目标,完成成长过程,进而表达主题。尤其从共同体美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一部影片无法与观众构建精神共同体,观众就无法对人物投入情感,观众的观影心理就会是淡漠甚至反感的。
(三)主题多是让人物或旁白的声音直接宣讲,而不是让“倾向性”自然流露
扶贫题材电影必然会通过展现扶贫干部(或农村中的有志青年)如何带领村民脱贫,赞颂主人公身上的高贵人格和无私情怀,肯定党的精准扶贫政策。但是,这种主题的表达不应该过于直白,也不能在情节的牵强与人物的孱弱之处,强行通过人物或旁白来发表议论,更不能“以一种图解化的宣传思维来阐释和解读脱贫攻坚国家战略,遮蔽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民脱贫攻坚中的现实矛盾和危机”。②饶曙光、兰健华:《脱贫攻坚主题电影:争做文化扶贫的排头兵》,《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9期,第12页。
《岭上花开》的结尾,旁白的声音说,通过引进资金、合作开发、技能培训、科教普法,精准扶贫举措得以全方位实施,外出务工人员陆续返村,崇家岭焕发出勃勃生机。《一恋之差》的结尾,旁白也说,无数青年返乡创业,这成为他们在农村播种希望、实现梦想的选择。这种“卒章显志”的方式并不是电影创作的最佳境界。一部影片不断让人物在情节中解释个人动机,在结尾重申主题,这是创作者不自信的表现,也是情节和人物处理不成功时的被动补救措施。
在艺术氛围营造不充分、情感铺垫仓促潦草、人物刻画单薄虚假的状况下,观众根本无法进入戏剧情境,也就不能与主人公产生共情,对主题当然无感。这时,对共同体美学的重申就非常重要,“具体到电影而言,这种共同体美学也就是电影通过叙事与形象所达成的,与观众共情的审美效果。在审美感受的共鸣中,电影从观众身上召唤出了共同体的情感认同。”①鲜佳:《共同体美学的多维想象——基于近年国产影片发展趋向的分析与反思》,《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41页。
二、共同体美学视域下的正面人物形象塑造策略
扶贫题材电影天然适合选择戏剧式结构。因为,主人公(尤其是扶贫干部)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就是带领农民脱贫。脱贫攻坚的道路上,必然是困难重重的,包括自然条件恶劣、缺少资金和技术、交通条件落后等,也包括帮扶对象身上的一些消极因素或者被动、逃避心理等。观影过程中,观众不仅关心主人公如何取得成功,也关心主人公在此过程中的内心成长或者情感慰藉。
通过分析近年一些比较出色的扶贫题材电影,我们发现,它们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与共同体美学精神的不谋而合,在正面人物的身份定位、工作理念、行为逻辑等方面与观众形成了“情感共同体”,从而使人物与观众产生了深切的情感连带关系:
(一)淡化主人公的政治身份,突出人物身上的“普通人性”与“正常人情”
近年来的优秀扶贫题材电影中,主人公多为共产党员(扶贫干部要担任第一书记,必然是共产党员),但也有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企业家、返乡的快递员、普通农民、归乡的大学生等。在这个更为丰富的人物谱系中,我们看到扶贫工作已经牵动全社会的心,也看到了创作者艺术观念的调整。影片为了减弱观众对人物因需仰视而产生的疏远感,尽量淡化人物的政治身份,从“人”的角度去强调人物的情怀、内心的感动、朴素的感恩心理和责任意识。这正是共同体美学进行“共同体叙事”的重要策略。
在《我和我的家乡》(2019年)中,与扶贫有关的短片包括《天上掉下个UFO》《回乡之路》《神笔马亮》,这三个短片中,主人公的政治身份都被弱化,突出他们作为“社会人”的一面,如普通的村民、在外经商成功的商业精英、文艺工作者。这些主人公改变农村贫穷现状的动力,不是来自上级的安排,或者作为公职人员的职责所在,而是由于个人的特殊经历或者自我的情感需要。《天上掉下个UFO》中的黄大宝,因为当年交通不便,与心爱的姑娘失之交臂,才会想着制造现代化的物流工具,让这里富起来,不让类似的爱情悲剧再次上演。《回乡之路》中,乔树林作为孤儿,受过高妈妈及那片土地的恩泽,经商成功之后,产生反哺家乡的念头就在情理之中。《神笔马亮》中的马亮,是农民的儿子,“功成名就”之后想利用自己的专长,为农村建设尽一份力,乃是不忘本。这三个主人公帮助村民脱贫都源于“私人动机”,并未体现出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却真切动人,能使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通过淡化主人公的政治身份,强调人物与农村的关系、与农民的关系,能够为观众进入人物内心打开一条敞亮的情感通道。尤其当人物面对困难时,他们在用共产党员的精神和信念支撑的同时,也以人的意志与力量去战胜困难、去克服内心的动摇与畏惧心理。这样,观众与人物之间的情感交流与互动,就因人物的“平凡化”处理而拥有了一个精神共同体的场域。
(二)主人公对帮扶对象,不是居高临下地施舍,或冷漠粗暴地排斥、鄙视,而是从共情的角度出发,体现出宽广的胸怀和厚重的人文情怀
在精准扶贫的政策中,因为强调因人因地因户制定扶贫对策,“对扶贫干部能否真正融入扶贫对象之中,能否真正与扶贫对象产生情感交流,做到同呼吸、共命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②李百晓:《空间逻辑与文化使命——精准扶贫题材电影创作研究》,《电影艺术》2020年第6期,第47页。只有当扶贫干部能从“人之常情”出发,才能与扶贫对象结成命运共同体,并将观众纳入一个共同的情感场域之中,从而获得心灵的感动和净化。
影片《秀美人生》(2020年)中,虽然和所有参与扶贫工作的干部一样,黄文秀需要运用现代文明知识,帮助村民们走上致富的道路,但影片“却用了更多的笔墨,去描写黄文秀对村民们精神世界的理解和抚慰”。①何亮:《扶贫电影的叙事选择:情感力量的形成与主流市场的实践》,《电影艺术》2020年第6期,第53页。黄文秀这种倾听的姿态,是与村民的一次次心灵交流与精神沟通,也是她能顺利开展工作的法宝。
影片《三年》(2019年)中,面对王老大烂泥扶不上墙的窝囊样,牛书记由衷地感慨,“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只有在思想意识上脱贫,才能真正达到脱贫的目的。”对此,柯书记也表示赞同,“(对于接下来的工作)要有明确的思想,更大的决心,精准的措施。”接着,他们改变了策略,不再简单地为王老大提供所有条件让他被动脱贫,而是让他去养猪场打工,让他收获通过劳动改变现状的自尊与自豪。至于光哥这样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两位书记既采用雷霆手段,也能雪中送炭——为光哥恢复了“光明竹编厂”。这使光哥泣不成声,跪倒在柯书记面前,给他磕头,又给众乡亲鞠躬致谢。在两位书记帮助王老大和光哥的过程中,他们没有一味地“送温暖”,而是能够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对王老大是以促其“立志”为主;对光哥则能体察他内心的苦闷与无望,为他的人生找到出路,使他有奋斗的依托和动力。
从物质脱贫到精神突围,从外部输血到主动造血,这是扶贫工作所要达到的真正目标。这实际上对扶贫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不可能仅凭着一腔热情、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就可以攻无不克,而是必须有科学的理念、开放的视野、开阔的胸襟,还要有通透的人生智慧,以及对贫困群体心理状态的敏锐把握。“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者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这种情感同人性中其他的原始情感一样,绝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的。”②[英]亚当·斯密著:《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页。因此,“若要对贫困文化有所干预,首先需要努力进入到这个‘共同体’中,深刻理解贫困文化的形成机制,然后通过对话和交流的方式逐渐形成影响,以实现对贫困文化的形塑。”③饶曙光、兰健华:《脱贫攻坚主题电影:争做文化扶贫的排头兵》,《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9期,第17页。
(三)主人公参与扶贫工作,不仅是出于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
任何人都生活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都会有现实的烦恼和世俗的纷扰;一个人的伟大不是因为他斩断了与世间所有的羁绊,而是因为他能够战胜私心、能够超越困境,在各种历练中完成自我的修炼而收获圆满。一部优秀的扶贫题材电影,人物刻画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能够让观众看到人物如何在现实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中,昂首挺胸,勇往直前,在成就别人的同时成为更好的自己。在此过程中,人物内心的焦虑与渴望,人物实现目标后得到的情感慰藉与内心成长,能以一种真切自然的方式拨动观众的心弦。
《又是一年三月三》(2018年)中,黄永华40多年前曾在南山插队,与南山的杜鹃产生了真挚的情感;闯下大祸后,莫大山挺身而出保护他。更为重要的是,当年没有打通引水隧道,成了黄永华40多年以来的一块心病。因此,黄永华主动来到南山担任第一书记,有很多私人原因,为了怀旧,为了报恩,为了人生圆满。这里有他美好的青春、纯洁的初恋,也有他最难舍的牵挂、最诚挚的感激和最深切的愧疚。这样,黄永华与南山不仅有着地缘共同体的关系,还有情感上的牵挂,形成了私人层面的精神共同体。这些因素使黄永华的行为动机朴素又动人,深深地打动了观众,这正是共同体美学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我和我的家乡》之《神笔马亮》中,马亮放弃留学深造的机会来到农村担任第一书记,既是出于报恩心理,也未尝没有“私心”。马亮作为一个画家,他的作品本来只能供少数人品鉴,难以转化形成直接的社会效益。当马亮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作画、在稻田里作画、在祖国的大地上写下人生的壮丽诗篇时,这正是一种更为昂扬的人生志向和更为恢宏的自我实现。
在这些比较优秀的扶贫题材电影中,当主人公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扶贫工具”,他们也开始在扶贫过程中体验人生的成就感和内心的满足,这不仅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富有心理深度和生活质感,也更能得到观众的情感接纳和精神致敬。因为,“电影创作最重要的方法和智慧,就是尽可能与最多的观众达成最大公约数,建构有效的对话渠道、对话空间,形成共情、共鸣、良性互动的共同体美学。”①饶曙光:《实践探索、理论集成与传统承继——再谈共同体美学的三个维度》,《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24页。
三、共同体美学视域下的“后进人物”形象刻画
扶贫题材电影中,主人公在帮助农民致富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其艰辛与豪迈自不必说,观众则在感动于主人公的无私与执着之余,也在探询这些地区陷入贫困状态的原因。
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贫困,其首要原因是先天不足的地理条件,包括土地贫瘠、交通落后、气候恶劣等。《又是一年三月三》中的南山,土地石漠化严重,而且干旱缺水,农业生产极为困难。 《我和我的家乡》之《天上掉下个UFO》中的贵州,曾经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农业生产受到极大限制,更不要说与外界的商业交流。
只是,如果贫困全部是因客观条件所致,观众会觉得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处于那种贫瘠荒凉、闭塞僻远的穷山恶水之中,进而以一种隔膜的心态看待村民们的生存挣扎。甚至,观众会发出疑问,既然有些村庄人口不多、先天条件无法改变,国家只要让他们整体搬迁,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因此,贫困的原因显然还包括人的因素,这才是影片能与观众深度共情的切入点。
在电影中,情节的形成源于冲突,如人物与自然环境、时代、邪恶力量的抗衡,或者人物如何战胜内心的犹豫、恐惧等情绪。对于扶贫题材电影来说,自然环境肯定是影片中非常重要的一股反对势力,但若人物只需要与自然环境搏斗,情节就会显得有些单薄,人物会显得空洞、没有心理深度,因而必须要呈现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斗争、妥协、圆融,也就是要设置相应的“后进人物”。“更普遍的情况是,这些影片的冲突落在了人与人之间,即国家话语的代表/党的基层干部和好逸恶劳的个别农民之间。这一冲突发生于观念层面,它进而使得‘扶贫’故事中的人物形成了先进者/教育者和落后者/被教育者这样的(对立)关系。”②陈犀禾、赵彬:《新时代扶贫题材电影的中国性研究》,《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115页。
在共同体美学的视域中,观众必须对人物的处境有切肤之痛,才能对人物的心理状态和人生选择感同身受。这时,就不能简单地将扶贫题材电影中的“后进人物”定性为负面道德形象,而是从人物的困厄处境中找到他们精神贫困的原因,进而在隐喻层面将人物的“困厄”拓展为一种人生的普遍性,这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遭遇的人生际遇,这样就能使“后进人物”也与观众产生道德和情感共鸣。因为,这些“后进人物”在行为和心理上的不同表现,正对应了所有人面对困境的不同心态。
扶贫题材电影中的后进人物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有着乡土社会特点和惰性的普通农民
在许多文艺作品的描述中,农民形象总是与木讷、憨厚相关联,有着淳朴善良、勤劳节俭等美德。事实上,因为长期与土地打交道,农民生活的凝滞与循环使他们不愿接受剧烈的变革,也不愿去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在2020年的《一点就到家》中,老一辈农民遵循祖辈种茶的传统,不愿改变,也不敢改变,甚至对尝试创新的李绍群进行驱逐、隔绝。
近年优秀的扶贫题材电影中,创作者不仅努力揭示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纠结与痛心,更深入挖掘“后进人物”身上的短板。这些短板不是知识水平低下,而是观念上的保守、自我认知的短视、性格中的自私、心胸的狭隘等。这是一种更有新意的情节设置方式和人物刻画方式。
影片《李保国》中,李保国带领农民试验种植苹果新品种,进行科学培育时,农民们充满疑虑,不敢去冒险。《一点就到家》中,农民们对现代商业理念难以接受,只想着钻空子,导致彭秀兵的快递站亏空了他的所有积蓄。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存在一种阿波罗文化,体现出静态意向的特点,“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①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同时,乡土社会存在差序格局,即以己为圆心,以亲属关系联系成社会关系的网络。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的线条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产生意义”。②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因此,农民身上的这些劣根性,是中国乡土社会几千年来的因袭沉重物,仅靠思想教育很难有改观,只有通过经济模式、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调整,才能真正冲击农民的心理结构和思想观念。
正因为这些影片能够立足乡土社会的土壤来刻画农民形象,从现实世界的烟火气中凸显农民身上的弱点,观众在观影时才不会产生隔岸观火的道德优越感,而是会在返身观照时意识到:任何人在习惯了自己的环境、安然于自己的处境之后,都容易受制于自己的思维视野、被禁锢于自己的行为经验中。这些农民走出自己的思维误区、走出人生舒适区,开始去适应时代的潮流、主动谋求改变,这是一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能够对每一个观众产生深层的心灵触动、丰富的人生启发和澎湃的情感力量。
(二)消极悲观、得过且过、麻木不仁的落后分子
在现实的打击和冷酷的现状面前,大多数人可能会默默忍受、伺机寻求突破,但少部分人也会因此变得消沉、颓丧,失去改变现实的勇气和信心。在这种“认命”的麻木与自暴自弃中,贫困会如影相随,甚至代代相传。近年来一些优秀的扶贫题材电影就让观众意识到,相对于客观条件的劣势,人的精神、观念、意志、格局才是能否脱贫的关键因素。
《又是一年三月三》中,农大安是扶贫攻坚战的旁观者和泼冷水者。他对黄永华与女儿香竹正在推进的引水工程持悲观态度,经常冷嘲热讽。对此,黄永华表示了理解,因为40多年前这个工程的功败垂成,耗尽了全村人的希望和热情。还有卢有望,年近40岁,家无余粮,成家渺茫,每天处于半醉半醒的状态中。确实,面对生活的无望,历经多次打击,一个人很难一直保持坚挺的信心,很容易在生活的洪流中麻木不仁或者随波逐流。
《三年》中,王老大沉湎于酒精,柯书记、牛书记让他养鸡,为他解决了鸡苗问题,联系了技术人员,可王老大居然把鸡吃一部分、卖一部分,卖的钱又用来买酒。
对于这类人物,影片没有一味地从道德上加以指责或者鄙视,而是以一种包容的心态去理解他们,通过对主人公的点化或者刺激,让他们主动完成改变、谋求发展,这也是脱贫攻坚战的应有之义。因为,“精神脱贫理念是精准扶贫思想的战略重点。扶贫先扶志,不论造成贫困有何种直接原因,精神贫困始终是主观上的首要根源。”③唐任伍:《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阐释》,《人民论坛》2015年第30期,第30页。
这些落后分子看上去与我们距离遥远,实则与我们并非绝缘。从社会共同体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他们的命运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的安定、繁荣。甚至,这些人物面对生活的打击产生的消极情绪,我们每个人都并不陌生。只不过,他们遇到的是经济贫困的问题,我们遭遇的可能是工作不顺、情感受挫、晋升受阻等问题,这时,我们的心态一定会比这些“后进人物”更为刚健吗?
粗略地看,这些“后进人物”都呈现出精神贫困的某些特点。我们可能不会深陷影片中那些贫困人口的生存处境,但精神上的贫困却是普遍存在的。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和贫困人口是一个精神共同体。而对于中国的稳定、富强来说,这些贫困人口和我们又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因此,扶贫题材电影不仅可以让观众看到“我”与“贫困”的关系,“贫困”与“我”的关系,还能看到“我”与他人、与国家的关系。
结 语
大部分扶贫题材电影在市场上反应平淡,甚至根本就没有进入院线,而是通过在电视台、网络上低调播映,或者组织内部小规模放映等方式,来发挥影片的“教育”功能。这种冷遇,是因为其主创未能以更加开放、更为超脱的心态去理解扶贫题材电影,未能以共同体美学为旨归去引发观众与人物的深度共情。
通过《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等影片在票房和口碑上的双丰收,我们看到,扶贫题材电影同样可以时尚感十足,可以有较强的娱乐性,可以在艺术的氛围中发挥教化的功能,并对观众产生正向的情感触动。扶贫题材电影在更有人情味更具“普适性”的操作中,不仅可以和我们这个时代产生共振,还可以与人心产生共情、共鸣。尤其在共同体美学的视域中,扶贫题材电影中不仅可以融入地缘共同体、血缘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的内涵,与观众建立一种情感共同体,还可以在社会共同体、国家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等方面完成有力度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