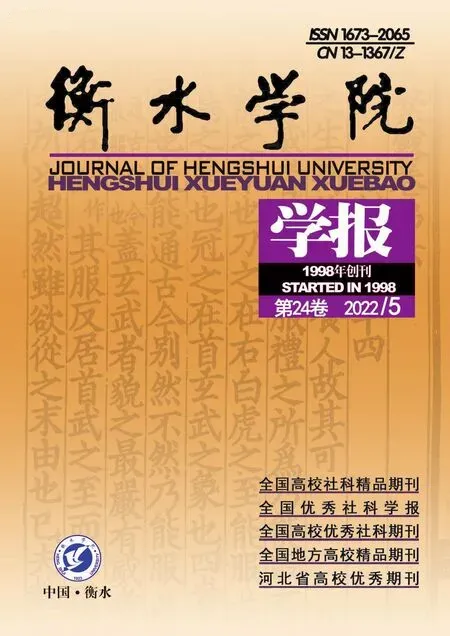杨义的“缀合”之学及“生命分析”
——以《论语还原》为例
张中宇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义先生著有专著60 余部、发表论文500 余篇,而他显然也是当代中国最重视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学者。在他的数百篇论文中,约一半都多少涉及方法论问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等刊物的专门或主要研究方法论的论文也有20 篇以上。专著如《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等同样以方法论为主旨或主线。杨义先生的方法论涉及中西比较、文学地理学等,尤重视中国特色的现代学术方法探索。杨义先生后期的研究逐渐转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领域,因此史料“缀合”及“生命分析”等方法逐渐凸显,本文主要讨论杨义先生在古代文化与文学领域的方法论突破及其价值。
一、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推进
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实证”。与自然科学的实验、测量等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的实证传统首推“书证”,即以传世文献等作为依据。但传世文献不但总量有限,同时也存在作者的主观性,书写的失误,版本的真伪,流传过程中的毁损、篡改或散佚等,因此仅靠“书证”有不少问题还是难以解决,而且所谓已解决的问题也不一定可靠。在中国,王国维首先提出“二重证实法”,后来通称“二重证据法”,即在“书证”基础上增加出土的考古实物证据,“文字数据”与出土文物互证,可一定程度补“书证”的不足或校正其中的讹误。但是地下考古材料比传世文献还要有限——除非像甲骨文献大量发掘这种千载难逢的重大进展。而研究对证据的需求总是无止境的。于是学者又提出所谓“三重证据法”,即在“二重证据法”基础上再增加一个证据来源。关于第三方面的证据,主要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口传史料”,与传世文献(“文字数据”)和地下考古文献(“实物”)构成“三重证据”;一种是文化人类学资料与传世文献和考古文献构成“三重证据”。
其实即便“三重证据”,也未必能解决大量遗存的学术疑案。杨义先生对此提出的是“会通”“旁通”,他指出:“学术方法通论的第二个层次,是在不同的学科和学科分支之间求‘通’。在本文中主要是会通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文化人类学和思维科学。……学科之间的能力和方法的移植借用,往往能够产生在原先学科相对封闭的状态中难以想象的综合效应。”[1]137杨义主张拓展证据来源,而不一定限于“三重证据”,更不必陷入何为“三重证据”之争。他推崇文学地理学,同样基于拓展文学研究空间以及拓宽证据来源的要求。杨义先生还指出:“方法论的运作,存在着四个功能性的点:(1)立足点,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本原;(2)着眼点,着眼于参与世界文化的深层对话;(3)关键点,关键是推进学理的原创;(4)归宿点,归宿于建立博大精深、又开放创新的现代中国的学术体系和体制。”可知他强调方法论的立足点必须是“中国文化的本原”,但又必须“着眼于参与世界文化的深层对话”,是一个既有文化本原根基又强调“对话”“开放”的现代主张,他称之为“世界思潮与本土血脉的双构性”[1]145,141。
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就是对所获材料的“缀合”。“补缀”原是人类特有的技能,用于工作和生活中工具、器皿、衣物等的修复,在学术上则成为考古学等的基本技术及方法。杨义先生注意到:“考古者都不甘心或满足于任由这些碎片零散地……而是对这些碎片视若珍宝,尽量按照其形状、纹饰、断口、弧度,设法与同类器物进行比照,从而呕心沥血地运用专门知识对其作出科学的修复还原,在裂缝、断口处填上黏合剂、填补材料(有时填补黏合的材料甚至超过原有的碎片)。如果没有古器物修复专家这种端庄、严谨、高明的修复还原劳动,人类早期文明行踪就很难令人震撼地以相对完整的实物形态呈现在今人的面前,许多大博物馆也会因此而黯然失色。”[2]10王国维再早也从考古学的“补缀”法悟出甲骨学、历史学研究的方法,他在编撰《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时,发现其中一片甲骨和《殷墟书契后编》中的一片有关系,应该是“一片折而为二”,于是将这两片连缀起来,称之为“补缀”,开创了“断痕相接”的甲骨文补缀之法,通称“甲骨缀合法”,成为甲骨学最为常用的基本方法。后来郭沫若进一步提出“遥缀”之说,即由于年代久远、毁损等找不到直接的“断痕相接”,但“断片”之间文字刻画的相似性、内容的相关性等具有共性,仍可进行合理“补缀”或“间接缀合”。
杨义先生把“补缀”这种技术性工作,进一步提升为相对抽象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他指出:“这个道理同样也适合于先秦诸子的还原研究。历史材料的分散辑录和严重残缺,更需要当今学人抱着对原始材料的高度尊重和珍惜,全面系统地搜集文献材料和出土材料;并将它们作为人的生命痕迹进行高智慧分析,洞察其发生、传播、结集成书的方式,考虑到有若考古地层学所出现的文化地层叠压的现象,辨析真虚、考索原委、还原现场,捕获生命信息。”[2]10因为不管是传世的“文字数据”还是考古文物,大多存在“历史材料的分散辑录和严重残缺”问题,“补缀”之法由此成为必要甚至“迫切”。杨义先生把这种方法也称之为“缀学”:“在面对着原始材料零散残缺之时,首先需要做的,不是将之更深地‘碎片化’,而是抱着一种尊重心,对之精思明辨,穷原竟委,进行认真、审慎、科学的复原性缀合。这就有若考古学上将出土的陶片按其形状、部位、纹饰、弧度、断口诸要素,在缺失部分补充石膏,复原出古陶罐的全型。这其中蕴涵着一种文化态度,不是将已经碎片化的历史残片再捣成粉末,而是进行以碎求全的‘逆向工程’,尽可能地还原古老的全罐。”[3]131
“缀学”看似简单,有的学者甚至可能怀疑“补缀”之功是否有必要称作“缀学”。其实不然。对于“补缀”来说,理想的状态是“断痕相接”,可是“断痕”恰好“相接”并不多见——通常极少,多数情况恐怕都是“似接非接”,这就需要根据“断痕”的性质、“走势”“弯曲度”等许多特征,去做出判断,可以说相当考验修复者或研究者的硬功。而且,“断痕”之间的“空缺”——有时候这个“空缺”还不小,对这些“空缺”的“补缀”甚至可能产生很大的争议。但也只有进行必要的“补缀”,“就是要把冯友兰先生说的‘也许有’但没有被记载没有流传下来的东西予以还原和真实呈现”[4]47,才能“对大量材料碎片进行全息性的梳理整合”[3]136,形成比较完整的“证据链条”。“材料碎片”之间的“空缺”既是巨大的“遗憾”,也是学术原创的重要空间。“缀学”强调“全息性的梳理整合”,与多见的“散点”式文献搜证相比,具有整体“还原”、系统整理的特点,实为传统文献方法的“升级版”。
二、《论语还原》的开创性贡献
杨义先生提出的“缀合”之学、会通等用于诸子研究,获得了什么新进展?这是检验方法论有效性必须面对的考验。杨义先生专门研究过道家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5]147,以及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的还原等。不过在杨义的思想体系中,儒家文化显然占据主导地位,他本质上是个儒者。例如“诸子还原四书”合计约92 万字[2]5,但他的《论语还原》就超过100 万字,其所用心用力,可以一目了然。这里主要以《论语还原》为例,一窥杨义先生学术方法所带来的新突破、新贡献。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300 多字,是《论语》中最长的一章,其中对曾晳着墨最多。但这一章把许多人读得一头雾水。第一个疑问是,“曾晳”到底是何方神仙?弟子对答,一般都是毕恭毕敬,但孔子点名曾晳回答问题后,曾晳却“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非得慢悠悠把一支曲子弹完了才煞有介事地回答孔子的问题,这不但在一部《论语》以及所有有关孔子及其弟子的原始记录中绝无仅有,就是在中外教育史上乃至现代教育中,这样对待老师提问恐怕都找不到第二例,以至曾晳看起来不像只是孔子的弟子。第二个疑问是,曾晳回答己“志”:“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对照“侍坐”章开篇孔子提出的问题以及子路、冉有、公西华的回答,曾晳的答对实在玄乎①历代费尽心机解释这一句的意义,各有说法,都很牵强。汉代包咸说是“歌咏先王之道”,宋代邢昺说是“知时”:“三子不能相时,志在为政,唯曾晳独能知时,志在澡身浴德,咏怀乐道,故夫子与之也。”(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附校勘记)》(清同治六年阮元主持校勘《十三经注疏》重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9、101页)朱熹引程子的话“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与包咸注差不多(朱熹:《论语集注》,见《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1页)。但清代袁枚《论语解》根本不赞成二程及朱子之说,指二程等“不得其故”(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2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21页)。今人杨树达《论语疏证》则认为:“孔子所以与(赞同)曾点者,以点之所言为太平社会之缩影也。”(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73页),孔子却说“吾与点也”。更奇怪的是,整部《论语》约500 章,曾晳仅出现在这一章,没有提出过任何重要言论也无更多事迹流传,子路、冉有甚至公西华在《论语》中出现都要频繁得多、地位重要得多,曾晳却可以留在孔子身边自由出入、随便提问。杨义先生指出:“此章是在曾子去世后,曾门弟子重编《论语》时加入的,因为行文三称孔子为‘夫子’,尤其是曾点当面问‘夫子何哂由也’,乃是战国时人的称谓方式。”[6]16其目的在于褒扬“曾子家族渊源”[7]102。杨义先生“缀合”相关文献、梳理曾氏家族及其在鲁国的地位等指出,曾门弟子利用最终撰定《论语》的“特权”,浓墨重彩塑造曾子父亲曾晳的形象。
这个解释是合理的——所有上述疑问都可迎刃而解。根据杨义先生细致梳理,曾氏家族已在鲁国经营好几代,人脉丰富、家财殷实[3]134。对于“少也贱”的孔子,曾晳投入孔子门下,曾氏家族无疑可以为早期孔学提供重要的人脉以及经济支持。我们知道能言善辩、为政经商的子贡是孔学后期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支柱,而在子贡之前,曾晳家族极有可能扮演着子贡的角色,他不是一般的弟子或仅仅只是一个弟子。由于很可能是孔学的经济和人脉资源的支持者,所以曾晳才可以在孔子身边自由出入,甚至可以询问孔子对子路、冉有、公西华的态度,其地位明显高于其他弟子。曾子在《论语》中载入“侍坐”章,其目的当然是褒扬“曾子家族渊源”。但还不止于此,曾子恐怕还要彰显——尤其是告诉其他弟子曾氏家族在儒家早期发展中的作用或贡献——这是孔子都心里有数和肯定的,以此来确立曾子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这些汇集起来,“侍坐”章足可成为曾子及其门徒最终编定《论语》最为重要的“内证”。唐代柳宗元在他的《论语辨》中提出《论语》为曾子及其弟子编定,但并没有注意到这条更有说服力的证据②见《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8-69页)。关于《论语》的编定,唐以后不少学者采柳宗元“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但这并非柳氏本义,因为柳宗元在这句话之前有“或曰”二字。“曾氏之徒”说不可信,是因为“编定”不是仅指增补少数几章或者统一“有子”“曾子”称谓之类,而是指材料的辑纂、篇章的整体审定、结构的全面安排等。这些关键的工作,庐墓三年已完成大半,其后有子、曾子等进一步搜寻、辑纂、完善。像这样极其重要的工作曾子自己不做,反而交给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且不问曾子放不放心,起码不合逻辑(现代也不可能有教授把重大工程的核心工作交给研究生去做)。柳宗元自己的观点是“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即曾子的弟子“参与”了《论语》的编定。。也正是由于传统研究方法多“散点”式的文献搜证而缺乏全面的“补缀”、会通,历代在《论语》的编定问题上颇多分歧。因为这些分散的证据如果缺乏必要的“缀合”以及会通旁证,是很难看清整体面貌的,而且还可能相互抵牾。
《论语还原》“内篇”共19 章,从第1 章到第18 章,共223页,约20 万字之巨,以讨论《论语》撰编为核心,其中会通篇章学、政治学、考据、统计等,包括“缀合”之法,提出颇多超越前人且极具开拓性的新见,在此无须一一复述。事实上,在《〈论语还原〉的方法论效应》一文中,杨义先生提出三种“方法综合”:“一是对本有生命的复原性缀合,……三是对大量材料碎片进行全息性的梳理整合”[3]129,除了不可少的“辨析”一种,两种都涉及“缀合”之法。杨义先生明确提出的“缀学”是否可以成为古代文献及历史、文学等研究解决问题抑或原创的新的“增长点”,或许有待观察。不过从汉代到清人多少有些支离破碎的“书证”或有限列举(不乏故意遮蔽不利证据之嫌)等局限来看,“缀学”强调整体“复原”以及“全息性的梳理整合”,肯定是方法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论语还原》之“外篇”合计21 章,其中9 章考索《孔子家语》之真伪、原委等,一个显然的动机是以《家语》与《论语》互补、互证,亦即《家语》等可作《论语》研究需“缀合”之碎片的“材料”来源。《论语还原》“年谱篇”进一步以史料补成“孔子暨《论语》年谱”,搜求各种散落的“碎片”以集成孔子暨《论语》发展线索,与考古学的搜求和“修复”异曲同工。
三、“生命分析”的复杂性及其风险
杨义先生指出:“《论语还原》须推求原始,走近历史现场,进入文本脉络,发现一部‘活着的《论语》’。关键在于将文本看作是人之所写、人之所编,是人之精神活动的痕迹,从而因迹求心,对文本进行深度的生命分析。”[3]130“发现一部‘活着的《论语》’”其实是“对大量材料碎片进行全息性的梳理整合”的必然结果,也是颇有意味的学术走向或一种学术境界。一部《论语》不但承载着元儒的思想,也承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甚至那个时代人们的悲欢。《论语》中的孔子不是遥不可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至圣,而是与他的弟子和那个时代的人们一起欢笑歌舞,一起颠沛流离,喜怒哀乐,充满人性与个性。这大大超越了历代解经首先把孔子捧作“非人”的神仙,支离破碎搜求训诂、无线上纲的传统经学。朱寿桐先生指出:“杨义的学术之路是将还原的指向直通古代思想家自身,直通他们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感兴”,“生命学术观实际上是相对于历史学术观的一种时代新创,至少是在历史学术观之外开辟了另一种研究历史特别是历史人物和人物思想的可能性。”[8]
王长华先生也指出:“学界以前研究孔子和《论语》的常态,是拿《春秋》和《左传》记载与《论语》相佐证,也就是说《论语》中的记载如果与《春秋》《左传》记载相吻合,那么它就基本能够获得认可,相反,如果记载仅见于《论语》,而与《春秋》《左传》相关记载不符,它就可能因证据不足而被冻结或存疑。是风相沿已久,而导致的研究现实是,有关《论语》研究的文献资料翻来覆去就那么几条,还原的事实就那么一些,结果造成有关孔子和《论语》研究的视野只能日趋狭窄。”[4]47这并不只是研究孔子和《论语》的常态,也是古代文献学、文学、历史学等的常态,大致也是中国人文科学的“传统”,至清代愈盛,当然也被现代学者承袭甚至恪守。朱寿桐先生认为“生命学术观”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即便是两千多年以前,生命感兴中的人情世故,人生境遇中的好恶爱恨,心性心理中的心灵折叠,与今天的学者和读者的生命体验都是相通的,因而从生命感性的解析去研读古书,去分析古人大抵是可靠的,至少比死守古书,死抱着古典不放的原真材料还原法更加合理,也更有时代意味。”[8]“生命体验都是相通的”,是“生命分析”的前提,也是我们还能阅读先秦典籍的前提。若世间不存在这种“相通”,先秦任何典籍我们都将无法解读(文字只是连接这种“相通”的媒介),杨义先生自然也无法与孔子及其他诸子实现精神的沟通以及还原。“生命体验”的相通就思想而言,进一步演变为思维方式的相通,思维方式的相通演变为程序性的形式逻辑,而逻辑学古今中外都是相通的——它还是源自生命体验或生命的逻辑。
创新即意味着风险,方法论同样如此。创新力度越大,争议往往就越大。“缀学”及“生命分析”这些非传统方法的提出以及相关研究,必然触动学术界固化的思维。在《论语还原》2015年出版之前,杨义先生关于《论语》的研究成果已陆续在多篇论文或演讲中发表。《〈论语〉早期编纂过程及篇章政治学》分为两部分分别刊于《学术月刊》2013年第1、2 期,已大致形成《论语还原》“内篇”的基本纲要。陈桐生教授随即著文“商榷”:“编纂《论语》这一神圣事业,在杨文中成为一个名利的搏斗场。杨文《论语》篇章政治学的要害,是遮蔽了《论语》和煦的道德阳光,使《论语》变成一座阴森恐怖、鬼影幢幢的迷宫。”[9]87陈桐生教授照例先把《论语》“神圣”化或“去生命”化——先入为主地断定孔子及其弟子必定个个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圣人或至少全是谦谦君子。他似乎忘记了孔子弟子来源颇为复杂,孔子甚至骂宰我“朽木不可雕也”,而试图以“道德阳光”代替学术的细密分析和对人性的解剖。其次,把杨义先生的“生命分析”,述为“使《论语》变成一座阴森恐怖、鬼影幢幢的迷宫”。我们看《〈论语〉早期编纂过程及篇章政治学》等论文以及100 余万字的《论语还原》,杨义先生分析包括生命群体力量博弈形成的政治学分析有之,孔门弟子派系争斗对《论语》篇章编纂的影响有之,但无论如何找不到哪怕接近于诸如“阴森恐怖、鬼影幢幢”之类的描述。当然,我们不一定怀疑陈桐生教授对学术的追求,但可以肯定创新必定带来某些“不适”。方法论也总要探索它可适用的边界或“临界点”,这无疑意味着学术冒险。“缀学”及“生命分析”等的复杂性抑或某些不确定性更需要微妙把握,否则可能产生某些“越界”。但无论如何,高度创新的方法及其研究成果,都远胜于思维的固化以及墨守成规的不作为——或如王长华先生所说“造成有关孔子和《论语》研究的视野只能日趋狭窄”。
杨义先生的成名作《中国现代小说史》140 余万言,其中对中国现代小说原作以及原作发表报刊、早期版本等所作的大量翔实的实证研究,一开始就显示了杨义先生的硬功甚至“苦功”。他指出:“治学的关键在于把握住两头:一头是过硬功夫,一头是原创思想。以过硬的功夫托出原创的思想,以原创的思想照亮过硬的功夫。”[2]11方法论是由“过硬功夫”导向“原创思想”的桥梁。没有更具现代视野的方法论,“过硬功夫”有可能徒然耗费于重复抄写或学术生命的原地打转;而缺乏“原创思想”,也就没有知识和智能的“增量”、累积以及中华文明的持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