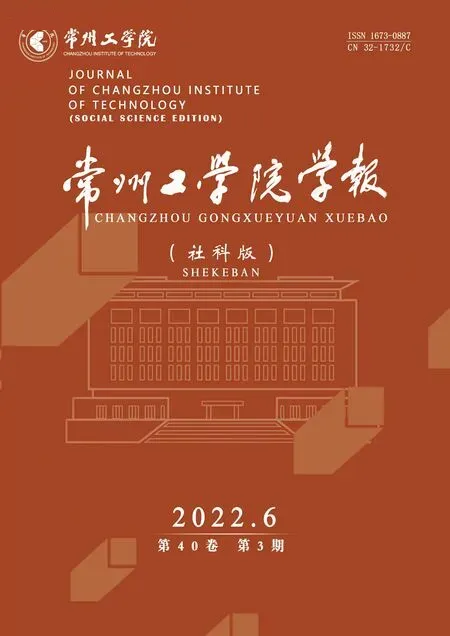融媒体时代大运河文化影像建构与传播转向
彭伟
(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江苏 常州 213022)
大运河是我国“通南北、鉴古今”的伟大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1]。这给大运河文化的影像建构与传播提出了更高要求。事实上,自大运河申遗成功后,相关主题影像成果鲜有佳作,无法满足融媒体语境下大运河文化的当代传播需求,大运河文化的影像建构与传播亟须完成从目标定位到范式策略的自我更新。
一、文化遗产影像化概述
“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概念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二战”后首次提出。全球化、工业化等社会变革加速了全球对自然与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文化遗产被破坏或滥用现象严重,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势在必行。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旨在保护文化古迹、历史建筑和自然遗址等物质与文化遗产[2]。“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于2001年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宣布计划”项目中首次提出并得到广泛关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再次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将文化遗产定义为一种代代相传的,作为对社会环境、自然世界和历史的回应而进行的再创造成果。从文化遗产的概念演进历程不难发现,文化遗产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融合,大运河文化就是一种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廊道式遗产集合体。
正是由于文化遗产具有集合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很早就认识到影像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作用。首先,在申遗过程中,申请地区除了需要提供书面材料,还需提交包括照片和视频在内的遗产要素可视化内容,文化习俗的视听记录和表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建议了相关影像创作的内容、时长和技术要求,但对制作方法、风格和目标观众却只字未提。后来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发现,过多的限制不利于文化遗产的影像化。其次,影像本身就是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世界记忆工程”,以确保世界上珍贵的文献遗产得到关注、保护和推广。该工程包含文稿、文件、地图、书信、录音、影像等各类文献遗产,并借助数字化手段和互联网进行宣传和推广。最后,从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保护”包含鉴定、记录、研究、保存、活化、推广、教育和传播等职责,并在其中突出“普遍价值”的核心理念。在传承过程中,影像也为“引导人们对文化遗产投入广泛兴趣”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影像化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然选择。
西方最早的文化遗产影像是以民族志记录方式出现的。1895年,法国人类学家费利克斯·路易斯·雷格纳特拍摄了西非沃洛夫妇女用传统技艺制作陶器的过程。随着电视的普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化遗产影像都是以新闻报道或旅游宣传片的方式出现的。纪录片专题创作出现后,非遗影像的视听呈现方式逐渐发生变化。20世纪40年代,玛格丽特·米德和格雷戈里·贝特森系统而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影像记录。
相较于西方国家,我国的文化遗产影像化创作起步较晚,多以专题纪录片方式出现。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影像化,不仅形制上有明显的学习痕迹,而且也形成了诸如“知识分子介入”等本土化特色。正如德瑞克·吉尔曼所言,人们总是有目的地阐释文化遗产的价值。大运河文化具有独特的廊道遗产线性组织特征,因此在影像化的过程中,需要聚焦整体文化形象特色的建构[3]。
二、大运河文化的影像化传播困境
文化遗产的传播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定社会文化的展示方向和接受水平。大运河文化在经历了申遗阶段的集中影像化创作后,逐渐面临创作模式陈旧、类型同质化、传播目标失焦等问题。
(一)后申遗时代的传播失焦
对比大运河文化影像创作的前两次高峰,申遗成功后的影像化出现了传播“失焦”的问题。1986年的纪录片《话说运河》是大运河文化影像化的第一项重要成果。该作品由冯骥才、刘绍棠、李存葆、汪曾祺等撰稿,费孝通、林一山、钱正英、侯仁之等学者参与创作,影像具有一定的文献、史料价值。《话说运河》不仅引起了全社会对大运河的关注,其创作方式的种种创新之举对后来的纪录片拍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2014年,大运河申遗阶段,央视纪录片《大运河》《中国大运河》等在助力申遗的同时,推动了大运河文化的可视化推广。不管是《话说运河》对水文化以及民族自信的关注,还是《大运河》对申遗的推动,文化遗产的影像化都有明确的传播目标。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不仅指“物质的生产”,也是“表意的”或者“象征的”体系[4]。后申遗时代,一方面,全社会对挖掘、继承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期望很高,另一方面,影像化成果却没有更清晰明确的聚焦点。具体表现为:首先,近年来少有作品在前作的基础上作继承性创新,现存作品多为既有范式的重复。其次,大运河文化遗产影像化创作者未在内容和方向上做更深入细致的挖掘。最后,在影像化的过程中,建构文化形象和文化品牌的意识不足。
(二)跨文化传播效能有待提高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跨文化传播,有助于有效地实现地区间、文化间的交流。就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影像化传播而言,其跨文化传播效能有待提高。大运河贯穿全国18个城市,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城市的知名度、被关注度和文化宣传投入力度不尽相同,因此其跨文化传播效能存在较大差距。比如,杭州在古代就被西方国家称为“天城”,马可波罗在对杭州“万桥”之城的描述中,将大运河与杭州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甘博兄弟于20世纪初拍摄的杭州大运河影像亦成为大运河文化影像传播的起点。这种传播效能的不平衡,必然会对大运河文化遗产完整立体的文化形象建构产生影响。即便如杭州、扬州、苏州等知名度较高的运河名城,在申遗成功之后,也没有形成更多有关运河文化遗产的影像化成果。这充分说明大运河文化遗产影像化程度不深,传播内容输出不足。
(三)传播资源的利用不充分
文化遗产的传播方式大致可分为口述传播、视像传播、事件传播3种类型,而影像化是能够将三者融于一体的当代传播形式。目前,我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影像仍以专题纪录片为主,对传播平台和资源的利用并不充分。从技术层面看,首先,文化遗产影像化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混合现实(MA)等技术已经将影像与交互结合起来,国外如PATRIMONI、FACTUMarts等诸多机构都在文化遗产的影像化方面取得了创新成果。我国也有类似创作实践,但运用在大运河文化遗产影像化方面的典型案例不多。其次,互联网和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为影像的传播提供了更多平台,但在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等国内主流视频播放平台上,大运河文化影像仍以电视纪录片为主,点击量不高。以“大运河”为关键词的公众号数量较多,但普遍存在关注者少、活跃度低的问题,且鲜见原创影像作品。此外,截至2020年8月,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数据显示,与大运河相关的社会组织达444个,运河沿线城市建有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等主题展馆,各地政府、高校以及各级各类大运河研究院是否有相关影像成果,如果有,以何种方式传播,不得而知。
三、融媒体语境下大运河文化的影像化传播策略
就融媒体时代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影像化传播而言,只有积极整合媒体资源,明确传播目标,深挖文化内容,完成从传统传播方式到融合传播方式的转向,影像才能在当代语境下充分发挥保护、传承、活化文化遗产的功能。
(一)媒体资源的多元融合
麦克卢汉认为,人类文化传播的历史已从口语传播和文字传播时代进入了电子媒介时代[5]。在激发更多媒介参与文化传播的同时,交融互动也促成了媒介形态由简单到复杂的不断变化。当下,主要从影像化资源和传播平台资源两个层面对媒体资源进行多元融合。首先,当下影像的类型和形制日新月异,如3D Mapping已经让影像跳出屏幕,进入开放空间。以交互投影方式让传统的、静态的文化遗产焕发新活力的尝试也越来越多。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技术的介入,让影像从记录内容走向参与创作和制造事件。在今天的文化遗产影像化过程中,不应回避这些新的传播形式。其次,影像资料的公开和共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播的要求。因此,许多国家都采用影像资料库上网的方式,展示、共享自己的文化遗产。德国、匈牙利等欧洲国家都建有自己的在线民族志博物馆,全球公众能够通过这些双向交流的平台访问文化遗产影像。国际博物馆理事会(ICOM)下属的国际多媒体委员会(AVICOM)负责向全球收集相关影像资料,并进行数字化规整工作。现如今,一方面,文化遗产影像的传播更加顺畅,吸引了更多的人关注和共同研究这些影像。另一方面,数字化也加速了文化遗产传播的多资源融合,有利于中国优秀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普及,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普及和推广[6]。对于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随着传承人的老龄化和习俗、环境的改变,影像资料的数据库化显得尤为迫切。这种开放式的共享,能够引导公众参与讨论,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和传承。
(二)影像传播场景的跨领域植入
除了独立作品的主题化呈现,大运河文化影像还应当通过主动跨界的方式,寻找在不同场景中的传播机会。文化遗产的具体要素是丰富的,遗迹、技艺、习俗等都是文化遗产的具体形式。仅就范围和接受度而言,如果在影视剧的创作中融入大运河文化要素,往往能取得比风光纪录片更好的传播效果。近年来,北京地区的文艺工作者以大运河为题材,创作了118部文艺作品,包括影视剧、话剧、动画、戏剧、交响乐等各种形式,《大运河》《守敬龙泉》《大运河奇缘2》《运通天下》等都是广受好评的优秀作品。以活动的方式完成“事件化”的传播,是大运河遗产影像跨界植入的另一种思路。例如,2018年,扬州举办了首届运河主题国际微电影展,在1 833部参展作品中,157部作品来自美、英、法等海外国家和地区。除了主题影像,与主题相关的活动的影像化,同样也是不错的传播行为。大运河主题歌舞剧《遇见大运河》在全球巡回演出,艺术家们在街头以“快闪”的方式与法国米迪运河、德国基尔运河、埃及苏伊士运河以及希腊科林斯运河“相遇”,这些有趣的快闪视频影像,成为传播运河文化的有趣形式。在2019年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出版集团推出了“穿越时空的中国”数字影像展,展览以大运河为创作背景,在巨型屏幕上用三维动画结合二维场景的方式,演绎了2 500多年的大运河文化变迁故事。跨界植入不但能丰富影像传播的场景,而且可以使运河文化影像传播的途径更加丰富。
(三)内容视角的主动转变与拆解
阿莱达·阿斯曼认为,文化遗产作为承载文化的“回忆空间”,是需要被解释的[7]。解释的内容和视角决定了遗产的文化形象。文化遗产的影像化创作者不应将作品拍摄成广告,这些影像的传播目的不是宣传,而是对遗产主题要素及其所处社会生态的可视化。人类在文化的传承中不断地改变着文化,形成新的文化观,影像化的过程可以帮助文化遗产形成新的阐释体系。就大运河文化而言,其影像化过程需要创作者有整体的线性廊道遗产的概念,以客观的态度对空间、时间、风物、人文、习俗等内容进行分类。正如特伦斯·霍克斯所言,任何事物只要它独立存在,并和另一事物有联系,而且可以被解释,那么它的功能就是符号[8]。大运河文化影像建构的具体内容应该具有符号性,当宏观的大运河文化被拆分后,这些符号仍然可以被解释,也容易被表现和识别,并可以通过不同要素的对话实现重构,焕发新生。从传播广度上来说,大运河文化影像传播的内容需要制造覆盖面更广的“共同话题”,让受兴趣驱动的受众主动参与文化传播。大运河文化的影像化主题需要更贴近大众的需求,以便在传播中实现更精准的投放和推送。在大运河文化遗产影像化和传播过程中,一方面要不断深挖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以影像化手段传承与弘扬文化经典,另一方面还要保持、凸显大运河的本民族文化特征,回归当代日常生活,回归对大运河文化整体生态的关注和展现,使内容在引发受众共鸣的同时,激发受众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助力构建当代大运河文化的共同记忆。
四、结语
做好大运河文化的对外传播,运用影像讲好中国运河故事,是关系到国家形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工作。大运河申遗成功后,大运河文化遗产影像化一度出现了传播失焦的问题,跨文化传播效能亟待提高。在当代融媒体语境下,媒体资源的多元融合、影像传播场景的跨领域植入、内容视角的主动转变与拆解,将助力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影像化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