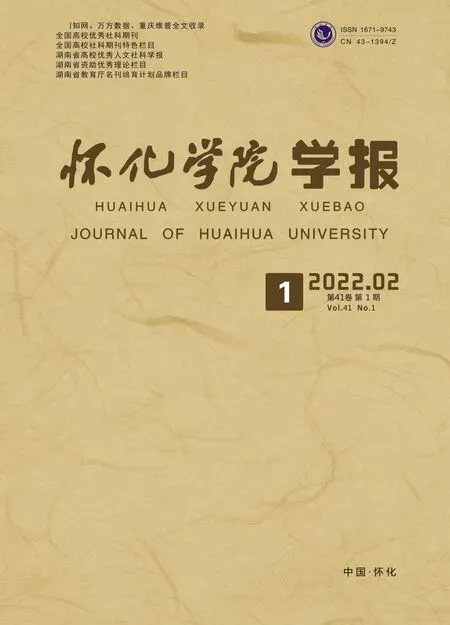金介甫《沈从文传》的跨文化互文叙事
肖远东, 简功友
(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张家界 427000)
引言
美国著名汉学家、沈从文研究专家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 自1972年开始研究沈从文,他认为研究沈从文的作品不应局限于乡土方面,只有中国人的研究,而要从世界文学的视野来思考。随后其出版的《沈从文传》 (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1987) 震惊了海内外学界,金介甫本人也获得了“国外沈从文研究第一人”的美誉。《沈从文传》全书用英文写就,夹叙夹议,论证翔实,除了极力糅合历史资料还原沈从文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金介甫更是花费了大量笔墨来讨论沈从文的作品与西方文学流派、西方作家及西方经典作品之间的关系。就这一部英文人物传记而言,作者在材料的选择与结构的安排上,不仅处处体现着传记的叙事伦理,更是时时与中国文学对照体现出跨文化互文的特征。所谓“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也称为“文本间性”,最早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于20 世纪60年代提出,意在综合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巴赫金(Bakhtin) 的语言理论[1]8-31。克里斯蒂娃[2]66指出:“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她认为,文本并非个体的、孤立的,而是各种文化(社会) 文本的集合,也就是说,广义上的“互文性”存在于一切文本之中。此后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3]1-2又对“互文性”给出了相对狭义的解释,称其“本质上是一个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实际体现”,主要体现为引用、抄袭、影射等手法。虽然该术语被广为使用,却很少有人对其下过一个精确定义。李玉平[4]67在《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一书中试着对“互文性”进行定义,认为“互文性是指文本与其他文本,文本及其身份、意义、主体以及社会历史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转化之关系和过程”。在这一定义的启发下,我们对于“互文性”的研究将不再局限于文本语篇之间,而应该对文本及其背后的集合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因此,我们认为“互文性”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文本语篇的生成与文化有关,“象征着对一种文化的话语空间的参与[5]8”,并且存在跨文化性。韩艳梅和陈建平[6]32,37从语言学的角度阐释了“异国文本被引入本国文本的过程是一个参与本族文化话语空间并经历再语境化的过程”,即“跨文化互文实质上是文化的再语境化”。作为与传主身处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金介甫,在创作英文传记《沈从文传》时,必然会将大量中国文本引入西方,并展开西方文化话语构建。也就是说,金介甫《沈从文传》的创作过程是一个跨文化互文叙事过程,即:文本与异国文本、身份、意义、主体以及异国社会历史等集合体之间相互联系与转化的关系和过程。本文拟从跨文化互文性出发,从不同维度分析金介甫《沈从文传》的特殊叙事策略,以期为同类型文本的写作与鉴赏提供新的思路。
一、跨文化摘译:《从文自传》的再语境化
传记的叙事创作通常离不开作者对现有文本材料或直接或间接的引用与改编,这无疑是一种叙事上的互文建构;如果作者引用或改编的文本材料来源于异国文化,则会为这种互文叙事附加一层跨文化的属性。金介甫在《沈从文传》 的创作过程中,引证广博,言必有据,偏重学术考证,使之成为一部“几乎可以说是沈从文本人认可的传记”。为了确保传记文学创作应有的真实性,搜集到最真实的一手资料,金介甫数渡重洋,实地寻访,与沈从文本人密切往来,仅是创作的资料卡片就搜集多达六千张,注文字数几乎为正文一半。据《沈从文传》中文版译者符家钦先生[7]374粗略统计,金介甫在注释中提到的晤谈作家学者高达118 人次,可见其专业与用心。在上述材料中,1932年出版的《从文自传》无疑是《沈从文传》史料的主要来源之一。笔者统计后发现,《沈从文传》书中646 条注释中,超六分之一来源于沈从文先生的《从文自传》,尤其是在故事叙述性最强的第一章《湘西少年》 与第二章《青年时代:沈从文和湘西都在自谋出路》。可以说,《从文自传》是金介甫创作《沈从文传》的基石,金介甫有选择性地摘译《从文自传》中的文字,并使其得以在西方文化中再语境化,这对于传记初始世界的构建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沈从文传》的第一章中,金介甫首次介绍镇筸城(今湘西凤凰县) 时曾有过这样描述:
清军在苗山深处建起了许多边境军事哨所,有城墙也有岗楼。其中有一个小镇建于1700年,用来管理生活在镇溪和筸子坪的苗民,此处名为镇筸。1704年,当统辖整个湘西兵马的兵备道将总部设在这里时,这里成了当地汉族和满族治下的政权中心。尽管1911年定居在镇筸城里的人只有3000 至5000人,但驻扎在附近的正规军人却高达7000 名。他们的职责不仅在于安抚山里的苗民,还要做好“开化的”沅水流域以及临近省份的绥靖工作[8]18。(笔者译,下同)
仅仅几行文字,金介甫就向读者交代清楚了凤凰县城在湘西历史上的“地位”和旧名缘起,一幅宏伟的湘西画卷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循着传记中的注释,笔者在《从文自传》中找到了与此段文字对应的出处,发现实际上金介甫笔下对凤凰县城的介绍是对《从文自传》所载内容的摘译与补充:
只由于两百年前满人治理中国土地时,为镇抚与虐杀残余苗族,派遣了一队成卒屯丁驻扎,方有了城堡与居民[9]1……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辰沅道皆驻节在此地。地方居民不过五六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七千[9]3。
田英华[10]209在对比传记体文本与虚构性叙事文本的不同特点时曾指出,“传记体中的互文性更多的是强调主文本与互文本之间的一致性,以依靠一致性来达到真实的效果。”如上述案例所示,金介甫对《从文自传》中相关内容的摘译,实现了该部分内容在西方语言文化中的再语境化,使得主文本《沈从文传》与互文本《从文自传》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致性,主文本《沈从文传》内容的真实性因此得到了佐证。在介绍沈从文童年趣事时,金介甫几乎“照搬”了《从文自传》中的相关内容,使得读者纵然与沈从文所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与不同文化环境,仍能够透过金介甫笔下的传记切身地感知湘西人民的淳朴智慧以及沈从文童年的快乐时光。比如在介绍游泳时“往裤子里兜空气做‘水马’”这个活动时,金介甫就这样写道:
沈从文的童年生活是如何度过的,倒是用不着我们去瞎猜。他的同伴都是自家亲戚和壮实的野孩子,他们常常一同爬树、打架、挖竹笋、摘浆果,有时还会采药草来医治打闹留下的伤口……夏天孩子们喜欢捉蟋蟀,看木偶戏,或者花一下午时间捉螃蟹,再或者跑去河里游泳。如果你不会游,就把裤腿绑紧,然后往裤子里面兜满空气,用作救生用途。但沈从文会游泳,且老是下河去游泳,完全无视家人对他安全的担心[8]24。
作为一名来自异国的作者,要想在本族文化中原汁原味地还原沈从文的童年生活并不容易,这一过程必然离不开各类可靠文本材料所提供的辅助支撑。金介甫在上述段落中所描绘的场景,就是分别摘译了《从文自传》中第26、27、30 等页的相关内容,并将其糅合重组,转化成其本族语言:
每天上课时照例上上,下课时就遵照大的学生指挥,找寻大小相等的人,到操坪中去打架……几个人一下课,就在校后山边各自拣选一株合抱大梧桐树,看谁先爬到顶……因为爬树有时跌下或扭伤了脚,刺破了手,就跟同学去采药,又认识了十来种草药[9]26。我学会了采笋子,摘蕨菜……在那里最有趣处是可以辨别各种禾苗,认识各种害虫,学习捕捉蚱蜢分别蚱蜢[9]27。天热时,到下午四点以后,满河中都是赤光光的身体。不会游泳的便把裤子泡湿,扎紧了裤管,向水中急急地一兜,捕捉了满满的一裤空气,再用带子捆好,便成了极合用的“水马”。有了这东西,即或全不会漂浮的人,也能很勇敢地向水深处泅去[9]30。
罗勋章[11]87在谈到传记文学中的叙事伦理时指出:“无论自传、他传还是别传,传主与传者(作者) 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因此,若说《从文自传》是一部客观而审慎的自传,借用数学中(a=b,b=c,则a=c) 的等量代换定理来看,金介甫先生大量汲取《从文自传》中的内容来进行传记创作,或直接引用,或揉碎重组,选择以不同主体发声,不仅凭借介于他者塑造与自我讲述之间的互文关系证明了《沈从文传》内容的真实性,建立起两种不同文化间读者、传者与传主沈从文的联系,还为海外读者全方位了解沈从文提供了可信的文本支撑,让他们能够亲切体悟到中国一代文坛巨匠所经历过的人生起伏。在叙事过程中,沈从文通过自传映射出的人生经历被金介甫摘译并再创造在其本族文化中,这无疑是《沈从文传》与《从文自传》——一部由美国人书写的英文传记与一部中国人写就的自传跨越语言文化背景互相阐发的互文性凸显。
二、跨文化批评:从文作品的再语境化
前文提到,跨文化互文叙事是指文本与异国文本及其背后的集合关系间的相互联系与转化,这不仅体现在不同语篇之间,也同样适用于同一文本内部。田英华[10]209在《语言学视角下的传记体研究》一书中将传记体中的主要互文表现形式分为“文本内部的互文性”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两个方面。其中“文本内部互文性”的表现形式中,又以“不同叙述文本单元之间的互文性”居多,这在金介甫《沈从文传》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作者的引述单元与叙述语言间形成的互文关系,即在叙事中恰当地选取沈从文的作品来阐释、例证自己对沈从文作品的批评与赏析,使得《沈从文传》兼具评传的特点。
白保罗[12]185曾评介《沈从文传》 一书,称其“最大的一个优点是提供了大量事实材料”。在《沈从文传》的序言中,金介甫也曾明言这是一本“记述沈从文的一生,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他的艺术,从全方面来进行考虑”的书。因此,这部人物传记并没有过分专注于一些细枝末节的八卦故事,而在倾尽全力挖掘“为中国文坛造就了一个沈从文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沈自身的个性根源[13]6”。事实上从本书第三章后面部分开始,金介甫就有意识地解读沈从文的作品及其背后的思想转变,传记中第四、五、六章的内容更是如此。为此,金介甫搜集、研读了上百本沈从文的作品和中文文献资料,并选取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进行分析、研究和鉴赏。比如在谈到沈从文的“第一批新式作品”时,金介甫就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对沈192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棉鞋》进行分析,认为在其写过的众多自伤贫贱的作品中,“这一篇写得最有讽刺意味且富有幽默感”[8]88,从写作手法上来看,故事的结构“可以说是继承了中国话本小说的技法,也可以说是现代意识流作品不连续写法的前驱[8]91”。在这样一个传记叙事情景中,金介甫对作品《棉鞋》的解读内容与从小说原文中摘译来的示例片段之间形成了跨文化互文关系,后者为前者奠定了事实基础,前者是后者在异国话语空间中的再语境化。
除此之外,同一传记文本中多个引述单元之间也可能存在互文性,这在《沈从文传》中同样常见。传记的后半部分内容以分析沈从文的作品为主,因此金介甫在解读沈从文的一些包含湘西历史、文化、风俗的乡土作品时,自己所搜集到的真实史料与从沈从文作品中直接摘译的文本内容之间也会产生跨文化互文,相当于在传记的创作过程中同时引用了多个具有互文关系的不同文本,大大加强了论证的说服力。例如第四章《沈从文乡土文学的根源》中,金介甫为了论证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在谈到19 世纪湘西男女唱歌求偶风俗时将自己专门搜集到的资料附在文中:
……有些地方甚至专门开设马廊,以供未婚男女见面,求爱,不必受到父母的干预。通常,年轻人们是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可供约会的,例如在新年和椎牛大典,否则,散落在山间各处勤劳生活的人们很难聚在一起[8]141。
随后他提到沈从文受到当地风俗的启发,也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写过青年男女结伴找对象的细节,并附上沈从文作品《龙朱》中的一个片段来证明:
白耳族男女结合,在唱歌庆大年时、端午时、8月中秋时,以及跳新年椎牛大祭时。男女成群唱,成群舞。女人们各穿了峒族衣裙,各戴花擦粉,供男子享受。平常时,在好天气下,或早或晚,在山中深洞,在水滨,把男女吸到一块来,即在太阳下或月亮下,成了熟人,做着只有顶熟的人可做的事[8]141。
鉴于上述金介甫搜集到的资料与沈从文作品中的选段叙述对象完全相同,因此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并列”的引述文本,彼此间存在互文关系。李玉平[4]61受修辞学启发,曾将“互文性”分为“积极互文性”和“消极互文性”两种,认为“积极互文性是指当互文性要素进入当前文本后,发生了‘创造性的叛逆’,与原文本相比产生了新的意义,与当前文本形成了某种对话关系”。沈从文对小说《龙朱》的创作不仅是被动地取用湘西风俗,更是对其的承续与创新,二者之间存在“积极互文性”关系,因此这种引述单元间的“互文性”为传记本身的叙事带来的影响无疑是正向的,搜集到的事实材料与传记中沈从文作品选段的再语境化内容都能够为金介甫所阐明的观点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罗勋章[11]88在谈到史实与传记的叙事伦理时曾提到,传记的叙事常常是建立在众多的既有文本材料的基础上,是一种“对叙事的叙事”。金介甫在沈从文传记创作的过程中,不仅考证翔实,精选了大量能再现沈从文生平的传记史料,同时还细致地阅读了沈从文的每一部文学作品,结合时代背景,用沈从文的艺术作品来分析佐证他的思想和精神,使读者不仅能够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审视湘西近现代社会的变迁,也能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解读沈从文的小说及其背后的价值。这种引述单元与作品呈现之间形成的种种跨文化互文关系,为这部传记的叙事增添了更加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学术价值。
三、跨文化阐释:从文思想的再语境化
“互文性”的特性决定了我们对它的讨论不仅可以基于文本、作者,还可以基于读者层面。我们之所以认为读者的阅读活动也具有互文性,是因为读者在阅读之前已经具备小到生活常识,大到社会文化、历史地理等认知前提,在对作品进行互文性解读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无论是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提出的“作者已死”还是伊瑟尔(Wolfgang Iser) 提出的“文本保留剧目”等概念都能证明。李玉平[4]116认为“读者的经历有助于对文本的互文性解读,反过来,文本也会影响到读者的生活”,因此我们可以在作者叙事与读者接受之间找到一种广义的互文性关系。事实上,由于《沈从文传》的目标读者多为外籍人士,金介甫在此部传记的叙事中也特别关照了这种互文性关系。
作为一位研究沈从文多年的学者,汉学家金介甫学识渊博,精通中西文化,在《沈从文传》的创作过程中,除了还原沈从文的主要人生经历、介绍其作品风格外,金介甫还致力于探究发生在沈从文身上的“中西文化碰撞”及影响,将沈从文的各种传记事实以及沈从文文学作品中艺术特色通过相关的西方文化理论来进行阐释,实现了沈从文思想在西方语境中的转化。这在国内沈从文研究专家凌宇所撰写的另一部《沈从文传》中却并未体现,虽然两本传记都是广受学界认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沈从文研究专著,但凌宇版《沈从文传》的叙事局限于对沈从文人生经历的诗意描写,少了一些客观分析和理性思辨。李伟[14]47的观点也可证明这一点:“书中(《沈从文传》中,笔者注) 金介甫用了大量篇幅分析沈从文思想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的部分,并将这种影响看作是沈从文人生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比如文中第三章金介甫谈到沈从文的作品角色依据时就曾认为这是对西方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借鉴:
沈从文小说中提到的外国文学名大多都是以西方文学中的人物命名的,主要是19 世纪俄国与法国小说家、剧作家,其中在中国出名的有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理、高尔基、莫泊桑、都德、法朗士、福楼拜、纪德、易卜生、王尔德和安徒生。这些作家的作品不全是现实主义,却为沈提供了社会的、情节上的借鉴[8]80。
除了借鉴人物名称和情节,金介甫认为沈从文在创作的过程中也应用了西方心理学等西方思潮,比如“1925年沈从文在小说《用A 字记下来的事》中就提到了‘潜意识’;1926年创作散文《怀化镇》时还使用了自由联想的本事[8]80”。他认为这些都是西方思潮对沈从文创作思想带来的影响。
在对沈从文作品进行密集介绍的章节里,金介甫更是将沈从文的作品与西方的名家们的作品频频作比,使得西方读者可以凭借自己的认知前提在阅读过程中与沈从文的思想产生“互文性”共鸣,确立了沈从文及其作品在西方读者心中的地位。比如书中第三章介绍沈从文的长诗《曙》时,金介甫就将其与小仲马的《茶花女》 和歌德的《少年维特》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在情节上有异曲同工之妙[8]80;提到沈从文1928年的另一部作品《阿丽思中国游记》时,金介甫认为其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更能体现18 世纪文学里前浪漫主义时代的精神,并且“显然是从路易斯?卡洛尔那里得到的启发[8]93”;对于沈从文创作的《中国旅行指南》,金介甫又认为这“完全看得出这是在模仿斯特恩的《项狄》[8]94”。再如在介绍沈从文的抒情诗人身份时,金介甫首先将其与福克纳相比较,认为“沈从文早期的作品中,诗并不占重要地位[8]118。”随后他又举了《我喜欢你》 《颂》等例子来阐述沈从文诗歌的主题与维多利亚时期的浪漫派爱情诗人拜伦和勃朗宁一样:“写美人,写得不到的女人,写沉溺于自然,时间飞逝,生命季节匆匆消逝,灵魂自由却有极限以及是否有爱女人的资格”[8]118。对于诗歌的用词,金介甫又觉得沈从文用词平易,富有视觉和触觉等感官体验,读起来并不晦涩朦胧,有些诗甚至是在模仿泰戈尔[8]119。
通过金介甫的这一番对比阐释,外籍读者能够凭借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个人经历和知识储备等认知前提对传记中沈从文的思想、作品进行科学解读,因此更能理解沈从文为何值得作者为他著书立说。作者意欲表达的信息与读者的接受能力得到了适配,沈从文的创作思想由此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进行了再塑造,其人及作品在世界文坛中的地位与价值也得以确立。
结语
金介甫的《沈从文传》除了是一部获得传主认可的成功传记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是一部由外国学者直接撰写的国人传记。也就是说,这部传记先天具备一种跨文化性。但无论什么样的传记作者,在传记的写作过程中,“互文性的存在是客观的也是必然的,这是由于传记体特殊的功能和特殊的生成方式所造成的”[10]207。“互文性”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传记体文本的真实性,使其区别于虚构类文本。在《沈从文传》的创作过程中,历史学出身的金介甫首先通过大量摘译传主自传中的材料,为外国读者了解沈从文提供了充实、丰富的文本支撑,实现了他者塑造与自我讲述之间的跨文化互文凸显;其次,金介甫细致阅读了沈从文的大量文学作品,并精选相应的史料来对其进行批评赏析,实现了传记文本内部引述单元与沈从文作品、传记文本内部众多引述单元之间的互文性,强化了自己论证分析的准确性;最后,金介甫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出发,对沈从文思想进行阐释,通过在西方文化理论和沈从文思想之间搭建互文桥梁,让陌生的外国读者对沈从文作品的价值和地位能够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总而言之,金介甫通过跨文化摘译、跨文化批评和跨文化阐释等策略,借助文本间的互文性关系进行叙事,突出了文本真实、客观的传记叙事效果,让沈从文这位从湘西走出来的本土作家,站上了世界文学的舞台,并变成了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这也是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较于一般传记更加突出的特色所在,同时也是传记叙事艺术研究应该拓展的视角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