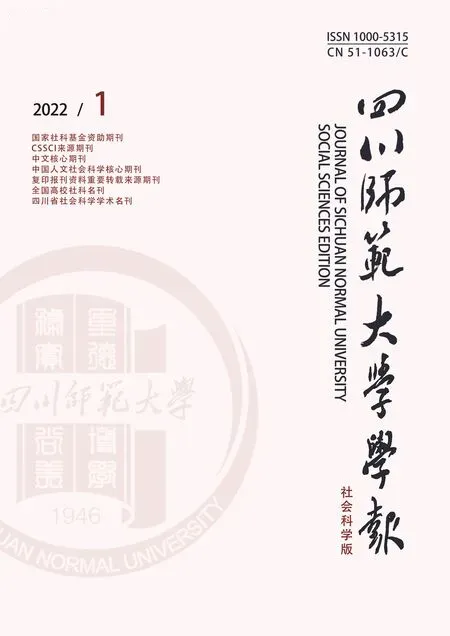儒学“弦歌沧海滨”
——论儒学在黎族地区的双向互动和发展
李元光
明代“理学名臣”丘濬在《南溟奇甸赋》中,从“理学”之“地脉”、“人脉”、“文脉”角度,论证了中华大地一脉相续,中华民族一脉相传,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在这个共同体中,探讨孤悬海外的海南如何赓续中华文化基因,对正确理解“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意义尤为重大。
在我国56个民族中,海南黎族是一个古老民族,早在三千多年前黎族先民就生息在这个美丽而富饶的海岛上。在周秦汉文古籍中就有了关于黎族的记载,“雕题”、“儋人”、“绥耳”、“杨越”、“珠崖人”、“俚”等是对其族名的称谓。就海南岛而言,唐虞三代属化外,秦朝属编外,汉朝才正式将其纳入版图。汉之后,在建制上多个朝代时废时立,几经反复至隋朝才稳定下来。
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黎族是接触儒家文化最晚的少数民族之一。对海南而言,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孕于古、启于唐、兴于宋、盛于明。三代至隋为孕育期,这一时期将黎人生活的海南岛逐渐纳入中央政府的治下,历朝历代进驻海南的官员、戍边的士卒、避难或经商的民众等中原人的到来,土著黎人开始接触汉人与汉文化,成为日后儒学在海南传播与发展的铺垫。唐代将海南作为罢免官员的流放场所,这些官员到来后,开始兴办识字学文之类的讲学堂,为传播儒家文化之肇始。宋朝特别注重对少数民族的儒学教育,随着海南第一所高等学校“琼州府儒学”的诞生,各州县纷纷建立的儒学堂达13所之多,特别是这些学校皆注重吸收黎族子弟入学,加之当时以贬官苏东坡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也纷纷举办“载酒堂”一类的儒学交流与传授场所,海南竟出现了时人李光描述的“弦歌之声,洋洋盈耳”,“学者彬彬,不殊闽浙”的可喜局面。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不仅重视对少数民族的儒学教育,而且一改过去丑化、歧视海南的态度,称其为“南溟奇甸”。儒学在海南的发展也可谓盛况空前,上升到对儒学理论作出重大贡献的“创新性发展”新阶段。
一 孕于古
明人王佐曾说:“切[窃]见古珠崖地乃今琼州府十三州县也,唐虞三代未入《禹贡》职方,汉武帝元鼎五年平南越,明年始与南海等并立九郡为内地。汉不择守者,因鄙夷其民,治之不以道,遂致郡县陷没,复为裔土,终两汉之世以迄六朝五百余年。唐宋监汉失选守牧,治以内治,数百年间遂成雅俗,衣冠文物与中州等。元始以土人为官,分管州县兵民,卒受其弊,九十三年之治无足观者。我朝圣圣相传,百年以来风移俗易,媲美唐宋,蔑以加焉。伏观太祖玉音,尝称海南为南溟奇甸,又称其习礼教,有华夏之风。”(36)王佐《进〈珠崖录〉表》,王献军主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一,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第461页。王佐的意思是,汉代以前海南岛尚未纳入中原王朝的治下,两汉至六朝虽在海南设郡县以管制,但用人不当,鄙视少数民族,没有用心加以治理,招致郡县时立时废。唐宋吸取其教训,加强了对海南治理与教化,经过几百年中原文化的浸润洗礼,原本蛮荒之岛,风物人情渐趋中原。元朝依赖“土官、土舍”,施“以黎治黎”之策,无赖“土官、土舍”凭借其把持地方的实力与地位,架空朝廷命官,使得中央的治理政策不能真正落到基层黎峒。他们对上欺瞒、推诿,对下巧取豪夺,民不聊生,黎人的反抗暴动不断,其治理乏善可陈。明太祖始视海南为珍宝,百年以来,移风易俗,华夏之风光耀全岛。王佐的描述虽杂有美化明王朝的献媚之辞,但其以极简略的文字概括了两千年来中原王朝对海南治理与教化的历程,不失为我们研究海南同中原文化关系的重要参考。
(一)由化外到化内
据何成轩先生的考证,儒学的南向浸润传播,从其产生的初期就已表现出来了。他认为,“华夏文化在南方地区的长期、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客观上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将岭南正式划入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37)何成轩《儒学南传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道光琼州府志》记载,海南岛“唐虞为南交,三代为杨越之南裔,秦为象郡之外徼”(38)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王献军主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一,第482页。。说明秦之前黎族同胞所居之海南岛已是大陆属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岭南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将海南作为象郡的边地。
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39)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86页。随着秦国统一进程加快,版图迅速扩张,长期征战及戍守需要大量的兵员,而繁重的兵役已是怨声载道,呈“中国劳极”之态。当赵佗征服岭南后,所率五六十万大军除少数因伤病返回外,需要长期镇守该地,军人的婚配就成为问题,于是借口“士卒衣补”需要单身女性三万人,说明赵佗已作长期戍守打算。当然这只能解决少部分人的燃眉之急,大部分军士不得不与当地人成婚。加上秦朝推行“以谪徙民”的移民政策,当时戍边的官兵、贬谪或是避难的官员、发配或是逃亡的罪犯、躲避战乱或是逃荒的民众、牟利的商贾各色人等纷至沓来,“与越杂处”。秦朝的移民戍边政策使汉族与岭南百越各族民众交流交往,增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在文化层面形成碰撞,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毫无疑问,作为中原文化的支柱的儒家思想开始浸润这方热土。
关于这一时期文化交流情况,《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曾描述:“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40)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36页。表明秦王朝是不断将中原的罪犯发配至交趾,与百越族杂处,在客观上促成了文化的交流。
汉高祖刘邦也曾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桂林、象郡、南海),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它(佗)为南粤王。”(41)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3页。“徙中县之民”是对前述“徙中国罪人”的扩展。
秦朝“移民戍边”政策虽然改变了百越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使统治得以加强,但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法家思想,当然不会用儒家文化来教化少数民族。而赵佗偏安南方一隅,山高皇帝远,采取“文理”政策,以“诗礼化其民”(42)何成轩《儒学南传史》,第77页。是有可能的。
(二)儒学南渐
据《道光琼州府志》记载,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越。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洲。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置珠崖、儋耳二郡”(43)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王献军主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一,第482页。。知汉武帝平定南越后,设置九郡,其中就包括海南岛的珠崖、儋耳两郡。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在海南岛设置郡县,海南岛也因此正式隶属于中央王朝治下。汉朝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奉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重视儒家学说在维护政权上的“德治”作用。
据《后汉书·循吏列传》记载:“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阯,每致困乏。(任)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娉,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初,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阯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王莽末,闭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贡献,封盐水侯。领南华风,始于二守焉。”(44)范晔《后汉书》,第2462页。另据明朝万历年间《琼州府志》卷六《学校志》记载:“学校人才风化所关,琼广潘属郡,汉锡光建学,导之礼义。”(45)唐胄纂《琼台志》卷十五,《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60册,上海古藉书店1982年版。知西汉平帝时锡光为交趾(今越南河内)太守,东汉初年任延为九真太守,对民夷教其耕稼,置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聚;建立学校,导之礼仪。
三国至隋三百多年间国家处于分裂动荡之中,战火连连,民不聊生,佛学、玄学得到快速传播和发展,儒学处于低谷。在这一期间岭南出现了“巾帼第一人”(46)周恩来语,参见:王献军等主编《黎族的历史与文化》,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冼夫人。她对平息各方纷争,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特别是对海南文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深得黎族人民爱戴与崇敬。
冼夫人(513-602)是南朝高凉郡人,俚族(黎族与之有亲缘关系)。冼夫人天资聪颖、襟怀宽广、胸有谋略,据传出嫁前就能抚循部从,行军用师,镇服诸越。冼夫人在梁大同年间,上奏朝廷在海南岛建立崖州。“时高凉冯冼氏,(率)儋州归附千余峒”(47)戴熺、欧阳灿总裁,蔡光前等纂修《万历琼州府志》,王献军主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一,第277页。,从此结束了从汉代以来海南岛建制时废时立的格局。她多次平定叛乱,隋高祖“赐夫人临振县(今三亚)汤沐邑,一千五百户”(48)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03页。。其后代子孙也一直秉承夫人遗志,始终致力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她“使民从礼”,“每劝亲族为善,由是信义结于本乡”(49)魏徵等《隋书》,第1800-1801页。。正是冼夫人用儒家的礼义训导家人,教育百姓,改变了这一地区的陈规陋俗。冼夫人虽为岭南俚族,但纵观其一生之德行可用三个字概括:忠、信、义。冼夫人对国家的贡献深得历代皇帝的赞赏,隋文帝赐书冼夫人“敦崇礼教,尊奉朝化”,“甚有大功”(50)魏徵等《隋书》,第1803页。。冼夫人的儒家君子风范更令包括海南岛在内的岭南百姓崇拜她,在各地建立了不少寺庙纪念她。仅在海南岛,据初步统计就有51座冼夫人庙,且有一项经久不衰的纪念冼夫人的活动——“军坡节”。冼夫人的儒学践履对海南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显著的。
二 启于唐
回顾唐以前近千年的儒学历程,其南向发展的春风渐次拂至海南,开始沐浴浸润这块远离大陆的土地。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亚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当时全球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加强控制,儒家学说成为维护国家及其制度的统治思想。唐王朝高度重视儒学对异族的传播与教化,据《贞观政要》第七卷记载:“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51)吴兢编《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16页。
唐朝的文教政策对海南岛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据《琼台志》转引无名氏记:“琼筦古在荒服之表,历汉及唐,至宣宗(847-859年)朝,文化始洽。”其《学校志》记载:“唐岭南州县学仅四五十人,虽旧与诸郡同,其后人材之盛,则独与广潮齐声。”(52)唐胄纂《琼台志》卷十五,《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60册,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版。《琼台志》是保存下来的最早一部海南岛地方志,而地方志又只撰写与本地有关的事项。由此推知,唐代海南已有官办州、县学,虽然每校仅四五十人,但意义重大,这是传播儒家文化的主要平台。
有确切记载的是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王义方被贬为儋州吉安(今昌江黎族自治县境内)县丞时开办的讲学堂。据《旧唐书·王义方传》载:“蛮俗荒梗,义方召诸首领,集生徒,亲为讲经,行释奠之礼,清歌吹龠,登降有序,蛮酋大喜。”(53)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74页。除了王义方,据统计唐代流谪海南的官吏有22人。以唐朝宰相李德裕、翰林学士韦执谊等为代表被贬官员来到海南,士不得志,一生本事无以施展,便醉心于诗词歌赋以明其志,舞文弄墨“以训传诸经为事”,有的甚至开办学校以训导处于蛮荒状态的黎族百姓,这对儒家文化在海南的传播有开启之功。
三 兴于宋
宋承唐制实施“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海南建立了“第一所高等学校”——琼州府儒学,地址在郡城东南隅,建有殿堂御书阁和尊儒亭。绍兴末年(1162年)设学宫,“淳熙九年(1183年)帅守韩璧重修明伦堂,朱文公(朱熹)书匾”(54)唐胄纂《琼台志》卷十五,《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60册。为记。与琼州府儒学同时建立的有儋州儒学。此后陆续建立的有昌化县儒学、琼山县儒学、文昌县儒学、澄迈县儒学、临高县儒学、万州(万宁)儒学、乐会县儒学、吉阳(崖州)儒学和陵水县儒学。在当时海南岛的州县中只有宁远一县没有设立地方官学,学校教育的兴盛可见一斑。加之当时海南虽处“天涯海角”,但也得天独厚,如宋代被贬海南大臣李光《迁建儋州学记》中所说:“海南自古无战场,靖康以来,中原纷扰而此郡独不与兵。里巷之间,晏如承平。时人知教子,家习儒风,青衿之士,日以增盛。郡试于有司者,至三百余人。”(55)《儋县志》上册,儋县文史办公室、儋县档案馆1982年依据儋县档案馆所藏《儋县志》点校重印本,第634页。时人琼州知事庄芳在《琼州通守刘公创小学记》中说:“琼之为州,在天下极南。文物彬彬,有中土风。……虽黎獠犷悍,亦知遣子就学,衣裳其介鳞,踵至者十余人。人叹曰:前未有也。”(56)唐胄纂《琼台志》卷十七,《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60册。在一所刚刚新建的小学中,就有十余黎族学生,可见其时极端落后的黎族对学习文化的重视。就全国范围来看,两宋时期,由于频繁的战乱,冲击着统治者大兴文教的政策,但海南的文教事业不但未受影响,反而如日中天,进入繁荣发展时期。前述唐朝王义方等人被贬海南,开始传播儒家文化,这种传播还是点状的。到了宋代,琼州府儒学等的建立,其传播便是有组织、有系统、成规模的了。
苏轼(1037-1101)号东坡,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单就个人对海南文化影响来讲,苏轼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他给海南人民留下的文化遗产至今被人乐道。在他留下的诗篇中,洋溢着对海南黎老的深情厚意和对天涯海角的深深眷念。他在《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中说:“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在《食荔枝二首》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甚至认为:“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以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年谁人地舆志,海南万里真吾乡。”面对普遍存在的民族歧视,苏轼言:“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怨忿劫质,寻戈相因。欺谩莫诉,曲自我人。”他认为黎族与汉族本来平等(一民),指责黎人粗鄙残暴是荒谬的,因“贪夫污吏,鹰鸷狼食”(57)《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30、499、540、541、513、513页。,黎人又无处申冤才有反抗暴动,所以“曲自我人”。其实纵观海南黎族人民从汉代以来的历次反抗,东坡可谓一针见血:“贪夫”(不法汉商)、“污吏”是主因。
苏轼在谪居海南期间尊重黎族风俗习惯,“着黎衣冠”,饮黎小酒,自觉融入黎族社会,同当地百姓打成一片,“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亲”(58)《苏轼全集》,第529页。。他初到海南不懂黎语,但他认为“鴂舌倘可学”,誓愿“化为黎母民”(59)《苏轼全集》,第521页。。苏轼的深情厚意也收获了黎族同胞满满的回报。在当地百姓帮助下,苏轼在城南桄榔林中建了一间草房“桄榔庵”,后来还在众人捐助下建起了“载酒堂”。黎族同胞的关爱加上海南独特秀丽的风景,使苏轼心情愉悦,心灵获得极大的慰藉,常怀感恩报答之心。苏轼诗篇中写道:“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60)《苏轼全集》,第510页。他以为即便人生不如意,一身的真才实学也要让其大放光芒,因此他要效法古代的箕子,让蛮荒之地接受中华文化的洗礼。
他对儒家的“仁”也有独特的理解,“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61)《苏轼全集》,第722页。。“仁”不是抽象的爱人,而是要以爱人之心行教化之实,使受教之人“有知”、“有能”。为了培养黎族百姓的知识与能力,苏轼做了大量工作。他写道:“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粳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予既哀之,乃和渊明《劝农》诗,以告其有知者。”(62)《苏轼全集》,第513页。鼓励他们改变生产方式,发展农业生产。当他了解到海南无医无药,治病方式是杀牛祭神,结果常常是“人牛皆死”,他上山采集荨麻、苍耳等,并亲自研制验证药物功效,教导百姓服药治病。他还带领百姓开凿水井,改变饮水习俗,等等。
苏轼对海南文化的贡献与影响,首先是在海南期间著书立说。《宋史》记载:苏轼“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他还要求一直跟在身边的小儿子苏过“作《孔子弟子别传》”(63)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818页。。这一时期他撰写了大量的著述,其中有《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书传》十三卷以及尚未完成的《志林》书稿。其实苏轼初贬黄州时已有此志向,他在《与滕达道书》中说:“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恐了得《论语》、《书》、《易》。……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64)《苏轼全集》,第1696页。后来他在《答李端叔》信中说:“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65)《苏轼全集》,第1740页。也就是说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他一生最看重的三书成就于海南。他的著作不仅推动了海南及后世儒学的发展,即便在宋元两代都引起了很大反响,朱熹、吕祖谦、魏了翁、林之奇、蔡沈、吴澄、陈栎等著名学者都对其著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加以引用,其中《书传》甚至被朱熹称为“最好”的《书》作。
其次是体现在教育上。他一到海南便去考察学校:“闻有古学舍,窃怀渊明欣。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邦风方杞夷,庙貌犹殷因。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忍饥坐谈道,嗟我亦晚闻。永言百世祀,未补平生勤。今此复何国,岂与陈蔡邻。永愧虞仲翔,弦歌沧海滨。”(66)《苏轼全集》,第512-513页。当他偶闻在蛮荒之地尚有古学舍,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赶紧整饬衣装前去察看,不料却空无一人,查问原由是先生没饭食。通过与饿着肚子的老师促膝论教,感叹直到现在自己才知晓实情,并以三国时的虞仲翔(67)虞仲翔“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参见: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21页。来勉励自己,一定要让儒家的礼乐教化放歌沧海之滨。有了这种崇高的志向和强烈的责任感,使苏轼虽然在海南只有短短三年多,但其对海南文化的影响无人能出其右。他在众乡亲的支持下办起了学堂,招黎家子弟入学,亲自讲授儒家经典和文化知识。当他傍晚听到孩童们琅琅读书声,很是欣慰,提笔挥毫写下了“九龄起韶石,姜子家日南。吾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68)《苏轼全集》,第527页。的著名诗篇。这也道出了他一贯秉持的民族平等思想,不因民族地区的落后而否认其人性中的良知良能,只要教化沐浴,成仁成圣是可期的。事实也证明,正是以他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的辛勤耕耘,在海南出现了人才辈出的局面。
在前来向苏轼求学的士子当中,姜唐佐备受东坡期待。姜唐佐是琼山人,为向苏轼请教,住儋州半年多。苏轼以他有中州士人之风,“甚重其才”,赠诗道:“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苏东坡鼓励姜唐佐进京应试,相约“子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69)《苏辙集》第3册,高秀芳、陈宏天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09页。。姜唐佐后游学广州(1103年),在苏东坡去逝两年之后,终于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此后,海南代有人出,宋代有进士15人,到了明代,人口不足30万的海南,竟有进士63位,举人500多,达到历史顶峰,出现了“海外衣冠盛事”的景象。在苏轼离世后,李光在《迁建儋州学记》写道:“绍圣间苏公端明,谪居此郡。……今十余年,学者彬彬,不殊闽浙。异时长材秀民,业精行成,登巍科,膺膴仕者,继踵而出。”(70)《儋县志》上册,第635页。王国宪在《重修儋县志叙》也认为,“儋耳为汉武帝元鼎六年置郡,阅汉魏六朝至唐及五代文化未开。北宋苏文忠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文忠公之教泽,流传千古矣”(71)《儋县志》上册,第1、2页。。
宋代像苏东坡一样被贬至海南的还有一大批官员,他们同本地官僚与乡绅开展多种形式的儒学教育,对儒学在海南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元朝统治者也高度重视教育,在海南保留了宋代儒学建制,新建有会同县儒学和定安县儒学。至此,琼州府及所属各州、县都建立了儒学,并形成了三级儒学网,儒学教育走上了正规化轨道。关于元朝在黎区的儒学教育情况,时人罗伯龙在《南宁军儒学田记》中说:“秦灭学而亡,汉崇学而兴,唐宋以来,文风益炽。迨我皇元,教养之方,勉励之术,虑周且悉也,至于遐荒远裔,莫不有学。盖地有华彝,性无华彝,教而养之,则顽梗皆化而循良矣。不但责之郡守,而复委之宪台,自古未如焉。”(72)罗伯龙《南宁军儒学田记》,王献军主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一,第468页。
四 盛于明
回顾海南历史,汉代置珠崖、儋耳二郡,但因黎人暴动不断,不久撤销两郡建制,降为一县隶属合浦郡管辖。以后各代时置时废,直到梁朝“复就儋耳地置崖州”(73)戴熺、欧阳灿总裁,蔡光前等纂修《万历琼州府志》,王献军主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一,第277页。才固定下来。汉代废郡,贾捐之是依据“蠢尔蛮荆,大邦为雠”,鄙视、敌视少数民族的观念,认为“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74)黄佐纂修《嘉庆广东通志》,王献军主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一,第56页。此后各朝虽视为治下,但歧视犹存。所以在对黎政策上,始终以“平黎”为主,“抚黎”、“化黎”为辅,一遇黎人暴动,总是派兵血洗黎峒了事。而生性耿直的黎族民众不惧高压政策,遇见不平,重又反抗,陷入恶性循环。宋代开始对此进行反思,苏轼明确指出黎人的暴动“曲自我人”,“贪夫”、“污吏”是主因。其子苏过承袭父亲的观点,将前人治黎之策归结为三种:“或欲覆其巢穴而夷其他,或欲羁役其人而改其俗,或欲绝其通市以困其力,然皆不得其要。”关键是没有找到黎人为乱的根源——“我曲而彼直”。具体讲就是“‘黎人之性,敦愿[厚]朴讷,无文书符契之用,刻木结绳而已。故华人欺其愚而夺其财,彼不敢诉之于吏’,何则?吏不通其语言,而胥吏责其贿赂,忿而无告,惟有质人而取偿耳”。而过去治黎之策老想着怎么“治他(黎)”,但问题的根子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因此苏过提出:“上策莫如自治”,也就是首先管理好自己的人。即:针对奸商“当饬有司严约束,市黎人物而不与其直者,岁倍偿之,且籍其家而刑其人”;对“吏敢取赂者,不以常制论;而守令不举者,部使者按之以闻。又为之赏典,以待能吏。如此能者劝,慢者惩,贪胥猾商不敢肆其奸,边自宁矣”(75)苏过《斜川集校注》,苏大刚等校注,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492、494、494、494、494、494页。。
如果还要进一步深究“曲自我人”,那就是民族不平等,鄙视少数民族。即使像苏过这样能坦荡自省、较为理性的学者,在此所称的“我”人、“自”治,实质上还是将黎族同胞看作了外(他)人。他并未像他父亲那样将自己定位为“黎母民”,在汉黎均“一民”的前提下,来谈汉黎(自他)关系。他在文章中将黎人称为“贼”,并认为“夷狄之性如犬豕然,其服可变而性不可改也”(76)苏过《斜川集校注》,苏大刚等校注,第493页。,将黎人视为另类。
明太祖朱元璋在《劳海南卫指挥使敕》称“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数千里”(77)《儋县志》下册,儋县文史办公室、儋县档案馆1982年依据儋县档案馆《儋县志》点校重印本,第218页。,一改过去历代对海南“天涯海角”、“鬼门关”的认识。他反对将海南视之贬官流放场所,强调要选择贤良官员加强治理与教化。他说:“前代谓儋崖为化外,以处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用如此?若其风俗未淳,更宜择良吏以化导之,岂宜以有罪人居耶?”(78)《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八,《明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第955页。朱元璋称海南岛为“南溟奇甸”,并称“天下一家”,相对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来说,系民族观念上之一进步,这对推动包括黎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有积极意义。
(一)重视对少数民族的儒学教育
朱元璋提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育以学校为本”(79)张延玉等《明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86页。的方针,承袭宋元做法在海南大兴学校教育,“儒学俱遍于州县,学设讲堂,以会文养士,庙建礼殿,以祀孔子”(80)唐胄纂《琼台志》卷十六,《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60册。。
明朝在边疆和民族地区置卫学,当时全国有卫493个,设卫学近200所。弘治(1488-1505)初年,琼州设卫学一所,为副使陈英所设,另在清澜、万州、昌化、儋州、崖州设卫学七所。
明朝还大兴社学,“今之社学,即古者闾巷之小学也,……于州县学之外,乡都之间。”(81)唐胄纂《琼台志》卷十七,《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60册。这种由地方官募筹开办的学校,仅洪武七年(1374年)在黎族聚居区就有24所,其中崖州16所、感恩3所、昌化3所、陵水2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人迹罕至的琼山县黎母山腹地,建立了专门针对黎童的水会社学,此为“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抚黎通判吴俸建,延师专训黎童,并置学田”(82)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王献军主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一,第526页。。
明朝海南地方官吏也秉持朱元璋“文德以怀远人”的旨意,在“平黎”、“抚黎”对策中,皆重视对黎人的教化。因此,有明一代,海南各地开办了大量各级各类学校,在这些学校中注重吸收黎族子弟入学。《明史》记载教育内容和课程设置,“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题试士”。(83)张延玉等《明史》,第1693页。
(二)海南儒学“创新性发展”
经过唐宋数百年中原文化洗礼的海南,到明朝已从传播吸收的“浸润”,上升到对儒学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创新性发展”阶段。不仅输出了像薛公远、邢公宥、丘文庄等大批治国栋梁之才,还造就了一批声名远播的本土巨儒,对儒学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丘濬
丘濬(公元1421-1495年),字仲深,琼山人。弘治八年卒,“赠太傅,谥文庄”(84)张延玉等《明史》,第4809页。。在中国历史上海南人至“宰相”者,唯明之丘濬矣。他的《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和《朱子学的》是儒家经典著作,他还撰有《家礼仪节》八卷。由于丘濬对明代理学的非凡建树,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他在海南儒学上的贡献分有四个方面。
第一,体现在《大学衍义补》中。丘濬在该书卷七七引用朱熹话说:“《大学》是为学纲领。先读《大学》,立定纲领,他书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诚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大学》是个腔子,要填教他实。”并认为这是南宋真德秀作《大学衍义》的原由。他认为真德秀填得不全,缺少“治国平天下”一节,所以要为之作补。他在第一卷开篇即对本书在儒学中地位和作用作了自我评价:“宋儒真德秀《大学衍义》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谓‘审治体’者矣,而此治国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总论朝廷之政,何也?盖前之所审者,治平之体,言其理也。此之所论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于知,一主于行。盖必知于前,而后能行于后。后之行者,即所以实其前之知者也。理与事,知与行,其实互相资焉。”(85)《大学衍义补》,邱浚著、林冠群、周济夫校点,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659、659、1页。如果说真德秀主要拓展“内圣”,那么丘濬重点致力于“外王”,《大学衍义补》的主要贡献也就是将儒家思想用于国家治理实践上。《道光琼州府志》称该“著论发明慎独,内省真切,有先儒所未及者,盖其独得之见也。名之曰《大学衍义补》值孝宗嗣位,乃表上之。上览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篡书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裨政治,朕甚嘉之’”(86)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王献军主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一,第611页。。
第二,体现在《朱子学的》中。这虽是一部关于朱子学的入门书,但丘濬一反传统儒学必始于道体的思路,他在《朱子学的·后序》篇中说:“人之为学,必自下学,人事始下学,则可以上达矣,是则儒者之学也。儒者之学,学所以至乎圣人之道也,其要莫先于为己为人之辨。……学者下学人事,而至于上达天理。”(87)丘濬编辑《朱子学的》,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03-104页。“下学而上达”出自《论语·宪问》篇,后学对此多有不同阐释。丘濬借用此语,是认为儒学初学者要“得其门而入”,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即儒学虽是成圣之学,但它首先是成人之学、为己之学。在学习五经的次序上也一改过去“《易》、《书》、《诗》、《春秋》、《礼》”的传统,先《诗》、《书》、《礼》而后及《易》、《春秋》。此如《四库全书总目》引蔡衍鎤对《大学衍义补》所作序言:“上编自《下学》以至《天德》,由事而达理,而终之以韦斋,所以纪朱子之生平言行,犹《论语》之有《乡党》也。下编自《上达》以至《斯文》,由理而散事,而终之以《道统》。”(88)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08页。
可见《大学衍义补》与《朱子学的》的独到之处,就是着眼于“事”与“行”来拓展儒学。
第三,体现在《南溟奇甸赋》中。丘濬依太祖朱元璋《劳海南卫指挥使敕》,以“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数千里”指称海南为题,聚焦“奇”“甸”二字做文章。“甸”在“五服”中是对王城郊区的称谓,然世人眼里的“天涯海角”何以称“甸”?“穷山恶水”、“岚瘴肆虐”的蛮荒之地又何以称“奇”?丘濬先是从“理学”的“地脉”角度给出答案:“邈舆图之垂尽,绵地脉以潜通,……气以直达而专,势以不分而足。万山绵延,兹其独也。百川弥茫兹其谷也。”“总收中原百道之脉者也。”(89)丘濬《南溟奇甸赋》,王献军主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一,第331页。这是说海南岛恰因地处中华大地山水之尽头,得以收“气”、“势”之精华,“兹其独”,“兹其谷”,按“远曰反”,故可称“甸”。再从人脉、文脉上看,“黎人天性纯朴,有太古之遗风”(90)许崇灏编著《琼崖志略》,王献军主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一,第696页。,“隐然太古风致”(91)钟芳《钟筠溪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众多学人,皆异口同声用‘太古’一词刻画其风土人情”(92)李元光《黎族“太古风致”的哲学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7期,第60页。。是因海南“其域最远,其势最下,其脉最细。是以开辟以来,天地盛大流行之气独后其至,至迟而发也迟,固其理也,亦其势焉”(93)丘濬《南溟奇甸赋》,王献军主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一,第332页。。正因黎族“人之初,性本善”的“太古”本色犹存,虽是“迟发”,但经儒家文化“薰染过化,岁异而月不同。世变风移,久假而客反为主”,以致“无以异夫神州赤县之间”,所以“孰云(海南)所谓奇者,颛在物而不在人哉”。总之,“奇甸之言,乃独以专美兹地,非甸而谓之甸,未奇而豫期以奇”(94)丘濬《南溟奇甸赋》,王献军主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一,第332页。。这不禁使人想起苏东坡语“沧海何曾断地脉”(95)《苏辙集》第3册,第909页。,罗伯龙语“地有华彝,性无华彝”(96)罗伯龙《南宁军儒学田记》,王献军主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一,第468页。。身居中华大地之尽头的丘濬,有感于华夏中原之“脉动”,依“地脉”、“人脉”、“文脉”的“理”路,提出中华大地一脉相续,中华民族一脉相传,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观点,对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具参考价值。
第四,丘濬虽居官在外,但非常关心海南文教事业的发展,曾上书朝廷主张大办儒学。他亲自在海南郡城西北隅创建了奇甸书院(明成化八年1472年),他在府学堂后建有藏书石室一间,以供后学阅览。他先后写下了《琼州府学祭器记》、《琼山县学记》、《重修文昌县明伦堂记》、《万州学记》和《崖州学记》等有关海南教育的文章。
2.海瑞
海瑞(公元1514-1587年)字汝贤,琼山人。海瑞一生刚直不阿,特别注重名节。中举后,初出道任南平教谕,“瑞教诸生以古圣贤道”(97)原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原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黎族古代史资料》下册,海南出版社2015年版,第438页。,教导学生道德文章不可分割,并躬身垂范。
他依据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98)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39页。的观点,在《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篇中,阐释了他培养士之“浩然之气”的义利观。他说:“学问人心,合一之道。……学也者,学吾之心也。先圣人得心所同然于古,是以有古之学。学非外也。……维彼视学问为辞章,视为爵禄阶级,甚至假之以快其遂私纵欲之心,扇之以炽其伤善败类之焰,失圣人问学之意矣。”(99)陈义钟编校《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02-503页。也就是说学问的最终目的应是修养自心,非是外求功名利禄等,他批评朱熹“舍去本心,日从事于古本册子,章章句句之。好胜之私心,好名之为累。据此发念之初,已不可以入尧舜之道矣”(100)陈义钟编校《海瑞集》,第323页。。
他依据孟子“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101)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第158页。的观点,在《赠养斋蔡侯抚黎序》一文中,认为长期以来治黎无效,皆因失之于“诚”。他认为黎族“自有天地至今,尚存太古风致,然诺信义,死而不移,天性之真,独有存焉者乎?动以刀弓相向,自昔记之。盖以弓刃为雪仇之具,不能自至守令之庭曲曲直直,势使之然,无他意。……而又赋役繁难,官吏刻削,彼自为诚,我自为诈,有以灰其心而格其志。至诚之为,难乎其为动矣”。他认为黎人天性中同我们所有人一样具“真心”,打打杀杀并非出自本心,而是如东坡所说“贪夫污吏,鹰鸷狼食”,无处伸冤,只好用这种方式表达不满,并“无他意”。由此看来“彼自为诚,我自为诈”,而我们往往分析黎人为何难治时,“不曰己之无诚也,诚不足为动也,而曰犷悍之不可为驯,古昔则然,可信也哉!”他感叹道:“予尝以为黎人之不我向也,乃我之无以致其向。”说到底,黎人的反叛是因我们从未尊重他们,没有用“诚意”去打动其“真心”,做到“以心换心”。他赞扬蔡侯“变诈之世而得有如侯者,黎人得以舒发本真,民士宁适”,并认为“苟朝廷之上,薄赋轻徭,承宣之吏,还淳返朴,举蔡侯而为之,无不可矣”(102)陈义钟编校《海瑞集》,第365-366、366、366、366页。。
可见,海瑞对儒学不空发议论,而是用儒家思想之精华分析世事,指导实践,是一个儒家思想的坚定践履者。他虽日理万机仍不忘关心家乡黎人的教化问题,在《平黎图说》中讲:“仍急立寨学,延师训导,各营及各处村峒皆立社学训诲。”(103)原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原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黎族古代历史资料》上册,海南出版社2015年版,第230页。他对海南儒学的贡献,历史学家黄仁宇是这样评价的:“这位孔孟的真实信徒,在今天却以身体力行的榜样,把儒家的伟大显扬于这南海的尽头!”(10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增订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5页。
3.钟芳
钟芳(公元1475-1544年),字仲实,号筠溪,明朝崖州(今三亚市)人,二甲进士及第,曾任兵部侍郞、户部侍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当地人称其为“海前丘后论人才”,视他为上承丘濬、下启海瑞的“岭海巨儒”。其儒学思想集中表现在《学易疑义》、《春秋集要》两本著作中。一般将其思想归入程朱理学(“宗理学”),但他又同朱熹在理气关系、知行观上均有分歧。
当代学人周济夫研究发现,钟芳与同代的大儒多有交集,其中与王阳明过从甚密,除了嘉靖四年在广西一起共事外,此前的正德五年至十一年,两人还曾在江西、南京有过交往。当王阳明去世后,钟芳曾为之撰写了《祭王阳明文》。文中钟芳自述:“某岭海末学,忝在交游,宦辙所经,每亲绪论。”(105)钟芳《钟筠溪集》,第334页。因此陆王心学对钟芳的理学思想有一定启发。不过针对心学家批评当时士子受程朱理学影响而向外驰骛、戕害本心、流于支离的时弊,他有不同主张。
王阳明龙场悟道,“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106)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4页。。其主张返本归心“致良知”,“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107)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09-110页。。钟芳则批评阳明以知遮行的“致良知”:“而阳明之意不如此,乃曰致吾之良知,以见之于事,则致字已属行,而所谓良知者,人人皆可即其所见而推致之,此其不可晓者。彼证父攘羊以为直,尾生抱梁柱而死以为信,岂不自信其良知,以为直且信也。惟于理有蔽,则各据以为是,而至死不悟也。”(108)钟芳《钟筠溪集》,第287-288页。“证父攘羊”、“尾生抱梁”的例证,说明阳明的“致良知”论有烛理洞彻不明之嫌。虽不赞同阳明的观点,但为了避免同理学“知先行后”直接冲突,他委婉借用阳明“知行合一”来阐发其独特的“以行为本”的知行观。他说:“前奉拙稿,论知行合一,实借王阳明之说,稍宛转以发,明圣人立教本意。”(109)钟芳《钟筠溪集》,第287页。
钟芳指出:“《中庸》知为达德,而诚以行之,皆有明训。故君子之学,未尝不博,而其博也,乃在于人伦日用之实,而益致夫精择固守之功。”(110)钟芳《钟筠溪集》,第149页。他认为,作为践行天道的“诚之者”,择善(知)与固执(行)、博文与约礼是统一的,但最终要落脚到日用工夫(行)上。他进一步指出:“曰存诚者,大本之所以立,犹所谓‘涵养须用敬’。曰精义者,达道之所以行,犹所谓进学则在致知。虽有圣贤生熟之不同,而忠信二字彻首彻尾,不可须臾离也。”(111)钟芳《钟筠溪集》,第287页。可见,“诚者”就是忠信,是“大根本”;“存诚者”必择“忠信”之善而固执之。“忠信”是本,进学“忠信”工夫就是致知。因此知行虽合一,但“一”在“行”上,以行统知。他是以这样的逻辑来释“知行合一”,故“学无大小,以行为本,而以穷理诚身为要”(112)钟芳《钟筠溪集》,第212页。。因此针对时弊,他与王阳明都强调要回归“大本(体)”,但阳明回归的是“(良)知”,他却认为“在今世,书籍议论满天下,不患不知,患不能行”(113)钟芳《钟筠溪集》,第472页。。
上述观点不仅表明他的实学取向,而且也表明了其唯物倾向,这同他在《理气》篇上的观点一致:“夫子曰‘易有太极’。易者何?阴阳也,气也,而有至极之理存焉。则理之与气,固未尝离而为二,亦未尝混而无。说曰:其理者阴阳之理,非别有所谓理。”(114)钟芳《钟筠溪集》,第208页。
钟芳还以儒家特有的“仁爱”之心阐释他的治黎之策。他认为黎人之陋俗是源自未开化的原始状态:“然其重契箭,谨信约,毫发不爽,虽士人不过也。怒或叛其父,而于母也至死不悖焉。……其敦朴浑厖之风固在也。其太古之民乎?太古之风不可见,吾于黎獠得其仿佛焉。使得沾圣王之化以渐之,则不日而变矣”。他推崇“建社学,择师训蒙,易巾服,习书仪”的“教化”方针,反对一味的杀戮,始终推崇以“仁民爱物”的思想治理国家与社会。钟芳强调治理民众要施行仁政,“非仁民无以伸事上之义”。施仁政的要义在于“夫政以顺民欲恶为要”,“夫仁者不负其民”,“而以惠泽及物为贵”,“大抵此时民穷财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强调减轻徭役,精兵简政,谨慎用刑,“政以敷治,刑以辅政,政所不及,不得已而后刑”。(115)钟芳《钟筠溪集》,第506、188、117页。
4.王佐
王佐,字汝学,号桐乡,临高县人,曾于广闽等地为官,一生清正廉洁,素以诗书为友,“博学多识,精思力践,见道精审,故其诗辞和平温厚,文气光明正大,当比唐宋诸大家”(116)戴熺、欧阳灿总裁,蔡光前等纂修《万历琼州府志》,王献军主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一,第325页。。他与丘濬、海瑞及清代张岳崧并称为海南四大才子,主要著作有《鸡肋集》、《经籍目略》、《原教篇》、《庚申录》、《珠崖录》、《琼台外纪》、《金川玉屑集》等。
5.唐胄
唐胄,字平侯,号西洲,琼山县人,官至北京户部左侍郎,史称唐胄“好学,多著述”,其《正德琼台志》是海南现存最早的地方史志,史料价值极高。他也因明经通史而被《明史》立传,誉为“岭南人士之冠”(117)张延玉等《明史》,第5359页。。其著作除《琼台志》外,还有《广西通志》、《西洲存稿》、《传芳集》等。
综上,海南儒学巨匠皆有重实学实践、身体力行的特质。其对儒家思想创新性发展所呈现的“弦歌沧海滨”盛况,恰如丘濬所说“贤才汇兴,无以异夫神州赤县之间”(118)原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原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黎族古代历史资料》下册,第687页。。清末海南先贤王国宪在《扬斋集》序中总结:“海南风雅,盛于有明。其时人文蔚起,出而驰誉中原,垂声海内。自丘文庄、王桐乡、唐西洲、钟筠溪、海忠介、王忠铭而后,有专集者数十家。海外风雅之盛,莫盛于是时。不仅理学经济,文章气节,震动一世也。”(119)王永烈《扬斋集》,海口市海南书局1922年版,第4页。
五 文明之光乍现黎峒
“孕于古、启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是从海南儒学发展历程上讲的,实际上直至前清时节,文明之光并未普照整个黎区,生黎、熟黎乃是泾渭分明。对于那些长期居住在深山腹地的生黎来说,其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仍未受到多少中原文化的影响。清代蓝鼎元(1680-1733)的《琼州记》描述了当时黎人的情状:“大抵十三州县民黎杂居,峒窠房屋,无处无之。居近地者为熟黎,供赋役,极忠顺;居深山者为生黎,又深者为生岐,皆不服王化,旧常出为民患。五指山谓之黎母,竟若蛮獠私家,汉人不得过问,一隅之地,如分秦越,非国家之体也。”他感叹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岂有十三州县衣冠文物之王民,反为蛮鬼藩卫,仅居边陲之一线,独虚其中以让黎岐为声教不及之地?腹心不治,四体虽安,欲保百年无病,断不可得。”(120)原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原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黎族古代历史资料》上册,第148-149、149页。他的观点虽充满民族歧视,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生黎的情状。
清代推行“文教为先”,重视对少数民族的儒学教育,出台了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的文教政策。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议准:粤东凡有黎瑶之州县,悉照连州,一体多设官学,饬令管理厅员督同州县,于内地生员内,选择品行端方,通晓言语者为师,给以廪饩,听黎瑶子弟之俊秀者入学读书,训以官音,教以礼义,学为文字”(121)原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原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黎族古代历史资料》下册,第646页。。
乾隆四年(1739年)潘思榘上疏,“疏言:‘……惟黎僻处海南,崖、儋、万、陵水、昌化、感恩、定安七州县为最多。生黎居深山,熟黎错居民间相往来,语言相习,请于此七州县视瑶童例设义学,择师教诲,能通文义者许应试。’部议从之”(122)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三百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88页。。要求依照瑶族地区的做法,在黎区设“义学”,即设立主要招收黎族的少数民族学校,实施特殊的教育政策。乾隆五年(1740年)两广总督庆复“疏言:‘琼州四面环海,中有五指山,黎人所居。请设义学,俾子弟就学应试,别编‘黎’字,州县额取一名。’……均从之”(123)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二百九十七,第10396页。。
虽有朝廷“从之”支持,但在黎区开办的学校还是难以为继。时两广总督硕色、广东巡抚岳濬联合上奏:“广东连、韶、琼等处,先后经设瑶黎各学,每年动支公费,给馆师脩脯。今查各处因无瑶童从学,久废,惟韶郡之乳源一处尚存,就学者亦无瑶人子弟。黎学虽有馆师,黎童甚属寥寥,且语音各别,教无所施,应概裁。额支馆师脩脯银,仍归原款充公。”(124)原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原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黎族古代历史资料》下册,第646页。看来,设立专门的少数民族学校并非那么简单,由于民众求学意愿不强,语言不通,以致有名无实。但封建官员不检讨政策本身如何加以改进,而是以“概裁”了事。
最终修建“十字大道”,打通文化传播“最后一公里”,消除隔离状态,让全体黎族同胞接受文化教育,张之洞、冯子材二人居功甚伟。
张之洞(公元1837-1909年),直隶天津府南皮县人,曾任两广总督。他高度重视儒学教育。其主政两广期间,在海南“设岭门、南丰、闵安三抚黎局,责以抚率黎民,开设学校,修治军路大政,而以雷琼道监督之,开辟琼州数千年未有之政绩。又虑琼之科第无多,奏请遵台湾例,隔科定额举人四名,有十人以上赴会试,取进士一名,部议定隔科二名为额,此皆大有造于琼州者。创建广雅书院,定琼州五名课额,拔取琼山四名。……大开海南风气,琼士之知实学自此始”(125)朱为潮等主修《民国琼山县志》,赵红主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二,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页。。
冯子材(公元1918-1903年),生于广东钦州沙尾村。《钦县·民卅五年志》说他“俱尽厥职,尤以在琼开五指山十字大路,开各县小路三千余里,为后来山脚开县得所凭借。又设塾以四书教黎人子弟。制衣裳作样,使变易黎人裸处,尤为开化黎峒之先河”(126)原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原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黎族古代历史资料》下册,第470页。。民国许崇灏在《琼崖志略》中认为“黎人之正式接受中国文化,恐仍以冯子材时为始”(127)许崇灏编著《琼崖志略》,王献军主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一,第717页。。此观点虽值得商榷,但若仅指以五指山为中心的生黎所居区域应是切当的。因为这是许崇灏组团深入黎区心腹地带实地调查访问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说,明人王佐所谓“南溟为甸方恰才,未及十纪,而人物增品之盛,遽与隆古相追陪,衣冠礼乐之美,遽与中州相追陪,诗书弦诵之兴,遽与邹鲁相追陪”(128)王佐《南溟奇甸歌》,王献军主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一,第333页。,应不包括生黎所居的核心区域,生黎仍处于“蛮人”状态。
许崇灏的五指山调研还指出,说起冯子材,黎人无人不知无人无晓,今天的保亭县即是当年冯宫保停辕之处,几乎当地每个黎人都能说出它的渊源。“十字大道”的开通意义特别重大,从此黎汉交流加强,货物贸易畅通,对黎人接受先进文化、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等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后来民国政府新设专门治理生黎聚居区的三县打下了基础。
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深知曾任广西提督冯子材骁勇善战,当中法战争爆发之际,奏请调冯子材驻守镇南关。七十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从而扭转了整个战局。此后1886年,张之洞又调冯子材赴海南平黎乱。在海南平黎抚黎中,二人合作对生黎地区的开化与发展贡献如下。
第一,开通十字大道。作为治黎之策,尽管前朝海瑞等人多次上疏呼吁在海南开通十字大道,使国家治理直达生黎居住的五指山核心区,但三百多年过去了,却无人真正实施。由于道路不通,生黎仍生活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张之洞上疏皇上:“查抚黎以开路为先,开凿险隘,芟焚林莽,令其四通八达,阳光照临,人气日盛,则山岚自消,水毒自除。前代虽有开通十字路之议,迄未举行。……兹拟开大路十二道。”(129)原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原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黎族古代历史资料》上册,第312页。同时提出由冯子材统领督办,所开大路也由十字型变成了井字型,其余各州县团夫分开小路,以合于大路。
第二,设官安营。纵观整个海南岛,自从汉代设郡开始,历代帝王的基本统治方法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稳步推进州(郡)、县、屯、所的设置,步步为营,逐渐将海南大部分地区置于自己的实际管辖之下。黎人也被分为生黎与熟黎,直到乾隆时期萧应植等编撰的《琼州府志》仍称“生黎居深山,性犷悍,不服王化,不供赋役,足迹不履民地”(130)萧应植修、陈景埙纂《乾隆琼州府志》,王献军主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一,第444页。,也就是说直到清代仍有大片区域并未纳入政府的实际管控。明人顾岕曾在《海槎余录》中道其原委:“其地孤悬海岛,平旷可耕之地,多在周遭,深入则山愈广厚,黎婺岭居其中,以为镇。自汉武迄今几千年,外华内夷,卒不可变者,以创置州、卫、县、所,必因平原广陌,故同周遭近治之民,渐被日深,风移俗易,然其中则高山大岭,千层万叠,可耕之土少,黎人散则不多,聚则不少,且水土极恶,外人轻入,便染瘴病,即其地险恶之势,以长黎人奔窜逃匿之习,兵吏乌能制之,此外华内夷之判隔,非人自为之,地势使之也。”(131)原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原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黎族古代历史资料》上册,第8页。
我们认为生熟之分虽“非人自为之”,但绝非单一的“地势使之”,应是封建王朝长期不作为、乱作为造成的。关键是历代统治者对海南的蔑视和对黎人的歧视,汉代设郡后又罢郡,唐宋还将其视为惩罚罪臣的流放之地,世人也视为“天涯海角”、“鬼门关”。加之生黎居住在高山密林之中,其间有瘴气,“人欲穷其高,往往迷不知津,而虎豹守险,无路可攀”。(132)周光非撰《岭外代答》卷一,商务印书馆发行,第6页。所以历代统治者多用“平黎”,试图通过残酷镇压,震慑生黎不敢为乱,而不愿深入生黎聚居区建立所、屯、县,进行“抚黎”、“治黎”,元代也仅勒石山脚“大元兵马至此”而已,均未实现对生黎的有效管理与控制。近两千年来,反抗、镇压、再反抗、再镇压……恶性循环。要将其纳入实际管治,必须重视黎人,开通道路,设立各级政权机构。但这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还必须做通黎人的思想工作。因此在张之洞、冯子材之前,明代韩俊也曾指出:“为今之计,莫若革去土舍峒首,立以州、县、屯、所,量拔在外军民,杂处其中为防引,开辟五指山十字道路,均通四处往来,遍立地方更甲,严为法制禁约。”(133)《儋县志》上册,第590页。他提出在生黎核心地区设州、县、屯、所加强管理,但终未见行。
在张之洞发给冯子材的《致冯督办》的电报中明确指示,“将来开通十字路后,择要设官安营,各村黎长,编立土目,就中酌设总土目数人,散目给顶带,总目授土职,自为约束”(134)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三册,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254页。;同时“路通地辟之后,应于内山要隘广饶处所,建置城寨,设官安营,以资化导控制,举办一切,俾此奥区永为乐土”(135)原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原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黎族古代历史资料》上册,第313页。。在张、冯二人建设基础上,民国陈汉光在生黎区域设立三县,才真正实现了将生黎纳入政府的实际管控。
第三,设义学。1886年张之洞上疏提出:“每数村仿内地设一义学,延请塾师习学汉语、汉文,宣讲圣谕广训,所需经费,就地筹办。令在籍绅士总兵林宜华、副将符鸿升等分遣通晓黎语团绅,经历各峒,剀切宣谕。其霞黎、苗黎、哮黎,干脚岐(黎)各种,类多裸处,酌给衣袴,令其渐被冠裳之化,训其顽固之俗。”(136)原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原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黎族古代历史资料》上册,第311页。在《致冯督办》的电报中指示:“每数村须设一义学,习汉文,讲圣谕,经费就地筹办。”(137)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三册,第254页。冯子材也忠实执行了这些计划,据说保亭县内一小学即为当年冯氏所建,《琼崖志略》称:“此小学校,可以说是五指山腹地黎人文化的发源地。”(138)许崇灏编著《琼崖志略》,王献军主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一,第709页。保亭黎人能读书写字,从此小学始。
关于张、冯二人的功绩,清人罗汝南《中国近世舆地图说》:“张之洞督粤,遣人开设义学,教以汉文汉语,并宣讲《圣谕广训》,于是黎民知所向化。且开大路十二道,东三路,西三路,北路,南路,东北路,东南路,西北路,西南路各一,其路横纵相交如井字,宽者一丈六尺,狭者亦有八尺,均以五指山为中心,盖千百年未辟之地,至是始化为坦途矣。”(139)原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原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黎族古代历史资料》下册,第603-604页。
综上海南儒学传播与发展历程,有以下几点感想与启示。
第一,从儒学在黎族地区的双向互动发展,说明各地、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在儒家学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忽略民族地区人民的重要贡献。
第二,是否实行民族平等政策,是制约海南儒学发展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海南儒学的兴与衰,是与封建统治者对民族地区是重视还是歧视密切相关,如汉朝与明朝就是明证。
第三,海瑞认为治黎无效,是失之于“诚”。面对敦厚质朴的少数民族,要“开诚心、布公道”,“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14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版,第31页。不但要加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更要交心交情,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才能实现有效治理。
第四,从晚清才开通“十字大道”,文明之光乍现黎峒,说明对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因时、因人制宜,采取特殊优惠政策,特别是要将政策、政令落到实处,否则就会“停留在纸上”,或“概裁了之”。
第五,民族地区改善民生,基础在教育,要实现教育公平。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了,如苏东坡所言,哪怕是落后的黎族也能“弦歌沧海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愿望。
第六,海南儒学的兴盛,是一大批身处逆境,但对海南人民不离不弃,如苏东坡等人潜心耕耘的结果,也是包括黎族在内的海南同胞勇于探索、革故鼎新的结果。今天我们也要“择善固执之”,“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141)《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货载民族共同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