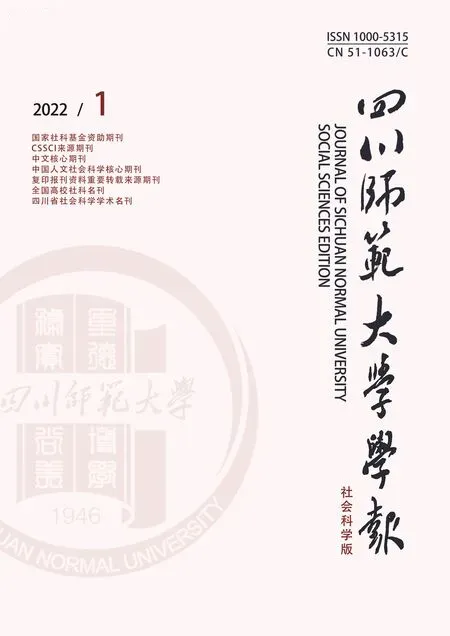论“语录”与“语录体”
夏德靠
目前有关“语录”与“语录体”的含义、起源、类型、文体生成及特征的认识还存在不少分歧。“语录”与“语录体”是两个相关而有所差异的术语,它们之间有着比较复杂的关联。“语录”可以指文献,而“语录体”通常是指文体,在这个意义上,“语录体”是从属于语录文献的。不过,“语录”有时也指文体,这种文体意义的“语录”既可以指专书文体,也可指篇章文体,而“语录体”则指专书文体。由于专书文体是由篇章文体构成,这样,“语录体”也就包含“语录”,当然,专书文体意义上的“语录”与“语录体”的内涵就是一致的。从起源角度来看,“语录”先于“语录体”出现,“语录体”是“语录”发展的结果。正是由于“语录”与“语录体”之间存在这种复杂关联,那么,厘清这些分歧,对于把握“语录”与“语录体”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一 从“语”到“语录”、“语录体”
人们在讨论“语录”时,通常会对其含义进行辨析。就目前来看,在这方面的看法还并不一致,归纳起来存在如下这些方面的认识。
“语录”表现为问答形式。杨玉华指出,语录体“一般语句简短,多用问答形式,随事记录,不避俚俗”(1)杨玉华《语录体与中国古代白话学术》,《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108页。。马自力指出,语录体是“记录言谈议论的内容,以及对话或设为问答的文体形式”,是“直接记录讲学、论政,以及传教者的言谈口语的一种文体”(2)马自力《语录体与宋代诗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60、62页。。
“语录”是记录人物的言论。陈士强认为,语录是“用来记叙禅师们在不同的居住地、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所说的种种法语”(3)陈士强《禅宗语录两大集解读》,《五台山研究》1992年第2期,第9页。。龙连荣以为语录体“记录或摘录某人的言论而成文。这有自录或他录的,是不折不扣的手写其口的作品,故也称之为记言文”(4)龙连荣《语录体·对话体·专题议论文——先秦诸子哲理散文文体嬗变轨迹试论》,《凯里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91页。。刘伟生指出,语录体“多指禅师的言谈与宋儒的论学之语”,而广义的语录体则指“言语的记录或摘录”(5)刘伟生《语录体与中国文化特质》,《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6期,第265页。。王旗认为语录体“是将自己或他人的言论辑录而成文本的一种文章的格式或样式”(6)王旗《语录体与对话录:东西方不同语言表达形式的成因》,《课程教育研究》2017年第3期,第10页。。
“语录”表现为语录形式。刘绪义认为语录体“是用语录写成的文体。语录原为禅宗祖师说法开示之记录书。禅师平日说法开示,并不藻饰华词,大多以通俗语直说宗旨,其侍者与参随弟子予以记录,搜集成册,即称语录”(7)刘绪义《〈尚书〉——中国最早的语录体散文》,《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第46页。。陈静认为语录最初是一类记录文人言语的作品,所记载的语录也多是其所处时代多个文人的机锋辩谈或者散杂哲思;宋代丰富的语录体作品的出现,标志着语录体己经有了足够的文本积累和文体重视;至清代,语录体己经被当作一种有固定体例的文体形式(8)陈静《程门四先生语录体散文研究》,吉林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页。。
“语录”是用日常口语白话写作的文体。郑继猛指出,语录体散文“是直接用日常口语白话写作而形成的一种文体形式”(9)郑继猛《南宋语录体散文初探》,《殷都学刊》2007年第4期,第93页。。
“语录”是记录人物的言行。官贵羊指出,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有一种特殊的文体,“它常用于门人弟子记录导师的言行,有时也用于佛门的传教记录。因其偏重于只言片语的记录,不重文采,不讲篇章结构,不讲段与段甚至篇与篇之间时间及内容上的必然联系,故称为语录体”(10)官贵羊《语录体的几种形态及作用——以诸子语录、禅宗语录、宋儒语录为立足点》,《安徽文学》2011年第12期,第142页。。
“语录”是格言、警句。王旗指出,语录体是“碎片式的判断、结论,与所谓格言、警句相类”(11)王旗《我国古代文学理论“语录体”特点及成因》,《文史杂志》2016年第5期,第56页。。不过他又认为语录“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谓的格言、警句,很多都是独句独句的判断、结论,点到即止,言简意赅”,而语录体“是将自己或他人的言论辑录而成文本的一种文章的格式或样式”(12)王旗《语录体与对话录:东西方不同语言表达形式的成因》,《课程教育研究》2017年第3期,第10页。。
“语录”是阐述宗教经义的文体。刘振英认为,“禅宗语录体是一种阐述宗教经义的文体,是绝对信仰之精神(佛)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思维的语言阐释,或得道高僧对佛教经典和佛法的语言疏解,包括对西土28祖和东土6祖的传承谱系的记录,以及禅宗盛衰流变的宗主的语言记录”(13)刘振英《唐宋禅宗语录体的文体特征和多元包容性》,《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第74页。。
以上这些对语录的看法,既存在相通的一面,也存在不一致之处,而且有的将“语录”和“语录体”相提并论。其实,要澄清和把握“语录”的内涵,还应该联系“语”与“语录体”来加以分析。“语”是先秦以来非常重要的一类文献,其根本特征表现为有教益的人物言论。何晏《论语集解叙》指出:“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14)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刘向认为《论语》载录的主要是孔子的“善言”。《国语·楚语上》“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韦昭解释为“治国之善语”(15)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529页。。所以,有学者指出,“‘语’这种文类之所以成立,主要不是因为某种特定的形式,而是特定的体用特征:明德。因而,只要是围绕这种体用特征编选的,不论其篇幅长短,也不论是重在记言,还是重在叙事,都可称之为‘语’。要言之,明德的体用特征是‘语’的身份证明和统一内核”(16)俞志慧《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以言类之语为例》,《文史哲》2007年第1期,第9页。。人物言论的教益性质是衡量“语”作为一种文类的标志,但需注意的是,先秦时期“善言”的呈现方式是多样化的。具体而言,“语”存在篇章语体与专书语体之分。从篇章语体角度来看,有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等;从专书语体来看,有国别体、语录体等。按照这个划分,“语录”首先是以篇章语体的面貌出现,它可以是格言,也可以是对话,甚至可以是事语。至于“语录体”,与“国别体”一样,体现的则是专书语体的特征。一般而言,专书语体可以容纳多种篇章语体,因此,“语录”与“语录体”之间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明确这一点,再来看上述诸种说法,所谓问答形式、人物的言论、格言警句等,这些说法大都站在篇章语体角度,讨论的多是“语录”;而记录人物言行的说法,则是站在专书语体的立场上,说的主要是“语录体”(也可指“语录”)。下面结合相关资料,进一步分析与澄清“语录”与“语录体”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语录体”的文体特征。
二 《论语》与“语录体”的生成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语录”和“语录体”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就发生而言,“语录”早于“语录体”,在一定意义上,“语录”是伴随“语”而出现的,但“语录”的出现并不必然表明“语录体”的生成。先秦文献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如《尚书·泰誓下》:“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17)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页。《酒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18)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380页。《盘庚上》:“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19)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232页。《左传·僖公七年》:“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2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317页。《诗经·大雅·荡》有云:“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管子·君臣下》:“古者有二言:‘墙有耳,伏寇在侧。’”(21)戴望《管子校正》,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76页。《论语·子路》记载孔子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22)杨伯峻《论语译注》(修订本),第141页。《孟子·公孙丑上》:“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23)焦循《孟子正义》,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08页。《吕氏春秋·简选》:“世有言曰:‘驱市人而战之,可以胜人之厚禄教卒;老弱罢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材;离散系系,可以胜人之行陈整齐;锄櫌白梃,可以胜人之长铫利兵。’”(24)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440页。这些地方引述的人物言论,通常被视为格言,但这些格言也未尝不可看作是这些人物的“语录”。从盘庚明确提到所引言论出自迟任来看,“语录”的出现是非常早的。另一方面,尽管“语录”的出现为“语录体”的生成创造了条件,但从这些“语录”来看,似乎还不能完全说明“语录体”已经出现了。
有关“语录体”的出现,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第一种看法是源于《论语》。杨树增强调“语录体是由《论语》创立的”(25)杨树增《先秦诸子散文:诗化的哲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杨玉华认为“由孔门后学记录整理的孔子教学实录《论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语录体著作”(26)杨玉华《语录体与中国古代白话学术》,《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108页。;李光生认为“由孔子后学记录整理的孔子教学实录《论语》是现存最早的语录体著作”(27)李光生《宋代书院与语录体》,《兰州学刊》2011年第2期,第134页。;官贵羊指出“《论语》被称为中国第一部语录体著作”(28)官贵羊《语录体的几种形态及作用——以诸子语录、禅宗语录、宋儒语录为立足点》,《安徽文学》2011年第12期,第142页。;陈立胜认为“语录体的出现,可以追到《论语》”(29)陈立胜《理学家与语录体》,《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129页。;王旗指出“‘语录体’是将自己或他人的言论辑录而成文本的一种文章的格式或样式,……《论语》就是最早的代表著作”(30)王旗《语录体与对话录:东西方不同语言表达形式的成因》,《课程教育研究》2017年第3期,第10页。。第二种看法是源于《尚书》、《论语》。郑继猛指出,“语录体散文就是直接用日常口语白话写作而形成的一种文体形式。早期的经典如《尚书》、《论语》、《孟子》都含有白话语体形式”(31)郑继猛《南宋语录体散文初探》,《殷都学刊》2007年第4期,第93页。;马自力指出“诗话中的语录体与宋代诗学语录体作为一种记言的文体形式,诞生于先秦。在上古历史文献总集《尚书》中,有许多篇章是记录先民言论和上古帝王讲话的,如《盘庚》、《汤誓》等;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中,如《论语》、《孟子》、《庄子》等著作里面,有关诸子讲学、论辩等言论的记录,更是比比皆是”(32)马自力《语录体与宋代诗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60页。。第三种看法是源于禅宗。陈士强认为语录“是禅宗僧人创造的一种文体”,“禅宗之有语录,始自《六祖坛经》”(33)陈士强《禅宗语录两大集解读》,《五台山研究》1992年第2期,第9页。。第四种看法是近源禅宗,远源《尚书》或《论语》。李壮鹰指出“语录始出于唐代禅门”,又说“语录之体,发源甚久,先秦人所撰史籍,举其大要,不过二端:一为记事,一为记言。前者如《春秋》、《左氏》,后者如《国策》、《国语》,而《国策》在广义上来说都可以说是语录。至于《论语》、《孟子》,门徒记录师说,问答兼具,叩发相济,与后世狭义上的语录在体例上就更为接近了”(34)李壮鹰《谈谈禅宗语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65-66页。;刘绪义认为语录作为一种文体始自唐代,但《尚书》具备语录体的本质特征,是语录体散文的最初范式(35)刘绪义《〈尚书〉——中国最早的语录体散文》,《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第46页。。第五种看法是缘于先秦诸子。龙连荣认为“先秦诸子哲理散文最早的文体形式,的确是语录体”(36)龙连荣《语录体·对话体·专题议论文——先秦诸子哲理散文文体嬗变轨迹试论》,《凯里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91页。;杜绣琳指出“语录体论说文作为论说文的初级形态而出现,如《论语》与《老子》”(37)杜绣琳《〈淮南子〉“语录体”论说文的说理分析》,《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01页。;刘晓珍指出“现代论者也多把禅宗语录体形成的渊源推至《论语》,……若从文体形式着眼,《论语》的简短‘问答式’言语记录的确可视为禅宗语录的源头,但若就文风(表达方式、语言技巧)来看,它与《庄子》更为神似”(38)刘晓珍《禅宗语录与〈庄子〉文体文风相似性研究》,《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63页。;陈静指出“语录体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先秦诸子散文”(39)陈静《程门四先生语录体散文研究》,吉林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
与此同时,有关“语录体”缘何而生问题也是众说纷纭。较普遍的看法是缘于教学活动。杨玉华认为语录体“是对教学情况与学术论辩的如实记录”(40)杨玉华《语录体与中国古代白话学术》,《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108页。。李光生认为宋代语录体是书院制度的直接产物,“宋人语录与先秦语录和禅宗语录一样,都是对教学活动的记录”,“从教育角度言,宋代语录体作为书院教学的如实记录,寓深奥的义理于浅易俚俗的语言中,无疑是书院教学案例的成功标本”(41)李光生《宋代书院与语录体》,《兰州学刊》2011年第2期,第134、135页。。刘伟生分析说:“语录是讲学的产物,《论语》是在史官文化氛围中诞生的诸子语录的先驱。……禅宗语录虽说是印度佛教文化传统的结晶,但同为教学活动的产物。宋儒语录既受禅宗启发,又仿诸子问答,更是书院制度与讲学风习的直接产物。”(42)刘伟生《语录体与中国文化特质》,《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6期,第267页。陈立胜指出:“道学团队之结社,不是一般的社会活动,而是修道共同体之结社,‘语录’说到底是修道、证道过程之中师生对话的记录。语录体之流行反映了理学家讲学活动之盛与相应的书院之发达。”(43)陈立胜《理学家与语录体》,《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133页。当然,也有人认为语录体的产生还存在其他因素。郑继猛指出“南宋讲学风气浓厚,因此语录体散文繁荣”,同时,语录体还与公文有关系,“朱熹是南宋大量使用白话写作的第一人。在《朱子大全》里,他和朋友、弟子讲论的书信多达40卷,占《朱子大全》三分之一”,朱熹用白话给朋友写信显然不属于讲学(44)郑继猛《南宋语录体散文初探》,《殷都学刊》2007年第4期,第93、94页。。张子开分析说,诸子语录、禅宗语录和宋儒语录出现的原因各不相同:春秋末期私学兴起,受巫史记录传统和“述而不作”观念影响,孔门弟子将教学内容形诸文本,是为《论语》;唐代禅宗沿袭印度佛教教学方法,以语言文字为方便法门,故而模仿结集,采用散文、韵文相间的佛经体裁以总结禅师生平言说;宋代理学家受禅宗启发,兴建书院以论道,再仿照诸子语录而记录师徒问答(45)张子开《语录体形成刍议》,《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517页。。官贵羊指出:春秋末期私学兴起,受巫史记录传统和“述而不作”观念影响,孔门弟子将教学内容形诸文本,于是有语录体的开山之作《论语》;诸子仿其体式而作各自的语录著作,“诸子语录和禅宗语录都是对教学活动的记录,追忆或整理,但二者却源自中印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它们独立发展很多年后,终于在宋代完成合流,形成宋儒语录”(46)官贵羊《语录体的几种形态及作用——以诸子语录、禅宗语录、宋儒语录为立足点》,《安徽文学》2011年第12期,第142、143页。。刘湛哲认为“语录体”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包括:一是私学的兴起,使掌握文字的群体不断扩大;二是“述而不作”观念的深入人心;三是书写工具和文字载体的笨拙与局限(47)刘湛哲《从“语录体”到“语录现象”——现代视域中的“语录体”嬗变研究》,暨南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5页。。陈静指出,讲学是语录体形成的先决条件,而另一根源是“述而不作”的思想观念(48)陈静《程门四先生语录体散文研究》,吉林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11页。。此外,陈士强指出,语录“是禅宗僧人创造的一种文体,用来记叙禅师们在不同的居住地、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所说的种种法语,包括上堂示众、室中垂语、勘辨对机、偈颂、歌赞、拈古、颂古、短文、行状、塔铭、序跋等”(49)陈士强《禅宗语录两大集解读》,《五台山研究》1992年第2期,第9页。。李壮鹰指出,“禅门不重对经义的义解,而重对学人进行随机接引,故丛林中禅师的说话和他们与学人的对话,就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人把它记录下来,以便参究,便成为语录”(50)李壮鹰《谈谈禅宗语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65页。。刘绪义认为,“语录原为禅宗祖师说法开示之记录书。禅师平日说法开示,并不藻饰华词,大多以通俗语直说宗旨,其侍者与参随弟子予以记录,搜集成册,即称语录”(51)刘绪义《〈尚书〉——中国最早的语录体散文》,《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第46页。。谭家健指出,“今本《墨子》中,《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四篇,性质属于语录,文体与《论语》《孟子》相近,故后世又称‘墨家论语’。四篇作品多为墨子与门人弟子的谈话、论辩,少数是墨子独白”,“各章互不连属,篇题取自首章首句,看不出中心思想。似为墨家弟子各记师说,而后杂凑集合成篇,与儒家著作《论语》《孟子》之编辑方式相同。记录者或即当时,或在事后”(52)谭家健《墨家语录研究》,《齐鲁学刊》1998年第1期,第90页。。
前已指明,“语录”先于“语录体”出现,“语录”通常表现为篇章语体,而“语录体”则以专书语体存在。其实,随着“语录”的出现,有关“语录”的整理及编纂行为也发生了。有学者指出,“语”在形式上大致可分为重在记言和重在叙事两类,每一类又表现为散见的和结集(或成篇)的两种(53)俞志慧《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以言类之语为例》,《文史哲》2007年第1期,第10页。。散见的言类之“语”,通常是以“格言(语录)”的面貌出现,这在前面已经讨论了。其实还应注意言类之“语”的结集形式。据考察,目前所见有《国语》之《周语》、《鲁语》、《郑语》、《齐语》、《楚语》,《论语》,《逸周书》之《武称》、《王佩》、《周祝》,《文子》之《上德》、《符言》,《管子》之《枢言》、《小称》、《四称》,《大戴礼记》之《曾子制言》(上、中、下)、《武王践祚》,《新语》,《新书·修政语》(上下篇),《淮南子》之《诠言》、《说山》、《说林》中的记言部分,《说苑·谈丛》,以及出土文献郭店楚墓竹简《语丛》、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马王堆汉墓帛书《称》篇及银雀山汉简《要言》(54)俞志慧《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以言类之语为例》,《文史哲》2007年第1期,第11-12页。。在这些文献中,《论语》可暂毋论,应特别注意《逸周书》之《武称》、《王佩》、《周祝》,《文子》之《上德》、《符言》,《管子》之《枢言》、《小称》、《四称》,《淮南子》之《诠言》、《说山》、《说林》中的记言部分,《说苑·谈丛》,以及《语丛》、《为吏之道》、《称》篇及《要言》,这些文献不仅显示格言的面貌,亦即具有“语录”的特征,而且还汇集成专篇。比如《周祝》“是把许多格言、谚语式的词句串连集合在一起的”,《殷祝》“以叙事为主,讲述了汤放桀的故事,然而篇末……与《周祝》颇为相似”(55)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302-303页。。马王堆帛书《称》“篇中不少地方,似乎是辑录当时的格言,甚至流行的俗谚”(56)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298页。。《文子·符言》篇,王利器说:“符者,契也。言者,理也。故因言契理之微,悟道忘言之妙,可谓奥矣。”(57)王利器《文子疏义》,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5页。不过,《符言》收录的是老子的格言,可视为老子格言的专篇。《语丛》四篇,其内容体例与《说苑·谈丛》、《淮南子·说林》类似。《谈丛》、《说林》均为格言集,《谈丛》收集81则格言,这些格言大都散漫而缺乏有机联系,《谈丛》只是简单地辑录这些格言。《说林》收录的格言显然经过精心整理,较《谈丛》更进了一个层次。尽管这些文献在编纂层次上还存在差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们均属于格言的集合。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不同于单纯的语录,而是若干“语录”的集合。这也就意味着,“语录”出现了专篇,甚至专书。关于“语录”的这种情况,还应注意《仲虺之志》、《史佚之志》。史佚是周初很有影响的史官,《左传》、《国语》等文献多次征引其言论,《左传·僖公十五年》“且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文公十五年》“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昭公元年》“史佚有言曰:‘非羁,何忌?’”(5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59-360、611、1224页。;《周语》“昔史佚有言曰:‘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亊莫若咨’”(59)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第114页。。这些地方只是单纯引用史佚言论。然而《左传·成公四年》也引用史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话,不过却标明《史佚之志》(6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818页。。《左传·襄公三十年》还征引了《仲虺之志》。王树民指出:“‘志’的性质是略以类分,故有《军志》、《礼志》之称,又或以人或以国为区别,情况相当复杂,而主要为杂记有关言论与事实之书。其本身亦随时间而有发展,大致早期的‘志’以记载名言警句为主,后经发展,也记载一些重要的事实,逐渐具有史书的性质,其后则追记远古之事,杂记明神之事,泛记当时之事,成为别具一格的史书了。”(61)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5页。由此看来,《仲虺之志》、《史佚之志》应该是汇集仲虺、史佚格言而成的专书。这样,在先秦时期,不仅出现散见的“语录”,也早已存在结集的“语录”。结集的“语录”无疑为“语录体”的出现奠定基础,但结集的“语录”与“语录体”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是因为“语录体”所蕴含的文体形态超越了结集的“语录”。可以说,“语录体”的生成与《论语》密切相关。正是《论语》的出现,才标志着“语录体”的正式生成,这一点,可以从《论语》的文体特征与“语录体”的比较中得到答案。
三 “语录体”的文体生成及其特征
作为传统文献中的重要类别,语录文献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形态。目前一般将语录划分为诸子语录、禅宗语录和宋儒语录三类。如张子开论述诸子语录、禅宗语录和宋儒语录(62)张子开《语录体形成刍议》,《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517页。,陈静将语录划分为先秦诸子语录体、唐宋禅宗语录体、宋儒语录体(63)陈静《程门四先生语录体散文研究》,吉林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页。,王汝娟指出中国古代的语录作品主要包括诸子语录、禅宗语录、儒家语录(64)王汝娟《从出版史角度看南宋禅僧语录刊刻之意义》,《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51页。,等等。不过也有例外,任竞泽提到唐宋儒道释语录(65)任竞泽《论宋代“语录体”对文学的影响》,《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第134页。,刘伟生分语录为先秦诸子语录、宋明禅师语录、理学语录、毛泽东语录、网络语录(66)刘伟生《语录体与中国文化特质》,《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6期,第265页。,刘湛哲指出语录呈现出先秦散文语录、唐代禅宗语录、宋代诗话语录、红色革命语录等不同形式(67)刘湛哲《从“语录体”到“语录现象”——现代视域中的“语录体”嬗变研究》,暨南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页。。官贵羊对语录进行如下分类:(1)根据语录参与者的不同,分对话式和独白式;(2)根据语录发话人的不同,分为名人语录和佚名者语录集;(3)根据文本语气的不同,分交流体和传授体;(4)根据语录体式的不同,分口说体和笔记体;(5)根据语录内容的不同,分教育类语录、文化类语录、管理类语录、生活类语录、娱乐类语录等。(68)官贵羊《语录体的几种形态及作用——以诸子语录、禅宗语录、宋儒语录为立足点》,《安徽文学》2011年第12期,第142页。可见,参照标准的不同,语录文献的类型也就存在差异。
就传统语录而言,诸子语录、禅宗语录和儒家语录三者最为典型,它们在文体上呈现怎样的特征呢?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指出先秦诸子散文发展的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论语》和《墨子》,前者为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文;第二阶段是《孟子》和《庄子》,前者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后者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的形式而发展成专题议论文(69)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60页。。官贵羊指出诸子语录喜用独白方式反映被描述体的精神风貌,在大多数语境中,诸子语录的人物交流都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论语》之后语录体多采用“问答”体式,禅宗语录与宋儒语录也都沿袭这种方式(70)官贵羊《语录体的几种形态及作用——以诸子语录、禅宗语录、宋儒语录为立足点》,《安徽文学》2011年第12期,第143页。。谭家健指出,墨家语录的“文章已能熟练运用比喻和类比推理以加强说服力,恰当地引证历史作为立论依据。体裁不同于十论,而接近《论语》、《孟子》,不过风格韵味与儒家语录显然有别”(71)谭家健《墨家语录研究》,《齐鲁学刊》1998年第1期,第90页。。龙连荣指出《论语》512章中有近200章不是语录体而是记事或记对话的,有的则以“××问××”提起,然后孔子作答;有的于对话前有背景交代,对话中有相关叙述,对话后有反映或结果说明。大约314章是“纯语录体散文”,这些语录体都以“子曰”、“孔子曰”或“××曰”领起,篇幅上长短相差很大(72)龙连荣《语录体·对话体·专题议论文——先秦诸子哲理散文文体嬗变轨迹试论》,《凯里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91页。。杜绣琳指出《论语》中的语录体基本上用口语写成,大都语段很短,简洁而概括,一般只叙说观点,不加详论,言简意赅、精炼警策,富于哲理性和启发性;《老子》中的语录体是有韵的简明扼要的哲理格言,不求修饰,但所蕴涵的道理玄奥深刻,具有逻辑辨思的特点;《孟子》中的语录体篇幅增长,论述、议论的成分增多,很多段落围绕一定的中心展开,论说结构完整,条理清楚,文采飞扬,俨然是精彩的论说文(73)杜绣琳《〈淮南子〉“语录体”论说文的说理分析》,《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02页。。袁宾指出禅宗语录表现为空灵玄虚、奇怪突兀、机巧诙谐和大量使用口语(74)袁宾《禅宗语录的修辞特色》,《当代修辞学》1988年第2期,第18-19页。。李壮鹰指出禅宗语录多采取师生问答,不重文本,“不立文字”;多用俚俗的土语方言,质朴无文;禅师出语多简短而有机锋,有时甚至诡怪离奇,不可理喻(75)李壮鹰《谈谈禅宗语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65页。。刘晓珍认为禅宗语录只是在文体形式上继承《论语》的师徒问答方式,而在文风上与《庄子》更为神似(76)刘晓珍《禅宗语录与〈庄子〉文体文风相似性研究》,《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63页。。刘振英指出《金刚经》、《心经》表现为代佛立言,以答问为主的语录体;而《坛经》“变得更具文学性,语录体语言可以讲故事,可以说诗,为了便于诵读,韵语增多,为了强化传承谱系,也出现了人物纪传体的倾向”(77)刘振英《唐宋禅宗语录体的文体特征和多元包容性》,《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第75、76页。。关于宋儒语录,李光生指出理学家“善于采取问答式和点悟式的教学方式,点到即止,不作长篇宏论,以俚俗白话的语言,讲经论道。作为书院制度的产物,宋代语录体内容上注重推阐性命、关涉义理,语言上讲求方言口语、鄙俚通俗”(78)李光生《宋代书院与语录体》,《兰州学刊》2011年第2期,第135页。。任竞泽指出宋人语录在“形式上,哲人学者讲学或与时人辩论、师徒问答,山门徒弟子记录下来”,“内容上,推阐性命,统论义理,关涉道学理学”,“语言上,方言土语,鄙俚通俗”(79)任竞泽《论宋代“语录体”对文学的影响》,《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第134页。。
对于上述诸种认识,“语录”溯源与《论语》的编纂就成为澄清这些问题的两个关键因素。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语录”条中强调语录的兴起与佛教相关,认为释家语录始于唐代(80)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422页。。但据学者的考证,禅僧语录的编集始于晚唐五代,今本所收中唐以前所谓的机缘语,多是后人根据传言甚至想象而补编的(81)李壮鹰《谈谈禅宗语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65页。。其实“语录体”之出现最初与释家并没有多少关联,《辞源》说:“《旧唐书·经籍志》上《杂史类》有孔思尚《宋齐语录》十卷,为语录二字之始。自唐以来,僧徒记录师语,以所用多口语,故沿称语录。”(82)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商务印书馆2010年修订本重排版,第3161页。孔思尚不仅明确使用“语录”这一术语,而且还十分清晰地赋予其专书文体的意义。这就使此前尚处于隐晦状态下的文体因这一称谓而在世人面前豁然开朗起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齐语录》对于领会“语录体”无疑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宋齐语录》著录于《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然而该书已佚,不过《太平御览》还引几段文本:
梁特进沈约撰史,王希聃尝问约曰:“从叔太常,何故无传?”约戏之曰:“贤从叔者,何可载?”答曰:“从叔惟忠与孝,君当不以忠孝为美?”约有惭色。
虞愿字士恭,会稽人,祖为给事中。中庭有橘树,冬熟,子孙争取,愿独不取,祖及家人并异之。
张元字孝始。祖丧明三年,元每忧涕,读佛书以求福祐。后见药师经云盲者得视,遂请七僧燃灯,七日七夜,转药师经行道。每自责曰:“为孙不孝,使祖丧明。今以灯施普照法界,愿祖目见明,元求代暗。”其夜,梦一老人以金治其祖目,谓之曰:“勿悲,三日之后必差。”元于梦中喜跃惊觉,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目果渐见明,从此遂差。(83)李昉编纂、任明等校点《太平御览》第5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78-79、118页。
上述第一、三例记载的是人物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似乎与教学无关;第二例显示的是人物的行为,而非记言。根据这些佚文,可以推测《宋齐语录》中的“语录体”表现为言、行两录。《史通·杂述篇》说:“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松玠《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84)刘知几《史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1-82页。刘知几将《宋齐语录》与《世说》相提并论,显然明确表达了二者在文体方面具有一致性。《世说新语》虽然在文体上呈现“世说体”的特征,但是它与《论语》是一脉相承的。依据杨伯峻《论语译注》,《论语》分512章,其中纯粹记行的46章,记言的405章(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格言体,为267章;二是问对体,为138章),记行与记言杂糅的61章(即“事语体”)。纯粹记行的章分布在《公冶长》、《述而》、《子罕》、《乡党》、《先进》、《季氏》、《阳货》、《微子》中,以《乡党》最为典型;记行与记言杂糅的分布在除《学而》、《里仁》、《季氏》、《阳货》、《尧曰》之外的15篇中,记言则遍布全书20篇。就专书文体而言,《论语》已经具备言、行两录的特征。这样,尽管《宋齐语录》最早以“语录”命名,但作为一种专书文体,“语录体”显然始于《论语》。
《论语》言、行两录文体的生成,是编纂的结果。《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85)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7页。《论语》是先秦语类文献由“国语”转向诸子“家语”的重要界碑。早期编纂的“语”体如《尚书》、《国语》大都以王朝或诸侯国为单位,春秋中晚期以后,随着史官渐次流入卿大夫家,“家语”文献开始出现。蒙文通指出,春秋时期大夫家史是“以大夫个人作为记载中心,反映个人思想的言论在作品中的比重大大增加”,在此意义上,“大夫家史自可称为《家语》”。这种大夫“家语”在春秋晚期又有新的变化,《史记·秦始皇本纪》提及“百家语”,《李斯列传》也有同样的说法,“百家语”是指诸子,诸子之书被称为“家语”,表明诸子是自家史发展而来。(86)蒙文通《先秦诸子与理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格局而促使私学风气的兴盛,在此背景之下,弟子或门徒在一定程度上充当史官的角色而负责载录其师富有教益的言论,《汉志》所谓“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即是表明这一点。这种孔门实录为《论语》的编纂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当孔子去世之后,孔门开始着手《论语》的编纂。这项工作的进行,《汉志》只是用“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一语带过,对其具体过程并未进行细致描述。《论语》的编纂由谁主持,哪些人参与其中,什么时候完成,这些问题至今还制约着人们对《论语》编纂的认知。不过这方面的讨论,已经有学者做了相关梳理(87)具体请参看:唐明贵《〈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8页;唐明贵《论语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68页。。此处着重从《论语》编纂的角度去揭示“语录体”的生成。
有学者指出,《论语》编纂“在不需要交待语境而能读懂的情况下,直接以‘子曰’的形式载录经典语录;如果必须交代语境才能读懂语录,也只是采取概括提炼的方式,尽量避免繁琐的问答;即使有问答和对话,也仅仅是三两个回合,很少长篇大论”(88)侯文华《〈论语〉文体考论》,《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35页。。比较《论语》与《孔子家语》、《孔丛子》,这个判断大体是符合《论语》实际的。不过,这一说法似乎暗示《论语》遵循简化的原则。陈桐生指出,《论语》是从七十子后学的笔录素材中精选来的,是孔子语录的“节本”或“精华本”;同时,七十子后学又对原始笔录素材进行扩充和阐发,大小戴《礼记》记载孔子应对弟子时人的文章及上博简《仲弓》、《子羔》、《鲁邦大旱》,是孔子语录的“繁本”或“扩写本”(89)陈桐生《孔子语录的节本和繁本——从〈仲弓〉看〈论语〉与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形式差异》,《孔子研究》2006年第2期,第116页。。他的分析也支持简化的编纂原则。但是,无论就编纂方式还是文体来说,《论语》均呈现复杂性,单单简化的原则似乎不足以生成《论语》的多样化文体。事实上,无论是《论语》还是《礼记》等文献中的孔子言论,它们大都源于孔门实录。对于孔子的谈话或口头的孔子语录,孔门弟子在记录时有详略之别,而《论语》或《礼记》等文献中的孔子言论均有可能对之进行节录、扩充或照抄。因此,虽然不能排除《论语》编纂过程中确实存在简化的原则,但《论语》的编纂方式是多样化的。如《卫灵公》篇: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90)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65-1067页。
此文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子张提出“行”的问题,二是孔子的解释,三是子张的记录。这三方面一同构成完整的叙事。然而,这则文献提示我们应该注意这样的事实,即“书诸绅”的对象。结合《卫灵公》篇的具体语境来看,子张记录的不太可能包括此文本的全部内容,而只能是孔子的言论,亦即第二部分内容。据此,可以推论孔门弟子的原始笔记主要以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为中心,而对于事件的过程往往是忽略的。这也就表明,孔门笔记的原始形态当以人物言论为主。但事实上《论语》的文体却呈现出多元特征,这显然与不同的编纂方式相关。
我们曾从粘合、扩充、原文迻录及改造等四个方面归纳《论语》的编纂方式(91)夏德靠《〈论语〉文体的生成及结构模式》,《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09-111页。。比如粘合,《八佾》篇载: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92)程树德《论语集释》,第200-204页。
这个文本没有具体记载哀公的提问,但有宰我的回答,以及孔子的评论。很清楚,孔子并没有直接参与他们的对话,而只是对他们对话的评论。因此,从这个文本来看,哀公的提问与宰我的回答构成第一层次,而孔子的评论属于第二层次。既然回答与评论并不构成问对,它们应该出自两种不同的语境,而被编纂在一起则是粘合的结果。当然,这种粘合是有条件的,即被粘合的内容存在关联。关于扩充,一般来说,孔子与弟子及他人的对话都存在具体语境,但是,《卫灵公》篇“书诸绅”表明,子张记录的只是孔子的话,并没有将当时对话的具体语境完全笔录下来。这样,孔门实录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孔子的话语,一般是以书面文献存在,当然也存在口头形态;二是对话的具体环境,这部分内容主要依赖记录者的记忆或口传。前已指出,孔子去世后不久孔门就开始《论语》的编纂。杨义认为《论语》前后经历两次编纂,《论语》“最初的汇编当在孔子初逝,弟子在泗上庐墓服丧三年之际。哀戚追思,自然会忆谈先师的音容笑貌,弟子或其随从的后学记录在编,以存夫子之道”,而“《论语》另一度较成规模的编集成书,是在曾参身后,……曾门弟子重编《论语》的原则,除了强化曾子的道统地位之外,对于已有的或其他来源的材料,大体上采取兼容的态度”(93)杨义《〈论语〉还原初探》,《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第6-9页。。第一次编纂由于“时间切近,情境宛然”,“不少情境中的与闻者犹在”(94)杨义《〈论语〉还原初探》,《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第6页。,特别是编纂者很多就是原始笔记的记录者,所以他们对孔子或弟子言论的许多具体语境还记忆犹新,在编纂过程中自然能够把原本储存在记忆中的东西用书面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样,就形成《论语》中较完备的问对体及事语体。这些问对体与事语体自然是在原始笔记的基础上经扩充而形成的。然而,当再次编纂《论语》时,情况发生了改变。此时孔门弟子已经凋尽,主要是再传弟子负责编纂,这些人对原始笔记的具体语境不再像其师辈那样熟悉,这就使他们在处理一些笔记时大都原文迻录,并通常冠以“子曰”,从而形成格言体。
粘合、扩充、原文迻录这些编纂方式导致《论语》记言文体的形成,然而《论语》还存在记行文本,它们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既然孔门原始笔记是《论语》编纂的基础,那么,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孔门原始笔记在记言之外是否还有记行的文本。《汉志》没有讨论记行文本,现在也不好判断它是否注意到原始笔记记行文本的存在,在此只好通过其他方式来推测原始笔记是否存在记行现象。《乡党》篇除三句简短的对话文本之外,其余则是叙述体,属典型的记行文字。通常认为《乡党》篇记叙的主体是孔子,但是也存在其他的看法。《乡党》篇第一章“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庭,便便言,唯谨尔”(95)程树德《论语集释》,第635-636页。,明确出现“孔子”的称谓;但第六章的开头为“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96)程树德《论语集释》,第665-667页。,出现“君子”的提法。此处的“君子”是指谁呢?一种看法认为:“君子以孔子言之。曰君子者,见非孔子私意为之,而君子之事也。《孟子》曰:‘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此不曰孔子而曰君子,亦是类也。”(97)程树德《论语集释》,第667页。通过引用《孟子》的话以证明此处的“君子”即是指孔子。但也有论者认为此处的“君子”只是一个泛称,因为《论语》其他各篇没有把孔子泛称为“君子”的例证,所以不赞成把此处的“君子”理解为孔子(98)刘诚《〈论语·乡党篇〉辨伪》,《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2期,第110页。。其实,此处的“君子”虽不能坐实为孔子,但也不妨碍是孔子自比,《乡党》篇第六章很可能是孔子的一段语录,而今本《论语》误脱“子曰”:
〔子曰:〕“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推测,是因为此类句式在《论语》中很常见,如《学而》篇:“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99)程树德《论语集释》,第33-36页。又同篇:“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100)程树德《论语集释》,第52页。《为政》篇:“子曰:‘君子不器。’”(101)程树德《论语集释》,第96页。《八佾》篇:“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102)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53页。《里仁》篇:“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103)程树德《论语集释》,第247页。就这些引例来看,《乡党》篇第六章很可能是孔子的一条语录。这样的话,《乡党》篇就不存在称谓歧异的问题了。孔子在五十二至五十五岁之间先后担任鲁国的中都宰、司寇,并摄行相事,《乡党》篇就是他居官期间行为的记载(104)刘诚《〈论语·乡党篇〉辨伪》,《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2期,第108页。。该篇所记载的有关孔子公私生活、饮食起居等行为在孔门原始笔记中应该有所记录,因此,原始笔记或应存在记行的现象。如此,《论语》记行文本的一部分应是渊源于原始笔记,编纂者对此只是原文迻录。不过《论语》记行文体的生成还存在其他方式。《论语·先进》篇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105)程树德《论语集释》,第742页。这纯粹是叙述体,不妨视为记行的一种变式。然而据《新序·杂事》“孔子曰:‘言语:宰我、子贡’”及《史记·冉伯牛传》“孔子称之为德行”的记载(106)程树德《论语集释》,第742页。,《先进》篇所论“四科十哲”大约出自孔子之口。另外,《七经考文补遗》指出“古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107)程树德《论语集释》,第742页。。结合这些例证,“四科十哲”大约属于孔子的一条语录,由于脱掉“子曰”,于是形成一种记行文体。这就提醒我们,《论语》中的一些记行文体是通过改造对话而形成的。因此,《论语》的编纂者在不熟悉或者有意忽略说话主体时就原文迻录相关笔记材料,在这种情况之下使原来的对话转化成记行。
尽管言、行两录的文体在孔门原始笔记中已经存在,但这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的。只有到编纂《论语》时,才有意识地去建构言、行两录。刘知几曾指出先秦史官的传史方式经历由言、事分立到言、事相兼的转变,言、事分立时期出现比较纯粹的记言文献,如《尚书》、《国语》;言、事相兼时期则出现“事语”,如《左传》(108)刘知几《史通》,第8页。。刘知几的看法确实能够较好地解释《尚书》、《国语》、《左传》等文献的生成,可惜他并没有考察言、行两录的编纂方式。“事语”文献最明显的特征在于言与事的结合,而且通常情况下言是针对事而发的。言、行两录则与此不同,言与行是彼此独立的,不存在谁解释谁的问题。据文献的记载,言、行两录在《论语》之前已经存在。《礼记·内则》曾指出:“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三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礼,皆有惇史。”孔《疏》分析说:“五帝宪之法,奉养老人,就气息身体,恐其劳动,故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者,……言老人有善德行,则记录之,使众人法。……三王养老,既法德行,又从乞言,其乞言之礼,亦依违求之,而不逼切。三代皆法其德行善言,为惇厚之史。”(109)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4-855页。据此可知,在先秦史官传统中,起初重视的是德行的记载,后来逐渐发展到载录言论,于是形成言、行两录。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的存在,言、行两录文献才得以生成。《尚书·皋陶谟》提到“五典五惇”,柳诒徵说:“《皋陶谟》所谓五典五惇,殆即惇史所记善言善行可为世范者。故历世尊藏,谓之五典五惇。惇史所记,谓之五惇。”(110)柳诒徵《国史要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这样,可以认为言、行两录的文献方式根源于乞言传统。因此,无论是孔门原始笔记还是《论语》的编纂均受到乞言传统的影响。乞言传统重视保存老人的德行、言论,根本原因在于它们能够发挥指导意义。正是因为这种功能,《论语》的编纂者才自觉继承这一传统,重视孔子(当然也包括若干弟子)言论及行为的载录。在乞言传统下,人物的言论往往不是长篇大论,而大都呈现格言的特征。早期乞言文献难以考见,《晋书·王祥传》载:“天子幸太学,命祥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师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陈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训之,闻者莫不砥砺。”(111)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43页。有关此处的“乞言”,史官只是用“陈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来概括,很难反映乞言文献的特征。《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云:“帝乞言于王祥,祥对曰:‘昔者明王礼乐既备,加之以忠诚,忠诚之发,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动乎天地,天且弗违,况于人乎!’”(112)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7页。这就比较清楚地显示王祥言论的格言特征。所以,《论语》“很少长篇大论”,很多时候不是简化的结果,而是受乞言传统的影响。也正因为这种缘故,以《论语》为标志的“语录体”就与早期的语类文献在文体方面出现差异。
根据上面的分析,对于“语录”与“语录体”来说,可以得到如下的认识。在早期语类文献发展中,很早就出现格言,这些格言其实属于语录。后来出现格言汇辑的现象,这可视为专书形态的语录。不过,早期的语录主要立足于篇章意义上,并且在文体形态方面以格言为主。《宋齐语录》不仅铸就“语录”这样的专名术语,而且使“语录”之称由篇章文体指向专书文体。《宋齐语录》表明,作为专书文体意义上的“语录”呈现言、行两录的特征,可见言、行两录是“语录体”的根本形态。依据对《宋齐语录》文体的观察,可以将“语录体”溯源至《论语》。这就是说,《论语》真正开启了“语录体”这一文体形态。由于早期语类文献在文体方面大都具有篇章语体与专书语体两个层次,《论语》在专书文体方面呈现言、行两录的特征,而在篇章文体上则存在格言、对话、事语这些次生文体。尽管这些次生文体的呈现方式多样,不过由于受乞言传统的影响,它们在篇幅上大都显得精炼简洁,即使是对话、事语也是如此。《论语》的这些特性,深刻影响后来“语录”文献以及“语录体”的生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论语》的始源文献大都与教学相关,但从《宋齐语录》身上则很难发现教学的踪迹,这一现象也就意味着“语录”文献的生成环境具有开放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