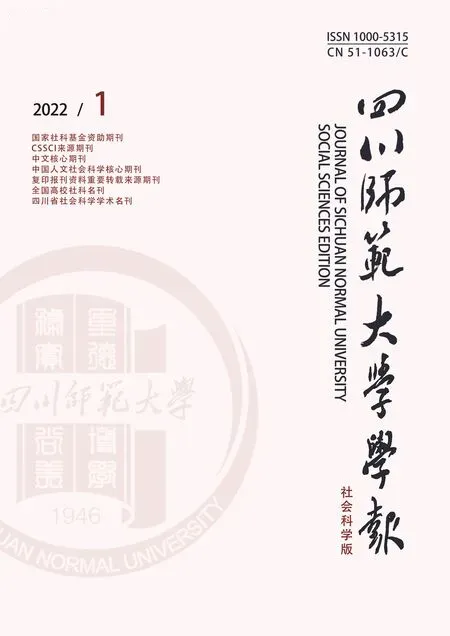试论中世末期京都町人的武装运动
王玉玲
应仁之乱(1467-1477)后,京都作为主战场被大面积焚毁,而且盗贼横行、土一揆频发,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极端无序的状态。而此时的室町幕府却今非昔比,已然无力维护京都的社会治安,取而代之的则是以三好氏为代表的各地守护大名对京都的轮番控制,加之细川氏的家督之争以及一向一揆对京都的进攻,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初期的京都始终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町人”作为新兴的社会阶层展开武装运动,不仅代替国家权力发挥守卫京都职能,而且在天文初年的一段时间内掌控了京都的市政权。对此,早期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町人“法华一揆”(亦称“天文法华之乱”)的宗教史研究,注重探讨法华一揆的宗教性质。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欧洲自由都市研究的影响,日本学界还出现了从都市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该事件的动向(1)关于法华一揆的研究,可参考藤井学法華衆と町衆(日本京都法藏館2003年版)、今谷明天文法華一揆—武装する京衆(日本東京洋泉社2009年版)等成果。从都市史的角度对京都以及京都町人进行研究的成果,可参考林屋辰三郎町衆の成立(载中世文化の基調,日本東京大学出版会1953年版)、秋山国三京都町の研究(日本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5年版)、脇田晴子日本中世都市論(日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版)、豊田武封建都市(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1983年版)、高橋康夫京都中世都市史研究(日本京都思文閣1983年版)等。。然而,无论是宗教史,还是都市史,往往都将法华一揆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件处理,而忽视了法华一揆与町人武装运动的衔接性以及町人武装运动对町人阶层势力消长的影响。我国学界尽管对町人并非全无研究,但相关成果主要集中于町人社会高度成熟的近世时期,而且多为考察町人社会心理、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成果(2)刘金才是国内研究近世町人的代表学者,曾发表过相关的一系列论文,如《幕末町人的政治倾向与历史作用》(《日本学刊》2001年第4期)、《论町人价值伦理的近代转型》(《东疆学刊》2006年第1期)、《中日前近代商人思想及伦理价值取向的差异——兼论中日近代化进程出现落差的思想原因》(《日本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等。此外,关于近世町人的相关成果,可参考张小龙《西方视野中的近代日本国民诚信度问题——以“町人根性”为中心》(《世界历史》2017年第4期)一文。。本文结合日本中世末期动荡的社会环境,对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期京都町人的武装运动进行考察,探究町人阶层成长、壮大并掌控京都支配权的历史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町人及其武装运动在社会动乱中发挥的历史作用以及对京都町人阶层发展的影响。
一 町人武装运动的社会背景
京都,作为日本平安时代都城平安京的所在地,自古就是重要的政治都市。进入中世时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其经济意义也日趋凸显。然而,应仁之乱后,在幕府权威急剧衰退的背景下,不仅各种一揆运动频繁爆发,而且各方大名势力也竞相入驻京都。结果,京都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町人作为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也都受到严重威胁。
(一)京都商业的繁荣与町人阶层的兴起
京都作为平安时代的都城,创建之初便在左京、右京分设东、西二市作为专门的商业地带,自古便兼具政治与经济意义。不过,由于平安京地势东高西低,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市同地势低湿的右京一并衰退。随之,左京成为京都的商业中心,并且在东市之外,即左京町尻小路与东西走向大路的交叉点上还形成了三条町、四条町、七条町等新的商业区域(3)林屋辰三郎町衆の成立,林屋辰三郎中世文化の基調,第189頁。。进入中世时期以后,京都作为公卿贵族、武士的聚居地以及众多寺社的聚集地,仍然不失为核心的政治都市。并且,随着庄园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京都经济都市的属性也进一步加强,成为了集生产、流通、消费于一身的经济大都市。据《明月记》记载,文历年间(1234),东起油小路、西至乌丸小路间的地段已然是“土仓不知其数,商贾充满,海内之财货只在其所”的状态(4)藤原定家明月記巻3,日本東京国書刊行会1973年版,第422頁。。直至室町时期,随着京都地域范畴的外扩,除左京的“下京”外,京外的“上京”,京都周边祇园社、北野社、清水寺、东寺、稻荷社等寺社周围也都出现了商铺林立的商业地带。这些商业地带不仅聚集了制作、贩卖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丝绸等纺织制品、漆器等工艺品、刀具等金属制品的各类手工业者,而且还有众多兼营或专营高利贷的金融业者。从上京、下京内经营布匹、木材、粮油和酒的商人分布情况来看,除以南北走向的町尻小路为中心形成的核心商业地域外,三条大路以北、六条大路以南同样有众多商人的存在(5)脇田晴子日本中世都市論,第285頁。,加之流动的商贩,可以想见室町时期的京都随处可见商人、商铺,商品经济异常发达。
随着京都商品经济以町为核心不断发展、繁荣,町逐步发展成为商业地带的代名词,而那些在各町开设店铺,制作、买卖商品的工商业者,则被冠以“町人”(6)町人通常用于概称江户时期居住在城市中的商人、手工业者,但早在镰仓时期已经有以“町人”称呼商人的用例,故本文采用町人指代中世末期的京都商人及手工业者。此外,中世末期的商人及工商业者亦称“町众”。之称。尽管京都町人的构成主体多样,从业内容亦不相同,但町人从事商业活动的基本形态却具有共同的特点,即町人对武家、公家及寺院等权门势力的依附与从属。町人对权门势力的依附,主要体现为以权门势家为“本所”(领主),通常以如下两种方式实现。第一,以“供御人”、“杂色”、“神人”、“寄人”等身份成为权门势家的从属民。例如,京中、河东及西郊的米商,以供御人的身份从属于大炊头中原家;三条町、七条町、锦小路町的棉布商人,以神人身份从属于祇园社;众多从事金融业的土仓、酒屋,作为寄人从属于比叡山延历寺等。第二,以“座”的集团身份从属于权门势力。所谓“座”,即从事同一行业的工商业者结成的同盟行会。“座”一方面是领主统治町人、收取赋税的重要媒介;另一方面也是町人获取包括对特定商品的垄断贩卖权、国家临时课役的免除权以及“关”、“泊”、“渡”等水路、陆路关卡的自由通行权等在内的各种商业特权的基本保障(7)網野善彦日本中世の非農業民と天皇,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84年版,第92頁。。祇园社丝绵商人的绵座、北野社麹商人的麹座即分别垄断着下京丝绵与洛中麹的贩卖权。町人与权门势力如此密切的结合,一方面满足了贵族、武士、僧侣等城市主要消费阶层的各种物质需求,另一方面也为町人阶层不断积蓄财富、发展壮大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室町幕府的衰退与地方大名的入京
应仁元年(1467),围绕将军地位的争夺,山名氏与细川氏汇集当时中央与地方的各种对抗势力,发起了历时11年的“应仁之乱”。长期的内乱,不仅开启了战火连连的战国时代,而且直接导致了幕府权力的衰退。关于乱后将军与守护权力的变化,兴福寺大乘院门迹寻尊在日记中如此写道:“虽为近国,近江、美浓、尾张、远江、三河、飞騨、能登、加贺、越前、大和、河内等,全然不应将军之令,皆无年贡等物之上缴。(中略)将军所治之国,限播磨、备前、美作、备中、备后、伊势、伊贺、淡路、四国。然,纵使以上诸国守护受将军之令,至于守护代者,则全然不从。总之,日本国中全无应将军之令者。”(8)辻善之助編大乗院寺社雑事記巻6,日本東京三教書院1933年版,第353頁。换言之,随着将军权威的衰颓,室町幕府的支配范围大幅缩减,彻底由足利义满时期君临公武的全国性政权跌落为畿内地区的区域性政权(9)永原慶二下剋上の時代,日本東京中央公論社1965年版,第323頁。。正因如此,长享元年(1487),将军足利义尚率兵征讨近江守护六角氏时,仅有畿内近国的守护军及将军的直属军随行出征。而在地方上,随着以守护代为代表的地方武士势力的抬头,守护大名的权威亦遭到挑战。为恢复领国秩序,守护大名纷纷离开京都返回领国,以守护大名驻京为基础构建的“幕府-守护制度”亦宣告瓦解。明应二年(1493)四月,细川政元发动政变,废黜足利义植(义材)、拥立义澄为将军(明应政变)后,室町幕府名存实亡,彻底走向衰落。
明应政变后,幕府实权由守护大名细川氏家督掌控,室町幕政进入细川氏专政时期。但由于幕府实力的整体衰退,加之细川氏内部的分裂(10)永正四年(1507)细川政元被杀后,细川家彻底分裂,其养子澄之、澄元、高国以及澄元之子晴元便围绕家督之位展开争夺。,即便仅是畿内地区,单凭细川氏的一己之力也已经无法有效进行统治。于是,大内氏、三好氏等地方大名的军事力量便成为细川政权的有力支持,纷纷指向京都。以大内氏为例,永正五年(1508),大内义兴举兵入京,不仅成功拥立足利义植复位,而且帮助细川高国夺回了细川氏家督之位以及幕政的掌控权。同样,继细川高国之后获得细川氏家督之位的细川晴元,也是在阿波、丹波大名的支持下重掌幕政。大永六年(1526)秋,波多野植通与其义弟柳本贤治在丹波举起反旗,反抗细川高国的统治。同时,流落阿波的细川澄元之子细川晴元,在三好氏的支持下趁机反攻京都。最终,在三好氏与柳本氏的共同支持下,细川高国败走,细川晴元取而代之,开始以和泉国堺为据点对畿内进行统治。在细川晴元建立的幕政体制中,厥功至伟的三好元长、柳本贤治分别出任山城国与河内国的守护代,占据十分重要的政治地位。而在将军足利义晴、细川高国出逃后,京都则成为各方势力竞相争夺之地,陷入了长时间的政治动荡期。
(三)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土一揆的勃发
应仁之乱后,随着室町幕府的式微,京都的社会秩序也陷入了极端无序的状态之中。公家贵族甘露寺亲长曾在其文明十六年(1484)六月的日记中写道:“无管领,无侍所,无诸司代,无开阖,无纠明之事,处处有如此事,末世之至也。”(11)笹川種郎編親長卿記巻2,日本東京内外書籍株式会社1941年版,第219頁。换言之,以管领、司代为代表的幕府中央高级官员以及侍所等统治机构皆形同虚设,毫不作为,京都社会一片混乱。具体来说,京都的混乱,首先源于土一揆(12)“一揆”由平安时代末期的农民斗争发展而来,泛指为实现某种共同目的而采取一致行动的反抗行为,土一揆、国一揆、宗教一揆(一向一揆、法华一揆)等即是中世时期常见的一揆形式。其中,土一揆泛指被统治阶层发起的一揆行为。德政一揆作为土一揆的一种,多以要求颁布解除借贷关系的德政令为诉求。的频繁攻击。正长元年(1428),以京郊农民为代表的广大高利贷债务者,在繁重的经济压力下,为取消与高利贷经营者间的债务关系,对京都内从事高利贷行业的“土仓”、“酒屋”等发起了暴力打砸、抢夺的集体行为,是为日本历史上最初的土一揆,亦称“德政一揆”。此后,尽管室町幕府出台德政令,认可了取消借贷关系的合法性,但要求德政的土一揆仍然没有缓和的趋势,自正长元年(1428)以来便频繁对京都发起攻击。应仁之乱爆发后,土一揆曾一度减少,但乱后很快便再次活跃起来,频频攻击京都。从应仁之乱结束(1477)到织田信长入京的天正元年(1573),京都共遭受土一揆攻击18次,而其中10次都集中发生在文明十六年(1484)至明应四年(1495)的十余年间(13)应仁之乱后至织田信长上京前的土一揆次数,由青木虹二百姓一揆総合年表(日本東京三一書房1971年版)统计而得出。。并且,与应仁之乱前的土一揆相比,随着地方武士的上京,土一揆的参与主体变得更加宽泛,除京都周边村落的百姓、武士以及京都的流民外,远国的地方武士也参与到了土一揆之乱中(14)今谷明天文法華一揆—武装する京衆,第78頁。。尽管土一揆爆发时,多以酒屋、土仓等金融业者为主要的攻击对象,但实际上土一揆造成的影响却时常波及全体町人以及整个京都。尤其是当土一揆遭遇幕府的武力镇压时,所谓“土一揆乱入京中,土仓之外,乱入家宅,强取杂物,肆意放火”(15)辻善之助編大乗院寺社雑事記巻3,第207頁。,除土仓外,对普通的民居、寺社等也不加区别地进行打砸,对京都社会造成了极大破坏。
与此同时,细川氏内部的夺权斗争进一步加剧了京都社会治安的恶化。永正四年(1507),细川政元被杀后,为争夺家督之位,细川氏内部纷争不断。大永七年(1527),细川晴元与细川高国围绕京都的控制权展开攻守战。五月,三好元长、柳本贤治作为细川晴元方势力,二度占领京都。其后,为搜寻细川高国势力的余党及同谋,三好元长、柳本贤治等人频繁以搜寻“敌方残党”、“牢人所缘”为由,闯入与细川高国关系密切的公武宅邸、町屋,肆意抓人、抢夺财物。据同时期公家日记记载,在大永七年(1527)十一月至翌年正月期间,京都共发生9起强闯民宅事件。如十一月二十六日,波多野军以藏匿“牢人妻子”为由,闯入三位刑部卿入道宅邸,“打砸,强取杂物,片物不留”;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好军以“牢人所缘”为由,闯入位于一条乌丸的畳屋;十二月十日,三好军闯入净土寺宿坊;十二月十一日,柳本贤治部下武士闯入上京柳原大森宅邸,“强掳女眷数人”(16)山科言継言継卿記巻1,日本東京太洋社1941年版,第86、88、90頁。;等等。可见,遭受三好、柳本、波多野等军势力侵扰的不仅有公卿、武士,连僧人以及普通町人也未能幸免。
简言之,中世末期的京都尽管经济异常繁荣,但自应仁之乱开始便始终处于动荡之中。一方面细川氏主导的室町幕府日渐衰败,另一方面各地的有力大名趁势崛起,并纷纷加入到中央的夺权斗争中。结果,京都成为各方势力竞相争夺的对象,不仅不断遭受战火的侵袭,而且土一揆频发,社会秩序极度恶化。在幕府将军、管领纷纷逃离,京都真正成为“无主之都”的背景下,町人成为了京都社会的中坚力量。
二 町人武装运动的历程
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初期,在京都社会秩序极端恶化的背景下,町人最初拿起武器、进行武装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自卫。而在一向一揆对京都发起攻势时,町人的武装运动则由被动自卫发展为主动出击。结果,不仅成功阻挡了一向一揆对京都的攻势,使京都得以免除战火的侵袭,而且极大地打击了一向宗势力。就町人武装运动的整体历程而言,依据其目的性、组织性的不同,可以将其历史过程划分为武装自卫的前期阶段与法华一揆的后期阶段。
(一)前期町人的武装自卫
在前期阶段,土一揆以及地方大名势力对京都的武力控制是破坏京都社会秩序的两大因素。就以德政一揆为代表的土一揆而言,由于其攻击的主要对象是高利贷业者,因此,初期町人应对土一揆侵扰时,主要是以土仓、酒屋等金融业者为主体。具体来说,即或是以重金贿赂幕府管领请求幕府出兵镇压,或是重金聘请有力武士对土一揆进行武力征讨。但二者的收效都不大,要求德政的土一揆仍然层出不穷。于是,文明元年(1469)以后,京都的金融业者开始自主组织武装力量,与土一揆进行对抗。如文明十八年(1486),土一揆占领东寺时,洛中“土仓质屋之辈”身穿甲胄,与细川氏被官一同对抗土一揆的进攻(17)笹川種郎編親長卿記巻3,第128、129頁。;延德二年(1490),土一揆在京中打砸时,酒屋经营者土仓野洲井参与对抗土一揆,并杀死了土一揆主谋(18)笹川種郎編親長卿記巻2,第286頁。。随着土一揆影响的进一步扩大,京都的普通町人也被卷入其中,农民与高利贷业者之间的矛盾随之升级为农民与全体町人的矛盾。除所谓“土仓质屋之辈”外,京都从事其他行业的工商业者也开始加入到应对土一揆的行列。明应四年(1495)十月,西冈土一揆进攻京都时,以泽村细仓为大将,由町人及土仓众组成的军势一同在高辻室町抗击土一揆,杀死土一揆参与者数十人(19)近衛政家後法興院記(下),日本東京至文堂1930年版,第1062頁。。
同样,面对各方入京武士势力的侵扰,京都町人也进行了自主的武装防卫与抵抗。尤其是大永七年(1527),细川晴元势力控制京都期间,町人武装与动辄“乱入诸家”的三好元长、柳本贤治等武士势力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三好军以抓捕“牢人缘者”为由强闯位于一条乌丸的畳屋时,包括乌丸町町人在内的两三千町人对三好军进行包围,以高呼抗议的方式予以阻止;翌日,为对乌丸町人进行惩戒,传言三好军计划再次出动,然而乌丸町人不仅没有四散逃跑,反而决议奋起反抗,在町四周构筑称为“町围”的防卫设施(20)高橋康夫京都中世都市史研究,第403頁。。同样,享禄二年(1529)正月,柳本新三郎以对权大纳言一条房通所领征收赋税为由进入其领地,也引发了町人骚动。同月十日,上京革堂(21)上京行愿寺的革堂以及下京顶法寺的六角堂是京都市民举行集会的“町堂”。的钟声响起,町人闻声从四方赶来,围攻柳本军;次日清晨,钟声再次响起,町人再次集聚,双方对立进一步激化,包围柳本军的数百名町人,一如往常,高声呼喊,土仓众高屋弥助等人射死柳本军三人、射伤七八人;最后,幕府政所执事家臣、伊贺守护被官等介入调解,事件才以双方和解的方式了结(22)山科言継言継卿記巻1,第128、129頁。。
由此可见,前期阶段的町人武装运动主要以自卫为目的,且规模比较有限。通常是在某町遭遇袭击后,附近的町人率先群起而动,同时敲响附近寺院的早钟,而后上、下京町人闻声前往,进行武装支援。作为被统治阶层之一,町人同农民一样在混乱的社会环境中拿起武器,实现了武装化。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土一揆相比,该阶段的町人武装运动并没有特定的政治或经济诉求,也没有明确的组织性,可以说是在金融业者主导下,以地缘为基础、以维护共同利益为目的,随时进行的一种自卫性质的武装运动。不过,通过前期的武装运动,町人阶层内部显然已经达成了一致战线,形成了有别于“座”的普遍结合,并且在维护町人阶层的利益以及京都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后期町人的宗教斗争
在一向一揆对京都构成威胁后,町人便转以一向宗势力为对象展开了后期的武装运动。町人与一向宗势力之所以形成对立,与町人的宗教及政治立场密切相关。在中世末期的京都,日莲宗是备受町人阶层崇信的佛教宗派。所谓日莲宗,由日莲始创于镰仓中期,因以《法华经》为最上佛典,故又称法华宗,13世纪末由日莲的直系弟子日像传入京都。由于受到广大町人的欢迎,日莲宗在京都实现了很大发展。天文初年时,京都的日莲宗大寺院已达到21座(23)杨曾文《日本佛教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13、498页。。所谓“京都日莲宗繁昌,每月新建两、三寺,京中大抵成题目之巷”(24)日置謙校一向一揆と富樫氏,日本金沢石川県図書館協会1934年版,第127頁。,京都日莲宗异常兴盛。作为新兴的佛教教派,日莲宗教义极具特色,对待他宗历来采取批判、“折伏”的态度,且允许以“护教”之名蓄备兵杖。在这种教义思想的影响下,町人的武装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逐步实现了组织化与规模化。在16世纪初的乱世中,不断壮大的日莲宗势力,很快引起了细川政权的注目,并在细川政权镇压一向宗势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向宗,即净土真宗。与京都的日莲宗不同,一向宗主要以农民为布教对象。在莲如出任本愿寺第八代法主期间,一向宗获得了显著发展,不仅获得了众多地方武士和农民的皈依,而且通过与村落组织的结合形成了由本寺-末寺-道场组成的集权式宗教组织,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一向一揆(25)一向一揆即以一向宗信众即农民为主体发起的一揆。。而就16世纪初一向宗势力与细川政权的关系来看,二者的关系先后经历了从合作到对抗的变化。享禄五年(1532),在一向一揆大军协助细川晴元消灭阿波国三好元长的大军后,一向一揆势力在大和、摄津、河内、和泉等畿内全域快速扩张,而且火烧奈良兴福寺,直接导致其与细川政权的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为压制一向一揆的壮大势头,细川晴元决定对一向一揆进行镇压,一方面命木泽长政等对畿内各真宗道场进行大肆打砸,一方面向真宗以外的各大寺社发出号令,意图利用宗教势力对真宗实施包围战。
京都日莲势力即是当时细川晴元动员的宗教势力之一。与前期相比,作为法华信众的町人,采取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政治态度,不仅不再反对细川政权,反而激进地支持细川政权,成为细川晴元政权下由武士领导的武装力量。天文元年(1532),在细川晴元方与一向一揆方正式交锋前,传言一向宗欲“退治日莲宗”,对法华宗进行讨伐(26)塙保己一等編新校群書類従巻20,日本東京内外書籍株式会社1929年版,第8頁。。于是,京都日莲宗势力蜂拥而起,发动法华一揆。同年八月七日,在法华信众应召出征处于京都东郊的一向宗大本营山科本愿寺之前,在武士山村正次的率领下,其信众与细川军联合举行了示威游行式的“打回”(27)16世纪前半期特有的军事用语,即市民的武装集团示威游行。在开战前,具有召集兵力、扩大军势的作用。,即所谓法华一揆在日本史上的初见。据公卿鹫尾隆康日记记载,当日“京中町人等”法华信众汇集的兵力达“三四千人”(28)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二水記(四),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版,第87頁。。凭借武装规模的优势,町人武装不仅在细川晴元正式发动对山科本愿寺的包围战之前多次协助细川军阻断一向一揆对京都的进攻,而且在八月二十四日细川军发动总攻的过程中,会同木泽长政等多方势力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结果,一向一揆势力大败,大本山山科本愿寺及其寺内町被付之一炬,“不残一屋”、“寺内外不留一家”,盛极一时的山科本愿寺化为一片焦土(29)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二水記(四),第90頁。。其后,由于一向宗的信众以农民为主,布教据点多分布在京郊的村落内,因此町人武装还放火烧毁了许多京郊村落。如天文二年(1533)十二月二十五日,因疑虑本愿寺余党与细川晴国势力潜藏在京都西郊的村落内,“日莲众今朝于西边土西院、山中、郡、梅津、河端等十一村放火”(30)山科言継言継卿記巻1,第285頁。,烧毁了11个村落。此外,法华一揆还进一步介入一向一揆与细川政权的抗争,解除了一向一揆对细川氏大本营和泉国堺的围困。期间,为支援和泉方面,“日日敲响集会之钟。……终夜终日振聋发聩”,京都法华一揆连日敲响革堂、六角堂的早钟,动辄汇集数千兵力,“吹锣打鼓”,奔赴战场(31)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二水記(四),第94頁。。
可见,进入后期阶段以后,在外部环境与自身信仰的双重作用下,町人的武装运动在多个层面发生了质变。首先,日莲众作为京都町人的另一标识,成为了町人开展后期武装运动的共同宗教身份;其次,武士与日莲僧侣加入其中,并在组织、领导町人武装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细川政权对日莲宗势力的利用以及日莲宗与一向宗宗教冲突的政治化,使町人武装运动增添了政治斗争与宗教斗争的双重色彩。结果,町人的武装运动不仅达成了守卫京都、守护町人利益的基本目的,而且协助细川政权成功打击了一向一揆势力。
三 町人武装运动的历史影响
在一向一揆与细川政权和解后,细川晴元并没有立刻返回京都,而是继续留在和泉国堺。换言之,京都仍然处于“无主”的状态。而町人作为守卫京都、击退一向一揆的最大功勋者,不仅使日莲宗获得了在京都更大的发展,而且顺势接管了京都的市政权,既包括京都的防卫权、治安权,也包括经济方面的税收权等。但町人以及日莲宗势力的快速崛起及其对经济权益的过分追逐,却引起了传统宗教、贵族势力的极大不满以及细川政权的警觉,结果天文五年(1536)日莲宗被驱逐出京,町人掌控京都的短暂历史随即告终。
(一)法华一揆的成果及町人武装运动的终结
法华一揆的胜利,不仅为细川政权解除了来自一向一揆的威胁,而且使町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并逐步掌控了京都的市政权,获得了诸多特权。首先,町人通过控制“京七口”通行权的方式掌控了京都的防卫权。所谓“京七口”,是指进出京都的七处关口。自天文元年(1532)八月开始,京七口的通行权便处于町人的控制之下。其次,在打击一向宗势力的过程中,町人还掌控了京都的刑事裁判权。实际上,在与一向一揆对抗时期,就已经存在町人不经守护代、郡代自行对他宗僧侣进行处刑的情况。如天文二年(1533)二月十八日,3名一向宗门徒就因火烧下京日莲宗显本寺而被日莲众逮捕、处死(32)山科言継言継卿記巻1,第225頁。。最后,町人还通过不缴纳“地子钱”的方式获得了经济上的免税特权。“地子钱”,是京都工商业者向屋地所有领主缴纳的赋税,与农民向领主缴纳的年贡类似。对于町人而言,地子钱是其主要的经济负担。而在庄园经济逐步瓦解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地方庄园收入趋于断绝的都市领主而言,地子钱则是其重要的经济来源。在町人与一向一揆进行武装对抗期间,地子钱作为军费被临时免除,而在一向一揆对京都的武装威胁解除后,不缴纳地子钱则进一步发展成为町人常时性的经济特权。所谓“公方样,桑实御座以来日莲宗之时,不致洛中地子钱,有名无实”(33)鹿王院文書研究会編鹿王院文書の研究,日本東京思文閣2000年版,第220頁。,即在将军足利义晴滞留近江桑实寺的天文元年(1532)至五年(1536)期间,京中全无“地子钱”的上交,町人不缴纳地子钱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
此外,町人还意图涉足对京郊农村的支配,进一步扩大其经济特权。天文三年(1534)三月,日莲众通过山城守护代木泽长政、近江守护六角定赖向幕府请愿,成为宇治郡十一乡、山科七乡、东山十乡等京都周边庄园的“请负代官”。代官请负在中世后期是都市领主对地方庄园进行支配时十分常见的方式,简单来说,就是代官以每年向领主上缴一定数量的赋税为条件获得地方庄园的管理权及税收权。不过,分布在畿内地区的“膝下领”,通常不采用代官请负的支配方式,而是由领主直接进行一元化管理。因为代官请负虽然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赋税的上缴,但也意味着领主支配权的退步。正因如此,町人提出的代官请负请求,立刻引起了各京都领主的警惕。领有山科七乡的山科家,随即为拒绝町人的要求而四处奔走,最终朝廷以山科七乡为守护不入之地、乡民承担禁里门役为由,令幕府拒绝了町人的请负要求(34)山科言継言継卿記巻1,第320頁。。
可见,原本从属、依附于京都领主的町人,在实质上掌控了京都的市政权后,为获取更多的经济权益,展开了一系列与领主利益相冲突甚至反领主的行动。这样的做法很快引起了京都领主层对“日莲党”的极大不满,对日莲宗以及日莲众的恶评四起。并且,在“松本问答”(35)天文五年(1536)二月,山门僧人华王房与日莲信众(松本久吉)进行法论,结果华王房论败,史称“松本问答”。该事件被视为引发山门对日莲宗进行讨伐的导火索。事件后,以比叡山为首的传统宗教势力也对日莲宗展开了攻势。天文五年(1536)七月二十七日,比叡山与近江守护六条定赖的联军对京都日莲宗势力发动了武力攻伐。结果,日莲宗惨败,而且下京全域以及上京的三分之一地域都在这次动乱中被烧毁。同年九月,细川晴元正式返京后,日莲宗的崇信、布教、建寺等行为一律被列为禁制的对象,日莲宗势力彻底被驱逐出京,町人的武装运动也随之终结。
(二)町人武装运动的影响
天文五年(1536),细川晴元返京后,京都局势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稳定。在町人生活回归常轨的同时,町人的武装运动也淡出历史舞台。褪去宗教外衣的京都町人,失去了武装规模化的可能。法华一揆后,町人获得的各种特权也随之丧失。但町人武装运动对町人阶层的发展以及町人自治社会的形成却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天文五年(1536)后“町组”的出现。所谓“町组”,简单来说,就是以町的所在地为基础形成的町的联合体。历史上,京都町人以町为单位结成的共同体,最早出现在南北朝、室町时期(36)脇田晴子日本中世都市論,第296頁。。但与天文五年(1536)以前散在的町人集团相比,町组则是町与町之间更大规模的结合体,如下京的西组、艮组、中组、巽组、七町半组以及上京的立卖组、小川组、西组、一条组等都是典型的町组。从町组的组织构成来看,一个町组通常由多个町组成,例如下京的西组、艮组、中组、巽组即分别由11町、15町、18町、13町组成。并且,其中各町的大小规模也不尽相同,规模较大的町往往被称为“亲町”,下部包含数个规模较小的“寄町”(亦称“枝町”)。在此基础上,上京、下京的各町组进一步结合,便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上京中”与“下京中”町共同体。从町组的运营模式来看,各町组内部都有各自的自治机构,以“月行事”、“宿老”为代表的各町负责人承担着町组的运营与管理责任。同时,还有按月轮流负责町组事务的“月行事町”。
在中世末期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尤其是在都市领主对町人统治力度衰减的背景下,町组成为了町人实施自治的重要社会单位。以町组为基础,町人在财政、赋税及刑事警察权方面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治。前文提及,京都町人从事商业活动的前提在于其对贵族、寺社等都市领主的依附关系,这些都市领主作为町人的“本所”,在赋予町人经营特权的同时,掌握着向町人征收地子钱、杂公事等赋税以及处置领内民事、刑事纠纷的权力,即所谓税收权与刑事警察权。在町人控制京都市政权期间,京都领主对町人的税收权与刑事警察权一度丧失。尽管在日莲宗被驱逐出京后,京都领主的相关权利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但町人实施自治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财政方面,各町组实行了自主的财政运营,出现了向町内居民借贷钱物、出租房屋以及向行人收取通行费等方式实现自主的财政开支(37)川嶋将生町衆のまち京,日本東京柳原書店1976年版,第63頁。;税收方面,町组成为都市领主向町人征收地子钱的媒介,出现了由町组负责的所谓“町组请”;刑事警察权方面,上、下京的各町组以及町组的负责人代替领主乃至幕府成为处理町人纠纷的主体。当各町间发生纠纷时,上、下京的各町组以及町组的负责人积极介入调解,自主进行解决的方式成为普遍的矛盾处理方法。
总而言之,在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初的乱世中,京都町人同其他社会阶层一样,在武装化的基础上展开了积极的武装运动。尽管町人的武装运动最初源于与土一揆的对抗,但从结果来看,町人的武装运动不仅成功抵御了土一揆对京都的进攻,达成了守卫京都的基本目的,而且开创了町人支配京都的历史。町人作为新兴的社会阶层,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果,可以说与町人自身的法华信仰以及细川政权的政治需要直接相关。一方面,共同的法华信仰,使町人完全克服了以金融业者为代表的上层富裕町人与下层町人间的经济矛盾,使町人以共同的宗教身份结成了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共同体。另一方面,细川晴元政权镇压一向一揆势力的政治需要,使町人武装与政治权力结合,并获得了与一向一揆进行武装对抗并对京都进行支配的合法依据。而导致町人武装运动转瞬即逝的原因,则较为复杂。首先,京都町人的社会基础相对薄弱,与具有广大农民信众基础的一向宗相比,在人数上并不具有优势;其次,法华一揆的构成主体相对单一,基本由日莲僧侣与町人信众组成,在失去了武士的领导后,其武装战斗的实力必然大受影响;再次,町人阶层的经济属性限制了町人武装运动的可能性,町人既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也并不具备统治、支配京都的政治能力;最后,京都作为公、武政权的所在地,具有极为重要且特殊的政治意义,也是造成京都町人武装运动迅速终结的重要原因。不过,毋庸置疑的是,这段历史在京都町人阶层的成长历程中以及京都的城市发展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是町人自治组织的建立及其自治的初步形成,对近世町人社会及其自治体制的成熟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