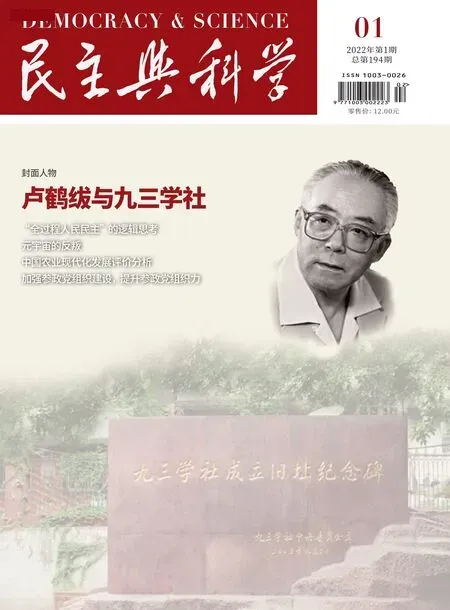红丸案与明末党争
刘润浩
明季党争之缘起,在于皇权的恣意无约束,各党之主张也要臣服于“维护皇权利益”,因此这种党争具有鲜明的“皇权主义”色彩。党争手段之残酷令人不寒而栗,无论是东林党还是阉党,都不乏致对方于死地的斗争取向。这种血淋淋的争竞方式,无论如何都无法与现代社会相兼容。因此,明季的“党”,绝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明朝中后期,朋党之争日趋激烈,大名鼎鼎的明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无一不与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三案原本为宫廷内事,但正如温功义先生所言:其影响所及,却已远逾宫廷,波及于都城内外,以至边关和江南。一众党派围绕这三案大做文章、攻伐不止,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明朝的覆灭。在这三案中,“红丸案”是第二案,属于前之“梃击案”的衍生,同时又直接导致了后之“移宫案”的发生。再加上在此案中,东林党人上疏最多,之后阉党借助《三朝要典》翻案时,此案牵涉的东林党人亦最广,可谓与党争之纠葛最深,故而此案值得专门加以剖析与审视。而通过耙梳此案亦可发现,明末这些所谓的“党”,无论是在斗争的缘起还是使用的手段方面,都还与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去之甚远,亦即他们仍不脱传统朋党之窠臼。
一、缘起:国本之争与梃击案
欲明红丸案之始末,则势必绕不开在此之前所发生的、对大明政局产生深刻影响的“国本之争”(或称“争国本”)。此事可以说是明代后期诸多政治事件的导火索,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导致明末三大案的发生。
(一)国本之争
“国本之争”是指,明万历九年的某日,明神宗朱翊钧(也就是俗唤作万历皇帝者)前往慈宁宫向其生母李太后请安,一王姓宫女(明时称宫女作“都人”)为神宗盥洗。恰好李太后未在,神宗一时兴起临幸了王都人。王氏遂有妊,后产一子,起名朱常洛,为神宗的庶长子。朱常洛只是神宗偶然兴起的“产物”,因此他和他的母亲均不受宠。神宗所爱者是贵妃郑氏,万历十四年,郑贵妃生子,起名朱常洵,神宗爱屋及乌,也对朱常洵宠爱有加。由于彼时神宗尚未立太子,再加上他不喜长子朱常洛而偏爱三子朱常洵,一时间“废长立幼”的流言飞起,有鉴于此,朝臣纷纷上疏请立朱常洛为太子,以靖浮言。神宗其实确有废长立幼之心,但面对汹汹清论还是有所忌惮,不敢一意孤行。迫于无奈,神宗使出了“拖”字诀,索性将太子之事搁置了起来,迟迟不定太子的人选,但与此同时,其又变着花样提高朱常洵的待遇,以与朱常洛比伉。太子者,国本也,神宗、郑贵妃及朱常洵与廷臣、朱常洛这场旷日持久的太子人选之争,就被史书唤作“国本之争”“争国本”。虽然此事最后以神宗让步、朱常洛于万历二十九年被立为太子而告终,但朱常洛的太子之位坐得并不安稳,看似平静的政局背后实则一直有着暗流涌动。果不其然,万历四十三年,矛头直指朱常洛的明末三案第一案——梃击案发生了。
(二)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的傍晚,一男子手持一根枣木棍(也就是所谓的“梃”),径直闯进了太子所居的慈宁宫,打伤守门太监李鉴后,意欲行刺太子。韩本用等一众太监闻讯赶来,迅速将此人制服。巡皇城御史刘廷元即时就审,查明此人叫张差,但再问其他事项,则其言语颠乱,状若疯傻。刘廷元遂以“按其迹,若涉疯癫,稽其貌,实系黠猾”之论上报刑部。刑部以其为疯癫之人报给神宗,但却被东林党人王之寀窥得端倪。王之寀巧施手段,查明张差背后果有主使,而其所供出的庞保、刘成等人,俱是郑贵妃宫里的内侍。此论一出,舆论哗然,郑贵妃谋刺太子的嫌疑令其百口莫辩。郑贵妃大惶惧,急忙求救于神宗。神宗认为,舆情汹汹不能强压,只能由太子出面以解此厄。事到如今,郑贵妃别无他法,只得向太子求情。朱常洛说只追究张差一人之责即可,不要株连他人。此案遂以张差伏法、其余张差所供出者或发配边疆或秘密处死而告终。震动晚明政坛的“梃击案”就此不了了之。
争国本和梃击案后,虽然朱常洛的太子之位最终得以坐稳,郑贵妃一干人等再也无力与太子争竞,但双方之间的关系恐怕远非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和谐。应该说,前述的桩桩件件早已给朱常洛和郑贵妃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深深的裂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红丸案的发生埋下了伏笔,就缺一个引发的机会了。而随着万历四十八年神宗驾崩、太子登基,针对朱常洛的第二场阴谋“红丸案”,遂悄然展开了。
二、案发:红丸案发微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朱翊钧驾崩,八月初一日,太子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即明光宗。此时最不安的,恐怕莫过于郑贵妃了。在争国本一事中,郑贵妃为给自己的儿子争太子之位,与朱常洛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而之后梃击案的发生,再度给两人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故二人之间自当存在着比较深的芥蒂。朱常洛继位后,郑贵妃处境之危险尴尬,毋庸赘言。
不过,神宗可能也预感到了郑贵妃或将面临的尴尬处境,遂在驾崩前给光宗留下一道遗训:尔母皇贵妃郑氏,侍朕有年,勤劳茂着,进封皇后。面对这个烫手的山芋,光宗巧妙地把它甩给了内阁,令内阁“传示礼部查例来行”。而面对这个有违礼制的要求,礼部不出所料的将本顶了回来。但郑贵妃又岂是坐以待毙之人,其早就将人脉延展到了光宗内闱,结交了光宗宠妃李选侍。既然先帝遗诏被驳,郑贵妃遂故意向光宗为李选侍求封后,李選侍为回报郑贵妃,亦向光宗求封郑贵妃为皇太后。光宗宠幸李选侍,难以直接拒绝其请求,而且郑贵妃为李选侍求封后又正中光宗下怀,这下轮到光宗左右为难了,局面一度陷入僵持。
先帝遗诏未起作用、自己又与时君有隙,显然这种僵持的场面对郑贵妃更加不利,如何破解此局呢?左思右想之下,郑贵妃决定使用美人计。于是,郑贵妃精心挑选了八名美女,盛装巧饰,觑得一个机会,亟献于光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示好,光宗倒也未加多想,直接悉数笑纳。光宗在神宗朝时,太子之位坐的战战兢兢,觊觎其位者终日虎视眈眈,令光宗提心吊胆,不敢稍懈,以免被人抓住把柄,如今终于得继大统,骤然轻松,岂有不放纵之理?正好借着郑贵妃献女的机会,光宗遂纵情声色、耽于逸乐。光宗身体本来就不好,这么一通折腾下来,健康状况更是急转直下。而光宗作为一国之君,其身体状况直接牵涉到朝局稳定,故随着光宗渐成沉疴,朝中亦逐起阴诡之风。
光宗在自觉病重后,急召御医治疗。但御医治病讲究循序渐进,光宗急切之间哪里等得,于是转令掌管医药的宦官崔文升诊治。此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崔文升对这样一位身体虚弱的病人竟下了泻药大黄。这使得光宗一昼夜腹泻达三四十次,身体状况大受摧残。崔文升本就是郑贵妃宫中内侍,再考虑到光宗病重这特殊的时间点,很难说崔文升此举与郑贵妃毫无关系。再加上此时国子监李胜芳告诉杨涟说,郑、李二人相互勾连,刺探宫中内事,崔文升下泻药确实是有意为之,因此崔文升用泻药,很有可能是受郑贵妃指使。
面对这一紧急局面,十六日,周嘉谟在杨涟、左光斗的倡言下,大会群臣,当众叱责郑贵妃之侄郑养性,言说郑氏一族贪得无厌、包藏祸心,恐无噍类。众人并令贵妃移宫,郑贵妃迫于压力,只得移居到了慈宁宫。
尽管朝臣们的奋起直言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郑贵妃等人的奸谋,但无奈光宗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糟糕了,十九日光宗降旨说自己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之后于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之交、二十六日以及二十九日,光宗三次召对重臣,其间已有托孤之语。
在这三次召对之后,便是李可灼进献红丸。但早在二十九日之前,李可灼就已有主动进奉之举。二十四日,首辅方从哲及阁员韩爌、刘一燝入阁办公,忽有鸿胪寺官员李可灼自称有“仙丹”,欲进献皇帝。面对这一贸然请求,无论是方从哲还是韩爌、刘一燝都不敢冒险,因而未允李可灼之请。当然他们不知道的是,李可灼未能通过阁部上达,竟自行往思善门进药,内监虽然也不敢自作主张擅行引入,但光宗知道有仙丹一事并在后来问起,大概就是在此时获悉的。
二十九日召对时,光宗忽然问起进药的鸿胪寺丞,并传见。李可灼到后为光宗诊脉,所言病源、治法均颇令光宗满意,于是光宗遂令李可灼进药。众人退出来后,群臣让李可灼与御医商量,但是否进药谁都拿不定主意。然而不久内中有乳妪出来,催促制药进奉,万般无奈,群臣只得再次与李可灼共进,令其现场调配。不一时丹药制毕,光宗用之,竟觉得颇为受用,连称李可灼“忠臣”。群臣遂再次退出宫外等候,少时内中传曰:“圣体用药后,煖润舒畅,思进饮膳。”众臣为之欢欣。李可灼及御医留侍,时当巳午(即九点到十三点)。比及申未(当在十五点前后),李可灼出言:“上恐药力歇,欲再进一丸,诸医言不宜,骤传趣益急,因再进讫。”辅臣询问药效,李可灼但说:“圣躬传安如前。”但是等到次日五鼓,大内紧急传召众臣,明光宗朱常洛于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卯时驾崩,享年三十九岁。结合五鼓、卯刻等时间点,光宗当死于凌晨五点前后。
若仅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红丸案”,则此案开始于泰昌元年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进献红丸而光宗服之,结束于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凌晨五点光宗驾崩,但无论是时人还是后代史家,俱将红丸案至少前溯至光宗登基时郑贵妃献女,甚至是万历时的国本之争,之后的结束则更无一定之规,其案追查、反复,延宕数十年之久,直至明亡,亦不见有定论。而此案也早就从单纯的探究光宗死因,变成了借为光宗查明死因、追究凶手之机相互攻讦、排除异己。此案自缘起时便渗透了宫闱之争,其间夹杂着正邪之争,之后又沦为党派之争的工具,其复杂纠葛,实在令人咋舌。
三、后续:以东林党为核心的朋党之争
(一)泰昌朝及天启朝初年之纠劾
1.东林党与方从哲之争
光宗驾崩之初,朝臣普遍认为其死与崔文升下泻药、李可灼上红丸两事不无关系,因此彻查光宗死因以及惩办崔文升、李可灼的奏疏一直不绝如缕。但仅仅要求处罚这二人的上疏占比并不多,朝臣更多的是将矛头指向了内阁首辅方从哲。因为光宗死后,方从哲为洗清自己的干系,竟模拟大行皇帝的口吻对有弑君嫌疑的李可灼加以赏赐,这种荒唐的举措令满朝震愕。此举遭劾后方从哲又“罚可灼俸一年”,却不处理之前的赏赐,顾此失彼、举动失宜,时臣对此大加嘲讽:
李可灼轻用其药,陷先帝于仓卒,中外人心共怀愤恨,以为诛之先加,必此人也。未几而赏行矣,臣愚不知此賞为何名也;及御史王安舜言之始议罚,臣愚又不知此罚为何名也。
尽管李可灼是否有弑君之实并无实证,然在传统司法语境下,“许世子不尝药犹曰弑君,况此亲下手之人乎!”对于针对君上的犯罪潜在着“有罪推定”的理念。而对于崔文升,方从哲则仅“拟令旨司礼察处”,但根据《大明律》,下药过误已经是十恶重罪中的“大不敬”罪。《大明律》明确规定:
六曰大不敬。谓盗大祀神御之物,乘舆服御物,盗及伪造御宝,合和御药误不依本方,及封题错误,若造御膳误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坚固。
可见根据帝制时代的司法惯例,崔文升、李可灼均是无法逃脱弑君罪责的。而方从哲如此处置,按照儒家之传统亦可谓“弑君”矣。《礼记》有云:
言此等之人,若见弑君弑父之人,无问尊卑,皆得杀之。谓理合得杀,若力所不能,亦不言也。故《春秋》崔杼弑庄公,而晏子不讨崔杼,而不责晏子。若力能讨而不讨,则责之。《春秋》董狐书赵盾云“子为正卿,亡不出竟,反不讨贼,书以弑君”是也。
因此方从哲身为首辅,有能力但却不严惩至少是有弑君嫌疑的崔文升、李可灼二人,为群臣所诟病理所当然。再加上方从哲本就是各方势力妥协下才得以借机登魁,原非雄才且为政平庸,故而围绕方从哲的攻讦抨击源源不断,某种意义上属于借纠察红丸一案之名行倒方之实。如九月初八日,东林党人惠世扬上疏,言辞犀利,径列方从哲有十罪、三可杀,历数其为政之种种失误,称其不堪膺首辅之重任。可见红丸案中方从哲为崔文升、李可灼脱罪只不过其罪之一,众臣之真实目的实为借此倒阁,对方从哲进行全面的清算与攻伐。
果然惠世扬此疏上后方从哲立有辞呈递上,熹宗不允。郑宗周再上劾章,方从哲再请辞官,仍不获准。之后弹劾方从哲的奏章仍不间断,方从哲亦屡屡求退,熹宗皆优容之。最后至当年十二月,方从哲辞呈业已六上,终于得以极高规格的优遇辞官。
2.东林党与郑贵妃之争
随着方从哲的去职,朝臣对其的弹劾亦稍见平息,但劾章却并未停止,因为对此案另一关键人物郑贵妃及郑氏一族的交攻一直未止。
据杨涟自述,其于八月二十一日有疏上,其文激烈而恳切,一要严惩崔文升,无论其用药是否过误;二则怀疑崔文升此举与郑贵妃不无干系,甚至直言“第妇人女子,愚不知礼,妄不安分,臣虑假借之端,尚在希觊之念不止”,之后明面上评价郑养性上揭请收回封其姑郑贵妃为后,实则刺讽郑贵妃、要其安分守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杨涟认为“前日外传流言曰:兴居之无节,侍御之蛊惑,必文升借口以盖其误药之奸,与文升之党四出煽播以掩外廷攻摘文升之口耳。”虽然隐含有为尊者讳之意,但同时也旗帜鲜明地指出光宗病势沉重与崔文升下错药不无关系,而且这极有可能不是崔文升一人之举,而是存在着一伙欲有所图的政治势力在暗中指使。如此一来,杨涟已经非常鲜明地将矛头对准了宫闱之争,也可以说这封奏疏彻底地将宫闱之争与外朝之争纠缠了起来,继续延续了前朝国事家事混淆不清的政治格局。
逮及光宗崩殂,对于郑贵妃等势力的怀疑与抨击亦随之而起。郑宗周、惠世扬、焦源溥等东林党人及正直人士纷纷上疏,声讨郑贵妃。可以说虽然郑贵妃因其地位尊崇且系内宫中人,始终没有受到多严厉的惩斥,但对于她的怀疑则一直没有停息,由内闱争宠引发的外朝党争也一直未曾间断。虽然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架构中,帝王之家事亦国事,但这种由内而外衍生的政治斗争,始终围绕皇权展开,最终也还是以皇权为落脚点和归宿,这在客观上也揭示了明季党争与当代政党之一处不同。
(二)天启朝《光宗实录》《三朝要典》之修订
1.《光宗实录》引发的党争
天启元年六月九日,神宗、光宗两朝实录开馆撰修,围绕包括红丸案在内的三案如何定性再掀波澜,本已辞官的方从哲也再度被拉回争论漩涡的中心。东林党人孙慎行上疏,直言方从哲“速剑自裁以谢皇考,义之上也”,并云“臣以为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辞弑之名,益难免弑之实……若从哲之弑逆一日不讨,则朝廷之纲纪一日不明”。其疏可谓杀气腾腾,切齿愤恨溢于字里行间。一时间附合者甚众。
面对如此气势汹汹的弹劾,方从哲不得不再次上疏辨白,黄克缵亦以亲身见闻为之开脱。但显然朝廷之公议已一边倒地抨击方从哲,少部分辩护之词显得苍白无力,如之后江日彩便指出:“即谓从哲有心而故投不效之药,亦未必然……从哲为元辅,何故不置可灼于法,重则辟,轻则遣,只令回籍调理,而且赏之,其何以谢天下!”面对攻讦,黄克缵、方从哲亦不甘示弱,再复上疏,反唇相讥,争论之势极度激烈,争论内容更是从原先的定罪论责,到了现在的人身攻击,几乎到了白热化的境地。之后即使再行调查,《光宗实录》修毕,亦无法制止争辩,由于还涉及方从哲与郑氏相勾连,朝野之争越发复杂而难解。
由此亦可见,天启初年针对红丸案等三案的争论已不复倒阁等目的,门户之争、党派私见愈发严重。有论者认为,郑贵妃未被加以重责,反倒揪着方从哲不放,实在夹杂着过多的朋党意气之争,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算是“正邪不两立”,但是对于下野政敌的穷追猛打、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党争模式,亦构成了此类党争无从与现代政党相比伉的一个原因。
2.《三朝要典》的编撰与翻案
然而有关红丸案的争执并没有到此为止。随着魏忠贤的得势,原本为东林人士所贬斥者,纷纷转投魏忠贤的门下,一时间形成了与东林党针锋相对的阉党。杨涟、左光斗、王之寀、孙慎行等一众东林党人士被大加贬斥乃至杀戮,他们的观点、立场显然无法被阉党所容忍,因此对于红丸等三案,自然不能再遵从东林党人的认知,承认其中存在着人为的谋杀因素,而是应当秉持光宗病逝的基本立场,并以此为基调转过头来对东林党进行清洗与抨击。也就是说,“红丸案”到了天启朝,已经成为纯粹的党争之工具,其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已无关紧要。
魏忠贤掌权后,兴“汪文言狱”构陷东林党人,对此,杨涟上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时当天启四年六月。一时间弹劾奏章蜂起而至,虽经王体乾以及客氏周旋,众人弹劾未能伤及魏忠贤分毫,但魏忠贤却因此而深恨杨涟。之后魏忠贤逐步罢黜东林党人,慢慢扩张自身势力,迨及天启五年三月,将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和顾大章六人逮捕并虐杀之,此为大名鼎鼎的乙丑诏狱。魏忠贤既要彻底除灭东林党人,则亦需有正当之名义。于是次月,给事中霍维华上疏,要求重修实录,并汇总相关奏章撰修成书进行翻案。由此亦可明白,阉党之所以要为三案翻案,无非是为打击政敌寻求正当化基础,以免“师出无名”。
在此建议下,熹宗允许重修实录、更翻三案。天启六年五月,一部《三朝要典》横空出世,该作为阉党顾秉谦等人所撰,搜罗与三案相关的诸臣奏章,以时排列,并在很多奏疏之后以“史臣曰”的形式,妄自评断,尤其对东林人士的奏章多加驳斥。在书中,针对红丸案,阉党坚称“光宗病逝”,进而猛烈批驳诸臣对于光宗死因的怀疑以及要求惩办崔文升、李可灼以及方从哲、郑贵妃的奏议,对诸臣多加以“深文污蔑”一类的诬名,将其置于无事生非、令先帝不得安宁的被动地位,自己占据道义的制高点。此外《三朝要典》还在卷首列熹宗御制之序,熹宗在其中对群臣冠以“奸贼”“奸凶”之名,而在对于三案的界定中,也无一不把东林人士作为案件之罪魁,如在红丸案中,便将孙慎行归为罪魁。明见此为阉党用以打击政敌之工具矣。
至此,对于红丸案的争论由于阉党的强大压力暂时告一段落。但阉党对于红丸案的定性去实甚远,注定还会再生争议。
(三)崇祯朝《三朝要典》之毁弃
果不其然,随着朱由检登基称帝,对于阉党也随之展开了雷厉风行的大清洗,在这过程中,势必会涉及对于《三朝要典》的存废之争。对此有人主张保存、有人主张毁弃,不同观点的持有者事实上也反映着东林党与阉党争竞的持续。主张毁弃的倪元璐一语中的地点出了三案实已成为党争工具的现状,《三朝要典》之留无益。崇祯皇帝遂从其议,焚毁《三朝要典》的刻板,重新平反了三案,作为清除阉党的一小步,这就算是红丸案最后一次在党争中被借用了。至此,关于红丸案的党争终于基本落下了帷幕。
四、余论:明季朋党非現代政党
“红丸案”作为明末三大案之第二案,其既受到前案“梃击案”的影响,同时也直接为后案“移宫案”的发生埋下了伏笔。对红丸案作一回顾便可看到,围绕着红丸案,朝臣从开始的想要查明真相、处置“凶手”,逐渐演变成借助调查此案冀图排揎政敌、打击异己,以至于到后来光宗死去数年,仍有《三朝要典》编成,对红丸案等宫闱琐事数加评议,针对红丸案的争斗也移化为对《三朝要典》的去留之争。随着《三朝要典》在崇祯朝被毁弃,围绕红丸案的喧嚣之声也少得平息,但这番历时弥久的斗争却清晰地凸显出如下两点:
首先,明季党争之缘起,在于皇权的恣意无约束,各党之主张也要臣服于“维护皇权利益”这一名目的庇护,才会具有正当性。易言之,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守正之士是“为了守卫君主权”,而与之对峙的阉党等“邪党”显然攫取了不属于他们应有的君主权,因此这种党争具有鲜明的“皇权主义”色彩。
其次,明季党争手段之残酷令人不寒而栗,无论是东林党还是阉党,都不乏致对方于死地的斗争取向,只不过阉党较之东林更为野蛮与彻底。这种血淋淋的争竞方式,无论如何都无法与现代社会相兼容。
因此,从这两点我们就可以明确,明季的“党”,绝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