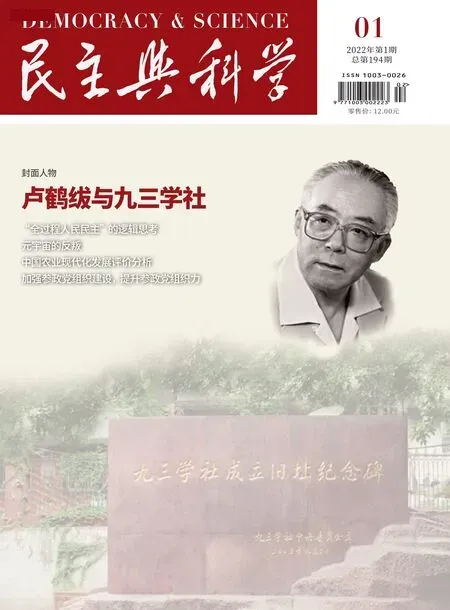宋阿云之狱
袁易鑫
纵观宋阿云之狱,不过区区乡野小案,却引得北宋一干重臣争论不休、皇帝再三下诏,这其中固然有党争的影响,但如果本案争论的焦点仅仅是关乎党争,司马光和王安石两派的论证也不会如此的鞭辟入里、各彰其疑,即使在今天看来,其中很多论证也颇具光彩、值得再三玩味。
一、区区乡野小案,震动北宋政坛
1.少女犯案,知州介入,风波渐起
宋熙宁元年(1068年),山东登州的一个夜晚,韦大熟睡时被人袭击。凶手用刀连砍十几下,韦大用手挡着,最终被砍断了一根手指,而凶手也夺门而逃。当地县尉经过调查,怀疑是韦大刚定亲的未婚妻阿云所为。于是县尉将阿云拿住,吓唬阿云说要对她用刑,阿云便承认凶手就是自己。阿云是个苦命的少女,案发时只有13岁左右。她自小没有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却在为母亲服丧期间被叔叔许给了韦大。而韦大已经30多岁,外貌丑陋、家徒四壁。阿云不满婚事,就犯下此案。案情清楚,县衙定罪,阿云触犯“十恶”重罪之一的“妻杀夫”罪名,被判斩刑。该案呈送到登州,知州许遵出场,改变了阿云以及整个案件的命运。
据《宋史·许遵传》记载,许遵是进士出身,又中明法科。许遵最初在大理寺当司法官,法律功底深厚,还当过多地的知州,当时政坛风传许遵将要升官到大理寺当差。据《宋史》及沈家本《寄簃文存》记载,许遵想要借推翻此案为自己的高升造势,所以积极插手此案。许遵认为阿云的行为不属于“妻杀夫”,而是“凡人相犯”,即属于发生在普通人之间的罪行。根据《宋刑统》规定,定婚夫妻之间,只有不能违约改嫁的限制,如果发生其他纠纷,就按照普通人纠纷处理。同时,许遵指出,阿云纳采发生在为母服丧期间,属于无效婚姻,更应以“凡人相犯”处理。
对许遵的以上判断,大理寺、审刑院是认可的。然而,对于许遵认定阿云的行为属于“按问欲举自首”,即拥有自首情节的这一判断,大理寺、审刑院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阿云的行为应以“谋杀已伤”罪名处理,应判处阿云绞刑,而非许遵主张的流刑。许遵对该判决不满,继续将案件上诉到刑部,但刑部支持大理寺和审刑院,甚至批评许遵过于狂妄。宋神宗也支持大理寺、审刑院,但他并未判处阿云绞刑。
根据《宋史》所记“诏以赎论”,结合司马光《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而自首状》中的“朝廷贷命编管,已是宽恩”,以及司马光《体要疏》中的“云获贷死,已是宽恩”,我们可以合理推断——阿云触犯重罪,本不能适用赎刑;但宋神宗下诏允许其破格适用,阿云得以免死。
2.两制两府,接连登场,波诡云谲
阿云之狱至此似乎走向结局,许遵正常的上诉渠道基本上已穷尽。但风云变幻,许遵在此时升官,判大理寺。他想借助职务来推翻原判,但御史台弹劾他沽名钓誉、徇私枉法。于是,许遵向宋神宗陈述来龙去脉。许遵认为刑部的审判结果阻碍了犯人的自首之路,向神宗请求将此案发给“两制”讨论。
两制包括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从唐朝开始,中书省负责替皇帝制定政策,其具体执笔之人就是中书舍人。从唐高宗开始,朝廷延揽了一批饱学之士,伺候皇帝草拟诏书、出谋劃策。唐朝中期正式成立了翰林院来安置这些学士,即翰林学士。翰林学士中加“知制诰”头衔的人,掌握着起草诏书、制定政策的巨大实权,他们往往是皇帝的心腹。北宋继承唐朝的制度,两制官员辅助皇帝决策。
另,士大夫的集体讨论是北宋解决司法难题的常用方法,其讨论的结果往往成为北宋立法的重要来源。据《宋史·刑法志》记载:“天下疑狱,谳有不能决,则下两制与大臣。若台谏杂议,视其事之大小、无常法,而有司建请论驳者,亦时有焉。”
宋神宗采纳许遵的请求,把阿云案交付两制讨论,即交给皇帝的政策咨询和制定班子讨论。由此,一件原本普通的乡野小案被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而此案之后便如同脱缰野马一般不受控制。在两制讨论阶段,核心人物是王安石和司马光。王安石赞同许遵的意见,认为阿云成立自首,应当从轻发落;司马光赞同刑部的意见,认为阿云不成立自首,应以“谋杀已伤”判处绞刑。司马光和王安石争论不休,而宋神宗此时是更看重王安石的,于是便支持了王安石的意见,于七月癸酉下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下诏后,群臣议论纷纷,御史台请求再选官员评议此案。宋神宗顺水推舟再次下诏,由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再行讨论阿云案。吕公著、韩维支持王安石,主张对阿云从轻处罚,宋神宗便也认同了王安石的意见。
案件看似告一段落,审刑院、大理寺却弹劾吕公著“所议为不当”。宋神宗只得就阿云案第三次下令,让审刑院、大理寺和王安石等人集议,但意见仍然不能统一。宋神宗不希望士大夫集团过于分裂,在阿云案发生的第二年,即熙宁二年二月下诏:“自今谋杀人已死自首,及按问欲举,并奏取敕裁。”此诏书折中双方意见,不判断谁对谁错,只确定了今后遇到类似案件由皇帝决断。但刑部官员以诏书内容不完备为理由,将诏书退还中书省,拒不执行。此时已升任参知政事的王安石也向宋神宗进言,请求撤回诏书。宋神宗认可王安石的意见,收回庚子诏书,于同一个月的甲寅下诏:“自今谋杀人自首及按欲举,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其谋杀人已死,为从者虽当首减,依嘉祐敕,凶恶之人、情理巨蠹及误杀人伤与不伤奏裁。收还庚子诏书。”宋神宗重申了熙宁元年七月的癸酉诏书,但刑部等支持司马光意见的官员们一直反对,要求将案件交到“两府”,即中书和枢密院,来进行讨论。宋神宗虽然不愿意,但秉持广开言路、但听无妨的态度,终将案件交给两府讨论。
但中书和枢密院也不能统一意见,眼看案件久拖不决,宋神宗深感皇权受碍,虽多次下诏却也不能贯彻自己的意志。此时阿云案自身的是非曲直不再重要,统一朝廷、疏通皇权才是要务。于是在熙宁二年八月,宋神宗下诏:“谋杀人自首及按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甲寅敕施行。”同时,之前很多对皇帝诏书持反对意见的官员也遭到贬斥。宋神宗一锤定音,给争吵一年多的阿云案画上句号。阿云案最终的争论结果是以凡人谋杀伤人罪论,当处绞刑,因成立按问欲举自首,依熙宁元年七月癸酉诏书规定,减二等处罚,阿云免于死刑。
对此结果,司马光等人上书争辩,司马光著名的《体要疏》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但宋神宗不理。一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司马光再度为相,这桩公案历经十七个年头才又被扭转。
二、论争核心,聚焦法理
明人丘濬在《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八指出:“阿云之狱……推原所自,皆是争律敕之文。”律在本案语境下主要指《宋刑统》,以司马光和王安石为首的两派官员对于《宋刑统》中关于自首的条文竟然进行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分别支持阿云不成立自首、阿云成立自首。敕在本案语境下主要指“嘉祐编敕”和熙宁元年七月的“癸酉诏书”,前者规定“若已经诘问,隐拒本罪,不在首减之例”,依此规定阿云成立自首的条件有待商榷;而后者则规定阿云的这种情形是可以成立自首,得以从轻处罚的。
应当注意的是,“癸酉诏书”应当是在阿云之狱发生之后出台的。据《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一记载,司马光在《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而自首状》中对许遵主张从轻处理阿云的论据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梳理,包括许遵所引用的苏州的案例、编敕、律疏问答等都列得清清楚楚。如果“癸酉诏书”的发布时间在阿云案件发生之前,许遵不太可能不引用这么重量级的条文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司马光也不太可能不对对方这么重要的论据进行反驳。因此,虽然不能肯定“癸酉诏书”的发布时间一定是在两制讨论阶段,但可以肯定的是,“癸酉诏书”的发布时间更有可能是在阿云案件发生之后。即“癸酉诏书”与其说是朝廷重臣争论的对象,毋宁说是朝堂争论的阶段性成果。
丘濬接着写道:“推原所自,皆是争律敕之文。谋与杀为一事为二事,有所因无所因而已。”即本案论争的核心是“律敕之文”,是关于“谋杀”是否可分、有无所因之罪的法理之争。且关于这两点的關键论证,在“癸酉诏书”出台之前就已经在朝堂中得以展现,之后的争论大多是重复和引申前述观点。另,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更是在“癸酉诏书”出台之后,本案的核心论争受到党争因素影响较小。因此,下文将从法理之争的视角来分析朝廷重臣的争论。
三、宋人所言,各彰其理
关于阿云之狱的法理之争,司马光和王安石可谓是主导整场论争的走向。二者分歧的出发点在于“谋”和“杀”是可分还是不可分,而这个出发点的不同直接影响了二者是否认可阿云成立自首。
1.司马光一派的看法
司马光紧扣条文,认为谋杀是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行为。因此谋杀没有所因之罪,阿云不能适用自首条文。据《温国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八《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状》所载,司马光进行具体论证的原文为:“臣窃以为凡议法者,当先原立法之意,然后可以断狱。窃详律文,其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司马光认为法律解释应贴合立法原意,即谋杀人未遂且致人伤害者不属于自首条文的适用范围,其论证如下:
“注云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所谓因犯杀伤者,言因犯他罪,本无杀伤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杀伤,除为盗之外,如劫囚略卖人之类皆是也。”北宋认为对于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可以减免他的所因之罪,依照“故杀条”进行处罚。司马光认为,律条中的“因犯杀伤者”指的仅仅是拥有所因罪名的罪犯,即本没有杀伤人的主观意图,而只是因为犯了其他罪名,例如入户盗窃等,在犯案过程中逼不得已对人进行伤害,致使有杀伤人的结果。如以上这般拥有所因之罪的罪犯(除非所因之罪是古代处罚很重的“盗”罪之外),如果自首,则可以被免除所因之罪的处罚,而只对杀伤的后果依照“故杀条”来进行处罚。总结而言,只有拥有所因之罪的罪犯才能够适用自首减轻处罚,阿云没有所因之罪,又怎能适用自首条文呢?
“律意盖以于人损伤既不得首,恐有别因余罪而杀伤人者,有司执文并其余罪亦不许首,故特加申明云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司马光认为该自首条文是出于减少官府对有所因之罪的罪犯笼统断罪、不加区分情节轻重而皆不认可自首的情况,而特加声明的,并不是于当前的法律体系之外又另立了一个罪名。另,司马光对“谋”和“故”的定义进行了严格的解释:“然杀伤之中,自有两等,轻重不同。其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者,则谓之谋;直情径行、略无顾虑、公然杀害者,则谓之故。”即“谋”指蓄意的、经过策划的、乘人不备的谋杀,而“故”似乎可以参考激情杀人来理解。“谋者尤重,故者差轻,今此人因犯他罪致杀伤人他罪虽得首原,杀伤不在首例。若从谋杀则太重,若从斗杀则太轻,故酌中令从故杀伤法也。”儒家论罪讲究“原心论迹”,即对犯罪的主观恶性加以重点考虑。司马光认为,谋杀的主观恶性要远远大于故杀,所以这种有预谋有计划的杀人行为不可允许自首。对于谋杀未遂,如果用“谋杀条”,则处罚过重;如果用“斗杀条”,则处罚过轻,所以折中采用“故杀伤法”来处理。“其直犯杀伤更无他罪者,惟未伤则可首,伹係已伤,皆不可首也。”即,对于没有所因之罪的谋杀,只有在受害人未受伤的情况下才能允许自首;如果已经致使受害人受伤,就不能适用自首条文。因此阿云不能适用自首条文。
司马光接着反驳了许遵将“谋”与“杀”分为二事的观点:如果仅仅是设想而不付诸行动的“谋”,即仅仅具有主观恶性而未有客观行为,则很难被认定为有罪,“彼平居谋虑,不为杀人,当有何罪?”司马光认为,许遵将“谋杀”二分,不过是苛察缴绕之论。
以上是就条文本身的理解层面来进行论证,此外,就阿云自身的行为而言,司马光认为其也很难满足自首的条件。据《温国文正公年谱》卷四所载原文:“况阿云嫌夫丑陋,亲执腰刀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十刀,断其一指。初不陈首,直至官司执录,将行拷打势不获已,方肯招陈,情理如此,有何可悯?”即阿云最初是没有自首的,一直到被官府拿获,即将被用刑时才招供,司马光认为此种行为很难称其为自首。
因此,司马光认为,阿云能被允许纳钱赎罪已经是天大的恩典,许遵竟然还得寸进尺,想将谋杀人未遂已伤也可以使用自首的个人观点上升到国家立法的层面,加以推广适用,许遵的做法可谓是“开奸凶之路、长贼杀之源”。
2.王安石一派的看法
王安石似乎也是紧扣条文来解释的。王安石认为“谋杀”是可以分割的行为,“谋”为“杀”的所因之罪,因此阿云的“谋”罪可适用自首条文而得以减免,其真正需要受到处罚的仅仅是“已伤”这一行为了。据《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刑考九》所记载,王安石进行具体论证的原文为:“窃以为律‘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谋杀与已伤已杀,自为三等刑名。因有谋杀徒三年之犯,然后有已伤、已杀、绞斩之刑名,岂得称别无所因之罪?”即王安石以《宋刑统》的规定为依据,认为“谋杀人”“已伤”“已杀”分别对应预谋杀人、杀人未遂、杀人完成三项独立的犯罪,进而构成“谋”“伤”“杀”这三条独立的罪名。既然分成三条罪名,那么“谋”当然也可以成为“所因之罪”,而不是仅仅是主观犯意的范畴了。阿云犯了“谋”和“伤”,“谋”是“伤”的所因之罪,自首可以减免所因之罪的处罚,真正需要接受惩罚的是“伤”这一项罪名。“今法寺、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谋杀,与法不得首免之已伤,合为一罪。其失律意明甚。臣以为亡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合从谋杀减二等论。”即王安石认为,刑部将法律允许自首的谋杀(因有“谋”作为所因之罪)和法律不允许的已伤(因“伤”没有所因之罪)混为一谈,是对法律条文的错误理解。
王安石的法律分析未免有些牵强,他似乎是从法条规定中刑罚种类的不同来倒推出本条中成立了不同的、独立的罪名。也许王安石也意识到该论证的说服力需要补强,他接下来又从举重明轻、法律政策的角度来继续论证自己的观点。“臣以为律疏假设条例,其于出罪则当举重以包轻。‘因盗伤人者,斩’,尙得免所因之罪。‘谋杀伤人者,绞’,绞轻于斩,则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即王安石认为,“因盗伤人”的罪名要重于“谋杀伤人”的罪名,连前者都允许自首,后者也可推知应该允许自首。但应当注意的是,举重明轻适用于“出罪”,即用于判断罪与非罪的界限,这一规则是否可以推广至自首、量刑的范围,宋代法律似乎没有明确的规定。且举重明轻多适用于“法无正条”的情况,而对于法律已经有明文规定的“盗”“谋杀已伤”,是否可以适用该原则,也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
再者,王安石从法律稳定性的角度加以论证:“然议者或谓,谋杀已伤、情理有甚重者,若开自首,则或启奸。臣以为有司议罪惟当守法,情理轻重则敕许奏裁。若有司辄得舍法以论罪,则法乱于下,人无所措手足矣。”从这一点看出,王安石认为有司的职责仅限于适用法律,至于有争议之处应由皇帝定夺;如果任由有司超越立法原意、舍法而论罪,则百姓对法律的稳定性预期会被打破,致使“人无所措手足”。
四、一桩公案,跨越时空,回味悠长
阿云之狱这一桩公案,从法律事件开始,似乎以皇帝的一锤定音结束,但对于这桩乡野小案的讨论其实从未停止,甚至跨越了时空。
关于阿云之狱究竟是“凡人相犯”还是“妻杀夫”,宋人少有将此作为整场争论的中心,明清学者却对此大书特书,视为重要着力点。明人丘濬在《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八中指出:“然则阿云之狱,何以处之?曰:司马氏固云,‘分争辨讼,非礼不决,臣请决之以礼。’夫夫妇,三纲之一、天伦之大者。阿云既嫁与韦,则韦乃阿云之天也。天可背乎?使韦有恶逆之罪,尚在所容隐。今徒以其貌之丑陋之故,而欲谋杀之,其得罪于天而悖于礼也甚矣。且妻之于夫,存其将之之心固不可,况又有伤之之迹乎?诸人之论,未有及此者。司马氏始是,刑部其后有弃常典、悖三纲之説,然隐而未彰也。臣故推衍其义,以断斯狱。”晚清沈家本的观点也与丘濬类似,主张以“礼”来处理此案,对阿云谋杀未婚夫的行为加以严厉处罚,以维护纲常伦理。
关于阿云是否成立自首,后世对王安石的观点似乎责难颇多。晚清沈家本在《寄簃文存》卷四《考释学断·宋阿云之狱》 中指出:“寻绎律意,罪未发是未告官司也,案问欲举是官吏方兴此议而罪人未拘执到官也,故得原其悔过之心以自首原减。若阿云之事,吏方求盗勿得,是已告官司;疑云,执而诘之乃吐实,是官吏已举。罪人已到官,未有悔过情形,按律本不成首。许遵删去欲举二字,谓被问即为按问,安石又从而扬其波,将天下无不可原减之狱,鲁莽减裂噫甚矣。”沈家本与司马光的论述有相似之处,沈家本认为阿云之狱是已告官司且官吏已举,阿云本无悔过之心,不应当认可其成立自首。王安石支持许遵,并将对自首的放宽适用上升到国家决策的层面,会致使犯罪猖獗而泛滥,其害实重。
纵观宋阿云之狱,不过区区乡野小案,却引得北宋一干重臣争论不休、皇帝再三下诏,这其中固然有党争的影响,但如果本案争论的焦点仅仅是关乎党争,司马光和王安石两派的论证也不会如此的鞭辟入里、各彰其疑,即使在今天看来,其中很多论证也颇具光彩、值得再三玩味。在宋神宗依王安石的主张,逐步放宽自首条件后,流放犯人的沙门岛人满为患,财政开支浩大,且因按问自首活命而逃亡的恶徒增多,犯罪呈现猖獗之势。宋神宗对此不满,责问王安石,王安石答曰:“案问欲举法宽,乃所以疑坏贼党,虽宽一贼,必得数贼就法。恐须如此,乃无配沙门岛者。”此语其中深意,恐怕并非一句“鲁莽减裂”可概言。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責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