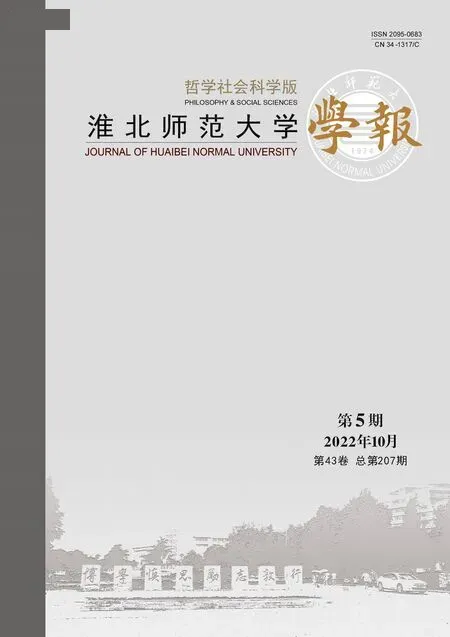华兹生与倪豪士《史记》英语译介之比较
魏 泓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积淀出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它们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史记》位列二十四史之首,具有极高的历史与文学价值。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体大思精的《史记》早已走向世界,在多国被多次翻译,“《史记》吸引了中国、日本与西方许多杰出学者的关注,从1828年开始,《史记》的许多篇章被翻译成欧洲语言”[1]138。“《史记》有过多次翻译,其中四次最重要的翻译项目由沙畹、华兹生、越特金和倪豪士团队的翻译”。[2]6这四次最重要的《史记》翻译就包括两次最大的《史记》英译,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翻译与20 世纪80 年代末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主导的《史记》全译工程,倪译翻译目前还在进行中。这两次翻译都是产生在美国,其翻译与接受状况可谓大不相同。“比较是不可避免的,但却大有裨益”[3]597。通过文献检索可见,目前尚无对此两大英译的专门而综合的比较研究,而对两者的翻译与接受及其产生原因的比较大有裨益,故本研究力求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描写、比较、分析、归纳,以资参考与借鉴。
一、华兹生与倪豪士的《史记》英译
华兹生的《史记》翻译与倪豪士的《史记》翻译在选材、目标、策略等方面都大为不同。
(一)华译《史记》
华兹生的《史记》诞生于20 世纪50 年代。华译面向一般读者,侧重于《史记》的文学性价值。1956年,华兹生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赞助基金,开始着手对《史记》的翻译。华兹生对《史记》中文学性强的篇章感兴趣,他的翻译目的是为了西方的一般读者,即非专家读者的翻译。他明确表示:“我们在介绍中已经清楚地申明了我们的目的与目标……是为了一般大众读者与非中国历史专业的学生”[4]114。他说:“我对《史记》文本的兴趣主要在于文学方面,我认为我已经翻译了非常有文学趣味与影响的大部分历史章节。”[5]204华兹生是个人翻译,采用倾向于读者接受的归化翻译。他1961 年的《史记》译本选择了文学性强的66 篇进行翻译(其中57 篇是全译,9 篇是节译)。他在翻译中打乱了原文顺序,把所译篇章按照汉朝缘起、发展的顺序进行重组,即把所译内容组建成有头有尾的叙事故事,以便适应西方读者的审美叙事习惯。他关注译作的文学吸引力而很少采用脚注的形式,多是在译文中进行解释性增译,避免使用汉语的专业性术语与称呼。华兹生为了西方一般读者能阅读顺畅,他牺牲了严谨的忠实性。他的译文优美流畅。
(二)倪译《史记》
倪译《史记》是团队共同合作的结果,是一种典型的学术性翻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倪豪士教授领衔翻译《史记》。倪教授是《史记》翻译工程的译者、编者、组织者、协调者,其团队多国的学者与专家。倪译《史记》(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第一卷诞生于1994年,后来陆续又有七卷译本问世。倪译的内容顺序和原作内容的顺序是一致的,译本整体结构为:致谢、介绍、使用说明、度量衡对照表、缩写表、译文的页下的详尽注释、译文后面附有译者的评注、译本的后面附有全书的参考文献目录、关于《史记》及司马迁的研究以及相关作品与索引等内容。倪译详尽精当,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尽可能保留原文的语言与文化特质。倪译团队的目标是为了西方的专家、学者、专业学生,努力忠实再现出《史记》的原文内容与风格。倪译团队运作过程是:单个参与译者先提交个人翻译,这些翻译被分派给其他参与者提书面建议,最后再提交给小组讨论、直到达成一致意见,“多么繁重的过程,多么严峻的挑战。”[6]139倪译《史记》得到多方赞助,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院研究委员会、太平洋文化基金会、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等。倪译《史记》注重精确性与完善性,参考了法语、日语、德语等不同语言的《史记》译本,咨询了许多国家的专家的意见。倪译侧重于《史记》的学术性价值,倾向于充分再现原作的异化翻译。
二、华兹生与倪豪士的《史记》英译的接受
作为有着不同翻译目的与翻译性质的两个译本,倪译和华译的接受迥然有异。华译在正面与负面接受中孕育了倪译的诞生,倪译在对比评价中更是凸显出不同的接受效果。
(一)华译本
华译《史记》整体上接受良好,尤其是在文学性接受上大受称赞。华译接受广泛,在美国起到重要的普及性与引导性作用。不过,华译因缺乏学术性而日益受到诟病。华译的接受呈现出肯定接受与否定接受两个方面。
华译《史记》被作为世界文学经典译本而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性著作选集:中国系列丛书。华译多次出版,第一版于1961 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分为上、下两卷出版发行,此版本于1962 年与1968 年两次再版。他的第二个版本《〈史记〉选篇》译有《史记》19 篇内容,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1969 年出版。1993 年,华兹生修订1961 年版2 卷本的《史记》译作而再次出版,同年又选译了《史记》秦朝部分13篇内容而出版《史记·秦朝》译本,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华译影响深远,基于OCLC FirstSearch 数据库检索可见,世界各地拥有华译《史记》(1961)藏书的图书馆多达八百多所。华译本诞生后,可谓万众瞩目,学者们纷纷撰写书评,捷克汉学家鲍格洛(Timoteus Pokora)一言概之:“华译《史记》有相当多的书评,其中大多数都是好评。”[7]295华译本文学性强,可谓文学杰作。“华兹生通过自己的分析与雄辩的文风把《史记》的文学方面成功地介绍给了西方读者。”[8]9华译本接受广泛,影响弥深,带动了《史记》在美国的阅读与研究。华译本可读性强,“华译读起来流畅愉悦。”[9]200华译本文学效果突出,易于吸引读者阅读,因为“更多的公众也许对《史记》的文学而不是历史方面更感兴趣”[6]138。华译不够严谨,注释极少,但华译读起来生动流畅、朗朗上口。华译广受认可与称赞,在美国起到重要的引导性与普及性的作用。1961年华译《史记》的问世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对《史记》的关注。后来的译者倪豪士教授曾总结道:许多后来的美国学生就是通过华兹生的翻译而开始接触《史记》文本的,他也不例外。[8]9华译诞生之后,美国的《史记》研究论作增长快速。华译本催生了美国全方位多角度的《史记》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史学、哲学、文学、叙事学方面,如著作有克尔曼(Frank A.Kierman Jr.) 的《从四种战国后期的传记看司马迁的撰史态度》(1962)等,文章有何四维(A.F.P.Hulsewé)的《〈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的真伪问题》(1975)、艾伦(Joseph R.Allen)的《〈史记〉叙事结构初探》(1981)、杜润德(Stephen W.Durrant)的《处于传统交叉点上的自我:司马迁的自传体著作》(1986)等。另外,美国学界对中国文学、历史等方面研究的著作或选集里都会选用华译《史记》的内容或在参考文献里列出华译《史记》书目。
华译本在西方颇受好评,但另一方面,因它过多关注可读性而缺乏精确性而受到学者与专家的批评。美国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Mote)认为:华译《史记》被当作一部关于中国战争与和平的小说对待,为了读者而削减节略,以一种让读者最感兴趣、最易于阅读的方式而被翻译出来,而译者不应去除诸多意思而呈现可读性的却具有误导性的翻译。[9]200美国汉学家德效骞(Homer H.Dubs)认为:对于专家与学者而言,华译的非学术性翻译难以起到相应的作用。虽然华译被阅读与引用,但无论学者还是专家都不能获益良多;许多篇章缺乏精确性;上千页的英译本,没有学术注释,学者使用将非常有限。[10]201
尽管华译《史记》存在着弱点与缺陷,但“不管怎样,这个领域的学者无疑会从译本中受益匪浅”[11]336。
(二)倪译本
倪译《史记》是在学者们的学术期待中诞生的,其定位就是为了专家学者而译,极尽忠实与精确。倪译在与华译对比中,其学术性效果更为突出。
1.学术接受期待中的倪译
倪译是在西方学者的阅读期待中诞生。汉学家鲍格洛早在对华译表示欢迎的同时就提出了学术接受期待:“但,最需要的是新的《史记》全译本,这个全译本由最好的译者所组成的博学团体按照最高的标准所译成”[12]157,同时还提出了国际性合作翻译模式,认为:国际性的合作更为理想、更有希望。三十多年后,倪译开始努力完成这一期待。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对倪译本高度赞赏:尽管有批评与错误,倪译是一项杰出的汉学成就,是集中于一所美国大学的国际性合作团体的优秀产品。[6]142
2.与华译对比中的倪译
倪译《史记》初卷于1994 年问世后,美国学界纷纷撰写书评,且对倪译的评论往往是在与华译相提并论中进行的。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两次《史记》翻译,其相互间的对比评价不可避免,而相互比较则使得倪译不同于华译的特征更为凸显。
倪译是注重精确度的学术翻译,影响深广。Barbara Meisterernst曾对倪译与华译对比评论道:华兹生的翻译不包括许多学术注释,因为他翻译目的是为了更广泛的大众读者(a more general public);倪译团队翻译基于广泛的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丰富注释。[2]6卜德用实例进行比较:华兹生的翻译为了让译本更容易读懂,减少了学术用语、简化中国人名与称呼、避免文本不确定性、也没有插入话语解释原文隐含的不明确的内容以获得翻译中的明确性;例如,在翻译《史记·项羽本纪》中,倪译用了289个注释,而华译只用了17个注释。[6]138
倪译也注重《史记》的文学价值,不过,华译的文学效果更胜一筹,无可超越。华译散文式翻译可读性很强,反映出原文本的艺术风格,而倪豪士等散文风格的翻译因译者不同而变化很大,整体风格上不如华译优雅。[13]462-463
美国汉学家侯格睿(Grant Hardy)对华译与倪译进行综合评价道:“华兹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本质上是小说形式的译文,我对华译仍旧喜爱而欣赏;但是我认为倪译将更值得仔细反复阅读……”[14]151
倪豪士教授曾在笔者对他的访谈中说:“一般而言,西方学者总是产生两种翻译,一种是为了普通读者的翻译,注释很少而非常流畅,而另一种是为了学者的翻译,这种翻译对文本与上下文都给予广泛而详尽的注释”[15]86。华兹生的《史记》译本是优秀的流行版本,而倪译目标是提供一种学术性译本,因而主要被西方的学者、专家与学生所阅读。[15]85
3.倪译的整体接受情况
倪译本迄今已连续出版《史记》英译本8 卷(Vol.1,2,5.1,7,8,9,10,11),都由知名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倪译《史记》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接受度与影响力是比较可观的。从OCLC 数据库检索来看,世界各地拥有倪译《史记》(Vol.1)藏书的图书馆多达四百多所。倪译《史记》在世界图书馆藏书量没有华译多,但拥有倪译《史记》(Vol.9)电子资源的图书馆多达一千二百多所。倪译《史记》的接受度日益增强,这是多元化时代进程与世界文明发展的选择结果。
倪译是西方最富有学术价值的《史记》英译本,它严谨精确、文献厚重。倪译进行了歧义释义的考证,并提供了中外一些学者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倪译以忠实而确切的学术性翻译而受到好评与关注。张磊夫对倪译评价道:倪译将使更多英语读者感知《史记》的学术性;通过这部译著,西方的学术界和文学界将对早期中国的辉煌和浪漫有更多了解,并对由伟大史学家所展现出来的人类教训有更好理解。[3]598
倪译工程的启动与译本的发行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史记》在美国的阅读与研究。《史记》研究在90 年代出现高潮,研究内容向着专而深的方向发展,并出现了里程碑式的研究论作。1999 年,侯格睿出版专著《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以比较历史撰写方法来探讨司马迁与西方史学家写史目的的不同。1995 年,杜润德出版专著《模糊的镜子: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对《史记》文本的文学性及潜在的文学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杜润德与侯格睿两本专著是《史记》研究领域的重要贡献。李乃萃(Vivian-Lee Nyitray) 撰写了博士论文《美德的写照:司马迁〈史记〉中的四位君子的生平》(1990)。侯格睿先后发表了《司马迁〈史记〉的形式与叙事》(1992)与《论司马迁的多重叙事法》(1994)两篇文章。另外,倪译在90 年代陆续出版以后,美国学界对中国研究的著作或选集里,尤其是具有学术性的著作与选集,几乎都会在其参考文献里列出倪译《史记》书目。
倪译接受具有广泛性,更具深入性。倪译更适合想真切了解中国历史文明的读者,“倪译本不是为了普通读者、而是为了认真的学生而提供一个详尽的研究……”[16]315倪译更有益于中国研究领域的美国专家与比较历史领域的研究学者,但外行读者可能不太喜欢倪译本,有学者认为:“我怀疑非专家们,特别是大学生,会不太乐意去读这样的翻译。”[17]137
整体而言,倪译的接受多是正面而肯定的,当然也有负面的微词。不管怎样,倪译拥有自己的特色、价值与读者群,起到了深入介绍与加强的作用。倪译必将使读者更加真切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明。
三、华译与倪译的接受探因
华译与倪译都在相应的美国社会环境与读者阅读期待中产生,是美国不同时期的接受环境和读者期待视野改变的呼唤。不同接受环境中不同读者的期待视野必然对翻译策略选择与译本接受效果有着深深的影响。
华译《史记》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中美关系尚处于敌对状态,美国政府推行以美国文化为主导的对外文化战略方案,对待外来文化比较专断而随意。在汉学研究上,20 世纪初法国沙畹所出版的五卷本《史记》是西方第一部重要的《史记》译著。50 年代的美国,《史记》研究论作只是零星出现。不言而喻,当时的美国读者对中国文化与文学普遍不甚了解,对司马迁的《史记》几乎一无所知。华兹生本人在其译本出版之前没来过中国大陆。为了西方读者接受,华兹生进行调适翻译,对全书整体内容做了重新安排,避免使用专业术语与较多注释,以便让译文流畅易懂、具有可读性与吸引力,满足美国读者猎奇与浅层了解的愿望。本就喜欢文学的华兹生多次说明自己的翻译目的:他在翻译中尝试关注作品的文学吸引力,把注释降到最低……[18]36。他认为:理想的翻译应是满足于各种读者,但满足专家所需的注释数量很可能失去只想获得整体意思的读者;一些学者认为严格的直译是合适的,但对许多读者来说却是痛苦的。[18]36
美国的汉学研究与《史记》研究进展很快。在国际环境上,中美关系于70 年代开始缓和,80 年代末相互间官方与非官方的合作迅速发展。随着全球化与世界文明的快速发展,美国提出了比较开放而平等的文化观,认为世界上不同价值体系间应该互相尊重与学习。倪译所产生的八九十年代的美国社会环境与读者期待和五六十年代自然有着天壤之别,因为不同时代由读者个人主观情感、知识基础、生活阅历、价值取向等多种因素所合成的期待视野是不同的。为了适应美国新一代接受者的阅读心理期待,倪译团队所译《史记》尽可能完整、忠实、精确地保留原著的风貌与内容。倪译注释颇多、资料详尽,采用侧重尊重原作、充分再现原作信息的异化策略,目的是为了满足西方学者与专家深入研究的需要。华译与倪译都有着明确的读者对象,华译为了读者需求而简化内容,而倪译为了读者需求而增厚内容。《史记》在美国两个时期两次不同的重大翻译是改变了的接受环境与读者需求的呼唤,“反映了中国文化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地位的消长过程。”[19]129
倪译与华译两次不同的翻译模式展现出从简单到复杂的《史记》翻译合作化趋势与世界性倾向。这两次翻译与接受情况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过程,这是美国内部接受环境与全球化发展的宏观外部环境相生相息的作用结果。随着世界文明与全球史的快速进展,世界越来越需要一种精准而统一的英语译本,以宜于对人类早期历史与文化的深入研究。可读性强的华兹生译本越来越不能顺应学术研究的深入需求,而倪译团队的《史记》翻译是注重历史性与本真性的全译工程。历史典籍需要实事求是的异化翻译来突出它的历史真实性,从而还原历史本真原貌。只有精益求精的本真翻译才有被一再解读与研究的价值。历史典籍翻译应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向世界读者负责。倪译保证了译文的精确度,必将会使世界人民更加真实地了解中国早期文化与人类共同的历史文明。
结语
华兹生所译《史记》与倪豪士所主导翻译的《史记》大不相同,而且这两个译本的接受与影响也可谓迥然不同。这两次翻译各具特色与功能,华译起着引导与普及作用,而倪译起着深入与强化作用。两译本相辅相成、对立统一,正如侯格睿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所做的表述:两个翻译很不相同,但却奇妙得互补[14]146;华译本的读者可能会更多,但是,被华译吸引的读者可能会去读倪译,进而再去读原著;华兹生优雅的翻译会继续发挥作用,特别是对那些主要兴趣是把《史记》作为文学作品阅读的读者来说。[14]151两译本优势互补、相互引介、相互加强,共同成就了《史记》在美国、在西方传播的效果与价值,包括它的文学与史学价值。总之,中国典籍《史记》在美国经历了两次最大的翻译(即全球最重要的两次英译)之后,在世界上会更加光彩四溢、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