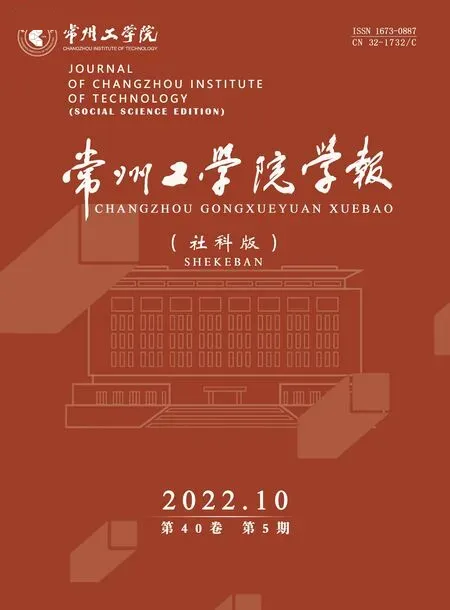《绣谷亭薰习录》集部初探
刘占康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康乾之际,统治者经过几十年的武力征讨,统治基础不断巩固,社会逐渐稳定,文化事业也渐趋繁荣,私家藏书尤为发达,由《四库全书》中的进呈书目亦可见一斑。其中,吴焯之子吴玉墀进呈的书籍有152种1 777卷,存目101种,8种无卷数。《绣谷亭薰习录》便是吴氏父子为家藏书籍所作的提要目录。
一、吴焯父子及其《绣谷亭薰习录》的编撰
私家藏书至明清而大盛,与此相应,目录学著作也呈现繁荣的景象,涌现了毛晋《汲古阁书跋》、钱谦益《绛云楼题跋》、钱曾《读书敏求记》、缪荃孙《艺风藏书记》等一大批优秀的私人藏书目录,为整理我国古代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绣谷亭薰习录》便是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私家藏书书目。
(一)吴氏父子
吴焯,字尺凫,号绣谷,晚号绣谷老人,清代钱塘人,生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卒于雍正十一年(1733),“喜聚书,凡宋雕元椠与旧家善本,若饥渴之于饮食”[1]467,建构“瓶花斋”“绣谷亭”,专以藏书吟咏为业。绣谷亭藏书多达万余卷。赵昱诗曰:“故人绣谷翁……插架饶万卷。”[1]468吴焯著有《渚陆鸿飞集》《药园诗稿》《南宋杂事诗》等。吴焯与厉鹗、毛奇龄、朱彝尊等当时名士多有来往。张熷有其行状。其长子吴城字敦复,号瓯亭,钱塘监生,雅好聚书,能承父志,凡“插架所未备者,复为搜求,勤加校勘,数十年丹黄不去手。城子为金、中麟均能文”[2],著有《瓯亭小稿》《配松斋诗集》等。另,吴玉墀,字兰陵,号小谷,吴城之弟,焯之子,乾隆庚寅科举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任太平县教谕,五十四年(1789)任贵州遵义知县[3]10,五十九年(1794)任正安州知州[3]25。四库开馆,玉墀献书数百种。玉墀妻应世婉,聪颖能诗,有遗诗《漱玉亭稿》4卷。
可见吴氏家族为书香门第,喜藏书,尤着力于宋元珍本的收集。而《绣谷亭薰习录》一书便是对瓶花斋所藏书籍的记录,其中不乏秘书宝册。
(二)《绣谷亭薰习录》
《清史稿·艺文志》载:“薰习录二十卷。吴焯撰。”[4]但该书在流传过程中散佚。叶德辉《书林清话》载:“存经部易一卷,集部三卷,近仁和吴昌绶校刻。”[5]现存松邻丛书乙编本,即仁和吴昌绶双照楼刻本,有易类1卷,105种,集部2卷,210种,分作2册。原本具体卷数和分类已不可考。集部2卷依据时代划分,楚辞4种,唐人集23种,宋人集102种,金人集4种,元人集58种,明人集19种,共210种。
该书前有其子吴城、吴玉墀序文,可惜首页阙佚,但依然可以从中大略看出该书的写作原委。其文如下:
(前叶阙)君子①其或取诸。
一作者生平事迹,惟以正史为断,史所不载者,则考之志乘,志所不载者,则参之晁氏《读书志》,马氏《文献通考》……其遗事逸语,见之诸家文集野史说部,中者悉采入焉。如同时远省之人则询之是邦故老,不惮再三,期于核实而后已。
…………
一雍正癸丑,先子见背,讫今三十余年矣!始克收罗散失,重加编校,或前为钞本,今已刊布者;或前为秘籍,今始流传者。不无互异,一遵原稿,以存先志。
男 城、玉墀 恭记[6]5
可见,该书内容搜采广泛,以史书为主,间考各种书目文献,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马端临《文献通考》、钱曾《读书敏求记》、朱彝尊《经义考》等。其他各类书籍,即便是野史小说,如有相关者也悉为采入。倘若条件许可还会实地考察,询问故老,以期核实,其严谨笃信可见一斑。另外,通过该序还能够大致确定该书的编纂时间。序文末言“雍正癸丑,先子见背,迄今三十余年矣”,雍正癸丑为雍正十一年(1733),所以吴焯应死于1733年,那么该目录编纂成书当在30年之后。
此外,由此序文可知,该目录为吴焯所作,后由其子吴城、吴玉墀整理而成。吴焯生前已为其藏书作过诸多题跋识记。如精抄本《元和郡县图志》题识一条: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四十卷,篇首皆有图,凡海宇要隘依约可睹,得王公设险之道焉,其后图既散亡,志亦阙逸,已见程大昌后跋中,则编有阙文在宋时已然矣。余今以《唐书》校之……第不知焦氏何所据而指为五十四卷也……余搜求廿年始获得之。维日冬至从桥西观海棠盛开,归披此卷,良快心志,篝灯泛览,不觉达曙。康熙丁酉十一月二十日绣谷亭主焯。[7]429
《绣谷亭薰习录》史部内容亡佚,无法与此文相对刊,实为遗憾。跋中先列作者、卷数,然后介绍该书的内容和流传情况,考证校勘卷数的分合。这些体例模式基本奠定了该书的写作基础。不仅如此,吴氏作为书香世家,其子吴城、吴玉墀皆能继承父志,喜读书聚书,在此过程中也积累了大量资料。影枕碧楼丛书《南轩易说》跋称:
此东北部末跋语云“静惕堂古林书目有此,此即其藏本也。从湖州书贾得之,识数语以志喜”。当为吴敦复所记。[8]
又《善本书藏书志》中《读书敏求记》条载吴玉墀手记一则:
是钞为知不足斋藏本,癸巳夏鲍兄举以赠予,昔竹垞太史乞钞于也是翁,小胥与以金不应,脱所衣青狐裘益之。先子乞钞咸涪临安志于花山马氏,予钱二万,经半年乃得半部,复予钱二万始允借钞,前辈爱书如此。今藏书家如市儿说合矣。世风不古,即此可证。丙申春,仲小谷跋。[7]552
可见,其子吴城、吴玉墀也对藏书作有题识、附记等内容。只是这些题跋都是随手而记,缺乏统一格式,往往还夹杂着许多私人琐事和个人情感。如《南轩易说》跋称该书“从湖州书贾得之”,《读书敏求记》更是大段叙说书籍的来处。吴焯《元和郡县图志》也有“维日冬至从桥西观海棠盛开”等生活琐碎内容的记叙。还有一些比较感性的记录,如“良快心志”“世风不古”“数语以志喜”等表达情绪的词语。而在《绣谷亭薰习录》中,此类同书籍本身无关的内容多已删去,形成了规范的统一的体裁格式。因此《绣谷亭薰习录》由吴氏父子两代人共同完成。
二、《绣谷亭薰习录》的目录学价值
目录之书起源于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后由《汉书·艺文志》保存下来,对考察书籍源流以及了解亡佚书籍等方面具有很大价值。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中言“则知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9]。吴氏父子文化积淀深厚,《绣谷亭薰习录》一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目录学价值。
(一)版本记录详细
有宋《郡斋读书志》开私家藏书目录之先河,为后世私藏书目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本的体例范式。其体例为介绍每书作者、卷数和主要内容,后世多沿袭。后尤袤《遂初堂书目》开始简单记载各书版本。如《尚书》,《遂初堂书目》:“旧监本《尚书》、高丽本《尚书》。”[10]至明代,许多书目都有意识地记载书籍的不同版本。如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李鹗翀《得月楼书目》等,但大多与《遂初堂书目》类似,只记载版本为宋本或元本之类,不描述具体内容,甚而不载卷数及撰人。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首次将版本纳入提要范畴,而不仅仅是单纯地对版本进行“账簿式”的罗列。如李白诗集,《读书敏求记》:“李翰林全集三十卷,太白集宋刻绝少,此是北宋镂本,阙十六卷之二十二、十六卷之三十,予以善本补录,遂成完书。前二十卷为歌诗,后十卷为杂著,卷下注别集,简端冠以李阳冰序,盖《通考》所载陈氏家藏。不知何处本,或即此耶。”[11]可见,在《读书敏求记》的提要中,第一部分介绍了《李翰林全集》的版本来源为宋刻本,第二部分说明各卷内容划分。在《读书敏求记》中许多提要的条目介绍了书籍的版本内容,这已成为该书的一大特点。《读书敏求记》虽开了于提要中记录版本的先河,但所记比较简略。《绣谷亭薰习录》在此基础上,对版本记载得更为详细,会提及具体的刊刻者或刊刻时间、地点等。如《龙筋凤髓判》条:“沈润卿刻本,丹阳都穆跋其后。”[6]8《重刊校正笠泽丛书》条:“元后至元五年鲁望之十一世孙德原刊于书院。”[6]10有时连版刻数量和字数也会记载在内,如《黄州小畜集》条:“并开载工价,计雕五百三十二版,依旧本凡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四十八字。”[6]12可见其对版本记载得非常详细。有的条目还详细介绍其书刊刻过程,如《台阁集》条:“案克家上蔡人,先为谏议大夫,言蔡京事,后以龙图阁待制知台州。嘉佑于上元中尝刺台后守,表扬前烈,因刻于郡斋。”[6]7该按语结合谢克家生平经历,说明此本《台阁集》的刊刻原委,也能由此间接地了解该书的主旨大意。
有的条目还会还原其版本流传过程。如《曲江集》条:“明琼山邱濬录自阁本,成化九年序而刻于韶郡;万历十二年,南韶兵备豫章王民顺重翻。”[6]3《李贺歌诗编》条:“京兆杜牧序,元至正丁丑复古堂翻雕,遵宋临安陈氏书坊旧本,明再翻,有刘淮东之跋。”[6]7有的条目全文都是对版本流传的介绍,可见作者对版本的重视。如《道乡集》条:“绍兴五年李纲序,公之二子柄、栩镂板传世。既经散失,明初谢应芳龟巢访其遗文,著为《思贤集》五卷,刻于常州成化中,翰林学士王思轩从内阁录得原本以授公之十四孙量,于是此集复行翻雕,并《思贤集》附,此本无《思贤集》名,当是量未翻雕以前钞本也。”[6]35这对把握该书的流传过程、正确评估其版本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二)考证精审
《绣谷亭薰习录》除了对版本内容作了详细的记录外,还对书籍相关内容作了考释,包括作者的生平爵里、作品的真伪等。作者也自言博览百家诸子之书,虽遗事逸语,悉加采入,乃至实地考验,询问邦国故老,其考证之精审核实可知。
1.考证人物生平爵里
古代通讯不便,加之作品保存困难,许多诗人作家作品散佚严重,作者的生卒年等一些问题难以确定。《绣谷亭薰习录》在参考各种文献的基础上,加以合理推测,对这些问题进行考证释疑。如《姑溪居士集》条:“陈氏称之仪为尚书之纯之兄,考本集,之仪乃从弟也。之纯字端伯,之仪字端叔,可证。”[6]27又如《李太白集》条花费了近1 000字的笔墨对李白生卒年、出生地等进行考证,驳斥《新唐书》《旧唐书》等说法的讹误,并一一追溯其致误之原,甚为详审。对于像李白系狱年份这种复杂的问题,作者也并未下断言,只是认为《南丰序》所言更为“精当”而已,并感叹“信乎考订之难!”。可见作者于考订下了很大功夫,对其中的酸甜苦辣深有体会。
2.考辨作品真伪
对于混入文集中的伪作,作者会在《绣谷亭薰习录》中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考察和推断。如《浮溪集》条:“末附罗愿所撰显谟阁学士程迈司业胡伸二传,因高宗尝书御屏‘文章汪藻,政事程迈’,而时人语有‘江南二宝,胡伸汪藻’,故编集者取二人以附之,往见录本,失去标注并原名,误认为藻作矣。”[6]28作者根据文本中的错误,推测《浮溪集》中程迈、胡伸二传撰者致误的原因:整理者将当时的时人谚语与高宗御屏语相混淆,由此导致署名的误会。又《韦苏州集》条:“又今本末卷有《鼋头山神女歌》《寇季膺古刀歌》二篇,古本所无。观其笔势繁缛,不似韦作。”[6]7从韦应物诗歌的版本和风格判定该书为伪作。现存韦集基本上是以王钦臣重编10卷本为底本,而在此本中并无《鼋头山神女歌》《寇季膺古刀歌》,吴氏言“古本所无”当指此。宋代在王钦臣重编本基础上凡有三刻,补入8首诗,后《全唐诗》又增补5首,其中就包含此2首诗。“必须注意的是,无论宋代三刻所补入的八首诗,还是《全唐诗》所补入的五首诗,都有很不可靠之处。”[12]因此,《绣谷亭薰习录》将其定为伪作,虽稍嫌于武断,却也为考察其作品真伪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参考性。
3.考证卷数
“卷”是书籍的计量单位,每卷文字多少,并无一定的规制,这也造成了同一部书卷数会有出入。尤其是雕版印刷出现后,书籍的传播发行更为便利,不同的版本卷数不同是常见的现象。《绣谷亭薰习录》能在考察版本流传的同时,注意厘清不同版本卷数的分合,这在之前的书目提要中不多见。如《居士集》条:“此欧公存日集已行海内,迄无全本,自周益公集诸本编次且为之年谱曰《居士集》,外集而下至于书简集凡十,名刻于家塾。其子纶又得欧阳氏传家本,乃公之子棐所编,属益公旧客曾三异校正,即《文献通考》所载《六一居士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四卷、年谱一卷是也。明嘉靖中行人陈珊总旧集厘为一百三十五卷,刻于江西藩署,而其先天顺、弘治、正德、吉安皆有刊本,皆祖庆元刻也。此编或疑非祖本。案公志表皆云《居士集》五十卷,即益公十集中之一。而陈氏云:‘《居士集》,欧公手(所)定(也)。’今卷尾有熙宁五年男发等编定。案年谱,公以是年闰七月卒,则此五十卷是当时手定本。至益公庆元刻本始汇其全耳。”[6]15该序说明了欧阳修《居士集》卷数由50卷到153卷,再到135卷的演变历程,清楚地展示了其各个版本的卷数发展情况。
还有一些书籍卷数记载前后矛盾,或不同书目记载各言其是,纷繁复杂,提要会指出疑误所在,并作出推测。如《苕溪集》条:“焦氏题行简《苕溪集》五十五卷即此是已。又载刘一止《类稿》五十卷,一书字一书名,其误特甚。考韩元吉行状只称《类稿》五十卷……考其全编,前五十三卷皆本集,第五十四卷行状,五十五卷告敕,则卷帙又与韩状不侔,岂后人又加编定欤?”[6]31
三、《绣谷亭薰习录》的文学批评价值
《绣谷亭薰习录》所录书籍,以记版本为主,兼有考证,文学评论相对较少,只是偶尔提及,有时还是引述前人评语,草草了事。如《眉山集》:“陈氏称其‘长于议论,着论精确’,刘夷叔称其‘属对工巧,诗自成家’,并属定论,不愧苏氏后尘矣。”[6]27又如《养蒙集》:“阮亭尚书论其诗文皆肤浅不工,信然。”[6]49作者只是引用前人评语加以肯定,并无自己独特意见,然而由“并属定论”“信然”等词亦可想见作者的文学态度。加之集部保存相对完整,后序云:“经史子三部六册不知流落何处,幸此集部一类尚完好足焉。”[6]67即便大多是只言片语,我们也可据此大致窥探吴氏的文学批评思想。
(一)尊儒崇“道”,注重诗法
《绣谷亭薰习录》表现出儒家道统思想,这自然与儒学占据统治地位有关。且清代考据学盛行,知识分子大多沉溺于考经订史,对辞赋文章不甚在意,戏曲小说更是等而下之。《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言:“今扫除畛域,一准至公,明以来诸派之中,各取其所长,而不回护其所短,盖有世道之防焉,不仅为文体计也。”[13]吴氏在《梧溪集》中亦言:“彼于宋末前闻犹为传述,况乎闻见所至,一一可惊可谔之事,发乎放言高论之间。盖欲以草野之诗,备一代之史,所谓不以风云月露浪染笔尖者也。”[6]54所不同者,《四库全书总目》虽不提倡“风云月露”的纯文学性写作,但还是肯定了它们的存在,而《绣谷亭薰习录》则明确认为“风月之形”的描写是“浪费笔墨”的无用之作,甚至对《网山集》中《浮屠氏论》一文提出强烈批评,这可看作吴氏的政治及文学宣言。其文如下:
呜呼!佛入中国以来,其教既行,举中国而西方之矣。所谓裂其衣冠,去其须发,逃父割妻,毁灭形骸,此蠢夫愚妇之所为。而学士大夫往往指空说性,凝思于虚,观心于寂。即贤如苏子瞻、张无垢辈犹蹈入禅学焉。孟氏诛其心,韩子罪其迹。时各不同,后先一律,岂得以西土之俗,置之不论不议之列乎?[6]37
由此可见吴氏笃信儒家之诚,对儒以外的其他思想采取排斥的态度,大加挞伐,认为是“蠢夫愚妇之所为”,可以说“尊儒崇‘道’”这一思想基本上贯穿了他文学评价的始终,把符合儒家之旨作为最高的评价。如《龙川集》言:“今观适序……发其秘藏,见圣贤之精微以不失儒者之旨。其推崇亦至矣。”[6]38但在强调诗文思想正统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形式的美,肯定诗法。在《广陵集》中列举《春雪》《京口》《润州》《春城》诸诗,认为“皆可为诗法”[6]23。又如《鹿皮子集》:“期以孔子为师而折衷群言之是非,可为特立独行而无畏慑者矣……诗七言绝佳,第多出韵不可为法。”[6]51对陈樵诗文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给予肯定,同时对其诗歌不合韵律要求感到遗憾,认为“不可为法”。可见《绣谷亭薰习录》所提倡的文学之美应符合思想与形式并胜的要求。
(二)以人论诗,讲求气骨简重之美
《绣谷亭薰习录》评价作品时往往会联系创作者的品格和生平,如《鲁公文集》:“公一代伟人,与日星河岳长留天地,其词章翰墨散落人间,当亦有鬼神为之呵护者矣。”[6]3并未直接评价颜真卿的文学成就,而是赞扬了其伟岸品格,间接对其作品表达了肯定态度。由此可见《绣谷亭薰习录》评价文学作品往往从其人品格出发,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与其“尊儒崇‘道’”的思想是一致的。由此而来,《绣谷亭薰习录》对诗文的审美评价更着重于文章气骨以及简练厚重的美学风味。吴氏在《湛然居士集》条中言:“余尝论《中州集》与元诗绝不相类,读《湛然集》犹存余响,在元人中别是一种气骨也。”[6]46赞扬之情油然而生。又如《杜清献集》条:“读诸条奏,剀陈时事得失,犹觉生气凛然。”[6]39对于简练厚重美学风格的追求,在《绣谷亭薰习录》中更有多处论述。如评王禹偁诗文,认为其“能去五代繁缛之习,一出于典雅简重,是所谓能开风气之先者”[6]12。《北山小集》条“古诗坚洁犹有宋初风味,然颇负著述,当时人亦尊之”[6]31,简练并不是淡而寡味,相反意味着厚而有味,因此作者吴氏也特别强调诗歌所蕴含的醇厚之美,如《澹居稿》条:“其诗不失温厚和平之旨,力矫江西派艰涩一路,学者当知之。”[6]60《虞文靖集》条:“其文醇正雄简,宗门之子长也。”而对于不符合这一标准的诗文,哪怕其外在形式多么完美,在吴氏看来都是有弊病的。如《不系舟渔集》条:“永嘉自四灵宗尚唐法,沿及子上,犹有余风,然失之薄矣。”[6]53
四、结语
古今书籍散落多矣,赖目录之书可保存一二,以供后人了解当时所存图书及文化发展情况。《绣谷亭薰习录》是吴氏家族两代人相续努力的结果,虽然散佚严重,所存不多,但依然可以从保存相对完整的集部目录中略窥其内容特点。它上承钱曾《读书敏求记》,对书籍版本及流传有详细记载和考辨,对后世研究某一书籍的版本有重要借鉴意义。该书虽涉及文学思想和艺术的内容不多,但依然可以看出当时普通知识分子对文学的评价标准和审美追求。总之,《绣谷亭薰习录》一书是清前期具有代表性的目录著作,虽历经风雨,但依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注释:
①由下文推断,此处所缺之处当为“先君子”,即其父吴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