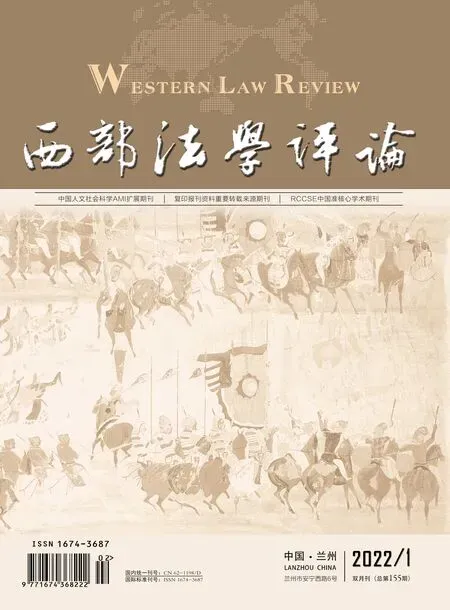现实危险:概念、机能和学说
温建辉
自2021年3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十一)》开始生效,新增的多个危险犯进一步扩大了犯罪圈。《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第134条之一的危险作业罪,指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一规定具有重要的刑法史意义,它是我国《刑法》在犯罪构成上第一次明文规定了“现实危险”的法律概念。一个全新的概念的产生,必有其产生的理论和现实的基础,并以其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机能,对刑事法治实践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现实危险”这一法律概念具有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机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提倡。
一、现实危险的概念
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与犯罪行为的现实危险密切相关,它们在犯罪行为危害社会的过程中辩证统一。理论界常将刑法上的“危险”划分为行为的危险和行为人的危险。(1)黄悦:《刑法中的危险概念及其展开》,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本文所论现实危险中的“危险”指危害行为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而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这样的危险有所区别。
(一)现实危险的哲学底蕴
现实危险是一个法律概念,这一法律概念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可能是包含在事物中,预示事物发展前途的种种趋势,是潜在的尚未实现的东西。”(2)萧前、李秀林、汪永祥:《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第3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7页。《刑法》第134条之一规定的“现实危险”正是一种可能,一种导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可能。“可能本身又有现实的可能和抽象的可能。现实的可能是在现实中有充分根据,在目前条件下可以实现的可能。”(3)萧前、李秀林、汪永祥:《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第3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刑法》第134条之一规定的“现实危险”就是这种现实可能。现实危险是犯罪行为本身具有的导致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并且在当前条件下可以实现的可能性。危害行为的现实危险是一种现实可能,而犯罪主体的人身危险性是一种抽象可能,应注意区分。“人身危险性最基本的概念应当是指再犯可能性”(4)游伟、陆建红:《人身危险性在我国刑法中的功能定位》,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再犯可能性是基于已然之罪的犯罪经历对犯罪人的预测,并无考虑实施犯罪的具体条件,因而是一种抽象可能。
危险犯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它们分别对应具体危险和抽象危险。具体危险指具体危险犯的行为具有的危险程度可高可低,只有具备高度危险时才成立犯罪。例如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对飞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不能一概入罪,而只有暴力行为危及飞行安全的情形,才可以追究该罪的刑事责任。抽象危险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这种行为通常都具有高度危险,所以无需特指某种具体危险的发生;二是行为具有多种多样的危险,不一而足,所以抽象出其共性而统称危险。辩证唯物主义也将可能分为现实可能与抽象可能,那么,刑法上的具体危险和抽象危险与哲学上的现实可能和抽象可能是否具有对应关系呢?笔者认为,它们之间不具有对应关系,刑法上的具体危险和抽象危险同属于现实可能,而抽象可能“在现实中缺乏充分根据,在目前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可能”(5)萧前、李秀林、汪永祥:《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第3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所以,不应认为刑法上的抽象危险属于哲学上的抽象可能。
(二)现实危险的联动解释
我国《刑法》在罪状中明文规定“现实危险”仅此一例,而其他的犯罪没有使用“现实危险”这一术语,具体规定亦多种多样。其中结果犯和行为犯有着明显的危害事实,自不待言,那么,其他的犯罪行为呢?
在《刑法》中规定的危险犯,无论是具体危险犯还是抽象危险犯,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危险。具体危险犯多以“危及公共安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等标识危险的措辞规定,抽象危险犯虽未陈明,却也将行为的危险暗含其中。那么,这些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所具有的危险与危害作业罪中的“现实危险”,是否相同或者说实质一样?笔者认为,因为作为危险犯,在平等适用刑法原则的要求下,它们在入刑标准的危险程度、危害后果等方面应当一样,因此,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应当具有程度相当的现实危险。
举动犯,《刑法》没有对其规定危险,那它是否具有危险?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这些由《刑法》总则规定的故意犯罪停止形态是否具有危险?以及教唆行为、组织行为、帮助行为等共犯行为是否具有危险?对此,笔者认为,作为构成犯罪的危害行为,都能够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刑法中不存在没有危险的危害行为”(6)杨兴培:《危险犯质疑》,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举动犯、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教唆行为、组织行为、帮助行为等犯罪形态全部都有危险,而且,基于平等适用刑法原则的要求,这些犯罪形态在定罪上具有实质相同的现实危险。但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在新增第134条之一危险作业罪中规定了“现实危险”,而《刑法》对其他犯罪都没有规定“现实危险”的构成要件,那我们将所有犯罪的危害行为全部解释为具有“现实危险”,是否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呢?换言之,遵照平等适用刑法原则进行法律解释,能否获得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效果?笔者认为,《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平等适用刑法和罪责刑相适应等三个基本原则,分属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它们分别适用于各自的层次领域,彼此独立,各司其职,因此,它们不可相互替代和补充。将所有故意犯罪的危害行为全部解释为具有“现实危险”,是因为《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第134条之一危险作业罪规定了“现实危险”,那么,按照平等适用刑法原则,所有《刑法》规定的犯罪的危害行为自动匹配上“现实危险”,而是否构成犯罪,是否符合法定的危险犯、举动犯、犯罪的停止形态,以及共犯形态等罪状情况,仍然由罪刑法定原则予以规定。可见,《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第134条之一危险作业罪中规定了“现实危险”之后,平等适用刑法原则则揭示了其他犯罪危害行为同样具有“现实危险”,这是一个以点带面的去魅过程,如此解释提高了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和效率。
(三)现实危险性的辩证法
现实危险性表现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主观恶性是犯罪人在犯罪行为过程中,包括罪过部分的犯罪心理和非罪过部分的犯罪心理等心理活动的综合性质,显然,主观恶性与主观罪过不同,主观恶性反映的心理内容更为全面和丰富。现实危险反映的危险内容,也就是主观恶性的心理内容:(1)犯罪动机。动机的卑劣程度直接反映了主观恶性的大小,比如卖火柴的小女孩为了不被饿死偷了一只烤鸭与盗窃成癖的富翁盗窃一只烤鸭,她们的主观恶性是不同的。(2)违法故意。在一些犯罪中存在违法的故意,虽然不是罪过心理,但也能反映主观恶性的大小,例如闯红灯引发的交通肇事罪中的故意闯红灯心理,它不属于罪过心理,但反映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3)罪过心理。这是反映犯罪人认可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是主观恶性的主要内容。这些主观恶性内容决定了现实危险的程度,现实危险是主观恶性的外在表现。因此,可以说现实危险和主观恶性的关系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现实危险是危害行为的本质属性。危害行为是一种实体,现实危险或曰现实危险性是一种属性,现实危险性是危害行为的本质属性,就是危害行为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现实可能性。主观恶性在实践中以危害行为表现自己,而危害行为的本质属性是现实危险性,所以说,主观恶性是现实危险性的根源,现实危险植根于犯罪人内心的恶,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通过危害行为表现出来的现实危险,作用并危害于社会。
如果说现实危险性是可能性,那么社会危害性就是现实性。现实危险性是犯罪人主观恶性的现实表现,现实危险性还不是实害,而只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虽然具有充分的根据,在现有的条件下能够实现,但是由于它是一种对他人、对社会不利的可能,会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防范和控制,所以很难得逞,在现实危险实现的过程中,表现为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等多种停止形态,在这些停止形态中,只有犯罪既遂实现了它的可能性,也就是从可能发展到了现实,从现实危险发展到了社会危害。可见,现实危险是危害结果的前身,危害结果是现实危险的结果。
二、现实危险的机能
作为《刑法修正案(十一)》在犯罪构成上的新增法律概念,现实危险对于刑法立法论、刑法解释论具有重要的支撑机能,兹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危害行为的定罪根据
1.现实危险的特征解读
现实危险性的“现实”特征解读。现实,指客观存在的事物。(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67页。它不是消逝的历史,也不是徜徉的未来。现实危险,指客观存在的危险实现为实害的可能性。界定现实危险的“现实”应把握两个关键点:第一,在现有条件下,该危险或早或晚是肯定“能够”造成实害后果。第二,在现有条件下,如果没有外来干预,该危险“必然”造成实害结果。如果一个行为本身有很大的杀伤力,但不具备条件,也不能对社会或者他人形成杀伤力,就谈不上行为具有现实危险。
直接故意犯罪是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希望”表明了行为人积极追求危害结果发生的意志倾向,显而易见,这样的犯罪行为充满了“现实危险”。间接故意犯罪是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放任”表明了这种犯罪行为与造成严重后果是同时存在的,行为之时,危害结果也正在发生,并且是明知的,否则便不能放任,可见,间接故意犯罪的危害行为具有“现实危险”。
过失犯罪是没有预见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或者已经预见到了危害结果可能发生,该“预见”精确地描述了过失犯罪行为与危害结果的不同步性,即行为当时,危害结果尚无发生,或非同时发生,抑或结果发生后才发觉。虽然如此,这样的危险仍然是“现实”危险。如果行为有可能造成危害结果发生,也可能不造成危害结果发生,那么,该行为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仅具有抽象可能,而不是现实可能,该危险就只是抽象危险。定罪只能依据现实危险,而不能依据抽象危险。
现实危险性的“危险性”特征解读。刑法上的现实危险性,不同于一般的危险。“现实危险”中的“危险”是高度的危险,而不是轻微的危险,其造成的危害结果应予刑罚惩罚,比如,非法殴打他人致人轻微伤,这样的殴打行为具有的危险不属于刑法上的现实危险。危险可能是紧迫的,也可能是非紧迫的,比如预备犯罪行为的危险通常是非紧迫的,而实行行为的危险是紧迫的。危险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比如帮助犯罪行为的危险是间接的,而实行行为的危险是直接的。
2.现实危险与预防刑
预防刑适用的正当性与危害行为的现实危险密切相关。预防刑与目的刑是相同内涵的概念,目的刑论认为,“刑罚只有在对预防犯罪或者教育罪犯具有特定效果的时候,才具有正当性。”(8)贾宇主编:《刑法学(上册·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296页。如此论见,有导致为预防犯罪而无限度扩张适用刑罚的倾向。如何限制预防刑的无限度扩张,笔者认为,行为的正当性也就是行为与效果之间互为充要条件的对应关系。其逻辑结构是:B行为是E效果的充要条件,那么,B行为就是一个正当行为;它的逻辑形式是:[(B↔E)∧E]⟹B。(9)温建辉:《法律行为的逻辑结构》,载《社会科学家》2020年第1期。因此,预防刑的正当性也就在于它能有效预防犯罪行为的现实危险向实害结果的转化,也即预防刑对危害行为的适用是必要的,同时也是足以预防危害结果的发生。由此可见,预防刑的适用取决于危害行为的现实危险,现实危险越大,则预防刑就越重,现实危险越小,则预防刑就越轻。
预防刑的正当性限制了犯罪圈的任意扩张,危害行为现实危险的情况决定了危害行为能否入刑。具有现实危险的危害行为入刑,首先应当根据现实危险性考虑它入刑的必要性,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行为会招致不可补救损害的现实危险可入刑。如《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妨害安全驾驶罪、高空抛物罪等犯罪。第二,需要刑事侦查才能确定责任主体的具有现实危险的行为可入刑。如《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等犯罪。第三,对屡教不改或持续不断的危害行为可入刑。如《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危险作业罪、妨害药品管理罪等犯罪。其次,应当依据危害行为的现实危险性考虑适用的刑种和刑度,使刑罚可充分实现对危害行为现实危险的管控,避免现实危险实现为实害结果。
3.过失行为不构成过失危险犯
过失行为的现实危险程度决定其不构成过失危险犯。依《刑法》规定,过失放火、过失决水、过失爆炸等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是结果犯,需要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才构成犯罪,而过失放火等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在过失行为中的现实危险性可谓是最高的了,所以,按照体系解释,危险性程度比过失放火等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低的过失行为,就不应成立过失行为的未遂犯,或者说在立法上不会规定过失危险犯,在司法上不应对过失危险行为的未遂行为定罪处罚。体系解释的底蕴是罪刑相适应原则,体系解释具有合理性,这是过失行为不构成过失危险犯的首要原因。
《刑法》上不应规定过失危险犯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失危险行为难以用刑罚实现预防。对于危害结果已经发生的犯罪,只能用刑罚进行惩罚,对于实害结果尚未发生的犯罪,才谈得上预防。因为危险犯是实害结果没有发生的犯罪,对其适用刑罚是从预防的角度考虑的。疏忽大意过失行为由于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危害后果没有预见,没有预见,怎么预防呢?对他适用刑罚也起不到预防犯罪的作用;过于自信过失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有预见、持放任的意志倾向和排斥的情感态度(10)谢勇、温建辉:《区分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的最终方案》,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1期。,总体来说是一种侥幸的心理,行为人是冲着危害结果不发生采取行动的,那么,对这样的行为用刑罚进行预防理由似乎不充分,有不人道的嫌疑。
当前主张我国《刑法》中存在过失危险犯的观点比较一致地以危险驾驶罪为典型,但危险驾驶罪在司法实务中是作为故意犯罪进行认定的,典型案例如下:2016年1月10日,温某醉酒驾车,与张某乙驾车相撞。温某驾车继续行驶,张某乙驾车追赶。温某驾车逃逸中,撞到停在路侧的一辆客车。温某驾车继续逃逸,张某乙驾车继续追赶。后温某驾车又与一辆轿车相撞。相撞后,被撞轿车又与另外一辆轿车相撞。发生致温某及王某甲、宋某乙、马某受伤住院,多方车辆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经交警大队事故责任认定,温某负本事故的全部责任,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温某醉酒驾驶,与其他机动车连续碰撞并多次发生交通事故,致3人轻伤和财产损失234592元,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张某乙构成危险驾驶罪。(11)温某犯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张某乙犯危险驾驶罪二审刑事判决书,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11刑终35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在这个典型的追逐竞驶案例中,温某造成多起交通事故,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参与追逐竞驶的张某乙构成危险驾驶罪,很明显,追逐竞驶在没有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时构成危险驾驶罪,在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可见,危险驾驶行为的既遂形态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者的犯罪性质相同,都是故意犯罪。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大数据检索,证实其他的危险驾驶罪也都是以故意犯罪定罪,其中有2个案例以过失犯罪进行辩护,且都未被法院采纳。(12)杨得智危险驾驶罪一审刑事判决书,西吉县人民法院(2018)宁0422刑初97号刑事判决书;陆启彭、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分公司危险驾驶一审刑事判决书,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7)黔2601刑初8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二)唯物决定论的基石
传统刑法理论存在宿命论和主观武断的两大质疑。第一,当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部门,关于间接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主流认识里,存在着唯心主义的幽灵,即间接故意行为和过失行为的危害结果发生了就构成犯罪,危害结果没有发生就不构成犯罪(13)贾宇主编:《刑法学(上册·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209-210页。,行为是否成立犯罪,仅凭危害结果是否发生,定罪成了上帝玩骰子,完全地听天由命。
第二,对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定罪面临着主观武断的质疑。我国《刑法》规定了危险犯,包括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在司法定罪中,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等犯罪形态,都存在实害结果尚未出现而定罪的情况,那么,对这些行为定罪是否武断?如果被告人提出被定罪的行为是没有发生实害结果的,即便行为实施完成最终实害结果也没有发生,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这样的情况被定罪是不是冤枉了人?
为将游荡在刑法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幽灵彻底逐出刑法学说,在刑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中全面贯彻唯物决定论,以及回答对未完成的危害行为定罪的质疑,需要借助“现实危险”这一概念,对这一《刑法》新增法律概念的科学理解和准确界定,可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法律智慧,以“现实危险”这一磐石支撑起唯物决定论的犯罪论并科学化对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定罪根据,也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在科学立法上的重要贡献。
在间接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这些结果犯的定罪问题上,既然从结果是否发生来理解和认定,为听天由命的唯心主义留下了空间,所以应转换思路和转变认定对象。对未完成危害行为定罪的主观武断的质疑,必须从未完成行为的本质特征进行界定和说明。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唯心主义、一个是主观武断问题,它们的共性是不客观,脱离了客观现实,所以,解决这些问题应转变到客观方面,即危害行为。而现实危险是危害行为的本质,因此,扫除刑法上结果犯中唯心主义存在空间和避免对未完成行为定罪的主观武断这两大任务,加诸在危害行为的现实危险身上。
从“现实危险”上阐释结果犯的成立和未完成行为的定罪问题,关键是揭示现实危险的危险机制。刑法上因果关系的逻辑分析学说为“现实危险”的危险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按照因果关系的逻辑分析学说,犯罪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应当是充分条件的因果关系,直接故意犯罪行为由于是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所以即便其“危害行为”是危害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直接故意的“犯罪行为”也是危害结果发生的充分条件,而充分必要条件包含了充分条件,因此,直接故意犯罪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包括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和充分必要条件的因果关系;间接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包括充分条件和充分必要条件的因果关系,没有必要条件的因果关系。(14)温建辉:《非理性犯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7年版,第55-56页。以B代表危害行为,以H代表危害结果,据此形成了危险机制类型图(表1)。

表1 危险机制类型图
从刑法上因果关系的逻辑分析学说可以得知,无论是间接故意行为、过失行为,还是危险犯中的危险行为,抑或直接故意犯罪的未遂行为、中止行为,它们不仅具有“现实危险”,而且都是危害结果发生的充分条件,它们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都是必然的,无可置疑的,因此,对这些行为定罪不会冤枉无辜,相反,这是发挥预防刑防患于未然的重要体现。在以危险机制类型图对间接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危害行为进行严格限定以后,它们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必然的关系,危害结果的发生将不再是一种随机现象,以危害结果的发生定罪也不再是听天由命的宿命论了;由于未完成实行行为具有的现实危险必然导致危害结果,因此在现实危险实现为危害结果之前以预防刑进行干预管控,也不存在冤枉无辜的可能。
(三)违法性论的新探索
1.三阶层犯罪论违法性论的内部论争
违法性判断是大陆法系三阶层犯罪构成学说的重要环节,源于对违法性判断标准的不同,经历过形式的违法性论和实质的违法性论,“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思考违法性问题的路径不同, 由此导致犯罪成立范围、认定犯罪过程、犯罪和刑罚的关系、刑法和社会的关联性都不相同。”(15)周光权:《违法性判断的基准与行为无价值论——兼论当代中国刑法学的立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这就是当下的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在违法性论上的交锋。
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各有所长,相持不下。行为无价值论者直指结果无价值论要害,从违法性论的发展史、结合刑法立法和司法实务、仅有法益侵害没有规范违反也是不法势必扩大处罚范围等三个角度论证了“仅有结果无价值是不够的。”(16)周光权:《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关系》,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期。结果无价值论者针锋相对地指出了行为无价值论的主要缺陷在于,“强调犯罪的规范违反性,与保护法益的刑法目的相冲突;突出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偏离了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普遍承认主观的违法要素,导致认定犯罪的整体性,既混淆了违法性与有责性,也不利于区分未遂犯与不能犯,且不利于贯彻共犯从属性说;注重主观的正当化要素,不仅未能限制刑罚适用,反而扩大了处罚范围;采取规则功利主义,导致对国民行为的过度干预,也不利于保护法益。”(17)张明楷:《行为无价值论的疑问——兼与周光权教授商榷》,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社会中, 刑法首先应当是裁判规范, 而不是行为规范”,行为无价值论的违法性判断标准牵强附会。(18)黎宏:《行为无价值论批判》,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客观地说,双方的观点都有道理,但他们的立场不同而且各自坚守。
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也有统合的趋势,但在如何统合的路径选择上,行为无价值论者和结果无价值论者各有所重。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折中融合的初期表现为行为无价值论从一元的行为无价值向二元的行为无价值的嬗变,其后期为从伦理违反的二元行为无价值论到法规违反的二元行为无价值论。对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论折中的第一阶段,有学者指出,折中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的“二元论”,不能成为重构犯罪论的路径。(19)黎宏:《行为无价值论批判》,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对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论折中的第二阶段,有学者指出,新规范违反说的理论“基因”决定了其难以彻底“告别”伦理规范,并在具体司法案件中得到回归。(20)贾健:《新行为无价值论的困境与出路——兼与周光权教授商榷》,载《现代法学》2018年第6期。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都有立场和充分的理论根据,它们双方所认为的对方的不足不仅是己方所长,相反可以用己方的理论佐证对方学说的成立,而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各自不能自圆其说,却在对方的理论中得到佐证,例如行为无价值论者说的“仅有结果无价值是不够的”,而结果无价值论者指出的行为无价值论者的缺点也恰好是己方的观点所能给予弥补,这成为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统一和融合的内在驱动力。依笔者看来,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具有本质一致性、内在互补性和必然统一性。
2.四要件犯罪论的违法性论
我国传统的四要件犯罪论对行为违法性的判断不仅没有缺席,而是更为全面和严格。四要件犯罪论对犯罪违法性考察具有不同于三阶层犯罪论的特征:第一,四要件对行为的违法性是刑事违法性的认定,我国实行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二元分立,违法行为不是犯罪行为,所以我国的违法性判断是刑事违法性的认定;而德日等三阶层论国家实行一元化的犯罪治理,违法即犯罪,它们的违法性判断与我国具有实质的不同。第二,四要件犯罪论对刑事违法性的认定较之三阶层对违法性的判断,更为全面和严格,四要件犯罪论对刑事违法性的认定需要从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四个方面进行认定,而且这四个方面的认定是一个联言判断,有一个不成立,刑事违法性就不能成立。第三,就对犯罪行为性质的认定而言,四要件犯罪论认为刑法是裁判规范,而不是行为规范,因此,将对犯罪行为性质的判断称之为对犯罪行为的认定;三阶层犯罪论由于缺乏整体性思维模式,它们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考察分散而孤立,立足于客观主义而从犯罪的客观诸要件入手,导致合法的行为和无责任的行为也被认为符合犯罪构成的结论,因而它的犯罪符合性层次的判断范围宽泛,就在第二层次补充了违法性的判断,对责任的考究在第三个层次,这是三阶层犯罪论对符合性判断的自我补救,德日等大陆法系的三阶层犯罪论尽管符合德日等国的思维习惯,但不符合我国的思维习惯。可见,德日等国的三阶层犯罪论不是出罪机制完善,而是入罪认定粗糙,不得不多次筛选和补救。
3.现实危险概念对违法性论的统合
“现实危险”是联系犯罪构成四要件的枢纽,也是犯罪行为刑事违法性的集中体现。 具有“现实危险”的危害行为由人实施,符合刑事责任能力规定的人就是犯罪主体;“现实危险”是主观恶性的表现形式,表明了犯罪主观要件的存在;“现实危险”是危害行为的本质属性,表明了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确定的直接的因果联系;“现实危险”是危害结果的前身,表明了犯罪客体所受的危害。因此,“现实危险”集中体现了犯罪的刑事违法性。
“现实危险”概念能够统合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现实危险是主观恶性的表现,所以,行为无价值违法性论所坚持的犯罪主观因素在“现实危险”概念中得到了考虑。现实危险是即将实现的危害结果,危险状态与危害结果内在一致,所以,结果无价值违法性论的坚持在“现实危险”概念中得到落实。可见,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统一于现实危险概念。进而言之,三阶层犯罪论与四要件犯罪论虽然道路不同,但现实危险概念从客观的角度科学阐明了它们的机理相通和牵连一致,使三阶层犯罪论与四要件犯罪论在违法性论上得到更多的趋同和对话的机会。
三、现实危险的学说
基于现实危险概念的重要机能,提倡现实危险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现实危险说对当代刑事法治实践的重要影响。
(一)风险社会刑法立法的转向
1.风险社会需要风险刑法
风险社会常见三大表现:第一,工业化大生产的监督管理稍有不慎,就能导致相关人民群众的重大损失,例如污染环境罪等;第二,人们的生活生产相互依存度高,一方稍有闪失,就会给相关人造成严重危害,例如《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危险作业罪、高空抛物罪等;第三,产业链长,行业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对人民群众造成较大的危害,例如《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等。“为了能在风险社会中保持社会共同体的安全,必然要求刑法不能等到实害结果发生时才介入。只要行为人本身的行为显示出了某种危险性,具有造成危害性结果的可能性时,刑法就应当有所作为。”(21)郑明玮:《论刑法中危险犯的“危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风险社会需要风险管控的刑法,其以控制风险为显著特征。
2.风险刑法以危险犯为核心范畴
危害行为的本质属性是现实危险,现实危险附着的危害行为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类危险犯,是以犯罪的未完成形态表现出来,即犯罪预备行为、犯罪未遂行为、犯罪中止行为,这些行为都具有现实危险;第二类危险犯,是以共犯形态表现出来,教唆犯罪行为、组织犯罪行为、帮助犯罪行为,这些行为同样都具有现实危险;第三类危险犯,是以具体的独立的罪名表现出来,它们无疑都具有现实危险。这三种以现实危险为基础成立的犯罪,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危险犯是依据刑法总则在刑事司法中确认的危险犯,第三类危险犯有刑法分则规定的独立罪名,这三类犯罪属于广义的危险犯,第三类危险犯是狭义的危险犯。在当前风险刑法比较流行的语境下,风险刑法的核心范畴是危险犯,特别是第三类危险犯。
探求危险犯的兴替时期可从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其一是从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可知,这是直接的认知方式。西周法律关于犯罪的规定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典范,其规定的罪名主要有不孝不友罪、犯王命、放弑其君、杀越人于货、群饮、违背盟誓、失农时等罪名。(22)曾宪义:《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48页。这些罪名都是以行为犯和结果犯为形式的实害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罪名有“十恶”“七出”“六脏”等罪名,这些罪名也全都是实害犯。到了民国时期,同旧刑法典相比,新刑法典对普通刑事犯罪降低量刑幅度,而将打击的锋芒更加集中指向所谓犯“内乱罪”“外患罪”“妨害国交罪”“杀人罪”“强盗罪”等严重危及国民党政权及其所需要的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并惩罚“预备犯”“未遂犯”, 从而更加明确了刑法打击的主要目标。(23)曾宪义:《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页。可见我国刑法进入20世纪后,危险犯在犯罪形态的家族中,开始成为占比较大的重要成员。
其二可以从犯罪与刑罚的联系中反推出犯罪的形态。第一,从法制史可见,同态复仇是世界各国在刑法起源上的共同现象,同态复仇通常表现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杀人偿命”等,从罪刑直接对应的情况可知人类社会早期的犯罪都是实害犯。第二,刑罚的嬗变对应了犯罪形态的演变。在刑罚的嬗变史上,刑罚始终不能脱离它的报应属性,但有从严酷到缓和的趋势。我国奴隶制典型五刑为墨、劓、剕、宫、大辟,封建制典型五刑为笞、杖、徒、流、死,当代《刑法》的五种主刑为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刑罚从古到今的嬗变对应了犯罪形态的演变,犯罪圈从严重的实害犯扩张到危害不太严重的实害犯和未完成形态的犯罪。第三,刑罚从注重过去到重视将来对犯罪形态的影响。“在科学时代,刑罚的重心由犯罪转移到了犯罪人。刑罚已不再只是回顾已然的犯罪而且是前瞻未然的犯罪的手段。”(24)潘凤林:《刑罚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从刑罚的进化反推犯罪形态的演化,可知犯罪形态的最初形态是实害犯,直到19世纪后半期在刑事实证学派的影响下,危险犯开始登上刑法舞台,并逐渐成为群魔乱舞的主角。
3.危险犯的本质
关于危险犯本质的见解。关于危险犯中危险的性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主要有“行为危险论”“结果危险论”和“行为危险与结果危险分说”三种观点。这几种观点的背后分别为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所支撑,各有所长,各不相让。在我国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分别支持了行为属性危险论和结果属性危险论,有立场的观点形成不可调和的争论。笔者认为,“犯罪的本质是犯罪活动中支配行为认可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而且这种心理态度是包括知、情、意三种因素在内的心理活动的综合体现。”(25)温建辉:《犯罪本质新论》,载《理论探索》2012年第1期。因此,危险犯的本质是伴随危害行为的以现实危险表现出来的主观恶性,它包括犯罪动机、违法故意和罪过心理等犯罪心理。
关于危险犯的既遂未遂问题。因为第一类危险犯为未完成形态的犯罪形态,作为未遂犯罪不言自明,第二类危险犯是以共犯形态表现出来,它的既遂未遂问题依实行行为的既遂或者未遂而确定,这就转向共犯的独立性说和从属性说的问题,所以,谈到危险犯的既遂未遂问题,通常是在第三类危险犯的范畴中进行的。关于第三类危险犯的既遂未遂问题,有未遂说、既遂说和折中说之争。既遂说是我国的通说,马工程教材认为,“以行为人实施的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是危险犯。”(26)贾宇主编:《刑法学(上册·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213页。折中说认为,“危险犯是实质的未遂犯,法定的既遂犯。”(27)舒洪水:《危险犯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既遂说和折中说都认为危险犯是既遂形态,这就面临两个难以解释的问题:第一,既然危险犯具有发生危害结果的危险,那么,这种危险不可实现吗?这种危险实现以后,又是犯罪的什么形态?难道不是犯罪既遂吗?一个犯罪可以有多种犯罪既遂的形态吗?第二,在危险犯的危险状态出现后,既然是既遂,那么,这时“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还能构成犯罪中止吗?按照既遂说就不能,但这可是《刑法》第24条规定的标准的犯罪中止。因此说,既遂说和折中说都不能成立,笔者赞成危险犯的未遂说。未遂说认为“犯罪既遂包括行为犯和结果犯两种形态。犯罪成立与犯罪既遂是两个概念,犯罪未遂同样可以被规定为犯罪,危险犯就是被《刑法》规定的一种未完成形态的结果犯。”(28)温建辉:《论犯罪既遂的标准》,载《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现实危险是危险犯的本质特征。
(二)刑法预防主义的当代含义
1.预防主义的嬗变和扬弃
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而预防犯罪归根结底是预防现实危险向危害结果的实现,因此,刑罚预防主义的基本思想也就是用刑罚管控现实危险。预防犯罪说根据预防对象分为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即双面预防说。(29)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220页。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分别针对已然之罪和未然之罪。(30)贾宇主编:《刑法学(上册·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297页。一般预防主义和特殊预防主义的分野已成定局,双面预防主义是主流趋势。(31)孙道翠:《积极一般预防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话语》,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特殊预防是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进行教育改造,预防他们重新犯罪;一般预防,是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威慑、警诫潜在的犯罪者,防止他们走上犯罪道路。预防主义滋生出预防刑,“基于预防犯罪目的所裁量的刑罚是预防刑。”(32)张明楷:《论预防刑的裁量》,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1期。
用刑罚管控现实危险依预防主义理念的不同而各有特征。我国法治文化博大精深,从法制的历史长河来看,“刑罚体系的历史规律,不是要求肉刑和自由刑互相结合和并存,而是要求用自由刑来代替肉刑。”(33)蔡枢衡:《中国刑法史》,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刑罚的这一历史规律,伴随着成文法的制定和完善所提供的历史条件,体现了刑罚从报应主义向预防主义嬗变的趋势。在从报应主义向预防主义演进的过程中,认罪伏法是一个关键环节。因为如果惩罚的适用脱离了犯罪人的“认罪伏法”,那它仅仅是一出悲剧而已,可能激起更多的社会反叛,效果会适得其反,因此,报应刑效果的充分发挥需要犯罪人的“认罪伏法”,而“认罪伏法”的范例效应和宣传效果又成为预防主义的摇篮。可见,预防主义脱胎于报应主义,并在报应主义的实施中得到成长。
我国刑罚的特殊预防源远流长,自奴隶社会以降,奴隶制五刑是墨、劓、剕、宫、大辟,这些法定刑除了直接的惩罚功能之外,还具有显著的特殊预防机能。例如,为了防止脱逃,原则上刺墨,例外割鼻、去膑。(34)蔡枢衡:《中国刑法史》,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奴隶制五刑通过肉体惩罚同时实现了对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危险控制。我国刑罚的一般预防同样历史久远,消极的一般预防主义首先登上法制舞台。消极的一般预防主义,指依靠刑罚的惩罚性和强制性威慑社会上不稳定分子的思想和做法。法制史记载,秦国商鞅有云:“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35)《商君书·说民》。“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36)《商君书·赏刑》。以及后世各个朝代奉行的“乱世用重典”,无不体现出消极的一般预防主义,通过严刑峻法震慑了社会上一些人以身试法的现实危险。随着以威慑为目的的消极一般预防主义的盛行,作为其赖以存在的实践基础的犯罪人的认罪伏法的范例效应和宣传效果也达到顶峰,这又直接导致积极的一般预防主义应运而生,以规范确证或者规范强化为目的的积极一般预防主义被统治阶层奉为圭臬。西方国家在1979年,海因里希·贝克曼(Heinrich Beckmann)正式提出了“积极一般预防”这一术语,他完成了新理论与传统消极一般预防理论的分离,并将其正式命名为“积极的一般预防”。(37)陈金林:《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页。积极一般预防这一术语虽然最先出现在西方国家,而反观我国,中华法系岂在人后,我国法制史记载,礼刑并用是西周之首创,“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38)《后汉书·陈宠传》。显而易见,出礼入刑、以刑护礼,与积极一般预防主义的理念毫无二致,足见中华法系文明之领先。
2.当代预防主义的反思
在犯罪行为的现实危险导致危害结果发生之前管控犯罪行为才是预防,而在现实危险实现为危害结果之后只能惩罚。就特殊预防而言,对再犯的预防刑的适用存在有罪推定之嫌,因为它完全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或者纯粹是一种“一日做贼、终生是贼”的偏见,是对犯罪人日后再犯罪的预先惩罚,或者是对一个犯罪事实重复评价后的双重处罚,所以对犯罪人的特殊预防应当仅限于对已有之罪的预防,而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其必将继续犯罪并预先惩罚。因此,对已有之罪的预防,就是对正在实施的具有现实危险的犯罪行为在危害结果尚未发生之前适用刑罚的预防。也即是对犯罪预备行为、犯罪未遂行为、犯罪中止等行为在危害结果没有发生前适用刑罚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39)温建辉:《刑事责任根据新论》,载《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对教唆犯罪行为、组织犯罪行为、帮助犯罪行为等共犯形态在没有促成实行行为完成的情况下,以刑罚制止其对实行行为的加功,削弱实行行为的现实危险向危害结果的转化。对举动犯和狭义的危险犯适用刑罚,阻止举动犯和危险犯的现实危险实现为危害结果。可见,特殊预防犯罪的实质是对危害行为的现实危险的管控问题。
消极的一般预防主义和积极的一般预防主义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在法制粗疏的时代背景下,积极的一般预防主义缺乏存在的条件,只能以“刑罚”威慑人不犯罪,而只有在法制相对完备详尽的条件下,用“刑法”规诫人遵纪守法才成为可能。我国自西周就产生了积极的一般预防主义及其法制实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礼仪大邦,礼法完备,为积极的一般预防主义提供了得以施展的“规范”条件。而西方的英美法系作为不成文法传统国家,它们的习惯法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英国及至19世纪中叶以后,国会才开始大量颁布刑法立法(40)林榕年、叶秋华:《外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刑法始具规模,美国步英国后尘则更晚一些;大陆法系作为制定法传统国家,它们亦非文明古国,而刑法立法及其完备有着极其缓慢的发展和积累过程。西方国家与我国在刑法积极预防主义的产生路径上不同,它们的刑法积极预防主义是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风险社会的历史阶段,刑法为了应对日益增多的社会风险,提出了风险刑法的概念,积极的一般预防主义也是此时代产物,由此可见,积极的一般预防主义在我国诞生在文明社会之初,在西方国家则出现在文明社会的近期,这样的分别都有其历史文化背景。
就消极的一般预防而言,惩罚罪犯的示范性威慑效果,可以收到消极的一般预防之效,而不是为了一般预防而惩罚犯罪。这是因为以惩罚犯人实现一般预防的观念是不人道的思想,即通过对一个人的惩罚来达到预防别人犯罪是“杀鸡儆猴”把人当作了工具,这样的刑罚工具主义违反了以人为本的现代人权观念。无论积极的一般预防,还是消极的一般预防,在笔者看来,都是适用刑罚的附带效果,而不是首要的追求。就积极的一般预防而言,惩罚罪犯作为反面教材具有规诫社会的作用,规诫观者遵纪守法,可以起到积极的一般预防之效。然而,积极的一般预防同样面临着消极的一般预防的违反以人为本理念的诘难。因此,从根本上说,预防主义特别是一般预防主义,乃刑事立法的指引,而不是刑事司法的遵循,只有特殊预防方可纳入司法实践的思考。
3.预防主义以管控现实危险为限度
刑罚正当化的根据。传统刑法以结果犯为中心,而风险刑法以危险犯为中心,风险刑法的立场使它与预防主义的目的刑论不谋而合。传统刑法主要针对已然之罪,刑罚的根据是报应;风险刑法防控对象突出了未然之罪,刑罚的正当性在于预防。目的刑论为扩大刑法目的和目的效果更大化,有无限度扩张刑罚适用范围的趋势,如何约束预防刑或者说预防刑的限度是什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预防刑的限度,只能基于现实危险的考量,而且不可逾越到非现实的危险,比如人身危险性不能成为定罪的根据,因为人身危险性是一种抽象危险。刑罚作为预防和管控现实危险的治理手段,它具有必要性和充分性,这是预防刑的边界。
首先,预防刑的正当性在于它的必要性。刑罚作为一种官方实施的合法的有重大损害的行为,它应当将损害最小化,除非在必要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在能不使用的情况下决不使用。刑罚适用于犯罪具有必要性,是指适用刑罚为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所必要。报应刑的必要性是针对危害结果已经出现的犯罪应当给予惩罚;预防刑的必要性在于适用刑罚预防犯罪的必要性,是针对危害结果尚未发生的犯罪运用刑罚管控现实危险。其次,预防刑的正当性也在于它的充分性。刑罚适用的充分性,是指适用刑罚能够达到惩罚犯罪和预防现实危险的实现,惩罚犯罪的充分性是针对危害结果已经出现的犯罪给予公正的惩罚,预防犯罪的充分性是针对危害结果尚未发生的犯罪运用刑罚管控现实危险使之不能实现。比如故意杀人既遂的犯罪,判处1年有期徒刑,这能实现杀人偿命的公平正义吗?这样的刑罚适用不具有报应刑的充分性。对于故意杀人未遂,判处半年有期徒刑缓期一年,这能达到控制故意杀人的现实危险和实现预防故意杀人的目的吗?这样适用刑罚也不具有预防刑的充分性。
(三)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发展
1.现实危险是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契合点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在批判大陆法系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刑法原则,它取两者之精华而熔铸于一身。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坚持唯物辩证法,反映了犯罪活动过程中诸要素的联系和动态的特征。客观主义主张刑事责任的根据是犯罪人的行为及其实害;主观主义坚持刑事责任的根据是犯罪人的危险性格即反复实施犯罪行为的危险性。(41)张明楷:《新刑法与客观主义》,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6期。客观主义认为惩罚应当与犯罪的恶害相对应,从而实现相对主义立场上的刑罚报应,同时期望通过刑罚的适用来防止社会一般人走上犯罪不归路(一般预防);主观主义则认为适用刑罚应当促进对犯罪人的改善、劝导、教育、再社会化,坚持目的刑论、教育刑论,强调刑罚的特别预防效果。(42)周光权:《刑法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融合》,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间的互不相让,只是因为它们之间没有找到契合点,而现实危险正是促和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共通之物,因为客观主义所主张的行为的本质属性是现实危险,其所主张的实害是现实危险的实现,而主观主义所认为的犯罪人的危险性格的具体表现也正是现实危险,所以现实危险概念兼容并蓄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基本观点。
2.未完成犯罪行为和非实行行为的客观标准
预备行为是为了犯罪而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危害行为,这是我国《刑法》第22条第1款的规定,但显然不是所有的为了犯罪而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都是犯罪,它有几个条件的限制,第一必须是直接故意犯罪,第二必须是重罪。即便符合了这两个条件的犯罪预备行为被认定为犯罪仍然遭到了违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诘难,而在大陆法系的国家里基于客观主义的刑法立场,它们原则上不处罚预备犯,因此,对预备行为的定罪处境颇为艰难。笔者认为对预备行为的定罪处罚如果不进行严格限制,确实存在主观归罪的嫌疑。而在犯罪预备行为具备前两个条件的基础上,并且能够确定该预备行为对犯罪实行行为具有确定的促进关系,也即该预备行为必须是促进实行行为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或者充分必要条件,另外,该预备行为也必须具有现实危险,虽然不是直接的紧迫的危险,但也是现实存在的可以实现的危险,也就是说,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该预备行为的现实危险确实会促进实行行为,并最终导致现实危险的实现。据此,对预备行为定罪处罚就有了客观依据,而不会产生主观归罪之嫌。如果该预备行为对实行行为的实施可有可无,没有确定的促进作用,那么该预备行为只具有抽象危险,该预备行为便不应定罪处罚。可见,以现实危险为标准限制和确定预备行为的处罚范围,使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得到了发展。
关于举动犯,通说认为包括两种构成情况:一是预备性质的犯罪构成,二是教唆煽动性质的犯罪构成。(43)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145页。笔者对此观点的商榷主要有三点:第一,刑法不必改变犯罪事实的性质。《刑法》只是对犯罪事实的规范确认和刑罚应对,它不改变犯罪事实的性质。犯罪预备行为不必定性为犯罪既遂才能给予惩罚。第二,《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是犯罪成立的条件,而不是犯罪既遂的条件,即便《刑法》分则对犯罪预备行为以具体罪名规定了具体的法定刑,也只是表明了这种犯罪预备行为与刑罚之间的罪刑关系,并不属于犯罪预备行为性质的改变。第三,教唆煽动行为本质上属于犯罪预备行为。我国《刑法》第103条规定的煽动分裂国家罪、第249条规定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第295条规定的传授犯罪方法罪等等,它们属于激发犯罪意志、制造犯罪主观条件的预备行为。(44)温建辉:《非理性犯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7年版,第95-86页。既然举动犯实质上属于犯罪预备行为,那么,举动犯危害行为范围的限定应适用前述的预备行为的限制规则。
犯罪未遂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危害行为,这是《刑法》第23条第1款的规定,犯罪中止是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危害行为,这是《刑法》第24条第1款的规定,同样不是所有的未遂和中止的行为都成立犯罪,它的成立也有几个限制条件:第一是直接故意犯罪;第二必须是重罪;第三是有既遂的现实危险。该现实危险是直接的和紧迫的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危险,即未遂行为或者中止行为原本在不受外界干预或者自动放弃的情况下,必然造成危害结果;而如果没有客观障碍或者自动中止,未遂的行为或者中止的行为也不是必然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对这样的行为不能定罪处罚。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在严格的结果无价值论的语境中,因其没有造成构成要件规定的危害结果而定罪,也有违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诟病,在此,结果无价值论得到了扬弃。由于危险犯实质上属于犯罪未遂行为,因此,对危险犯的危害行为的限定应适用与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相同的规则。
教唆行为、组织行为、帮助行为等共犯行为的主客观相统一问题。非实行行为的共犯行为当然是具有现实危险的行为,但这些共犯行为一概认定为犯罪也有主观归罪之嫌。共犯行为对犯罪实行行为同样应当具有确定的促进关系,即共犯行为必需是对实行行为加功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或者充分必要条件;而如果该共犯行为对犯罪实行行为的顺利实施无实质的加功作用,甚至是可有可无,对这样的共犯行为定罪处罚,难避主观归罪之嫌。因此,只有具有现实危险并对实行行为具有确定的加功作用的教唆行为、组织行为、帮助行为等共犯行为,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3.规范责任理论的客观归罪之嫌
规范责任论是在心理责任论之后产生的刑事责任理论,规范责任论与心理责任论相争不下。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进行审视,心理责任论固然有可完善之处,但规范责任论则走向了客观归罪的道路,未免有失偏颇。规范责任论侧重于责任年龄、责任能力、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和期待可能性等客观情况和规范评价,而对相应的心理因素考虑不足,甚至于在缺乏与客观要件相对应的主观要件的情况下定罪追责,比如他们对客观处罚条件在定罪中作用的认可,这就将刑事责任的追究引向了客观归罪的歧途。为限制规范责任论冤枉无辜的可能,德国刑法理论界提出了客观归责理论对危害行为进行了限定。客观归责理论已成为当前规范责任论的基本观念,客观归责理论在(必要)条件关系的基础上对行为制造风险的归责问题进行了研究。客观归责理论包括三项内容:行为制造了法不允许的风险;行为实现了法不允许的风险;结果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客观归责论中的风险在刑法上即现实危险之实,其中的行为是具有直接的紧迫的现实危险的实行行为,该风险虽未冠以“现实危险”之名,实际却有现实危险之意。由于客观归责理论立论的粗疏,在理论的自我完善的进程中,从避免冤枉无辜的一端走向了放纵犯罪的另一端。例如,在德国客观归责理论影响下,帮助自杀、自残行为不被定罪。而按照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将帮助自杀、自残的行为限定为为他人实现自杀、自残必不可少的帮助,可以构成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支持了这一主张。其他如大陆法系不处罚预备犯也存在这样的疏漏。由于三阶层犯罪论符合性立论的粗疏,为了限制客观归罪,又以客观归责论和消极的责任要素等多重补救措施以限制危害行为的成立范围,以至于放纵犯罪而不知。
结 语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危险作业罪的罪状中,我国《刑法》在犯罪构成上第一次明文规定了“现实危险”的法律概念。本文从概念、机能和学说三个层次,循序渐进进行了阐述。首先,从概念上说,现实危险的法律概念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以平等适用刑法原则为指引,它对于理解刑法中的危险犯、举动犯等危害行为的属性,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现实危险是刑法学的核心概念,它能联系和规定危害行为、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等诸多基本概念。其次,从机能上看,现实危险概念以其科学内涵成为司法定罪的根据;它也是在犯罪论中全面贯彻唯物决定论的基石;现实危险概念使三阶层犯罪论与四要件犯罪论在违法性论上具备了更多的趋同和对话的机会。最后,从学说上讲,在当下的风险社会里,现实危险概念当之无愧地成为了风险刑法的核心范畴,它科学阐释了刑法预防主义的当代含义,并且以现实危险说,推动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本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