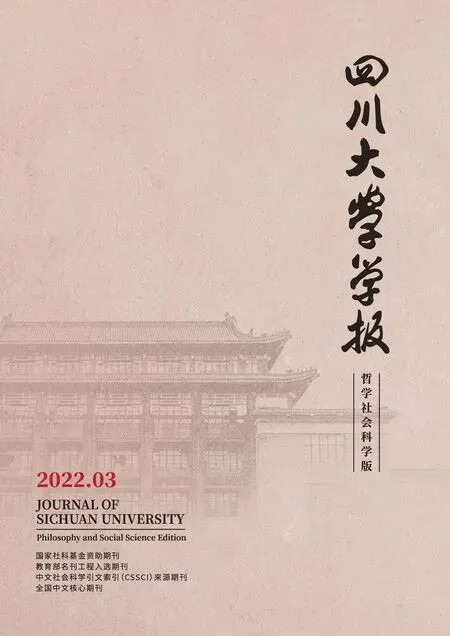朱熹人欲思想在日本近世的误读
——以古学派对“无欲说”的批判为线索
高 伟
在日本儒学研究领域,关于德川时期(1603—1867,亦称近世)儒者对人欲(人情)的认识一直备受关注。日本思想史家丸山真男(1914—1996)所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可谓这一方面的经典论述。他分析了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古学派儒者对人欲(人情)的积极主张,以此展现所谓朱子学之“连续性思维”在日本近世的解体过程。(1)参看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3-183頁。这种着眼于人欲(人情)话语的分析视角,对此后学者把握日本古学派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韩东育的《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一书就系统考察了徂徕学派的“人情论”,认为由于人情每每表现为人欲,人欲不可去犹人情之不可无,故徂徕眼中的理想政治即是道合乎人情,而非人情合于道。(2)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74页。王青在《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中指出:荻生徂徕的哲学思想反对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主张道德修养不应以内修成己、独善其身为务,而应以经世济民为目的。(3)王青:《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导言”,第3页。
这些研究表明,日本古学派关于人欲(人情)的主张是以批判朱子学的人欲说为立论基础的。自然,《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所用的“朱子学”一语并不专指朱熹个人的思想,而是“从周濂溪到朱子一连串思想系统的总称”,或者说除陆王心学以外的“宋学”。(4)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30頁。即丸山真男是以一种“广义朱子学”的视角展开考察的。这种视角对于提炼整体性的思维方法或精神倾向确实极为有效,但不可否认这种宏观式的把握也会忽略许多宋学内部的差异,对于日本古学派的宋儒观也不能进行批判性的省察。比如古学派儒者所提出的“人物之情欲,各不得已也。若无气禀形质,则情欲无可发。先儒以无欲论之,其差谬甚矣”;(5)山鹿素行:「論人必有情欲」,『山鹿語類』第四,東京:国書刊行会,1910—1911年,第24頁。“主静无欲等说,……其害道特甚”;“儒者之学……初无灭欲以复性之说”(6)以上参见伊藤仁斎:「語孟字義」卷之上,関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第6巻,東京:東洋圖書刊行會,1927—1938年,第19、37-38頁。由于《日本儒林丛书》是按篇目重新编排页码,此页码是指该篇目显示的页码,下同。等说法,皆以宋儒主“灭欲”“无欲”之说作为非难的重要理由。但比照朱熹思想,特别是《朱子语类》中的主张,我们不难发现,朱熹虽常讲“灭人欲”“去人欲”,但并不是要人“灭欲”“无欲”。
对于朱熹人欲说被等同于无欲思想的原因,中国思想史研究家沟口雄三(1932—2010)的观点首先值得思考。他在探讨“中国式近代的渊源”时指出:清儒戴震(1723—1777)将朱子的“胜私欲”断定为追求无欲,是对朱子的曲解。这种曲解的由来,和戴震及其所处时代以“人的全部生存欲”来指代“欲”有直接关系。(7)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望》,龚颖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384-387页。沟口的研究并未涉及日本古学派,但他从具体历史状况来把握概念流变的思路,为我们理解朱熹人欲说被误读的原因提供了重要参考。在这种社会史观察视角之外,以黄俊杰、吴震等为代表的东亚儒学史研究者还着眼于从后世儒者的解经方法来阐明朱熹人欲说被批判的缘由。黄俊杰认为,伊藤仁斋虽反复批判宋儒以“存天理、去人欲”来论“王道”,但仁斋自身也并未完整理解孟子的“王道”概念,遗漏了其超越性一面。因为他在运用训诂学方法去把握《孟子》古义时所承袭的是汉儒旧注,故未能进入孟子思想的超越层面与宋儒的思想系统。(8)黄俊杰:《伊藤仁斋对孟子学的解释:内容、性质与涵义》,《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第146-149、153-160页。吴震对荻生徂徕“古文辞学”的分析则表明,徂徕主张“以古言征古义”、反对“以今言视古言”是对“古言”的绝对化。这导致他无视经典诠释及其思想义理的发展,拒斥朱熹对儒学思想的任何创新发挥。(9)吴震:《东亚儒学问题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4、141页。
他们的研究为我们反思朱熹人欲说为何在后世会遭到误解和非难,分别在时代文脉和学问方法上给出了极具启发性的解释。然而,这些解释还不足以回应朱熹人欲说为何会被日本古学派视为无欲思想这一最初疑问。因为沟口之论虽关涉无欲之说,但缺少了对日本古学派的考察。黄、吴的研究虽剖析了古学派学问方法与反朱子学的关系,但未考究“灭欲”“无欲”泛标签化的现象。故而,我们仍有必要以无欲思想批判作为线索梳理日本古学派对朱熹人欲说的误读过程。只有把握这一脉络,我们才能更好地看清古学派对朱子学人欲说的批判中朱熹相关话语所处的位置。借此考察,亦可反思广义朱子学视角下可能遮蔽的问题。
一、朱熹辨“情”“欲(慾)”“人欲”
朱熹关于情感欲望的主张因涉及儒学传统主题人性论、性情论,故此类论述见诸于朱熹的多种著述中。《朱子语类》作为朱熹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于“情”“欲(慾)”“人欲”的讨论自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可以成为我们展开后续分析的基础。
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情”“欲(慾)”“人欲”这些范畴关系紧密,但并不是同等的概念。如下一段的经典论述,就是讨论了“情”和“欲”的微妙关系。
性是未动,情是已动,心包得已动未动。盖心之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谓“心统性情”也。欲是情发出来底。心如水,性犹水之静,情则水之流,欲则水之波澜,但波澜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类;不好底则一向奔驰出去,若波涛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则灭却天理,如水之壅决,无所不害。孟子谓情可以为善,是说那情之正,从性中流出来者,元无不好也。
朱熹在这段文字中指出,“情”作为心之已动,可善可不善。“欲”由情所发,是“情”的流荡激越处。虽然“欲”是激越之情,但也可善可不善。趋于儒家所推崇的价值——如“仁”,则是善之欲;背离儒家价值的激越之情,则流为不善之欲。若再联系到《朱子语类》中作为对立概念的“天理人欲”说来看,如“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10)以上引文参见朱熹:《朱子语类》卷五、十三,《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9、388页。则我们不难发现,在朱熹思想中不但“情”与“欲”是不同范畴,“欲”和“人欲”也是差别甚大的概念。(11)关于朱熹区别“欲”和“人欲”,学术界早有指出。如金炳华等主编《哲学大辞典》“人欲”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1186页)就认为:欲是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正当要求,人欲则是过分的要求。朱熹就人的饮食欲望解释了此二者的不同,比如“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显然,“人欲”是需要被消除的“不好的欲”,其范畴似乎更接近朱熹讲的“有心慾字”的“慾”:
无心“欲”字虚,有心“慾”字实。有心“慾”字是无心“欲”字之母,此两字亦通用。今人言灭天理而穷人慾,亦使此“慾”字。……这“慾”字指那物事而言,说得较重。这“欲”字又较通用得。凡有所爱,皆是欲。
这里的“慾”与过分的物质欲求有关。朱熹以“慾”解释“人欲”,可见“人欲”多含有物质性贪欲这种意味。简单来说,朱熹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了“人欲”一词(包括“私欲”),对于单字的“欲”其解释则是多途的。“凡有所爱”即是“欲”,“欲”字指代范围更广,其中包含了一些带有积极意义的用法,如上述的“我欲仁”。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欲”字存在与“人欲”相混用的情形,比如“君子以道,小人以欲。君子小人,天理人欲而已矣”。(12)以上引文参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十三、八十七、一百○一,《朱子全书》,第17册,第3172页;第14册,第389页;第17册,第2961、3398页。此类例子虽然不多,但也是文本上导致后世读者混淆“欲”与“人欲”的潜在原因之一。
相比起能够展现“欲”与“人欲”之别的那些诠释,朱熹的“天理人欲”之辨与“去人欲”之说则显眼得多。比如他说“尽去人欲,全是天理,方诚”;“在天理则存天理,在人欲则去人欲”。在《朱子语类》中,此类“去人欲”“灭人欲”之说比比皆是。然而,朱熹却不言“去欲”“灭欲”,不主张寻常人“无欲”。他对周敦颐无欲之说的系列评点充分表明了这一态度:“周先生只说‘一者,无欲也’。然这话头高,卒急难凑泊。寻常人如何便得无欲”;“濂溪言‘寡欲以至于无’,盖恐人以寡欲为便得了,故言不止于寡欲而已,必至于无而后可耳。然无底工夫,则由于能寡欲。到无欲,非圣人不能也”。门人提问“寡欲以至于无”之意时,朱熹回答:“此寡欲,则是合不当如此者,如私欲之类。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13)以上引文参见《朱子语类》卷十五、七十八、十二、九十四,《朱子全书》,第14册,第484页;第16册,第2670页;第14册,第370页;第17册,第3172页。这些见解表明,朱熹认识到常人不可能通过无欲来学贤做圣,因此不苛求无欲工夫。故而,朱熹人欲说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为:他区别“欲”与“人欲”,排斥作为过分欲求的“人欲”(私欲)而不否定正当欲望的存在。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尽管对“情”“欲”“人欲”作出了如此细致的区分,周敦颐所讲的“无欲”或许也并非要禁绝人的一切感性欲望,(14)陈来在解释周敦颐“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时指出:“无欲”并不是要人禁绝一切感性欲望,而是指在特定修养过程中达到意识静虚状态的必要条件。参看陈来:《宋明理学》,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61页。但从日本古学派对无欲思想的批判来看,朱熹对情感欲望各概念的区分与不主无欲的思想并未得到应有的注意。黄俊杰指出在概念史研究中要留心“‘单位观念’之结构性或阶层性”。(15)黄俊杰:《东亚儒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儒家诠释传统研究刍议》,《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第14页。显然,朱熹思想中的这些概念关系并未完整传递到日本古学那里。如果按照守本顺一郎的说法,古学派儒者山鹿素行对朱子学的批判是“通过朱子的著作来进行的”,(16)其言:“山鹿素行的朱子学批判,与其说指向的是当时的日本朱子学,不如说是直接指向作为日本朱子学源流的中国朱子学,即通过朱子的著作来进行的。”参看守本順一郎:「山鹿素行における思想の歴史的性格」,田原次郎、守本順一郎校注:『山鹿素行』(日本思想大系32),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第501頁。那么我们将如何看待古学派对朱熹人欲说所作的“漏读”与“误读”?以下我们通过考察山鹿素行、伊藤仁斋与伊藤东涯父子(古义学派)、荻生徂徕与太宰春台(古文辞学派)对无欲思想的批判来展现这一漏读与误读的脉络。
二、山鹿素行对无欲思想的批判
山鹿素行(1622—1685)为日本近世前期的儒者,一般认为他是当时公开反对朱子学的先驱和古学派的始祖。其积极主张情感欲望的正当性,反对严格主义。表现在对无欲之说的批判上,山鹿素行有如下一段常被征引的话:
人有气禀形体,则有情欲。四支之于动静,耳目之于视听,喜怒哀乐之感内,饮食男女之索外,皆情欲之自然,而人物悉然。其间人者得二五之中,而其知识尤多,故其欲亦过。物者,寡知识。故情欲亦寡,而只见闻之间耳。故无深计远虑之谋。人物之情欲各不得已也。无气禀形质,则情欲无可发。先儒以无欲论之,夫差谬之甚也。(17)山鹿素行:「論人必有情欲」,『山鹿語類』巻三十三,東京:国書刊行会,1910—1911年,第四冊,第24頁。
在山鹿素行看来,人存在情感欲望是由于“气禀形体”这种物理性存在使然,情感欲望的多寡则与智识深浅有关,故无欲之说实为无稽之谈。山鹿素行此处把批判矛头指向了“先儒”,然而其所谓先儒究竟指哪些儒者,文中并未道明,这就使读者容易根据“反朱子学的先驱”这一标签,而误以为他在批判朱熹。但实际上,山鹿素行的无欲论批判主要针对的是周敦颐之说。
我们知道,周敦颐在《太极图说》《通书》与《养心亭说》中提出了关于无欲的主张,如其《太极图说》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无欲故静。立人极焉。”《通书》云:“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要,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动直则公。”《养心亭说》一文则就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之说指出:“予谓养心不止于寡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18)以上引文参见《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31、52页。对于周敦颐这些说法,山鹿素行认为:“周子以圣学之要为一,以一为无欲。其辞易简而其宗在异端。……以异端立无欲为宗,违天地之大经也,周子之说尤差谬。”山鹿素行所讲的“异端”,自然是指佛老之说。因为在他看来,“周子《通书》,……非圣学之书,毕竟以虚静、无为、无欲为宗。此等语意,无圣人论出以为宗,唯老庄释氏之所说也。”而周敦颐的学说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特征,是由于“周子初入释氏,……后专归于儒,而其所宗在虚静无欲,是习来之所致乎”。(19)以上引文参见山鹿素行:「儒家者流」,『山鹿語類』巻三十五,第四冊,第99、98頁。山鹿素行指出了周敦颐的无欲之说与佛老思想间的关联,以一种批判异端的态度来审视周敦颐的思想。
与严厉指摘周敦颐之说不同,山鹿素行对于朱熹则显示出极为不同的态度。虽然在山鹿素行看来朱熹也是主张无欲之说的,如他指出:“朱子曰:‘无欲之与敬,二字分明。要之,持敬颇似费力,不如无欲撇脱。人只为有欲,此心便千头万绪。’此是朱子亦为无欲之说。”山鹿素行此处所引的“朱子曰”,出自《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圣学”篇,为朱熹与门人探讨如何成圣时所发之语。然而,山鹿素行并没有将周敦颐和朱熹的无欲之说等量齐观,而是认为它们存在如下差别:
宋周子曰:“养心不止于寡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周子以无为养心之要,无是令情欲无之也。喜怒哀乐发而中节者,圣人之教也。令是至无底,是异端之断见也。人竟所不能至无也。朱子以无,为指心之不流于欲。少虽似说得好,周子之意见,悉自此无字流出来也。(20)以上引文参见山鹿素行:「儒家者流」「辨或問心之応用」,『山鹿語類』巻三十五、四十二,第四冊,第99、369頁。
山鹿素行认为,周敦颐讲的“无欲”意在使人消去任何情感欲望,和佛老的“绝情灭欲”说无异。朱熹讲无欲则是为了防止人心陷入欲望的迷途,并不要人真正绝情灭欲。可见,山鹿素行没有因为朱熹论著中出现了“无欲”字眼,就把他归入异端之列。这种态度的差别,实与山鹿素行对周敦颐和朱熹二人的不同历史定位有关。
在宋代的道统论中,周敦颐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例如朱熹即在《祠记》中指出:“秦汉以来,道不明于天下,而士不明于所以为学。……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炽。道学不传而异端起。……宋兴,……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后天理明而道学之传复续。”(21)朱熹:《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朱子全书》,第24册,第3768页。山鹿素行当然也承认周敦颐对于宋明理学的开创性地位:“宋悉排训诂专门名家,其学曰‘理学’、曰‘心学’,其端自濂溪周子以来也。”但他强调:“周子之学,其所本以虚静无欲,其所宗在胸中洒落。故非孔门之教,非圣人之学。”认为儒学由于受到了周敦颐的这种影响,“自是周孔之道疏阔,圣人之学无可见。至宋学大变,其说同异端,尤可叹息也”。(22)山鹿素行:「儒家者流」,『山鹿語類』巻三十五,第四冊,第97頁。可见,与朱熹把周敦颐置于道学之复续者这种高度评价不同,山鹿素行视周敦颐为致使圣学沦为异端的元凶。
山鹿素行对周敦颐的这种历史评价,从他对儒学道统的描述亦可看出。山鹿素行认为圣人之道“未尝离日用彝伦之中”,其道“尤简易,……无新奇空妙之可论”;但孔子殁后,“圣人之统殆尽”,其后虽有曾子、子思、孟子“因循来于夫子”,然不可企望孔子;其后,汉唐儒者或局限于“章句文词之习,或杂老子释氏之言,皆私意见”;到了宋代,“周、程、张、邵之大儒,相继而起,因易谈太极,欲尽其渊源。竟有高过之病,于日用不交涉。圣人之学,至此大变。……道统之传,至宋悉泯灭”。山鹿素行主张道要切近人伦日用,故对周敦颐如此大加挞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朱熹却评价甚高,认为朱熹“近取日用平常之际,论彝伦之上。章句大学中庸,集注论语孟子,注解诗、易。……定家礼,编纲目;教小学,详启蒙。其有功于圣门,孟轲之后,唯朱元晦也”。在他看来,朱熹这种“近于日用之间”的学风显然与“舍近求远,处下窥高,驰心空妙之域”的其他宋儒非常不同。只是朱熹由于身处南宋时代,无法不汲取“先儒之余流”,故导致其学问中“尤有寻本然之善,欲复天命之性、持敬存心之弊”。假若朱熹身处“周子之地,无余流之染”,则其“必可承不传之统”。(23)以上引文参见山鹿素行:「儒家者流」,『山鹿語類』巻三十五,第四冊,第110-111、108、111頁。山鹿素行显然期望宋代理学的开创者是朱熹,以为若朱熹首开宋代理学之端,则孔孟之正学本可复兴。
在山鹿素行看来,朱熹之学虽然也曾“初入佛老,专说求心见心”,但后来则“觉其非”;虽曾受学于李侗,但“实与延平(指李侗)别意思”。因此,“朱子解周子之无极,为别不有无极,论静坐为无益”。他眼中的朱熹之学,是一种与“日用”不脱节的学问,既“求之于句读文义之间”又“谨之于视听言动之际”。它绝非一种注重“静”的学问,而是充满了实践性,具备“动”的特性,这就与主张“虚静”的周敦颐之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山鹿素行如此解读朱熹的学问,自然不可能将周、朱二人的无欲之说等量齐观。对山鹿素行而言,前者代表了儒学在宋代“异端化”的开始,后者“其学志不远圣学”“近于日用之间”,(24)以上引文参见山鹿素行:「儒家者流」,『山鹿語類』巻三十五,第四冊,第108、109頁。构成了道统沦落后的唯一光环。山鹿素行的这种看法,往往并不为我们所注意。人们一般强调日本古学派对宋儒的批判,而忽视山鹿素行对于朱熹的赞美之词。当我们以“反朱子学”之先驱来称呼山鹿素行时,也应意识到其对宋儒的不同态度。
当然,在此后日本古学派对朱子学的批判中,朱熹并未如此幸运。伊藤仁斋、伊藤东涯父子对无欲之说的非难则主要对准了朱熹。
三、古义学派对无欲思想的批判
作为日本古学派之一的古义学派,是由儒者伊藤仁斋(1627—1705)所开创。伊藤仁斋主张恢复孔孟儒学本来的意义,著有《论语古义》《孟子古义》《语孟字义》等书。其子伊藤东涯(1670-1736)则主要致力于伊藤仁斋学问的普及与阐释,写下了《太极图说管见》《通书管见》《太极图说十论》《古今学变》等著作。如同山鹿素行对无欲思想的批判是围绕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通书》所展开一样,仁斋父子也通过指摘其中的命题来驳斥无欲之说。比如《太极图说十论》就是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朱熹的《太极图说解》中抽取了以下10条命题,逐一辨析了儒学古义、周子之意和朱熹之解的出入(见下表)。在仁斋父子看来,“晦庵之解,既非濂溪之本旨。而濂溪之本旨,又非圣经之意”。(25)伊藤仁斎:「読近思録鈔」,『日本儒林叢書』第5巻,第2頁。即周子之说并非儒家经典的本意,朱熹对周子之说的阐释也与周子本意不符。

命题伊藤东涯之辨①“无极而太极”论无极者理而太极者气也。且辨圣人不言理。②“无声无臭”论《诗》之所谓“无声无臭”并非说理。而“冲漠无朕”并非儒家之语。③“继善成性”论《图解》所引与《易》之本旨异,且非《图说》之本意。④“五行一阴阳”论《易》言阴阳不言五行,非万物化生之本。⑤“无极之真”论圣人之学不言理,而理之不可穷。⑥“五性感动”论周子以“刚柔善恶中”五者为五性,而不指“仁义礼智信”。⑦“阳善阴恶”论既曰“阳善阴恶”而后曰“主静”,则是反其类。《易》以阳生为复,而《图解》以静为复,则其旨不同。⑧“定之以中正仁义”论“中正仁义”言仁义之中正者,非言“仁义礼智”。⑨“无欲主静”论“无欲主静”与孟子之意异,亦不可以此说仁。⑩“体立用行”论古者无体用之说,而又不可以阴静为太极之体。
以上述条目来看,仁斋父子对无欲之说的批判似乎只在第9条,但实际上其批判理路的展开与他们对太极、阴阳、动静等概念的认识有关。如伊藤仁斋认为,周敦颐提出“无极而太极”,意在说明“有斯理而后有斯气”,因为“无极者,谓无物之前自有理,太极即指一元气而言”,即“无极”与“太极”在周子那里是不同的范畴。但朱熹在解释此命题时却“以为无极即太极”,主张“盖自无形体之可指而言,则曰无极;自为万化之根柢而言,则曰太极。随其所指,本无差别”。(26)以上参见伊藤仁斎:「読近思録鈔」、伊藤東涯:「太極図説十論」,『日本儒林叢書』第5巻,第2、1頁。由于“周子之意,以太极为气而以无极为理”,故而朱熹的《太极图说解》“以太极亦为理之名”并不符合周子之本意。伊藤仁斋还指出,“班固《艺文志》曰:‘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易疏》曰:‘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亦即汉唐诸儒“以太极为一元气者,乃易之本旨”,由此他认为周敦颐对于太极的解释乃遵从了“汉唐旧注”。相比之下,“朱子之学,本自禅庄来。故以理为本,而以气为粗,为善恶杂。而不知天地间,唯此一元气”,故而朱熹“以太极为理者,乃其臆见,非《易》之本义”。(27)以上参见伊藤東涯:「太極図説管見」、伊藤仁斎:「読近思録鈔」,『日本儒林叢書』第5巻,第1、2-3頁。可见,对于伊藤仁斋而言,至少在解释“太极”这个范畴上周敦颐是接近古义的,而朱熹不但偏离了古义且又曲解了周子之书。
但这并不意味着仁斋父子完全认同周敦颐“无极而太极”这一命题。伊藤仁斋认为:“大传以一阴一阳往来不已为道,而未尝就斯上面论理。盖阴阳二气充满天地,相推相荡。万古不已,不知谁使然,即所谓道。倘于一阴一阳往来不已之前求理焉,则老庄虚无之说,非圣人之旨也。”伊藤东涯亦指出:“古者圣人之所以论天道者,至于‘乾元资始,坤元资生’而止。自是以上,本无其说。其所谓太极者,亦唯言‘元气’耳。而周子于其上面,求所以然之故。而曰:‘无极而太极。’今审‘无极’之言,本出于《老子》。圣贤之书,未尝言及也。”(28)以上参见伊藤仁斎:「読近思録鈔」、伊藤東涯:「太極図説管見」,『日本儒林叢書』第5巻,第2、4頁。对于道(天道),仁斋父子所关注的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循环往复这一现象,并不着意此种现象缘何存在。在他们看来,讨论元气背后的“所以然之理”——“无极”,既缺乏儒家经典上的依据,又容易与佛老虚无之说相混淆。仁斋父子以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来把握道(天道),显示出与周敦颐在终极关怀上的巨大差异。(29)古义学派对道(天道)的这种把握,伊藤仁斋在《语孟字义》中有更详细的阐述。比如:“盖天地之间,一元气而已。或为阴,或为阳。两者只管盈虚消长往来感应于两间,未尝止息。此即是天道之全体。”参见伊藤仁斎:「語孟字義」巻上,『日本儒林叢書』第6巻,第4頁。这自然导致他们无法接受周子之书中随后出现的“无欲主静”命题。
朱熹在《太极图说解》中曾就周子的“主静”如此注解道:“圣人全动静之德,而常本之于静也。……静者诚之复,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无欲而静,则又何以酬酢事物之变,而一天下之动哉!故圣人中正仁义,动静周流,而其动也必主乎静。”(30)朱熹:《太极图说解》,《朱子全书》,第13册,第75页。对此,伊藤东涯认为周、朱“以无欲主静为学之根本”让人难以理解,因为“易之取象也,阳为善、为君子。阴为恶、为小人。……易之所云复者,贵‘阳’之复也”,即《周易》所讲的“复”并非归于“阴”与“静”,而是归于“阳”与“动”。在他看来,二程“以动之端为天地生物之心,真合《周易》贵‘阳’之意”,他们不言《太极图》,正因为深知“贵乎静”的思想出自老庄之学,与《周易》之旨相背驰。既然“主静”不合“天地生物之心”,与表现为阴阳二气交互变化的天道相背驰,那么“无欲”显然是毫无意义的修养工夫与境界。因而伊藤东涯指出,以无欲为作圣之功,始见于周子之书;但儒家圣贤之书未尝有无欲之说,只是主张对于欲望“必制之有礼有义”。(31)以上参见伊藤東涯:「太極図説管見」「通書管見」,『日本儒林叢書』第5巻,第4、5、9頁。
伊藤东涯关于无欲之说的批判中,十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周敦颐所论之“欲”内涵的界定。为此,他首先引入了这样的观点:“解者云:‘所谓欲者,谓人心之流于恶者。若夫耳目口鼻之欲,乃人心之必不能无者。周、朱之旨,岂欲使人绝灭之,如枯木寒灰之无复生意也哉?唯其淫邪非僻,败度乱礼,名之曰人欲。周子所谓欲者,乃指此耳。’”此“解者”指谁,伊藤东涯在文中并没有进行说明,但毫无疑问此解者维护了周、朱之说的正当性,为“无欲”的含义进行了辩说,认为周、朱只是想让人消除“淫邪非僻,败度乱礼”的那种欲望,即“人欲”。若联系上文朱熹对“欲”和“人欲”范畴的不同所指,可以知道,解者之诠释至少是比较符合朱熹本意的。但伊藤东涯并不同意这种对周、朱本意的辩解。他认为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说中的“欲”,正如朱熹集注所示,乃“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而周子所作《养心亭说》,正引用了孟子提出的“养心不止于寡而存尔,盖寡焉以至于无”这一主张,故周子所谓“欲”,就是指“声色臭味人心所必有者”,而不是指“淫邪非僻之欲”。这种无欲境界,与“反观内省,游心于虚无冲淡者”相同。伊藤东涯强调,如果孟子所说的“欲”是指“淫邪非僻之欲”,那么孟子无异于容人作恶,这就与庄周所谓的“为恶无近刑”类似,孟子定非此意。故而,无欲之说“不可以为训也”。(32)以上参见伊藤東涯:「太極図説十論」,『日本儒林叢書』第5巻,第14頁。
伊藤东涯通过辨析“欲”字在儒家古典中的含义,判定它就是指人必然具有的欲望,否认了解者所代表的观点,以此驳斥周敦颐的无欲之说。但需要指出的是,伊藤东涯虽然引出了“唯其淫邪非僻,败度乱礼,名之曰人欲”这一说法,但古义学派在其自身的概念体系中,并没有将“欲”和“人欲”作为不同范畴加以区别。伊藤东涯《通书管见》中即云:“盖人之有欲也,犹水之有流也。……圣人之以礼义治人欲,尤导水而由其道也。夫所谓欲者,将指何耶?不过曰饮食男女、居处衣服而已耳。”(33)伊藤東涯:「通書管見」,『日本儒林叢書』第5巻,第9頁。在这里,“欲”和“人欲”无疑是同一范畴,都指代人所必有的生存欲望。不难看出,解者提示的朱熹对“欲”和“人欲”的区分,在伊藤东涯这里被无视了。
古义学派对无欲思想的批判,如上所论,是通过演绎周子之学与儒家经典间的差异以及朱熹对周子本意的“曲解”来展现的。不同于山鹿素行斥周扬朱的做法,古义学派认为周子之学较之朱子之学更接近儒家古典的本意,朱熹在解释上的创新是对传统经典的背离。古义学派对周、朱之学态度的不同,与其尊古而斥理这一学问倾向有关。(34)伊藤仁斋排斥“理”这一范畴,在其《语孟字义》一文中专设“理”这一条目进行了辨析。他认为圣人曰“天道”不言“天理”,以理为主则必归于禅庄。参见伊藤仁斎:「語孟字義」,『日本儒林叢書』第6巻,第16-18頁。古义学派后世门人原田直曾给出精当的总结:“周子之学,虽不能无诡乎圣道,而厥于旨趣,稍为近古。程朱虽有所本,而其所主者,专在理也。”(35)原田直:「通書管見跋」,『日本儒林叢書』第5巻,第1頁。显然,在古义学派眼中,“主理”的朱熹不但误解了圣人之旨,也曲解了更为接近圣人之旨的周子之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伊藤东涯提请人们要注意宋学内部的差异,指出“大抵周程张朱,虽同为伊洛之渊源,而其所立说各自不同”,(36)伊藤東涯:「古今学変」,吉川幸次郎、清水茂校注:『伊藤仁斎·伊藤東涯』(日本思想大系33),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第488頁。但在对无欲思想的批判上,仁斋父子自身都没有很好地区分周敦颐与朱熹之说的差异,而是将二者一并归入无欲论的范畴。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对“欲”和“人欲”的区分以及不主无欲的思想,更是未能反映在古义学派的著述中。
四、无欲思想批判的扩大
自山鹿素行与仁斋父子对无欲之说进行指摘以来,古学派内部肯定情感欲望价值的呼声不绝于耳。其中尤以古文辞学派的荻生徂徕(1666—1728)与其门徒太宰春台(1680—1747)的主张最具代表性。但他们的立论依然无视朱熹对于“情”“欲”“人欲”诸范畴的区分,而是在混用这些概念的情况下展开他们的批判。荻生徂徕运用其古文辞学的方法考究了《礼记·乐记》中“人欲”一词的内涵,对于程朱的人欲说提出了如下意见:
天理人欲,出于乐记,而程朱失其义者也。……人欲者,人之所欲也。曰:‘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又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又曰:‘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由是观之,人欲者,人之所必有,而不可去者也。程朱乃言人欲净尽,而天理流行,妄矣哉。(37)荻生徂徠:「蘐園十筆」,『日本儒林叢書』第7巻,第183頁。
天理人欲,出乐记。……所谓人欲者,即性之欲也,即好恶之心也。味其文意,唯言礼乐以节耳目口腹之欲而平其好恶而已。初非求人欲净尽也。(38)荻生徂徠:「辨名」,吉川幸次郎、丸山真男など校注:『荻生徂徠』(日本思想大系36),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第246頁。
荻生徂徕认为《礼记·乐记》所言“人欲”是指“人之所欲”“性之欲”“好恶之心”“耳目口腹之欲”,故程朱在修养方法上要求人们去除人欲是荒谬之论。当然,从《礼记·乐记》自身文脉来看,将“人欲”看作人应接事物时无法避免的自然欲望,这种理解并无不妥。但以《礼记·乐记》中的这种“人欲”概念来攻击程朱理学中的人欲说,实际上是无视了学说本身的发展史。因为程朱的人欲说,尤其是朱熹之论,已经超越了《礼记·乐记》中“人欲”范畴的规定性,形成了新的关于“情” “欲”“人欲”等概念的体系化诠释。荻生徂徕的批判胶着于“人欲”字眼的古典内涵,否认了儒学概念细分与延展后的时代价值,于是程朱的人欲说就被其视为一种禁欲主义。如果他能够运用古文辞学方法细心体察朱熹对于“欲”和“人欲”的不同用意,那么他对朱熹人欲说的误解或将改观。但追求文辞古典内涵的学问倾向在观念上限制了荻生徂徕对“人欲”新意蕴的认可,结果以程朱人欲说背离先王之道的看法在古文辞学派内部沉淀。这种误读在徂徕弟子太宰春台那里有进一步的扩大。
与荻生徂徕一样,太宰春台也以“人欲”在《礼记·乐记》中的文脉内涵来批判程朱。在他看来,“灭天理而穷人欲”一语之所以会在《礼记·乐记》中提出,是因为古代君子以礼乐养性,舍礼乐则无养性之具,亦即礼乐作为节制人欲的工具,废礼乐则人欲必恣。但程朱误解了此语,“直以天理为人性之体,以人欲为性之妨碍,主张遏绝人欲以存天理”。太宰春台认为这是模仿佛教“断无明、显佛性”而所立之妄说,其实《礼记·乐记》并不以人欲作为性之妨碍,而只以“灭天理,不养性,穷人欲”为罪,人欲虽各种各样,但以饮食男女之欲为重。他指出:“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大欲,圣人凡夫并无不同。一切生者,不能离此大欲。……圣人之道,决无绝人欲之事。若为绝人欲之道,则无夫妇婚姻之礼。程子、朱子亦有妻儿,其遏人欲之工夫,在何处耶?《乐记》所言人欲,乃人必有之情欲。”(39)太宰春台:「聖学問答」,頼惟勤校注:『徂徠学派』(日本思想大系37),東京:岩波書店,1972年,第105-106頁。太宰春台以孔子曾言饮食男女之大欲,并追问程朱若能遏制人欲则为何亦有妻儿,此番论说可谓辛辣。但朱熹从未要求人们去除“饮食男女之欲”,只是指出其存具可使人入“危”的一面,如他与门人的这段对话:“问:‘人心、道心,如饮食男女之欲,出于其正,即道心矣。又如何分别?’曰:‘这个毕竟是生于血气。’”(40)《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朱子全书》,第16册,第2666页。这和太宰春台所指出的《礼记·乐记》以“穷人欲”为罪,在警醒世人方面可谓旨趣相通。然而太宰春台却彻底否认程朱人欲说的合理性,显然与荻生徂徕一样他也把儒学范畴在后世的演化看作对古典真意的背离,也把“欲”“人欲”“大欲”等概念视为同一范畴。于是,程朱要求人们遏制不正当欲望的“灭人欲”“去人欲”之说,再次作为禁欲主义受到猛烈批判。
当然,除了在概念理解上存在差异这一原因外,太宰春台非难程朱的理由还在于他认为先王之道讲求“以礼制心”,并非佛道式的“以心制心”,而程朱的人欲说正是对佛道“以心制心”修养论的模仿。为此,他以“见色”取譬,比较了儒佛两道在规制欲望上的不同,指出在圣人之道中,“见他人之妻女,心中觉其为美女而悦其色,若身不行非礼之事,则为守礼之君子。此为‘以礼制心’”。“以礼制心”旨在以礼乐规范行为,而“不问心目之罪”;佛道却是“专务治心,即便不行背离法度之事,苟心有不善,即以之为罪。虽见毛嫱西施,则闭目以之为腐肉朽骨,以此禁其欲”。他据此认为注重“心法”的宋明理学正是受到了佛教“以心制心”方法的影响,指出“凡儒者言心性,始于邹人孟子,至宋儒盛也。程氏、朱氏为魁首,而二氏皆以心法为学”,都是阳儒阴佛。(41)以上参见太宰春台:「聖学問答」,『徂徠学派』,第126、175-176頁。太宰春台把程朱人欲说等同于佛教的灭欲论,以心法为佛门工夫,否认理学所重视的内心修养,并由此将整个宋明理学斥为“阳儒阴佛”。这种批判较之于山鹿素行与仁斋父子给出的有褒有贬之评价,显示出彻底否定理学价值的态度。可以说,日本古学派对无欲思想的批判到太宰春台这里已经到达了一个顶峰。
太宰春台以程朱漠视礼制当然是偏颇之见,但我们在此需要探讨的并非太宰春台与朱熹在礼学思想上的差异,而是日本古学派为何整体性地误读了朱熹的人欲说。
五、朱熹人欲说被误读的历史文脉
从文本诠释的规律来看,一种话语在流播过程中其原本的规定性往往并不容易得到传递,这是因为构成读者“前理解”的诸条件并不一致。文本的作者与解释者即便生活在同一文化地域,文本与解释也有可能出现差异,更何况一种经典在不同时空的异域传播,其过程更容易衍生新的理解。中国儒学经典在日本近世的容受正体现了话语流播的这种规律。在古学派批判朱熹人欲说之前,日本早期朱子学者与阳明学者关于“人欲”与“无欲”就已给出了相当特性化的解释。
比如被誉为近世儒学之祖的藤原惺窝(1561—1619)在《千代茂登草》中就“人欲”指出:“人出生以降,人欲存焉。欲心深切,迷于所见所闻。人欲盛,则明德衰。形虽为人,心同禽兽。”(42)藤原惺窩:「千代茂登草」,国書刊行会編:『続々群書類従第十』,東京:平文社,1969年,第30-31頁。这种主张看似与朱熹人欲说不相违,但实际上没有体察朱熹关于“赤子之心”与“人欲”关系的论说。朱熹讲“赤子之心”注意到了作为人出生之后最初状态的“赤子”这一存在,曾与门人有如下对话:
问:“赤子之心莫是发而未远乎中,不可作未发时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有未发时,也有已发时。今欲将赤子之心专作已发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发时,亦与老稚贤愚一同,但其已发未有私欲,故未远乎中耳。”施问:“赤子之心。”曰:“程子道是‘已发而未远’。如赤子饥则啼,渴则饮,便是已发。”(43)《朱子语类》卷五十七,《朱子全书》,第15册,第1831-1832页。
在朱熹看来,赤子之心也存在“未发”与“已发”。“已发”的表现如“饥则啼,渴则饮”,但“其已发未有私欲”,“未远乎中”,亦即人尚为赤子时并不存在所谓“人欲”。但藤原惺窝的人欲说并没有像朱熹那样去关注赤子之心,且仅从字面来理解,他的上述主张还可以被解释为:人自出生,人欲即已存在。这种直观理解虽然不一定就是藤原惺窝的本意,但也是一种容易产生的认知。由此来看,藤原惺窝的人欲说是一种未考虑欲望多样性、且易引发误解的主张,它只是表明要警惕人欲之害。朱熹对于“饥则啼,渴则饮”等本能欲求的辩证态度未能在藤原惺窝的人欲说中得到体察与传播。这种缺失也并未在其身为幕府儒官的弟子林罗山(1583—1657)的人欲说那里得到弥补。
林罗山在说明何谓“人欲之私”时指出:“所谓人欲之私者,即目之见色而生欲;耳之闻声而生欲;鼻之嗅香而生欲;口之尝味而思食。”(44)林羅山:「春鑑抄」,石田一良、金谷治校注:『藤原惺窩·林羅山』,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第125頁。这与朱熹关于人的目耳口之生理机能的见解不同,朱熹认为:“人心是知觉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底,未是不好,只是危。若便说做人欲,则属恶了,何用说危?”(45)《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朱子全书》,第16册,第2668页。他只是把知觉器官感受外在刺激时的自然反应作为“危”的状态,并不将其等同于人欲,而只有当这种自然反应流溢失节,与天理相违时,才构成人欲。朱熹还以饮食行为作比指出,“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饥欲食、渴欲饮者,人心也。得饮食之正者,道心也”。(46)《朱子语类》卷十三、七十八,《朱子全书》,第14册,第389页;第16册,第2666页。但朱熹所指出的这种欲望的正当性却被林罗山忽略,林罗山将“尝味而思食”这一身体自然反应也归入“人欲之私”的范畴,由此,朱熹关于欲念所讲的“人心”便被林罗山替读为“人欲”。
在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前人研究中,常列举山崎暗斋(1618—1682)作为演绎朱子学严格作风的典范。(47)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37頁。但从上述例子不难看出,对自然欲望秉持严格主义的倾向在藤原惺窝、林罗山之时即已显露,并且是以超出朱熹思想的严格形态来展现的。这种对欲望的极度警惕或正反映了乱世初定期日本儒者对人向善本能的悲观,他们无法同朱熹那样“对人的纯善的本性(理)抱有绝对的信赖”,(48)关于林罗山对人类情感流向恶之可能性的强烈危机意识与时代成因的分析,可参看龚颖:《“似而非”的日本朱子学:林罗山思想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115-118页。于是聚焦于演绎人欲之害和劝诫世人,而忽略了朱熹对“欲”“人欲”的区分和对正当欲望的认可。
在表现对人欲的严苛性上,近世初期朱子学者的主张确实具有代表性,而同一时期其他学派儒者亦有类似倾向。日本阳明学之祖中江藤树(1608—1648)与其弟子熊泽蕃山(1619—1691)对于“人欲”的排斥程度甚至强于同期朱子学者,这集中体现在他们的著述中频频出现的“无欲”字眼和对无欲境界的推崇。中江藤树认为,“欲”和“无欲”的区别不在于所行之事的内容,而在于行事时的内心——一种使“洁静精微之神理”得到明净,符合“其事时中之天理”的状态,即如《周易》艮卦辞中“止所艮背不获身,上下敌应不相与”所表述的那种圣人行事时平静无欲的状态,尧舜禅让、汤武放伐都是出于此心。不同于佛教以释迦摩尼不就王位、唐代庞蕴舍弃家财这种拘泥于外物而本质仍是“谋利之私”的“无欲”,圣人之心对于天下万事“不论大小高低,清浊美恶,丝毫没有好恶选择之心”,只是满腔大中至正的神理。倘若释迦摩尼悟到此心,则其必以王宫为灵山,以天子位为摩尼轮,以礼乐刑政为说法,不会厌弃王宫而入山。中江藤树从心学出发,把明明德、合乎中节等德目作为儒家论无欲的关键,以此区别于佛道弃绝尘世的无欲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江藤树所讲的无欲境界由于强调心之状态,不拘泥于事物内容本身,因此较之于佛教清苦主义式的无欲似乎更为宽容。但正如他认为“君子明明德,不为习气所染,无丝毫人欲,当然无酒色财气之惑”,(49)以上参见中江藤樹:「翁問答」,山井湧など校注:『中江藤樹』(日本思想大系29),東京:岩波書店,1974年,第147、148、174頁。《周易》艮卦辞见第148页头注“艮背敌应不相与”。这种描述表明中江藤树依然对人的感性欲求显示出极大警惕。
作为中江藤树的弟子,熊泽蕃山也极力渲染无欲的价值,特别是其对于政治的神奇功效。他首先指出无欲是人的固有本性:“为人者,固有无欲之性,知晓无欲之理。然若以欲为心,则不异于禽兽。”进而提出无欲是政治上无为而治的根本。在描述无欲而治的政治理想时,熊泽蕃山对无欲进行了极为乐观的推演。他在《集义和书》中有两处论述描述了为政者与万民皆无欲时的太平图景:
在上者无欲,不蓄积财物,则财用自然散于下民,下民之心自然服于上。人心归服,则益莫大于是。以无欲无虚饰为素朴,此为上古风俗。如此,则不治而天下平。此时,天气和顺五谷丰登。故,民无不仁。人人无欲且知足,则乱由何处生?盗贼从何处起?
俭约之本乃无欲。上无欲则事寡,喜无事者不贵财。不贵财则不集财,财散之于天下,民亦不以之为财。不以之为财,则无相争之事。……如此之时,刑政无所用,垂衣裳而天下治。此为礼乐之质也。
熊泽蕃山既把无欲看作是内心修养的重要方法,又把它视为治理天下的不二法门。他提出的“心法、治道皆始于无欲”之命题就充分说明了无欲在其学问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熊泽蕃山的无欲论在根源上虽然受到了道家清静寡欲思想的影响,如其所言“我亦黄老学者,希望清静少欲之事。不贪荣利,皆圣人之一端”,(50)以上参见熊沢蕃山:『集義和書』,後藤陽一、友枝龍太郎校注:『熊澤蕃山』(日本思想大系30),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第110、114、180-181、114、180頁。但道家之说被他吸纳进儒学的政治论中,二者糅合转化为一幅为政者以无欲来平治天下的美妙图景。
藤原惺窝、林罗山、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作为日本近世前期代表性儒者,在各自的学问立场上对“人欲”与“无欲”进行了阐发。虽然分属日本朱子学与阳明学阵营,但作为宋明理学在日本近世的重要引路人,他们共同演绎了对欲望的严格主义。尤其是藤原惺窝和林罗山,他们因严格主义而错失完整地传递朱熹关于“欲”和“人欲”的精微之论与相对宽容的主张。此四者以及本文未做展开讨论的山崎暗斋等对“人欲”“无欲”的诠释,构成了之后日本儒者认识理学的严格主义的基础。
面对早期儒者构筑起的严苛理学意象,稍后登场的批判者们亦难区分宋明理学各流派在人欲思想上的差别,尤其是对此差异的关注还会受到个体对理学拒斥程度的影响。如上文所论,对朱熹尚存敬意的山鹿素行看到了周朱之异,而彻底否定宋儒的太宰春台则直接把程朱人欲说视为佛教灭欲论。捎带一提,在反儒学的日本国学那里甚至还出现了此种偏激之说:“异朝之书不论何种书籍,总是严格议论人之善恶,于事物之理则故作高明。”(51)本居宣長:「紫文要領」,大野晋、大久保正編集校訂:《本居宣長全集》第4巻,東京:筑摩書房,1969年,第29頁。日本国学正是深受荻生徂徕与太宰春台人欲(人情)说影响的学派。在日本古学派与国学派强调情感欲望之价值、脱“理”而主“情”的过程中,宋明理学内部各版本人欲说之间原本就不甚清晰的思想边界被不断消解,成为同质性的严格主义或禁欲主义。
综上所论,日本古学派以“无欲”“灭欲”作为批判朱子学的重要标签。在他们的话语中,朱熹并不主张无欲的思想始终是被忽视的。相比起《朱子语类》,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等著述与朱熹的《太极图说解》成为古学派体认朱熹人欲说的主要线索和进行无欲思想批判的对象。本文所考察的山鹿素行、古义学派的仁斋父子、古文辞学派的荻生徂徕与太宰春台,虽然常被称为反朱子学的古学派儒者,但他们对于宋儒的态度并不一致。既有褒朱熹而贬周敦颐者,也有褒周斥朱者,甚至出现了把整个宋明理学斥为“阳儒阴佛”的主张。古学派内部围绕人欲说出现的这种差异往往被我们所忽视,正如朱熹对“欲”与“人欲”之分辨与不主无欲思想被日本近世所忽视一样。
由此反观日本近世早期的朱子学者可知,他们绝非如哲学史家井上哲次郎与丸山真男所说,“其学问停留于对朱子学说的忠实介绍”。(52)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33頁。刚好相反,有观点认为藤原惺窝一开始便非纯粹的朱子学者,林罗山“在思想上并不注重朱熹的文献”。(53)土田健次郎:《近世日本的朱子学与反朱子学》,吴震主编:《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311页。但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进行了漏读或误读,他们的学说均演绎出了不同于朱熹思想本身的特性,其所展现的朱子学成为此后日本儒者理解宋明理学的重要基础,古学派忽略朱熹人欲说的精微之处便与此种历史语境不无关系。当然,从个体层面来看,儒者对人欲说的关注还受到其理学认知及叙事目的的影响,如在彻底反理学的部分儒者那里,把握了理学人欲说的大致轮廓就足以支撑其人情论的展开,而宋儒理学内部人欲说的差别则被弃之身后。然对于今天的中日儒学比较研究而言,这些细节恰恰最能反映中国儒学在特定异域时空中的境遇。因此,当我们运用广义朱子学视角抽取了某种整体性脉络后,不该忘记看似同质的对象内部还存在着许多不可忽视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