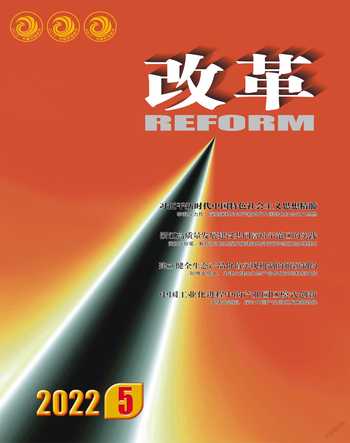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演进逻辑与改革取向
邓朝春 辜秋琴
摘 要: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变迁体现了从重视土地分配公平到注重土地利用效率的转向,是土地的政治、社保和经济功能互动调试的制度表达。未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将在“三权分置”制度框架下朝着弱化非经济功能和强化经济功能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要落实集体所有权,逐步剥离承包地社会保障功能,健全承包地流转交易市场体系,不断创新农地经营模式。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三权分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2)05-0143-12
农村土地具有政治、社保和经济三重功能属性[1]。与迅速、平稳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进程相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遲缓而谨慎,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远滞后于城市土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潜力巨大,据估计,2020—2035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获得总经济潜能的61.3%~68.2%,是未来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2]。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部署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2016年中央提出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办法,深化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探索创新承包地“三权分置”的实现形式。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存在功能超载和效率缺乏等问题,亟须通过改革来松绑减负,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打造成具有确定法律内容和健全权能体系的民事法律权利[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不仅能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和农民收益,而且有利于解决“细碎化”土地经营缺陷,助推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向“适度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模式转变,实现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4]。
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演进历程与逻辑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经历了从重视土地分配公平到注重土地利用效率的渐进演变,是土地政治、社保和经济功能互动调试的制度表达。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实现了承包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并持续进行边际调整,不断朝向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和农民重建土地财产权的方向演进[5-6],最终催生了“三权分置”的制度框架。
(一)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确立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的人民公社体制,它造成了劳动效率的低下[7]。发端于安徽凤阳地区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快速增长,基本解决了农民温饱问题。这种生产经营制度很快在全国农村地区推广并被中央所确认、鼓励和稳定,后来中央提出第一轮承包期结束后再延长30年,而200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为30—70年。
1.“大稳定小调整”与公平取向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初期,土地是广大农民的生存之本,农民与土地的粘连度极高,人多地少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使得“按农村人口均分土地”的承包原则成为必然选择,也就是说农村户口人数与承包地数量是严格对应的,这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承包原则。然而,在承包期内农户家庭的婴儿出生、婚丧嫁娶、家庭成员升学等因素会引起农村户口人数的变动和对应关系的变化,在人地关系紧张的情势下这些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会转化为农村集体和家庭的压力,迫使其调整承包地以保持公平性原则。但是,这种调整不会涉及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变更,因为农村家庭只是要求农村人口与承包地的公平对应,而且大规模调整意味着巨大的调整成本和效率损失,并不能增进多少公平程度;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家庭人口动态与农村土地总量不变的静态始终存在矛盾,从理论上说,一次性调整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因而家庭承包地的调整原则是,在村集体内部实行“大稳定小调整”政策,这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折中做法。从实践经验来看,不同地区土地承包期不一,通常只有1—3年,所以小调整不断,各地承包地调整政策开始分化。
2.公平原则受到侵蚀
“大稳定小调整”政策在承包期上开始分化,且在操作效果上无法实现“按农村人口均分土地”的承包原则。大多数地区调整方式是“增人即增地,减人即减地”,也就是说:人口减少的家庭将按照减少的人口数量划出土地;人口增加的家庭将按照增加的人口数量划入土地;划入土地的总量必定也只能以划出土地的总量为限;人口数量不变的家庭,承包地不变;村集体作为中间方接收土地和分配土地。以上调整方式对公平原则是一种侵蚀,原因如下:
第一,由于既有承包地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承包得来的,并没有将每块地的权属明确归属到每个家庭成员,因而对于需要划出土地的家庭而言,减少一人划出一份土地数量是确定的,但划出哪些承包地是可以选择的。土地肥瘦不均,位置远近不同,经济价值不同,理性家庭将划出劣等土地或“边边角角”土地凑足数量交给村集体,村集体在确认具体的土地权属方面无能为力,调整方式内含着原先的公平原则无法真正实现。
第二,划入土地的家庭面临尴尬的处境。接受价值降级的边际土地意味着接受不公平;不接受则只能向村集体申诉,很难改变被动局面;如果划出土地的总量不够分配时,划入土地的家庭最终不得不在质量和人均土地占有量上遭受双重侵蚀。同样地,对于划入土地的家庭,当在下一次土地调整时角色转换成划出土地的家庭时,他回报别人的选择将是可以预期的,公平性在不断的调整中被改变了原来的含义。
第三,除了划出与划入家庭之间的不公平外,不必调整的家庭也会有不公平感。不必调整的家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家庭人口本身没有变化,另一种是家庭人口本身发生了变化但人口总数不变。对于这类家庭,村集体总人口的增加没有影响其土地占有量,而人口效应完全作用于其他两类家庭,显然从“均分土地”原则来看,村集体人口总量增加意味着人均土地占有量应该下降,因而“大稳定小调整”政策的公平保障功能趋于弱化。
(二)家庭承包责任制朝着效率取向演进
若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而演变,在此过程中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会要求最终以大调整来解决。然而,随着内外部条件的变化,人地关系有所缓和,对基于公平取向的承包地分配方式的调整压力有所减轻;同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经济效率考量日益凸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持续向效率方向演进。
1.内部条件的变化
“均分土地”原则内含着人与地紧密结合和紧张关系。一旦人与地结合方式变得较为松散,紧张关系缓解,“均分土地”的诉求和压力就会下降,再加上土地调整成本较高,寻求对既有承包地的有效利用和优化要素投入组合将会成为家庭经营户的现实选择。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越来越严格的执行,扭转了农村人口过快增长的局面。1984年以后,随着劳动效率的提升、技术进步和农民温饱问题的解决,人与地的緊张关系得到根本缓解,这些内部条件大大减缓了人口对土地政策施加的调整压力。按理说,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土地单产的增加,将促使人口增长的家庭更加努力争取划入土地,但由于土地调整是一项集体行动,存在“集体行动困境”,因而这种争取需付出很高的成本,且不一定会成功。对于人口增长的家庭而言,尽管额外划入的土地会增加家庭作物产出量和经济价值,但是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加强家庭内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能够通过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而获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对土地增量和公平性的诉求。
这种从公平原则向效率原则的转变具体反映在中央政策文件的内容变化上。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和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禁止土地流转交易①,因为交易虽然能够提高效率,但是会导致家庭占有土地量变得不均。由此可以推论,中央此时认为让人口增多的家庭免费获得更多的承包地是合理的,但是通过付费交易从别人手中获得更多的承包地是不合理的,说到底还是均分原则占据主导地位。而到了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社员可以在经集体同意后自找对象协商转包,此时中央已经不再纠结于均分原则,而是转向关注效率,但适用的范围和领域都集中在粮食种植业,当中央鼓励开展多种经营时,这种效率原则就扩展到经济作物领域。
2.外部条件的变化
内部条件变迁对家庭承包责任制效率转向的影响是比较缓慢的,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则促使农村家庭迅速作出反应,改变了承包土地与家庭成员之间的要素投入组合方式,形成了更加多样化的生产经营形式,从此,“承包地如何分配”的问题完全让位于“承包地如何经营”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的兴起、对外开放的加速和城市改革的全面深化等外部条件的变化,为农业人口转入农村工业和流入城市就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大量农业富余人口转入非农就业,急剧地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人口压力逆转为“人口红利”。一方面,部分承包地被国家征用或征收转入非农用途;另一方面,农民家庭与土地的关系逐渐变得松散,承包地对农民家庭的收入贡献不断下降,土地流转不再受到过多限制,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开始出现。200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国家开始立法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到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及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各级政府开始鼓励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对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等进行财政直补,促进了大量的产权组织形式和经营实体的产生。可以看出,从早期关注承包权,发展到关注经营权,再到保护经营权和鼓励“适度规模经营”,党和政府在政策层面及时追踪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效率转向,并加以确认、引导和促进,使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不断更新和完善。
3.家庭土地承包权的稳定
重视经营权的经济效率必定回溯到对承包权进行重新审视,因为经营权是从承包权中派生出来的。如果家庭拥有的承包地和承包权不稳定,土地的经营权如何会稳定?大量学者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经营权的稳定对于土地的产出和投资会有明显的促进效应,因而从经济效率来看,稳定家庭土地承包权是必要的。但真正的问题是,如果获得承包地的家庭由于某些原因,并不将自己不耕种的承包地流转出去而是“抛荒”或低效率使用,这难道也符合效率原则?或者有的农村家庭已经离土离乡落户城市,难道也要保留其承包地而置农村人口增多的家庭无法索取所需要的承包权而不顾?此时中央政策制定者权衡利弊之后,决定稳定承包权,并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来解决家庭对额外土地的需求。1993年11月中央提出第一轮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30年;200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200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第二轮承包到期后耕地的承包期再次延长30年;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并对承包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充分体现了承包权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关于是否要稳定承包权的问题,学术界争议较大,农民群体对此也意见不一。
(三)承包地“三权分置”的实施
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价值必须体现在土地经营权上,中央政策的关注点从承包权转向经营权,最终促使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的出台,中央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并行,由此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进入新的阶段。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充分阐述了“三权”的权利边界以及“三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新增加了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权能内容,丰富和完善了承包地的产权体系,加深了承包地市场化配置程度。201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给予了法律保障。
1.“三权分置”中的新增权能
承包地经济价值的提升,不仅可从“三权”分设中实现,而且可通过在“三权”分设基础上增设新权能实现。“三权分置”制度框架中新设了多项产权权能,具体表现在:第一,所有权中新增了“监督权”,村集体有权对承包农户和经营主体使用承包地进行监督,并采取措施防止和纠正长期抛荒、毁损土地、非法改变土地用途等行为。特别是在承包权人转移进城而流转经营权的情况下,更要强化农民集体对土地使用的监督权,保护农地资源用于农业,维护集体土地权益[4]。第二,承包权中新增了“抵押权”“退出权”“退出补偿权”“社会保障权”等,拥有承包权的农户可以就承包土地经营权设定抵押;可以自愿有偿退出承包地;承包土地被征收的,承包农户有权依法获得相应补偿,符合条件的有权获得社会保障费用等[4]。第三,经营权中新增了“改良土地权”“优先权”“抵押权”等,经营权人经承包农户同意,可依法依规改良土壤、提升地力,建设农业生产、附属、配套设施,并依照流转合同约定获得合理补偿;在流转合同到期后按照同等条件优先续租承包土地;经承包农户或其委托代理人书面同意,再流转土地经营权或依法依规设定抵押等[4]。可以看出,这些新增权能无不指向产权的经济效能,为承包地产权的市场交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2.农地市场化配置程度加深
一方面,“三权分置”及其新增权能的政策设定,促进了全国各地区关于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改革试点或实践的深入开展,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不断地进入各地区改革试点和实践的制度设计中。比如,上海、山东、宁夏、湖北等省(区、市)的部分县(市、区)开展了农村承包地退出试点①,退出权的制度设计都坚持了市场化导向。
另一方面,“三权分置”最为重要的政策效应体现在,它催生了各种探索土地有效利用的新型组织形式和经营实体,极大地促进了农村承包地流转交易。从流转耕地面积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比重来看,1996年全国只有2.6%的耕地发生了流转,2006年为4.6%,2010年上升至14.7%[8],2014年则达到30.4%②,2018年跃升至37%左右,农村土地市场化配置的规模跃上新台阶。截至2021年4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到225.9万家,联合社超过1.4万家③。返乡创业、工商资本下乡等促进了土地、资本和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深度结合。土地流转产生了股份制、信托制、托管制等新的经营模式和服务模式,农村土地市场化配置程度向纵深方向发展。
二、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面临的约束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焦点已从当初的强调土地分配公平转向关注土地利用效率,但由于被赋予政治和社会保障功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要受制于前置性制度和配套性制度安排的约束;同时,拥有农村承包地所有权的农民集体也面临着产权利用的交易成本高和土地流转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这些因素都会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构成约束。
(一)农村承包地制度改革的底线约束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提出“守住政策底线”: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前文分析指出了国家强调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稳定性所蕴藏的经济效率追求,然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稳定性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9]。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形式,是实现农民当家作主和共同富裕的制度性保障,是防止工商资本下乡后控制土地要素等其他生产要素的重要制度条件。
从理论上讲,农村土地产权承载着国家公权属性,而非纯粹的民法私权。忽视土地的公权属性,容易导致土地私有化的偏狭观点和操作:认为要想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借助欧美经验,走土地私有化改革道路,通过明晰个人产权,实行一次彻底的大变革[10]。这种观点错误地把土地问题完全还原为经济问题,忽视了土地的政治功能和历史观意义,忽视了中国的国情。产权制度设计内含国家与农民关系建构的基本原则[11],单从私权角度来看,农村土地走市场化道路无法保证集体所有制不被侵蚀或瓦解,国家意志不得不介入,对自物权的经济效率和市场化的自由度规定一个限度,即农村土地要素配置变化不得动摇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不能动摇的底线约束。
(二)农村社保制度发展滞后及对土地保障功能的依赖
农村土地为农民提供了基本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12]。土地对农民具有重要的福利保障功能,是以往农地制度安排的基调[13],也是国家对农民群体缺失社会保险制度的一种应对措施。社会保障功能旨在追求社会公平,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人有份、均等享有”和“限制性市场流转”[14]。这妨碍了经营权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导致了效率损失。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与经济功能之间存在冲突,且难以兼容[3],制约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
按照實物保障的基本含义,随着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增加,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农民承包户会减少对土地的依赖,土地的保障功能会趋于弱化,承包地就会获得更大的配置自由。但现实中,农民存在“迷恋”土地保障功能的现象。2018年,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高达2.88亿,其中7 533万农民工已在城镇稳定就业,但83.6%的农民工希望进城后能定居并保留承包地。社会保障对土地保障的替代效应主要作用于高土地依赖型农户,对低土地依赖型农户的影响不显著[15]。年收入高于5万元的农户群体中有72.63%的农户认为农地是一种保障,年收入不足5万元的农户群体则为52.41%,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认为土地是保障的比例反而越高[16]。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村集体土地已经从基本保障工具转变为最为重要的市场要素,但农民对土地保障功能的“眷恋”限制了土地作为市场要素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基于社会保障价值取向的土地制度安排导致了土地的“细碎化”,非农就业和收入的增长降低了土地抛荒和粗放经营的机会成本,在土地产权界定不清和保护不力的情形下,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会受到抑制。这也预示着当前改革试点地区以“土地换社保”“承包权设定抵押担保”“承包地有偿退出”等制度设计内含阻力和风险,剥离承包地社会保障功能可能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影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
(三)农村土地流转交易机制不健全
非农就业造就了农村承包地流转的供给主体,土地规模经营与集约经营收益催生了需求主体,在供求双方的作用下承包地流转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创造新业态提供了条件,较自由的土地流转具有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12],我国农村承包地流转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土地流转交易机制不健全,土地流转交易市场仍然是一个“过渡性市场”,呈现不完全市场形态,具有有限性、渐进性、调适性和稳定性特征[17]。
1.农村承包地流转的交易成本过高
科斯认为:“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去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合约,督促合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18]一般而言,交易成本包括搜寻成本和信息成本、谈判和签约成本、监督成本等。
一是搜寻成本和信息成本。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并不存在组织土地流转的市场平台或中介组织,具有土地流转愿望的供求双方不可能在大范围内对接,或者对接所需要投入的搜寻成本和信息成本太高,以至于转出承包地农户不得不在熟人农户群体中寻找需求者以节省交易成本,而熟人之间的土地流转带有强烈的社会伦理色彩,并不是纯粹以经济效率为目标,他们之间形成的合约大多以口头协议为主,形成典型的“关系型合约”。合约关系不规范、不稳定,严重影响了土地的投资预期和土地的有效使用。
二是谈判和签约成本。工商资本下乡和农民返乡创业,为农业发展和规模经营创造了机会,各类经营主体对大面积土地的租赁需求不断增长;土地租赁合约涉及大量土地相邻的农户或村庄,协商和签约成本是决定合约能否达成的重要因素。由于农户对土地经济价值评价和期望并不相同,逐一谈判和签约成本高昂,甚至存在村民“敲竹杠”的行为。为了降低此类成本,需求大面积土地的个体或企业不得不求助于当地村干部作为中间人或担保人来达成协议,甚至直接与村委会签订流转协议而不直接面对村民群体,形成一种“非标准化合约”,这不利于市场交易的规范化运行。
三是监督成本。流转合约签订之后,需要投入成本来监督合约的执行:租金是否按约足额支付,土地是否改变用途,环境安全是否得到保证,等等。无论是由村委会还是村民自身实施监督,都需要投入成本。村民群体监督本身存在“搭便车”问题,而如果村干部倾向于维护经营者的利益,则会出现监督失效问题,妨碍土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展。
2.价格机制(租金机制)作用有限
价格机制包括价格生成机制和价格响应机制[19]。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市场越成熟,价格机制(租金机制)越能有效引导土地流转交易,而现实中,由于市场范围狭小,交易主体过少,市场竞争性不够,难以形成竞争性均衡,限制了价格机制(租金机制)的有效作用。
在農村的“熟人社会”中,村庄生存伦理、家族关系和村落共同体传统等“非正式制度”限制了价格机制(租金机制)的作用。亲友、邻居等社会关系亲近的群体间达成的契约具有口头性、短期性特点,流转租金也非市场化条件下的均衡租金[20]。2005—2015年,我国农地流转率以平均每年20.53%的速度提升,但实际发生的农地流转主要为“村落里的熟人”间的关系型流转,总体上并非由价格诱导的市场型流转,发生于亲友邻居、同村普通农户之间的农地流转合约占全部农地流转合约的比例高达88.48%[21]。
如果以资源是否掌握在利用效率更高的主体手中作为市场运行效率判断的基准,那么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呈现的“高租金”与“低流转”①表象背后,隐含着“有价无市”的市场失灵现象。潜在转出农户对农地的多重依赖和多维价值评价引发农地“价格幻觉”,大大降低了其参与农地流转的可能性;流转双方对农地价值的评价差异,表明农地流转的价格生成及其响应逻辑与一般物品存在差异[19]。由于农地“价格幻觉”有随着农户非农转型而不断增强的趋势,因而以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推进农地流转的意图和政策可能效力有限。
三、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的地方实践
在“三权分置”框架下,全国各地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为基础展开了各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改革与探索,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经营模式,以适应当地具体的内外部环境与实际需求,比较典型的经营模式有广东的“南海模式”、贵州的“塘约模式”、湖南的“沅江模式”和四川的“崇州模式”等。这里以这四种模式为基础来分析和比较其产权结构、运行特征和适应性效率。
(一)“南海模式”
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在广东南海地区兴起。乡村工业化、城镇化与土地租赁市场的兴起,为当地农村土地带来了巨大的升值空间,为农村土地“非农化”提供了机会;集中分散的家庭经营的土地由村集体统一经营,是土地租金收益最大化的选择,它是对外部市场经济带来的潜在利益的积极反应,是典型的诱致型制度变迁。“南海模式”的特点重在“统”,是名副其实的集体所有制下集体统一经营模式,各家庭以承包地入股形式成立土地合作社,集体积累股为51%,社员分配股为49%,由合作社整合规划土地生产经营,在保证农业生产的同时,重点发展二、三产业,从而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和价值的最大化。显然这种模式适用于经济发达地区,在苏南地区、上海郊区和浙江杭州地区比较流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则不大适用。
但是,“南海模式”为重建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提供了一种创新探索。2015年以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取得良好成效,2017年全区村(居)集体在不含土地折价的情况下资产总额达到411.51亿元[22],其成功经验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为“三权分置”框架下的土地经营制度改革提供了样本参考。
(二)“塘约模式”
相较于发达地区的“南海模式”,贵州安顺的塘约村为欠发达地区或贫困地区农村重建集体经济组织从而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提供了新的思路。村委会通过将全村的集体资产、机动地和自留地以股份形式量化到集体成员,按照“合股联营、村社一体”的思路成立“金土地合作社”,合作社按3∶3∶4的比例给合作社、村委会和农户分红,而农户的40%按照土地入股的比例分红。全村325.4公顷土地在村集体的统一规划下实行集约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经营,同时在政府的帮扶下开展多产业联合经营,探索出一条新型农业集体化和乡村社会再组织的道路。2013年塘约村人均收入不足4 000元,而到2018年人均收入跃升至14 120元;村集体经济2014年不足4万元,2018年则突破312万元[23],形成了有名的土地经营模式——“塘约模式”。
可以看出,“南海模式”的成功在于充分利用了外部市场,而“塘约模式”的成功在于外部力量(政府)的帮扶。塘约村作为贵州省乃至国家重点打造的试点村庄,接受了大量的资源和项目[24],因而有学者认为其实践意义较为有限。这种观点过于悲观,欠发达地区或贫困地区的集体经济组织,在初始阶段借助外部支援扶助,而后再推向市场竞争,未必没有自生能力。奥斯特罗姆指出,产权结构设计、制度执行与监督规则合理的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克服“公地悲剧”,实现有效运作。
(三)“沅江模式”
客观而言,我国许多的农村地区并不具备重建集体经济组织的条件,因为设立组织、运行组织和改变组织都涉及巨大的交易成本问题,其中特别是激励问题和监督问题。如何解决土地细碎化,实现规模经营以及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湖南沅江市探索出另一种土地经营模式,即“土地信托”:初级形式的信托模式主要针对不愿耕种或无力耕种的农户,将他们的土地委托给新的经营主体代管代种,这种模式组织化程度不高,在四川乐至县也较为流行。组织化程度很高的高级信托模式是2010年由沅江市政府主导,成立土地信托公司,吸引大量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公司利用财政资金或支农资金将土地进行规划整治后,作为中介人或担保人将土地流转给种植大户或外部投资者生产经营。同时,为响应土地规模经营所形成的社会化服务需求,全市成立农业产业化服务组织、农机租赁公司和劳动服务公司,为各种经营主体提供社会化服务。可以看出,政府介入大大降低了土地流转交易成本,并实现了农业规模经营和产业结构调整,是小农户参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生产经营的有效形式。
“沅江模式”取得了较好的示范效果。截至2014年,全市农村土地流转面积2.82万公顷,耕地流转率达到51.4%,其中农村土地信托流转面积5 500公顷,信托储备土地1 066.7公顷,引进规模经营农业企业115家。全市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社400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68家(其中省级8家),种养业规模经营户6 000多户,带动农户10.46万户[25]。
(四)“崇州模式”
“崇州模式”兼容了以上三个模式而独具特色:借鉴“南海模式”和“塘约模式”中的土地入股成立合作社,但它不是整村入股而是坚持自愿原则(外村农户也可以入股);它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非农产业或政府扶助项目而是农业产业;在规模经营过程中借鉴了“沅江模式”中的土地托管和社会化服务,解决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问题,但中介不是政府而是合作社,它更具市场化特征;最具特色的是合作社经營者是职业经理人,完全按照现代公司形式设立,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建、共营、共享”的新型经营格局。“崇州模式”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土地经营模式,它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前提,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农户为核心主体,以盘活农地经营权为线索,实现了农业经营的规模化、专业化和组织化[26]。
崇州的“共营模式”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认为这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与示范意义。同时,不少地方政府也开始借鉴“崇州模式”,比如大连市创建农业共营制试点5个,组建村级土地股份合作社11家,入社农户3 681户,入社面积1 161.2公顷,正在组建中的村级土地股份合作社15家、农业综合服务超市5家[27]。2018年,崇州市五星土地股份合作社被评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取向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存在功能超载和权能缺失等问题,未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将朝着落实和完善“三权分置”的方向探索推进。具体而言,要落实集体所有权,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等配套制度,健全承包地流转交易市场体系,创新农村土地经营模式。
(一)落实集体所有权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耕地保护是深化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坚守的“底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必须能够确保耕地得到严格保护和有效利用。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中可能出现的流转合同纠纷、农地破坏、农地经营“非农化”和“非粮化”、农业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需要集体所有权去承担相应的监督和管理职能[28]。落实集体所有权,一要落实集体所有权的归属主体,二要落实集体所有权的具体权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在村一级设置了两类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的机构——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意图摆脱所有权主体“虚位”问题。由于村民委员会是公法人,由其代表行使属于私权的集体所有权,容易诱发公私不分的问题;集体经济组织是私法人,由其代表行使集体财产所有权,可以弥补集体财产所有权人虚位的问题[29]。
因此,落实集体所有权的关键在于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与集体经济组织,尊重和落实好集体经济组织在占有、处分方面的权能,发挥其在监督处理土地撂荒、主导平整和改良土地、组织建设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促进土地集中连片和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的作用[30]。在发达地区,村社集体强有力地统合土地,进行地权“再集体化”,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地权集体化相互耦合,集体土地所有制得以延续,并因地制宜形成了多样化的农地制度创新[31]。“再集体化”顺应市场规律,采取鼓励性政策与制度安排引导分散的承包户自行选择重新组织生产要素的形式,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保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争取实现集体土地的市场价值,是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是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中集体所有权的一种有效尝试。
(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等配套制度
关于农民对土地保障功能的“迷恋”,罗必良认为,虽然非农就业比农业就业收入高,但是在非农就业的岗位和收入尚不稳定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民仍将土地视为“活命田”“保险田”和非农就业的退路,宁可粗放经营或抛荒,也不愿轻易转让和放弃土地[13]。即使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也不愿意退出土地,反而阻碍了农民的退出;提升农民的非农就业能力也不能强化农民的“弃地”意愿。
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保障水平偏低的情况下,对土地保障功能的认知和依赖在短期间内难以改变,农村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和财产价值的市场化配置改革必须考虑其作为实物保障功能的限制。政府应不断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综合运用财政转移支付、服务供给、灾害救助等措施,提升对农民和农民工群体的风险防范和生活保障能力,降低他们对土地保障功能的依赖。同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人口转移和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将农村承包地从“保命”或保险功能中解放出来,提高其要素配置自由和效率,以满足工业化、城镇化和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对农地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的要求。
(三)健全承包地流转交易市场机制
第一,推进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随着土地交易主体的增加、竞争性均衡价格形成机制的完善,以及信息充分共享机制的形成,承包地流转过程中的“价格幻觉”问题会逐渐得到矫正,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能更好地引导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政府需要正确处理自身与市场的关系,在减少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的同时也要弥补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功能的残缺[32],促进土地要素市场发育成熟,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贡献力量。
第二,培育市场中介组织,促进供求双方对接,降低搜寻成本和信息成本等交易成本。加强对流转合约的规范引导,充分发挥村委会在土地流转中的协调服务功能,同时加强监督和信息公开,减少流转交易过程中的寻租行为。
第三,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职业农民”队伍,以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政府鼓励工商资本下乡,形成新型经营主体,规范其经营行为,防止超越规划违规利用土地、过度开发土地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同时,适当利用财政税收、金融政策促进流转市场的不断扩大,发挥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租金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等,引导各权益主体充分竞争与合作。
(四)不断创新农村土地经营模式
本文归纳的四种典型土地经营模式各有千秋,适用性效率也各不相同。鉴于全国差异性较大,政府应该继续鼓励在“三权分置”的框架下,各地区努力探索适合当地的土地经营模式,并总结经验教训,为各地改革创新提供更多的经营模式选择。
第一,有的地方在进行土地入股成立合作社时,采取了“确权不确地”的新做法。对于在大量农民离开土地的情况下如何有效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问题,一些地方采取了“确权不确地”的方式来加强农户的产权保护,具体做法是,只确定农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不与具体的地块挂钩,不与具体的土地面积挂钩,只确定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享有的股份。这种做法保障了离地农民的承包权利及其财产性收益,还可避免个别“钉子户”阻挠土地规模化经营。
第二,土地规模化经营促使人们探索有偿退出机制。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建立农户承包地有偿退出机制,在退出的基本程序、补偿标准、退出土地利用和退地农民生活保障等方面积累经验,形成和不断完善制度设计,为适度土地规模经营创造良好的条件。2016年贵州省湄潭县开展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试点,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全国各地关于承包地“退出权”试点的制度设计中,充分尊重了农民的意愿和意见,让农民的理性选择成为引导承包地退出的主导因素。
第三,探索土地规模经营的不同模式。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弊端在于土地“细碎化”损失了规模经济效益,在农地承包權归属农户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是一条基本途径。除了前述四种典型模式外,我国各地在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集约化模式,如上海市松江区的家庭农场模式、山东省平度市的“新两田”制度设计、广东省清远市的“土地互换并置”模式等,它们的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借鉴。但也要认识到,农村土地规模经营面临组织运行成本问题和市场风险问题。如何降低规模经营中的组织运行成本和防范市场风险,是现代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汪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三重功能属性——基于罗马氏族与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的比较分析[J].比较法研究,2014(2):12-25.
[2]周天勇.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能的定量估计[J].财经问题研究,2020(7):14-31.
[3]赵万一,汪青松.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功能转型及权能实现——基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视角[J].法学研究,2014(1):74-92.
[4]刘守英,高圣平,王瑞民.农地三权分置下的土地权利体系重构[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134-145.
[5]钱忠好,牟燕.中国土地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及其特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3(5):20-26.
[6]程雪阳.重建财产权: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与方向[J].学术月刊,2020(4):98-108.
[7]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8]郜亮亮.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现状及完善建议[J].中州学刊,2018(2):46-52.
[9]臧知非,周国林,耿元骊,等.唯物史观视阈下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20(1):153-203.
[10]孙乐强.农民土地问题与中国道路选择的历史逻辑——透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一个重要维度[J].中国社会科学,2021(6):49-76.
[11]戴炜.“三权分置”视阈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二元构造[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89-95.
[12]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00(2):54-65.
[13]罗必良.农地保障和退出条件下的制度变革:福利功能让渡财产功能[J].改革,2013(1):66-75.
[14]肖卫东,梁春梅.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内涵、基本要义及权利关系[J].中国农村经济,2016(11):17-29.
[15]李琴,杨松涛,张同龙.社会保障能够替代土地保障吗?——基于新农保对土地租出意愿租金的影响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9(7):61-74.
[16]张广财,张世虎,顾海英.农户收入、土地保障与农地退出——基于长三角地区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20(9):104-116.
[17]马池春,马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三重维度与秩序均衡——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J].农业经济问题,2018(2):6-13.
[18]COASE R H.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3): 1-44.
[19]朱文珏,罗必良.农地价格幻觉:由价值评价差异引发的农地流转市场配置“失灵”——基于全国9省(区)农户的微观数据[J].中国农村观察,2018(5):1-15.
[20]栾健,韩一军.农地转入规模、中介组织与契约选择偏好[J].农村经济,2021(5):54-63.
[21]罗必良.合约短期化与空合约假说——基于农地租约的经验证据[J].财经问题研究,2017(1):10-21.
[22]陈楚钿,陈楚庭,程高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广东实践探析[J].法制与社会,2021(1):115-117.
[23]马良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社会再组织——以贵州省塘约村为例[J].中州学刊,2021(2):66-72.
[24]夏柱智.集体经济发展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反思——对话“塘约经验”[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24-32.
[25]刘卫柏,彭魏倬加.“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土地信托流转模式分析——以湖南益阳沅江的实践为例[J].经济地理,2016(8):134-141.
[26]罗必良,钟文晶,谢琳.重新发现“农业共营制”——从农业经营到乡村振兴的制度性拓展[J].乡村振兴,2021(10):23-26.
[27]夏振泉.深入贯彻落实“三权分置”办法 大力推广农业共营制模式——大连市的工作实践[J].农业经济,2017(11):26-27.
[28]米运生,罗必良,徐俊丽.坚持、落实、完善:中国农地集体所有权的变革逻辑——演变、现状与展望[J].经济学家,2020(1):98-109.
[29]张先贵.集体经济组织享有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谬误与补正[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112-118.
[30]叶兴庆.集体所有制下农用地的产权重构[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2):1-8.
[31]张晓山.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理论探讨[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10.
[32]孔祥智,周振.我国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历程、基本经验与深化路径[J].改革,2020(7):27-38.
Evolution Logic and Reform Orientation of Rural Land Contract Management System in China
DENG Chao-chun GU Qiu-qin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land contract and management system reflected the shift from focus on fairness of land distribution to the efficiency of land use. It is the institutional express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olitic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functions of land. 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contract management system will further strengthen its economic function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that is to implement collective ownership, gradually peel off the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 of contracted land, improve the circulation market system of contracted land, and innovate the management patterns of land.
Key words: rural land contract management system;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rural land system reform
基金項目: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海南自贸区(港)建设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HNSK(YB)19-2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地租量的规定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18BJL01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模式、绩效评价及政策优化研究”(71963013);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对策研究”(2021JDR0069)。
作者简介:邓朝春,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讲师;辜秋琴,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