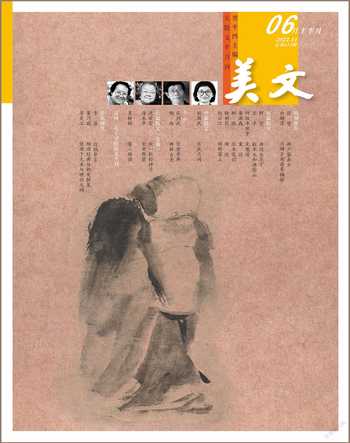只鳞片羽诗界撷拾

白婉清
前言
我与诗歌界结缘始于1953年。从中国作家协会的诗歌工作者到诗刊社编辑,十多年来交往过的诗人不少。直到1965年《诗刊》停刊,又遭遇下放改行,我才与诗界完全脱离关系。60多年过去,当年交往过的诗人们绝大多数已经作古,和他们相处中的许多鲜活场景,在岁月的冲刷中也仅余若干碎影残片存留在脑海之中了。考虑到即使点滴记忆,也应是有益的历史资料吧。因此,只鳞片羽也罢,点滴光影也罢,把它们撷取捕捉下来,留痕纸上,也就不致辜负这段诗界情缘了。
徐迟
1957年《诗刊》创刊时我担任编辑,认识徐迟就在这时候。当时主编是臧克家,副主编是徐迟。他们只是不定期来编辑部转转,了解情况,做点指导。虽然不坐班,后勤部门仍然按编制给他们配备了办公桌椅。那时办公用具的分配有着一定的等级差别:主编副主编等高层领导的办公桌是“两头沉”(两侧都有接地的抽屉和柜橱),座椅是皮面弹簧软椅;中层领导如编辑部正副主任用的是“一头沉”和有软屉心的座椅;我们一般编辑人员用的则是小三屉桌和硬板椅。这本是正常的现象,徐迟却对这种安排大感不平:一线编辑人员干的事具体而繁琐,十分辛苦,却成天坐硬木椅;需要处理的稿件最多,掌握的资料庞杂,一个小三屉桌怎么够用?而我们两主编的大办公桌和舒适座椅,却只是作为摆设闲置,太不合理了!在他的主张之下,立刻对这“不合理”的现象做出变革:把两位主编的桌椅同我和另一编辑进行对调。于是我这年轻的小编辑居然坐在豪华的大办公桌前享受着高层领导才有的待遇,不免诚惶诚恐。而那两套蜷缩一隅显得寒酸的桌凳所隶属的主人竟是声名赫赫的人物,令人意想不到。这一巨大反差彰显出徐迟那率直的性格和与众不同的作风,给我留下深刻而独特的印象。
和徐迟更深入的接触始于1959年上半年。那时他这位副主编正式进驻编辑部,担起具体领导工作。他的领导作风若用通常“平易近人,热情亲切”的词汇来形容仍感不足,许多时候,他更像个活泼快乐的大朋友,时不时用幽默的谈吐和机智的打趣给紧张的编辑生活注入轻松欢快的气氛。他思维灵活,工作中常会有新的想法跳出来,也曾让我从中受益。
编辑都有联系诗人的任务,每人大致有自己负责的范围,徐迟也不例外。他除了给外地诗友常通信组稿外,也不时走访市内的诗界老朋友。一天,他突然意外提出要带我去拜访郭沫若,让我很是惊喜,能有机会见到这个重量级的大人物自然求之不得。我怀着期待又忐忑的心情跟随徐迟来到位于西城区“大院胡同5号”的一处大宅院,在宽大的客厅里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名人郭老。他戴副眼镜,身材比徐迟较为瘦小,热情健谈却和徐迟差不多。两位老友见面自然相谈甚欢,我却只能枯坐一旁。大概怕冷落了我吧,郭老忽然转头问起了我的年龄,我答29岁。“呀!”他望着我厚厚的眼镜片惊奇地说,“这么年轻就这样近视了!大概看书太多了吧?以后要多注意了。”我知道他是在有意开玩笑,虽然有点尴尬,但心情放松多了。不记得后来又谈了哪些关于诗的正式话题,只有这句玩笑话倒让我始终忘不了。
《詩刊》每期刊发稿件及排定顺序的决定权在主编手里。一次徐迟却突发奇想,把下期稿件的编发工作交给我这只有两年编龄的年轻编辑全权负责,使我受宠若惊。大约是想锻炼和考验我的业务能力吧。我只是抱着别出纰漏就好的态度,照猫画虎地从已经审定的稿件中按照轻重缓急,结合当前形势遴选出一批稿子,凑够了一期内容;再按照质量高低、题材类别排出顺序,编成目录就算完成任务。然而在目录的编排上却不懂得参照以前各期的样式做出适当调整变化,连按不同题材分组隔开都没有做到,只是简单地一顺连排到底。对这毫无特点死气沉沉的目录,徐迟岂能没有看法?但他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我明白他想锻炼培养我的良苦用心,既然让我负责就完全放手,不想打击我的积极性。然而这目录事后越看越让我惭愧,感到有负他的信任和厚望。
作为全国性的刊物,编辑部去外地出差的机会不少。我因主要负责联系本市的诗人,一直没有出远门锻炼的机会。徐迟知道这个情况后,精心为我安排了一次既简单易行又能有所收获的出差任务——去工业重镇哈尔滨访问诗人严辰,同时参观市内各大重工业工厂。严辰原本也是《诗刊》副主编,后来从北京迁居哈尔滨;他夫人逯斐曾是我在中央文学研究所进修时的同学。这次走访无异是故人重逢,太好办了!考虑到我没有出远门的经验,徐迟不仅提前写信通知严辰,还通知哈尔滨市文联的熟人协助接待。这样我下火车时不仅有人接站,还安排好了下榻旅店,生活交通一路绿灯。严辰夫妇更是在家中热情接待我,还特意拿出两天时间陪我游览市内名胜,把访问的任务变成了快乐的旅游。至于参观工厂也非常顺利:用作协的介绍信到省委宣传部换成给各工厂的参观介绍信。有了这个“尚方宝剑”,每个工厂都无例外地由厂党委宣传部派专人陪同我挨车间参观讲解。就这样在短短几天之内,我一共参观了八个重型大工厂,确实感到收获多多,眼界大开。然而我对参观只是抱着完成任务的目的,没有认识到这是难得的体验生活的机会。虽然那些先进的生产技术让我赞叹,气势磅礴的生产流程让我震撼,祖国伟大的建设成果让我自豪,却没有认真思考应该为这写点什么。参观时虽然做了一些简单记录,也没有及时整理成资料保存。留在头脑里的零散印象时间一长也忘掉了。访问严辰的结果只是了解到他的创作规划和供稿承诺,并没有带回他的作品。因此,我这次出差回来基本是两手空空。徐迟虽然没有说什么,我事后想起却觉得惭愧,没有体会到他为我设计这次出差的深意,没有好好地利用这机会留下点收获,实在有负他的关怀和期望。

徐迟
D0F23CC6-C940-415F-BDD7-509E68B5E11B徐迟十分重视群众作品,认真扶持群众创作。1958年全国掀起新民歌创作高潮时期,徐迟曾下乡辅导和推动群众的民歌创作,还为他们编辑出版了一个诗集。到他主持《诗刊》工作的1959至1960年,在他的倡导下,《诗刊》不断从群众来稿中遴选编发新民歌组合,除了农村题材的民歌外,还包括工人、战士、其他行业作者写的民歌。除了民歌形式以外,也注意刊发其他形式和内容的群众作品。有时还将一些群众作品组合排在显著位置,以表重视。
徐迟在《诗刊》编辑部和我们相处了不到两年,1960年下半年他就选择到武汉作家协会去当专业作家了。本来,一个才华横溢、思想活跃的诗人,他的岗位应该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火热的战斗生活中,而不是长期局限在小小的办公室里为人作嫁。他的离开我们既恋恋不舍,又为他高兴。他走之前,主编臧克家和接任的副主编葛洛来到编辑部,为他举行个小小的欢送会,并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徐迟人虽走,心仍留在编辑部:不时有信件或诗稿传来,传递信息和问候,展示行踪和战果。偶然他还会出其不意地回到“娘家”看看,和大家畅谈叙旧。一个盛夏,让人挥汗如雨的时候,徐迟却神情轻松地跑来了,满意地说:“啊,总算逃出武汉那个大火炉,回北京避几天暑了!”哈!不比不知道,我们原来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呢!还有一次,诗刊社组织一个在京诗人的聚会,正好徐迟也回来了赶上参加。开会这天我们正在会场忙于布置的时候,突然有人从背后蒙住了我的眼睛,但因有眼镜遮挡,只能用手虚掩。还没等我转过身来,耳边就传来吃吃的笑声。没错,就是他!徐迟这个年近五十的人,竟然还用这种孩子般的游戏方式来表达故人重逢的惊喜,或许是想拿我当作孩子来逗弄吧。总之,这就是徐迟——一个童心未泯的快乐朋友,一个纯真而浪漫的诗人!
1964年10月,我有幸到武汉出差,才得到机会到徐迟家拜访。第一次见到他美丽而娴雅的夫人陈松,也感受到他们和谐美满的伉俪之情。早听说徐迟喜欢音乐,他从一大堆唱片中挑选出他喜爱的古典音乐和民歌,一张张放给我听,并介绍它们的特点。在他那温馨又浪漫的家庭氛围中我过得十分惬意而舒畅。
此后不久,《诗刊》停刊,人员星散,我下放到塞外张家口地区。虽然还可以乘回京探亲之机,探望作协和诗刊社的老友,但能见到的故人不多,大约到了1974年,我回京时听说徐迟已回京小住,我立即邀了一位诗刊社老友去看望他。虽曾久处逆境,他依然锐气未减,还是那副活泼健谈的样子。当我们慨叹韶光易逝、人生易老之时,徐迟却毫不在意地笑着说:“我今年六十岁了,整六十!”啊,六十岁!这岂不是人进入老年的起始吗?在我们惊愕的目光之下,他那神情却仿佛是个孩子告诉人自己又长了一岁似的,他那灵动的双眸闪烁着的仍是那乐观自信的光芒。这就是徐迟,一个思想永不老的大孩子!
后来,他很快又成了大忙人,释放出被压抑已久的精力,焕发出60岁以后的青春重新投入创作。而且独辟蹊径地扎进科学领域,和科学家们交上朋友,用文学手段为科学服务。在形象而抒情地弘扬科学家们伟大的科研成果时,也深入探讨他们的内心世界,揭示出他们无私无悔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于是一篇篇震撼人心的报告文学作品问世了:《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流的漩涡中》,尤以《哥德巴赫猜想》轰动一时。是他以文学家的细腻笔触,托举出了虽获惊世成果却未为人所知的年轻科学家陈景润;是陈景润以他苦行僧般为科学献身的传奇经历,成就了他为人传诵的报告文学作品《哥德巴赫猜想》。文学与科学的绝妙结合,出现了空前的轰动效应。听到他的骄人战绩,比见到他本人还高兴。就这样,徐迟的一些行动信息便常在我们诗刊的故人中相互传递,牵动着大家的思绪。但到后来,一些不妙的消息也接踵而来:爱妻陈松去世、女儿疏远、第二次婚姻失败、对生活失望、重病住院……最后,一个重磅消息轰然炸响——跳楼自杀!啊!这个难以置信的极端行为怎能与那个积极乐观的头脑和活泼进取的性格联系起来呢?然而,这就是徐迟吧。既然到了精神和肉体的痛苦都难以承载的时候,就选择与众不同的方式和82岁的生命告别——以血肉之躯扑向大地,也将不羁的灵魂放飞天堂,只把大大的震撼和长长的思考留给了众多思念他的人。
阮章竞
在上大学期间读到了阮章竞的民歌体叙事长诗《漳河水》,就深深爱上了它。爱它那兼具古典诗词和民间口语美、琅琅上口的诗句和描述生动鲜活的农村人物故事。不久又在剧院里看到了同一作者写的歌剧《赤叶河》,被那震撼人心的剧情和凄婉的歌词唱段深深打动。自此牢牢记住了阮章竞的名字。参加工作来到作家协会和诗刊社后,阮章竞则是作协党组成员和《诗刊》编委,开始在一些会议场合有了见面的机会。虽然还没有深入的接触,他那诚朴和蔼的面容、沉稳庄重的举止和带有南方口音不疾不徐中气十足的言谈,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1960年底,领导《诗刊》编辑部工作的副主编徐迟离任,他的工作由新上任的副主编葛洛接替,但原本已经担任副主编的阮章竞仍常和主编臧克家一起到编辑部来研究工作,或召开编辑部会议商讨有关问题。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主副食供应都很紧张,大家的粮票都很少,食堂里菜量也不足。阮章竞对大家的生活状况很关心,一次他特别到编辑部来看望,谆谆叮嘱我们要想方设法增加营养,可以学习社会上的一些对应措施或自己想办法,千万别搞垮身体。他说到“要增加营养”时那焦虑的神情、恳切的语调打动了我,于是在食堂吃饭时往往要多喝一碗伙房特备的据说含蛋白质的小球藻汤,剩下菜汁为了“加强营养”也不敢随意丢弃。当然大家的身体也都没垮,好好地挺过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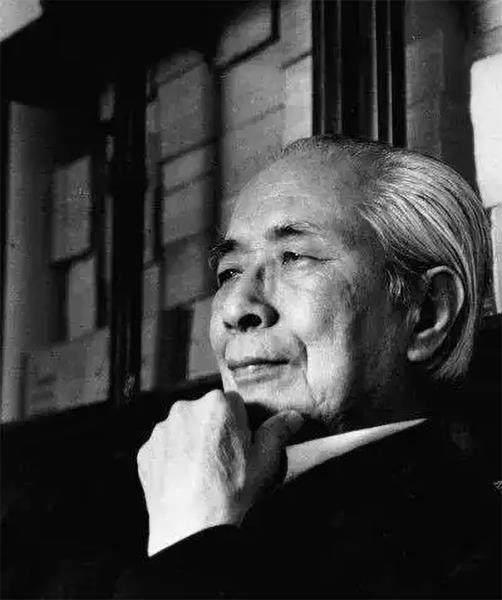
阮章竞
1962年起,阮章竞不再担任副主编,到编辑部来的次数少了,但参加诗刊社组织的各项活动和稿件的提供并不少。他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这情况在诗界并不多见,以自己的诗与画互配尤为难得。1962年2月他去江西瑞金革命老根据地体验生活,带回来一组诗,也收获了一批画。于是《诗刊》在同年第4期刊发了他的一组诗画,以《沿着历史的长河走》为总题,包含了8首诗和4幅画。画经过照相缩印,小而模糊又无彩色,显得逊色不少,但这种刊发形式却比较新颖。其中一組诗画《红军桥》尤为引人注目:画面简洁清新,右方一丛垂柳和几株树木,正面是寥寥几笔勾勒出的高架木桥,上有人影负重往来,蓝天上掠过几只飞鸟。与之匹配的诗同样清丽简洁:“春柳垂枝挂珠帘,挂在潋江绿水前。红军桥头山歌起,鹰影飞过江底天。”诗美画美,相得益彰。借着编发这组诗画的契机,我们几个编辑得以去参观了他的画室。只见宽阔的房间里大大的画案上,摆放的是排排画笔、颜料盘和纸张。四周墙壁、地上也都是成品画作,说明作者的爱好和勤奋。这些画大都是国画形式的风景画,其中就包括那幅《红军桥》。我趁此机会请求他再为我画一幅同样的画,他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下来。D0F23CC6-C940-415F-BDD7-509E68B5E11B
没过多少天,他到编辑部来时就将一个画卷交给了我。我欣喜地展开一看,果然就是我心仪的那个画面。这是一张八开大小的竖长版面,构图虽相同,笔法却似更加潇洒写意,色彩纷繁又淡雅自然,那首诗则用清秀流利的行书小字抄在左上方。“题款是:上款,‘婉清小友嘱画;下款,‘章”竞工间操事。表明他是利用如做工间操的间隙时间随手画的,带有谦虚之意。这幅画我很珍爱,处理方法却很随意,只用图钉将四角钉在墙壁上随时欣赏就算了。直到下放张家口后,才认真地把它和臧克家给我书写的诗条幅一起装裱成长轴,挂在客厅。有如双璧,为陋室增辉,由来客欣赏。(这里需要补写一笔的是:前若干年一个经营旧书及文物的书商来我家收购旧书时,看中了墙上的字画想要收购。在我坚决拒绝下仍不死心,多次带礼物上门软磨硬泡,终于利用我面善心软的弱点将阮章竞的这幅画“抢”收走了。只把臧克家的诗作为最后底线保留下来。现在想来虽然遗憾,但换个角度想想,这种名人遗迹,若一直存于我私人手中倒不能体现其价值,也许作为文物流入社会反而更有意义吧。)
阮章竞留在我记忆中的最后一个亮点,大约是在那些最易受冲击的名人们大都已平安无事之时。隔绝多年的诗界故人又可自由来往了,我就趁一次回京之机独自一人去阮章竞家中看望,对于尚处寂寞之中的他自是十分高兴。会面的具体情景和谈话内容都已模糊,只有临别时的情景记忆最深。我告别时他坚持送我走出院门,恋恋不舍地说:“以后再来吧,见一次面少一次了!”这颇有伤感意味的话刺痛了我的心,我郑重承诺一定会再来看他。其实这种意思还有个积极的说法是“见一次面就多一次了。”然而,不论“少一次”还是“多一次”,我却连一次都没做到。以后不知怎么总是阴错阳差,始终没得到机会再去看他,那一次就成了最后一次。而那句临别的话和我的承诺一直萦绕心头,随着时间推移,成了永难抹掉的心头之憾了。
艾青
第一次知道艾青这个名字是在高中期间读到他的长诗《火把》,那鼓舞青年抨击黑暗追求光明的激情立刻在心中引发共鸣。大学时代又读到他那感情深沉浓烈的诗集《向太阳》,更对作者产生敬佩。北京解放不久,大约是在一个各大学文艺团体的集会上,请到了时为华北大学领导之一的艾青来做报告,得以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诗人。会场是一个十分简陋的空屋子,大家席地而坐,只给报告人准备了一套桌椅。艾青穿一身旧灰布棉制服,带有解放区老干部的朴素风貌。他用带有江浙口音的普通话慢条斯理地介绍解放区文艺创作情况,听来很是新奇。可惜我并没记住多少,只是留住了对他的印象。没有想到的是,几年之后竟和这位诗人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工作联系。
1953年夏,我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分工担任诗歌组干事。主要的一项任务是为在京诗人会员开展业务活动做具体工作。负责活动安排的是诗人中选出的干事会,成员有艾青、臧克家、田间、袁水拍等。艾青任组长,于是许多有关诗歌组的业务活动我都需要和他联系。作家协会位于北京东城区东总布胡同22号的一个大宅院,大红门里面层层叠叠多重院落,两厢有回廊相连,旁侧还有跨院。最后面的院里有一座二层小楼,已是专业作家的艾青离婚后就独居在小楼的二层。我们创委会则在小楼前面的院落里办公。诗歌组的业务活动不少:1953年下半年到1954年1月份,就召开了关于李季的长诗《菊花石》和诗的形式问题的讨论会各三次,诗歌朗诵会一次。为组织好这些会议,干事会在每次讨论会前后都要认真研究、组织发言并做好总结。干事会开会地点就在艾青住处那间宽大的客厅里,我则负责发通知、做记录。有时会议开到中午,艾青就做东请大家到附近饭馆用餐,我也便跟着沾光。后来干事会组长换成了臧克家,开会地点为了方便仍在艾青住所。于是艾青那间二楼客厅我不知出入了多少次,每次他几乎都是从那宽大的写字台前转过身来,以温和的笑容迎接我,从容地听我汇报或请示工作,再做出下一步安排。有时他也向我展示他的写作成果和发表情况,或闲谈点个人琐事。比如他的笔名之由来,他原名蒋海澄,因自己耻于与蒋介石同姓,就在蒋字的草字头下打了个大叉,结果“蒋”字就变成了“艾”字。至于“青”字大约是随便找了个与名字“澄”字的方言谐音就算了。总之,“艾青”的取名源于偶然。
1954年夏,艾青需要出国参加诗歌活动。当时寄给他的邮件特别多,多是各杂志社出版社寄来的刊物信函之类。他通过创委会领导委托我为他代收邮件,我便专门腾出一个抽屉来装。约半月之后,艾青回来了。我立即把积满一抽屉的邮件给他送去,他也送给我一个从国外带回的塑料小盒子。这是一个巴掌大小的红色圆盒,有一个可旋拧的盒盖,盖子上绘有艳丽的异域风情装饰画。那时塑料制品还十分罕见,我一直珍惜地将它保存下来。后来用它来存放各个历史时期获得的纪念章,现在这些纪念章和这个小盒子本身都成了珍贵的纪念物了。
那几年,艾青平静地生活、写作。每有新的诗集出版,他都会签名送给我一本,如1955年出的诗歌总集《艾青诗选》以及较早出版的《欢呼集》等。1957年《诗刊》创刊,我成了《诗刊》编辑,艾青是编委。创刊号上他的诗是重点,仅排在毛主席十八首诗词之后。我们的关系便成了编辑和作者的关系。他那时已经重组了家庭,搬到崇文门内一个僻静的小胡同里,我有时因工作需要也去登门拜访,不过见面次数比过去少多了。
平静的生活过得不算长,1957年下半年,全国掀起一阵风暴,艾青不幸被卷入其中。大约由于诗人在解放后没有完全把手中的芦笛换成战斗的号角,没有完全把牧歌的调子换成时代的强音;他那显得有点孤傲的性格和常带尖刻嘲讽语气的言谈也容易出现纰漏吧,最后,这位曾经在黑夜高举火把、带领青年人向太阳奔跑、讴歌光明到来的时代歌手,就此销声匿迹,从高高的文坛坠入社会底层,全家被放逐北大荒再到边远新疆。20年来,人们再也听不到他那深沉而激越的歌声,得不到他的任何信息,诗人真的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吗?
终于,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结束,文艺界的春天回归。1978年下半年,当停刊后又复刊的《诗刊》社接到筹编建国三十年诗选的任务时,新组建的编辑部难以胜任,只好把我们几个诗刊老编辑从天南地北借调回来承担这一工作。回到复苏了的诗坛,重见一些诗界故人,大家都有恍如隔世的感觉。这时一个高兴的消息传来:艾青已经回到北京了!我便迫不及待地打听到他的居住地点,抽了个空赶去看望。他住的地方好像是在一个大院里的一处偏僻小院,里面有一排房子,房门开在侧面。当我绕过房前从侧门进去时,只见艾青正背对着我坐在面窗的书桌前。其实他已经从窗里看到我过来了,也知道我已进门,却不动声色。待我激动地叫了一声“艾青同志”时,他才缓缓转过身来,布满沧桑的面容带着平静的表情,恬淡而缓慢地说:“啊,你来了。我还以为你不会来看我的呢。”这跨越20年风雨的会面竟以这样一句话开头,不免让我心头掠过一丝酸楚。我赶紧用轻松的语调冲淡了沉闷的气氛,并且尽量谈自己的情况,避免触碰他的伤疤。当话题铺开之后,他也逐渐恢复了自然幽默的常态。甚至当我的面对夫人用嘲讽的语气来打趣:“一个女人不要像个茶壶一样,一手叉腰,一手伸出去指斥别人,样子太难看了。”让人又看到了过去的艾青。我知道坎坷的遭遇是击不垮他的。

艾青
过了些天,作协组织一些作家到白洋淀等地参观,我们几个被借调回来的人也有幸参与。在参观的队伍中我又见到了艾青,他正和大家谈笑如常。在一处似乎是石油开采的地方,我们见到黑色的油柱从管道里喷涌而出,十分壮观,大家都为之赞叹。我故意对艾青开玩笑说:如果诗思能像这样奔放就好了。他也故作驚讶地说:“哦!像这个吗?那就太可怕了!”哈,艾青还是那个艾青啊!两三个月后,我们的建国三十年诗选已编出初稿,一些诗人虽然还没有以作品和公众见面,但也都名列其中。对艾青的诗我们选的多是当年回归后的新作,更多的是和“四人帮”斗争的题材,感情更加昂扬激奋。
从那以后,我虽然没有见过艾青,但从多种渠道都能得到他的消息。他又成了大忙人,足迹遍于国内国外。他出现在多种活动场合中,他诗思如潮,新的诗集不断问世。“重生”了的诗人似乎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年过古稀又重新焕发了青春。他奉献给读者的是艺术更加成熟、题材多样、感情炽烈、思想浑厚的作品,他又成了新的时代歌者,没有辜负他热爱的祖国,没有辜负他热爱与热爱他的人民。
(责任编辑:马倩)D0F23CC6-C940-415F-BDD7-509E68B5E1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