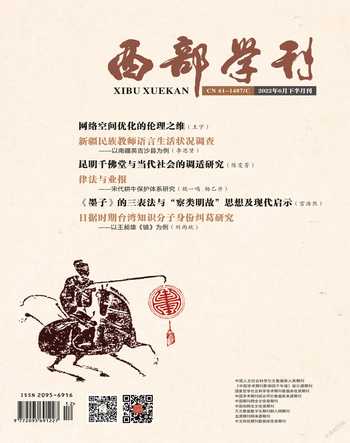庄子“逍遥”与郭象“逍遥”之比较
摘要:郭象的《庄子注》不仅仅是单纯的对庄子文本的译注,其中掺杂了他本人的哲学思想。他对于“逍遥”的理解与庄子之“逍遥”有本质上的不同。庄子之“超越逍遥”追求的是精神自由境界。而郭象之“足性逍遥”是对万物本性的满足和实现。二人“逍遥”概念之不同在于:(一)“逍遥”的实现主体和理论结构的不同。庄子主张“离形去知”,跳脱世俗;郭象则主张自足其性分,即可达“逍遥”。(二)境界层次和现实性的不同。庄子的“逍遥”所追求的是精神超越,是与万物为一的无我境界;郭象强调满足于现世的“冥然与时世为一”。本质上来说,庄子的逍遥只是一种理想境界,不具有普遍的现实性。郭象的逍遥是作用于现实社会的“逍遥”,具有可实现性。
关键词:郭象;庄子;《庄子注》;超越逍遥;足性逍遥
中图分类号:B223.5;B23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12-0173-04
一、两种逍遥观
《庄子》一书,在流传中经过多次编撰、整理,至淮南王刘安将其划分为内、外两篇,再至魏晋时期司马彪、郭象①将《庄子》分出杂篇。现今流传的版本,是由郭象所著并流传至今的最终定本。
魏晋时期,《庄子》一书盛行于上层社会,形成了数十人注庄的盛状。其中以郭象所著《庄子注》最为流行。郭象是继向秀之后又一位研庄、注庄的大家。其所著《庄子注》吸收魏晋时期各家注写庄子之所长,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理论特色。郭象的《庄子注》不仅仅是单纯的对庄子文本的译注,其中掺杂了很多郭象本人的哲学思想,实际是在以借《庄子》对自身思想进行再阐释。《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二中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可见郭象是在以“六经注我”的方式对庄子思想进行再解读。
郭象对庄子之“逍遥”境界进行了儒家式的改造,使“逍遥”具有了可能性。
(一)庄子的“超越逍遥”
庄子的“逍遥”思想主要体现在《逍遥游》一篇中。“逍遥”一词,本义为游,引申义为调畅逸豫,放浪自得。《逍遙游》篇是《庄子》中文风最恣意的一篇,也是对逍遥义阐述最详尽的一篇。
讨论庄子的“逍遥”,首先需要对庄子的天命观进行分析。其原因在于,庄子所追求的“逍遥”的大境界,即是庄子对“道”的追寻。而进入到逍遥境界的人就是得道者。
庄子讲“安时而处顺”,死生为常态。庄子对生死的看法是秉持着“以道观之”的方式去体悟的。庄子认为大道浑然为一并衍生万物。无所不包,无所不在。不管是神怪人皇,天地日月,还是万事万物的生成与消亡都因“道”的状态而随意变化。所以生与死也是一样,二者都是“道”自然而然的两种变化状态而已。生与死被提升到了同等的高度。“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1]68可见庄子主张死生皆为常态,生和死的变化就像白天与夜晚的交替流转,都是大道之下自然的变化。所以庄子提出对于生死的态度应该是顺应、安命。
这种安命论,在《庄子·大宗师》篇,“子来言造化”的寓言中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子来借“大冶铸金”的例子,将人的生老病死都归结为大道自然而然的变化过程,人本身是无法选择的。
庄子的安命论虽然是一种命运前定说,但庄子强调其中作为“大熔炉”去造化万物的道本身,是没有意志的。人在大道的作用下经历的一切境遇,都是没有任何客观意志的干预的。道与天,在庄子这里并不具有意志。
基于这种安命的思想基础,庄子认为人应安于大道所赋予人的形态与境遇。不以人的生而感到快乐,也不因人的死而感到悲伤。超脱于现世之外,将内心归复于生而为人之前的状态,将精神放置于与大道等同的境界,以平静而超脱的心境坦然面对所处境遇的好坏。
这种超脱于现世,与大道同一,即“以道观之”的境界。庄子认为不是人人都能够达到的,而需要修养。也就是通过“心斋”“坐忘”等修养方法达到人的内在的超越。庄子主张“坐忘”,即忘掉一切外在;“离形去知”,即忘掉自己肢体以及心智。如此跳脱出世俗世界,超脱痛苦,将自身与大道融为一体,回复到最本真的状态,也就是大道的状态。这时就达到了“逍遥”的境界。
实际上,庄子所想要说明的“逍遥”的境界,就是道家所主张的自然的、超脱物欲的自然之性。强调人要摆脱外物的役使,祛除外在的联系。对于人事以及外物都“以道观之”。即站在道的高度,将万物万事等齐看待,没有人与人的区分,亦没有人与物的区分。甚至对于是非观念,庄子同样以“齐”待之,主张去除是非观念。庄子认为是非引发争论,是非没有道理,每个人都会因为自身的立场不同而有不同的是非判断,其争论永远没有尽头,更无意义。
所以庄子主张,去除外物的侵扰,归复于大道的高度来看待人事与万物,如此之境界,也就是庄子所讲的逍遥境界了。超脱出人世“以道观之”,这种境界即是一种“超越的逍遥”境界。
(二)郭象的“足性逍遥”
郭象对于“逍遥”的阐释与庄子正好相反。从上一节可见,庄子之逍遥是向外的、从尘世求向大道境界的超越的逍遥,而郭象是向内调和的、“自足其性”的足性的逍遥。
郭象对庄子之“逍遥”的改造,是从对庄子的大道自然的境界,推及人自身所本有的人性的境界。
论及郭象之“逍遥”,首先要探讨的,是他的“独化”理论。在独化论中,郭象直接对庄子“道”的存在进行了否定,认为“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2]60,万物化生不是大道演而化之,而是自生自有的。且事物之间没有任何因果依赖关系,人与人之间所产生的交集,只是一种“相因”。郭象认为万物生化无待于外物,自生而偶然,万物之间之所以会存在偶然的相遇,是因为存在高度的和谐。这种高度和谐没有目的性,只是出于偶然。
而“独化”既然自生、自有,必然的需要一种动力。这种动力,郭象认为就是“自性”。郭象在《庄子注》中讲,“物各有性,性各有极”[2]6。此物之所以为此物而非另一物的依据,就是因为物有其“自性”。且物的存在与他物存在亦无关,对他物产生的或好或坏的影响,都是出于偶然。所以说“蒙泽者不必谢,凋落者也无须怨”[2]314。这样就将万物的命运和境遇交由万物的“自性”而定。基于这一点,郭象与庄子的“逍遥”思想逐渐背道而驰。
郭象强调物有其“自性”,在本性之内的所为都是在“足其性”,是有助于人之“自性”的实现的。所以郭象认为,“逍遥”就是这样通过万物足于其性,从而达到了逍遥无别,进而获得精神自由的境界。
所以“足性”即是达到“逍遥”的关键。郭象在《逍遥游》中注言,“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2]15。在这里郭象举例认为,对于君王而言,君主能够通过充分的统治进行统治,这就是达到逍遥的境界了。也就是说,通过“各足其性分”,实现对万物本性的满足与实现,那么“逍遥”的境界也就自然而然地达到了。
可见郭象的“逍遥”是不同于庄子超越于人世之境的“超越的逍遥”,而是一种向内寻求人的“自性”之实现的“足性的逍遥”。郭象思想中所追求的是在现世之中,各自“足于其性”,并充分尊重万物之自性,以达到道家出世境界与儒家入世境界的统一。
二、庄子与郭象“逍遥观”之不同
刘笑敢先生区分庄子的“超越逍遥”和郭象的“足性逍遥”,认为两人的“逍遥观”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5]。并在《两种逍遥与两种自由》中说,“庄子之逍遥与郭象之逍遥有某种根本的对立。从庄子的理论角度看郭象,可以说郭象将超越的逍遥游拉到了现实的泥淖之中,完全没有精神的、超越的追求,是对逍遥游的严重歪曲和庸俗化,将批判的、超越的庄子哲学转化为安于现实、维护现实的郭象哲学。从郭象的理论立场看庄子,可以说庄子的逍遥只是少数个人的精神享受,与现实社会和人生毫不相干,对一般人毫无意义,对社会秩序的维系毫无贡献。”[3]
基于刘笑敢先生的总结,以下对于郭象与庄子的逍遥观进行了总结区分。
(一)“逍遥”的实现主体和理论结构的不同
从实现主体来讲,对于“逍遥”的实现,庄子与郭象在主体性上存在着不同。庄子的“逍遥”境界是真人(一种悟道之人)才能达到的境界。真人通过“心斋”“坐忘”“见独”的修养方法,进而“离形去知”,彻底地忘掉自己肢体、心智。跳脱世俗,游于尘世之外,达到“逍遥”的精神超越的境界。但这种境界,是只有真人才能够达到的境界。
但郭象的逍遥正好相反。郭象通过万物自生、自有的独化论,进而说明万物皆因其“性分”而自足。也就是说,万物自生之后,已经先天的具有了“逍遥”的天性。所以只要万物自足其性分,人人都可以达到“逍遥”的境界。所以郭象通过这样一种“足性的逍遥”将“小大之辩”进行了模糊的处理。
郭象曾注言称“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馀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2]5他认为,虽然人与人之间有所差异与不同,但这都是其“性分”的表现。人足于性就能够达到逍遥,所以人人皆可逍遥。这与庄子所说的,只有真人才能达到“逍遥”的境界是有着极大的不同的。
而且区别于庄子不具有现实性的“逍遥”,郭象的“足其性分”是具有可实现性的。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关于君主对其性分的实现,万物自生之后先天的具有其各自的特性,只要根据这种特性行事,“足其性分”即充分的完成自身本職工作,就可以实现“逍遥”的境界。而无需通过庄子所说的“心斋”“坐忘”等一系列的修养过程,直接通过万物本“性”的满足与实现来达到“逍遥”。
从理论结构上来讲,庄子的“逍遥”是递进式的、立体的理论结构。庄子以“顺应”“安命”的天命观为基础,提出了逍遥的理想境界。对于庄子来讲,安于大道之熔炉,生之不喜,死亦无悲,人世之中万物无有差别。想要寻求更高的境界,现世已经无法满足。所以庄子对逍遥的寻求,是朝向于现世之外的,向道的境界寻求精神上的超越。
庄子试图通过“心斋”“坐忘”的修养方法,离形去知,超脱自身,达到“无己”的境界,进而达到“逍遥”的精神超越。
庄子的逍遥境界存在过程的渐进性,而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达成的。达到“逍遥”的境界,就是要最终站在“道”的高度“以道观之”。而如何达到“道”的境界,庄子在《庄子·大宗师》篇中讲了一个南伯子葵问道于女偊的故事。南伯子葵问女偊,“道可得学邪?”女偊答道,道不可学。想要得道,需要先天的具有圣人之才,而即使是具有圣人之才,领悟大道很容易的人,也需要女偊教之,三日后忘记天下,七日后忘记了万物,九日后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达到了清明透彻的心境,之后方能感受到大道,体悟到大道就能超越时间的限制,如此就进入了无关乎生死的境界。如此可见,达到道的过程是渐进的,是逐渐修养的过程,且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去修习。
庄子的逍遥境界也是立体的。是直接超脱出人世,达到独立于万事万物之外的“道”的境界。或者说庄子的逍遥是精神层面的追求与超越,所以它难以达到。甚至我们可以从庄子的文本中窥见,庄子也并不认为逍遥是能够普遍达到的,而只是少数“真人”、圣人才能够进入的境界。所以庄子的“超越的逍遥”带有一定的不可实现性。
而郭象的“逍遥”与庄子的“逍遥”不同,其“逍遥”是在同一维度上来讲的,是停留在现世之中,具有现世的可实现性。不存在庄子哲学中超脱现世,达到精神境界的超越性。郭象认为万物只要“各足其性”就能够达到“逍遥”境界,即满足“自性”的要求就能够实现“逍遥”。
(二)境界层次和现实性的不同
除了在实现主体、实现方式以及理论结构上的不同,二人的“逍遥”在境界层次上也存在不同。
庄子的“逍遥”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超越,是与万物为一的无我的境界。《庄子·逍遥游》中讲,“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1]6所以庄子心中真正的“逍遥”是无所依持的。这种精神境界的追求与超越是不存在区分的。但在郭象的哲学中,“逍遥”出现了“有待”与“无待”的区分。
郭象的“逍遥”不同于庄子在精神境界上的超越追求,而强调满足于现世的“冥然与时世为一”[4]。所以是人人都可达到的现世意义上的境界。所以其“逍遥”随之出现了两个层次,“有待”的逍遥和“无待”的逍遥。“有待”的逍遥是普通世人的逍遥,而“无待”的逍遥是圣人的逍遥。郭象认为“故有待无待,吾所不能齐也”[2]11,也就是说,“有待”与“无待”的逍遥,二者不能够等同。
在《庄子》中,同样也讲“有待”。但庄子所讲的“有待”具有凭借的意思,用于说明列子想要达到某种目的,亦要“有所待”,即有所凭借才能达成。所以庄子的“有待”,并没有形成“有待”与“无待”这样的相对的概念。
而郭象在其《庄子注》中,对“有待逍遥”与“无待逍遥”进行了明确的区分。郭象认为,“有待”的逍遥,即是寻常人也可达到的逍遥。普通人安于自身的性分,对于自身所处的位置、应尽的本分,进行充分的实现,这样就能够实现“逍遥”了。所以他讲:“苟有待焉,则虽列子之轻妙,犹不能以无风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2]11即使是像列子一般身姿輕盈,也需御风而行,不能够在无风的情况下快速的行走,所以世人之“逍遥”必须要有所待才能够达到。
这种普通人的有所待的逍遥是通过“自足其性”的方式达到的,是“性足”之后对于自我之性的实现。
除此之外,郭象还提出了与之相对的“无待的逍遥”。“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御六气之辩者,即是游变化之涂也。如斯以往,则何往而有穷哉!所遇斯乘,又将恶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2]11郭象讲,圣人安时处顺、物我同冥,通过自身的修养以达到不依赖于外物的“玄同彼我”的状态。如此便是无待的逍遥了。
“有待”“无待”皆是逍遥,所以郭象注解庄子的“无待”,将其解释为无所不待,而不是无所待。郭象的“有待”之逍遥与“无待”之逍遥分别代表了现世与超越,郭象将二者结合,把庄子停驻在理想境界的逍遥拉入世俗,获得了现实的可能性。所以二人的“逍遥”境界具有现实性的不同。庄子所讲“逍遥”是完全作用于精神世界的精神追求,在现世是难以达到的。是庄子在不满足于现世的情况下所追求的对现实世界的彻底抛弃与遗忘。通过对外在束缚的摆脱,达到精神世界的超越。所以本质上来说,庄子的逍遥只是他理想的一种境界,不具有普遍的现实性。
而郭象是在独化的基础上,寻找整体上的“相因”,也就是绝对和谐。通过人的“各足其性”,满足“性分”之下对不同存在的不同现实要求。本质上来讲,这是对处于不同的社会分工之下的人,强调每个人都要尽其职分,安于职分,如此即可达到“逍遥”的示意。其目的具有一定的政治性,用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这是一种作用于现实社会的“逍遥”,具有可实现性。
综上所述,庄子与郭象的“逍遥”概念,存在着“逍遥”的主体、实现方式、理论结构、境界、现实性等区别。
结语
本文对庄子与郭象之“逍遥”从不同层面进行了简要区分,试图较为完整的对其不同之处进行分析说明。
郭象之“逍遥”与庄子之“逍遥”的不同,与郭象身处其时代的特殊性以及《庄子》文本的复杂性、丰富性是紧密相关的。其区别的最紧要处在于是否具有可实现性。郭象所处魏晋时期,当时的哲学家们主要都在围绕如何将儒学从僵化的经学之中脱离,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展开讨论。所以郭象注庄子之“逍遥”义的最大不同,也是就这一点而产生。
庄子之“逍遥”是基于“道”的宇宙生成论之下的,其“逍遥”本质上是对于“道”的追求。而郭象之“逍遥”以万物自生自有的“独化”论为基础,否定了大道化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过程。认为万物“各足其性”,达到“自性”的充实,即可进入“逍遥”的境界。郭象在宇宙生成上对“道”的权威,以及庄子的“安命”思想进行了否定。这一思想的改变,是郭象《庄子注》对于《庄子》根本性的颠覆。
注释:
①郭象(约252—312年):字子玄,河南洛阳人。西晋玄学家。少有才理,好《老子》《庄子》,能清言,常闲居。辟司徒掾,稍迁黄门侍郎。东海王司马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任职专权,为时论所轻。尝以向秀《庄子注》为己注,述而广之。一说窃注之事,恐未必信。力倡“独化论”,主张名教即自然,为当时玄学大师。
参考文献:
[1]杨柳桥.庄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6-68.
[2]郭象.庄子注疏[M].成玄英,疏.北京:中华书局,2021.
[3]刘笑敢.两种逍遥与两种自由[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
[4]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216.
[5]刘笑敢.从超越逍遥到足性逍遥之转化──兼论郭象《庄子注》之诠释方法[J].中国哲学史,2006(3).作者简介:刘佳鑫(1996—),女,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单位为黑龙江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责任编辑: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