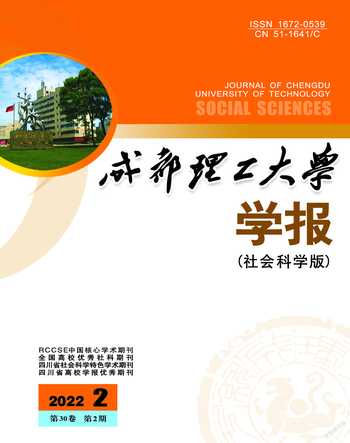国家监察权规范运行的学理阐释与建构方向
摘要:对监察权研究从整体上进行规范分析及规范构造是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化的核心范畴。从规范分析视角出发,阐释监察权的双重属性、演进逻辑及功能定位,理性认识其在现行宪法中“监察权”规范结构。通过将其置于“政党-国家”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以人大宪法制度下功能主义结构为分析框架,进一步阐明监察权在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功能发挥,打通纪法贯通下监察权的结构逻辑和效能,破解监察权运行实践中的规范性不足等问题,从而建构科学的、面向本土法治实践的监察权规范体系,正确定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监察法;监察权
中图分类号: D926.3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2)02-0028-11
监察是中国政制的专门概念,在不同的监察体制下,监察权具有不同意涵表达[1]。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新型监察权作为监察制度的基础性权能,在属性上表现政治权威性和法律权威性的有机统一;在功能上表现为监督、调查、处置、授权四种职责形态;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表现为党纪与政纪监督、职务违法调查、职务犯罪调查一体多维面相;在体系上表现为多功能、高效率、一体化的整体指引[2]。宪法学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体现在监察权本身复合性如何精致界定。从“规范主义”宪法学视角考察,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宪法修正案》)使得“本已复杂的内部结构更加复杂化,形成了多元复合的宪法体系”[3],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总纲,从而将政治话语中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转化为宪法规范的总目标。因此,积极展开学理构建,针对宪法文本中相对完备的“党的领导”规范体系[4],以应然、系统的视角构建监察权理论。对监察权的规范阐释要坚守既要关注其内部规范要素,也要考察规范形成的历史条件以及规范之间的关系。对时代变迁中的规范分析不能停留于现有的法律规定本身,必须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视角加以阐释,增进规范与实践之间交互影响。
一、监察权的基本内涵
监察权的规范阐释是监察理论生成与实践运行的基础,对监察权的规范阐释既要关注政治实践动态,也要将政治实践融入理论的创新和提炼之中,通过集成和再造重构赋予监察权不同的时代内涵。目前,对监察权的研究主要围绕监察权属性、权责配置、组织体制以及改革过程中配套措施等层面展开,有以下学术观点。
其一,强调监察权在宪法制度下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属性。叶海波教授认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应当落实宪法的指示,合理配置监察权,建立监察组织法、行为法和基准法的融贯体系,以法律明确监察权限、监察程序和监察标准,并以既有的机关监督机制为基础建立环伺式的监察权监督模式,形成‘有限’和‘有效’监察的国家监察法治体系。”[5]秦前红教授认为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间关系及运行需以宪法为遵循,同时需注重宪法制度下之国家机构设置与权力运行的轨迹[6]。刘小妹教授认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通过重整监察权,“重构国家监督体制和宪法权力结构,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监督国家机关和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二元’监督体制”[7]14-27等。
其二,强调以纪检监察合署办公为逻辑起点进行分析,将“监察权”纳入纪检监察合署办公体制对“纪检监察权”加以形塑。刘怡达博士指出,将党内法规引入纪检监察权力体制,“实现纪检监察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共治”[8]。王建国教授与谷耿耿博士认为,要处理好纪检监察合署办公引发的监察权与党的监督权合二为一的权力行使方式问题[9]。张梁博士认为基于我国国家治理中“决策、执行、监督”的逻辑结构,监察权涉及党的治理和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二维”属性,“二维”监察权的本质属性是为制约执行权及服务决策权的监督权[10]等。
其三,强调监察权与行政权、司法权的有效衔接及反向制衡。龙宗智教授认为通过监察委员会内部设置相对独立的刑事调查部门可以增加与司法机关协调衔接,构建国家机关之间权力配合、制约新格局[11]。朱福惠教授认为监察机关的职务犯罪调查具有原职务犯罪侦查的法律效果,属于刑事诉讼之发动,应当构成检察机关反向制约监察机关的法律依据和基础[12]。卞建林教授认为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銜接,应当主动关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以及以审判为中心的实质作用,构建惩治腐败与保障人权兼顾的体系[13]。陈伟教授认为监察法与刑法中的相关概念并非一一对应,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调查,应采取监察法和刑法分别判断的二元论。同时,刑事实体法需要调整彼此之间的非协调性,确保监察法与刑法之间的衔接顺畅和规范运行[14]。王青斌教授认为通过赋予被调查人程序性权利,创制监察内部申诉机制、保障被调查人诉权及国家赔偿责任等实现监察权与被调查人权利保障并重[15]。
其四,强调中国特色反腐败治理的结构安排与功能实现。李晓明教授、苪国强教授等提出了将“监察权定位为宪法制度下国家集中设置的反腐败权力,并以其为中心提出国家监察体制构建的构成要素”[16]3-4。张震教授等认为监察权监督的基本属性和职权拓展应当以回应和契合时代变迁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为中心,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监督体系[17]。
可见,上述学术观点都基于不同的视角,合理地揭示出了监察权表现出的不同内容,为推动监察权规范阐释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支撑。然而,监察理论及其制度的发展滞后于监察实践的发展,监察权的规范与实践之间存在眺望监察法治远景“鸿沟”[18]。监察权理论、监察法理论的发展滞后,不能对立法进行有效指导,直接影响了监察立法及相关配套立法。在国家监察领域中,监察法属于基本法,但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中还存在大量的概念概括、抽象、模糊的涵义以及“留白”,不足为监察理论与实践提供足恰的制度供给。如何有效破解此间的壁垒?公法学者试图建构“国家监察法学”理论体系,形成以法学学科为背景下“合法性原则、民主正当性原则、功能优化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的监察法治原理为轴心,以监察基础理论、监察法律制度和监察实践应用的立体化监察法学范畴[19]。反腐败研究学者则通过建构以监察立法为起点,以监察职权为范畴、监察法理为支撑,形成以相关法律制度、监察实践及其规律的开放、融贯、发展监察法体系[20]。值得肯定的是,部分学者已转向关注系统性、应然性立场建构监察理论体系。这也正如英国政治学家约翰·密尔所言:“监察机关是对行政部门中的疏忽、徇私或假公济私行为规定精心设计出来的控制办法。”[21]基于我国本土资源为基础将监察权定位为反腐败权力,围绕反腐败权力系统配置各类要素具有合理性[16]3。
法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有兩对方法论范畴,即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22]。“规范分析方法主要关注法的合法性、法的运行效果、法的实体内容,全方位考察法的构成要素,由此制度事实构成规范分析的对象。”[23]可以讲,宪法不可能脱离政治形态而存在,其本身是一种价值法和政治法,“其规范性与一个国家占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治力量之间不可能产生完全符合的逻辑的一致关系”[24]。目前,监察权研究缺乏系统的规范分析,导致监察理论构建滞后且监察权定位模糊,对服务于监察法治实践中的问题解释难以自洽,监察理论也无法为监察法治实践提供可靠性的系统理论支撑。显然,围绕法律文本和规范分析展开探讨,不可脱离特有的政治立场[25]。在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所以,监察权规范阐释必须考虑执政党这一核心因素,阐明监察权在党政体制中的特殊规范结构,界分监察权在法律关系中的具体表现。探明建构国家监察理论的监察权基本理论基础,进而指导监察法治实践,形成国家监察法治理论与监察法治实践之体系融贯。
二、监察权的历史溯源与理论逻辑
(一)监察机关监督权的历史演进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战国、两汉时期,为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早期形态;第二个阶段为唐宋元时期,为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基本定型期;第三个阶段为明清时期,为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最后发展阶段[26]。总体上看,在古代中国,皇权赋予监察官员秩卑权重,通过以官秩较低官员监察官秩较高官员的方式,快速诊断国家治理中的弊端,以卑察尊的政治目的在推进君主决策和提高监察权运行实效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汉代“选第大吏,所荐位高至九卿,所恶立退,任重职大”[27];唐代“持有制命,奉制巡按”[28]等制度。监察官员秩卑权重的制度设计与历代君权控制下的古代国家治理和权力运行实态相契合,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皇权的烙印,古代监察制度与监察权运行有违权力监督自上而下的常态,引发监察权过度干扰行政权,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2018年以后,监察权已作为一种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新型国家公权力被纳入宪法权力结构之中。事实上,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务监察发展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奋斗中反腐倡廉历程是一致的。1921年至1949年,从党的纪律建设到党的监察制度;从工农检察委员部(会)制度、参议会监察制度、华北/陕甘宁边区人民监察制度,这个阶段党内监督和政务监察的探索为新中国成立监察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监察权伴随人民监察委员会、监察部(局)等机构的设置、撤销呈现不同的形态。从新中国的监察制度发展历史看,可以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监察制度、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监察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的监察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监察制度[29]。
(1)对监察制度的奠基和曲折探索时期(1949-1982年)进行考察,可以大致总结出以下特点。第一,政务监察权主要发挥加强政权建设,如1951年政务院颁布《各级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设置监察通讯员试行通则》规定,各级政府内广泛聘用人民监察通讯员,以“密切联系人民,加强监察工作”[30],直至1959年4月撤销监察部。第二,党纪监察权主要功能是对党员的检查和处分以及接受党员控诉和申诉。如1956年9月2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七章专章恢复设置“党的监察机关”,并规定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地方监察委员会的选举方式、工作职责及领导关系。然而,1969年和1973年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将“党的监察机关”删除,这也为监察法和监察制度发展的暂停埋下了伏笔。在1977年《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恢复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和团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具体职责,包括纪律教育和检查纪律情况等。总体来讲,这段时期人民监察委员会的职权定位较低,党的监察机关的组织、职责摇摆不定,在“立”与“撤”中举步维艰,群众监督制度保障缺失,基于“政务监察-党纪监察”实效不彰在所难免。
(2)对监察制度恢复和发展时期(1982-2018年)进行考察。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并在此党章的第八章专章设立“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详细列举了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责、职能、工作流程等。同年12月《宪法》颁布后,我国开始着手恢复重建国家层面上的监察机关。1986年11月,在《关于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议案的说明》稿件中,首次将监察机关定位为“专司监察职能”的国家机关。然而遗憾的是,在1990年颁布的《行政监察条例》中规定“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专门机构”。1993年监察部和中央纪委合署办公,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模式[31]。基于1982年《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1995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正式成立。自此,我国权力监督制约构建起了“以纪委为主导、检察院为保障、政府监察机关为补充的‘三驾马车’模式”[32]。从1993年至2018年,以“三驾马车”模式下权力监督制约与反腐败制度试图通过权力分立制约,构建“纪检监察、行政监察、检察监督”协调衔接的高效反腐模式,然监察范围狭窄、监察职能分散、“同体监督”难证,此25年间我国监察制度和监察法制在不断探索、重组和发展[33]。此外,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九大对党章进行“修改”或“修正案”中对“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进行了专章保留并不断完善。行政监察、法律监督法制中相关条文亦如此。对监察制度全面整合提升时期(2018年至今)的考察。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将试点地区人民政府的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职能进行整合和重组,组建监察委员会,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2017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3)截至2018年2月底,全国31个省级、340个市级、2849个县级监察委员会全部完成组建,划转编制6.1万个,转隶干部4.5万人[34]。全国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全部完成组建。2018年《宪法修正案》通过,在宪法“国家机构”中增设“监察委员会”。中共十九大以来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形成不敢腐的震慑。与过去的行政监察机关相比,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地位、独立性前所未有地提升,有效整合多种反腐力量。在监察对象上,监察范围扩大为法定的六大类。在领导体制上,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后,既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要对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上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接受其监督[17]80-82,在中国特色国家监察制度史上具有史无前例的开创性意义。
(二)监察权监督属性的理论逻辑
监察权作为“治官之权”“治权之权”,其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它是以马克思国家权力监督观为基础,以“权力制衡思想”为借鉴,创造性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型国家权力监督观。
1.分权与制衡之结构性权力制约的批判与反鉴
人类至今几千年的政治实践表明,对权力必要监督制约与发生腐败现象成反相关。正如阿克顿所言:“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35],“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在的或内在的控制力”[36]。从早期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合而为一的“君权神授论”,到以洛克、孟德斯鸠倡导的权力分立理论所提倡的“权力民授论”,再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开创的“人民主权论”,人民(公民)始终是权力来源的核心。“三权分立”可以从制度上保障公职人员廉洁从政,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公职人员的廉政问题。我国分权制衡观的核心在于“分”,规范约束之功能;制衡在于“合”,强调权力之间行使协调与衔接的体系性调整功能。马克思主义国家权力监督观认为,权力监督是政党与国家的基本职能,同时也是维护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重要方式。随着政治制度的不断发展,监察制度在政治机构和政治治理中扮演着平衡国家权力及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37]。例如,我国老一辈公法学者王连昌先生很早就洞察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监察权则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事业不可缺少的武器”[38],并提议重建国家监察机关。新时代,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基于时代变迁需要创设出了监察权,并根据分工负责、功能适当等原则将该权力重组并配置给了监察机关。作为一种新型国家权力的监察权,其调整功能主要表现为在国家机构中“引入”党政体制,以执政党的绝对领导为监察权行权的出发点,以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为监察权运行的基本保障[39],彰显分权制约理论的中国智慧。
2.分工与配合之功能性权力监督的基础与发展
诚如青年政治宪法学者田飞龙指出,我国宪法结构表现为人民主权在“基于真理的党的领导代表制+基于程序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非代表的参与民主制”[40]的“三重肉身”。传统的权力制衡模式是突出人大制度模式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制约与配合功能,而在我国政治实践中,“执政党本质上应当是一种社会权力,然基于我国特殊的政治传统及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影响,执政党的权力也是应当属于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重要部分”[41],基于党的领导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各自形成纪检检查权、人大监督权、行政监察权、法律监督权四项监督权力。党的纪检督权是由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行使,通过对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业务情况以及政治生活等方面展开政党内部监督,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政党内政治秩序及作风制度建设。人大监督权是指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为全面保障国家法律的实施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法定程序,对其产生的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开展的检查、调查、督促、处理的强制性权力。行政监察是指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依照国家法律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法律监督权是指在法律实施中严重违反国家法律的情况所进行的监督,表现为专门性监督和程序性监督两个方面。基于上述四项监督权力,分别在各自的场域开展监督工作,各项权能难以逾越权力间“高墙”壁垒,在出现监督职能交叉、僭越时或极力避免抑或争论不止。一方面,监督权的独立性难以有效保障,同体监督的实效不彰[42];另一方面,监督力量分散,各类监督监察主体在各自的领域内开展监督工作,难以形成实质意义上的监督合力[43],不可避免地形成权力制约的有限性、同体性及分散性监督乏力等弊端。例如,检察机关集公诉、监督、侦查于一身,既参与诉讼,又监督诉讼;既自行侦查,又自行审查起诉,有违侦、诉、审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的法治原则,饱受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诟病,客观上减损了司法公信力。所以,就需要在人民主权制度下对权力“元素”重新分离、重组,形成新的分权与配合的模式。监察权是独立于行政权、司法权的一项新型国家公权力,它将原隶属于党的党纪监督权,政府的行政监察权与行政违法预防权,原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与职务犯罪预防权从原有的“党纪监督权、行政权、法律监督权”中抽离出来,在党的领导与人大制度统合下的国家权力结构范畴内进行重新分配、重组的新型国家权力。
需要注意的是,新型监察权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所代表的党内监督职权相结合,共同構成我国以反腐败为主要导向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组合使得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实现了紧密契合,优化了国家监督职权的运行效能。于逻辑上而言,监察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主要缘于现行的监察体制未能有效地发挥其预期功效,监察体制自身及其运行皆存在某些问题。而此次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则是实现了对不同监督部门监督“职权的整合”[44],以促进监督实效的提升。此外,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使得监察委员会同时具有这两类国家机构的属性,既是党的监督和国家监督协同衔接,又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和报告工作。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权最终来源于人民的赋权,同时又要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因此,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使得作为政治原则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得以一定程度的法权化[45]105。监察权基于“社会关系双方主体的调整,既制约他人也制约自身”[46],复合型监察权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监督新模式及权力相互制约、相互配合新格局。
三、监察权规范建构的基本属性与功能定位
(一)监察权的属性定位
监察权在中国特色监督体系中表达鲜明的政治属性和法律属性,两者并行不悖。政治属性体现党对监察工作的领导地位;法律属性体现监察权运行必须受制于法治规范,监察权必须受到人大制度下宪法制度分权的制约与监督。
1.鲜明的政治权威属性贯穿监察权运行始末
“国家监察委员会履行监察职能的最高政治原则与价值功能是维护中央权威、巩固执政党地位、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党纪国法的尊严和权威。”[47]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监察权之根本。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实现“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其核心要义是“党统一指挥”,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制度70年以来实践优势的彰显,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发展历程。同样也是构建国家监察制度、中国特色监督体系的正当性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福祉的无产阶级德性政党的逻辑前提。基于党史考察,党的不同历史时期,只有将党内监督作为根本,以党内监督带动外部监督并不断完善“政党-国家”协同监督体系[48],才能实现政治清廉、国家良法善治、社会安定有序之局。
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最本质的特征”写入总纲。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的政治话语转化为法律话语。同时,2018年《宪法修正案》赋予各级监察机关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监察法》第二条规定:“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采取合署办公模式,因此,它既是执纪机关,又是执法机关,履行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的双重职责,合署办公的根本目的是要强化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从纪检机关与监察机关两者的属性和依据上看,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是经《中国共产党章程》定位的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监察委员会是经《宪法》定位的国家监察专责机关。因此,纪律检查机关与国家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共同构筑起了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防线”,增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力。改革后,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明显,主要表现为:首先,在党的直接全面领导下,监察机关代表党和国家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全面性、零死角”的监督,既调查职务违法行为,又调查职务犯罪行为。可以看出,监察体制改革契合我国“广义政府”的范畴下国家机关权力行使的实践[49]。从总体位阶上看,监察权是依托纪检、拓展监察、衔接司法的三维层次展开,总体指向构建“一加一大于二”的新型国家监察模式。其次,纪检监察合署办公是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的监督逻辑位阶,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监察纪法贯通的全面覆盖。有效回应原纪检部门与检察院在各自工作范围内展开协调配合时也存在众多阻滞。
二是,执纪执法中的政治属性贯穿监察法治实践。“良法产生美德,美德产生良法。”[50]实践表明,良好的政治生态的形成通过监察机关和紀律检查机关合署行使得以彰显。党政机构合署采用的是新公共治理中的混合式组织形式,通过党规和国法的混合法实现组织关系规范化后,其权力的行使必然依法进行。党政机构合署是在合理分工,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实现内部权力分配与协调、衔接,共同在党政场域中的组织任务。在具体的公职人员腐败行为中往往会牵扯到错综复杂的利益甚至严重政治问题。例如在日本、新加坡早期腐败案件中,一般都存在党、政、财“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51]。公职人员的贪腐行为既削弱党和政府公信力,又破坏某个区域甚至全国政治生态,也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传统查办公职人员职务违纪违法、职务犯罪的调查或侦查模式已是捉襟见肘,亟待向制度顶层诉诸“政治权威”襄助。
反腐败是关系政治生态和人心向背的重大政治问题,政治生态直接关系法律的实施和政治治理的双重实效,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党员、公职人员廉洁从政从业良好形象的认同与信任。《监察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进行监督检查。”可见,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进行监督检查,既是监察机关的法律职责,又是一项政治职责。世界上多数国家都认为,一旦出任公职以后,政府官员就应比一般老百姓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因此其公然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也属于腐败范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抓作风建设,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反对奢靡之风,就是提出了一个抓反腐倡廉建设的着力点,提出了一个夯实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切入点[52]。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是始终坚持党的统一领导,通过将“党的领导”这一政治根本原则执纪、执法的全过程,实现党和国家集中统一、高效权威反腐败目的,也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政治原则的重要表征。
2.极强的法律权威属性保障《监察法》全面实施
《监察法》所确立的监察制度和监察权, 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具有监督、调查、处置三项权能,以及讯问、询问、留置、搜查、调取、查封、扣押、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调查措施,这些措施几乎涵盖了《刑事诉讼法》中的八项侦查措施。这种前所未有的法律权威性表现为监察权职权的全面性与纪法贯通性、独立性与异体监督权威性两个方面。
第一,全面性与纪法贯通性。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旨在构建多功能、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监察权,实现党纪监督权、行政监察权、检察监督权三项权能的有效整合、重组,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制度。一是监察对象依法全面覆盖。根据《监察法》第三条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改变了行政监察“监察对象失之过窄,权力监督存在盲区”[53]的弊端。重组后的国家监察权监察范围更广泛,其覆盖了从党、政机关至一切依法行使公权力的人员。因此,国家监察全面覆盖已经超越了对传统“公权力”监督对象的涵射范畴,覆盖从公权、公职、公务、公财等实质要件为要素判断和界定的所有公权力所涵射的法定监察范围[54]。二是调查措施依法全面覆盖。为依法全面开展监察工作,《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在行使调查权中可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调查措施,这一系列的措施几乎涵盖了《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查强制措施规定。以“讯问”“留置”措施为限制人身、财产等权利最为严厉,“搜查”等措施的强制力次之,同时配置相应法律程序严格调查权的行使。例如《监察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调查人员进行讯问以及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备查。”可见,同步录音录像范围在监察法中得到更加广泛的使用。《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显然,这里的“非法方法”要比刑事诉讼外延更宽。再如《监察法》第二十二条对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的使用条件、审批程序、场所、期限等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这是对监察机关适用留置措施合法性的确认,实现了“两规”的法治化。三是监察职能依法全面覆盖。《监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依法赋予监察机关行使监督、调查、处置的职能。从广义上讲,监察机关监督职责相较于调查和处置两项职能更广泛且居于首要地位[55]。从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至留置等履行方式均有体现。因此,开展调查、形成调查结论、形成处置意见或建议都是为最终的监督提供支撑。从狭义上讲,《监察法》规定开展日常监察的具体履职方式为廉政教育和监督检查工作两项,监督职能是调查、处置的前提和基础,“三者有机统一于强化国家监察、加强权力监督、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生动实践”[56]。可以说,在合署办公体制下,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执纪、问责与监察机关的监督、调查、处置是对应的,实现党纪与国法相衔接、相贯通。
第二,独立性与异体权威性。根据2018年《宪法修正案》的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由此可见,监察权的独立性表现为监察权在运行的整个过程中不受来自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以及社会团体和个人的不当干涉,而保持一种相对独立的半封闭状态。独立性特征较为明显的表达监察委员会能够充分发挥异体监督的比较优势,从而对各国家机关展开充分且适当的监督。监察委员会不会受制于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避免了监察权不独立所带来的监督无效、低效的诟病。有学者指出,我国宪法赋予国家机关的“独立行使”概念是一种相对概念。例如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批权,仅指独立行使审判权,而非法院独立,更非司法独立。因此,这种相对独立状态应当是将“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检察机关、中国共产党除外,就是说,他们可通过合法途径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必要的干预”[57]。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权的独立显性优势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监察机关独立于“一府两院”,其融入人大宪法制度之下,由人大任命,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形成“一府一委两院”的权力制约格局,监察机关是依法独立的反腐败专责国家机关。首先,创设国家监察权的初衷即是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高度和视角上重构对国家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而公权力的扩张性天然地排斥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势必对监察权的独立行使造成较大困扰。因此,监察权保持宪法层面的独立性,才能最大限度地抵制国家权力(实践中主要是规制行政权及其他依法赋予的国家公权力)的恣意侵扰。其次,监察机关依法不受干扰地行使监察权是监察权独立运行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障。因此,这里的“依法”是指监察机关履行职责所必须遵循法治基本原则,一方面,监察机关必须给监察“全面覆盖”划出“监察红线”;另一方面,监察机关自身须设定恪守权限,不仅体现在人大制度下权力制约与监督,以及《监察法》具体条文及法治价值的承载为规范指引[7]17;还体现在纪检监察合署办公模式下更加强调党内监督的功能。把监察权“关进制度笼子”,监察委的权威和效率才可得以全部激活和彰显。
二是,新设监察权是一个专门承担反腐败综合职能并与其他国家权力相独立的宪法性权力。监察权相较于行政监察权、检察监督权(职务犯罪侦查权)而言,其行使独立监察、异体监察之职能。通过改革将“分散”的部门监督权力整合并转化为国家监察权。确立国家监察权的宪法独立性定位,在人大制度下构建权力分工、配合、制约的关系。监察权的独立行使是与实现权利与权力的价值相平衡,实现监察权与宪法制度下其他权力的平衡,实现监察权与其他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58]。因此,监察权独立运行是监察活动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世界各国都根据自身发展赋予相应反腐败机构较为独立的反腐败特别调查权,如新加坡在1952年成立专门反贪机构——反贪调查局(简称CPIB)赋予其独立的案件调查权、逮捕权、搜查权、扣押权、搜集腐败犯罪信息权等[59]。《芬兰宪法》第38条规定独立的议会监察专员,其《议会监察专员法》赋予监察专员自主、广泛的监督调查权[60]。北欧国家通过法律赋予监察专员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的监督权,主要职责是对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的监督[61]。这充分说明在这些全球高清廉指数国度中,它们均结合自身的文化制度赋予国家监督(监察)机构极高地位且具独立行使监督权限、手段,形塑一个强力的监督机关以对抗被监督者的不当干扰。
(二)新型监察权的功能定位
在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两个问题上,功能性分权关注的是权力的运行,功能性分权提出了通过改善权力运行的方式和功能,逐渐对权力结构提出改革的要求。监察权的创设便是功能性分权的产物,对监察权的功能定位应置于新的权力运行之下,通过逐渐优化监察权运行方式和功能推进监察体制改革。《监察法》第三条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职责是“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具体履职方式为“监督、调查、处置”。通过国家立法把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机制法定化,逐步将中国特色监督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监察权职权和运行上看,监察权的运行须同党内监督结合起来。
1.横向上的功能,监察机关依法行使监察权包含三层次的功能
第一层次,依法对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第二层次,依法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第三层次,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等,以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勤政、廉政监督的全面覆盖。
2.纵向上的功能,监察权主要包括调整功能和保障功能
(1)调整功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地方试点→国家立法”形式展开,通过创新权力制约监督方式推动权力制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层面上的革新,本质上是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实践,是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的最新成果。从调整结构体系上看,监察权的创制是通过党领导实践与党领导立法赋予监察机关履行国家监察职能,从宪法制度层面赋予其政治属性与法律功能,其目的是要实现维护党中央权威、党纪国法权威、巩固执政党地位、维护国家统一。纪检监察合署办公模式既是对原党的纪检机关和行政监察部门合署办公模式内核的承继,又是根据新时代的具体国情需要对国家权力监督模式进行的自主性调适与创造性重构。因此,监察机关与党的纪检机关合署办公模式从逻辑上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这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政治原则的重要表征”[45]105-106,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前提下的各有分工、相互配合协作关系的具体化。纪检监察合署办公模式的完善就必須依赖国家监察权的行使过程中党纪与国法的有效处理和衔接,这亦是打通中国特色监督模式的必由路径。目前,以原有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模式为基础,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拓展,“形成了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视监督、派驻监督四个全覆盖的权力监督格局”[62]。
首先,从调整范畴上看。改革后,党内法规对纪检监察机关的影响将更为直接,甚至成为纪检监察机关组织运行的重要依据。纪检监察机关同时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两种职能,其职权源于党章及党内法规和宪法、监察法及监察法规,其具体履职依据则包括党内法规和国家监察法律法规。党内法规要求任何党组织、任何党员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无期限的,个体一旦加入党组织,就必须要让渡一部分权力到党组织。可见,党内法规比国家法律的调整范畴更大,它强制要求党员在行动和思想上与党的要求保持高度一致,不得偏颇。
其次,从调整内容上看。“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蕴含着没有起点、没有终点,执纪没有时限限制,保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员干部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的违纪违规行为,均要依纪依规严肃惩处。然而国家法律是全社会、全体公民的规矩和“社会底线”。《宪法》第五條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国家法律要求任何行为都必须限定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任何破坏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应受到依法制裁。党内监督与国家法律监督具有两个不同规制范畴,党内法规对社会中党组织、党员进行规范。国家法律是对全社会成员,它规范的社会成员群体更广泛。党内法规侧重于对党组织、党员的“高标准”规范,国家法律侧重于全社会成员的“最低行为”规范。因此,必然会出现党内监督的范畴与国家法律监督的范畴存在极大的重合性、交叠性,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要构建既统一又相互独立的纪检监察合署办公模式。
(2)保障功能。
根据宪法规定,国家机关监督首要还是突出人大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产生国家机关,产生的国家机关受人大监督。按照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职权,人大监督的方式主要为:听取审议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提出询问或质询等,对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权力运行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以防止其权力滥用,保证国家机器按照人民的意志依法运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设立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是逐步推进人大监督具象化的体现。
首先,从保障的党和国家体系分层上看。监察权是人大宪法制度下党和国家机关监督制约的新型国家权力。监察权的设置是保证政令畅通,维护政治纪律,提高治理效能。监察权的保障功能在于独立的国家监察权强化了国家机关的分权与制衡。一是监察权保障监察机关履职。有效保障国家机关权力运行处于同等的监督与制约,规范其他国家其机关行使权力的边界及限度,特别国家机关权力秩序的合法化,规范国家机关接受监督的常态化、制度化,构建从“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权力制约新常态。二是监察权保障国家监督体系构建,增强廉洁行政和效率行政的目标。通过监察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所管辖部门单位形成“敢抓敢管、严抓严管”的局面,促使国家、区域的政治生态持续向好。三是监察权保障调查权规范行使及规范监察对象职权行为,构建有效防止滥权和保障监察对象的合法权益的国家监察价值目标。
其次,从保障的纪法贯通体系融贯上看。监察权构建起了党内法规到国家法律的“全面覆盖”实施方式。一是,党内法规是一切党组织、党员行为的准则和底线。党员一旦违反,依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条等条款规定,经谈话函询、初步核实、审查调查等党内执纪监督程序认定后,依纪依规可采取约谈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谈话、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等党内处罚措施,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另外,《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十四条规定:“党组织违反党内法规且失职的也必须问责。”因此,党内监督是对德型政党的“高标准”“严要求”规范,但其不具有刑罚处分权,是一般处分权。二是,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国家法律监督主要以强制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政治权利、经济文化社会权利,严重者可以判处其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依法剥夺生命刑。可见,国家法律惩罚的严厉程度要远高于党内纪律处分。基于党内处分与国家法律惩罚的“二元”结构,必然造成“阶下囚”与“好干部”无法衔接,易导致机械的“二分”结构,出现“虚监、失监、漏监”的真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着眼于所有公职人员党纪、政纪责任的全覆盖式监督,重视追究效率、追究范围和追究力度。《监察法》“监察程序”专章从第三十五条至第四十九条规定弥补了党内监督与国家法律监督实质效力上的“缺漏”。在纪法援引依据上,初步形成了党内法规到国家法律法规的贯通、衔接;在纪法惩治手段上,构建刚性问责机制与加大打击腐败力度。
3.刚性惩戒与柔性惩戒的协同实施功能
考察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历史沿革,古代设置了监察机构和监察权,主要是维护中央集权,监察朝廷百官。通过实施立法监察、行政监察、司法监察,不断扩大监察权力,实现对监察对象的全覆盖,形成了扼制官吏腐败的全国监察网络。1928年至1948年训政时期建立了独立的监察院,赋予监察院弹劾、审计、调查、纠举、建议和同意等监察权。在社会主义中国,依法行使国家权力的公职人员具有对宪法和人民忠诚的法定义务。对掌握国家权力的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都做出严格的规范,一旦公职人员背离公职人员规范行为模式,就易滋生腐败行为。设置监察权的目标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通过监察权的惩戒功能发挥,净化国家公权力行使的环境。
首先,刚性惩戒。国家监察制度在宏观上是构建国家权力监督的制度保障。惩戒腐败、防止权力行使异化,是现代监察制度产生的动因,强化监察权在促进公权力规范运行与推进党和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则是监察权目标指向。所有腐败的形成则是驱使权力违背、脱离其产生的轨道。因此,通过国家监察制度的创设,形成权力监督制约架构,以最快的速度修复受损的区域或国家政治生态,形成公权善治。从根本意义上来讲,监察制度、监察权具有净化的作用及功能。通过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扭转公权力腐败、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通过高压反腐,对“老虎苍蝇一起拍”产生震慑效应。
其次,柔性惩戒。柔性惩戒功能主要是监察权针对某个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行为的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监察法》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四十五条中规定或暗含“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宽严相济”的价值,其中总则第五条是对监察惩戒功能基本规定,第一条第一款是对公职人员事前的监督,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通过谈话、前期检查可以约束公职人员正确履职,发现问题苗头可以及时处置,纠正偏差,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截然对立的状况,确保公职人员良好的履职能力。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都属于事后监督,通过开展监察调查,提出监察建议等措施,防止腐败的进一步蔓延。第四十五条是在处置结果中贯彻“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等原则。可以看出,监察权的柔性惩戒功能,既注重事前抓早抓小的防范,也注重惩治与教育相结合,这个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在监察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在宏观层面,拔“烂树”是刚性惩戒,治“病树”和正“歪树”是柔性惩戒。刚性惩戒和柔性惩戒相结合,才能不断净化政治生态。
参考文献:
[1]朱福惠.国家监察体制之宪法史观察——兼论监察委员会制度的时代特征[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25-35.
[2]黄鑫.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法治化构建之维——兼论“社会中心主义”与反腐“理性构建”[J].时代法学,2018,(5):64-71.
[3]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纲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119.
[4]秦前红,刘怡达.中国现行宪法中的“党的领导”规范[J].法学研究,2019,(6):18-31.
[5]叶海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约束[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14.
[6]秦前红.我国监察机关的宪法地位以国家机关相互间的关系为中心[J].中外法学,2018,(3):555-569.
[7]刘小妹.人大制度下的国家监督体制与监察机制[J].政法论坛,2018,(3).
[8]刘怡达.论纪检监察权的二元属性及其党规国法共治[J].社会主义研究,2019,(1):79.
[9]王建国,谷耿耿.监察权独立行使的法治逻辑[J].宁夏社会科学,2020,(6):67.
[10]张梁.中国特色“二维”监察权:属性、使命与功能[J].广西社会科学,2020,(2):110.
[11]龙宗智.监察与司法协调衔接的法规范分析[J].政治与法律,2018,(1):2-18.
[12]朱福惠.论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的制约[J].法学评论,2018,(3):13-21.
[13]卞建林.配合与制约: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的衔接[J].法商研究,2019,(1):15-22.
[14]陈伟.监察法与刑法的衔接协调与规范运行[J].中外法学,2019,(2):334-356.
[15]王青斌.论监察赔偿制度的构建[J].政法论坛,2019,(3):164-175.
[16]李晓明,苪国强.国家监察学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
[17]张震,黄鑫.监察权的逻辑认知与功能拓展: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阈[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135-142.
[18]金承光.《监察法》施行后的理论、实务与人才培养探索——“2019年监察法理论与实践暨监察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综述[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9,(3):122-129.
[19]秦前红,石泽华.新时代监察法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建构[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32-39.
[20]吴建雄.监察法学学科创立的价值基础及其体系构建[J].法学杂志,2019,(9):34-45.
[21]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M],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8.
[22]刘永林.法学方法论研究[J].法学研究,2001,(3):42.
[23]谢晖.论规范分析方法[J].中国法学,2009,(2):36.
[24]莫纪宏.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注重对监察权性质的研究[J].中州学刊,2017,(10):49.
[25]李忠夏.宪法变迁与宪法教义学 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15-16.
[26]张晋藩.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借鉴意义[J].经济导刊,2018,(10):88-95.
[27]班固.汉书(卷八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1:2533.
[28]王溥.唐会要(卷六十)[M].北京:中华书局,1955:1056.
[29]刘晓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监察制度发展历程、演进趋势及改革目标[J].社会主义研究,2018,(2):77-79.
[30]紀亚光.新中国成立初期“三位一体”监督体系建设初探[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5):6.
[31]晋藩.中国近代监察制度与法制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335-336.
[32]秦前红,叶海波,等.国家监察制度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3.
[33]秦前红.监察法学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157.
[34]钟纪言.改革开放40年纪检监察事业的创新发展[EB/OL].( 2018-12-18)[2021-11-20].https://www.ccdi.gov.cn/toutiao/201812/t20181218_185271.html.
[35]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候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88.
[36]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左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64.
[37]陶百川.比较监察制度[M].台北:三民书店,1978:1.
[38]王连昌.建议重建国家监察机关[J].现代法学,1981,(3):22.
[39]吴建雄,李春阳.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37.
[40]高全喜.革命、改革与宪法制度:“八二宪法”及其演进逻辑[J].中外法学,2012,(5):916.
[41]刘素梅.国家监察权的监督制约体制研究[J].学术界,2019,(1):114.
[42]刘艳红,夏伟.法治反腐视域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新路径[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89-99.
[43]秦前红.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与方法[J].环球法律评论,2017,(2):17-27.
[44]张春玲.监察权的宪法性质、职权配置与实践展开[J].学习月刊,2018,(8):49-51.
[45]翟志勇.监察委员会与“八二宪法”体制的重塑[J].环球法律评论,2017,(2).
[46]罗豪才.为了权利与权力的平衡:法治中国建设与软法之治[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6:184.
[47]徐汉明.国家监察权的属性探究[J].法学评论,2018,(1):9-10.
[48]曹雪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监督理念与实践的新发展[J].社会主义研究,2016,(4):61-68.
[49]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法规室.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52-53.
[50]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M]李桂林,李清伟,候健,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38.
[51]刘明波.外国监察制度:国外是怎样反腐败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7-156.
[52]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71.
[53]秦前红,刘怡达.监察全面覆盖的可能与限度——兼论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边界[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7,(2):17.
[54]谭宗泽.论国家监察对象的识别标准[J].政治与法律,2019,(2):66.
[55]纵博.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证据问题探讨[J].法学,2018,(2):122.
[56]余哲西.述评之二:监督、调查、处置一体推进——保证监察全覆盖的质量和效果[J].中国纪检监察,2018,(13):20-21.
[57]蔡定剑.宪法精解[M].2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441.
[58]黄鑫.借鉴与调适:贿赂犯罪调查模式宪法化探索[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34-135.
[59]新加坡预防腐败法[M].王君祥,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3-7.
[60]芬兰合作监察专员法 政府行为公开法案 预防和消除洗钱嫌疑法[M].赵晨光,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53-55.
[61]韩阳.北欧廉政制度与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37.
[62]闫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大举措[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10-31(01).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Construction Direction of
the Normative Operation of the National Supervisory Power
HUANG Xin
(School of Administrative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401120, China)
Abstract:The normative analysis and norm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research on supervision power as a whole is the core category of promoting the deepening of the nat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rm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dual attributes, evolution logic and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supervision power, and rationally understands its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upervision power” in the current constitution. By placing it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party-state” changes, and taking the functionalist structure under the NPC constitutional system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function of the supervisory power in improving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is further clarified, and under the connection of discipline and law, the structural logic and efficiency of supervisory power are analyzed, and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normativeness in the practice of supervisory power are solved. Construct a scientific normative system of supervisory power oriented to the practice of the local rule of law, and correctly position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al supervisory system.
Key words: reform of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party and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Supervision Law; supervision power
編辑:邹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