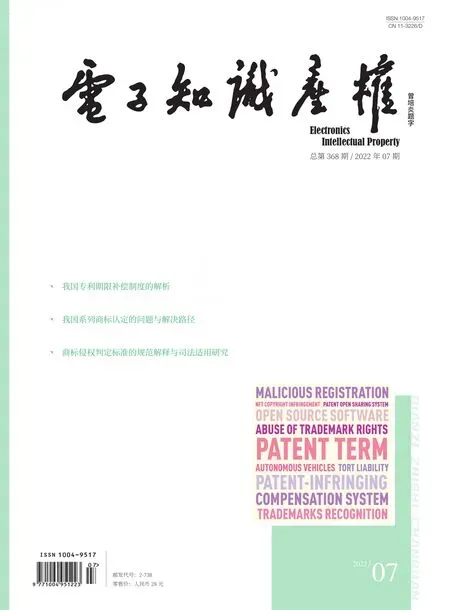我国系列商标认定的问题与解决路径
文 / 谢琳 曾俊森
一、问题的提出
实践中存在同一注册商标所有人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注册一系列具有共同构成要素的商标的现象。这类商标通常以“联合商标”“系列商标”“家族商标”等概念出现。1本文采用“系列商标”作为主要概念,“联合商标”“家族商标”等同于“系列商标”的含义。我国相关裁决往往会将数个具有共同要素的商标视为“系列商标”,将数个商标作为一个整体与争议商标进行对比,最终得出商标混淆的结论。然而,将数个商标作为整体看待意味着每个商标之间共享各自的知名度,商标强度由此提高,构成商标混淆的可能性也将更高。为了避免不当认定系列商标而导致产权外溢,对系列商标的认定需要相当严谨,并非注册一系列具有共同要素的商标就能被称为系列商标。在我国,由于登记制度的固有弊端与系列商标认定规则的缺位,相关裁决在认定系列商标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当前鲜少有研究对此进行关注。
(一)司法实践中的“系列商标”
在宣告商标无效的相关裁决中,商标权人将已注册的数个包含某一共同要素的商标作为引证商标,而争议商标也包含相同的要素。相关裁决往往会因为引证商标具有共同要素而将数个商标作为整体视之,基于争议商标包含各引证商标显著识别部分的共同要素,认定相关公众会认为争议商标是引证商标的系列商标而宣告争议商标无效。
1.基本案情
(1)“哈”字系列商标案2参见石狮市哈泉饮品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行终951号行政判决书。

在本案中,石狮市哈泉饮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泉公司”)是争议商标“哈泉”的权利人,第三人百威哈尔滨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威公司”)是引证商标“哈啤”“哈纯”“金哈”“哈”“哈尔滨”的权利人。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均被核定在相同或相似的商品种类上使用。争议商标被判无效。
(2)“诗仙”系列商标案3参见重庆诗仙太白巴乡春酒业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行终1765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行终1766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行终1767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行终1782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行终1783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行终1784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行终1785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行终1796号行政判决书。
在本案中,重庆诗仙太白巴乡春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乡春公司”)申请并注册了一系列含有“诗仙”的商标(争议商标),包括:“诗仙荟”“诗仙百年”“诗仙文化”“诗仙印象”“诗仙嘉宾”“诗仙小镇”“诗仙李”“诗仙美”等。重庆诗仙太白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诗仙太白公司”)持有的商标包括:“诗仙太白”(引证商标一至五)、“诗仙妹妹”(引证商标六)。争议商标被判无效。

2.裁判说理
在上述案例中,法院首先认为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的显著部分是商标的文字部分,如“哈泉”“哈啤”“哈欢”“诗仙太白”“诗仙荟”。紧接着,法院提炼出引证商标显著部分中的共同要素“哈”与“诗仙”,认为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均包含“哈”或者“诗仙”,在文字构成、呼叫、整体视觉效果等方面近似,相关公众容易认为使用上述商标的商品系来源于同一主体或者两者之间有特定联系,产生混淆误认。这种说理方式相当于通过共同要素将数个引证商标结合成一个整体,并将共同要素作为商标混淆的重点考量因素。换言之,注册数个具有共同要素的商标会加强商标的排他权,其他商标一旦使用相同的要素,就会提高构成混淆的可能性。
在考量引证商标知名度时,“诗仙”系列商标案并没有考虑引证商标的知名度。在“哈”字系列商标案中,法院从一系列商标的整体出发,认为“哈啤”“哈尔滨”系列商标在争议商标申请日之前已具有一定知名度,相关公众容易产生混淆误认。但是在判决中当事人仅提供了“哈尔滨”与“哈啤”知名度相关的材料,判决书中并未看到关于“金哈”“哈纯”“哈”商标知名度的证据。可见,在相关判决中,一旦数个引证商标基于共同要素被视为系列商标,商标之间就共享了知名度。
(二)判决存在的问题
我国商标注册以单个商标为基础,但是上述判决并没有通过单个引证商标与争议商标对比得出构成商标混淆的结论。相关判决说理遵循将数个商标作为整体的思路认定商标混淆:数个引证的注册商标均含有共同的要素,构成了一个整体,彼此共享知名度,一系列商标的整体强度因此提高,由于争议商标也含有共同要素,所以容易导致公众产生混淆或者误认争议商标是引证商标人的系列商标。然而,这种判决思路存在较大问题,可能产生与“单个商标对比”模式不一样的判决结果。其核心在于并非注册数个具有共同要素的商标就必然构成系列商标,商标权人不能轻易对商标的共同要素享有排他权。
以上述案例为例,商标权人注册了数个具有共同要素的商标,如“哈”或“诗仙”,法院基于数个商标的共同要素宣告争议商标无效,相当于赋予了商标权人对共同要素的排他权。但是,相关公众看到“哈”和“诗仙”是否会将其与特定的主体联系起来需要谨慎论证。举例说明,在看到“老干X”的时候,公众容易将其和“老干妈”联系起来,但是相关公众看到“哈”却未必产生与“哈尔滨啤酒”的联系,也有可能是“娃哈哈”。正如哈泉公司在“哈”字系列案中所抗辩,现存的许多注册商标也含有“哈”字,公众看到“哈”字不一定会与“哈尔滨啤酒”相联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指出,仅仅是某人使用一系列具有共同要素的商标这一事实,并不足以排除竞争对手使用同一要素作为商标成分。只有消费者认为注册所有人使用的一系列标志中的共同要素用以表明货物来源,使用这种共同要素才可能构成侵权。4Se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Introduction to Trademark Law and Practice, Geneva, 1993, p.56.正如兰德斯与波斯纳所言,对产品的描述越是冗长,消费者的搜寻成本就越高,对产品的描述越是精炼,其所传达的有用信息反而更多。5参见【美】威廉·M.兰德斯、【美】理查德·A.波斯纳,《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第二版)》,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4页。大家更有动力去选择和占领更简短的文字作为商标,文字越是简短和普遍意味着商标权的范围越大,商标权人所能获取的利益也更多。但是,这也导致公众能够选择商标文字的空间变小,如果相关主体想获得简短文字的独占权利,其需要通过使用商标付出与商标收益相称的成本。商标越是简短和普通,商标权人证明其知名度足以排除其他商标权人使用的义务越大。然而,相关判决对此缺乏充分的论述。
此外,在考量一系列商标的知名度时,法院并没有辨析商标知名度的获得是基于商标权人的注册行为还是商标的使用情况,可能会导致商标权利的不当延伸。6参见任毅:《商标延伸问题研究》,载《电子知识产权》2017年第3期,第40-43页。由于我国采取的是“一标一权”的注册模式,考量商标的知名度一般应当以单个商标作为考察基础。如果要将一系列商标作为整体对待,法院应当考察多个商标是否通过使用达到能够共享知名度的实际效果。以“哈”字系列商标案为例,法院认为“哈啤”系列商标具有一定知名度,争议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然而,法院既没有单独考量其他商标的使用情况,也没有考量其他商标是否通过与“哈啤”商标的结合使用获得知名度,容易让人误以为构成商标混淆是因为商标权人注册了多个具有共同要素的商标。如果注册数个具有共同要素的商标便能共享商标知名度,这种行为无异于“商标囤积”行为,有违商标法原理。
综上所述,我国在系列商标认定上存在一定的问题。系列商标认定的关键是何种情况下商标权人才能对“共同要素”享有排他权,使得商标之间能够共享知名度。本文通过商标法基本原理和法律制度分析相关判决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提出解决路径。
二、基于登记制度的问题剖析
部分国家与地区通过设置系列商标注册制度规定系列商标的注册条件。一旦数个商标被注册为系列商标,数个商标就会被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因此注册系列商标须满足较为严格的限定条件。我国并没有规定系列商标注册制度,相关裁决也没有坚持以单个商标与争议商标进行对比,导致裁决在认定系列商标上存在问题。通过考察其他国家的系列商标注册制度,可以从中认识到认定系列商标需要谨慎对待,避免登记制度所带来的系列商标产权外溢。
(一) 登记制度导致的产权外溢
在认识相关国家与地区为何规定系列商标注册制度以及我国为何要限制登记制度带来的系列商标产权外溢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分析为何登记制度会导致系列商标的产权属性外溢。
在没有现代商标法之前,商标保护主要通过类似“先占规则”的保护方式实现,如印上防伪标签,遵循洛克式的劳动划拨财产权理论。7参见【美】威廉·M.兰德斯、【美】理查德·A.波斯纳:《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第二版)》,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42页;参见【美】罗伯特·P.莫杰思:《知识产权正当性解释》,金海军、史兆欢、寇海侠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57-132页;参见【美】安守廉:《窃书为雅罪:中华文化中的知识产权法》,李琛译,法律出版社2010版,第18-19页。英美法系早期的商标保护主要是通过“仿冒之诉”(Passing off)进行。8参见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14版,第454-455页。然而,在知识产权法发展历史上,知识产权法存在不确定性与开放性等问题,导致其因为民众的不信任而受到废除的威胁。登记制度的建构使得现代知识产权法逐渐走向封闭,商标法从“在先使用主义”向“在先注册主义”转变。这意味着商标权保护从“占有所有权”转变为“纸上所有权”,商标权人通过登记的文字表述便能获得商标权的保护。现代知识产权法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被保护对象的表述而非该对象本身,因此,登记起到了管理和划定无体财产的界限范围的重要作用。9参见【澳】布拉德·谢尔曼、【英】莱昂内尔·本特利:《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演进:英国的历程(1760-1911)》,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5页。
然而“纸上所有权”会催生“搭便车行为”,不正当的商标囤积、恶意抢注和强势商标的不当扩张都可能属于这种情况。如果法律没有相应的限制,产权的部分属性就会溢出公共领域,这样的制度会激励公众投资以攫取溢出的利益,可能会导致过度投资而产生兰德斯与波斯纳所说的“由寻租所造成的浪费”。10参见【美】威廉·M.兰德斯、【美】理查德·A.波斯纳:《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第二版)》,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在系列商标注册的场景下,登记制度可能会导致公众将资源置于注册一系列具有共同要素的商标,攫取更大范围的商标权。
目前,我国商标法相关规定将重心主要放在典型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即规制抢注具有一定知名度商标的行为,如商标法第四条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和第三十二条的后半段。但是,对于通过注册一系列具有共同要素的商标从而扩张商标权范围的行为,我国并没有直接的限制性规定。
(二)系列商标注册制度
为了克服登记制度带来的产权外溢,部分国家与地区规定了系列商标注册制度。相关规定对待系列商标的态度相当谨慎,会严格限制系列商标注册的条件,对数个注册商标之间的相似度要求较高。如果相关商标不属于注册的系列商标,相关裁决将坚持以单个商标与争议商标进行对比。
在全世界范围内仍保有系列商标注册制度的国家与地区主要有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中国香港等。在系列商标注册制度的语境下,系列商标(Series of Trade Marks)是指在要素细节上彼此相似,且仅在不影响商标显著性的特征上有所差别的若干商标。系列商标注册制度在注册时将一系列商标视为一个整体并确定其权利范围。11UK Trade Marks Act 1994, Section 41,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94/26/section/41, last visited July 31, 2022.系列商标中的每个商标之间必然构成相同或近似,但是各国认定系列商标的标准不同。英国商标法的要求最为严格,其要求商标申请人一次只能申请6个商标,每个商标必须看上去、听上去和意思上是相同的。在英国每年有接近40%的系列商标申请无法通过。12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Guidance of Trade mark series applications, https://www.gov.uk/guidance/trade-mark-seriesapplications, last visited July 31, 2022.其次是澳大利亚,其商标法规定系列商标中的每个商标只允许在描述商品(服务)、数量、价格、质量或地方名称、商标颜色方面存在差别。13Australia Trade Marks Act 1995, section 51,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21C00445, last visited July 31, 2022.新西兰商标法在澳大利亚的基础上加入了兜底条款,要求商标的非显著变化不能实质性影响商标的识别性,要求较澳大利亚宽松。14New Zealand Trade Marks Act 2002, section 5, https://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2002/0049/latest/DLM164249.html?search=sw_096be8ed81b891ec_series+of+trademark_25_se&p=1, last visited July 31, 2022.新加坡则要求每个商标主体部分必须相同,差异在性质上不显著,其他部分不实质性影响商标作为整体的识别性。15Se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Series of Marks, Version 4, 2017, https://www.ipos.gov.sg/docs/default-source/resources-library/trade-marks/infopacks/tm_work-manual_8-series-of-marks_apr2017.pdf, last visited July 31, 2022.由此可见,在上述国家当中,如果将系列商标作为整体进行注册,登记机关需要对系列商标中每个商标的近似度进行深入考察。按照上述国家的标准,近似程度要求较为严格,只限定在相对特定的情形,商标共同要素之外的部分必须非实质性影响地商标作为整体的识别性。这源于系列商标注册制度的两个特征:第一,系列商标注册制度的重要特征是商标的整体性。这意味着数个具有共同要素商标被作为一个整体划定权利范围,即商标申请人通过一次申请获得了数个商标的集合权利。数个商标之间的差异越大,商标权人获得的商标权范围就越大。此外,在考量商标使用情形是否符合“三年不使用”的商标撤销规则时,系列商标里任何一个商标被使用都符合商标使用而无需撤销商标。16See Comic Enterprises v.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2016] EWCA Civ 455. 在该案中,欧盟高等法院认为,一旦数个商标被认定为系列商标,只要商标之间的差异要素并不影响商标的识别性,都符合三年不使用撤销的豁免条件。因此,系列商标对数个商标之间的近似性要求比较高,避免系列商标的权利范围过大而影响公共利益。第二,系列商标注册制度是在商标申请阶段认定系列商标,商标一经注册就具有初始效力,事后无效宣告申请人需要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确定权利范围需要更为谨慎。这也是为何印度的系列商标注册制度(或称联合商标制度 Associate Trade Marks)被批评者认为可能会导致商标囤积现象。17See Associated Trademarks in India, Intepat, April 20, 2016, https://www.intepat.com/blog/trademark/associated-trademarksindia/, last visited July 31, 2022.因为印度的系列商标制度规定比较宽泛。根据印度商标法的规定,同一所有人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和服务上拥有的商标,如果被所有人以外的人使用,可能会产生欺骗或混淆,登记官可随时要求该商标注册为联合商标。18India Trade Marks Act 1999, section 16, English Version in https://www.advocatekhoj.com/library/bareacts/trademarks/16.php?Title=Trade%20Marks%20Act,%201999&STitle=Registration%20of%20trade%20marks%20as%20associated%20 trade%20marks, last visited July 31, 2022.
可见,为了限制商标权人通过注册一系列具有共同要素的商标攫取商标权,相关国家与地区通过系列商标注册制度限定系列商标的注册条件。我国没有相关的制度,但是这并不影响相关裁决在事后对系列商标的认定进行限制。有研究认为系列商标注册制度并无实践价值。19参见王贵农、张春华:《论联合商标的作用与规范机制的构建》,载《政法论丛》2006年第4期。因为系列商标注册制度要求商标之间高度近似,只要争议商标与系列商标中的一个商标相似,其必然与其他商标相似。虽然我国采取单个商标的注册模式,但是单个商标与争议商标进行对比也可以达到系列商标注册制度的效果。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台湾地区在2003年删除了之前“商标法”中关于联合商标的规定,20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所谓“商标法”(2002年)第二十二条;我国台湾地区所谓“商标法”(2003年)。如今日本商标法中也早已看不到曾经存在的联合商标制度。21参见【日】田村善之:《日本知识产权法》,周超、李雨峰、李希同译,张玉敏校,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版,第167页。然而,我国相关裁决并没有坚持单个商标对比的模式,反而直接将一系列具有共同要素的商标作为整体与争议商标进行对比,即“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均含有‘某某’要素”。在此之前,法院并没有深入考量数个商标是否构成系列商标。从我国的现状来看,系列商标注册制度的限定条件对我国仍有一定的启示性意义,系列商标注册制度在注册阶段对系列商标认定进行限制,实际上也有助于我国知识产权局与法院在裁决时对数个具有共同要素的商标提高警惕。
综上,系列商标产权属性溢出问题来源于商标登记制度固有的弊端,需要对此进行限制。由于我国并没有规定系列商标注册制度,相关裁决也没有坚持单个商标对比模式,导致系列商标产权属性的外溢。一般情况下,相关裁决应当坚持以单个商标与争议商标进行对比,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能基于共同要素将数个商标视为系列商标。虽然系列商标注册制度并没有直接解决什么情况下商标权人可以对共同要素享有排他权的问题,但是这有助于我国认识到必须构建系列商标的认定规则,限制登记制度导致的系列商标产权属性溢出。
三、基于系列商标认定规则的问题剖析
美国同样没有规定系列商标注册制度,却在判例中发展出“家族商标规则”,以解决什么情况下商标权人可以对共同要素享有排他权的问题,从而限制登记制度导致的系列商标产权溢出。家族商标规则对我国构建系列商标的认定规则具有较大的意义。在家族商标规则中,系列商标认定是混淆可能性判断中需要重点考量的情形,系列商标的认定会提高混淆可能性,因此法院会严格考量具有共同要素的数个商标是否构成系列商标。我国同样可以基于商标法第三十条发展出系列商标的认定规则,这实际上也是相关裁决宣告商标无效的法律依据。然而,第三十条只规定了商标申请人不能在同一或者类似商品上注册与已注册或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并没有规定“混淆可能性”的要件。这导致相关裁决忽略了认定系列商标对混淆可能性的重要影响,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商标的形式相似性,一旦争议商标与数个商标均含有同一要素就认定混淆。
(一)家族商标规则(Family of Marks Doctrine)
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将家族商标定义为:“一组具有可识别的共同特征的商标,其中商标的组成和使用方式使得公众不仅将个别商标,而且将家族的共同特征与商标所有人联系起来。”如果商标权人拥有消费者认可的家族商标,法院就会认为家族商标中的所有标志都发展出了良好的商誉并对其进行保护。22See J & J Snack Foods Corp. v. McDonald’s Corp., 932 F.2d 1460, 1462 (Fed. Cir. 1991). 此案被普遍认为是“家族商标规则”的典型案例。家族商标规则早期发展于Burroughs Wellcome公司诉Mezger药业公司案23Burroughs Wellcome & Co. v. Mezger Pharmacal Co., 228 F.2d 243, 243-244 (C.C.P.A. 1955).中,原告声称自己注册了一系列具有“fax”音节的商标,被告申请注册的商标“Lipofax”含有“fax”容易导致混淆,商标申请应当被撤销。美国海关与专利上诉法院驳回了请求,认为原告不能在“fax”这一音节上享有排他权,不仅因为“fax”属于一个普通词汇,还因为很多第三人也注册了带有“fax”的商标,只要不构成商标混淆,就不能撤销被告的申请。可见,在早期的案件中,法院认定家族商标主要考量两个因素:家族商标中的共同要素的显著性,以及是否有众多第三人已经注册了带有共同要素的商标。早期法院都承认似乎存在家族商标这么一样东西,但是由于这项规则在实际当中很少被执行,而且也基本没有商标被认定为家族商标,因此这项规则几乎消失。24Jones & Laughlin Steel Corp. v. Winter Seal Corp., 291 F.2d 945, 946 (C.C.P.A. 1961).直到1963年的摩托罗拉公司诉Griffi ths电子公司案,这种格局才被打破。25Motorola, Inc. v. Griffiths Elecs, Inc., 317 F.2d 397 (C.C.P.A. 1963).法院进一步指出,第三人是否注册了具有相同要素的商标并不必然影响家族商标的认定,需要着重考虑的是在被告使用或者申请争议商标时,家族商标所有者的业务数量、价值、规模和持续时间。此后,家族商标规则进一步在美国案例法中得到发展。
1986年,家族商标规则在麦当劳公司诉McBagel公司案26McDonald’s Corp. v. McBagel’s, Inc., 649 F.Supp. 1268 (S.D.N.Y. 1986).中得到开创性发展。原告麦当劳公司在诉讼时已经注册了34个含有“Mc”与“Mac”的商标,被告McBagel公司在纽约开了一家快餐馆,并在当地的报纸和广播上进行推广。麦当劳主张,McBagel公司在相关市场上使用“Mc”产生混淆,侵犯了其“Mc”家族商标。法院认为,家族商标的认定是一个基于共同组成部分的显著性和其他因素的问题,包括家族商标的使用、广告宣传、推广的程度,以及共同要素在同一主体拥有的注册和未注册的商标中的情形。在判定麦当劳的一系列商标是否构成家族商标时,法院主要从以下要素进行判断:(1)麦当劳注册了一系列含有“Mc”部分的商标;(2)麦当劳投入了大规模的广告使商标为消费者所认知;(3)证明麦当劳含有“Mc”前缀的商标为相关公众所认识的证据;(4)麦当劳使用“Mc”家族商标的时长;(5)在被告使用“McBagel”之前,麦当劳在维持和监督“Mc”系列商标的使用上付出了许多努力。在认定了麦当劳“Mc”系列商标构成家族商标后,法院根据Polaroid因素27Polaroid Corp. v. Polarad Elecs. Corp., 287 F.2d 492 (2d Cir. 1961).进行混淆可能性判断时,认为McBagel与麦当劳家族商标的混淆可能性较高,判定McBagel构成侵权。由于认定家族商标与判断混淆性都以商标的来源识别性为核心,一旦确定了数个具有共同要素的商标为家族商标,具有共同要素的争议商标构成混淆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美国家族商标规则发展出以下判断因素:(1)商标权人先前登记或使用了一些具有共同要素的商标;(2)商标具有显著性,商标的共同要素不能是普通单词的最后一个音节,也不能是产品的通用术语,除非其通过使用获得了“第二含义”;(3)家族商标使用的广泛性和消费者的认可度,考量商品的性质、商品的销售价值、推销家族商标的时间长度、在被告进入时家族商标是否在行业有良好的地位;(4)是否存在其他人登记具有同样要素的商标,但是其使用情况不足以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从而影响对家族商标的保护。28See McDonald’s Corp. v. McBagel’s, Inc., 649 F.Supp. 1268 (S.D.N.Y. 1986); see also J & J Snack Foods Corp. v.McDonald’s Corp., 932 F.2d 1460 (Fed. Cir. 1991); Pure & Simple Concepts, Inc. v. I H W Mgmt., 2020-1211 (Fed. Cir. May.24, 2021).
在认定系列商标之后,法院会进一步分析混淆可能性。系列商标认定关注的是商标权人能否对共同要素享有较强的排他性权利,即系列商标的权利范围。但是,混淆可能性判断不仅需要考量系列商标的权利范围,还需要考虑争议商标的具体情况。因此,在相关的纠纷当中,系列商标是混淆可能性判断的其中一个考量情形。然而,这也意味着系列商标的认定会提高构成商标混淆的可能性。系列商标认定的考量因素与混淆可能性判断因素具有交叉重合之处。举例说明,混淆可能性认定需要判断在先使用商标的强度,包括商标的显著性程度与知名度,认定系列商标同样需要判断这些因素。系列商标一经认定,商标的整体强度也必然较大。要达到系列商标的认定标准,商标权人必须通过使用具有共同要素的商标提高商标的知名度,包括将数个商标结合使用或者单独使用商标,使得相关公众将商标的共同要素与商标所有人联系起来。因此,系列商标意味着相关公众将共同要素作为商品来源的识别标识,相关公众会将数个商标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此时,商标强度就不是数个商标知名度的简单加总,而是所有的商标基于共同要素共享了知名度。正如法院在Quality国际客栈公司诉麦当劳公司案29Quality Inns Int’l, Inc. v. McDonald’s Corp., 695 F. Supp. 198 (D. Md. 1988) .中所言,一个商标家族的协同识别可能大于每个商标的总和。虽然单个商标的强度可能不足以排除其他商标注册具有共同要素的商标,但是数个商标的使用情况使其知名度足以令相关公众将共同要素与商标权人联系起来,商标的整体强度就会变大。麦当劳的一系列“Mc”商标被认定为家族商标后,法院在后续的案件中考量商标强度时直接说道:“麦当劳的Mc家族商标是所有商标中最强的商标,这是社会中几乎所有成员都认可的。”30Quality Inns Int’l, Inc. v. McDonald’s Corp., 695 F. Supp. 198, 211 (D. Md. 1988) .商标的强度越大,其对于其他因素的影响也会越大,例如实际混淆因素、争议商标人的主观善意、在先商标扩张业务到在后使用者领域的可能性等。因此,在麦当劳案后,许多法院都倾向于在同类案件中作出即决审判(Summary Judgment),即法院在认定家族商标后不再逐一对Polaroid因素展开混淆可能性分析,如联邦巡回法院在Han Beauty公司诉 Alberto Culver公司案31Han Beauty, Inc. v. Alberto-Culver Co., 236 F.3d 1333 (Fed. Cir. 2001).中只考虑了商标相似性和商品种类相似性的因素。
综上,在家族商标规则中,系列商标的认定是混淆可能性判断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相关裁决在进行混淆可能性判断时必须深入考量引证商标是否构成系列商标,即共同要素能否识别商品的来源。只有经过充分的考量被认定为系列商标,数个具有共同要素的商标才能够被作为一个整体与争议商标比较相似性。在此之前,不能将一系列商标作为一个整体排除其他商标权利,混淆可能性判断只能结合单个商标的情形进行判断,否则很容易会得出构成混淆的结论。我国的相关裁决正是缺少了考量与认定系列商标的环节。其核心原因是我国商标法第三十条并没有规定混淆可能性要件。
(二)我国商标法第三十条的适用
如前文所述,系列商标认定是判断混淆可能性的重要情形。由于我国商标法第三十条没有规定混淆可能性要件,相关裁决没有认识到系列商标认定对混淆可能性的影响。我国商标法第三十条的适用需要考量混淆可能性,将系列商标认定纳入混淆可能性的判断中。在新加坡的相关案例中,法院也会在认定商标相似性时考量混淆可能性要件,并将系列商标认定纳入混淆可能性中进行考量。如果权利人没有注册系列商标,但是又诉称自己的商标构成“家族商标”,法院就会基于混淆可能性要件认定相关商标是否构成“家族商标”,即商标权人能否对共同要素享有排他权。32Lacoste v. Carolina Herrera, Ltd. [2014] SGIPOS 3; Monster Energy Company v. Glamco Co., Ltd. [2018] SGHC 238;Bridgestone Licensing Services, Inc. v. Deestone Ltd. [2018] SGIPOS 5.
商标本质是一种商业符号,理想状态下的商业符号能够直观表示其含义并且直接与特定的商品相联系。然而,商业符号并非客观且自然地与特定含义以及特定商品意义对应,商标依赖于符号、语义以及人的主观联想之间的互动,而运用语言描述符号以及主观联想的过程都是高度场景化和模糊的。33参见彭学龙:《商标法的符号学分析》,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0-51页;参见谢晓尧:《法律语词的意义寻绎——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文本》,载《知识产权》2022年第6期,第56页。这与我们的社会经验和文化有关,如“MLGB”商标在国外并不一定会符合商标注册的阻却要件,但是在我国判决中,“MLGB”则属于“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34参见上海俊客贸易有限公司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行初6871号行政判决书。对于商标的保护实际上都建立在特定场景下对商业符号进行联想和理解的基础上。商标的高度场景化与联想模糊性意味着信息成本较高,产权属性会部分溢出公共领域。同样,理想状态下的精确法律概念也是一种符号,是不需要任何解释的,即莱考夫与约翰逊所指的典型的能被直接理解的概念,如简单的空间概念(“上”“下”“远”“近”)、数字等。然而,正如莱考夫与约翰逊所指出,我们的概念系统更多是通过隐喻来建构的,许多情形下难以通过直接经验获得。35参见【美】乔治·莱考夫、【美】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6-159页,第233-234页。拉仑茨在《法学方法论》中也提到:“法律语言不能达到像符号语言那样的精确度,它总是需要解释。”36【德】卡尔·拉仑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4版,第201页。我们的法律概念与法律适用同样是具有语言模糊性且高度场景化。所以,法律在很多情形下是无法通过概念直接涵摄来界定商标的产权,例如“相似”概念,如果不对法条中所调整的商标产权属性逐一分析并综合评价适用,将会导致部分产权属性向公共领域外溢。
由此可得,商标和法律概念并非理想状态下的符号,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商标背后的联想都需要解释,不能通过简单比对符号的外观认定商标混淆。否则,高度模糊与场景化将使得法律无法完全界定产权,导致产权属性的溢出。因此,适用商标法第三十条不能简单地基于商标外观和法律概念直接认定商标“相似”,而是需要在具体场景下对商标的外观相似性与主观联想相似进行综合评价。如果仅考虑商标是否存在相同或近似,就会过度强调商标在客观形式上的相似,而忽视了其背后最重要的主观联想上的混淆。在当事人注册一系列具有共同要素的商标这种非典型场景中,相关裁决仅通过符号上的客观比对,便将具有共同要素的系列商标视为一个整体,进而基于商标的共同要素认定争议商标构成混淆,并没有基于数个商标的使用情况深入考量商标的共同要素多大程度上会导致公众混淆。正如前文所述,一旦引证商标被认定为系列商标,争议商标构成混淆的可能性就会提高。如果法院将重心放在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均含有某一共同要素,对于混淆可能性的考虑过于简单,这将无法实质限制当事人通过注册攫取更大商标权范围的行为。
因此,第三十条虽然没有规定混淆可能性要件,但是在适用第三十条时也应当与第五十七条的商标侵权判定和第四十六条的转让商标限制情形一样考虑混淆可能性要件。相关裁决应当基于商标法的功能——区分商品来源,充分考察个案的情形是否符合商标客观形式相似与混淆可能性的典型因素,形成综合的评价。37参见杨祝顺:《商标混淆可能性的多因素测试法比较研究》,载《电子知识产权》2019年5期,第59-71页。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38《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法发〔2010〕12号)第十六条:“人民法院认定商标是否近似,既要考虑商标标志构成要素及其整体的近似程度,也要考虑相关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所使用商品的关联程度等因素,以是否容易导致混淆作为判断标准。”在当事人注册数个具有共同要素的引证商标的场景中,系列商标的认定应当纳入混淆可能性判断中重点考量。如果不构成系列商标,相关裁决只能结合单个商标的情形判断混淆可能性。
四、我国系列商标的认定规则
系列商标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实质上是商标权人能否对数个商标中的共同要素获得排他权。如前文所述,系列商标认定是一个高度场景化的问题,在考量相关的判断因素时需要根据特定场景进行综合评价。虽然我国目前并没有形成如美国家族商标规则一样的系列商标认定规则,但是在部分判决中法院还是考量了相关的因素。对现有判决的分析有助于结合我国实际形成本土化的系列商标认定规则。
(一)共同要素的显著性
根据标志的显著性与它所指代的商品或服务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可以将标志分为:通用标志、描述性标志、暗示性标志、任意性标志以及臆造性标志。39See Abercrombie & Fitch Co. v. Hunting World, Inc., 537 F.2d 4, 11 (2d Cir. 1976).通用标志由于显著性低一般不予注册,而描述性标志如果没有通过使用获得第二含义,一般也不予商标保护。只有共同要素具有显著性,其才能被初步视为商标的显著部分。因此,如果系列商标中的共同要素属于通用标志或者没有获得第二含义的描述性标志,一般不予认定为系列商标。
1.宜兰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小小”系列商标案40宜兰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再审申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14409号行政判决书;宜兰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行终6293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行终487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行终2006号行政判决书。
宜兰公司注册了一系列包含“小小”的商标,包括:“小小”“益纤小小”“小小頭”等。“小小”酥食品是宜兰公司的著名商品。争议商标为“小小陈”“小小芭茜”“小小功夫”“小小”图形商标。法院认为“小小”在含义上具有修饰作用,显著性较低,虽争议商标与引证的一系列商标均包含汉字“小小”,但争议商标还包含有其他汉字及图部分,其整体明显区别于引证的一系列商标,未构成近似商标。此外,法院认为宜兰公司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引证商标一至四商标经过单独使用已经具有较高知名度,使相关公众能够将引证商标一至四与宜兰公司形成对应关系。
2.高平老奶奶公司“奶奶”系列商标案41广东义信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再审申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7104号行政判决书。
高平老奶奶公司注册了一系列包含“奶奶”字样的商标,包括:“老奶奶”、“何记老奶奶”、“怪奶奶”等商标,核定使用在牛奶饮品、加工果仁等第29类产品上。争议商标为“虹奶奶及图”。法院认为,“奶奶”一词一般用来指代祖母或与祖母辈分相同或年纪相仿的妇女,使用在“牛奶饮料(以牛奶为主)”“加工过的坚果”商品上具有显著性,进而认为商标的显著识别部分为“奶奶”,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一至七的显著识别部分相同,争议商标构成近似商标。
虽然法院并没有讨论引证商标是否构成系列商标,但是通过比较以上两个案例,共同要素的显著性会影响法院是否将一列商标作为整体看待。在“小小”系列商标案中,显著性较低的共同要素使得法院更加关注商标的差异部分,阻却了法院将数个商标作为整体看待并认定构成商标混淆。法院更是明确指出,单个商标的知名度并不足以排除他人使用带有“小小”的商标。法院坚持将单个商标作为混淆判断的考察基础。但是在“奶奶”系列商标案中,法院基于共同要素的显著性,倾向于将引证商标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当然法院也有考量商标知名度问题,在此不进行赘述。
(二)考量商标的知名度
共同要素的显著性是其作为商标显著部分的初步考量因素,商标知名度则是系列商标认定的核心考量因素。因为,认定系列商标必须证明相关公众会将数个商标的共同要素与商品的同一来源相联系。商标使用规则是商标产权界定的核心。商标所有人只有通过使用包含共同要素的商标获得知名度,且足以使相关公众基于共同要素产生混淆误认,才能获得系列商标权利。
1.“干露”系列商标案42湖州润兴酒业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行终4866号行政判决书。
商标权人维纳康佳阿拖拉公司注册了一系列包含“干露”的商标,包括:“干露酒厂·旭日”“干露酒厂”“干露酒厂·原野”等商标,争议商标为润兴公司申请的“干露”商标。在一审判决中,虽然法院没有经过论述便将“干露”系列商标视为一个整体,但是法院还着重考量了“干露”系列商标的使用情况。法院认为,《南方日报(广州版)》《重庆商报(数字版)》《渤海早报数字版》《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温州晚报》《重庆商报数字版》《广州日报》《都市时报(数字版)》等媒体在不同时间多次对干露及干露酒厂、干露酒庄葡萄酒进行了报道,由此可见,“干露”及“干露酒厂”在争议商标申请日之前可为相关公众所知悉,具有一定知名度。法院认为润兴公司申请的“干露”商标容易导致混淆误认。
2.“中检”系列商标案43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行终7178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行终7179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行终7181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行终7186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行终7187号行政判决书。囿于篇幅,本文不逐一列举其他同系列案件。
申请人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检公司”)是“中检”“中检集团”的商标权人,中检集团南方测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南方公司”)是“中检环境”“中检测试”的商标权人。申请人中检公司基于“中检”系列商标申请一系列含有“中检”的商标,包括:“中检优选”“中检评价”“中检生态原产地”等。中检公司认为自己是“中检”“中检集团”系列商标的所有人,且证明其商标和企业简称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然而,法院认为中检公司主张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简称或注册商标与本案争议商标存在差异。可见,虽然中检公司持有了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中检”商标,但是法院认为其知名度尚未达到排他性使用含有“中检”的其他商标。
3.“飘花”系列商标案44参见沈新东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行终1393号行政判决书。
义乌市伊人袜业有限公司拥有一系列包含“飘花”的商标,包括:“飘花伊人”与“飘花伊人PHYIREN”等商标,争议商标为沈兴东申请的“飘花真爱系列”。法院认为引证的一系列商标与争议商标均包含“飘花”。根据在案证据,“飘花伊人”商标经伊人袜业公司的宣传和使用在袜等商品上具有一定知名度。此外,法院还考量了地域市场因素。法院认为沈新东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两家公司均在浙江省义乌市进行经营,且属于同业经营者,沈新东理应知晓“飘花伊人”商标,理应避让在先商标,进而认定沈兴东主观上存在一定的恶意。综上,法院认定公众可能会误认为争议商标是引证商标的系列商标。
从以上的三个案例可以看出,部分判决在考虑商标权人能否排他性使用包含同一要素的一系列商标时,其重点考察了商标经过使用获得的知名度。知名度的考量因素包括商标使用的时长、商标的广告宣传力度、地域市场因素以及商标的其他使用情况。当然,地域市场因素具有一定的个案性,美国家族商标规则认定的系列商标往往具有普适性,能够直接为后续的判决提供指引。但是,基于我国不存在判例法传统,在个案当中考量地域因素对系列商标认定的影响仍然有一定的意义。
(三)辅助因素
在考量构成系列商标时,还需要结合一定的辅助因素进行判断。首先是在相关行业中是否有大量包含某一共同要素的商标被注册。在我国相关裁决中,这类观点主要出现于当事人的抗辩理由当中,如前文提到的“哈”字系列商标案,对此进行考量的裁决较少。在美国家族商标规则发展中,这一因素曾经被作为主要的考量因素。但是,在后续的案件当中,法院指出仅凭第三方注册并不足以阻止对家族商标的保护,除非证明竞争对手以并非微不足道的方式实际使用商标。此外,必须有消费者对第三方注册的商标的实际认可。45See McDonald’s Corp. v. McBagel’s, Inc., 649 F. Supp. 1268 (S.D.N.Y. 1986).其次是争议商标的其他构成部分是否具有较大差异。如果争议商标差异较大,即使其包含系列商标的共同要素,法院也不会进一步进行混淆可能性分析。46See Polaroid v. Richard Mfg. Co., 341 F.2d 150, 152 (C.C.P.A. 1965); see also Jones & Laughlin Steel Corp. v. Winter Seal Corp., 291 F.2d 945, 946 (C.C.P.A. 1961).
综上,系列商标认定需要结合具体场景进行综合评价。考量因素包括共同要素的显著性、商标知名度以及相关的辅助因素。其中,商标知名度因素是最为核心的考量因素。巴泽尔认为决定所有权最优配置的总原则是:对资产平均收人影响倾向更大的一方,得到剩余所有权(即产权份额)也应该更大。因为影响资产收入的因素很多,个人可通过推诿于其他因素,来掩盖其自身的低水平贡献。这种攫取财富的企图使得个人之间进行合作的成本变得很高。47【以】约拉姆·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第二版)》,费方域、段毅才、钱敏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版,第9页,第52页。这就意味着,对于产权属性贡献更大的一方应当获得更多产权份额。在系列商标产权界定的场景下,则体现为商标使用对商标产权的贡献程度。相关的裁决需要具体考察数个商标的使用情况,包括商标使用的时长、商标的广告宣传力度、地域市场因素以及商标的其他使用情况。只有商标的知名度足以使公众看到数个商标的共同要素就会产生混淆误认时,相关商标才能被认定为系列商标。否则,相关裁决必须以单个商标为基础考察争议商标是否构成混淆。
五、结语
“系列商标”“家族商标”“联合商标” 长期以来都被作为一种商标管理策略看待。这种观念也部分映射到司法裁判中。作为一种商标管理策略,系列商标有助于鼓励商标权人基于成本收益衡量,注册与知名商标相似的商标以扩大商标保护范围,如“阿里叔叔”“阿里姑姑”。面对我国一直以来所关注的商标囤积与商标抢注等问题,将系列商标作为一种管理策略而非正式制度或许更有效率。然而,这种管理策略的前提是商标相似性以单个商标作为考察基础。相关裁决简单地将数个包含共同要素的商标视为法律意义上的系列商标,同样会带来商标囤积问题。只是商标囤积人恰恰是通过系列商标管理策略来保护自己的人。相关裁决所存在的问题正是反映了我国系列商标认定规则的缺失,导致无法限制登记制度所带来的产权外溢。法律意义上的系列商标意味着商标权人对数个商标中的共同要素享有排他权,需要谨慎认定。只有商标权人通过使用商标获得知名度,使得相关消费者将商标中的共同要素与特定主体联系起来,相关商标才能被认定为系列商标。如果不符合系列商标的要求,相关裁决必须以单个商标为基础考察争议商标是否构成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