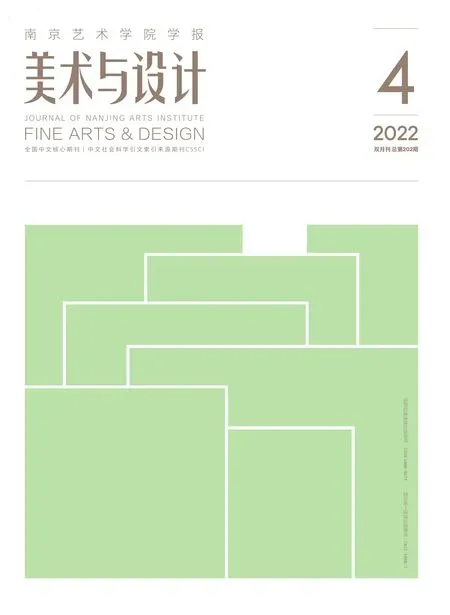波提切利绘画中的寓言和图像隐喻
——西蒙内塔的“尼禄印章”①
关家敏(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北京 100010)
一、波提切利的“新柏拉图”风格
瓦萨里在《名人传》中提及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的篇幅不多,主要描述了他从出生、师承关系到在美第奇家族时期的创作生涯。在瓦萨里看来,波提切利的艺术风格用“优美”一词即可概括;另一方面,瓦萨里对波提切利晚年的作品持一种轻视态度,这可能与瓦萨里丰富的情感表达或写作时出现讹误有关。理查德·史泰普福德(Stapleford,Richard)在研究中指出了这一点:瓦萨里描述了180多名艺术家的艺术历程,这使瓦萨里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学术成就,但他的错误也常常显而易见,因此给后人的研究留下了“怀疑的阴影”。
波提切利是早期文艺复兴佛罗伦萨画派的画家,梳理他的艺术生涯可能绕不开对美第奇家族故事的钩沉。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知识中心,美第奇家族对艺术家的支持造就了一批批成就卓著的大师,其中包括波提切利、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等。波提切利的出生地是亚历山德罗·菲利佩比(Alessandro Filipepi),身为皮革工人的父亲发现了幼年波提切利的艺术天赋,并设法将他送进弗拉·菲利波·里皮(Fra Filippo Lippi)的艺术工作室学习。少年的波提切利很快便显露出超越常人的天赋,不消数年即能熟练掌握老师的线条、色彩和造型处理技术。但正如其他艺术家一样,波提切利需要一个“贵人”的赏识才能正式进入历史。在里皮的工作室学习没多久后,皮耶罗(Piero)的妻子卢克雷齐亚(Lucrezia)就发现了这个天才的少年画家,遂邀请他进入美第奇宫殿并成为一名专职宫廷画家。进入美第奇宫殿后,波提切利第一件作品就是以卢克雷齐亚(Lucrezia de Medici)及其两个孩子洛伦佐·美第奇和朱利亚诺·美第奇(Giulianode’Midici)为表现对象的圣母玛利亚主题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保罗·斯特拉森(Strathern Paul)的研究,波提切利自少年时代就常与洛伦佐、朱利亚诺一家在美第奇宫殿聆听柏拉图学园会议。在柏拉图学园里,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ficino)的新柏拉图思想和波利齐亚诺(Poliziano)的古典神话研究为这几位少年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知识世界,新柏拉图思想与古典思想在波提切利、洛伦佐、朱利亚诺年幼的头脑中播下了种子。一路伴随洛伦佐和朱利亚诺的长大,波提切利的艺术风格日渐成熟,也为美第奇家族创作了许多作品,包括神话、寓言、肖像等题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春》(La Primavera)是波提切利为洛伦佐而创作,这幅现藏于佛罗伦萨乌菲齐博物馆的作品被创作出来时曾悬挂于卡斯特罗(Castello)的美第奇别墅里。一份拟于1499年的清单显示,洛伦佐·美第奇的堂兄弟洛伦佐·迪·皮尔弗兰切斯科·美第奇(Lorenzo di Pierfrancescode·Medici)在1477年收购了这座别墅,《春》则被认为是在此时间之后的1481年前后被创作;这一份表明洛伦佐堂兄弟财产的清单在1975年被发现,证实了《春》的归属正是洛伦佐·迪·皮尔弗兰切斯科·美第奇。

图1 《春》波提切利1481-82年,木板坦培拉,203x314cm,藏于佛罗伦萨乌菲齐博物馆
保罗·斯特拉森(Strathern Paul)认为,波提切利在《春》中实现了将柏拉图理念与古典神话的融合,他将轻盈、和谐的气氛描绘出来;维纳斯、美惠三女神、花神、仙女作为春天的象征,隐喻了波提切利对爱与美的新柏拉图式理解,女神们各自代表的纯洁、热情、爱欲、朴素等恰是波提切利对春天的理解。波提切利描绘的弗洛拉正是被佛罗伦萨誉为“女神”、朱利亚诺最心爱的西蒙娜塔·维斯帕奇(Simonetta Vespucci)。
贡布里希(E.H.Gombrich)指出,波提切利创作《春》的完整意图可以通过该作品的赞助者洛伦佐、费奇诺及艺术家本人的通信中找到答案,即《春》的创作方案显示了波提切利艺术的新柏拉图倾向。费奇诺作为年轻洛伦佐的导师,在通信中多次阐释了对“爱”的新柏拉图式理解,可见,他的新柏拉图思想可能对年幼的后者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费奇诺笔下的维纳斯并非欲望女神,而是代表了一种高贵的爱与美德,其中包括神圣的爱、仁慈、尊严与宽仁,端庄与清秀,妩媚与壮丽等品质,总之就是将人们对古典传统中爱情女神的美好想象汇聚一身。如贡布里希所承认的那样,年轻的洛伦佐所接受的关于美的教育隐含着这样的线索:美是通向神性的道路,而这正是费奇诺乐此不疲地赞扬视觉的高尚性和反复强调视觉美是神圣光辉象征的观念的结果。贡布里希的研究表明,《春》的创作方案在费奇诺的教育书信中得到体现,波提切利则是根据费奇诺对洛伦佐新柏拉图式引导的意图进行构思与描绘。
在波提切利的艺术生涯中,洛伦佐、费奇诺、波利齐亚诺、但丁等新柏拉图圈子对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比如《维纳斯的诞生》(The Birth of Venus)常被认为是对波利齐亚诺(Poliziano)诗句的描绘:“她穿行在白色波浪的海面上,一个没有人脸的少女,被狂风吹向岸边,在蓝天下,她出生在贝壳上。”保罗·斯特拉森指出,维纳斯的形象实际上与各种高度复杂的柏拉图式思想和典故融合在一起,传说菲奇诺和波利齐亚诺甚至专门组织一次柏拉图学园会议,主题则是讨论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中柏拉图思想的不同体现。

图2 波提切利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西蒙内塔)
二、西蒙内塔的故事
对比波提切利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他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相似的外貌特征,包括深邃眼神、清晰轮廓、尖眉毛、凸下巴、直鼻梁和长脖子,甚至卷曲别起的金黄色发型也一模一样。这些相似的形象出现在他的神话主题、寓言主题、宗教主题、纪念肖像画中,常识告诉我们,这些形象的模特可能为同一人。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形象展开了热烈而持久的讨论,如瓦萨里、贡布里希、瓦尔堡等人所承认的,波提切利的这个形象正是西蒙内塔·维斯帕奇(Simonetta Vespucci)。
在波提切利众多被认为模特是西蒙内塔的肖像作品里,最为人熟知的是《理想少女肖像》(Ideal Portrait of a Lady),这件作品现藏于德国法兰克福施泰德博物馆(Städel Museum Frankfurt am Main),因此又被称为“法兰克福的西蒙内塔”。在这件作品中,年轻女子穿着白色纱衣,五官轮廓紧凑分明,略带忧伤的眼神望向远方,修长的脖颈与后肩连接成好看的弧线;金黄色的卷发编制成各种复杂图案并装饰上珠子与鲜花,其中两组辫子从肩颈后方向前胸延伸,自然下垂后交叉编制在一起,与衣服造型完美结合;脖子戴着形似古罗马传统的金色项链,其中佩有墨绿色宝石链坠,上面刻有人物浮雕。

图3 《理想少女肖像(Ideal Portrait of a Lady)》,波提切利,1480-85年,木板坦培拉,81.8x54cm,现藏于德国法兰克福施泰德博物馆

图4 《西蒙内塔》,皮耶罗·科西莫,1480年,木板油画,57x42cm,藏于孔蒂博物馆
一个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这件作品是如何被创作的?在波提切利的其他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背景被描绘成景物,如窗户、城市或乡村风景等,这件胸像作品的女子则以全侧脸的角度面对观众,完整的黑色背景使人物轮廓更加凸显。画中女子飘逸的长发、奢华的配饰和复杂的造型绝非15世纪佛罗伦萨女子的日常发型装束。鲁道夫·希勒·冯·盖特林根(Rudolf Hiller von Gaertringen)指出,佛罗伦萨女子没有将头发蓬松披肩的习俗。从皮耶罗·科西莫(Piero di Cosimo)的《西蒙内塔》发型也可得到证明,黄金色头发被分成若干组,向后方盘卷并编制在一起,发髻中间装饰珠子与红色缎带。通过对种种非现实处理手法的分析,盖特林根认为该作品并非面对模特的写生绘画,而是波提切利根据某种理念进行创作“理想化肖像”。正如克里斯蒂安森的结论:“这件作品从一个真实的主题中抽象而来,就像波提切利的寓言故事一样,理念被转换成了拟人化的形象,换句话说,该作品显示了一种美德的化身。”“理念的拟人化”在该作品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女子胸前的古罗马风格项链上佩有黑色玛瑙宝石浮雕链坠一个,浮雕的主题已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古希腊神话形象阿波罗(Apollo)和马西亚斯(Marsyas),这种形式的链坠或图案被认为是15世纪流行的“尼禄印章”(Sigillo di Nerone)。如果我们用达尼埃尓·阿拉斯(Daniel Aresse)“从细节解读”的视角看,波提切利描绘“阿波罗与马西亚斯”主题的链坠应当有其深层含义。
事实上,对于该作品中的女子为何人的问题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被人们争论不休,更多人相信的是,法兰克福的这件作品的女子原型就是西蒙内塔·维斯帕奇(Simonetta Vespucci)。我们可以从作品诞生的年代中寻找线索,瓦萨里曾指出,科西莫一世(Cosimo I de'Medici)拥有一件由波提切利创作的朱利亚诺的情人西蒙内塔的肖像;伯纳多·普尔奇(Bernardo Pulci,1438-1488)将但丁的比阿特丽斯(Bertrice)、彼特拉克的劳拉(Laura)和西蒙内塔命名为“美德的理想化身”。波利齐亚诺则在他的短篇诗集《Stanze per la giostra del magnifico Giuliano di Pietro de Medici》中描述了朱利亚诺与西蒙内塔的柏拉图式爱情:她有洁白无瑕的肌肤,衣服上点缀了玫瑰、鲜花和珠子,金色的头发垂落在骄傲的前额之上。学者继而指出,“在文艺复兴思想中,美与美德紧密相连,因为身体美意味着精神的内在美——一个美丽的女人被视为一种媒介,可以通过爱吸引男人,并通过爱而面向上帝。”
根据佛罗伦萨的文件记载,西蒙内塔于1453年出生于热那亚(Genova)教区,母亲是卡托基亚·斯皮诺拉(Catocchia Spinola),母亲的婚姻并不幸福,最后一个孩子就是西蒙内塔。1469年,16岁的西蒙内塔嫁给了探险家亚美利哥·维斯帕奇(Amerigo Vespucci)的堂弟马可·维斯帕奇(Marco Vespucci),入嫁后即随丈夫来到了佛罗伦萨。然而,马可与西蒙内塔的婚姻最终只能证明是其父亲皮耶罗·维斯帕奇(PieroVespucci)为或利益而做的交易。因为在朱利亚诺追求已婚的西蒙内塔并得到后者的青睐时,皮耶罗并没有反对,而是为利益默许了这段婚外情,这在1479年的一封信中可以得到证实。“简而言之,皮耶罗·维斯帕奇将西蒙内塔送给朱利亚诺作为情人,以换取利益和经济利益。在所有这一切中,西蒙内塔不过是阿皮亚尼(Appiani)、维斯帕奇和美第奇三个家族为政治优势而斗争的典当。”西蒙内塔的美貌很快被佛罗伦萨城所赞扬,诗人、音乐家和画家都为其创作了不朽的作品,以至于后人将其视为“理想美的化身”。
近年来,关于《理想少女肖像》中的女子是西蒙内塔的话题有了新的论点。首先,该作品作为美第奇家族的财产,显然是由朱利亚诺委托波提切利创作;西蒙内塔作为当时佛罗伦萨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理想美的化身,也是朱利亚诺最钟爱的情人,其出资委托画家为西蒙内塔造像乃情理之中。其次,西蒙内塔在佛罗伦萨城的住处恰好位于靠近奥格尼斯·桑蒂教堂(OgnisSanti)的一条街上,波提切利的工坊就在同一条街上。由此可知,波提切利必定时常能碰见西蒙内塔,朱利亚诺委托一个熟悉西蒙内塔容貌的画家为她画像非常合乎逻辑。罗斯·布鲁克·埃特尔(Ettle Ross Brooke)指出,艺术史家将波提切利的《春》与《维纳斯的诞生》中所描绘的风景与与波托维内尔(Portovenere)附近的利古里亚海岸进行比对,结果发现有高度的相似性。而此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春》《 维纳斯的诞生》与法兰克福的西蒙内塔形象有高度的相似性,可以断定女主角为同一人;这三件作品创作时,西蒙内塔早已去世。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波提切利受朱利亚诺的委托,为她心中的女神造像,而在“委托方案”中,朱利亚诺要求波提切利将逝去的西蒙内塔的“永恒之美”描绘出来。可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波提切利在西蒙内塔逝世后为她绘制了一件充满了关于“美”的寓意的肖像作品,在这件作品中将倾注波提切利关于美的新柏拉图式观念(正如前文所述,波提切利的“美育”经历源于幼年时期的柏拉图学园)。

图5 里帕《图像手册》“赞美”(1764年版)
三、阿波罗与马西亚斯的寓言
在波提切利的笔下,西蒙内塔无疑是维纳斯的现实化身,她代表了整个佛罗伦萨城对美的想象。通过这件作品,波提切利成功将自己、朱利亚诺、波利齐亚诺乃至整个时代对西蒙内塔的赞美表现出来。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赞美同样具有古典传统,这一点可以从后来的里帕《图像手册》中得到图示:“赞美”(Lode: Praise)是一位身穿白色衣裙的美丽少女,胸前佩戴着墨绿色宝石,头上有玫瑰花环,右手持小号……墨绿色与玫瑰花表示赞美,因为佩戴者便能持续获得称赞和表扬。如前文所述,里帕的图像志来源于遥远的古代,白色衣裙、墨绿色宝石、玫瑰花等这些因素是古典传统对于“赞美”的象征;有资料表明,这块宝石正是美第奇家族藏的“尼禄印章”(Sigillum Neronis),我们知道这是一枚红宝石印章,波提切利将其描绘成墨绿色的原因可能是他熟知古典传统中“赞美”的图像符号。应该说,波提切利对西蒙内塔的赞美也如里帕描述的那样“持续获得称赞和表扬”,即西蒙内塔具有永恒之美,或者说西蒙内塔值得永远被赞美。西蒙内塔胸前的宝石可以证明上述观点,然而,正如艺术史家和评论家的推测,这件作品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含义,这一点可以从她胸前的宝石造型获得进一步的提示。

图6 《理想少女肖像》(局部)、尼禄印章(SigillumNeronis)
法兰克福的西蒙内塔胸前佩戴的浮雕宝石镶嵌在黄金外衬上,深墨绿色与规则的椭圆形使其在白皙的少女肌肤上凸显出来。浮雕表现的是一组三人形象,右侧是一个男子形象,其右腿屈膝,左手持工具,头部向右转动,躯干则朝向左边,这种微妙的运动平衡显示出明显的古希腊式造型方法;左侧是双手后束、双腿上抬屈膝,仿佛被捆绑吊起的男子;两人中间的下方蹲着一个模糊的形象。浮雕宝石的来源并不难推测,根据记载,这是属于美第奇家族的私藏宝石;这种宝石的形制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它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尼禄皇帝(Nero)时期,即所谓的尼禄印章(Sigillo di Nerone/ SigillumNeronis),现在这枚印章藏于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Napoli, Museo Archeologico Nazionale)。根据尼禄印章的主题和该宝石的造型,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这是古希腊神话主题“阿波罗与马西亚斯(Apollo and Marsyas)”。尼安斯卡·乔安娜(NiŻyńska Joanna)的研究指出,希罗多德(Herodotus)和色诺芬(Xenophon)的著作都证明了弗里吉亚(Phrygia)的马西亚斯河正是来源这个故事。
有一天,雅典娜(Atena)为了再现戈尔戈尼(Gorgoni)在珀尔修斯(Perseus)斩首修女美杜莎(Medusa)时发出的悲叹,发明了一种吹奏乐器——长笛。雅典娜在诸神的宴会结束之时,为了取悦宙斯(Zeus)及客人便开始吹奏长笛,尽管声音悦耳但仍引来众人取笑。雅典娜逃离奥林匹斯山(Olimpo)后来到了湖边并继续演奏,她很快就从湖水中倒映的图像看到自己因为吹奏而涨红和变形的脸庞,伤心的雅典娜丢弃长笛并对它下了诅咒。不久,来自弗里吉亚的作家马西亚斯捡获了长笛,他很快就掌握了演奏技巧;骄傲的马西亚斯甚至要挑战作为音乐之神和太阳之神的阿波罗。阿波罗拿出自己的竖琴,熟练地弹奏和唱起歌,而马西亚斯则无法像阿波罗那样边演奏边演唱,阿波罗获得胜利。为了惩罚落败的马西亚斯,阿波罗下令将其绑于树上并剥下皮肤,马西亚斯最终在残酷的折磨中死去,眼泪化成了一条河(马西亚斯河)。
根据劳迪娅·西埃里·维亚(Claudia Cieri Via)的研究,阿波罗和马西亚斯的主题在过去常被描绘在纸上,所谓的尼禄印章则可能是例外,现在保存在那不勒斯的这枚红宝石印章属于美第奇家族,它是在1428年由乔凡尼·德·美第奇(Giovanni de'Medici)购买,后来又被镶嵌上黄金外衬(现已丢失,故那不勒斯的尼禄印章没有镶嵌物),最后,这枚印章被归入洛伦佐·美第奇的财产中。通过波提切利的描绘或现存的印章可以看到,阿波罗以古希腊式姿势站在右边,手中拿着竖琴;奥林匹斯则跪在阿波罗脚下,似乎在恳求后者宽恕马西亚斯;马西亚斯反扣双手,挂在左边的树上,正在等待惩罚的到来。劳迪娅指出,在宝石上表现“阿波罗与马西亚斯”主题的作品极为罕见。以音乐比赛为出发点,阿波罗与马西亚斯的故事讲述的是失败者的惩罚,事件显示出强烈的残酷性,甚至说,这个血腥与暴力的故事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优美”或“典雅”相关联。
当面对波提切利这件作品胸前的尼禄印章时,我们不禁要发问:如果这件作品是表述对西蒙内塔诗意般的赞美和倾慕,那么为什么要描绘这个血腥的浮雕宝石,并且极力将其凸显出来?事实上,神话原型在不同时代常被人们根据社会文化需求进行阐释,于是出现同一神话母题含义在不断演进的历史环境中持续变化。古希腊时代对马西亚斯常见的解释是“傲慢的惩罚”,这种解释也同样适用于毕达哥拉斯的范式,代表普遍和谐的七弦琴被一种不和谐的特殊性(长笛)干扰;这种范式在古希腊很容易地被转化为政治术语,作为对社会和谐、国家秩序和政治等级制度的呼吁。
除此以外,我们应该考察阿波罗和马西亚斯主题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的象征模式。荷马(Homer)和赫西俄德(Hesiod)时代,阿波罗的形象还是射手、医术和文艺之神,其主要职能体现在战斗方面;直到希罗多德将原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剔除“十二主神”后,阿波罗正式转化为太阳神。实际上,阿波罗的形象在前苏格拉底到柏拉图时代被哲学家们重塑为理性之神,代表认知与辨证。
“一个和谐的名字(阿波罗),适宜用来称呼这位和谐之神……使人的身体和灵魂清洁和纯洁……阿波罗命令人们淋沐和涤罪,与此相关,称他为‘清洗者’是对的……”(《克拉底鲁篇》405.B.C.D)
在柏拉图看来,阿波罗在音乐、医术和预言等方面的才能使其具有“使万物和谐”的天性,他使人们洁净身体和净化灵魂,而这一切又寓于音乐的和谐之中。对于希腊人来说,阿波罗与马西亚斯的故事含义不像事件发生时呈现的那么直接,或者说,对马西亚斯的血腥惩罚只是一种隐喻。对于古希腊人的音乐理论来说,弦乐器代表了智力,而长笛则与感官相关;因此,阿波罗与马西亚斯的对立很可能是智力与感官的对立,或者说是精神与身体、理性与感性的对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毕达哥拉斯的象征主义变成解读这个主题的一个重要元素:在肉体与灵魂、理性与感性的对峙中,和谐比例成为美和神性的同义词,并在视觉艺术理论中发挥重要作用。

图7 《阿波罗和马西亚斯》,拉斐尔,1509年,105x120cm,壁画,梵蒂冈签署厅
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fosi)也为解读阿波罗与马西亚斯的隐喻提供了角度。奥维德写道,马西亚斯在被阿波罗剥皮时痛苦地呼喊出那一句“为什么要将我抽离自己的身体?”(Perché mi sfilidallamia persona/Why are you taking me off my person?)马西亚斯通过这句话传达了自身的苦难,但是奥维德却用这句话隐喻了这个过程中人性向神性的转化。阿波罗作为神圣音乐的代表,是理性、和谐、光明的象征,其作为神明战胜人类马西亚斯是必然的结果,而使用剥皮的惩罚则显示了柏拉图所说的“洁净身体和净化灵魂”的功能。在这里,马西亚斯喊出的那句“抽离自己的身体”实际上是宣告灵魂从苦难中脱离身体的过程,这一过程正是由和谐与理性之神阿波罗作为引导者。这个故事的隐喻正如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 la Mirandola,1469-1533)在1485年写的一封信中所提示:“剥去马西亚斯的皮囊意味着使灵魂脱离的世俗束缚,阿波罗的胜利就是神圣音乐的胜利。”从另一角度看,马西亚斯的被动“抽离”也可理解为主动向和谐与理性之美的趋近,这种对美的渴望和爬升正是费奇诺所说的“爱的状态”(《柏拉图<会饮>义疏》Volume 1.3)。
由此看见,法兰克福的西蒙内塔胸前的阿波罗与马西亚斯浮雕宝石实际上是关于肉体与灵魂、理性与感性、和谐与对抗的综合寓意的表述。波提切利看到了西蒙内塔被几个家族相互利用,看到了朱利亚诺与西蒙内塔的真挚感情,看到了人们对西蒙内塔美貌的倾慕。可以说,波提切利用阿波罗与马西亚斯的故事来隐喻他眼中看到的西蒙内塔是恰如其分的。他对西蒙内塔的赞美并非如佛罗伦萨城的人们那样表浅,而是用一种新柏拉图式的寓言表述了西蒙内塔的美与爱。在波提切利眼里,西蒙内塔作为凡人而深陷生活困境,但她拥有洁净的身体与纯洁的灵魂,神性的美与和谐在她身上显现,她的爱则表明了与神圣原型的联系。于是,波提切利借用了阿波罗与马西亚斯的故事隐喻了西蒙内塔的永恒之美,这种美正是在“灵魂抽离身体”后才获得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