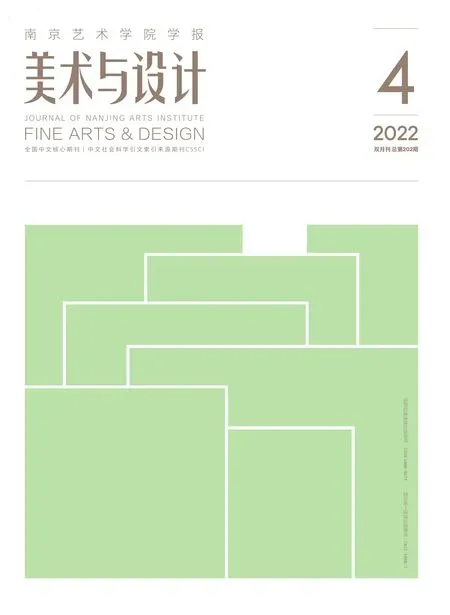从风格到工具:禅宗“散圣图”相关问题研究 ①
施 錡(华东师范 大学美术学院,上海 200062)
一、何谓“散圣图”
所谓“散圣”,是一些佛教传说中的高人异僧。《宋高僧传》将这些人物列入“感通篇”,该篇末尾附论曰:“若以法轮启迪,多作沙门之形;设如异迹化成,或作老叟之貌。”“在人情则谓之怪,在诸圣则谓之通。感而遂通,故目篇也。”《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归为:“禅门达者虽不出世有名于时者。”解题认为,这些从南北朝至五代时期言行神秘怪诞的异僧虽然不属于禅宗,但他们的思想和修行对禅宗有着强烈的影响。北宋仁宗时期镇国军节度使李遵勖(不详—1038)编的《天圣广灯录》卷三十中出现了“散圣”之称,将“东京景德寺僧志言”评为:“达者目为散圣,如佛图澄、寒山、拾得者也。”南宋释延琪《永嘉证道歌注》中云:“或人云无修无证者,乃诸散圣助佛扬化,已与往昔证,不复更证,譬如出矿黄金无复为矿。即宝公、万回、寒山、拾得、嵩头陀、傅大士等是也。”
至少在北宋就已出现了对散圣的绘制。日本僧人成寻(1011—1081)记天台县国清寺有“三贤堂”,其中的三贤者,即丰干禅师、拾得菩萨、寒山菩萨,丰干旁有虎,寒山与拾得作俗形。另剡县安下实性院有“傅大士影”。南宋释居简(1164—1246)的《北磵文集》卷七中“老融散圣画轴”:“自普化金华至蚬子凡十辈,意绪情态皆不失传记所载,非高怀逸想,经营磅礴,不见笔墨畦畛,若老融自成一家者,未易模写。曩留四明最久,间得之,好事者辄取之,今仅存觳觫一纸。议者以其微茫淡墨不足以永久,遂目之曰罔两画。行辈中寿此山一时名德,作诗尚奇涩,时号梵语诗。”散圣图可能以群像的形式,并淡墨画出,配以奇涩之诗。一些散圣图被布置在佛堂中,《禅林象器笺》“灵像门”:“僧堂中央所设像,总称圣僧,然其像不定。”“日本黄檗山万福寺僧堂,安布袋和尚为圣僧,未闻其有所据。”“散圣图”及题赞在宋元之间多有创作,大多从宁波一带被携带到日本,在中国反而很少得见。
“散圣图”与禅宗《列祖图》的制作与仪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楚石禅师语录》卷十四有“因陀罗所画十六祖闻上人请赞”,其后是“因陀罗所画诸圣闻上人请赞”,分别是空生、丰干、寒山、拾得、宝公、布袋、懒瓒、船子。这些祖师和散圣群像的绘制,可能在禅宗忌日的仪式中进行陈列,后传入日本。《禅林象器笺·报祷门》“祖师会”:“祖师会在岁旦,其达摩忌,张列祖像,亦是祖师会而已。《备用》称敷陈书画,似不局祖像。”
从能阿弥(1397—1472)编撰的足利义满(1358—1408)以来幕府收藏的中国画目录《御物御画目录》[10]来看,“布袋”“普贤”“四睡”的画题颇多,应是南宋至明朝间流行的“散圣图”画题,目前流传的诸多实物托于牧溪、梁楷、胡直夫等南宋画家名下,笼统地来说多为减笔墨画,但很难辨析风格与时代。
二、梁楷系的“散圣图”
目前较早期的有南宋画家梁楷名下的一些“散圣图”。梁楷的活动年代大致是13世纪前期,据《图绘宝鉴》:“梁楷,东平相义之后,善画人物山水释道鬼神。师贾师古,描写飘逸,青过于蓝。嘉泰年(宁宗年号,1201—1204)画院待诏,赐金带,楷不受,挂于院内,嗜酒自乐,号曰梁风子。院人见其精妙之笔,无不敬伏,但传于世者皆草草,谓之减笔。”《图绘宝鉴》同卷将梁楷师法的贾师古记载为:“贾师古,汴人,善画道释人物,师李伯时白描,绍兴画院衹侯,其人物颇得闲逸自在之状。”梁楷的减笔人物画可能受贾师古白描画风的影响。
寒山、拾得两位“散圣”,往往与丰干同在,有时伴随虎,组成对轴或三幅对等形式。丰干是唐代天台山国清寺的禅师,常伴一虎。寒山自天台寒岩入国清寺,拾得被丰干带到国清寺收养,个性诙谐,与寒山相好。《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分别为三人立传。寒山是一位诗僧,他与天台山国清寺丰干、拾得的友谊被津津乐道。成寻还提到贞观十七年(643),因丰干说寒山与拾得是文殊与普贤的化身,刺史闾丘胤赴国清寺相见,寒山与拾得把手大笑而去,刺史至丰干禅院,唯见虎迹。现在留存的一些以寒山、拾得为题的绘画,应是出自这则传说,其同时录于《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不同的是闾丘公赴国清寺拜谒是由于丰干曾为其治病。
寒山和拾得的形象一般是颇为夸张和滑稽的。《宋高僧传》卷二十二的“论”云:“(寒山、拾得)疮痍可恶,疥疠堪嫌。或逆逜于恒流,或譸张于下类。”据李舜臣研究,“寒山拾得图”是宋元散圣图中最多的一种。此外,丰干的另一个形象是布袋和尚,因为布袋也是弥勒的化身。《宋高僧传》卷二十一载四明人释契此,“形裁腲脮,蹙頞皤腹,语言无恒,寝卧随处。常以杖荷布囊入鄽肆,见物则乞,至于醢酱鱼葅,纔接入口,分少许入囊,号为长汀子布袋师也。曾于雪中卧,而身上无雪,人以此奇之”。其形象是身宽体胖,大腹便便,鼻子微蹙,出语无定,随处寝卧,杖荷布囊。
梁楷的《泼墨仙人图》(图1),由于风格特出往往是学界争论的对象。《历代名画记》卷二“论画体工用搨写”:“不见笔踪,故不谓之画。如山水家有泼墨,亦不谓之画,不堪仿效。”所谓“泼墨”是无笔踪之画。该图采用泼墨法画成,与同为梁楷名下的《李白行吟图》有很大的不同。若与牧溪的《潇湘八景图》相比,墨法显得更为放纵野逸。徐邦达先生曾道:“纸本,墨笔画一人独立,脸形丑怪,用较细笔描五官;衣纹则水墨浓淡涂搨,所谓‘减笔’,别具一格。款‘梁楷’二字。”并未明确提出质疑。但认为该画用笔软熟,款字不似一般梁楷所署,可能是明人之作。但王耀庭先生比较《泼墨仙人图》的款识之后,认为都带有破笔,可以说是豪纵的风格,不能排除是梁楷所作,笔者倾向于同意王耀庭的意见,认为是梁楷或其较接近的传人之作。王耀庭还曾在举出《北磵诗集》卷四有诗《赠御前梁宫幹》:“梁楷惜墨如惜金,醉来亦复成淋漓。”对比款识和风格后将《李白行吟图》也定于梁楷之作,同时代人亲见,梁楷有“惜墨”之作,如《李白行吟图》,又有“淋漓”之作,如《泼墨仙人图》。而《泼墨仙人图》中的人物可能是丰干,是布袋和尚的人物原型。

图1 南宋,梁楷,《泼墨仙人图》,册页,纸本墨笔,48.7x27.7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传梁楷的《寒山拾得图》(图2)画面来看,寒山与拾得带着滑稽的笑容,蓬发披肩,身穿道袍,一袒腹,一合掌。从画风来看,脱离了宋画中氤氲的墨法。左下角的款识与标准件梁楷款识书风不同,应是后人之作。但传承了《李白行吟图》的用笔,人物表情颇为滑稽,且用劲利之笔绘成,袍服用粗笔擦拭而成,水平高超,疑为其传派中画家制作。

图2 传南宋,梁楷,《寒山拾得图》,轴,纸本墨笔,81.1x33.9cm,MOA美术馆藏
《图绘宝鉴》卷四载梁楷有弟子俞珙、李权、李确,目前前二者的画作未见。“李确,白描学梁楷。”李确有《丰干·布袋》(图3)双幅藏于日本京都妙心寺。画中的用笔,与前述《寒山拾得图》非常相似,看似逸笔草草,实则简洁流畅。

图3 传南宋,李确画,偃溪广闻赞,《丰干布袋图》,二幅,轴,纸本墨笔,各104.8x32.1cm,京都妙心寺藏
南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对寒山子的接受进一步地巩固和深化,出现不少题寒山拾得等散圣画题的诗。如方回(1227—1305)有《题布袋和尚丰干禅师寒山拾得画卷(并跋)》,跋曰:“今有二异僧,一虎随之入城市,一曳布袋引群小儿,民间不鼎沸喧哄乎。”还有《又题画赤脚仙》,其中有句“甘作蓬头赤脚人”。而方回和李确的活动时期也相去不远。在《丰干·布袋》双幅中,丰干背一布袋,寒山身边有一虎。在画面的上方,有南宋偃溪广闻禅师(1189—1263)的题赞。《布袋图》赞:“荡荡行波波走,到处去来,多少漏逗,瑶楼阁前,善财去后,草青青处还知否。住径山偃溪黄闻。”“广闻印章”白文方印,“偃溪”朱文长方印,“五髻山人”朱文重郭长方印。对幅的《丰干图》风格与《布袋图》一致,但衣纹的绘制笔法似略为湿润,或出于两位画家之手。据说还有一幅由南宋临济宗禅师灭翁文礼(1167—1250)所赞的《达摩图》,与此二幅形成“三幅对”,现仍寄存妙心寺。从人物手部的绘制,也能见出二者的不同,《布袋图》更为劲利,《丰干图》则较为柔和。其上同样有偃溪广闻题赞:“只能据虎头,不解取虎尾,惑乱老闾丘,罪头元是你。径山偃溪广闻。”“广闻印章”白文方印,“双径”朱文壶印,“五髻山人”朱文重郭长方印。若仔细比对,两件的“广闻印章”和“五髻山人”印也都略有不同,但《丰干图》中的虎画得颇为生动,笔法简练,笔者以为此两件的时代相去不远。
若将李确之作与《李白行吟图》对比,从用笔来看,后者尚未完全脱离南宋墨法的影响,如李白的衣领和衣裾处都显示出墨色的氤氲。相同的是,人物的发式、五官和鞋履,带有笔毛杂出的效果。如发髻后面杂出的线条,鞋子下面的细线,突破了应有的轮廓,笔者以为并非刻意画出,而是有工具的作用在内。若细观人物的须发细部,会发现一束须发是一个笔触的尾端。如下胡须大致是由三笔或四笔画成,上胡须大致由两笔或三笔画成。
《李白行吟图》实际上是对幅中的一件,左上角钤盖元代八思巴文的“大司徒印”。日本画坛历来有重复绘制某一人物形象的传统,狩野探幽(1602—1674)制作了对幅的摹本,使另一幅《东方朔图》的图像得以保留。在探幽之后,19世纪的信章、狩野董四郎再次临摹了这套对幅(图4)。若观看笔触(图5),会发现徒具形似,但破笔处往往由几笔“做”成,失去了早期画家的肯定。笔者以为这是鉴别南宋至元的禅画与后世仿造的重要因素。

图4 江户时代,文政6年(1823),信章、狩野董四郎模,《東方朔·李白图》,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5 信章、狩野董四郎模本与梁楷原作细部对比
梁楷及其弟子的画风在其后得以传承。默庵灵渊曾绘制一件《布袋图》(图6),笔墨十分精到,风格接近李确,通过笔法的变化,将人物的衣袍表现为粗笔,面部和手脚采用较细的深墨,腹部、手臂、布袋等采用较细的淡墨。部分区域如脸颊和前胸等未曾完全闭合,带有一定形体的暗示性。此外布袋和手杖的墨色,与指天的姿势形成一种画面的平衡感。

图6 元代(14世纪),默庵画,了庵清欲赞,《布袋图》,纸本墨画,80.3x31.8cm,静冈,MOA美术馆藏
在日本,默庵被誉为“牧溪再来”。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画家长谷川等伯(1539—1610)的《等伯画说》中曰:“默庵的笔法如同牧溪一般稀有。”成书于16世纪前期日本室町幕府时代的《君台观左右账记》载:“默庵,牧溪再来,笔迹亦同。”据从元朝的中国归去的日本禅僧钝夫全快(1309—1384)所述,默庵是原名,灵渊是其在修行时所得法名。默庵入元后在了庵清欲禅师(1288—1363)的门下修行,后访问西湖六通寺,被院主称赏为“牧溪再来”,并赠予牧溪的两颗遗印。这件画作中正有他师事的了庵清欲的题赞:“指端光怪本相见,肚皮虽大眼已眩。放浪多游族姓家,只个布囊推不转。本觉比丘清欲赞。”“天台沙门清欲了庵言”白文方印,“公林心印”朱文方印。其右下方还有“灵渊”白文方印、“默庵”朱文方印,题赞与布袋指天的手势可以契合。
默庵笔下这一指天的布袋形象,也曾出现在16世纪室町时代的画家兴牧的笔下(图7)。若观察两件布袋的形象,最大的差别仍在于线条的浓淡和劲利之上。默庵之作有“魍魉画”之隐现感,形体更为简略,笔触和墨色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叠,简洁感产生了几何平衡的视知觉;晚期之作整体趋向于闭合。对于须毛的处理,默庵更为微妙自然;兴牧则不得不多层渲染来表现蓬松的毛发效果。

图7 室町时代(16世纪),兴牧,《布袋图》,纸本墨画,尺寸不详,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三、因陀罗系的散圣图
在元代还出现了因陀罗的湿润墨色对比风格。“散圣图”的格调为之一变,轮廓中既有破笔,又有均衡的简洁风格被打破。
首先简述因陀罗其人。根据《寒山拾得图》款识“佛慧净辨圆通法宝大师壬梵因/宣授汴梁上方祐国大光教禅寺住持”,他担任元代汴梁路上方祐国大光教禅寺的住持,法号佛慧净辨圆通法宝大师,法名壬梵因。《君台观左右账记》中载为:“印陀罗,天竺寺禅僧,人物、道释。”在《等伯画说》中,记为“天竺ハ因陀罗一人(唐へ布袋书之)”。据日本学者川上泾在《梁楷·因陀罗序说》中的考察,长尾美术馆旧藏的《寒山拾得图》的款记“王舍城中壬梵因笔”、川崎家旧藏《寒山拾得图》有印“沙门梵因”,京都国立博物馆的《寒山拾得图》和《维摩图》有“释氏陀罗禅余玄墨”的白文印,再加上前者款识中的“壬梵因”,正是画史中的“因陀罗”,全称或为“陀罗梵因”。现存因陀罗的禅机图断简,即《布袋图》《智常李渤图》《寒山拾得图》《智常禅师图》《丹霞烧佛图》,五幅笔法一致,可能是被后人分断的同一长卷。
因陀罗《寒山拾得图》(图8)采用减笔画法画出植物以及蓬发大笑的人物。松树已经程式化,松针呈现车轮形,枝条用连笔Z形画成。寒山和拾得形象虽简易,但墨色丰富,毛绒的蓬发干笔皴擦而出,五官用笔略为劲利,手脚结构自然。人物的腰带用浓墨,但并不干枯,同样的用笔还有树枝和花草。地面的土质用的是较干的淡墨,略似倪瓒(1301—1374)的折带皴。因陀罗的禅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用笔的纵横与肯定,几乎没有停滞和犹豫。这一墨色和用笔,也见于因陀罗的款识。左方有楚石梵琦禅师(1296—1370)题赞:“寒山拾得图两头陀,或赋新诗或唱歌。试问/丰干(删去“年”字)何处去,无言无语笑呵呵。”钤“楚石”白文方印。由墨迹和短边35厘米可见,这件横披实际上是手卷改装,位置可能是卷末,可能是适应茶室装饰的需要所改装的。

图8 元代,14世纪,因陀罗,《寒山拾得图》,轴,35×49.5cm,纸本墨笔,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国宝
《布袋图》(图9)画面题赞的格式与《寒山拾得图》一致。右方有楚石题赞:“花街闹市恣轻过,唤作慈尊又是魔。背上/忽然揩出眼,几乎惊殺蒋摩诃。”钤“楚石”白文方印。据《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画中内容为五代时人陈宗霸,与布袋和尚往来密切,布袋教其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为日课,并呼其为摩诃居士。一日摩诃陪着布袋在长汀溪中沐浴,和尚要摩诃居士为他揩背,摩诃居士忽见和尚背上有四目,迥然光灿,大为惊异,作礼道:“和尚是佛也。”布袋和尚说:“勿言。”与《寒山拾得图》相似,画中的人物面部用细笔画出,衣袋和草木等用浓墨,树用浅墨,地面用很浅的干墨皴擦暗。

图9 元代,14世纪,因陀罗,《布袋和尚图》,轴,35.8×48.8cm,纸本墨笔,根津美术馆藏
《丹霞烧佛图》(图10),典出《五灯会元》卷五。邓州丹霞天然禅师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烧火,院主诃曰:“何得烧我木佛?”师以杖子拨灰曰:“吾烧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师曰:“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主自后须眉坠落。这是一种禅师的机锋,用来引导应答者觉悟,一些著述也将这类画作称为“禅机图”或“禅会图”。右方有楚石题赞:“古寺天寒度一宵,不禁风冷雪飘飘。既/无舍利何奇特,且取堂中木佛烧。”钤“楚石”白文方印。左下还有一朱文印:“儿童不识天边雪,把乍杨华一例看。”

图10 元代,14世纪,因陀罗,《丹霞烧佛图》,轴,32×36.7cm,纸本墨笔,畠山纪念馆藏
《智常李渤图》(图11)也是一件禅画多用的题材。唐穆宗时期的江西刺史李渤问庐山归宗寺智常禅师:“教中所言‘须弥纳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纳须弥’,莫是妄谭否?”师曰:“人传使君读万卷书籍,还是否?”李曰:“然。”师曰:“摩顶至踵如椰子大,万卷书向何处著?”李俯首而已。李异日又问云:“大藏教明得个什么边事?”师举拳示之,云:“还会吗?”李云:“不会。”师云:“遮个措大,拳头也不识。”李云:“请师指示。”师云:“遇人即途中授与,不遇即世谛流布。”画面的内容,也是智常与李渤在对话。李渤身着官服,头戴幞头,手持笏板,正在弯腰请教;智常坐于山石之上,面前放着经函、净瓶。背后则是淡墨乔松,以及浓墨灌木。这件画作表现出因陀罗有意识地对浓淡墨的互用,如经函上的线条即为如此。左方有楚石题赞:“椰子中藏万卷书,当时太守焚分疏。山僧/手持椰栗棒,便是佛来难救渠。”钤“楚石”白文方印。

图11 元代,14世纪,因陀罗,《智常李渤图》,轴,35.2×45.2cm,纸本墨笔,畠山纪念馆藏
《智常禅师图》(图12),描绘的是智常禅师与诗人张籍的禅机问答。张籍晚年和僧道交往十分频繁,诗集不仅保留有他和僧道的酬别唱和诗,还有题写僧院道观之作。如《禅师》:“独在西峰顶,年年闭石房。定中无弟子,人到为焚香。”《题晖师影堂》:“日早欲参禅,竟无相识缘。道场今独到,惆怅影堂前。”左有楚石梵琦题赞:“堪笑归宗张水部,都无佛法与神通。若论向上宗门事,尽在山光水色中。”钤“楚石”白文方印。

图12 元代,14世纪,因陀罗,《智常禅师图》,轴,35.5×48.6cm,纸本墨笔,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这几件断简,人物均用湿笔画成,并不交叉重复,地面与树干用干笔,创作规律分明。楚石梵琦的书法风格与赵孟 颇为相近。正如启功先生所论:“有元一世论书派,妍媸莫出吴兴外。”这与南宋禅师雄浑有力的书风也已大相径庭。值得注意的是,画面的分割均采用在一株树下展示一组人物,与六朝砖画《竹林七贤图》、传唐代孙位的《高士图》的图式结构相似,也与元代张远的《潇湘八景图》,以山石区隔八景的结构有相通之处。
因陀罗的湿润笔法与墨色对比风格从何而来虽已不可考,但偃溪广闻在主持径山兴寿万圣寺(1256—1263)时所赞的一件《普化图》(图13),画风与其有相通之处。普化和尚的事迹记录在北宋人钱易的《南部新书》“庚”,咸平年间(998—1003)一位异僧,手持一铃铎,后示灭,不见人影,惟闻铎声渐渐远去。《普化图》与因陀罗之作都采用了湿笔及浓淡墨色对比进行创作。同时,在人物衣袖和衣领处用较大面积的墨色渲染,也存在类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普化图》的破笔较多,因陀罗的画风则更为柔和。虽然《普化图》不能确认为胡直夫所作,但很可能出自南宋末至元代之间的某位画家之手。

图13 传南宋,胡直夫画,偃溪广闻赞,《普化图》,轴,75.0x29.1cm,纸本墨笔,个人藏
四、从工具看散圣图风格
“散圣图”的风格经历了由南宋的墨法,到梁楷传派的劲利笔法的轮廓勾勒,以及因陀罗系的湿笔为主,墨色对比,笔者以为这一现象与工具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
从“破笔”之作来看,典型的有牧溪名下的《布袋图》(图14),同样采用淡墨画成,布袋的五官采用劲利的深墨,另一处幽深的墨笔则用在了水平放置的拄杖上,使画面达到了一种妙不可言的平衡,这与默庵非常类似。该画并无牧溪的款识,右下角有“善阿”印,关于这一印鉴,主流的观点认为是与足利义满的时代相近的,担任幕府财产的保管和出纳的善阿弥“善阿仓”的鉴藏印,钤印的对象则是幕府所保存的中国画。从淡墨的运用以及墨色的对比来看,这件《布袋图》可能是梁楷传派画家,甚至为默庵所作。几乎一致的“破笔”笔法,可以从玉涧的《庐山图》(图15)中见到。

图14 传南宋,牧溪,《布袋图》,纸本墨画,77.1x30.9cm,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图15 南宋,玉涧,自赞,《庐山图》,绢本墨画,35.5x62.7cm,冈山县立美术馆藏
正如前文所述,《布袋图》和《庐山图》中的“破笔”是笔触内部效果。玉涧的题赞与画用的应是同一支笔。在北宋蔡襄(1012—1067)的《陶生帖》中,若放大单个字体,就会发现这种“破笔”。而这种用笔,在现存日本的南宋张即之(1186—1263)以及前述偃溪广闻的书法中也能见到。
据何炎泉研究,蔡襄在《文房四说》中曾提到“散卓笔,心长特佳耳。”“近宣城诸葛高造鼠须散卓及长心笔绝佳。”当时著名的笔工为宣州的诸葛高。黄庭坚《笔说》曰:“宣城诸葛高系散卓笔,大概笔长寸半,藏一寸于管中,出其半,削管洪纤与半寸相当,其撚心用栗鼠尾不过三寸耳。但要副毛得所,则刚柔随人意,则最善笔也。”何炎泉认为,“散卓笔”是一种有心笔,用栗鼠尾的毛“三株”来“撚心”。黄庭坚《书吴无至笔》:“(吴无至)作无心散卓,大小皆可人意。然学书人喜用宣城诸葛笔,著臂就案,倚笔成字,故吴君笔亦少喜之者。使学书人试提笔,去纸数寸书,当左右如意,所欲肥瘠曲直皆无憾。然则诸葛笔败矣。”因没有用健毫为心,适合提腕书写,虽不适合初学者,但运转起来却不受撚心的限制。如黄庭坚所云:“东坡平生喜用宣城诸葛家笔……每得诸葛笔,则宛转如意……然东坡不善双钩悬腕,故书家亦不伏此论。”
无心笔的流行,大致是熙宁年间(宋神宗年号,1068—1077)开始的。散卓笔难以控制,对使用者来说形成挑战。叶梦得(1077—1148)曾说:“嘉祐(宋仁宗年号,1056—1063)前,有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云:‘一枝可敌他笔数枝’。熙宁后,世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首先是散卓笔写出的字在圆转线条时常有破笔出现,这可能也是北宋人爱作飞白书的原因之一。第二即如何炎泉所论,用散卓笔所作之书笔画粗细变化很大。第三,散卓笔在转折处不容易把握,有时出现硬笔的结块,徐邦达先生也曾提到,晋代王珣《伯远帖》中即有类似情况,与米芾临《中秋帖》丰润圆熟的视效完全不同。在起收笔处有时还出现杂出之笔。
以明确提到“散卓笔”的蔡襄《陶生帖》为例,笔画粗细变化大并有飞白视效。再苏轼《寒食帖》(图16),虽然用墨较湿,但在一些字上仍有同样的现象。采用这样的有心笔,给墨迹带来一种雄健质朴的气息。若比较自书“以羊毫作字”的米友仁《潇湘奇观图》的自题(图17),就会发现米友仁的笔画提按浓淡变化在同一字内较为均匀,长笔画较有飘移的柔性视感,笔画末端更加肥润。

图16 苏轼《寒食帖》局部

图17 米友仁《潇湘奇观图》题跋(局部)
禅宗的书风与时代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目前最古的宋代禅宗墨迹,是云门宗大觉怀琏(1009—1090)的《与叔通教授》。道潜号参寥子,是苏轼的挚友。韩天雍认为道潜的书法与苏轼中年的书法风格相似,也有颜真卿的骨骼。此件粗笔与细笔之间对比强烈,笔锋健韧。禅院中设置牌字和额字,有书写大字的需要,风格要求肃穆雄健,不拘一格,此类书法最为适应。至南宋时期日本僧人圆尔辩圆(1202—1280)向无准师范(1179—1249)索求的大字题额传到日本,风格亦如此,并与南宋张即之(1186—1263)所书极为相似。一般认为张即之学欧阳询、褚遂良及米芾,实际上他深受禅宗书法的影响。当传到日本后,成为流行的书体。从诸多“散圣图”的题赞来看,其他南宋禅师的书风也多为此类质朴有力的用笔。
再看玉涧《庐山图》中的题赞,同样是横画细,竖画粗,转笔略滞的书写。若对比无准师范、张即之、兰溪道隆、偃溪广闻、了庵清欲等禅师的书法(图18),也均类此,笔画粗细变化大,转折滞拙,末端尖锐有破笔,是南宋禅林流行的书风。至楚石梵琦(图19),笔法圆润温和,似为采用类似米友仁的无心羊毫笔,因陀罗自书款识亦为此笔,只是笔画开张仍未脱南宋至元禅师的质朴,中峰明本(1263—1323)所谓“柳叶书”亦有这一特点。

图18 张即之与兰溪道隆书法对比[36]

图19 玉涧、偃溪广闻、楚石梵琦、因陀罗书法对比
与上文所举工具的变迁相类似的是,梁楷系的用笔出现简洁有力的飞白破笔;而因陀罗的用笔则墨法湿润,浓淡对比。但这两种风格的笔法,都与部分“散圣图”中狂躁杂乱之状不同。
日本藏有的对幅,传梁楷的《丰干图》(图20)和传马麟《寒山拾得图》(图22),由活动于13世纪的石桥可宣题赞,应为托名之作。石桥可宣是拙庵德光(1121—1203)的法嗣,四川人,嘉定三年至九年(1210—1216)主持径山。但这件画作的干枯硬笔风格并非来自南宋,徐邦达先生认为可能是日本人所画。此对幅的墨法,与现存因陀罗之真迹不似,反而与石恪名下的《二祖调心图》(图23)很相似。画中的杂乱线条是多笔交织而成。此判定为元代以后的临创本。同样,《二祖调心图》从破笔来看仿造的是梁楷画风,从浓淡墨的对比来看又学习了因陀罗一路,笔者以为是这两种元代风格出现之后才进行仿制的,必定晚于因陀罗的时代。

图20 传南宋,梁楷,石桥可宣赞,《丰干图》,轴,纸本墨笔,90.5x32.0cm,东京个人藏,重要文化财

图21 传南宋,马麟,石桥可宣赞,《寒山拾得图》,轴,纸本墨笔,91.3x33.6cm,东京个人藏

图23 传北宋,石恪,《二祖调心图》,纸本水墨,35.5x129厘米,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整体而言,从南宋到元代的“散圣图”的变化,在形式上经历了从墨法“闭合”到笔法“开放”的过程;从简洁“破笔”到墨色“润笔”的过程,并同时体现在图像和题赞两个方面。后世出现的一些“散圣图”,刻意“做”成破笔,应排除于这两路风格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