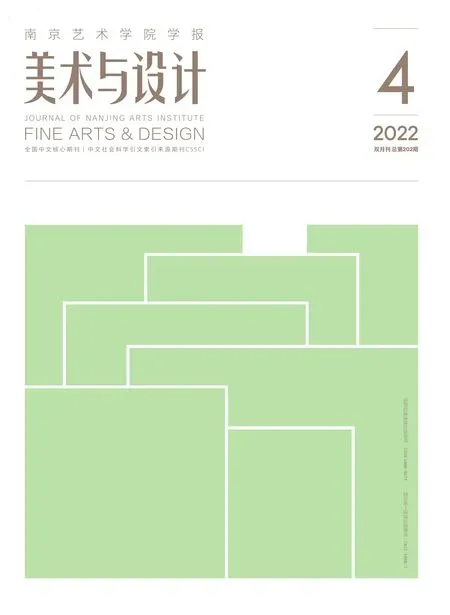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气象”说与道家“气”论 ①
毛文睿(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一、山水画论“气”与“象”的理论先构
与西方风景画相比较,中国画更注重展示一种浑然统一的整体格局。这当然不是绝对的,西方古典和现代风景画也有一种整体的和谐美感。但中国传统山水画那种将天地万物笼被于一体的审美气象,却是西方风景画所缺乏的。
中国传统山水画这种整体的格局和气象的形成具有深刻的思想渊源,它主要根源于先秦道家的“气”论思想。需要指出的是,先秦时期,“气”有着多重内涵。虽然“气”的概念并非先秦道家最先提出,但其论“气”的思想对中国传统山水画整体格局与气象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和根本的。先秦道家论“气”,尤其强调对天地万物进行化合作用,可以说正是由于“气”的调和,天地万物才能够生成、交融,构成浑然统一的整体。而由“气”生成的天地万物,也就是所谓的“象”。总之,先秦道家有关“气”的论述构成了后世山水画论“气象”范畴的理论来源和思想基础。
先秦道家的老子、庄子关于“气”有不少论述,这些论述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丰富的材料。老子说:
“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
这即是说,由于“气”的存在,天地万物得以交融为一个整体,有了“气”的调和,宇宙之“道”才衍化为天地万物。而“和”,正是指一种由“气”(“冲气”)构成的现实物象的整体存在。
庄子有关“气”的论述就更多了。例如,庄子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又说:“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调,四时不节。今我愿合六气之精以育群生,为之奈何?”庄子所说的“气”,内涵相较老子更为丰富,它既是物质自然之“气”,也是主体精神之“气”,但无论“气”指代什么,在庄子这里,“气”都象征天地万物的本源,它能够生发万物,亦能调和万物。可以说,庄子从本体意义上将天地万物界定为“气”,由此更加深刻地揭示了“气”的整一品格。这一观点在以下两则论述中体现得最为直接:
“通天下一气耳。”(《庄子·外篇·知北游》)
“游乎天地之一气。”(《庄子·内篇·大宗师》)
这就是说,天地万物皆由“气”构成,是“气”的不同形态,“通天下一气”“天地之一气”,都旨在说明“气”是造成天地万物统一整体的元素这个道理。庄子还用“混沌”的寓言故事讲述“气”浑然统一、不可分割的性质: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内篇·应帝王》)
这里所说的“中央之地”的“浑沌”,即指“气”在本然状态下浑然统一的特征和品质,一旦凿窍分别之,这个“浑沌”便被离析,不复存在。类似的观点,庄子还说过:“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物固自生。”此处“浑浑沌沌”与“浑沌”之喻一样,都是指“气”的整一品质。
老子、庄子还用“一”这个数量概念来表述天地万物(“象”)的生成具有的整一特征。例如,老子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
又说: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老子·第十四章》)
这里的“一”(“道生一”),就是由“气”(阴阳未分之“气”)形成的整一状态。后一段论述虽然讲的是“道”不可感知的性状,但“混而为一”,则表明完整统一也构成了“道”之本体的基本品质。庄子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又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万物与我为一”“有一而未形”同样昭示了“象”因“气”具有的浑整特征。
可见,老子、庄子论“气”,强调由“气”生成万物,万物大化为“象”,由此构成了现实的整体存在。这一整体存在同时也因“气”葆有着浑整的特征。这正是“气象”概念的思想内涵。
后来汉代哲学将“气”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更加强调“气”生万物,“气”统天地的浑然整一的品质。这集中体现在汉代两部重要的哲学论著《淮南子》和《论衡》当中。例如,汉代《淮南子》言:“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一气者也。”“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气始下,地气始上,阴阳错合,相与优游竞畅于宇宙之间,被德含和,缤纷茏苁,欲与物接而未成兆朕。”同时代的王充《论衡》一书中也讲:“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气”充塞天地间,自然万物皆含“气”而生,于是鸿蒙宇宙无非“一气”,在这“一气”中,“古之人同气于天地,与一世而优游”,“气”的浑整格局同样也会影响主体的生命活动,这为后世山水画创作确立了一种经纶天地、涵纳自然万物的整体意识。
“气”“象”这两个概念在先秦老庄哲学中虽然未曾连缀成一个独立概念,但两者在逻辑上相互包含、相互贯通,为后世山水画“气象”概念的提出和确立提供了思想条件。可以看到,后世山水画论要求画家对自然万物作整体的观照和把握,继而在创作中表现出浑整统一的山水格局。就如清代石涛所说:“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浑沌”的审美理念成为中国传统山水画创作重要的审美追求。
二、晋唐五代画论“气”“象”概念的提出
老庄哲学的“气”论思想在汉代有了进一步的理论发挥,尤其是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提出的“元气”说,将“气”论推至新的思想高度,对后世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
降至魏晋南北朝,在关注自然美的时代背景下,许多文人名士投身书画实践,关于“气”“象”的言论日趋丰富。
这里我们主要考察一下有关“象”的见解。其实老庄哲学(包括《易传》)对“象”便有精辟之论,但大都停留在哲学层面(这当然也是后世书画理论“象”的思想渊源)。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象”论,则带有鲜明的审美色彩,与艺术实践息息相通,这在书画理论中反映出来。例如,书法领域,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出文字构造的“象形”法则,就是很好的例证。书论中更是出现了大量有关“象”的表述。如,东汉蔡邕说:“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西晋索靖说:“科斗鸟篆,类物象形,睿哲变通,意巧滋生。”再如在画论中,东晋顾恺之说:“即形佈施之象。”又讲:“可于次峰头作一紫石亭立,以象左阙之夹,高骊绝崿。”南朝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像。”这些例证说明,这一时期书画论“象”,进一步建构出了具有审美意味的“象”,将哲学意义的“象”落实到了审美层面,因此“象”作为一个审美概念确立了起来。同时,书画理论中有关“气”的见解也日益丰富。例如南朝王微提出,绘画“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其中“太虚之体”即为“气”。书法谈“气”的论述就更多了。如,东汉赵壹言:“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又如,东晋王羲之言:“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尽管“气”的所指对象和内涵并不一致,但其审美意味却都是十分鲜明的。基于上述书画理论中“象”“气”的审美思想取向,南朝谢赫的“气韵”“象形”说应运而生,可见这是必然的思想产物,它是先秦至两汉以来“气”“象”思想的一个审美汇聚和理论结晶,为后世绘画理论中“气”“象”概念的逻辑连结以及“气象”范畴的铸成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谢赫在“六法”中有关“气”“象”的论述形成了相互关联的两个原则和标准——“气韵生动”“应物象形”,不仅揭示了中国绘画“气”“象”的内在关联,也彰显了形成一种整体统一艺术格局的可能性,这为后来明确提出“气象”概念铺垫了审美基础。我们看到,在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一书中,“气象”概念经由品评的方式被正式提出,并被用来评价部分画家的山水作品。例如,张彦远说:
“刘整,任秘书省正字,善山水,有气象。”
“恬好为顽石,气象深险,能为云,而气象蓊格。”
需要指出的是,张彦远关于山水“气象”的说法在当时还只是一般评语,“气象”的内涵还没有从理论上作出界定和阐发。而张彦远有关“骨气”与“象物”的论述则从侧面对山水画“气象”的概念内涵产生了影响。张彦远指出:“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在张彦远看来,“用笔”是绘画“气”与“象”得以酝酿而成的基础,画者通过“用笔”能够营构物象内在的生命气韵。可以说,这一观念对山水画“气象”内涵的完整呈现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可以看到,后世画家不仅持续关注“用笔”与“气”“象”(形)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意识到了通过“用笔”营构山水画“气象”的可能。
总体来说,从汉魏六朝一直到唐代,绘画理论有关“气”“象”的阐发从不同角度触及了“气”“象”的审美内涵,为后世绘画“气象”的理论概括作了充足的准备。特别是张彦远已然提出“气象”一词用来评价山水画,这意味着“气象”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概念正悄然成型。
三、荆浩“真元气象”论的理论概括
完整且有着明确内涵的“气象”概念,是在五代山水画家荆浩这里真正形成的,荆浩不仅正式提出了这一概念,还对它加以阐发,使其具有了明确的审美内涵。荆浩在《笔法记》中说:
“气象幽妙,俱得其元。”
“放逸不失真元气象。”
这些关于“气象”的论述至少有如下意义:一、它是对前人论“气”“象”的一种理论提炼和总结,其中也包含了荆浩本人对山水画实践的深切体察。二、在荆浩这里,“气象”有了较为本质的理论概括,荆浩认为,“气象”展现出的是一个浑然统一的山水格局。三、荆浩提出“真元气象”这一命题,用“真”“真元”规定了山水画“气象”的内涵,不仅强调出了“气象”的整体形状,还揭示了“气象”的真实品质,这种品质是统摄物象又超越物象的,是以“气”为主导,渗透在“象”当中,从而高于形似之上的“真”“气”“象”。荆浩说:“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又说:“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凡气传于华,遗于象,象之死也。”这也是讲,山水画“气象”应当符合“真”这一标准,要能够做到“气”“象”兼备,要将“象”的初始元气(即所谓“物象之源”)通过山水形态表现出来。四、荆浩认为,山水画“气象”的整体格局在笔墨层面也应当有与之相应的审美特征。荆浩认为,具有“气象”的山水作品,包含“动用逸常,深不可测”的特点,以及“用墨独得玄门”的特征。这就是讲,山水画的位置经营、用笔、用墨等表现手法应与浑然整一的“气象”相匹配。具体来说,就是用笔的痕迹与墨色晕化能够产生一种元气淋漓、浑然一体的效果,反之,画面的浑整意蕴便会荡然无存,对此荆浩补充说,未能表现浑整“气象”的山水作品多有“巧”“雕琢”的迹象特征:“巧者,雕缀小媚,假合大经,强写文章,增邈气象,此谓实不足而华有余。”“巧”“雕琢”着意人为工巧,不但无益于浑然“气象”的生成,还会造成华丽有余、繁复琐碎的形态。
荆浩关于“真元气象”的论述,显然与先秦道家(包括两汉)哲学的“气”论思想一脉相承,是对哲学“气”论的一种审美阐释,也是立足绘画实践的一种理论总结。在荆浩之后,山水画论有关“气象”的论述就更见丰富和深化了。比如,宋代郭熙言:“须远而观之,方见得一障山川之形势气象。”清代笪重光说:“夫山川气象,以浑为宗。”这里的“远观”“以浑为宗”,皆是对山水画“气象”内涵的进一步说明,同时也表明山水画“气象”的创造,首先需要立意高远,统摄整体,着眼布“势”,从而营构出一个由“气”推荡而成的天地统一之大“象”。另外,这里所谓的“势”,不仅要求画面布局统一,而且还要求笔墨赋形与整体格局打成一片,泯然一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大格局,大“气象”。有关这一点,清代布颜图和李修易就有过很好的阐发。布颜图说:
“制大物必用大器,故学之者当心期于大。必先有一段海阔天空之见,存于有迹之内,而求于无迹之先。无迹者鸿蒙也,有迹者大地也。”(《画学心法问答》)
清代李修易说:
“画家亦莫妙于布势,发端混仑,逐渐破碎,收拾破碎,复还混仑。”(《小蓬莱阁画鉴》)
可以看到,“大”“混仑”,是布颜图、李修易对“气象”整体之“势”的又一种理论说明。宇宙鸿蒙何其繁复、广阔!画家经由笔墨摄取天地景象,应有与之相应的表现方式,这就要求画家心中始终酝酿有“混仑”天地的阔大胸襟,并且画家观照自然的目光也应是流盼回环、远近取予的。于此,笔墨成形之初,才能蕴含于“无迹”之中,才能体察“发端混仑”的本质特征,从而在绘画创造中实现浑然统一的整体感。这即是布颜图说的“必先有一段海阔天空之见,存于有迹之内,而求于无迹之先”,也是李修易说的“发端混仑,逐渐破碎,收拾破碎,复还混仑”。概而言之,画家主体若能用一种“无迹”的视野统摄天地万有,便能在笔墨表现中,运化一片浑沌之“气”,山水画的“气象”也会有一种“海阔天空”的势态。
四、山水画“气象”个案考析
山水画浑然整体格局的体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这里我们主要以范宽、王蒙、沈周、朱耷四位山水画家的作品为例,探讨“气象”在绘画中的具体特征。
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图1)描绘了陕西关中一带的巍峨山岗,营构了一种雄浑高远的“气象”。由图可知,范宽这幅山水作品,其肃穆雄浑的“气象”是通过全景式的构图以及“高远”的丘壑势态显现出来的。画面中主峰拔地而起,占据中景和远景的位置,山头、山脚皆可一览入目,山腰处用留白作烟霭,凸显了山的高远之势,这使观者面对画中高耸、厚峻的山体时,内心自然充盈着与山体雄浑之势相对峙的崇高感——这正是山水“气象”所引发的。此外,范宽采用的雨点皴和积墨法,对“气象”的生成也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作品山壁由于雨点皴和积墨画法造成的土石交杂的质感,使山体显得十分沉厚,营造出了一种“如行山阴道中”的画面效果,就如论评曰:“范宽之笔,远望不离座外。”宋代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亦评范宽山水作品曰:“如面前真列,峰峦浑厚,气壮雄逸,笔力老健。”范宽《溪山行旅图》雄浑高远、压顶的势态,让人身临北方山水的雄绝“气象”之中。

图1 宋 范宽《溪山行旅图》,绢本设色,206.3cmX103.3cm,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王蒙作为元季四家之一,他的山水面貌以“繁”“密”著称,体现了一种苍郁深秀的浑整“气象”。如《青卞隐居图》(图2)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从图中可以看到,“其创解索皴法,兼用披麻、牛毛、云头等一类皴法上,用蜷曲如蚯蚓的皴笔,古拙而灵活,细秀而雅逸;密点主要表现在取鉴巨然焦墨大点方法,用散笔、开花笔、渴笔打点,常和淡笔皴山结合,山头、树丛或散或聚以干、湿、浓、淡、大、小、光、毛不同类型的丛点错落打点。其渴笔焦墨、破笔散毫等多种苔点的技法为前所少有”。这种“繁”“密”的创作手法使得整幅作品山峦迭起,布置繁复,皴法多变,笔法细腻,墨色更是混融一片,继而我们看到,画中山石、峰峦皆用淡墨结构筋骨,再叠以湿笔皴擦,点染布形之间,山峦层层推移,蜿蜒深邃,浑然天成。另外,淡墨之中间以焦墨渴点,因此作品蕴含了丰富的笔墨层次。上文提到,山水画的“气象”构成不宜有繁复、破碎的细节刻画,因为这样会肢离“气象”的整体格局,从而使画面与浑沦“气象”渐行渐远。但王蒙的《青卞隐居图》则不然,它能在繁密的手法中进一步“收拾破碎,复还混仑”,实现画面的包罗与统一。所以,在这幅《青卞隐居图》中,形模尽管纷露,却依然能与墨气相融,浑然一气。可以说,《青卞隐居图》是一幅于绵密笔意中凸显浑然整一的山水作品,它代表了一种以“繁”“密”为特征的山水“气象”。

图2 元 王蒙《青卞隐居图》,纸本水墨,141cmX42.2cm,现藏上海博物馆
明代沈周《庐山高图》(图3),更是山水“气象”的典范之作,作品体现了雄伟山势与清雅笔意的交融统一。这幅图创作于成化三年(1467),是沈周为庆贺其师陈宽(字孟贤,号醒斋)七十岁生日精心制作的祝寿图,落款内容曰:“成化丁亥端阳日门生长洲沈周诗画敬为醒庵有道尊先生寿。”沈周借用万古长青的庐山比喻老师的品格,表达了他对老师的敬仰与爱戴之情。画史上表现庐山题材的作品有许多,比如晋代顾恺之曾画过《庐山图》《雪霏望五老峰图》,五代荆浩画有《匡庐图》,明代唐伯虎画有《庐山图》,清代石涛也曾画有《庐山游览图》等,但是像沈周这样用大尺幅创作来表现庐山山水风光的作品却是绝无仅有的。它的构图以“高远”为主,山脉走势呈“S”形叠带而上,细处布置有山涧、屋木、石栈,景物随山势蜿蜒错落其中,隐隐透发着一股静谧隽雅之意。技法上,这幅图的山石皴法多为披麻皴、解索皴,中间间隔浓墨点苔,用墨浓、淡、干、湿得当,丰实华兹,总之,这张画糅合了王蒙等人的笔法,但用笔更为坚实,山形塑造更加浑厚。沈周的山水笔法有“细笔”和“粗笔”两种形态,这幅《庐山高图》结合了这两种笔法形态,所以作品既有细密清健的韵致,又有放逸浑朴的气息。应当说,相较王蒙《青卞隐居图》苍茫浑然的山水“气象”,沈周《庐山高图》的山水“气象”可谓亦柔亦刚,是刚柔交织的整合。

图3 明 沈周《庐山高图》,纸本水墨,193.8X98.1cm,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与上述三种山水“气象”不同,清代朱耷的山水“气象”省略了精细的物象描摹,弱化了山川的体势布置,笔墨意蕴更见苍润、朴拙,因此,他的山水画具有一种邈抹天成的浑整“气象”。这幅《秋山图》(图4)便是极好的例证。画面中山形坡度低缓,不复渊深,也不以雄浑见著。笔墨技法主要是以淡墨勾皴和浓墨加点。相较前人传统的“三段式”丘壑布置,这幅作品着意笔墨,弱化丘壑块垒,整体气息浑然一片。可以说,这幅作品尽管没有雄奇的峰峦轮廓,但作品依然具有涵纳天地宇宙的浑整境象,充塞着“气”的流动和贯通。这表明,山水画“气象”的表现,除了可以凭借布置山川构图和势态来实现之外,也可以像朱耷一样,通过淡化空间透视,弱化山势布置,以浑朴的笔墨来营造一种氤氲蒙养的山水景象。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作品中“树”的描绘对整体“气象”的构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树木与周围坡石比例差异不大,有的近景树木在视觉体量上甚至大于山形,远远望去,几株林木倚立横斜,错落有致地融入山峦与坡地,它们伸展的枝干仿佛在画面上切割出了许多空间,使画面由疏密间隙生成一种节奏韵律,从而将山水树木等物象统一起来。山形树影正是在这种节奏中交织一体,形成了墨气淋漓、自然天成的山水“气象”。

图4 清 朱耷《秋山图》,纸本水墨,182.8X49.3cm,现藏上海博物馆
我们当然还可以举出更多画作来验证“气象”的感性显现,但以上不同时代的四件作品可以作为典型例证,表明山水画整体“气象”不同的表现方式和不同的审美特征。
综上所述,山水画整体“气象”的营构,具有某种内在的审美规定。一,在位置经营层面,高远又深邃的山峦势态往往构成了作品“气象”的主要样式。这些山水作品的构图大多规模宏远,物象布构占据画面的视觉中心,或山势陡峭,从而带给观者“壮美”的审美体验(如《溪山行旅图》《青卞隐居图》《庐山高图》)。二,在用笔造型方面,画家善于运用一定的技法(如皴法)将笔意与山水物象质地有机结合,匹配无间。三,尤为注重用墨,由此营造出浑然氤氲的审美氛围,对此清代石涛在《画语录》中就有很好的论述,他说:“墨非蒙养而不灵。”又说:“笔与墨会,是为掞缊。掞缊不分,是为混沌。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
画家的山水创作当然不是根据某种明确理论观念进行的,但绘画实践显然又不是一种盲目自发的活动。中国山水画所展示出来的审美“气象”,与哲学观念有不期而然的契合关系。“气象”的理论阐释,尤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的相关论述,它们作为一种观念先构,对后世文化和艺术的审美取向必然起到一种预示和导航作用。而后世山水画“气象”形态所包含的笼被天地的精神意向,则是这种审美取向历史的感性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