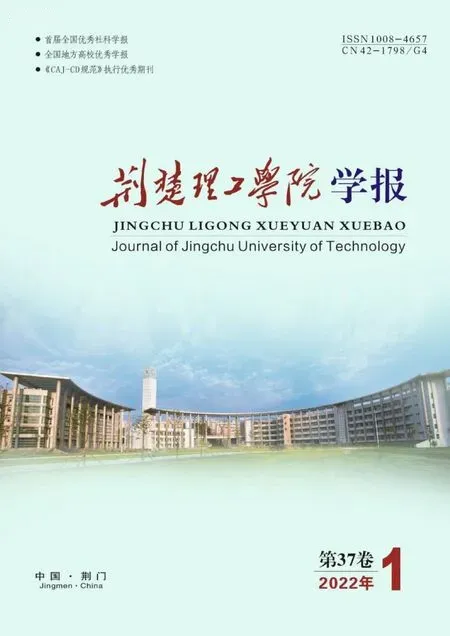论钱锺书“打通”治学方法的体现、目的及其学术启示
——以《宋诗选注》为中心的考察
李昭锟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宋诗选注》是钱锺书先生在建国后所撰写的第一部有关宋代诗歌研究的专著,它为我们较好地展现了宋代诗歌的多种艺术风格特征及其发展演变的进程。不同于钱先生在《谈艺录》《管锥编》等论著中一贯采用的书札体、笔记体的写作方式,以诗注体式为特征的《宋诗选注》,在他的著作集中显得颇为另类。不过相同的是,在这几部书中,钱先生始终使用着一种一脉相承的治学方法——“打通”法,它也无疑是在《宋诗选注》中被运用得最为成功的方法之一。实际上,钱锺书先生在青年时代所作的《徐燕谋诗序》一文中的几句话,体现并指引着他形成了自己一生善于“打通”的治学品格——“故必深造熟思,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在熟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人文社科典籍的基础上,自然容易实现“打通”,这便使钱先生形成了他一生最为重要的学术品格与学问境界。那么钱先生是如何在《宋诗选注》中运用“打通”法的,运用这种治学方法的目的又是什么,它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治学启示呢?
一、“打通”法在《宋诗选注》中的体现
我国传统的诗歌笺注,以字词名物考释、章句串讲为主要形式,钱锺书不以前人为法,大胆创新,寓具有宏阔视野的文学批评于广博的文献引证与科学考据之中,从而实现了时间、空间、文体、学科、艺术门类五个方面的“打通”。
其一,打通时间,纵览古今。传统诗歌的笺释以多引前代的文献为据,支持己见,而钱锺书往往不然,他在注宋诗的时候,曾使用了《诗经》《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多种古籍,但他也不仅仅以宋以前的文献为据,本着诗心文心共通的原则,以艺术的角度不分时代地选取可以佐证的文献资料来作注。比如,钱先生在注北宋诗人文同《织妇怨》“大字雕印文,浓和油墨污”一句中的“大字”时,引用了稍晚于文同的北宋诗人郭祥正《青山集》中的诗,并引远晚于文同的宋末元初诗人方岳的诗来同证。另如他在注王安石《初夏即事》中的“弯碕”一词时,也引用晚于王安石的宋代诗人袁易的《念奴娇》词作进行参证。
其二,打通空间,博采中西。中西会通式的教育模式与钱锺书好学深思的习惯培育了他学贯中西的学术才华。研读《宋诗选注》,我们会发现,钱锺书不仅对中国的传统学术熟稔于心,并且他对西学的诸种典籍的引用也是信手拈来。譬如,在论及诗史关系时,钱锺书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 《诗学》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在提及苏轼诗文评的写作风格时,钱锺书引用了恩格斯的 《反杜林论》、歌德《我们贡献些什么》、孟德斯鸠《法意》、黑格尔《哲学系统》等外国典籍来进行理论参证。在批评宋诗堆砌材料的弊病时,钱锺书借用欧洲古典主义发展到极端地步的实例来参照,并引用德·桑克谛斯的《意大利文学史》里的叙述来证明观点。为了说明明代诗人抄袭唐诗的行为在世界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一事,钱锺书特引唯达 《诗学》与费莱罗所编《马利诺及其同派诗人选集》等外国文献来证明文艺复兴时期的抄袭行为曾大行其道。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三,打通文体,探究诗心文心。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曾言:“吾辈穷尽气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参禅贵活,为学知止,要能舍筏登岸,毋如抱梁溺水也。”钱氏很早便认识到,所谓文体之分,只是一种文学的艺术形式上的差别,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有共通的诗心文心,而他的研究目的,正是在于寻找中西古今所共有的那种诗心文心。在《宋诗选注》中,钱氏不仅常以诗解诗,还以其他文体来参解诗歌。如在解王令《勿愿寿》中的“龌龊”一词时,钱氏在明代小说《西游记》中找到了答案:“从‘龌龊’两字来看,这首诗也是‘贾客乐’的用意,而从《西游记》第四十四回所谓不是‘长寿’而是‘长受罪’这个新角度去写。”以小说来解诗,颇为有趣。又如在释曾几 《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苏喜而有作》中涉及到的“秋夜听雨打梧桐”的意象时,钱氏引元人白仁甫的杂剧《梧桐雨》第四折后半折来证明这个意象常表达一种 “教人失眠添闷”的悲凉感情,这里以杂剧释诗,更是别出心裁。
其四,打通学科,多元解诗。钱先生是一名文学研究者,但他同时精通中国传统经学、史学与子学等学术,也对自西方兴起的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十分熟悉。钱氏在《宋诗选注》中对各学科知识的引用,简直是如数家珍。在注梅尧臣的《田家语》时,钱锺书解释了宋代的兵制,这是借用史学中制度史的知识。在注郑獬的《滞客》时,钱锺书解释了自六朝诗以来常描写的开船打鼓的风俗,这是借用民俗学的知识。在注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时,钱锺书引用了佛经里的几个故事来阐释黄庭坚与佛学的关系,这是借用佛学的知识。在注陆游《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诗时,钱锺书引用蔡美彪先生对诗中“天山”所在位置的意见,并引用《金史·地理志》,述金朝西北边疆界限,又寻绎诗意所指,最终赞同蔡先生的意见,这是借用历史地理学的知识。钱锺书先生的跨学科解诗,为后学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其五,打通艺术门类,寻求艺之真谛。钱锺书先生曾言:“诗者,艺之取资于文字者也。 ”在钱锺书看来,诗在更深的意义上,是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他从不讳言各门类艺术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但他显然更注重它们间的共通的艺术属性,对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他不仅多有涉猎,还经常探究它们与诗的艺术关联,寻求艺之真谛。钱氏曾在《谈艺录》中专设“诗乐离合,文体递变”一章,探究诗歌与音乐间的离合关系,他又作《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研究诗歌与绘画的关系。在《宋诗选注》中,钱锺书亦通过打通艺术门类,对宋诗做出了许多精妙的批评。在注王禹偁的《寒食》诗时,对北宋汴梁城中过寒食节的热闹场景的考察,钱氏除了用其他宋代诗人的诗作参证之外,还通过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人和动物的数量来引证,表现寒食节时当年北宋汴梁的盛况。另外,在论述文同的诗常与绘画联结一事时,钱氏提出,从文同开始,诗人才有意识地具体地把面前之景比作某种画法或某大画家的名作,钱氏继续指出,文同此种做法,“跟当时画家向杜甫、王维等人的诗句里去找绘画题材和布局的试探,都表示诗和画这两门艺术在北宋前期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了。”可见其对中国诗史与中国美术史的了解,不过钱氏又补充道:“当然晚唐的画家已偶有这种试探,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就记段赞善把郑谷、李益的诗意‘图写之’。 ”更见其对诗画关系的研究之精深。再如论述杨万里的“活法”理论时,对于杨万里在诗里表现出努力感知自然界事物的行为,钱氏引达·芬奇《画论》中的相关论述,用反证法褒扬了杨万里的行为。又如注罗与之的《商歌》,钱氏在为这首诗进行“破题”时,特意从音律角度入手,以音乐来解诗,这也是钱锺书进行跨学科解诗的一大体现。
二、《宋诗选注》运用“打通”法的目的
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将“打通”法运用得很成功。不过书是写出来了,可并没有使他完全满意,因为在他心中,《宋诗选注》只能算是一个“模糊的铜镜”,“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也许这个朦胧的状态本身正是某种处境的清楚不过的表现。”诚然,由于《宋诗选注》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那个特殊的年代,钱锺书又是一个对实际政治绝不感兴趣的人,当他接到郑振铎先生的著书“指示”后,为了尽量不被与自己的学术观念相异的某些学者批判,又要保证自己一如既往的学术理路得以贯彻实施,所以只有小心翼翼地谋求外界和自身的一种平衡,在“夹缝”中著书。钱锺书确实在结撰这部书时费了相当多的心思,从选诗、作序再到作注、为诗人写小传,字句斟酌,谋篇布局,煞费苦心,书中点滴的背后都是钱氏心细如发的考量,正如他自己所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 ”这里所谓的“别出心裁”,在夏中义先生看来,其实是钱锺书在当时那种文化语境下,以特殊的述学策略在《宋诗选注》中埋下的许多隐含话语,这些隐含话语在本质上构成了一种“暗思想。”
20世纪50年代,文艺反映论在我国文学研究界占据理论话语权,文艺反映论所持的观点与钱锺书在早年形成的文艺观点相牴牾。钱氏于1933年发表于《大公报》上的一篇书评《旁观者》中,就曾明确表示他对西班牙哲学家加赛德在《现代论衡》中提出的“一个时代中最根本的是它的心理状态(Ideology),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不过是这种心理状态的表现”之论持赞成态度,然而这种观点与文艺反映论却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当钱锺书在二十余年后撰写《宋诗选注》时,他的认知与性格也不会允许他向当红理论缴械投降,投怀送抱,“于是也就不难解当钱撰《宋诗选注》时(‘独尊反映论’的大氛围逼他只能把宋诗写成宋史的反映,而不宜去深化宋诗所以演化为宋诗的艺术史谱系),凭其一腔不世之才气、傲气和骨气,钱又怎可咽得下这口气?”
表面做宋诗研究,可实际上做的是宋史研究,这样的研究是钱锺书所不能接受的。钱锺书一生都以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身份自居,但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他既不能公开抗议,又不能以沉默来抵制指示,他唯有在书中有限度地运用自己的诗学研究观念,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以文学批评的方式进行宋诗研究的方法,提高艺术性探究在宋诗研究中的分量,那么凭钱氏淹博的学识,以“打通”的方法来尽可能地对宋诗的艺术成就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辨析与展示,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但“打通”不代表漫无目的,并不说明钱锺书的努力只是为了把一堆过去的知识堆砌在一起,事实上,钱锺书的“打通”一直是为了一个中心服务,这个中心即是文学研究。无论是对时间与空间的打通,还是对文体、学科和艺术门类的打通,钱锺书始终坚持这个所打通的事物,都要为文学与诗学研究服务,他所称引的古今中西的人与作品、文化现象,都无一例外对他要笺释与批评的对象具有一种十分明晰的指向性。比如,在为严羽作诗人小传时,钱锺书讲严羽的《沧浪诗话》在明清两代受到极大推崇,“连讲戏曲和八股文的人,也宣扬或应用他书里的理论”,并注他的观点是来自于王骥德《曲律》与董其昌《容台文集》、王铎《拟山园初集》等材料。 这看似漫不经心的随口一提,其实并不简单,钱锺书在这里用打通文体与艺术门类的方法,表面在说,严羽的《沧浪诗话》所提出并阐释的文学批评观点得到了研究戏曲和八股文的后人的认可,但这里隐含的意思其实是,《沧浪诗话》在某种意义上所提出并阐释的某些文学批评观点具有跨越文体与艺术门类界限的普遍性特征。之后,钱氏又讲,《沧浪诗话》里的主张与十九世纪欧洲盛行的一派诗论接近,又参看德国《梵文诗学史》研究一书,发现其竟与古印度的一派诗论暗合,钱氏同时指出:“印度的文艺理论没有介绍到中国来过,‘禅’不过沾了印度哲学一点儿边,所以这个巧合很耐寻味。”钱锺书在这里想要证明的,其实是他在1942年为《谈艺录》作序时提出的一个影响至今的论断——“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里对欧洲及印度文艺理论的引证,其实是他对他那一观点的演绎证明。由此我们知道,钱氏为打通所做的征引,所围绕的都是一个包含着文学现象、诗的艺术属性、诗之流变、文学批评等重要问题在内的所谓文学研究中心,其目的就是阐发文学的艺术价值与生命力,使多学科知识供文学研究驱使,为文学研究服务,以便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隐秘地、曲折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反复打通时间、空间、文体、学科、艺术门类等方面的现实原因与根本目的。
除此之外,钱锺书还有另一个目的,即为了反对建国以前长期存在的一种重考据、轻批评的“重史轻文”的文学研究模式,他在《宋诗选注》中通过诗论与诗歌笺注的形式将其表达出来,并有意忽略诗歌作者、本事、时地等元素。钱氏的这个目的,我们可以视作学术目的,他的目的是反对一种学术研究范式,从而捍卫一种学术研究范式。
胡晓明先生曾于1998年发表《陈寅恪与钱锺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一文,引发了学界一定范围内的讨论。该文指出,钱锺书与陈寅恪在诗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隐含的学术研究范式之争,钱锺书有意无意在各种场合反对陈寅恪的“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研究范式,导致形成了两大诗学研究范式的对立。胡先生所言不错,钱锺书反对陈寅恪“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研究范式,其意是捍卫他的那种打通时空、跨越学科壁垒的、以诗解诗的研究范式。钱锺书一直都反对将诗歌作为信史,忽略其艺术特性的研究观念与行为,他在《宋诗选注·序》中明确表示:“‘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钱氏从自己所选的诗中一连列举了几首,归纳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三种区别,并总结道:“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像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钱锺书如此费心地辨别诗史之区别,并不是他抛弃了“打通”的研究方法,而是他要坚持文学本位,坚守立场,做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所以他一定会对一些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泯灭诗史界限的做法进行批评。其实钱锺书在青年时代便强调:“政治、社会、文学、哲学至多不过是平行着的各方面,共同表现出一种心理状态。”钱氏强调这些因素之间相互映射的关系其实也是为他的打通四部、贯通古今的治学方法,以及“为他特别强调和突出文学在整个时代的审美自足性作了理论上的准备。”文学研究始终是钱锺书的学术研究的中心,钱锺书其实也并不仅仅是对陈寅恪的这种研究范式不满,实际上,他一直对风靡于解放前学术界的实证主义表示反感,批评陈寅恪的诗学研究仅仅是一个个案,有点“杀一儆百”的意味在其中,其实钱锺书的学术矛头的真实指向实为曾经风靡全国学界的、作为学术研究方法论的实证主义。
1978年,钱锺书赴意大利米兰参加欧洲汉学家第二十六次大会,在会上,他宣读了他新作的《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一文。钱锺书在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成功运用实现了对实证主义的造反,所谓的实证主义在钱锺书看来就是“繁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在解放前,实证主义的盛行“使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使考据和‘科学方法’几乎成为同义名词”,那时对作者与作品版本资料的考订才算是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沦为了“词章之学”,“说不上‘研究’的。”一番言语中透露着钱氏对解放前文学研究中充斥着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不满。不过钱锺书也是以辩证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实证主义的,“反对实证主义并非否定事实和证据,反对 ‘考据癖’并非否定考据”,但它并不能代表核心的与全部的文学研究:“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钱锺书的这种研究观念,在《宋诗选注》中常有体现。我们可以看到,钱锺书为诗人所作的注,皆不与传统笺注相同,他的注是一种以“打通”为方法,糅合了文学批评与史料考据的新注释法。所以,阐释这种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观念,捍卫这种以阐发文学与诗学的艺术属性与价值为研究目的的学术研究范式,是钱锺书在《宋诗选注》运用“打通”法的学术目的。
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一如既往地运用“打通”的研究方法,可能有自身习惯的原因,但联系当时的语境与政治环境,钱氏对“打通”的坚持更说明了他对艺之真谛的坚定追索,努力坚守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观念,捍卫自身所坚守的学术研究范式,也表现了他为创新古典诗歌选注的选诗标准、注释内容与形式所作的艰辛努力,更彰显了他作为一代学者的圆融智慧与不可亵渎的文化尊严,令后学不禁肃然起敬。
三、《宋诗选注》运用“打通”法的学术启示
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对“打通”法的精彩运用使他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同时也给予了我们无尽的学术启示。
第一,静心于学术,博览群书,无愧苍生,无愧自己。钱锺书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勤奋好学,甘于寂寞,默默耕耘,潜心学术,成就斐然。钱锺书在他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没有放过一分一毫的读书机会,在清华大学,他横扫图书馆藏书,在牛津大学,他为了读书甚至不想读博士。钱锺书在撰写《谈艺录》时,便已在书中引用了一千九百七十余种书籍,涉及诗人八百多人,撰写《管锥编》时,陆续在书中引用了四千余位作者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真可谓是他一生勤于读书、精于思考的最佳证明。在撰写《宋诗选注》时,钱锺书以一人之力,两年之功,对宋代诗人诗歌作品进行了穷尽式了解,并以独到的眼光、打通古今中西的方法,为我们奉上了这一道宋代诗歌研究的大餐。如果钱锺书没有一颗孜孜不倦、好学深思的心,他怎么能做到对时间、空间、文体、学科、艺术门类的多方面打通呢?钱锺书一直怀有一种坚定的人生信念:“世事澒洞,人生艰窘,拂意失志,当息躁忍事,毋矜气好胜;日久论定,是非自分。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人生信念,才使他能够在学术的海洋里一往无前地徜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钱锺书的一生是精研学问的一生,是光耀千古的一生,他在《宋诗选注》中所运用的“打通”研究,反映出他坚韧不拔的毅力与贯通古今中西的绝世才华,他无愧于苍生,无愧于自己,而我们,则有愧于他,笔者愿奉上蒋寅先生的一句读“钱”心得,予以共勉——“我唯愿同辈人多读书,包括多读钱锺书。 ”
第二,立体化“打通”,突破现代人文学科之藩篱。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对时间、空间、文体、学科、艺术门类的打通,给我们以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思路。自晚清以降,中国现代学术与教育制度逐步建立形成,受西方学科制度的影响,传统学术逐步分化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史、哲等各学科。随着我国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现代学术逐渐朝向精细的趋势发展,学科与学科间的壁垒日益厚重,“隔行如隔山”的现象日趋严重,做文学研究的人不懂历史,做哲学研究的人不懂社会学的情况屡见不鲜。各种“专家”遍地皆是,可真正意义上的“通人”却无处可寻。福柯早在《知识考古学》中指出,当今世界的知识已被分成了无数个“层次”,“每一个层次都蕴含着自己特有的分割:人们越是接近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宋诗选注》,投向钱锺书时,我们会发现,钱锺书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通才,他立足于文学研究的立场,对史学、哲学、心理学、艺术学、美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知识皆烂熟于心,而对多国语言的精通,又使他对中西各国的文学的前世今生了如指掌,他穿梭于各种文献、典籍间,如入无人之境一般,他做精密细微的考据,做文采飞扬的批评,皆如随心所欲般自由,似砍瓜切菜般容易。汪荣祖先生指出:“钱锺书因通读中西经典文学名著,故能检视中西语言、美感、思维等共同之处,推见至隐而知其异趣,从未强作比附,遂能驰骋于源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多元文本之间,作思想上之交流,阐明人文议题的多元性格。 ”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的打通,就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在21世纪的今天,培养具有宏大视野的跨学科式人才既是人文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时代的需要,我国已于2021年3月正式启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这一伟大工程,目的是适应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要求,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建立新的知识结构和话语体系,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思想话语,从而在全球语境中发出我们的声音。自古以来,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便是不分家的,在当下破除西方文化霸权与话语权的关键时刻,我们应时而动,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努力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文学科学术人才,恰恰是对钱锺书所强调的“打通”学术研究理念与广阔深宏的中华学术大气象的全面回归。我们不必要求未来培养出来的新文科人才都具有钱锺书先生的研究水平,事实上那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努力营造这种贯通博雅的学术氛围,培养后学的“打通”的研究意识,汲取钱锺书先生在“打通”方法上所注入的学术营养,为做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的学术成就而不懈努力!
四、结语
钱锺书先生在选注宋诗的过程中运用了 “打通”的治学方法,以超凡的学术才华将时间、空间、文体、学科、艺术门类等领域尽可能地全面打通,从而探究出宋代诗歌艺术中蕴含的诗心文心,最终成就了《宋诗选注》这部彪炳千古的学术大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钱锺书在不触及政治“红线”的前提下,尽可能用自己的述学策略,将自己运用“打通”法后所得到的学术成果,以诗注与文学批评等方式进行展示。时代已变,学风已转,在当今东西方学术交流互鉴的大背景下,如何做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的,并兼具世界意义的学术成果,这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与探讨的话题,而钱锺书的“打通”治学方法,将会是一盏明灯,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前行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