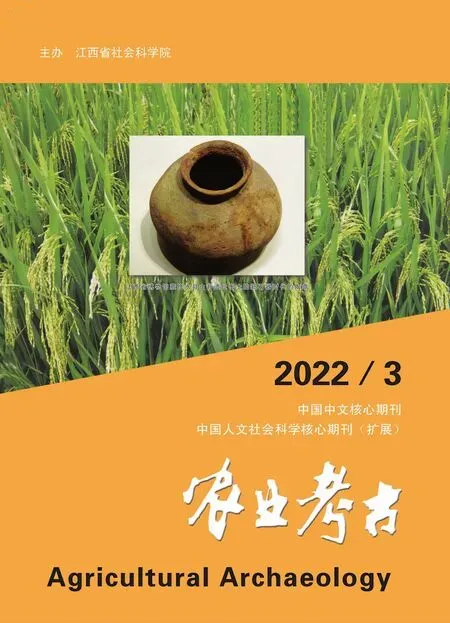民国政权更迭背景下的“庙会存废”之争(1912—1937)*
黄 昆
庙会空间是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为久远的公共空间之一。清末民初鼎革之际,随着王朝祀典被顺势废除,昔日承载神灵偶像之宗教空间因失去国家权力的荫庇而与世俗空间渐呈分离之势。但作为从传统社会延续下来的公共场域,如果不是“他者”话语的强势介入,宗教空间内承继的信仰符号及民众的主体性祭祀行为并不足以引起舆论的关注和社会价值的碰撞。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民国时期的“庙会存废”现象注目不多,仅有少数学者在“迷信”话语的研究过程中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有鉴于此,本文从政权鼎革的视角对1912—1937年的“庙会存废”问题进行探讨,力图呈现庙会存废的空间冲突与话语调适的多重面相及内在逻辑,透视知识精英和国家力量在思想酄魅和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历程中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一、晚清民国时期的政权更迭与“庙会存废”的时代语境
庙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宗庙社郊制度。历史的演进,促使其内涵和外延不断发生嬗变,特征和功能亦被深深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庙会空间经民众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精心浇筑和持续塑造,唐宋以降已衍化为拓展经济和愉悦身心的固定场所,由宗教空间和世俗空间共同构成。由于中央王朝希冀通过对民间神灵的笼络与控制,来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与规训,故以神道设教的方式来宣化愚民和宾服四方。因此,宗教空间在较长历史时期内被赋予浓厚的政治内涵与宗教意蕴,成为民众日常积聚的公共场所和精神圣地。
政权更迭及其合法性塑造是理解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对宗教空间采取不同政治实践的密匙。北洋政权的确立是清廷和平覆没和南京临时政府权力转移的共同结果。在政权合法性方面,北洋政权一方面承嗣了前清政权的领土主权与国际义务,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民主共和制度,因而获得国际社会及国内力量的普遍认同和共同支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北洋政府在政权合法性来源方面颇为正当和契应时势,这与国民党政权所处位置判若鸿沟,二者采取的政策自然大相径庭。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合法性塑造建基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愿景,主张以国民革命的方式推翻北洋政权,因而对王朝时代遗留下来的祠庙给予了较为激进的处理措施。早在北伐时期,国民党党职人员和军队就对各地的僧道寺观庙宇和神像进行大肆毁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内政部颁行了《神祠存废标准》(下文简称《标准》),进而从立法层面明确了诸多民间神灵的非法地位,而这也成为国民政府在此后岁月里长期施行的法律规范。
晚清民国之际的历史巨变为新式知识分子的废庙舆论扫除了制度性障碍。早在前清祀典被废以前,士绅阶层对庙会的批评之音已不绝于耳,他们在儒家崇尚节俭和化民易俗的道德要求下,对庙会活动中的“靡费”和“风化”现象严加斥责,这与此后的禁庙舆论在问题指涉和思想理路上截然不同。清季民初,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渐加深和近代自然科学法则为部分旅外知识分子所接纳,他们在中西巨大差距的现实观感刺激下,将科学主义话语作为检视国人精神信仰的标尺,希望对他们愚昧无知的刻板印象进行彻底改造。陈独秀对神灵崇拜现象进行挞伐,认为“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 都应该予以破坏。如果说陈是引领时代的思想巨匠和新文化运动旗手,此论并不足以说明科学主义话语在知识分子中的普适程度,那么《永泰县志》中“前清祭典所载,凡涉于迷信者,应行废止”和《德兴县志》中“民国破除迷信,崇尚实学,神权之说已不适用,尤无存在之必要”的言论就有一定的代表性了。
随着王朝祀典被顺势废除,国家权力从宗教空间中完全离场,民间神灵因失去权力的庇护而沦为挞伐的对象,但这不意味着北洋政权与新式知识分子之间态度已然趋同。前清祀典被废除以后,北洋政府虽明令对宗教信仰自由给予法律保护,但并未将民间信仰纳入其中。针对前清遗留下来的僧道寺观庙宇和神像,北洋政府仅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给予孔子庙由官奉祀的合法地位,而对大多数民间神灵的自发性祭祀行为并不做出明确规定,体现了北洋政府在新旧话语之间制定政策时的求稳心理和务实态度。纵观北洋政府时期,虽然王朝祀典的废除和国家权力的离场,使宗教空间因失去权力的荫庇而在庙会空间中渐居从属地位,但作为历史上延绵不绝并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活动,即使身处时代的风口浪尖且呈江河日下之势,庙会依然葆有继续存在的合理逻辑和顺应时代诉求的旺盛生命。
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政权鼎革,标志着大规模的废庙运动由舆论宣传转向政治实践。如果说国家权力的离场是触发社会舆论对庙会存废问题讨论的政治前提,那么科学主义话语的传播则是问题被舆论聚焦的思想基础,而民族主义话语的兴起及其与激进政治力量的结合,则是推动大规模废庙运动的动力源泉。民间信仰因其理论建构荒诞不经和循常守故,最终沦为此话语最为频繁的申斥对象之一。南京国民政府自诩为革命政权,主张破除封建偶像崇拜,重塑国民精神意志,通过与传统政治伦理相决裂的方式来重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信仰,实现“治内而御外”卷12《礼俗》,P6a)的政治目的。国民党政权推行的“反迷信”运动产生了强烈的时代回响,“昔之载在祀典之城隍、土地、昭忠祠及诸佛偶像等,亦多受时代之淘汰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迷信”话语开始广泛嵌入社会各阶层的思维意识和语言表达中。《阳原县志》反映了迷信破除的情况,认为“清代知县及民初知事必恭诣其庙致祭,有特别刑事案件无法审讯者,亦恒祷于城隍。但民十(笔者注:民国十年,即1921年)以后,该庙香火已衰。因科学时代,知县事者已不若前之迷信矣”。《呼兰县志》则阐释了迷信传播与国家命运的关系,认为“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足见无古今无中外,凡事不求之事实,但凭诸虚无,小则足以误社会,大则足以亡国家”。
由此可见,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庙会存废”之争产生于特殊的时代语境中。与王朝时代的禁庙言论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废庙舆论是在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作用下而兴起,最终在两次政权鼎革的时代背景下,完成了由舆论宣传向政治实践的转向。“庙会存废”之争是这一时代剧变的必然结果,其演变情形之所以持久而剧烈,乃是与诸多要素产生了紧密的社会联系。概而言之,王朝祀典的废除,让庙会空间失去了可供保障的制度基石,而科学主义话语的引介和传播,则从学理上揭示了神灵信仰的荒诞不经与现实无益。随着神灵崇拜对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阻碍作用日益加剧,大规模的废庙实践终将不可避免。
二、弃旧与趋新:“庙会存废”的空间冲突
近代的废庙实践带有明显的新旧论争的时代痕迹。虽然太平军的废庙实践与传统的宗教信仰冲突无异,清季“庙产兴学”亦将传统时代的“靡费”和“风化”话语夹叙其中,但两次重大废庙实践都与西学东渐密切相关,只是尚未从儒家伦理的叙述模式中完全跳出。随着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被更多的知识精英所接受,他们视科学精神为新国民必备之素养,对宗教空间内的烧纸、祈愿和酬神等迷信行为严加申斥,认为信仰的愚昧是国家落后的祸源。随着民族主义成为主流社会思潮之一,激进政治力量借助这一强势话语,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废庙运动。国民党政权的废庙运动是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与激进政治力量结合的结果。1928年10月,内政部颁布《标准》,对民间的祀神行为进行了法律规范。依据《标准》,地方当局应允许民间对先哲类、宗教类、古神类神祠进行祭祀,但应严禁为不符合《标准》的神灵举办庙会,诸如烧纸、点烛、娱神等事关迷信的行为应厉行取缔。在《标准》的约束下,神灵信仰受到空前的挑战和质疑,“除偶像,破迷信,庙产充公,改设学校,信奉者少”。根据1933年江苏省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的调查报告,当地交易型庙会占一半以上,其他为香火型和娱乐型庙会,民众参与庙会“不过是借着求神拜佛的幌子,而做他们的交易买卖及游艺娱乐的勾当罢了”。在洛阳农村地区,由于人们“对宗教信仰不如往昔之尊重,故庙会活动之性质亦渐渐已由宗教活动转变为经济活动,更进而成为乡民同乐大会”。
对于宗教空间的存废,新旧知识分子之间存在巨大的思想分歧。“迷信”作为一个外来词汇,当被引介国内,除了新式知识分子给予其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内涵建构外,传统知识分子也试图从本土语境去重构这一话语。他们反对将儒教视为“迷信”,认为儒教“皆与迷信相反之说”,“不言迷信者,亦惟孔儒而已”。对于“迷信”与“反迷信”的对立,他们仍依照传统的正祀和淫祀观念去进行区分,认为“唐狄梁公、清汤文正公皆毁淫祠,诚以欲弥乱源,先正祀典。近日长官命令拆毁淫祠,惜事中止”,坚称正祀信仰与迷信无涉,并且“嵇百神于祠祀,足以除迷信”。此外,他们反对以科学主义话语来推行废庙运动,认为科学尚有不可解释的领域,认为:“昔之所谓异,至今日已不足异矣。今日之所谓异,安知至他年不仍以为不足异耶?”提倡人们对“科学”应持进化之态度,所谓“人知迷信之当祛,不知迷信而外,尚有不可祛者存,则非除塑信者之所与知也”,感叹“新者多出于旧,而旧每不如新,善能演进故也。至有时新之太过,则或反不如旧”卷首。他们质疑民族主义话语宣扬的“反迷信”言论,认为信仰之优劣反映的只是国力之优劣,认为:“今日富强之国无逾欧西,而膜拜上帝之教堂行将遍及全球,非迷信而何?安得以五十步笑百步,以国势之强弱定礼教之优劣也哉!”并对政府的废庙运动提出批评,以为神灵信仰“虽有背现代潮流,而安慰愚氓”之效仍不可或,即便在当代,“可以补王法之不足,教育之不速、不诚”的缺陷,喟叹过去“虽迷信深而情挚, 今乃迷信浅而情伪”,对民间信仰在崇德报功、效法圣贤和维系人心等方面的作用颇为赞赏。
废庙运动对民众生活造成巨大波及,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反对。民国时期,虽然国家权力的离场导致宗教空间的神圣性遭受重创,但世俗空间却因经济变化、人口流动和思想解放而与民众生活的联系更为紧密,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首先是商品种类更加丰富,“乡人农圃之用具,婚嫁之妆奁,以及居家日用所需,率皆取于庙会”。其次是文娱活动更加多彩,既有戏剧、游艺、杂耍等传统节目,又有骑术表演、电影放映、自行车赛等新式娱乐活动,传统与现代娱乐方式交相辉映。最后是商业景观更加多元,形成了诸多错落有致而又具有现代气息的商品交易区。基于此境,废庙运动与普通民众的民生诉求形成了内在紧张,“一旦悬为例禁,则强者流为盗贼,弱者转于沟壑矣”。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大规模的废庙实践随着北伐战争而席卷全国,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让地方当局身陷困境。首先是疾风骤雨式的废庙运动对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较大波及卷13《风,大批祠庙管理者也因之失去了维持生活的依靠,许多工厂和商店被迫停产歇业,社会上陡增大量失业人口。其次是废庙运动成为权势者伺机掠夺他人或集体财物的借口,在“破除迷信美名之下”,“侵占庙产等事时有所闻”,“自谓破除迷信,即欲攘据产业”。最后是地方政府以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为废庙运动的宣传话语,当国家愿景与民众期待产生落差,“反迷信”不可避免被污名化,而地方当局为规避矛盾和转移视线,甚至“还魂”王朝时代官民共祀的互动模式,这种做法显然已经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美好愿景背道而驰。
庙会作为从传统社会延续下来,为社会各阶层不分畛域而共同参与的公共性活动,在民国时期依然拥有旺盛生命和继续存在的社会价值。“庙会存废”之所以在宗教空间与世俗空间酿成激烈的思想和民生冲突,乃是因为新式知识精英的废庙舆论和激进政治力量推行的废庙运动,是在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为内核的“反迷信”话语主导下而产生的,与传统语境和社会现实存在明显脱节。换言之,庙会集宗教、经济和娱乐活动为一体,其面临的毁灭性危机并非源于社会的发展而对庙会活动出现了替代,而是伴随着政权鼎革,由国家力量依据自身政治诉求而主动选择和实践的结果。从某种程度而言,“庙会存废”之争是中国传统社会被现代观念撕裂的一个缩影。在这个断裂的镜像里,有新式知识分子的理性和激情、政治力量的雄心和蓝图、传统知识分子的彷徨和坚守以及下层群众的失落和挣扎,他们共同在庙会空间中演绎碰撞冲突的多维画面。
三、断裂与延续:“庙会存废”的话语调适
宗教空间最初的功能是祭祀神灵和慰藉精神,在国家力量渗入以后,便具备了宣扬教化的职能。王朝时代的民间信仰具有从淫祀向正祀转换的可能,洪武礼制含糊规定:“天下神祠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反映了正祀与淫祀之间的转换取决于统治者的实际考量。清季民初,在科学主义话语的申斥下,宗教空间的神圣性招致新式知识分子的质疑和挞伐,在此场域向愚民继续宣扬神灵功德已颇具讽刺意味。民国时期,随着儒家思想失去了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地位,宗教空间“宣化愚民”的价值被“陶铸民魂”式的思想启蒙所替代。北洋政府时期,宗教空间只是失去了国家权力的庇护而未受到官方层面的毁坏,对于庙会空间存在的各种冲突,地方当局最严厉的做法也仅是以暂不开庙来因应时势。国家权力的离场让庙会空间成为思想宣传的自由场域,并充当中西文化交汇和新旧思潮交锋的重要舆论阵地。与传统时代官方长期主导宗教空间的道德宣教不同,这一时期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为趋新知识精英所主导,他们借助社会舆论来宣扬各种社会思潮。北洋政府在传统与现代的价值碰撞中,一方面对传统价值体系下的神灵信仰有所保留,尤其对孔子采取极高规格的祭祀礼仪,另一方面又对竞相迸发的各种社会思潮给予自由宣传的舆论空间。换言之,北洋政府在传统与现代的思想洪流中,并未主动去建构一套承前启后的兼容性价值话语,而是给予社会思潮相互争鸣和自由传播的舆论空间。从政权合法性塑造及所处的时代语境出发,与其说北洋政府在国人思想领域的建构上缺少主动作为,毋宁说其在传统价值观解构之后更多扮演新旧价值冲突协调者的角色,这种现状既是主动的政治选择,亦是受时代局限所使然。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政权扮演新旧价值冲突协调者的角色已不复存在,在思想领域取而代之的行为路径是去旧迎新,以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为愿景。这既是国民政府塑造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重要考量,亦是中国社会思潮演进和国族构建过程的必然结果。随着国民党政权执政根基渐趋稳固,以“迷信”话语对传统文化进行申斥的负面效应逐渐凸显,尤其是思想混乱和信仰失序造成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如何在新旧矛盾冲突中做好信仰的衔接,并体现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愿景诉求,无疑成为国民党政权亟须需解决的问题。《标准》正是在此背景下被制定出台,以法令的形式对民间信仰中的先哲类神祠给予保护,一改过去尽皆砸毁的激进做法,以志景仰之精义。依据规定,先哲类神祠包括:“对于民族发展确有功勋者;对于学术有所发明,利溥人群者;对于国家社会人民有捍卫御侮,兴利除弊之事迹者;忠烈孝义,足为人类矜式者。”
庙会作为从传统社会延续下来并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活动,虽然宗教空间随着国家权力的离场而失去了往日的神圣与庄严,但北洋政权的合法性塑造及世俗空间的新气象,让新式知识精英的“迷信”话语终难获得地方当局在实践层面的认可与支持。面对新式知识分子的废庙舆论,作为新旧之间的话语协调者,北洋政府更多是本着实用主义态度来决定是否取缔庙会。与北洋政府不同,南京国民政府的废庙运动是由“迷信”话语所主导,因而废庙运动最初是理念化的,而非策略性的。如果说对传统话语的选择性体认和重构是调适宗教空间价值冲突的巧妙路径,那么因迷信话语所引发的世俗矛盾,则需要在理念和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由于庙会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即使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废庙实践之后,人们在开庙之期仍像往年一样集结于庙址周围。国民党完成执政党的角色转变后,因废庙运动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无疑需要重新进行检视。为解决因废除庙会而造成的民生难题,地方政府也逐渐允许重开庙会,但对涉及迷信的相关活动仍严令禁止,并将庙会一律由农历改为公历期间举办。由于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美好愿景嵌入政府的施政蓝图中,在坚守“迷信”话语的前提下,“主张利用庙会,提倡农村游艺。如排演新戏、放演电影,以及乡土的音乐舞蹈,都是农村应有的正当娱乐。渐次把这种迷信的庙会,改变作游艺会”。弛禁庙会后,又因“迷信”活动死灰复燃,开征“迷信捐”逐渐成为地方当局普遍之举,如“香烛冥银及僧道醮筵,按其费用捐百分之二十”,由政府给纳捐者颁发营业执照。国民党政权试图以寓禁于征的方式来破除迷信,实际则是以掠夺人民财富的形式将迷信活动合法化,不仅遭致社会普遍反对,而且折射了在构建现在民族国家过程中的政治蜕变和现实困境。
民国时期的庙会呈现新旧并存的时代特征,但从宗教空间的场景运用来看,北洋时期处于“宣化”和“铸魂”的过渡时代,社会上各种思潮相互争鸣,政府扮演新旧思潮协调者的角色,宗教空间内仍沿用王朝时代的祭祀仪式,陶铸民魂的启蒙诉求主要由新式知识分子提出。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宗教空间内的祭祀行为仅供瞻仰、追思之义,新旧思潮的争鸣已为党化的国家主义话语所统合。国民党政权通过对宗教空间的利用,将党化的国家主义话语向民众进行规训,以实现陶铸民魂和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随着日本侵华事态的扩大,这种民族主义话语在宗教空间内的呈现更为明显。民国时期的废庙实践与王朝时代的禁庙行为具有根本不同,它是在现代话语支配下,由“废庙舆论”向“废庙实践”递变的结果,表现出弃旧与趋新之间叙事断裂的一面。为延续历史和因应现实,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为弥合“庙会存废”之争所作的话语调适,从某种意义而言,亦是在现代话语体系下对传统的延续。
四、余论
庙会作为中国历史上延绵不绝并葆有旺盛生命的社会现象,在政权鼎革的时代语境中已显然无法按照既定路径延续发展。“庙会存废”之争是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思想断裂和延续的一个缩影。庙会现象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有其自身的历史传承、发展规律和路径依赖,而大规模的废庙运动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与激进政治力量结合作用的结果,反映了传统社会断裂的一面。庙会植根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有推动自身演变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通过外力的强制作用去开展废庙运动并未根除“迷信”活动的土壤,宣传的民族主义话语及其传递的价值符号因与民众日常生活脱节也阻力重重。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和新旧思潮激荡的时代背景下,“庙会存废”之争,实际是社会转型期如何处理自身文化延续性的问题。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大规模废庙运动造成了庙会文化的断裂,此后的庙会改良可视作对庙会文化延续性的复归。遗憾的是,这一举措不是建基于对前一时期否定之上的超越,而是被迫做出的调适,尤其是“迷信捐”的征收,反映了国民党政权在弃旧与趋新之间的进退失据与治理困境。
①相关的代表性成果有:徐志伟的《一种“他者话”的话语建构与制度实践:对清季至民国反“迷信”运动的再认识》,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7期;沙青青的《信仰与权争: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之研究》,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