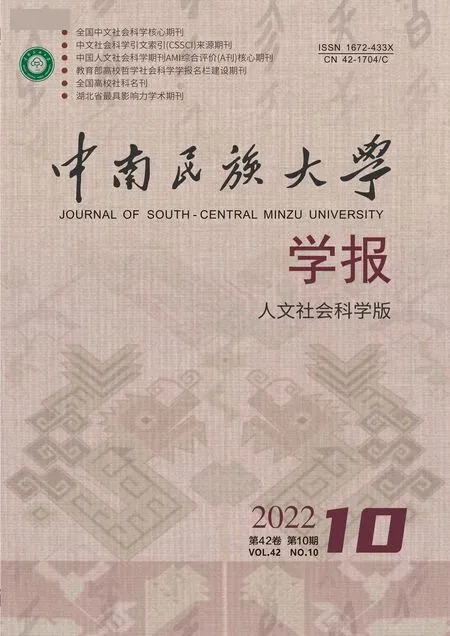李煜词的章法新变
吴晨骅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任何文体得以成立,必有其形式上的特点,章法即是其中之一。《文心雕龙·章句》论谋篇布局时就讲:“裁文匠笔,篇有大小;离章合句,调有缓急……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1]570苏俄文学批评家鲍·托马舍夫斯基也认为:“类别的特征,即组织作品的结构的方法,是主要的手法,也就是说,创作艺术整体所必需的其他一切手法都从属于它。”[2]词即以其上不类诗、下不类曲而成立。词学家唐圭璋先生说:“文章各有体制,而一体又各有一体之作法,不独散文与韵文有异,即韵文中之诗歌词曲,亦各有特殊作风,了不相涉。苟不深明一体中之规矩准绳,气息韵致,而率意为之,鲜有能合辙者。”[3]838唐先生在《论词之作法》中,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讲析词的章法,足见章法之重要。前人研究词学,多以写词为目的,对章法自然非常重视;而今世殊事异,研究词学未必写词,“当代词学界对词的章法似关注不够”[4]。五代词人李煜,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被人誉为“词中之帝”[5]。而李煜词之所以为李煜词,形成他独特的风格印记,也与其具有创新性的章法结构密不可分。然而,对于李煜词的章法研究,却还多停留在善用白描与对比上,且经常将语言风格的浅近、情感的自然同结构上的直接描写相混淆,罕见全面深入的剖析[6]。章法,其核心应为篇章的结构方式。“脱离开所有因素都服从结构因素,并被结构因素所变形的感觉,便不存在艺术事实。”[7]实际上,李煜词的语言和情感虽然真切自然,但其章法结构却颇见细密与多样。通过对全部李煜词脉络的把握和结构的归纳,穿透词藻与情感的“障眼法”,可以发现李煜词背后的章法言筌。而与前辈名家的比较,则能见出填词发展中艺术突破之所在。
一、李煜词的四种章法结构
李煜存词,依收录较多的《全唐五代词》(下文李煜词均据此),共计40首[8]。因为是考察章法,残缺不全者势必会严重影响篇章结构,故剔除失调名仅剩残句的2首和《谢新恩》中颇欠完整连贯的4首,余下34首,其中单调8首,双调26首。在这34首词中,李煜主要运用了四种篇章结构形式,笔者称之为:锁链结构、双层结构、点面结构、圆形结构。
1.锁链结构。李煜会在词中像直线一样使篇章意脉一贯到底,而其相邻句子间往往环环相扣,形如锁链。如《捣练子令》: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
先以两个短句写深院静、小庭空之环境,而接着便以砧声衬出院落之寂静,以风声衬出庭宇之空旷,紧扣前句。庭院的空静又暗示着诗人内心的空寂,遂引出下句孤寂无寐之人;且风、砧之断续,说明时间在不断推移而非静态,引出下句之夜长。倒数第二句的长夜无眠,点出时间在晚上,于是自然写到末句的月色。而砧杵意味着寒衣,寒衣寄送给远人,远人间阻山河之外,值此关山月色恰到帘栊,正与砧声叩至心头,叫人不能不辗转反侧,回应前一句之无奈。全词写主人公闻捣练之声,虽然仅有27字,但却是“匠心独运千锤百炼的成果,是不能轻易看过的”[9]。其匠心在章法上即表现为:无一字不与前后邻句发生关联,经过精挑细选的意象次第有序而出,在总势上呈一条直线,在单句间则一环接一环,终使情绪愈积愈深达到顶点。
这种锁链式结构,常用在李煜词的单调中,一些打破上下片的双调,如《一斛珠》(晓妆初过)也会使用。该结构便于集中一个核心意象,一气贯注。因为总的意思仍是一层,若是篇幅较长,则势必容易显得重复累赘,故在短章中更易于出彩。该方式很像修辞中的蝉联,但蝉联有显豁的字词,主要依靠外在的语词。而锁链结构则是依靠前后句意象的相关性,是内在的组织方式,虽不绝对排斥重复的语词,侧重点却大不一样。
2.双层结构。全词分为上下篇幅大致等量的两部分,每部分各有一个不同的核心意象或叙述逻辑,相互区别对立。这里的对立不一定是对比,而是矛盾对立统一的对立。唐圭璋先生总结的“有上景下情者,有上情下景者;有上今下昔者,有上昔下今者;有上外下内者,有上去下来者,有上昼下夜者,有上问下答者,有上虚下实者……上下相反者”[3]857,这十种上下关系,究其实质,都是上下侧重不同而又有内在对应关系的两部分。笔者即以矛盾的对立统一来概括,称为双层结构。李煜词使用双层章法的词作众多,以一片写景一片写情的最为明显,像他的几首《乌夜啼》,都是前景后情型的。下面这首名作就堪称典型: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上片写清秋人困深院的寂寥景象。后半夜无眠的主人公独上西楼,望着如钩残月意下凄凄,无言人对无言树,同困此寂寞深院。下片直言萦绕心头的愁情。愁绪萦怀,登楼欲遣却剪理无方不能去怀,况味万端难以名状。既是情景相对立,又是内外相烘托。
这种词家惯技读者往往一看便知,特别值得格外留意的,是一些双层结构隐藏在暗处的作品,比如《清平乐》: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像《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尽管也用情景交融的手法,但上下片的侧重还是很明显的。而这首《清平乐》,真是达到了“一切景语皆情语”[10]230的境界,上下片无一句不是以景来言情,乍一看没有什么对立之处。但实际上,上片有一个象征时间的核心意象落花,并以时间逻辑来组织句子,寄寓的主要情绪是伤春;下片有一个象征空间的核心意象春草,并以空间逻辑来展开,寄寓的主要情绪是伤别。当然,伤春归根到底由别离而起,这又是对立的统一之处。与此词类似的还有《浪淘沙》(往事只堪哀),该词同样情景交融不易区分,实则上片写日间的境况,下片则转而写入夜之境。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10]211,是贵曲不贵直的。双层结构适应词体的要求,使层次化单为双,增加转折。这里的双,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大致两分,文字量的均衡固然也促成了篇章对峙之势,但更重要的是用以表达意象的语词组织逻辑的两样。文字量之均衡,只需要从中一个逗点,人人皆会,而组织方式的和而不同,则非李煜这样的大词人不能精善。
3.点面结构。李煜善于使篇章在点面之间伸缩,在微观与宏观间形成张力,是为点面结构。比如他的两首《渔父》:
阆苑有情千里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快活如侬有几人。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轮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盈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两首词都屡屡用“一”示小,用“千里”“满”“盈”“万顷”示大,前一首是由大至小,而后一首则由小至大,仿佛摄影镜头之伸缩,在大小之间,在全景与特写之间,展现富有对比张力的留白空间。一山纵使千仞万里,也总归有固定的高度宽度,而中国山水画则常在半山间萦绕云雾,使得山势化实为虚,山上山下莫测其高。又设以流水幽邃,使山前山后莫测其深。如此一来,则全山之高远皆在尺幅之外,与山间的任意一树、一人或是一屋可以形成无穷大的对比。正所谓“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派,则远矣。山因藏其腰则高,水因断其湾则远”[11]。这两首词亦为同一机杼,恰是这种自由伸缩的广阔空间,这种在“大”中可以随意安置的“小”,在“小”中又能够收获纵览的“大”,给了我们渔父足以优游的闲适之感。点面结构与简单的上大下小或上小下大不同,不强求篇幅的均衡,如《浣溪沙》: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 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
红日已高仍添香,可知殿中歌舞自夜达旦后尚不消歇,又细致刻画舞者疾步而渐渐沉醉的姿态,前五句都是纵向深入写一殿一佳人,属于缩;末句点染别殿,横向宕开,显现众殿众佳人歌舞升平之状,“写足处处繁华景象”[12]31,属于放。篇章上,五句之缩就因一句之放,气息顿舒,唯呈富贵裕余之气,而免刻镂之讥。
点面结构的关键,在收放自如的张力,使阔大之境能收束,使集中之点能发散。李煜词中《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是突出的例子,上片写四十年、三千里之广远,下片强烈浓缩到辞庙之一旦,极缩放之能事,约束篇章劲力非常。
4.圆形结构。李煜词还有一种常用的圆形结构,如常山之蛇,往而复返,首尾呼应。在本文列入考察的34首李煜词中,计算每首词的句数,最多的一种体式,是全词共8句,上下片各4句者,占14首;其次是全词10句,上下各5句者,占8首。8句之词,无一例外可以2句作1组,视为4组。10句之词,如《一斛珠》《喜迁莺》《蝶恋花》《浪淘沙》等调,如果将各片中唯一不叶韵的短句与邻句合并看待,也可以形成4组。对这类词,李煜惯用ABBA状如圆环的组织结构。其典型,是他的两首《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风回小院庭芜绿。柳眼春相续。凭阑半日独无言。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 笙歌未散尊前在。池面冰初解。烛明香暗画楼深。满鬓清霜残雪思难任。
前一首作为李词代表作,历来论者较多关注名句、关注本事之语,而较少注意其章法。俞平伯先生谈到了其上阕的锁链式结构,“就章法言之,三与一,四与二,隔句相承也;一二与三四,情境互发也”[13]31,可谓ABBA结构中的A到B。唐圭璋先生提到“下片承上,从故国月明想入”[12]43,指的是此际的明月照见故国的雕栏玉砌,回首却朱颜已改,江山易主,同是一轮明月,沟通今与昔、此地与故宫,结构上也沟通了上下片,可谓从B到B的一环。及至末尾的问答,恰如带钩扣住了开头的两问,时间有多少、往事有多少,愁就有多少,此愁如春水、春花,无时能了。这层回应,正是回到开头之A的一环。从前学者论本词的艺术手法,往往喜欢强调无处不在的今昔对比,评说此词的意象选择,但从篇章组织的角度来看,实为一个首尾呼应的圆形结构,而不是平列的双层结构。后一首词没有名句故实炫人耳目,反而容易看清章法。开篇写春回,因似当年而转入回忆,这是由今到昔;下片由回想转到衰朽的现实,这是自昔到今;春色能重回而满鬓霜雪年华难回,这又照应了开头,依然是ABBA的结构。唐圭璋先生说《菩萨蛮》(人生愁恨何能免),“上言梦似真,下言真似梦也”[12]41,从结构上谈同样是这种类型。较之双层结构的照应式上下联系,圆形结构能进一步强化词的内在呼应,整体性更加突出。
二、章法结构的综合应用
这四种结构并不是相互壁垒、绝对孤立的,而是既有单用,又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合用的情况。在四者中,锁链结构和双层结构,因其与词调的片数及其中隐含的音乐因素的相关性,可以视为两种基本结构。词的一片对应乐曲的一遍,一遍之中的旋律总要保持整体性,势必使得该节中的文辞也要呈现一定的整体性,故单调以及双调中的单独一片,多呈锁链结构。过片之后,乐曲进入另一遍,故双调多用双层结构。34首李煜词的章法结构使用情况,可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8首单调中有4首使用了锁链结构,26首双调中则有19首使用了双层结构,分别达到50%和73%,这种锁链结构与单调、双层结构与双调的高度正相关性,印证了二者为基本结构。同时,因为李煜存词大部分为双调,所以双层结构也最多。另有4首单调用到了点面结构,也占到一半,可见,李煜试图以此扩展短小单调中原本较为局促的词境空间。而圆形结构则需要足够的篇幅来腾挪,否则如果词意尚未展开便已回缩,很难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所以使用圆形结构的这5首,李煜全是用在双调中,单调则较少使用。

表1
此外,点面结构与圆形结构,李煜多以复合使用的方式与前两者相结合。有5首词综合运用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结构方式,可称为复合式结构。例如这首《菩萨蛮》,最能反映这种复合式结构:
蓬莱院闭天台女。画堂昼寝人无语。抛枕翠云光。绣衣闻异香。 潜来珠锁动。惊觉银屏梦。脸慢笑盈盈。相看无限情。
从基本结构看,上片写女子睡时的静态;下片写醒时由静到动的变化,从这一点来说是双层结构。但全词从临院到升堂以至入室,再逐步推进具体到帘帷银屏之间,最终聚焦于女主人公的面容乃至眼眸,从远到近,步步深入,完全遵循时空顺序平稳推移。从这一点来说,既是线性的锁链结构,又如匀速推近的缩放镜头。这种章句间对节奏的精妙把握,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上下片的对立感。这种章法的停匀,可以折射出作为视角的男主人公探寻脚步的停匀。探访钟爱的女子,心情自然是有些急切的,但因为伊人昼寝,故而轻手轻脚匀步潜来,怜惜之情仅仅通过章法的节奏就表现出来了,流露出无限深情。此词就内容上言,不过是男女情爱,但就章法上来说,却能三种主要结构合一而用,堪称复合结构的典范之作。
三、篇章意义下的词、句使用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1]570,这是文章生成的历时顺序,篇章是最后的结果。“词积字成句,则字法与句法有关。积句成章,则句法与章法有关。”[14]若是反过来,从经过谋篇布局最终定型的文章来看,只有部分词、句能在全文的章法之中有着超出一般的结构性作用,这些词、句之所在,往往是章法的关节之所在。
1.在字词方面,李煜善于在过片换头之处使用能自然联系上下文的词。张炎在《词源·制曲》里说:“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须要承上接下。”[15]过片是结构的关键处,转而不断,最见功力。《乌夜啼》(昨夜雨兼风)的上片回忆昨夜失眠之状,在其末尾,李煜下了“不能平”三字,不平则鸣,遂启整个下片由此而发的感慨。在《长相思》(云一緺)中,上片全用侧笔写佳人的衣着容貌,几乎都是静态的审美勾勒,而过片只以一个“颦”字微动,引起感情色彩,使整个下片的环境描写尽染愁思,终篇之“奈何”亦有着落,下笔至简,结构作用却至大,大有“一波才动万波随”[16]之势。又如上文提到的《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中的“随步皱”,表面仅是修饰红锦地毯,而地毯之皱是因“步”,由“步”则而带出舞步之人,于是下片能就势写出舞者。
这些字词,都是技法纯熟、经过锤炼的结果。但它们乍一看并不那么特立突出,不像陆辅之《词旨》里的“词眼二十六则,示人炼字之法”[17],是为了一字一句的警动出彩。这正是李煜的高明之处。因为它们是整个篇章联系的枢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字词越不突兀,章法转折越自然,越能化去结构的斧凿痕迹。词家有“潜气内转”之论,况周颐说“作词须知‘暗’字诀。凡暗转、暗接、暗提、暗顿,必须有大气真力,斡运其间”[18],即是推崇这种结构的暗中变化之妙。
2.在句子方面,李煜则有两样妙用,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功能。首先,是问句的使用。常言道,有问有答。在词中使用问句,于读者的期待视野里必然要求答案,作者无论正面作答、反面作答乃至实际上不作回答,都能自然唤起下文。所以何均地先生论《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的下阕便说:“冠以‘几时’,形成问句,就章法来说是轻顿,为结句蓄势。”[19]75蔡厚示先生则称《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是“自问自答,一层深似一层”[19]88,也指出使用问句对结构层次的帮助。问句更有妙者,如《玉楼春》: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春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照烛花红,待放马蹄清夜月。
此词上片写歌舞的嫔娥,下片写赏玩的男主人公,本是上下两层的对立关系。词中换头处这一问,实际没有给出回答。然而只要一问,就产生了主客关系,问的主体是观者,客体是舞者,虽不回答,却将上下阕统一在了一起,实在是章法上的妙问。若改成“临春佳丽飘香屑”,便纯剩客体,全词断成两截,意味大减了。
其次,是对句子界限的突破。古人云:“言之不足,故长言之。”在律诗中,句子最长不过七字,有时情感深长一气而下,七个字尚不够抒泻,诗人就会采用流水对等形式打破句限。词作为专主抒情的文体,加之李后主一往而深的情感,寥寥数字时常不足表达情感,故后主颇善长句。他传词不多,但其中《虞美人》《乌夜啼》有好几首都是词中少有的使用九字句的词调。有一些点校者,试图在这些九字句中添一个顿点,变成二七、四五或者六三的形式。而焦循则认为,词“长至九字十字,长须不可界断”[20]。至少对李词来说确是如此,点断大可不必。将这些句子全列出来就能清楚地看到,李词的九字句没有统一的停顿点,他的本来意图,就是要一气呵成。故而俞平伯称赏“‘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长句一气直下”,与春水“之姿态韵味融成一片,外体物情,内抒心象,谓之入神可也”[13]34。
有时九个字都不足以抒泻后主的郁积之情了,而拥有十字句的《夜半乐》《摸鱼儿》等慢词长调不但数量极少且尚未流行,李煜就突破单句的长度限制。他常常把一句词的主语或者说内容中的行为主体放在前一句,抑或是把一句词的宾语或者说作用对象放到下一句,从而突破句读之限,使上下句成为一体。“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可视作主语的离恨或春草都在前句,谓语部分在后句。又如“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从小结构说,中心语“殿影”在前句,谓语部分“照秦淮”在后句;从整个句子结构来说,主语抒情主人公被省略,谓语“想得”在前一句,余下的宾语部分则被拆成两段,分列在前后句。李词突破句限的顶峰,是《采桑子》的上片:“亭前春逐红英尽,舞态徘徊。细雨霏微。不放双眉时暂开。”“不放眉开”的主体,是整个前三句所描绘的残春景象,跨越四句、三韵,沟通整片,章法高超。
在这种突破中,虚字常常起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唐圭璋先生说虚字“在句首作领字者,往往直贯到底,神韵尤胜”[3]842,随即举了《望江南》(多少恨)为例,盛赞“还似”二字领起,贯通了三句余下的十七字。上一段提到的“想得”,又如“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的“无奈”,“可奈情怀,欲睡朦胧入梦来”的“可奈”,都有这种作用。
四、李煜词章法的发展创新
在李煜之前,最具有典范意义的词家是温庭筠和韦庄。在语言风格上是如此,在章法上也是如此。王国维论三家的词作说:“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10]356谈句,谈骨,都还有迹可求,较易捉摸;谈神,则大有“羚羊挂角,无迹可求”[21]的味道。神是以人的精神面貌作比方,神秀不是一眉一眼、一手一足的漂亮,而是整个人精神气质的秀丽,这必然要求一个人举手投足间的协调。李煜词之所以神秀,是他的作品达到了浑成的境界。得意忘言,得鱼忘筌,虽忘却并非没有过言筌。同样的,李词之浑成,与他的遣词造句,与他章法的和谐统一是密不可分的。把篇章的统一放在第一位,其章法的创新性即在于此。
在章法技巧的发展过程中,温庭筠词于结构方面最为疏离,句子间缺乏虚字的勾勒。“温词大抵用实字写实景实物,构成境界,表达情意,正因为他不用虚字划清脉络,所以就显得深隐含蓄,不易理解。”[22]30温词的意象间不能说没有联系,但大多是在各句间独立而斩绝的,仿佛砌墙只排列的砖块而没有水泥,缺乏足够的沟通。“飞卿之词,每截取可以调和的诸印象而杂置一处,听其自然融合。”[13]14这如同电影里的蒙太奇,将不同画面直接并峙呈现在观众面前。如果画面间的关系较为显豁,观众自然容易理解,且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但如果画面间的关系隐晦,或者根本缺乏足够的逻辑严密性,就会适得其反,堆叠过度而不协调。如这首《诉衷情》:
莺语。花舞。春昼午。雨霏微。金带枕。宫锦。凤皇帷。柳弱燕交飞。依依。辽阳音信稀。梦中归。[8]121
整首词完全是实景的叠加,生生把这许多意象直截地抛到了读者眼前,竟无一个虚字为读者稍稍指出意象间的关系。此即“有些作品,骤然看来,只是一些人物形象和自然风景的罗列”[23]268。意象群虽也按顺序依次有四层,第一层室外春景,第二层室内闺房,第三层燕子成双,第四层征人不归,但作者既不明确划出层次,也不讲出四层意象间的关系。而词中女主人公见到昔日同欢的带枕锦被、当下成双的凤凰燕子,自己却在美好青春里寂寞独处的一切心理活动,全都需要读者自己去补足。接受美学将之称为“作为一种潜在联结的空白”,源自文学文本的“不确定性”[24],并认为读者在阅读中将其补足才能使文本完整。这一结构方式利弊并存,它“要求读者有一定的思想、道德、文化等方面的修养,有一定的接受能力和审美水平”[25],欣赏合意的读者会觉得是深隐含蓄,而不适应的读者就难以理解作品的深意了。
相形之下,韦庄词的结构就要紧密得多。“在篇章结构方面,则由于不一味刻画实景实物,不用大量词藻堆砌,词意连贯、上下一气,所以显得脉络分明,层次清楚,这就是他的词被称为‘骨秀’的缘由。”[22]30正如詹安泰先生所言:“较多用灵活的联系字。”[23]273如“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8]153,使用顶真串联;又如“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8]154,以如今、当时这样明白直露的对照之词沟通句子。韦庄《思帝乡》之起头之句“云髻坠,凤钗垂。髻坠钗垂无力”[8]167,与李煜的《捣练子》“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非常相似,同样是将前两个三字短句的意象连贯揉进到第三个长句中,但韦词中的“髻、钗”非常显豁以至有重复啰嗦之嫌,李煜则变为以不同侧面来叙述“静、空”,改进得自然圆转,意脉不断又不重复。韦庄这样组织篇章,自然少了温庭筠之词有时流入晦涩的不足,但“还乡”“髻钗”“如今”“当时”这些起关联性作用的词语,如人的骨架筋节,极为明显。章法技巧表露无疑,如同有扎眼水泥缝的墙。
词至李煜,一方面很好地将大部分起结构功能的词句隐藏起来,另一方面主要通过意象高度的内在逻辑联系相关合。在篇章层面,锁链结构的意象环环相扣,双层结构的上下对照,点面结构的张力,圆形结构的首尾呼应,都使得全词笼罩在一个整体之中。特别是圆形结构、复合结构的使用,在温韦词中很难看到。究其实质,是在一首词里同时用几种逻辑组织语言,既有经线,又有纬线,使全词成一严密的整体。在句子层面,现存温韦词里,最长的句子是7字句,而李煜达到9字句,语词的贯穿度更长;加之上文提到的对问句的使用,以及对句子界限的突破,都使得上下文的整体性大大加强。在字词层面,除了少量领字较易看出之外,李煜多用意象的深度关联暗中转换。他精心选取了一些易于联想的物象,表面仍是写物,实际却有影射,呼应了上下文,此即“寓比于赋的手法”[19]90。以上种种章法技巧的综合应用,超越了温韦等人的结构组织模式,最终实现“潜气内转”,消弭了墙上的水泥缝。
“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10]342王国维此语,从根本上道出了李煜词与温韦词的章法差异。王兆鹏先生说“‘花间范式’则是剪辑不同时空的意象叠合在一起”[26],从温到韦到李煜,已经显出叠、缝、织的差别。故而况周颐就认为,李煜词“无上上乘,一字一珠,勿庸选择”[27],不能以字句摘取,而全篇精胜。李煜词融汇锁链结构、双层结构、点面结构和圆形结构四种篇章组织方式,加之以字句上的研磨,使篇章的流畅顺应情感的真挚流露,达到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从这一点来说,词中之帝治国无方,但治词实在井井有条,章法齐备,足以“南面王”。